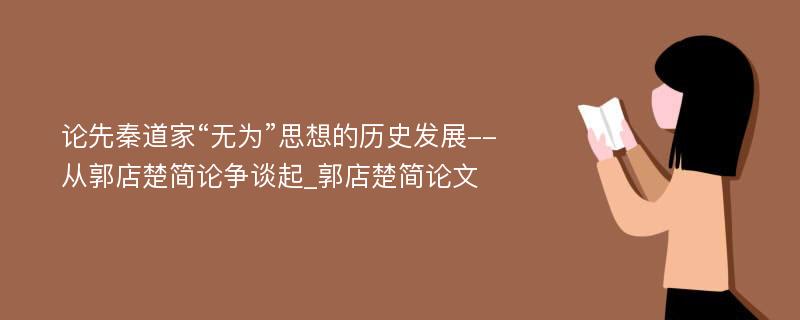
试论先秦道家“无为”思想的历史发展——从关于郭店楚简的一个争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道家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11-0084-06
一、问题的提出
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第13号简有“道恒亡为”说法,将“亡(无)为”定为“道”的最基本最常见的特质。由此可见,“无为”与老子哲学的“道”论关系极为密切,是老子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前辈学者对于老子的“无为”观作过许多研究,意见基本一致,多将老子的“无为”视为一种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如将老子的“无为”视为“不抵抗主义”,或将“无为”视为一种“君道,是“君人南面之术”。专家认为,传世本第48章“无为而无不为”表明了老子认为只要坚持“无为”的原则,那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所以老子的“无为”理论除了与世无争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积极进取的“无不为”思想。
自帛书和楚简《老子》出土问世以后,学者们对于老子“无为”观的理解出现了不少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子“无为”观中是否包括了积极进取的“无不为”的思想呢?
专家或将“无不为”的思想完全排除在老子思想之外,例如高明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通过帛书甲乙本之全面勘校,得知《龙子》原本只讲‘无为’,或曰‘无为而无以为’,从未讲过‘无为而无不为’”。高先生还将帛书乙本“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的说法与《韩非子·解老》做比较研究,进一步指出《老子》原来的思想是“无为而无以为”,后世传抄时才误作“无为而无不为”(注: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5页。按,原文残“无为而无以为”六字,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第55页据严遵《道德真经指归》本拟补。按,高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严遵《道德真经指归》卷3《为学日益篇》所引者确乎是“损之又损之,至于无为而无以为”,严遵释其意谓“损之损之,使知不起。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因存亡之机。不为事主,不为知师。寂若无人,至于无为”(《道德真经指归》卷3),严氏所见本《老子》此句作“无为而无以为”,确乎无疑。若采用“以老证老”的做法,联系到《老子》书其它的关于“无为无以为”的记载,更足资这个问题的旁证。)。高明先生据帛书而做出的推断应当说是有说服力的。
然而,郭店楚简出土之后,《老子》是否讲过“无为而无不为”的问题,重被提及。郭店楚简《老子》乙本载:“学者日益,为道者日员(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既然有“亡为而亡不为”之说,那么断定《老子》从未讲过“无为而无不为”,自然就有了可以商讨的余地。《庄子·知北游》篇曾经引用过“无为而无不为”之说,高明先生认为《庄子》之文有误。裘锡圭先生则据郭店楚简认为高明先生的说法“恐难成立”(注: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廖名春先生指出:“今本《老子》第四十八章的‘无为而无不为’说肯定是《老子》原本之旧,否定老子有‘无为而无不为’之说,不论从楚简本《老子》看,还是从帛书甲乙本、严遵《指归》本、《老子》一书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看,都是不能成立的”(注:廖名春:《〈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说新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裘、廖两先生的这个批评,应当说也是有根据的,并非无根之谈。
如何看待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呢?愚认为现在可以补充的看法是,似乎可以换一个思路进行考虑,即《老子》帛书乙本的“无以为”与郭店楚简的“亡(无)不为”是否可以并存于《老子》一书呢?是否可以做出另一种推测,即实际情况可能是《老子》书中既有“无为而无不为”之论,也有“无为而无以为”之说,两者并存,而非必有一误。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一个前提是,确如高明先生所说,“无以为”和“无不为”两个说法的意义“迥别”。如果可以肯定两说并存,那么意义相悖的说法并存于一书的现象如何解释呢?是不是《老子》书中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呢?这是我们所应探讨的问题的关键。
二、老子“道”论的逻辑发展必然导致“无以为”
要解决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十分明显的矛盾,愚以为应当从老子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缕析。郭店楚简的面世为道家“无以为”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确切的证据,传世本的材料与竹简本可以相互印证。传世《老子》王弼本第38章载: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必须注意的是,郭店楚简《老子》乙本和甲本皆有与之相应的文字,确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其它文字亦与王弼本相同。可以看出,“无以为”的思想在战国后期道家学派中应当是存在的。这个存在并非偶然,而是道家哲学发展的结果。作为老子哲学集中体现的“道”论,是围绕着本体论展开的。老子认为,超越人类认识、甚至超越人类语言的世界本原,本来是不可言说的,如果非要说的话,可以勉强称之为“道”。“道”存在于人类认识之外,“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注:王弼本《老子》第14章。)。基于这个认识,老子才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注:所谓“为学日益”,郭店楚简乙本《老子》作“学者日益”,虽文字稍异,但意义却同。或谓“为学钻研学问”,似非。河上公注谓“‘学’,谓政教、礼教之学也;‘日益’者,情欲饰文日益多”;而“为道日损”,意指通过钻研自然之道而使“情欲文饰日以消损”。如此看来,老子不赞成政教礼乐之学,而是提倡“为道”,即贯彻其道论思想的。)。老子的“道”论在认识世界方面有自己的独特系统,在指导人们的行动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路。依照其思路,从“道”出发,由此引伸展开,必然导向“无为”,此即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就是老子理论对于人们行动的启示。
现在必须讨论的问题,老子究竟是要将“无为”引向“无以为”,抑或是“无不为”呢?愚以为答案应在前者,即必然导向“无以为”。理由如下:
第一,老子认为自然是不可违拗的,人在自然天地间必须持顺应的态度,所以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尚弗能久,有(又)兄(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注:帛书《老子》乙本。)。谁来支配着“飘风”、“暴雨”等自然现象的运行呢?那就是“道”,跟“道”相比,天地尚算不长久,尚且无足挂齿,更何况人呢?既然不可违拗,那就必须顺从自然而“无为”。而自然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也就不需要考虑自然的运行了。
第二,人在自然面前不仅不要有为,而且不要考虑如何去“无为”,那么,人在“道”的面前应当怎样做呢?王弼注谓“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居,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所谓“与道同体”,即将个人融入于道,消失在道之中,如此说来,人就完全不需要有什么“为”的考虑,这也就是“无以为”的意思。韩非子在《解老》篇中用“贵虚”来解释无为之意,认为“无为”就是“其意无所制”,亦即不仅不去“为”,而且不思虑去“为”。如果总是考虑着“无为”之意,那便是“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也就算不得真正的“无为”,韩非子和王弼对于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解深得其旨,是正确的。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第1号简所云“绝知弃辩”、“绝伪弃虑”,保存了老子“无以为”原意的本义,而后来的传世本则改作“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与老子原意已有较大距离。
第三,老子提倡“赤子”的境界,谓“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第55章),赤子即婴儿,处于无思虑的状态,所以人们应当“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28章),并且反问:“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拿婴儿为比喻,可以说赤子的境界是最为符合“无为无思”(《韩非子·解老》语)、不需要“有为”这一原则的。
总之,老子自然哲学虽然蕴含着无尽的内容,但其核心部分则是顺应自然,是“无为”。要做到真正的“无为”,必须根本不去考虑它,根本不想怎样做到“无为”的问题。显然,这种无为观即包含着“无以为”的思想。后世阐发“无以为”之论者以王夫之最为突出,他说“周子曰:‘诚,无为’。无为者,诚也,诚者无不善也,故孟子以谓性善也。诚者无为也,无为而足以成,成于几也。几,善恶也,故孔子以谓可移也”。又谓“神者无为也,形之未形,体之未体之者也”(注:王夫之:《尚书引义》卷3,《船山全书》第2卷,岳麓书社1988年版。)。按照这个理解,“无为”当即“无以为”之义,即不欲有所作为。“无为”之义其根本在于没有目的出现在人的头脑之中,如果出现,那就是“有为”,而非“无以为”了。总而言之,老子“道”论必然导致“无以为”的结论(注:关于“无以为”的意思,专家或谓“以”宇犹“所”,“无以为”即“无所为”。是说似可商。此处的“以”字当用如动词,意指思虑、谋划等行动。“无以为”意即不要谋划、考虑有所作为。按照老子的观念,如果有所考虑、谋划,那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无为”,所以说“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后来出现了“无不为”的说法。那是老子“道”论(特别是其“无为”观念)发生变化的缘故,并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初衷。
三、从“无争”之论看老子“无为”思想的转变
一般认为,可以将老子思想的形成概括为《史记·老子列传》所提到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个阶段(注:清儒所提出的先秦子书多非自著的观点受到当代专家普遍拥护。以此观点分析《老子》一书亦当如是。专家多谓它写成非于一时,写定亦非一人之手,此类论析是有道理的。关于《老子》的成书问题的研讨,烦请参阅拙稿《论老子哲学的历史发展》(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兹不赘述。)。据此而言,《老子》书中的“无为”之论,与崇尚自然接近者应属老聃、老莱子,与圣人治国接近者则属太史儋。这里可以顺便提及的是老子哲学基本思路应当是自然无为的出世哲学,但《老子》书却有相当部分是积极入世的论析横艮其间,显得不协调不融汇,我们明白了老子思想的历史发展,这个矛盾之处就容易认识了。
要了解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无争”的观念入手进行探讨。就一般的概念而言,“争”就是“有为”的表现,而“不争”则与“无为”接近。“争”或“不争”的问题可以折射出老子“无为”思想变化的轨迹。
在老子的思想中,“无为”应当是完全顺应自然的无为,而到了太史儋的时代则转化为积极有为的思想。因此,“争”或“不争”,就与“有为”或“无为”直接相关了。关于“不争”的思想在帛书乙本中是这样表达的:
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亓(其)言下之;亓(其)欲先民也,必以亓(其)身后之。不以亓(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
此处意谓圣人要想成为民的统治者,必定要先谦虚卑下,要想在民之前成为领导,必须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民众之后。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意是相近的。其意蕴完全肯定圣人不是不争,只是争得巧妙而已。“天下莫能与之争”则强烈地表现了积极有为的思想(注: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49页。“不以其无争与”之句,帛甲本作“非以其无争与”,意义一致。高明先生认为帛甲、乙本此句“保存了《老子》原义,今本凡作‘不以其争’,或‘以其不争’者,皆由后人所改,旧注皆不可信”。按,此说可疑,论者或有驳论。《老子》原义并非如此,观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相关记载可知。)。
在写作时代上肯定比帛书本早了许多的郭店楚简《老子》甲本(注:郭店楚简本和帛书本《老子》的抄写时代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郭店楚墓下葬的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前后,随葬的《老子》抄本的写成年代肯定在此之前。而帛书本《老子》出土于汉墓,甲本《老子》无避讳,而乙本则避“邦”字讳,所以推测甲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前,而乙本则在其后,是有根据的说法。关于两者内容的形成与编定时间,专家一般认为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内容则带有战国秦汉时代社会影响的标识,尽管它也是流传至汉代的古本,但是其内容的形成应当是比较晚的。),也载有与“争”或是“不争”相关的内容:
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我们可以推测,老子最初的思想是在强调“不争”——真正的完全的不争,彻头彻尾的不争,而不是心里想着“争”而嘴上说“不争”。只有持这种态度的“圣人”,民众才会真心拥戴他,乐于助其成功而不厌烦。《淮南子·道应训》解释“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谓“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其说与老子的“不争”之论是一致的。总之,“不争”的意蕴就是完全顺应自然。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与帛书《老子》乙本的区别,反映了老子关于“不争”理论的变化。
到了充满激烈竞争的战国中期,这种完全顺应自然而“不争”的理论就显然大不合时宜。可以推测,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道家学派才将“以其不争”,改为帛书《老子》乙本的“不以其无争与”,加上一个“不”字,直接将“以其不争”否定,而转换为完全相反的意义。帛书甲、乙本以及今传本此句所表达的意思有浓厚的权术色彩。其本质的、最终的目的在于“上民”、“先民”。尽管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但却要表现出相反的样子来给人看,说出相反的话来给别人听,以求取得“天下莫能与争”的结果,如果否定这与君王南面之术无关,恐怕很难讲通。郭店楚简甲本《老子》的“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说明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因为不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帛书乙本《老子》的“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所表达出来的是承继关系,意谓由于圣人争得巧妙(而不是“不争”),所以天下莫与之争。开始是不争,后来变为“争”,并且天下任何人都争不过他。
“争”或“不争”,“为”或“不无”,这两者的逻辑关系是一致的。“争”也就是“为”,“不争”就是“不为”,亦即“无为”。《老子》理论中关于“争”的思想的这种转变与其“无为”思想的转变走着同一条道路。
战国后期,道家思想的一大发展就是由“清静无为”发展为“无为而无不为”。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证。一是《庄子》外篇的《知北游》(注:关于《庄子》一书的形成,这里取专家们一般的看法,即“内篇”为庄子自著,而“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著。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在“内篇”中掺杂有庄子后学的某些论述,而“外篇”“杂篇”中也有后学所述的庄子理论。就总的情况看,可以说“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对庄子理论的发挥和发展。),是篇论黄帝之道时所言“不言之教”时说: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
此处所引“故曰”之后的内容见于今传王弼本《老子》第38章和第48章,可以推测庄子后学所见《老子》已有明确的“无不为”之说。《庄子·则阳》篇谓“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亦可证庄子后学确实已持“无不为”之论,其直接来源便是对于老子“道”论的发挥,从“无私”的“道”引出“无不为”的结果。
断定战国后期《老子》思想中确已有“无不为”之论的第二个证据,见于《韩非子·解老》篇。是篇谓:
所以贵无为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所无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显然,这里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改动《解老》篇的原文,没有理由硬说原文的“无不为”是“无以为”之误。我们应当据此肯定韩非子所见《老子》书有“无不为”之论。韩非子赞成“无不为”之论,与他积极入世的进取态度密切相关。我们可以肯定,韩非子时代的《老子》书中已经明确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
四、道家“无为”思想的历史演变
如果将《老子》思想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的话,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似乎可以把郭店楚简《老子》的时间(即公元前300年前后)作为分界。我们可以推测,此前的《老子》思想主张“无为而无以为”,此后则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而更主张“无为而无不为”。郭店楚简《老子》则正处于这个转变的时期,所以只是郭店楚简《老子》乙本里有一处提到:“学者日益,为道者日员(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而在此以前的历史时期的《老子》思想里,则有多处提及“无为”。并且十分强调“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注:见王弼本《老子》第38章及帛书甲、乙本《老子》皆同。),实将“无为”与“无以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无以为”意即不考虑有所为,也不考虑没有作为。“无为而无以为”是递进地说明,不仅不去做,而且连考虑也不考虑去做,即根本没有“为”的思想存在。
本文开始所提及的学术界专家的两种判断,应当说都是有根据的,虽然相互矛盾,但却不是水火不容。“无以为”和“无不为”的说法并存于《老子》书中恰是老子思想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证明。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而分析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战国后期的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沿着道清静虚无的思路发展,进而讲“无以为”,进而至于“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直至真正的虚无。最后是连“无思”也不必考虑,因为如果想要去“无思”,那毕竟还是思考的结果,还是为一个目标去努力。庄子学派将“无以为”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谓“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注:《庄子·知北游》。)。所以真正的“无思”便是什么都不去想,让自己处于混沌的状态。这个思路与老子哲学中“道”无所不包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注:关于道无所不包的性质,在《老子》书中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如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51章);“道者万物之奥”(第62章),这是讲道为万物的根本。再如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4章),这是讲道永不衰竭的特性。《庄子·知北游》篇的作者强调“无不为”,正是基于对广大无际的支配万物的“道”的特性的理解。)。
正是由于“道”可以“无思”而存在,所以,庄子强调“自为”,即没有任何主观影响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庄子·齐物论》篇讲天籁的时候,谓“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认为自然所发出的千差万别的声音,乃是各种孔窍自己的状态所形成的,都是自取的结果,再没有什么外力来鼓动它们发出声音,而非外界影响的结果。不仅天籁如此,而且万事万物莫不尽然,故《庄子·天道》篇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正由于这种自为,所以《庄子·知北游》篇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庄子这种“自为”的思想是对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老子固然也讲自为的意思,如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但那毕竟有人我、物我的关系存在。庄子讲这个道理,则泯灭了一切界限,即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自为”状态。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中的《道法》篇亦有类似的说法,谓“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页。)。可以说,由老子的“无为”至战国后期道家的“自为”,其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与发展,这个转变的理论意义在于要从事物自身寻找出“为”的原因,替道家的“无以为”的理论,找出了根本依据。
道家“无为”理论的这一发展方向,顺应了战国后期思想界对于心学进行探求的潮流,与儒家思孟学派的理论有些地方是不谋而合的。属于思孟学派遗篇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48号简云“凡人伪可恶也”(注:此简的“伪”字,其左原为竖心旁,其意指矫情、虚伪(见庞朴先生《郢燕书说》,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因为与伪字意近,故为方便计而迳写作“伪”。“为”字,在战国简帛文字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不加心旁者,类于今日作为介词或副词(表程度)的为,附加心旁者则表示思维活动,系动词或名词,《老子》书的“有以为”意思相近,其意义与“无以为”相对。按,《庄子·庚桑楚》篇是庄子学派中与老子学说比较接近的学者的作品。专家或断定它是“庄子早期作品”(见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说虽不误,但此篇列入《庄子》杂篇,可见前人并不认为它是庄子自著之篇。专家或认为它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谓其时代“当在晚周,即战国末期”(见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4页),此说较可信,今从之。),这与老子的“无以为”之说的涵意是相近的。
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在战国后期,道家思想不再强调绝对的“无为”,不再囿于“无为”的范围,而是强调一定条件下的“有为”,强调“不得已”而有所作为。《庄子·庚桑楚》篇谓: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注:严遵:《道德真经指归》卷1。)。
在老子哲学中,讲“无为之益”,讲“我无为而民自化”,讲“无为也故无败也”,讲“不争而善胜”。在“无为”的后面总是隐藏着“为”的实质,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成功,是天下大治,是胜利,是去小成而得大成。就人生态度而言,如果说前一个发展方向是“出世”道路的话,那么后一个则走着“入世”的道路。
道家的“无为”思想在庄子后学那里,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庚桑楚》篇谓:“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人的心灵(即“灵台”)是有所作为、有所操持的,只不过是没有自觉到自己有所操持而已。所以《庚桑楚》篇的作者主张“不可持”,成疏谓“若有心执者,则失之远矣,故不可也”,深得其旨。总之,这里强调有为、操持是必须的,只要不是有意地操持就行。西汉严遵释“无为”之意,谓“恬淡无为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于无极”,“天下咮咮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注:《盗跖》篇是庄子后学的重要资料,并非前人或谓的“伪作”。关于是篇所阐述的“无为”思想,拙稿《从〈盗跖〉篇看庄子后学的‘无为’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曾经有所探讨,烦请参阅,不再赘述。这里仅简要说明与本文关系密切的一些内容。)。此说将道家的“无为”思想转化为“无不为”之意表达得十分明晰,意即只要“灵台”——即心灵——无所执持和期待,那么个人的理想就会充满无极的玄域,就会感化和改变天下,“无为”由此也进入到了“无不为”的最高境界。
然而,细绎这个认识却可以发现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有为”和“有持”,总是人的主动自觉行动,如果没有自觉,怎么能够去“有为”和“有持”呢?因此《庄子·庚桑楚》篇所谓“不知其所持”,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淮南子·道应训》解释老子“无为”思想时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此正说明“无为”思想的核心是“不先物为”“不易自然”,由此而可以引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应当是:如果已经有了“物为”、有了“自然”之为,那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要有“为”的。战国秦汉间的道家认为这才是“无为”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再理会“无以为”的问题了。
五、庄子后学的自然观及其对于“无为”理论的贡献
道家“无为”理论,其基点在于强调人不应当刻意追求,甚至连想都不要想,而应当让一切都随顺自然。这在老子早期的理论中称为“无以为”。老子后期的哲学思想适应了社会形势需要,于“无为”理论中加上了积极进取的内容,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将随顺自然的命题加以改变,变为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庄子·盗跖》篇极具张扬活力的批判精神,就十分典型地表现了道家学派的这种新理念(注:《庄子·盗跖》成疏。)。庄子后学从多个角度说明各种身份的人们在“无为”原则面前是平等的,并没有所谓的“君子”与“小人”、“圣人”与“俗人”等区别。《盗跖》篇十分深刻地改造了道家“无以为”的理论。它认为人人都有理由自然而诗意地生活在社会之中,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抗争,因此:
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
这里是说,人们在社会上的拼争,甚至到处争(“争四处”),如盗跖之横行天下,原因在于不足,所以说都是合理的行为,而不算是“贪”。反过来说,放弃权力,甚至将天下君位让给别人,那也只是一种自然,也不要自为是“廉”。这些都是“反监之度”,即“反照于内心,各禀度量不同”(注:《庄子·盗跖》。按,这里的“动”字,前人有释其意为“举动”、“动用”者,或用为使动用法。愚以为此处释为“举动”较妥。)结果。这里所提到的“无以为”,其理念已经与老子有了很大的区别,其理念的核心是鼓励人们去拼争,去求取。这种思想是为新的社会形势下人的发展和理想的实现寻求路径。《盗跖》的内容表明,道家的“无为”理论,已经成为当时思想解放的一种理论依据,而不再具有“出世”的倾向。
战国后期,对于“无为”思想,知识界似乎已经有了共同认识,即断定“有为”即融于“无为”之中,所以《吕氏春秋·精谕》篇谓“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高注:“至德之人为乃无为。无为因天无为,天无为而万物成,乃有为也”。此论用于统治之术上,便是《吕氏春秋·君守》篇所谓“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亦即《吕氏春秋·任数》篇所谓“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无为”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政治艺术最高表现的代称。《吕氏春秋·乐成》篇谓:“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这里已将“无为”混同于“勿为”、“莫为”,但其意思则无改变。高注“夫唯贤主能无为耳。中庸之主不能无为,故不可与为无为也”,正道出其中的精义。
应当看到,道家“无为”理论实际上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按照“无为”的命题,必然要随顺自然、随心所欲。可是大千世界的千千万万人如果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社会必定出现混乱无序状态,还怎么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庄子后学提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知(智)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注:林疑独说。见储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篡微》卷96引。)。
这里所说的意思是,智慧者的举动和行为必须合乎一定的“度”,而这个“度”,前人或谓即指“心之法”(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3页。),当代专家则或释为“大众的原则”(24),都是正确的解释。此句的中心意思是指出智慧者的举动应当以老百姓的意愿为转移,一定不要违背老百姓的原则界限(“度”)。《盗跖》篇作者所提出的这个原则,应当说是十分理智而可取的,已经回答了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问题。类似的意思已经见于老子后期的思想,传世本《老子》第49章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这里强调了体察民意,顺应民情。庄子后学则更进一步,要以百姓的意志为行动的标准。有了统一的标准,自然也就会避免社会上混乱状态的出现。
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可以说《老子》的“无为而无以为”的思想,为后来的庄子后学中的隐逸派所接受,成为战国秦汉时期隐士阶层的圭臬。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则不仅成为战国黄老学派的法宝,而且直接影响了韩非子法、术、势三者结合一体的法家理论的完成,成为道、法理论结合的一个理论切入点。就此而言,说老子此论对于秦统一天下也发挥着间接的作用,也并不过分。再以后,它则成为汉代黄老政治的指导思想。几乎是凡有道家理论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多多少少有着“无为”思想的影子。
总之,在战国秦汉之际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道家的“无为”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道家理论的活力和对于社会发展形势的适应。由老子早期理论的“无以为”,变化为其后期理论的“无不为”,这是道家学派理论的一个飞跃,而在庄子后学那里,“无以为”的理论被重新诠释; “无不为”的理论还得到了补充。西汉初期,道家理论一跃而成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从政治上说,当然是矫正秦王朝暴政的需要;从哲学思想的发展上说,这也是道家“无为”理论深化与发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