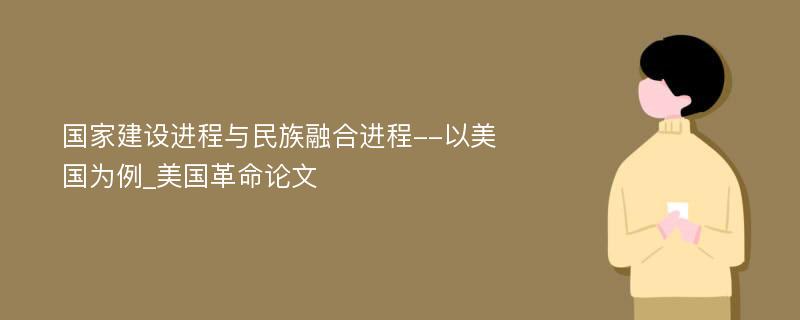
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国族的整合历程——基于美国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历程论文,过程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国家的真正目的在于处理和解决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的局面这样一个政治整合的难题:“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现代国家的建立,总是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而围绕着这个新秩序的架构,总是会发生一场基于利益驱动的政治讨论;这个讨论的结果不仅形塑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架构,而且也为现代国家的存续提供了理据。相对于封建国家而言,最早的现代国家萌生于欧洲,但美国的建立过程及其政治讨论在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不但是因为《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等历史文献在国家学说史上的地位,而且是因为这一建国历程对后世的现代国家建构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凸显特性与敌我辨识: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工具性价值 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的诉求,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富兰克林在1751年发表的《人类的增长》一文中,则以人口的增殖来论证北美独立的必然性。②但真正激发北美独立浪潮的契机,则缘于“美国的独立革命,肇端是受委屈的纳税人起而抗议”③:这种针对殖民母国的抗议背后,是迥异于英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口结构、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对北美殖民地特性的塑造,而这一基于特性的塑造和随之而来的建国,又引致了关于美利坚国族的形塑。不论是特性的打造还是国族的构建,都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大讨论不无关系。事实上,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总是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建构政治合法性的理据。 “(北美)殖民地时期民主运动的风暴中心,是殖民地总督与殖民地立法机关或议会之间的斗争。……这种冲突有助于发扬到处都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的民主精神。这是一个集合点,各种有利于独立和人民政府的倾向,都集合在它的周围”;而“殖民地实行自治的长期经验、殖民地远离英国以及如此遥远的基地成功施政的困难、殖民地利益与英国国家主义的冲突”,又使得北美殖民地“一有适当机会就可能表现为独立”。④托克维尔曾就此指出,“具有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民情和几乎相同的法律,并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因而可以说有强大的理由使他们彼此联合起来,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独立国家”。⑤ 纵观北美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学说可以发现,杰斐逊等人所揭示的那些旨在脱离殖民母国的政治理念,其实“没讲什么新东西。他所做的,是通过连续不断地反对宗教信仰不容异说原则,倡导自然权利、个人良心、公平税收等等熟知的观念”;⑥诚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北美独立革命的过程中,“经济利益、自由主义或者启蒙运动都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意识架构”,⑦而经由所谓“印刷资本主义”传播的、对殖民地与殖民母国之间敌我意识的建构和“美利坚国族”的想象,才是真正引致北美独立的“新的意识架构”。 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国家建构工具的思考,缘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目标指向的同一性,而这个具有同一性意义的特定地域及其最高合法性又来自于建筑其上的现代国家。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相关性而言,民族主义本身的诉求就要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⑧而在民族国家的时空背景之下,由于“各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领土意识形态形式,或者直接叫领土意识形态”,因此“真正激发民族主义的东西,是为建立、巩固、改革或拒绝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框架而进行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同国家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⑨日本政治学家猪口孝也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与主权国家的领域重合在一起。而且,当主权民族国家以这种民族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时,近代国家诞生了。民族主义以民族集团为基础,挖掘历史上共同具有的经历,利用一定的感情和象征加强忠诚心和凝聚性”。⑩ 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建构总是意味着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揖别,这种揖别在很多时候总是借助民族主义以呈现出一个敌我意识的建构过程:“民族主义及民族身份的含义尤其要依靠其民族和异民族及异邦的差异的多样的两分法来界定”;“民族身份是一个连续不断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社会构建过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赖任何客观的语言或文化差异,而立足于主观的差异体验”。(11)由于民族主义“明确要求特定的领土,这块领土是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是其强调所谓特殊性、例外性和历史性的依据”,北美独立革命期间的思想家因此都不约而同地将独立的理据集中在北美特性的强调,并进而据此将北美殖民地与殖民母国的关系处理为“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以此而言,敌我辨识是一个具有极端性的认同过程:这种极端性表明“我们”与“他者”已经冲突到不可调和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敌我分界来呈现彼此的异同并据此进行彻底、决然地划界和切割;“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较狭窄的区别感导致较强烈和较根本性的异同感。这种认识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12) 1776年,潘恩发表了深度影响北美独立革命进程的《常识》一书。在强调天赋人权的同时,他在这本小册子当中以大量的篇幅和刺目的词汇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暴虐进行了冷嘲热讽和无情谩骂。他不仅把英国这个殖民宗主国贬抑为“几个不能自卫的小小岛屿”,还把英国的政治制度贬斥为“孱杂着一些新的共和政体因素的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而且将英国的执政党称为“可恶的私党”,更把英国国王称为“魔鬼”、“野杂种”、“盗匪头领”、“狂妄暴君”、“僭称为‘人民之父’”、“大不列颠皇家畜生”和“冷酷、乖戾的法老”。(13)这些在士兵和民众中间如野火般广为传播的文字,真正目的其实就在于彻底地将“美国的资产阶级精英多年来一直都在积蓄着对其忠诚所依赖的理论基础的无言的敌对情绪”加以明朗化,同时使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如此一样令人憎恶”,“这也是任何宣传鼓动家所能用的最强有力的办法”。(14)时任北美大陆军司令的华盛顿不仅称赞《常识》中充满“正确的原则和无可辩驳的推理”;(15)而且因此断然放弃了与殖民宗主国“在光荣的条件下和解”的主张,转而“决心与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国家一刀两断”;(16)他后来在致英国友人的信函中,就直接效仿潘恩将英国首相诺斯訾骂为“凶神”和“煞星”。(17)经由这样一个敌我辨识的过程,北美殖民地和北美居民越来越多地被厘定为国家和新的族类共同体。第一,在1765年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上,克勒斯托弗·加兹顿在会上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在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18)第二,在1774年召开的第一届北美大陆会议上,来自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指出:“整个美洲已经融为一体……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新泽西人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利坚人”;(19)第三,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明白指出,“无论在英国或北美,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没有不坦白认为这两个国家是迟早要分立的”;(20)第四,在《常识》发表后不久的同一年,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在北美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以议案的形式指出,北美“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21)第五,在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中,第二次北美大陆会议在1776年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定义为“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21)这在杰斐逊的自传中也有更详尽的记载;(23)第六,1782年,克雷夫科尔在《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就观察到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经融汇成为具有北美地域特性的“叫做美国人的种族”;(24)第七,华盛顿在北美独立战争行将结束的1783年致函汉密尔顿:“战争终于结束,我感到极为欣慰。广阔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使用聪明才智指导培养,我们将成为伟大、受人尊敬和幸福的民族”,(25)而在另一封信函中,华盛顿将美国人称为“一个独立的民族”;(26)第八,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的1787年,杰伊在文章中明确地将美国的独立与美利坚国族的建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和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的文章一起被收入《联邦党人文集》(27)中:“人民已经接受一种观念:美利坚人民,应该继续坚定联合,这一点,无人反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犹如天作之合……由坚强的纽带相连,永不分离为几个彼此嫉妒、互不交往、互不相容的主权国家。”(28) 尽管克雷夫克尔在和塞顿-沃森(Seton-Watson)分别将北美独立革命时代的北美居民定位于种族(race)和“民族”(nation),但翻检杰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爱国者”的著述原文可以发现,他们更倾向于将北美居民称为“people”。此外,在费城制宪会议完成的美国宪法中,“nation”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意味着至少从潘恩开始,这些“爱国者”在每每谈及这一时期的北美居民时,总是有意识地使用“people”这个词。依据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格林菲尔德的研究,在16世纪初叶,“nation”在指称英格兰全体居民的时候与“people”是同义的:它们“意指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效忠对象”的、具有实体意义的“国族”。在北美独立革命和费城制宪会议完成美国宪法之前,由于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13个北美殖民地尚未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爱国者们”于是就使用“people”一词来指这13个殖民地的居民:“people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复数,这确实是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29)由“people”一词在这一时期的使用可知,它体现了“爱国者们”试图以国族理念来整合北美殖民地并进而构建美国这个现代国家的思考和努力。 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到本土特性的凸显和敌我意识的建构,北美思想家们关于国族和国家的建构的一系列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为国家学说的发展和具体的国家建构进程都提供了一个具有范式化意义的路径:它不仅对亚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在路径选择方面的参考,而且对“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也提供了意义深远的经验和借镜。 二、邦联、联邦与政治共识:国族主义在美国政体结构上的聚焦 通过北美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和邦联条约,13块北美殖民地成功地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否组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在北美各地存在不同的意见。争取和解决国家建构问题和北美居民的权利问题,是北美自殖民地时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不仅是北美独立战争当中政出多门现象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族构建之后的题中必有之义和独立革命的自然延续。首先,尽管各个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期间共同组建了北美大陆军、在第二次大陆会议期间还同意将殖民地改称为“邦”(state)并共同签署了针对殖民宗主国的《独立宣言》和邦联条约;但由于各邦各自完成了具有主权宣示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和具有立法权的议会组织并考虑到邦联条约中关于各邦“各自保留自己主权”的相关规定,(30)北美大陆军自始至终都不得不面对“不是受一个议会的影响与指导,而是受十三个议会的影响与指导”的窘境,这种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的状态让华盛顿无奈地感叹:“很快我们就会变成一头多头怪物,一种异质体,永远不能也不会步调一致”。(31)其次,国族的建构和由此而来的政治诉求在客观上要求通过国家这个“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而得到庇佑。 为了处理战后北美大陆主权分立的状况并探索整合北美的主权归属,除罗德岛之外的北美12个邦于1787年齐聚费城召开制宪会议。经由会议的辩论实录、美国宪法文本和政治家们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北美政治家们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思考过程和政治实践。 制宪会议自一开始就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在合众国中建立一坚强之全国政府之最可行办法”(32)方面。面对“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33)这样一个现实状况,联邦党人从一致对外的角度坚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美国:“历史已经证明,领土纠纷,是各国之间的肇事根源之一。分疆裂土的大量战争,最大根源,即在于此”;“每个国家,不论恨我们,还是怕我们,都想对我们分而治之”。(34)反联邦党人则更多地将其思考重心,放在北美各邦整合所可能引致的问题方面。他们从英国对北美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反省出发,担心单一制的国家架构和基于人口数量的多数机制会引致“大邦”对权利的独擅和“小邦”的权利丧失。首先,他们更多地强调各邦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而不愿意将全部主权让渡给一个单一制架构的统一国家,“当年脱离英帝国的时候,美利坚人民宁愿把他们自己建立为13个分开的主权,不想融合为一个主权: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公民权利、财产安全,都寄托给这些分开的主权,他们理当依靠这些主权”。(35)其次,有鉴于英国殖民者利用代表权对殖民地利益的肆意侵害和占有的历史经验,他们特别强调直接民主的意义和价值:“美利坚人民对他们的利益是如此小心警惕,对他们的公民权是如此留心提防,绝不会把剑和钱袋都交给一个单一政府机构,而且这个政府机构又不是他们直接选举出来的”。(36)再次,循着强调北美殖民地特性进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思路,他们强调各邦自北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差异性和地方特性以对抗“大邦任性统治其他邦”的可能性:“各邦大小的差别如此悬殊,是一个主要难题。……每个邦也和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和作风。他的幸福寓于其中。因此,他们不会把权力授予别人,来控制他们自己的幸福”。(37)最后,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关于权利保障的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则邦联对于独立后的北美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们建立起邦联政府,战争时捍卫整体,共同对付外国,保护小邦,不让大邦的野心得逞;他们害怕把不必要的权力授予邦联,惟恐这些权力会挫败他们建立联盟的初衷;惟恐这些权力将被事实证明危及各邦的主权,他们之所以结盟,正是为了支持各自的邦,不至于让小邦被大邦吞噬”。(38) 由此可见,反联邦党人的思考是基于人性恶的理论预设而展开的,尽管一些反联邦党人表示“需要一定的美德存在,否则自由无法生存下去”,(39)但他们在总体上似乎更愿意秉持消极政治观而不愿意将权利轻易地交托出去。而与反联邦党人相比,联邦党人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安排以抑恶扬善的积极政治理念:“政治推理,假定人人见利忘义,和假定人人刚正不阿,同样错误。代议制的原理,在于相信:人类含有一部分道德心和荣誉感,构成予以信任的理性基础”;“建立政府这个做法,不就是人性弱点的最大反映么?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倘若组成政府的人都是天使,对政府的外部控制,也都成为多余”;“人类自有某种程度的邪恶趋势,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和怀疑;人的本性中,还有其他品格,使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信赖,自有它的道理。共和政治,预先假设这些品格的存在,程度超过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40) 面对反联邦党人的诘问和政治思考,联邦党人对于反联邦党人的上述政治思考在表示尊重的同时,坦然承认这些意见不仅“增加了自己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且也由此开始“思考自己事先未曾想到的问题”。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就此总结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彼此如何才能妥协,使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的独立性两全其美;各邦政府如何得到总体政府的保障?不过,这个问题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设问,总体政府如何得到各邦政府的保障?”(41)为此,麦迪逊提出了联邦制这个兼顾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制度建构思想:“把大的集合性利益交给全国性政府,把地方性的具体利益交给各邦议会”。在麦迪逊看来,由于“联邦共和国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社会、依附于社会”,因此将集合性权利和具体权利分别交托给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去行使,不仅有助于在一个“复合共和国”当中克服多数暴政和少数暴政的威胁和侵害,而且有助于形成一个“(强者)既能保护弱者,又能保护自己的社会”。(42) 在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看来,联邦制是介于单一制和邦联制之间的一个制度架构,“因为其特性是修正并结合了其他两种政府形式的特性。联邦制把在一定范围内以邦联的形式保留主权的国家与在另一个范围内以单一的国家形式拥有主权的中央政府结合起来”。(43)联邦制在北美的建立,既是对毫无主权的殖民宗主国附庸和主权完全分立的邦联的反改变,也是对彻底将主权交托国家的单一制架构的拒绝。通过制宪会议的辩论记录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在国家结构光谱两极之间的选择,既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态的省思和创制,也是对北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检讨。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制的创建是北美政治家在长达116天辩论过程中折中和妥协的结果,这个面对面的宪政辩论的过程,既是政治共识的凝聚过程,也是政治理念的厘清过程。联邦制之于美国,不只是一种政治架构,而且是一种整合多元利益的一种路径和解决方案,更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联邦制还意味着一种从宪政层面上既对绝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权利有限交托机制,这种思考不仅要求政治权利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分权和制衡,而且要求在立法机关分别设置以人口和以地方为单元的双层代议机制。这种多重的复合机制,不仅显示了美国民众在权利交托和看管方面的审慎,也凸显出他们对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双重追求。 通过联邦制这个制度中枢,人民主权、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宪政原则被灌注到美国宪政架构当中,使孟德斯鸠、洛克等人揭示的政治思想和共和理念最终成为一个可操作、可持续的现实制度架构。在格林·菲尔德看来,这场决定着北美现代国家政治架构的宪政辩论和立法过程,深刻地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的忠诚应聚焦何处”(44)的内在本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基于人性观念的不同以及在维护权利时策略和立场的不同。在这场辩论中,双方尽管立场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这种经由冲突而达成的一致,显示出他们自辩论之初就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共识,这些共识确保了13个北美殖民地从主权分立的邦联走向统一的联邦制现代国家。首先,他们都主张北美各邦应该联合在一起并结成一个以国家形态为外壳的共同体;其次,他们都相信一个基于同意且经由充分讨论和仔细磋商完成的政治架构能够从制度上控制人性的弱点和由此造成的滥权。正是因为这两点共识的存在,决定了辩论双方都是“诚实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国族主义者。杰斐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曾经就此指出,“在我们过去的争辩中,竭尽全力争辩的情景有时会使初睹此景的人,由于他们不习惯自由思考,不习惯说出和写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无所适从”;但由于在构建统一国家时“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的共识,所以“不是每一种意见的分歧都是原则的分歧”。(45)由于“每个人都同意,美国是一个国家”且“他们的争议在于这个新的国家是一个联邦还是一个单一制政府”,(46)所以联邦制的统一国家也就成为美利坚国族建构进程的自然延伸和在政治上的必然诉求:“它的最终目标是美国人民所要建立的民族国家,而最终双方的观点也都是要建立民族国家”。(47) 三、印第安人与黑人:国族的辨识、准入与美国的族际政治特征 如果说独立前的敌我辨识旨在强调与殖民母国的分离和现代国家的独立,那么独立后的国族辨识则在于凸显这个现代国家在民族成分上的单质性和同质性。这在事实上不仅意味着脱离殖民统治的单一国家,而且意味着剔除异质的单一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北美独立革命所欲达致的目标,就是“建立单一的国家,并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这是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两项艰巨任务”。(48)在多民族的北美大陆,建构一个脱离殖民母国的现代国家并进而将这个现代国家构建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和经验,在阿克顿勋爵的总结中被归纳为:“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共和国人民必须是同质的,公民平等必须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和地理统一基础上。这一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49)而既然要求公民是同质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国族之外,而公民平等和社会平等,就不过是同质化公民之间和同质社会内部的平等;既然要求民族和地理的统一,印第安人的土地就是被合法劫掠和驱赶的目标,黑人就是被合法奴役的对象。 由于曾经受英国殖民者雇佣而与北美大陆军作战,印第安人被宣示北美殖民地主权的《独立宣言》定义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不仅被排除在建构中的美利坚国族之外,而且被视为敌国和敌人。在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曾经设想与印第安人划界而治:“我们将努力禁止我们的人民到边界线那边去打猎或定居,他们也不能到边界线这边来,除非是出于从事贸易、治病或其他正当事务的目的”;美国建国后,印第安部落依旧被视为主权实体,较大的印第安部落更被称为“nation”;(50)华盛顿政府的官方文件也明确规定“独立的印第安人族群(nation)和部落应被视为外国(foreign nations),而不是任何一州的臣属”。(51)恰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北美独立战争中任炮兵司令的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明确表明:“印第安人的独立联盟和部落应该被视为外国,而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国民”。(52)由于不具有美利坚的国族身份和公民权利,印第安人及其土地不是被肆意劫掠的对象就是被随意颁赠的赏金:“(美国独立)革命刚刚结束,发给参加革命的退伍老兵的抚恤金以及向参加革命者偿还债务的最坚挺的通货就是印第安人的土地”;(53)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甚至认为美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欲期和平相处,绝无可能”。 印第安人的反抗,对于建国初期的美国不啻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在建国初期就将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事务全盘交由美国陆军部下设的印第安人局来管辖;而担任华盛顿政府战争部长的亨利·诺克斯也就此承认,如果以战争对付印第安人,则美国至少要把5000兵力投到战场上,而且军费高达150万美元,这将是国家的沉重负担。(54)有鉴于此,美国在独立战争伊始就致力于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杰斐逊总统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致信印第安人说道:“我们,和你一样,都是美国人,都生在相同的土地上,有相同的利害关系”;(55)1793年,美国颁行了旨在“推动文明开化,也为了获得和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谊”的《与印第安人交往法》(An Act to Regulate Trade and Intercourse with the Indian Tribes);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度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保障条约规定的印第安人的权利,帮助他们走向开化,激发他们正确了解权利和政府的公正”;(56)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1797年表示,“我们要公允而人道地对待美洲的土著部族,使他们对我们更为友好,也使我们的公民对他们更为友好”;(57)1819年,美国颁行《对邻近边疆定居点的印第安人部落实行文明开化的条例》。对印第安人的“文明教化”,一方面是新生的现代国家及人口对土地的需求与渴望,另一方面是试图打破印第安人既有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并使之归化的国族构建动作:“使我们的居住地与他们的汇合并混杂在一起,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民族。把他们作为美国公民而结合到我们中间”;“全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开化一个主要依赖猎物为生的游动种族,乃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要驯化一个野蛮人,你必须把他拴在土地上,你必须使他了解财产的价值及其个人私有的好处”。(58)这就是杰斐逊和建国初期美国政府驱动印第安人以“我们认为合适的逐步的方式在法律和政府方面和我们融为一体”的本意。(59) 美国在建国后的次年即1790年颁布了《归化法》,明确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这就将世居在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遍布于美国的黑人关在美利坚国族的门外。随着“文明教化”的深入,美国联邦政府在1871年通过的《内政部拨款法案修正案》中宣布不再将印第安部落视为“独立的nation”,这在理论上不再将印第安人排除在美利坚国族之外;借由1868年颁行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开始获得宪法承认。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将印第安人土地以“份地”方式授予印第安人的《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这使得印第安人在拥有美国的公民权的可能性趋近实现,但这一法案是以彻底打碎印第安人部落为前提的。(60)1890年,有5307名印第安人成为美国公民;1900年,有53168名印第安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至1905年,有半数的印第安人已被授予美国公民权;而到1924年,已有2/3的美国印第安人获得公民权,同年颁行的《印第安人公民权利法》也明确规定,“在美国境内出生的非公民印第安人,就此宣告为美国公民”。虽经由《印第安人公民权利法》被全部纳入美利坚国族当中,但印第安人一直到1978年才通过《印第安人民权法》(1968年)、《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援助法》(1975年)和《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1978年)始得完整地获得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是“两个不幸的种族”:“在族源、外貌、语言和民情上均不相同;他们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们的不幸。他们在其所住的地区,均处于低卑地位;两者都受暴政的摧残。虽然两者所受的虐待不同,但虐待却来自同样一些人”。(61)尽管缔造美国现代国家的思想家们都强调“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国族主义观念,且在建国之后总是将“nation”与“美国”自然地勾连在一起,(62)但他们所指称的美利坚国族仅仅是北美的“自由白人”。不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将“同质性”视为美利坚国族成员的辨识标准,而原居于北美的印第安人和被奴役的黑人则都被刻意地排除在外:“这个群体应该有同样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天生的能力”;(63)“同质性不仅意味着相似性,而且意味着特定的相似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财富、影响、教育或任何其他事物的过度——它是温和、简单、顽强而有美德的人民的同质性”。(64) 在北美制宪会议上,来自蓄奴邦的制宪会议代表就坚称,“黑人没有自由,没有个人的公民权利……他们本身就是固定资产,与其他固定资产一样,完全服从主人的意志”;(65)身处联邦党人阵营的麦迪逊虽然拒绝这种“把奴隶仅仅看做财产,不在任何方面把他们视作人”的观点,但也承认黑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在我们的法律中,某些方面,他们被视作人,另一些方面,他们被视为财产”。(66)在制宪期间,黑人的选举权是与其身份相关联的:黑人奴隶没有选举权,而非奴隶身份的“自由黑人”则在除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这两个“极端蓄奴州”之外的11个州享有选举权;而在建国初期的美国宪法中,黑人的选举权只能按照其人口总数3/5来计算。由此可见,联邦党人关于“不仅要保护社会免受其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社会的一部分人,不受其他部分的不公正对待”的理念和制度,只限定在由“自由白人”组成的美利坚国族内部,并非普遍施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一面为自己要求生存、自由和幸福,而同时却否定黑人的这些‘天赋权利’”,(67)这种基于“是否是白人”的种族立场,自其立国之初就被固化在美国的政治架构当中。 据179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奴隶人数多达6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美国的奴隶制,使在北方的黑人“被役使……如牛马一般”,而在南方“黑人是财产”;(68)而依照1790年颁行的《归化法》,所有黑人均被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这意味着黑人只能以奴隶主的财产而在选举中按“3/5原则”来计数:不拥有公民权却可以有部分选举权,这就是美国黑人在建国初期的“非人待遇”。 “黑人是不是人”——这个由林肯揭示的议题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建国初期美国族际政治架构的核心:“如果黑人不是人,那么是人的人就可以借口自治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但如果黑人是人,说他不能也实行自治,岂不是把自治彻底破坏了吗?白人自己管自己是自治,但是,如果他管自己又管别人,这就不止是自治,这是专制。如果黑人是人,那末,我的古老的信念教导我,‘一切人生来平等’;一个人没有道德上的权利使另一个人做奴隶”;(69)“建国之初,我们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如今我们实际上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我确实反对扩大奴隶制,因为我的理智和感情促使我去反对,我没有理由不反对。如果为了这一点你我必须有分歧,那我们非有分歧不可”。(70)他还指出:“我认为黑人是包括在《独立宣言》所使用的‘人’这个字眼里的”;“‘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自由制度据以建立的伟大基本原则,奴隶制是违反那个原则的”。(71) 林肯关于黑人奴隶制的思考,更多地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理念,这突出体现在他关于“分裂的房子”的一系列演说当中:“我不期望联邦解体。我不希望房子倒坍,但我确实期望它停止分裂。它要末全部变成这一种东西,要末全部变成另一种东西。要末反对奴隶制的人将制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大,并使它处于最终消灭的过程中;要末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里,无论老州还是新州,都变得同样合法。”(72)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林肯在与道格拉斯进行辩论时坦然承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要声明,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实行奴隶制的州里干预这种制度。我认为我没有合法权力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我无意使白种人和黑种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处于平等地位,两个人种有体质上的差别。”(73) 与印第安事务的权限全权归属于联邦政府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美国对黑人奴隶制的处理是由各州负责的,这就使得奴隶制的存废成为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之间不断角力的关键点之一,而联邦政府的倾向性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以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为首的南部7个蓄奴州于1861年2月4日宣布集体脱离联邦并建立南部邦联。林肯在1861年3月4日宣示就职时明确表示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任何州均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而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一州或者几个州反对联邦当局政府的暴力行为都可以根据情况看作叛乱的或革命的”;“因此,我认为,从宪法和法律上来看,联邦是不容分裂的;按照宪法本身明确赋予我的职责,我将竭尽全力确保联邦法律在各州都得以忠实执行”。(73)1863年1月1日,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宣布“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75)1865年,美国国会在南北战争结束后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劳役存在,惟用于业经定罪的罪犯作为惩罚者不在此限”;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民权法案,规定“不管种族和肤色,也不管在此之前是奴隶还是非自愿仆役”与否,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在1868年,美国国会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对各州的权利予以限制,依据该法案,各州不得指定任何限制公民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各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各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1869年,美国国会经由《第十五条修正案》宣布“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和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和限制”。经由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的三个宪法修正案,美国黑人的奴隶制被彻底废止,美国建国初期关于黑人奴隶选举权的“3/5原则”也由此失去效力;也恰因如此,这三个宪法修正案由此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的第二个联邦宪法”。(76) 在亨廷顿看来,南北战争对于美国和美利坚国族构建而言意义极其重要:“它确实造就了一个国家(a nation)。还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无保留的认同”。(77)这种构建与打造,显然要归功于林肯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整合需要而不得不对扩大美利坚国族的包容性的举措。首先,林肯把白人内部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和征战视为美利坚国族内部的“一场民族大内乱”。(78)其次,林肯明白地拒绝在国族内部展开“敌我辨识”,“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敌人。虽然目前的情绪可能有些紧张,但一定不要使我们之间亲密情谊的纽带破裂”。(79)再次,林肯坚持认为美利坚国族是一个包容各族裔的“民族家园”,“美国人民在地球上占有和居住的这片土地只适合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家园,而不能作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大家庭的家园。它那广阔的幅员和多样化的气候和物产在过去不管曾对多少个民族有利,现在却只对一个民族有利。随着蒸汽机、电讯等现代发明的到来,一个统一的民族会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内乱不是起源于我们居住的土地,不是起源于我们民族的家园。要分离就只会使我们中的灾难增加而不会减少。就它的一切适应力和自然倾向来说,只能联合,不能分裂”。(80) 在林肯看来,因奴隶制而引发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铸下的历史宿命:“我们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的,是上几代人的;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这个冲突将会在没有剧烈震动的情况下永远平息下去”。(81)但从后来的一系列族际冲突的事实来看,林肯这种指望通过一场战争将种族问题消弭于无形的期望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仅就南北战争后出台的三个宪法修正案而言,它们的确为美国黑人的选举权提供了宪政保障,并为国族的扩容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关于各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的规定也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Ferguson)案的司法解释衍生出了针对黑人“分离但平等”的规定:“依据宪法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强制性种族隔离是合乎宪法的;种族隔离是自然的”。(82)这一事实不仅使得美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陷于黑白裂解的状态,“我们的国家正逐渐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一个是白人的社会,彼此分离,互不平等”;(83)而且表明“种族观念和种族偏见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美国生活中的事实”。(84) 四、国家与国族的一体与两面:简要的结论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的建构与国族的建构是一个一体两面、交互推动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国家的建构本身就隐寓并推动着国族建构的内容,而国族的构建又巩固了国家的建构并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建构和国族构建对外都意在完成对“他者”的揖别,而对内则依据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就单一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构的完成与国族建构的实现几乎是同步达致,这意味着公民身份与国族身份的同步准入与同步确认;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始自国家建构的国族建构则是一个贯穿于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发展全程的一个持续性的包容“他者”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既是公民身份的确认过程,也是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族裔纳入国族的确认过程。 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外部空间而言,国家建构是一个对“他者”的辨识和切割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极端情况下通常被处理为一个“敌我辨识”的过程;而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而言,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都是一个试图不断包容“他者”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显然需要“他者”的同意。 “美国的民族性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是对大帝国的反抗和脱离,二是国内的统一”,(85)卢瑟·路德克的这一观点清晰地诠释了美国现代国家和国族建构方面的历史进程。美国建国初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待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不仅显示出他们内心中“非我族类”的种族主义心态,也显示出他们在殖民与非殖民之间的紧张与矛盾,更显示出美利坚国族的整合还远未完成:“美国人为反抗英国人在东部的帝国统治而斗争,但在西部,他们却推行起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86)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②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载齐文颖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③[美]约翰·麦克里兰著、彭淮栋译:《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 ④[美]梅里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20、22页。 ⑤[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4页。 ⑥[美]路易斯·哈茨著,张敏谦译、金灿荣校:《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的美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74页。 ⑧[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盖尔纳此书在台湾的中译本名为《国族与国族主义》(李金梅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 ⑨[西]胡安·诺格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4页。 ⑩[日]猪口孝著、高增杰译:《国家与社会》,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11)罗伊德·克雷默著、邱文平译:《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陈垣执行主编:《历史与当下》(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8-19页。 (1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3)潘恩著、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6、29、10、15、14、30、35、30页。 (14)[美]路易斯·哈茨著、张敏谦译:《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的美国政治思想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15)华盛顿:《致约瑟夫·里德》(1776年1月31日),载(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姚乃强校:《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16)华盛顿:《谈处境的困难》(1776年2月10日),载[美]乔治·华盛顿著,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8页。 (17)华盛顿:《关于某些消息》(1778年5月30日),载[美]乔治·华盛顿著,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1页。 (18)转引自何顺果:《美国史通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19)转引自开邑编:《华盛顿传》,崇文书局,2009年,第69页。 (20)潘恩著、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38页。 (21)裴孝贤(Donald M.Bishop)编、美国新闻处(香港)校:《美国历史文献选集(英汉对照)》,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第12页。 (22)[美]康马杰(Commager,H.S.)主编:《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5年,第12页。 (23)杰斐逊:《自传:1743-1790》,载[美]梅利尔·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4页。 (24)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克尔:《一个美国农民的信》,载[美]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陈凯等译,许崇信校:《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76页。 (25)华盛顿:《关于各州间的猜忌与加强团结》(1783年3月31日),载[美]乔治·华盛顿著,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8页。 (26)华盛顿:《致德·拉法耶特侯爵》(1783年4月5日),载[美]乔治·华盛顿著,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9页。 (27)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合作完成的这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后习称“联邦党人文集”。就笔者所见,该书的中译本有五:《美国宪法原理》(严欣琪译述,法声新闻社,1948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联邦论》(谢叔斐译,香港今日世界社,1966年;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0年)、《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联邦党人文集》(张晓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和《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本文采用尹宣的译本,下同不注。 (28)[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29)[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祖国霞等泽,刘北成校:《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5、536页。 (30)[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15页。 (31)华盛顿:《谈州际猜忌情绪的影响》(1780年7月6日),载[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姚乃强校:《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9-170页。 (32)《召开联邦制宪会议国会决议》(1787年2月21日),载[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附录一)》,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3页。 (33)[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46页。 (34)(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7、42页。 (35)(36)(37)[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4-156页。 (38)[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4-156页。 (39)[美]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40)[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26、354、386页。 (41)[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42)[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4、356页。 (43)转引自[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王建勋译:《美国联邦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73-74页。 (44)[美]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538页。 (45)杰斐逊:《第一次就职演说》(1801年3月4日),载[美]梅利尔·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27-528页。 (46)[美]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44页。 (47)[美]杰克·N.雷克夫著,王晔、柏亚琴等译:《宪法的原始含义:美国制宪中的政治与理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48)[美]H.塞顿·沃森著、全地译:《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问题》,载《民族译丛》,1985年第2期。 (49)[英]约翰·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50)华盛顿:《致詹姆士·杜安》(1783年9月3日),载[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姚乃强校:《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62页。 (51)转引自李剑鸣:《文化的边疆: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52)转引自[美]罗伯特·卡根著,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53)[美]罗纳德·赖特著,高岳、潘洋译:《其实你不懂美国:新大陆秩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54)转引自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下册),齐鲁书社,2005年,第1044页。 (55)杰斐逊:《致约翰·巴布提斯特·得·克因兄弟》(1781年),载[美]梅利尔·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89页。 (56)华盛顿:《向国会发表的第八个国情咨文》(1796年),载[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姚乃强校:《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07页。 (57)约翰·亚当斯:《就职演说》(1797年),载李剑鸣、章彤编,陈亚丽等译:《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58)转引自李剑鸣:《文化的边疆: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416页。 (59)杰斐逊:《第八个年度咨文》(1808年),载[美]梅利尔·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82页。 (60)罗斯福总统曾就此认为,《道斯法案》是“分解土著部落的强大粉碎机”。详见(美]罗纳德·赖特著,高岳、潘洋译:《其实你不懂美国:新大陆秩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61)[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69页。 (62)[美]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63)[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3页。 (64)[美]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65)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63-264页。 (66)[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著,尹宣译:《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76页。 (67)[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纪琨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8页。 (68)[美]戴维·O.斯图沃特著、顾元译:《(1878年之夏:缔造美国宪法的人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69)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就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发表的演说》(1854年10月16日),载[美]罗伊·P·巴斯勒编、朱曾汶译:《林肯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04页。 (70)林肯:《致乔舒亚·斯皮德》(1855年8月24日),载[美]罗伊·P.巴斯勒编、朱曾汶译:《林肯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50、448页。 (71)林肯:《致詹姆斯·布朗》(1858年10月18日),载[美]罗伊·P.巴斯勒编、朱曾汶译:《林肯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954页。 (72)林肯:《一篇演说的草稿》(约1857年12月),载[美]罗伊·P.巴斯勒编、朱曾汶译:《林肯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17页。 (73)林肯:《林肯-道格拉斯第一次辩论》(1858年8月21日),载[美]罗伊·P.巴斯勒编、朱曾汶译:《林肯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28页。 (74)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年3月4日),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 (75)林肯:《最后解放宣言》,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3页。 (76)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77)[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78)林肯:《给亚历山大·里德牧师的信》(1863年2月22日),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8页。 (79)林肯:《第一次就职演说》(1861年3月4日),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3页。 (80)林肯:《致国会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9-220、221页。 (81)林肯:《致国会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载[美]亚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2页。 (82)[美]J.艾捷尔编,J·卡尔顿点评,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83)[美]拉尔夫·德·贝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吴世民、沈宗美校:《1933-1973美国史》(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2页。 (8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85)卢瑟·S.路德克:《导言:探寻美国特性》,载[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王波、王一冬等译:《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86)[美]霍华德·津恩著,许先春、蒲良国、张爱平译:《美国人民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页。标签:美国革命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印第安人战争论文; 美利坚民族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独立宣言论文; 联邦制论文; 常识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