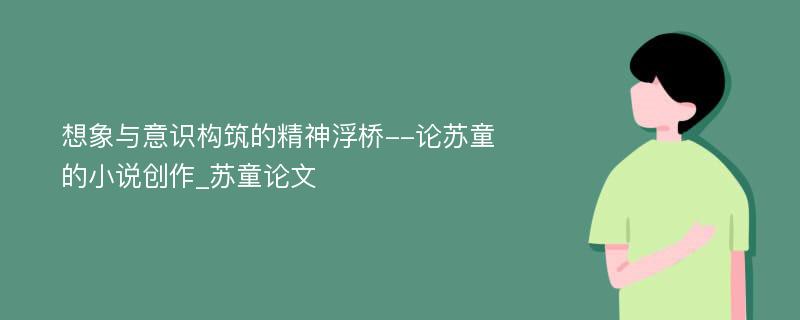
想象与意识架设的心灵浮桥——苏童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桥论文,意识论文,心灵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童曾这样说过:“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探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及整个生命。”(注:苏童著:《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在写作中所倾注的激情。特别是他充满激情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摹写世界的欲望。这些,幻化为独特的文学形象、文学感觉,构筑着他那神奇的小说世界。可以说,在小说这座迷宫中,苏童投入了生命的激情进行艺术的探索,这一点,似乎比他同代作家更多一些执著,更多一些心灵感悟与理性沉思的交接,而少些先锋意味的技术性叙述狂欢。因而,我们没有将其简单归入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等“先锋派”行列,而是重视其小说探索的先锋性精神,关注他“会流动、会摇曳,会消隐,也会再现”(注:苏童小说集《妇女乐园·序》。)的风格魅力。本文要探讨的是,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想象、激情与意象对其小说的文体风格、切入生活的视角选择、话语表现方式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对作家个人审美思维触角的观照上,获得对苏童小说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一
黑格尔认为,“艺术创造最杰出的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而“属于这种创造活动的首先是掌握现实及形象的资禀和敏感,要熟悉心灵内在生活”。(注: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2页。)
苏童的想象是创造性的,是心灵化的。想象和激情激发着他的写作,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架设着一座座彩虹般的浮桥。苏童依靠想象写作,他崇尚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的关于写作是“幻想、自传、讽刺、忧伤”的原则,他总是试图闯入陌生的空间去体会一种占有欲望,一种入侵的感觉,想闯入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认为这与他的现实生活有一个客观距离,但在感情上恰恰投合,兴趣与距离导致他去写作,而这种距离恰好激发他的想象力,“想到他人身上体验一种东西,这种体验写出来就是小说”。(注:《没有预设的三人谈》,《大家》1996年第3期。)苏童的小说写作也颇符合他喜爱的俄国流亡作家纳博科夫所说的意蕴:“小说应当如小说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解”,而且是“对自然、现实、先验的逻辑的反叛。”
苏童写作的敏感点和兴奋点正是源于这种想象与激情的一种反叛性体验,对生活深邃的心灵体验。具体地说,苏童切入生活的方式是通过三个表现视角实现的,即“少年视角”“女性视角”“男性视角”。其中,“少年视角”这一类小说,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作品如《刺青时代》、《舒家兄弟》、《桑园留念》、《游泳池》等,可以看到是最贴近他生活经历的“自传体”系列,而同是“少年视角”的《我的帝王生涯》、《南方的堕落》、《1934年的逃亡》以及“女性视角”写作的《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还有“男性视角”的小说《米》等均可看作是苏童想象性体验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是苏童纯然虚构的文本。这位60年代初出生的小说家对30~40年代的生活情有独钟,其超验性的表现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独特的个性魅力。苏童对陌生的生活进行着一次次“窥视”和浪漫玄想。
那么,苏童想象、虚构文本的激情源于哪些心理的、文化的、情感的渊薮呢?
他的小说在最初就不同于先锋派的彻底实验性倾向。他坚持至今的激越的情感与浪漫抒情风格,与那种实验性技巧操作和语言狂欢不可同日而语。苏童更偏重于依托情感、情绪结构小说、制造氛围。为此,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是从客观上讲,苏童作为80年代后期进入写作的小说家,其自身经历、文化底蕴,与前几代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相比,有相形见绌的匮乏,具有“历史的晚生感”。(注:参阅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留给他的是没有历史、没有现实、没有文化,只有孤零零的自我感觉。而且,这个“自我”还被空虚、苍白的无聊记忆所缠绕。所以这种对社会的、人生的、个人的情感体验在遭致长期禁锢之后,必然在心灵获得自由的时刻奔腾狂泻,在时代给他提供自由写作空间,开始他作为“梦幻的孤独的个体”(注:参阅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而写作。因此,苏童首先满怀深情地叙述自己的童年记忆。《刺青时代》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写实。对主人公少年小拐遭遇的描述凝聚着苏童对同龄人匮乏文化、荒芜心情的追悼,抛洒着令人战栗的几掬清泪。《桑园留念》这个短篇,苏童多次提及表示自己对它的怜爱,其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它较早地在小说中含蓄地表现未成熟少年性心理的真实状态。但是,这种接近纪实的叙述仍无法表现苏童更大的抒写欲望,于是,想象的翅膀借助乔装的“历史”在想象天地自由地舒展开来。《我的帝王生涯》是这种想象激情表达的出色文本。在这部苏童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长篇里,苏童真正地进入到自由的梦幻世界。他以一种体验的心态抚摸人物的命运与伤痛,通过少年端白在命运多舛的岁月所经历的崇高与滑稽,选择的无奈,命定的劫数来体会人生的况味。这里渗透着苏童的光荣与梦想,也是他对生存于“文革”乱世无法建功立业的扼腕慨叹与回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苏童试想在对小说中“走索王”生不逢时命运的叙述中,排遣自己心中无限的惆怅。这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文人传奇”,(注:王一川著:《中国形象诗学》,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苏童对少年帝王的描述没有停留在顾念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追求那种通过典型再现社会现实,而是沉浸在个人奇幻故事的虚构之中,并为这种虚构能力而沉醉痴迷。小说表现出他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的强烈欲望,也是对自身在逝去岁月里不能创造生活的一次心灵补偿。我们可以说,苏童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想象。
另一方面,苏童写作激情的获得还得之于他丰富的个人阅读经验,敏感的极具个性的思维触角,同时,真诚的生存态度,对文学良好的自信心也能使他进入真正的个人写作状态,进入这样或那样的生活。
阅读对苏童的写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位作家是海明威、塞林格、纳博科夫、卡森麦勒和博尔赫斯。特别是博尔赫斯的小说给苏童“带来了光明,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他“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注:苏童著:《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读者和小说家的苏童,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从马尔克斯、塞林格的叙述中,发现了他“真实”生活所缺少的东西。苏童这样描述他的写作:“孤独的作家进入创作状态中经常面对的是幽暗的房间和混沌的梦想,这时候稿纸还放在抽屉里离你很远,而某匹回忆和思想的快马却朝你的房间飞驰而来,它就是阳光,它这是你想要的一点点小小的阳光,小说就是在这种状态中依据幻听幻视幻觉产生了。”(注:苏童著:《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苏童在当代最有影响的两篇小说《妻妾成群》和《红粉》的成功,不仅仅是单纯仿真性写作的丰收,也是凭藉心灵、情感对生活这个“陷井”“迷宫”的体悟,是作家对自我的深层捕捉。这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创造的体验。苏童的艺术思维触角不是放在对观察到的事物的客观记录和重构上,而是对内在心灵世界的自我体验的有机表达,是贯穿自我的认同性体验。苏童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他的自我、个性与他者(描述对象)相互同化、合成的过程,这颇具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的意味。在写作中,苏童不是陈佐千家族、秋仪老浦悲观结局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以强烈认同性体验使小说的文本令人惊奇叫绝。文本所显示出的气韵,充溢灵性的文字透露着他个人体悟与发现的理性光辉。
二
在我们考察了想象在苏童写作中的意义之后,我们来分析作为想象的载体——文学叙述语言是怎样实现其心灵体验过程的。
在苏童小说中,我们充分地体味与感受着其舒缓优雅、纯美流畅的清词丽句,幽怨婉转、气韵跌宕富于节律的叙述结构。这种文体风格在当代小说中颇具特色。语言本身的魅力产生于独特情感、独有心灵体验对表现话语对应性的寻找。作家个人体验之中的形象体系井然地投影于语言系统之中,而内心的体验内容与语言陈述之间的差距一旦消失,前者则意味着获得了形式而转化为规范的小说艺术,这时,语言就为内在情感架设起心灵的浮桥。
自由语体的选择和对作品整体象征意蕴、意象的探索是形成苏童小说文体的重要内容。
作为叙述语体的小说,苏童在遵循语体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偏重运用抒情语体惯用的一些表现方式,如隐喻、象征、双关、反讽等。还创造性地改造对话体,如在叙述中取消人物对话引文标志,叙述人语言与人物语言杂糅,加大语流密度,这也给阅读造成简洁、畅快感。这样,他凭借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天才灵性,在写作中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语感、语调和语流,创造出一种独具一格、有灵性的自由语体。文体学家施皮策说过,人的精神生活与他的语言表达之间有基本的对应性,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因此,不同作家心理个性、写作动机、现实愿望的差异决定着作品不同的语言结构。《我的帝王生涯》和《米》这两部纯粹虚构小说,充分展现了苏童自由语体的叙述空间。苏童说“迷恋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小说中人物的似真似幻、扑朔迷离,体现了他对文化、对历史、对世界的思索欲望,语言的圆熟老到,叙述自始至终的从容不迫显示出他心灵对物质世界把握上的自信与果决。
小说极富传奇色彩的现代文人话语,使我们感到苏童在按自己的本性来写作,以求达到“吐纳英华,莫非性情”“才有庸隽,气有刚柔”的境界。我们将他的自由语体文本表现出的特色归纳为典雅、绮丽、委曲、悲慨、流动,正暗合他的求变愿望,也与他“去想象一种语言即意味着去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的写作方式相一致。不同的想象方式指向不同的风格体式和结构,不同的文学语言描绘、叙述表现着不同的意味。苏童这种语体风格具体表现为深层的文学语感特征,即以隐喻性象征为特征,通过意象体现作品表现力、创造力和想象力。使语言表现的内容在变形中完成对内容本身的本体性超越,写实化的语言表现着非写实化的情境,文学表现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
意象在苏童小说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作品较高的审美价值。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中,街与河这两个意象几乎贯穿所有小说。街是泥泞不堪,“狭窄、肮脏、有着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河是永远“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间或还飘流而下男人或女人肿胀的尸体。街和河在这里既构成人们生存的环境和背景,象征着凝固和流动着的古老历史文化,深刻地表现着其中封闭、乏味的生活和存在性焦虑。
意象的营造使小说表现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产生如神话、传说、梦幻、风俗一样的玄秘、久远的深邃的本性意味,呈现出寓言色彩。
苏童的小说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一点已为人们所感知。他的先锋精神和价值就在于他能不断地跳出自己的“陷阱”,让心灵超越平淡的生活,升华朴素的思想,寻找一个个未知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那个世界溶合了阳光与日光——这样的寻找有多么艰难!(注:苏童著:《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但我们深信,苏童会找到那根神往已久的灯绳,点亮并照耀一切,使生命存在、使艺术亮起持久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