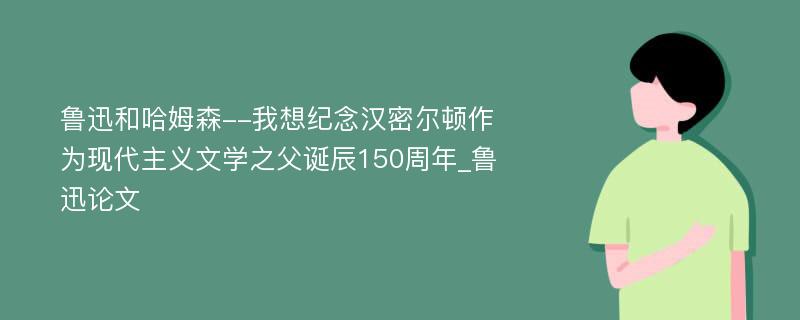
鲁迅与汉姆生——谨以此文纪念作为“现代派文学之父”的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姆论文,鲁迅论文,现代派论文,诞辰论文,之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9)06-0072-06
2009年是挪威著名作家、现代欧洲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派文学之父”[1](P284)、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姆生诞辰150周年。他的母国举行一系列纪念与研讨活动——但又比较低调:汉姆生在二战期间曾站在德国法西斯一边,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历史污点,并因此在战后被判刑。我给予此文的副标题不直言纪念他而说纪念“作为‘现代派文学之父’”的他,亦正因此。
鲁迅对于汉姆生①多有论述(在北欧作家中仅少于易卜生),但关于两人的关系研究,至今无人为之,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未曾得见。本文就是企图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可能杂乱一些,姑且算是关于鲁迅与汉姆生的札记吧。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鲁迅明显受有汉姆生的影响,但两人在思想与创作上却不乏共鸣与相似之处。鲁迅对其评论较多,亦根于此。
鲁迅最早谈及汉姆生是在他的杂文《论“他妈的!”》中:“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挪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2](P231)这是鲁迅在批评中国的“国骂”时以其他民族作为参照时所写,但从中可见鲁迅对《饥饿》的细读与精熟。此文写于1925年7月19日,那么鲁迅对汉姆生的接触当然在此之前。
两年后,鲁迅于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再次谈到汉姆生和他的《饥饿》:“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3](P115)此处所谈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事实上是为全文主旨张目:文艺家要忠于生活,对生活又特别敏感,而生活又多不如意,“肚子饿”就是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文艺家必然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对社会的批判态势,从而与任何一种极力肯定现状的政治家构成歧途。
一年多后(1929年3月3日),鲁迅为汉姆生写了一篇专文:《哈谟生的几句话》。此文大体上有如下几个内容:
一、虽然日本《国际文化》杂志1929年1月号《世界左翼文化战线的人们》将汉姆生列为左翼作家,但鲁迅认为,“看他几种作品,如《维多利亚》和《饥饿》里面,贵族的处所却不少”。[4](P328)
二、汉姆生的作品在俄国影响很深,“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4](P328)
三、指出汉姆生对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的批评特别尖锐,“于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之别,说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学,那就不在话下了”。[4](P330)鲁迅的笔锋指向创造社和新月社,亦与以前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中观点相呼应。
四、对汉姆生对于毕伦存(B.Bjrnson)②的颂扬有保留[4](P330)。可以见出鲁迅对于北欧作家之精熟。
五、汉姆生的《新地》“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4](P330)
综上,可以看出鲁迅对汉姆生的介绍有着这样的深意:以挪威的国民性格映照中国国民性;借汉姆生的创作对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更深刻的阐发,尤表现出对现代派文学的浓烈兴趣;借汉姆生的文艺批评对中国文坛表露微词;指出汉姆生的思想源流,从而也昭示出自己与汉姆生某种亲和的原因。限于篇幅,下面仅就前两个问题分别进行阐释。
鲁迅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立人”,所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P57)而中国国民性离此之距离有如天壤。所以,鲁迅要从事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他一方面挖掘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一方面探求中国国民性所缺乏者。而后者就使得他必然要将他民族之性格与中国人性格进行比照考较。他对外国文学的广泛兴趣与译介,正与此相关联。“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6](P209),这本是鲁迅对于自己引进和学习唯物史观的解释;倘若我们将其引申扩展开来,也不妨视为他译介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根本动机,只不过所谓“自己”不单单指自己这一个体,而是包容了自己整个民族而已,也就是说要借他山之石,创建民族的新文学、新文化,从而达到“立人”之目的。他民族之缺憾,使鲁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之劣点;他民族之优长,使鲁迅更加执着地改造本民族,使之能有理想的人性。前文所引鲁迅说汉姆生的《新地》“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其实并不止于《新地》,汉姆生的许多作品都有此种功能。
鲁迅多次提及的《饥饿》就是如此。鲁迅痛感于中国的“国骂”之粗俗,故作专文《论“他妈的!”》给予批评。在此文中鲁迅即将俄、德、日、挪威等民族骂人之语进行了比较,昭示出“他妈的!”确系中国之“特色”、中国之“国粹”。《饥饿》全篇是一个被饥饿折磨得几乎濒于死亡的社会最底层的人的自述,在这种情状之下,粗野的口吻自难避免,但却绝无与中国之“国骂”相类者。小说描写两个孩子打架,一个孩子骂道:“见鬼去吧,你这个木头脑壳,你这个臭吉普赛人!你这样的穷光蛋才掐人家的喉咙!”他母亲则这样骂他:“去!闭住你的嘴巴!别再骂了,像是婊子窝里长大的!闭上嘴进来!”这语言委实粗野,但其是在愤怒的情态下发自粗人之口,绝不若中国的国骂那样沦为全民族的不分环境与情态的口头禅。中国人向以崇尚伦理自居,尤为重视纲常秩序,然而将骂妈作为人人攻击他人之最常见之方式,甚至已经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真可谓绝妙的道德层面的自我撕破。马克思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骂詈之语同样折射着民族精神。可以说鲁迅读《饥饿》时,确实进行着中国与挪威民族性格的比较。
《饥饿》主人公“我”的性格的某些方面,亦足以烛照国人。鲁迅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7](P359)中国人性格的特点之一即是严重地缺乏自省精神,无论是对于民族的历史,抑或对于个体自身。《饥饿》主人公“我”与此全然不同:他在饥饿难忍之时曾萌发了向一位熟人要钱的念头但并未实行,但他却为此而“深感内疚”,骂自己“真是无赖”;他为自己的乞讨行为而自责:“我一下子却降到了最粗俗的乞讨,……这种丢脸的行为玷污了我”;他曾在一个店员多找了他钱而自己不加声张地拿走而长期地痛苦不堪,陷入无穷无尽地反省之中,最后终于找到那位店员说出真相,从而使自己获得了道德的提升、灵魂的救赎。阿Q同样也是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也曾陷于饥饿之中,但却从无自省,因而始终是一个可怜而又可鄙的人,决然成为不了可怜而又可敬的人。
这种自责与忏悔精神在汉姆生那里,不独发生于饥寒交迫的社会底层,也发生于较为上层的人们。《维多丽娅》中同名女主人公主要是由于自己家族方面的原因致使不能与相爱的人约翰内斯结合,但她为此而深深自责,在生命垂危之际给约翰内斯的信,依然满含着令人撕心裂肺的忏悔。即便是儿童,也会为私留了别人遗落的一支红蓝铅笔而长久自责——《土地的成果》中的两个男孩艾利修斯和西维特即是如此。鲁迅的小说中,所谓忏悔和自责,一般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如涓生,如狂人。下层的人们与此种精神状态基本无缘,《长明灯》、《孤独者》中的孩子们竟然参加了对先觉者的围剿,《狂人日记》中的孩子甚至也成为吃人者,却只能由狂人代他们忏悔和救赎。这不能不说是两人创作之不同,也正映照着民族性格之不同。
其实,《土地的成果》这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更能显示挪威的民族性格。主人公艾萨克“具有农人的冷静,情感简单,稳定和顽固”,他“有一种坚强的、健康的对待事情的态度”,无论是对曾经杀婴和有婚外恋的妻子,还是对曾伤害了自己的奥莲,都极度宽容。“他确实有一种雄浑和壮美,他的力量是惊人的。”他的妻子英格也是天性善良而聪明,心灵充满了欢乐,尽管她因自己兔唇曾受人嘲弄,所以将自己生下的也是兔唇的女婴杀死,甚至也曾红杏出墙,但从总体来看,她仍是一个坚韧而顽强的女人,是一个懂得忏悔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另一位农民艾克塞尔买了布列德的土地和家当,但布列德当时身陷困境,艾克塞尔就允许他一家仍住在那里。这同样是一种宽大和包容,是一种善良和爱。更有意思的是,奥莲将英格杀婴事举报后致使英格锒铛入狱,奥莲就来到艾萨克家代行主妇的沉重劳动。而艾萨克也接受了她(当地极为缺乏劳动力)。这种宽容与博大,还体现在法庭对待犯人的态度上:法庭不独允许他人在为英格作无罪辩护时对司法和社会制度进行攻击,并且表示充分理解英格杀婴的心理,并治好了她的兔唇,还教会了她一些技术。鲁迅曾写道:“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8](P304)倘若说挪威民族的坚韧顽强、勇于开拓,可能受惠于其濒临大海、遍布高山与峡湾、又异常空阔与寒冷的自然环境,那么其宽容、博大则肯定与相对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各种制度有关。“在原野里,每一个季节都有它令人惊叹的地方,但总是不变的有一种天地的宏大沉重的音响”,“除了善以外,这里没有别的”,这样的“土地的成果”就是艾萨克这样的人民。“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样的土地也势必造成闰土与阿Q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9](P3)丹纳的此种观点虽然曾被某些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所批评,但若是考之于鲁迅与汉姆生的创作,确有其道理。尽管汉姆生的人物也有一些不足(例如艾萨克有时也颇爱面子、奥莲喜好搬弄是非),但从更广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性格的许多方面堪为中华民族性格学习的楷模:“我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10](P89)挪威“鬼子”即一例也。
确实,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是难以找到汉姆生笔下的那样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的。少年闰土还是一个小英雄,而成年后的闰土却是一个“浑身瑟缩着”的木偶人;七斤是一个毫无主见、因没了辫子而被赵七爷恐吓得惶惶不安的农民;祥林嫂生活在因违背了礼教的惶恐中;阿Q更是一个被剥削得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并且连明确的姓名都没有的可怜而又可鄙的卑怯者。如果说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象征,那么汉姆生则是将艾萨克作为挪威民族性格的象征来塑造的(作品中一个前地方官员盖斯勒对艾萨克之子西维特说:“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三万两千个像你父亲这样的人。”)。中国最缺乏的还是人们之间(尤其是底层的人们之间)那种互相包容和宽大的和谐关系:祥林嫂何罪之有,却备受人们的冷眼和嘲弄;英格是个杀婴犯,但从整个社会(含上层,包括国王代表)得到的却是同情与关爱。两相映照,也透视出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11](P549)中国国民性的铸就,有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起支配作用的都是那一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文化。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个性,但也一定有着全人类所共同的东西。鲁迅的《伤逝》与汉姆生的《爱的奴隶》所昭示出的即是如此。
鲁迅1928年2月7日日记:“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二元。”[12](P701)这三本书中即有汉姆生《爱的奴隶》(宫原晃一郎译,译名《爱の物语》,东京新潮社1924年出版,系《海外文学新选》之一)。《爱的奴隶》系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酒馆的女招待,她单恋上一位几乎每日必来酒馆的酒客伏拉基米尔,但他却另爱别一黄衣女郎,可黄衣女郎并不爱他。在这一感情纠葛中,女招待不断地将自己的钱“借”(其实是送)给伏拉基米尔,伏拉基米尔则不断地用这些钱讨好黄衣女郎而无果。女招待成为伏拉基米尔的奴隶(他称女招待为“奴仆”,女招待亦甘愿受之),伏拉基米尔又成为黄衣女郎的奴隶。最后女招待因之失去工作,伏拉基米尔则自杀,女招待却以其遗孀自居。两人都因为爱——盲目的爱——而失去了自我。我们知道,鲁迅的《伤逝》事实上可以看作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续篇,以艺术形式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爱的物语》则使读者认识到盲目的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因爱为奴,事实上也是人性的一种异化。小说中译者裴显亚先生这样写道:“克努特·汉姆生……建议要同样重视世界主义的背景,并强调要洞察它的‘普遍人性’,而不只是重视挪威风格。他的《爱的奴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13](P4)此语系译者在谈及挪威短篇小说创作的“民族化”和“国际化”两个派别时而发。《爱的奴隶》所写自觉因爱为奴的现象,确实是不分地域国界的。婚后的子君其实也是“爱的奴隶”,连她最后的出走,也是秉承涓生的意志,同样是为奴的表现。将《伤逝》与挪威的两位大作家的相关作品置于一个系列进行比照考较,确实别有意味。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涓生与子君的恋爱从来就不是一种平等关系,先是施教者与被教者的关系,后来则是主与奴的关系了。并且子君与女招待一样,有着自觉为奴的特点。
鲁迅激赏《饥饿》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对人的饥饿感的描写太真实、太出色了。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因而人的此二欲望也一直成为作为“人学”的文学的重要表现领域。单以《饥饿》命名的作品,仅就我狭窄的阅读视野,即知除了汉姆生的这本之外,还有泰戈尔的《饥饿的石头》、乔治·亚马多的《饥饿的道路》、绥蒙诺夫的《饥饿》、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饥馑》、贝希尔的《饥饿之城》、梭罗古勃的《饥饿的光芒》等。其中,除泰戈尔和亚马多的作品外,鲁迅均曾提及,并翻译了绥蒙诺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
鲁迅日记1928年1月29日:“下午得淑卿所寄《饥工》,二十日发。”[12](P700)2月6日:“上午达夫来并见借K.Hamsun《Hunger》。”[12](P701)看来鲁迅可能《饥饿》的日译本和德译本都读过。但鲁迅最早读《饥饿》肯定早于1928年:如前文所说,鲁迅在1925年既已对《饥饿》作过细读,所以才能发现是书没有中国似的“国骂”,以及对饥饿的描写的细致与深刻。此种细致与深刻主要在于作品运用了现代主义表现方式。在写作《饥饿》的同时(1890年),汉姆生还写了一篇理论文章《头脑的无意识生活》,其中说道:
它们(按:指人的瞬间的思想活动)持续一秒钟,一分钟,它们如同一道闪烁的流光来去匆匆。但是,它们在消逝之前,却印下了痕迹,留下了某种印象……心灵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秘活动,无数的混乱印象,放大镜下看到的想象力的微妙生活;这些思想和感情的任意发展;头脑和心灵对人迹罕至的地区的游历;神经的奇妙活动;血液的低语,骨头的恳求,思想中一切无意识的生活。[14](P63)
此种瞬间的感觉印象,这种“头脑的无意识生活”,恰是现代主义艺术表现的主要领域之一;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的汉姆生在《饥饿》中亦正是如此为之。请看他是怎样描写饥饿带给人的生理痛苦和心理感受、描写饥饿者的感觉印象的:饥饿把整个人“吸干”;“每次只要我稍微有点饿过头,我就觉得我的脑髓好像全都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若是说此处还带有现实主义描写的质素,那么下边的描写就全然是现代主义的了:“一个人饿了感觉是多么怪啊!我觉得自己离那乐曲很近,融在了里面……”这即是一种饿到极点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我现在已经有些饿疯了:我浑身无力,并且觉不出痛了,我的思维也已失去控制。我心中暗自盘算着这所有的一切。我试着证实我这个新词(按:指他在饿得迷离之际自己杜撰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词汇‘Kuboaa’)的时候,头脑里产生一系列令人惊异的跳跃。它的意思不一定是‘上帝’或‘蒂沃力公园’,谁又说它非得是‘牲畜表演’呢?我使劲攥着拳头再次问道:谁说它非得是‘牲畜表演’呢?我仔细想了想,事实上也没有必要非得是‘扣锁’或‘日出’。”这是典型的意识流,以此昭示出极度的饥饿使人的心理已经处于一种精神失常的非理性状态、无意识状态。极度的饥饿不只使他迫切地需要食物,更引起了他的幻觉和狂想、他的神经的奇妙活动。类似这样的描写,在《饥饿》全书中俯拾即是。
作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几乎同时起步的”鲁迅[15],自然也善于描写人在迷惘之际的感觉印象,我以为最出色者当为《白光》中对陈士成第16回落第之后的心理描写。我在《东方意识流文学》一书中对此曾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16](P40-42),此处不赘。
《饥饿》中关于饥饿的描写,并没有直接呼吁人们走向反抗。尽管他饿得痛苦不堪,但他“脑子里却没有一点怨恨、妒忌或者辛酸”,结果最终消弭了反抗。“所以,这不是一本对社会有异议的书。作者对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造成那种饥饿的社会并不是大声疾呼,要求人们起来反对。”[1](P286)
其实,诚如鲁迅所说,《饥饿》(以及《维多丽娅》)中,“贵族的处所”委实不少。《饥饿》主人公虽然沦为下等人的处境,但却自视甚高,因为“很多人的幸福还寄托在这个哲学认识的调查上”(指他拟写的一篇文章),他以大众的救星自居,又认为自己“是在充满残渣的龌龊的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座洁白的灯塔”,明显地将自己与大众区别和对立开来;他本是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却很注意自己的服饰给年轻姑娘留下的印象,这也是一种贵族习性,而他从来就不是贵族。《维多丽娅》中的平民子弟约翰内斯对上层社会的维多丽娅的爱隐含着自身的卑微与对上层的敬畏,自然也是贵族的处所,是贵族意识在人物身上的烙印。鲁迅认为汉姆生并非真正的左翼作家,确有其道理。此类“贵族的处所”,是否与他以后的政治堕落有着深层联系(如同周作人的贵族化的家庭生活方式和对平淡、冲和的追求与其后来当汉奸有着必然联系那样)?值得深思。
鲁迅说自己也曾写过与汉姆生《饥饿》中类似的人物,但未点明;我以为此人应是阿Q。阿Q在“恋爱的悲剧”之后,发生了“生计问题”,谁都不找他做工,使他“肚子饿”,并且饿得“又瘦又乏”,竟然被小D战败。虽然已有夏意,他却因饿而觉得寒冷,东西也变卖一空。“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以后就有了偷萝卜和投身“革命”。在鲁迅这里,“肚子饿”就与“革命”联系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左翼”。虽然按通说此时的鲁迅尚未完成所谓世界观的转变,但鲁迅依靠自己的努力,早已与唯物史观暗合。《阿Q正传》中也有现代主义笔法:阿Q的“革命畅想曲”即是跳跃着的意识流。
鲁迅与汉姆生都依凭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人的饥饿作了真实的描写,尽管有详略之不同。鲁迅是很佩服汉姆生的描写的,说汉姆生的作品给了他“深的感印”[4](P330)。这“深的感印”,我认为主要是汉姆生以现代主义手法使文学对现实生活(含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生理的和心理的)的描写,达到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难以企及的细腻与深度,达到了一种最高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我们没有发现鲁迅对与其同时进入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一干人的赞赏,但他却明确地对比他更早从事现代主义创作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的汉姆生表示首肯。这确实进一步昭示出鲁迅与世界文学发展同步的伟大战略眼光。
注释:
①鲁迅曾译为哈谟生。
②又译为般生、比昂松,系与汉姆生同时的另一挪威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