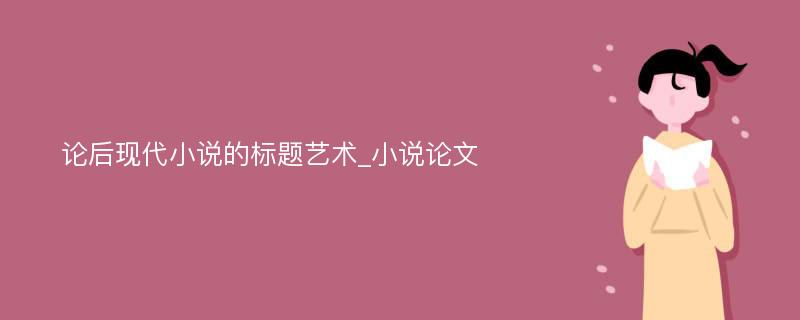
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标题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标题的审美之维同时代思潮往往是一致的,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标题制作就相应于其产生的时代并折射出时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小说标题亦是如此,它产生于20世纪,呈现出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诸多特征。这在其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不去关注作品内涵与思想意义的提炼概括,不像传统小说那样采用政治象征、双关隐喻等手段,让标题本身获得双重或多重意义诉说,尽可能地给出作品的思想深度信息,而是放弃了对小说本文的概括意图和解释权力,只以透露内容信息、呈示事件碎片、点触感觉意绪为己任,完全颠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传统小说标题对于小说本文的统治,消解了小说标题自我权威,使之以平等的话语姿态在接受者面前出现。
一、信息传达——“断片”化
从文本内容信息传达上看,后现代主义小说标题传达的不是文本的整体信息,而仅是有意义的“断片”。它不对小说整体进行全貌鸟瞰和全息总摄,仅以断点裂隙切入方式,去掀开文本一角。如《一束被遗忘的光投掷在矶岩上》、《恶地形》、《请女人猜谜》这类标题便是如此。它们似是而非,本身就是对小说文本的消解,因而根本无法判定其所指意义(即隐喻)与小说故事的干系,其能指/所指,叙述/隐喻等二元对立项紧密的线性联系被打断,展示出的文本框架结构靠能指追踪所指与感觉追踪事物而构成。它们暗示阅读小说文本的读者:小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开始,总是开始不完,引而不发。小说文本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文本的生长可能是无穷尽的,尤其是非消费性文本,它的“再生性”、“文本间性”,它的历史延展性均无法限量。当然,这也使阅读小说文本的读者耐性承受着严重的考验。
结构主义小说诗学认为,作者只不过是话语的载体。小说文本作为引文拼贴的场所,需要的是写字者,而不是作者,作者只是一个功能,他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文本不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相反,他成为文本展示自己的工具。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消失了,我们面对着的是有标题但没有中心信息的小说文本世界。因而理想的小说文本乃是一组能指而非所指结构,它没有起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入口接近它,没有哪一个入口可以被权威地宣称为主要的入口。[1] 那么小说文本的标题自然应该为文本自身运作以及读者的介入开启多种可能性。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在小说标题上的制作灵感,就来源于这种小说诗学理论的大大激发。
罗兰·巴特认为,“总体性是控制和异化的别名,它暗含着中心、等级制和人为的秩序感。断片则将总体性撕开裂口,它摧毁了总体性的堤坝,让那些异质之流自由地涌动。”[2] 这实际上是责难整体性存在及这一存在的秩序原则,而肯定“断片”的非整体活性。杰拉特·霍夫曼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强调阅读过程,“从交流观点看,现代主义似乎强调创作的敏感性与艺术作品的关系,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信息发出者与信息的关系。”[3] 这些观点无疑对于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的认识有着积极意义,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标题的方式从来不只是方式问题,信息的传达从来不只是传达的问题,它实际上包含着小说作者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因此,后现代小说标题以呈示本文“断片”信息介入文本,善待文本,并为其松绑,赋予其驰骋的自由、开放的空间,以平等的姿态“共生”、“互生”,迤逦前行。它解构了传统小说标题的“看守”、“控制”和“论事”特性;解构了传统小说标题关注事物的意义,表象间的联系和“深度”,以及那种介入全面深入,命名即统治、驾驭,经“炼意”而“载道”的方式。实际上沉潜着后现代主义反抗现代启蒙思想中“基础主义”的“大叙事”、“元话语”及“表象主义”中的“反映论”的消解冲动。后现代小说标题传达文本信息的这种方式也展示后现代作家对小说文本内容表述的结果从来不屑一顾,只对表达的方式即形式充满宗教式的热情,进而充当了用语言来游戏,同时又被游戏所困扰的角色,最后使他们的小说成了操作性的游戏范本,因而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本自具有浓郁的后现代色彩。
二、阅读期待——文本“增殖”
从小说标题的阅读期待来看,小说标题总是立于作品之“额”,以不同的姿态召唤和期待阅读的到来。但像《来劲》、《呼吸》、《千万别把我当人》、《从乡村到京城的路途》等这些后现代小说标题则向我们告示:后现代小说已无意于讲述历史故事,它不是一个呼唤接受者到来的叙述者,一个召唤受教人前来的启蒙者,一个期待学生倾听的教导者,或听书人喝彩的说书人,也不传播“真理”和革命的理想,而是诗意地播放文本断片,神秘地晃悠意义“碎片”,它所召唤和期待的阅读已完全相背于传统小说标题,仅像一个伴游,邀约游者一道尽情游历,相互指引搀扶,直至小说文本深处,其意在把阅读者带向对小说文本的愉悦。
罗兰·巴特认为对文本的愉悦有两种意义:一是愉悦,一是极乐。狭义的文本是可读的文本,即我们知道如何读的文本。在这种阅读中,我们寻找透明的意义,要求透过符合文化习惯的、更为舒适的阅读来获得满足。极乐的文本是不可读的文本,它给读者一种缺失感,它扰乱了读者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假定,并使读者和语言的关系发生危机。所以,这里的极乐并不意味着极度快乐,它更多地指向极度沮丧。他在其代表著作《S/Z》中,列出了“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的基本类型即“读者的”(lelisible)和“作者的”(lescriptible)两种文本。在他看来,“读者的”或“可读性文本”的文本是一个只能被阅读,不能被重写的封闭的文本,有着意义固定、封闭、自足的特点,阅读完全可以把握其有限的意义,而不是“重写”、“增殖”,这样的文本基本上承袭传统的模式,有明确的人物、情节、故事。对于这样的文本,读者只能是一个消费者,而不能是一个参与者。这是一种消费型文本、“轻松阅读”文本。而“可写性文本”则是具有空间开放性、意义多重性、语言活动无限性等特点,阅读便可以参与阐释、再生、创造,是可以重新书写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摈弃了传统的模式,总在玩弄语言的游戏,总在探讨作品本身形成的过程,因而呈现出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指涉性。对于这样的文本,读者不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他始终不断在以积极的想象参与、强化着文本自身的再创造。
如《迷失在游乐场中》、《虚构》、《锦色》、《先锋》等这些后现代小说标题,便暗示其文本不是意义的定向性限制意义的多重性,从而消解深度;不是阅读的教化限制阅读的提升初衷,而是具有自身的开放性:阅读空间的给定性与开放性融合、作品阐释的意义模写与意义增殖融合、阅读行为的作者中心与读者中心融合。它无疑是“可写性”小说文本,是典型的“作者的”小说文本。
按照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文本在批评性阅读中是没有任何终极价值的。因为,一件艺术作品独具一种“特殊语言”,它在观众身上引起一种不断地“把它的外延转变为新的内涵”的“宇宙”感。在这样的进程中,在指示行为的一个层次上,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而符号科学研究那些已经确立起来的、作为一切符号结构基础的一般原则可能被“耗尽”,这样,它就成为另一个层次上的能指。[4] 后现代小说标题是作为一个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层次的不中断的“多级”指示系统而发生作用的,它的外延不断地变成内涵,永无止境。所以,我们决不会完成标题所给信息的“最终的”解码或“阅读”。后现代小说标题所指示的小说文本在生成的过程中是普遍向读者开放、向阅读开放的,以便让读者与作者一块儿进行写作,“读”进自己的一些东西。它把我们带向对文本感到愉悦的目的,实际是为了追求阅读期待中的“增殖”。
与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相呼应,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惯常使用非线性的叙事技巧,即拒绝传统小说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并且完全打破那种由开头(故事背景)、高潮(矛盾与冲突的激烈交织)、结尾(故事的结局)组成的叙事模式,其“反情节”的倾向十分明显。作家们时常把人物故事切割、分离成许多断片或碎片,从而使作品的情节结构变得松散零乱,难以辨认——其叙述过程要么前后跳跃、颠三倒四,要么头绪纷乱、扑朔迷离;有时是现实世界与人物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有时是事实、回忆、联想、梦境的混杂,并无逻辑性可言。
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眼里,传统小说的那种意义连贯、人物行动的连贯、情节的连贯是一种“封闭性”写作,必须打破,以形成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性”写作。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没有秩序和理性的时代,人类生活被无数的“碎片”所充塞,毫无逻辑性和必然性可言,所以这种非连续性的叙事最能反映生活和世界的本质。这也导致后现代小说标题显示的阅读期待不是高高在上,视读者为被动的、被灌输的群体,为他们洗礼布施,诱导他们在阅读中产生向心性、趋同性,最终放弃反思、阐释、创造欲望而迷失在文本阅读中,将其吸纳和收编。而是邀约思想型读者从自身的语境中解放出来,使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与作者的约会,激活其阐释的欲望与想象力,去把握超出文本空间所能想象所能提供、甚至未能想象未能提供的多样性意义,进而反思以往的传统理念与经验符号内容,从而获得重新阐释、重新书写的快乐。如《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抚摸》、《黑手高悬》等标题本身无不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以非确定的隐喻间接指向现实,依靠字面意义与隐喻义的悖谬关系,拆毁原生指称关系产生指称幻觉,其能指中心位移,使读者注意力转向语言符号本身,而不寻找这背后的意义。
三、阅读经验指向——“不可确定性”
从小说标题指向的阅读经验看,后现代小说标题不是先行透露出本文要义,给出作品的结语,为读者提供由结语进入本文,由已知经验导入阅读的“确定性阅读经验”类型。如《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寻找外景地》、《四月三日事件》等这些小说标题无不是只点触本文意象,作为游历文本的引言,所提供的是由引言进入本文,由未知经验导入阅读的“不确定性阅读经验”类型。德国接受理论家伊瑟尔指出:“一篇文本的语词是既成的,语词的解释是确定的,既成因素和(或)阐释之间的间隔是未定性。”[5] 就是说,物化的本文是确定的,而文本的意义阐释是不确定的。 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播撒”理论最引人注目之点是‘不可确定的’(undecidable)这一术语的出现,“它彻底搅乱了本文,使人无法最终判断其意义”[6]。 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哈桑则指出:“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这一范畴有着诸如模糊性、间断性、散漫性、多元论、异端、反讽、断裂等多重衍生性含义,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这些理论观念意味着后现代小说从标题到文本都是敞开的,内容是模糊的、不可确定的。作者、小说人物与读者的意识一样,都处于开放的对话之中,处于不断地建构之中,文本的意义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无限地衍生。读者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可以充分享受文本的开放性、复合性、无序性、相对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些小说叙述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试图传递的作者旨意是:在当代社会,政治理想主义和纯真的东西正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愤世嫉俗和怀疑主义”[7]。
后现代小说标题及文本的模糊性是和无序性相联系的,因为无序与混乱,读者必然会感到模糊。纵观后现代作家的小说,有的是因混乱而模糊,有的则是故设迷阵,从而使读者陷入迷惘与困惑之中,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作家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从认识论意义上讲,迷惘与困惑意味着主体对认识对象感到迷茫不解的精神状态,是主体对事物整体的但并非明晰的直觉把握,它同时体悟到事物各方面的复杂样态。从心理意义上讲,内心困惑与迷惘是指某种认知的不和谐状态,它一方面体现为认知主体所把握的信息与其习得的认知格局(过去的经验、知识与逻辑推理)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又呈现为主体对事物作多种可能乃至冲突性解释的认知状态。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形式主要在于追求深度感的精神象征,在思维方式上通过高度抽象的运思过程表达形而上的孤独、荒诞和焦虑体验,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执著于平面表演,在思维方式上通过现象运思过程削平深度模式,让一切回到表层,形而下地关注当下的生存问题。这也使后现代小说标题意识的“不可确定性”与“平面性”共振。后现代作家通过这样的标题引导读者进入认识与心理的两种状态中,就是要激发读者强烈的探求欲,引导人们参与创作,激发人们的探求欲,从而在认知以及心理上去感觉、赋予他们一种怀疑精神与审视意识,从而在作者所营造的文学世界中揭示生活的底蕴。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特征几乎都是与现代主义特征相逆的,所以“确定性”与“不可确定性”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对垒现代主义的论辩焦点之一。因此当小说标题指向“确定性”与“未定性”的不同阅读经验类型时,也就指向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阅读模式与阅读立场。
总之,后现代小说标题不是以总结发言的全知全能角色意识,意图将阅读领上先验把握文本规范的“确定性”轨道,先行透支本文,让阅读成为文本经验的“历史”重复。它摆脱了传统小说标题控制阅读的意念,以引言导语式发言让读者“把多元性和模糊性看作是文学的美德而不是文学的罪恶”[8], 交出文本思想与语言的生长权力,让阅读面对“不确定”的自由空间,每一步都是本文全新经验的独特体验,每一步都是“历时”、都是“当下”、都是自己。后现代主义小说标题本身就在提醒读者:你正在阅读的是虚构的小说,所谓“现实”在仅仅用以描绘的语言中,而所谓的“意义”也仅仅存在于小说的创作和解读过程中。
四、语言生成——“原创”性
从小说的语言生成方式来看,《裸色鸟群》、《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敌人》、《万寿寺》、《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后》等这些后现代小说标题的到来往往令我们猝不及防,对阅读的诱惑是致命的。较之传统小说标题,它们的自身形态、语言生成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前苏联文学评论家柯瓦辽夫曾指出帕斯捷尔纳克诗中那些意想不到的语言及细节“似乎是从作者心里突然冒出来的”[9]。后现代小说标题诗一般的语言穿透感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这种语言效果的奥秘主要来自于直觉与内心经验基础上的“自发性”。“‘自发性’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所具有的一系列直感的可能性,它决定于这个人的内在品质以及过去与当前的经验,……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有意识的控制,允许意象情感和想法自由进入意识。”[10] 语言正是因“自发性”而获得异质裂变的自由,从容抵达心灵深处,从而“抓住”创造性和爆发感的奥秘。海德格尔说:“我们将语言托付给言说。我们不希望将语言建基于不是语言自身的事物,我们也不愿意用语言解释其他事物。”[11] 后现代小说标题就是重视直觉与内心经验,忽视因循已有的理性经验,使自身语言构成方式和形态不受“控制性”的约束,因而对文本概念没有“附着性”。它淡泊于文本“解释”,淡泊于意识形态话语,只是关注自身的语言原色与美感,关注自身的时代气质特征。它与本文相互依存而共生,以自身邀约阅读,而不是“建基于”语言以外的他物,因而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而“此在”。标题不经由象征、双关隐喻等语言途径构织出颇有寓意的“意境”,而是顺从直觉情感、内心意绪的指引生发出一个个新奇的“意象”。其意境往往既不完整、豪壮、悲壮,也不力图透出崇高感、神圣感、说教性和永恒性。只是散淡的意象,它拒绝崇高而安于平凡,拒绝永恒而珍视瞬间,拒绝说教而意在触动。
如果说现代主义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将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和革新。前者通常将人的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加以描绘,刻意揭示人物的内在真实并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而后者则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并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反身文本”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而是用语言来制造一个世界,从而极大地淡化乃至取消了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现实”只存在于用来描绘它的语言之中,而“意义”也仅仅存在于小说的创作与解读过程之中。由此观之,后现代小说标题的语言策略是通过活生生的语言和杜撰的语言将自然转变为文化,又将文化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符号系统。这种策略延伸在文本创作上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多破碎情节、多离散聚焦、多中心。这正如左勒·缪萨拉所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他们似乎接受一个由随意性、偶然性与破坏性支配着的世界。一条与对世界的这种看法相一致的基本构成原则,是‘离散中心’原则。后现代主义小说提出有许多情节(有时是不连贯的情节),有许多同等的艺术中心,有许多叙述场合,而不只是有一个主要情节,……也不只是有一种主要的聚焦手段和一个主要的叙述者。”[12] 而另一个极端是无情节、无中心、无人物。由于后现代作家变革的目的是使接受者更好地品味、体悟作家的作品从而进行再创造,所以在创作时,对传统的叙事艺术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一反传统的清晰有序、完整而有理性,变得混乱无序、模糊含混、荒诞奇异、简约空泛。
后现代派认为所谓价值是人的虚构,所谓意义只不过人造的语符差异。他们不重视经验的“过去”性、外在性和完整性,关注的是内心的、移动的、当前的经验。其小说标题在意义经验上无“附着性”、造语经验上无“控制性”、审美经验上无“意境性”。语言的原创特征非常突出。这种语言生成方式不但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而且是对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及其叙事方式的怀疑,因而后现代小说创作力图突破小说形式的外部边界,模糊它与各种体裁形式的分野,破坏小说的叙述常规,并以此语言生成方式来取消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特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纯艺术表现和受众之间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