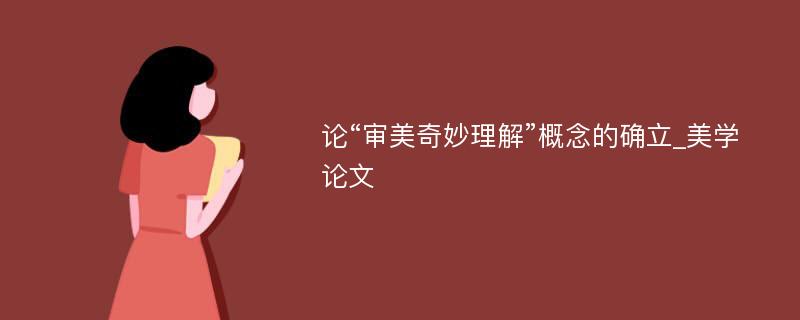
论“审美妙悟”概念之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妙悟是不是一种审美活动?(注:妙悟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最早见于后秦僧肇之著作中。《般若无名论》云:“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僧肇在《长阿含经序》中亦云:“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其后在中国佛家哲学中,这个概念使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禅宗中,妙悟更成为其推崇的根本认识方式。宋明理学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在艺术理论中,妙悟的概念在唐代已多见,李嗣真说:“顾生思侔造化,得妙悟于神会。”张彦远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而南宋严羽关于妙悟的学说最负盛名,他倡导的“一味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的学说在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史上有广泛的影响。其后如明董其昌提倡“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妙悟方式,石涛强调“此道唯论见地,不论功行”的重要观点,都是对妙悟学说的丰富。)不可否认,妙悟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区别于一般的认识活动,一般的认识活动是科学的、功利的、知识的,而妙悟是彻底地超越知识和经验,超越个体的功利,从而对世界作纯然的观照。妙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的认识方式。
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论及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概括起来,一是知的途径,一是非知的途径。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很多艺术理论家都肯定一个无法通过理性把握的世界的存在。平时我们认识的世界是能够通过语言来描述的,在我们的习惯中,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世界往往被视为非存在,或者干脆将其忽略,使我们认识问题就以此为界限。但艺术是微妙的,正像歌德所说,艺术家都是能感之人,他们通过自己微妙的心灵去感受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如何将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又感到语言的捉襟见肘。晋陆机《文赋》描述的一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突发性际遇;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的“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的超越于一般知识的独特思维,就属于这种独特的妙悟活动,这种活动如同“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不可以理智究诘,在无知无言中感知。
这两种思维若用《维摩诘经》的说法来区分,其一可叫做“识识”,这是一般认识方式,是凭借知识的认识;另一可叫做“智识”(注:《维摩诘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识识。”),这是智慧之知,以智慧观照。(注:熊十力先生又有智知和慧知的区别,他所谓智知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慧观照,而其所说的慧知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识知。(参其《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45页))临济宗的实际宗师唐代希运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希运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之“心”,一个是见闻觉知之心,一个是“本源清净心”。一般人以知识见闻觉知为心,而妙悟就是去除见闻觉知之念,返归本源清净心。值得注意的是,希运并不认为见闻觉知之心和本心了然无关而予以彻底排除,他认为妙悟就是在见闻觉知之上的超越,即见闻即妙慧,而不是闭目塞听,等待空寂本心的到来。
其实,《庄子》中对这两种认识方式就有比较细致的区分。《知北游》假托“知”为了“道”的问题云游四方,先问“无为谓”,“无为谓”没有回答,后来又去问狂屈,狂屈欲言又止,于是,这位自以为聪明、热衷于知识解答的“知”去请教“黄帝”,他们有一番对话:“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黄帝”以为,无为谓最高明,因为他“不知”;狂屈次之,虽然忘记了知,但没有彻底地放弃“知”的欲望。而他以为,自己和“知”是最次的,因为他们都是停留在“知”。庄子以为,不知和知都是认识的方法,知为小识(或称小知、多知),不知为大识(或称大知、一知)。以知识去解说天下,到底是“小识”,而“危然”独立,无知无识,心中混茫,葆纯全之志,这就是大识。大识就有大得。儒家之学也有关于不可以理性把握达到的独悟之知。
当然,妙悟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式,并不必然决定它就是一种审美认识形式。但妙悟活动所具有的特点,恰恰是审美认识活动的题中应有之意。妙悟是一种非科学、非功利、非知识、非逻辑的认识活动;是一种无目的的宁静参悟,但又是在无目的中合于最高的目的;妙悟活动符合审美的愉悦原则,它不追求功利的快感,而是一种以生命愉悦为最高蕲向的体验过程;妙悟活动合于审美活动的表象运动的特征,它是一种再造生命形式的活动,妙悟活动不受表象的限制,超越表象,同时又不离表象,再造一种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世界,是妙悟活动的根本目的;妙悟活动也符合审美活动力求把握世界“质”的特点,妙悟强调摆脱知识的束缚,强调以生命的智性来创造,以期洞穿世界的“质”的特性,等等。妙悟具有类通于审美认识活动的潜质,即使在有特别认识目的的道、佛、儒哲学中,也具有这种类通于审美认识活动的特性。
儒、佛、道三家所强调的妙悟活动和美学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说,孔子的默而识之、庄子的心斋坐忘就是一种审美活动,我也并不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以为这些思想“不期然而然而与审美精神相合”。我以为,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妙悟理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判断其与美学的关系。一是其理论本身具有潜在的审美特质,而被美学理论所吸取,进而成为一个美学问题。这是主要的方面。中国美学的理论形态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纯粹的美学著作非常少见,不仅从一个“美”的语汇上总结不出中国美学的规律,而且也无法从中国纯粹的美学著作中爬梳出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来。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缺少美学的思考,有的学者进而对中国是不是有美学产生质疑,如果这一质疑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依照此一逻辑,对中国哲学、逻辑等许多学科的存在产生质疑。这是以西方文化为惟一知识的岸的心理的体现,根本不值一驳。中国美学的大量思想散落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等著作中。就哲学中的妙悟学说而言,其中确实具有和审美认识活动共通的内涵,不仅其非知识、非逻辑、非功利等思想与审美活动相通,而且妙悟过程中的凝神注意、静观默照等也与审美活动类似,更有趣味、理想、判断方式上与审美活动的共通。因此,它为美学和艺术理论直接取资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美学中的妙悟理论是在哲学导夫先路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中的妙悟理论可以说具有一种“前美学形态”。如张彦远在评价顾恺之时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是一个美学评价,他所言妙悟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但这一评价基本袭用庄子之语。因此,我们不能说张彦远所说的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庄子所说的与美学毫无关系。二是有些哲学家论述妙悟时本身就具有美学价值。如王夫之在讨论现量时说,此量“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他转述的是法相宗的量论思想,但他说的是一个美学问题,其现量惟有在妙悟中才能产生。正是在上述所论基础上,我以为,中国哲学中的妙悟问题,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美学问题,只是它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没有哲学那样直接罢了。故此,我以为,中国哲学和艺术理论中的妙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
二
妙悟作为一种审美认识活动和一般审美认识活动又有显著不同。
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审美的目的上。中国美学为何在一般审美方式之外提出妙悟的审美方式,并且强调妙悟才是最根本的认识方式?我以为,这主要在于中国美学赋予审美认识活动更多的内容:审美过程不仅是对美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历练。审美的深入和人生真实意义的揭示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后者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竹子是中国画家喜欢表现的对象,无论是文同、倪云林、吴仲圭还是郑板桥,都想在画面中创造出更新颖更潇洒出尘的竹的形象,都想通过竹子表现其审美趣味和生活情操,表现他的道德取向,更重要的是,都想通过竹子获得自我深层的心灵愉悦,获得自我性灵的超越。因此,艺术活动不仅在于表达什么,同时也在于艺术活动本身,在于艺术活动的过程。艺术家在过程中展现,也在过程中充满,从而获得快感。所以有人认为,艺术过程甚至比所创造的作品更重要,作品是给人看的,而过程是自己完成的。如水墨山水创造之初的唐代画家张璪就非常陶醉此一过程,符载描绘当时张璪作画的过程,作画者、观画者,共同组成了特殊的创造空间,张生不为作出画而满足,更为这过程而满足;观者的兴趣也不全在画家的作品,而更在这个充满趣味的过程。
这种审美与人生合一的追求,对审美过程提出了更特别的要求。妙悟正是适合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妙悟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但它又与一般审美认识活动不同。一般审美认识活动虽然是审美,但也是知识获得的过程。审美创造就是它的“知识”,意象融凝就是它的“知识”。它有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主体和对象在审美过程中展开丰富复杂的活动,从而达到审美的飞跃。但在妙悟活动中,没有审美主体,也没有对象,或者可以说妙悟的过程就是消解审美主体和客体,就是将审美主体和客体合而为一。妙悟不是一种无目的的活动,它有双重目的,即审美创造和性灵优游。但此一目的追寻,正可以用道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来表示。妙悟的过程就是无为,而在这无为中实现了有为的目的。因此,妙悟活动虽然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但其内涵远远超出一般审美认识的范畴,与其说妙悟活动关心悟的结果,倒不如说其更注意妙悟的展开过程,妙悟说到底是一种性灵的游戏。即是说,妙悟不在于“悟后知”,而是在“悟中游”。云行水流,游戏自在,最是妙境。
中国哲学美学中的“游”实在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词汇。云游于天,鸟游于空,鱼游于水,在中国人的想象世界中,这些都没有大地上的拘束,人足踏于地,有山的阻碍,有水的限隔,更是实在的、感性的,而游则是不粘不滞,自在飘动,忽焉而东,忽焉而西,忽焉而淡,忽焉而浓,中国的艺术家不是要在大地上创造意义,而是要在空灵的世界中创造意义。所以,有鱼游,有云游,也有心游。在如鸟斯飞、如鱼斯游的境界中,人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主宰自己的权力,更在游中,获得了伸展自己的机会。游是自由的,烟霭飘渺,白云腾挪,清风骀蔼,都是游心的象征。“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妙悟就如庄子这里所说的,是在无穷的无形的世界中游。
再从审美心理构成上看,一般审美认识活动的心理因素包括想象、情感、联想、意志、感觉、经验等等。如一般审美认识活动是奠定在感觉基础上的,而审美妙悟活动则是超感觉的,它强调,在感觉基础上出现的情绪倾向将影响审美活动的纯粹性,妙悟是一种非喜非乐的体验活动。无论是道家的至乐境界、中国佛学的无喜无受的思想,还是儒家的吾与点也之乐,都突出了超越感觉、超越简单快乐原则的特性。因为在妙悟理论看来,一切悲喜之“受”都是功利主义驱动的。从对待经验的态度上,一般审美认识活动需要有审美经验的参与,而且日常经验在审美活动中也起到积极作用。而审美妙悟活动是一种“截断众流”的活动,是妙高顶上一孤人,清幽夜幕一孤月,虽然它不是完全排除日常经验、审美经验的作用,但在进入妙悟的当顷,则是一丝不挂,一切经验都退出。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一般审美活动需要有情感的作用,情感是推动审美活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在妙悟活动中,不是以情感推动去认识对象,而是以“自性”(一种深沉的悟性)去推动认识。自性的世界是对情感世界的扬弃,任何情感倾向性的介入,都无法进行真正的妙悟活动。感时花溅泪之类的移情和妙悟活动了不相类。再从对待理的态度上看,一般审美认识活动虽然不是科学的认知活动,它重视感性对象本身,不是以逻辑去概括世界,不是以理性去分析世界,但审美意志在这种认识活动中仍然发挥它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审美过程中,理性的力量后退或缩小,但并不是“淡出”,它表现为对经验世界的组合、联想活动以及判断活动等不同的内容中。正如叔本华谈到艺术直观时所说的:“一切直观都是理智的。”(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而中国美学中的妙悟活动是无言无知的,以“不知”之心去“知”,它是一种彻底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活动。像禅宗对逻辑的嘲弄,就是为了突出这一特性。
故此,妙悟活动和一般审美活动虽不具有本质的差异,但却具有不同的特性,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认识活动。
三
正因为具有审美悟入和人生证验的双重目的,所以,妙悟特别强调本心的恢复。在一般审美活动中(如欣赏美的活动以及艺术创造),主要是由知识的判断、功利的判断等转为审美的判断,但在妙悟这种混合着特殊人生需求的审美活动中,所要求的是智慧之光的恢复,而不仅仅是审美心胸的拓展。妙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智慧之光的过程。
人类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三种: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妙悟一般被视为直觉思维。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直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直觉被当作人类直观把握客观世界的独特思维形式。柏拉图就曾强调非理性的直觉思维的作用,他以为艺术创作往往来自于这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非理性的力量,他称之为灵感,灵感是神赐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近代非理性哲学的奠基者叔本华那里,这一思想得到了加强。叔本华强调:“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他所说的直观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是对事物直接的、整体的认识,是心灵中偶然降临的不能以理性解释的心理现象。他认为,艺术必须以直观来创造。显然,叔本华是从他的唯意志论出发来谈直观问题的,世界即为我意志的直观。柏格森认为哲学来自于直觉,直觉是和逻辑完全不同的思维形式,他说:“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务馆1969年版,第3~4页。)“无法表达”意思是理性所无法达到的。荣格将直觉看做一种先天的自发的能力,是主体完全无法把握的一种思维形式。而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利坦则认为直觉是主观和客观的神秘统一,是一种不明所以的神秘力量,它可能来自于神灵的凭依。在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中,强调直觉的作用早已为很多科学家所揭明,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重大发明总是和直觉有关,他说:“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性的,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是逻辑性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0页。)
妙悟具有西方直觉说的一些特性。但又显然不同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的直觉。如果说妙悟是一种直觉思维,那它是一种独特的直觉。与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的直觉理论相比,它在认识活动的目的、认识活动的动因以及认识方式上等都存在重大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妙悟所具有的独特发生机制。
在西方传统的直觉理论中,直觉一般被看做反于常态的非理性思维,对于这一非理性思维的形成动因,或以为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神秘力量,或以为是神灵凭依的产物,或者是人的性灵深处所潜藏的非理性本能,等等。而妙悟所强调的内在动力因素与此截然不同。妙悟是由“智慧”发出的,是一种“慧的直觉”(注:牟宗三先生提出的智之直觉的思想,对我很有启发。他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指出康德哲学有两种直觉,一是感性直觉(esnsible intuition),一是非感性直觉(non-esnsible intuition),这种非感性的直觉又称“智的直觉”(intellectural intuition),康德以为人类具有的直觉能力是感性直觉,而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会有。但牟先生以为,康德将那个派给神灵的智的直觉,其实在中国哲学中则是很普遍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哲学中,智易和知识纠缠,而佛学中强调“慧”才是灵魂的觉性,是妙悟能够发动的力量。所以,本文名之为“慧的直觉”。),妙悟的过程就是对“慧”的恢复。“慧”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的自性。妙悟作为一种直觉活动,是对人本来面目的当下直接的觉悟,妙悟强调的是以定发慧,以慧(或庄子所说的“明”)来观照,所以是一种慧的直觉。这种直觉并非仅仅强调突然的偶然的发现,而强调对生命本来力量的发明,这一直觉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回到生命本体的活动。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活动,不是对知识对象的把握,而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是对存在价值的肯定,对生命意义的确认。与其说此一活动是审美认识的深化,倒不如说是自我真性的张扬。所以,一般直觉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而慧的直觉则越出认识论的畛域,而包含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一般所说的直觉可分为感性直觉和理性直觉两类,前者强调通过直接知觉和想象直观,和外在对象发生关系,后者是通过直接的认识而发现对象的本质。而慧的直觉既不是立足于感性基础上的瞬间超越,也不是立足于理性基础之上的忽然间对对象本质的把握,而是对灵魂深层的智慧力量的发现,对人的存在真实地位的发现。所以,妙悟不是静默的哲学,而是发明人内在本明(慧)的哲学。
与西方传统直觉理论不同的是,这一灵魂深层的智慧力量并非是知识的途径所获得的,也不是神灵凭附的超自然力量,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觉性。它是一粒“种”,熏染能够改变其存在的状态,却不能灭没其根性。“悟”在汉语中,就有发现了本来有的内涵的意思,悟就是悟出了原先的真实,悟是对人心灵中本来具有的特性的恢复。正像松尾芭蕉的俳句所说的:“当我细细看,呵!一棵荠花,开在篱墙边。”呵,原来如此,它是这样的熟悉,又是这样的陌生。悟说到底就是人找到了长久丢失的生命钥匙。“庐山烟雨浙江潮,未悟千般恨未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苏东坡的这首解道诗就道出了此一境界。就是这样的平常,这样的熟悉,悟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生命的燕子归来了。
悟的发动机制就是这丢失而需要恢复的东西。这原先的存在就是人的性,人的觉性,人的性灵的本明,人灵魂中的智慧之性。悟以慧悟,无慧则无悟,悟不得意则不得其悟。慧则明,迷则无明。直觉以明去照,迷则无明以隘思。
所以,在中国佛教中,妙悟被称为“智慧观照”。“当起般若观照”是禅宗中的习语。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藏于人的深心的。在大乘佛学看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这个灵魂深层的本明,但是凡夫为种种虚妄所遮蔽,这一本明的世界隐而不见了(但并非不存在)。妙悟为恢复此一本明世界的必经之路。
庄子的观点与此颇相近。庄子认为悟道就是“恢复”灵魂的本明,人的内在世界本来充满了光明,但外在俗世却将这本明的光隐去了,悟道就是从无明走向道的光明之路,悟道就是“朝彻”,就是“遂于大明之上”,在心斋、坐忘中使心灵定下来,从而拨亮心灵的明灯。《庚桑楚》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不论是庄子所说还是他的后学所言,其理论意义是不容怀疑的,我甚至以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庄子悟道理论的概括。它说明了由悟而明、由明而悟的重要思想,而这正是内篇中反复道及的思想。静心(心斋坐忘)可以“定”(一种深沉的安宁,而不是与外在喧嚣相对的宁静),在这深沉的安宁中,“天光”自露。何谓“天光”?天光就是人性灵中的本明,就是天赋之光,就是道之光、自然之光,是作为人性的光,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深层契合点。这一层是由悟而明。而“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则是由明而悟,在智慧中观照,在智慧中一切都自在显现,我不以我念去干扰物,物不以具体感性的特征扰乱我的心。“见”是显现,而不是看见。天光照耀,智慧观照,并非知识观照,此是无分别、无对待的境界。这与南宗禅的“见性成佛”的观念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佛学中,悟由智慧发出;在庄子中,悟由天光发出;而在王阳明的世界中,悟则是由良知发出。这良知也就是他所说的“灵明”。(注:王阳明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唐代山水画家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具有相当普遍的影响。而这两句话的核心内涵就是“智慧观照”,而不是简单的内求于心、外观于物,更不是有的论者阐释的心物交融、情景结合。唐时刘禹锡有“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董氏武陵集记》)的说法,宋郭若虚有“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表述(注:“心源”一语取自于佛学,《四十二章经》说:“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心源也就是心之源,心为万法之根源,所以说是心源。心源即真如,即般若,即智慧。艺术理论中所说的“中得心源”,就是在妙悟中回归真性,点亮智慧之灯,从而以智慧之光去照耀。因此,师造化,亦即是以心之真性契合万化之真性,以智慧之光照彻无边世界,不着一念,不挂一丝。由妙悟而归于智慧,以智慧来观照万物。
在“智慧观照”中,观照是悟的展开,而观照是由智慧发出的,无智慧即无观照,智慧为体,观照为用。熊十力释此“智”道:“是故体万物而不遗者,即唯此心。见心乃云见体。然复应知,所言见心,即心自见故。故是照体独立,而可名为智矣。”他在旁加注云:“心既是不物质化的,所以是个觉照精明之体而独立无倚的,因此把它名之曰智。”(注: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所以当起智慧观照之“智慧”不是知识,知识理性实与真正的智慧成反比。明紫柏真可说:“夫智慧之与聪明,大相悬绝。聪明则由前尘而发,智慧则由本心而生。故聪明有生灭,而智慧无依倚也,所以不生灭耳。”(注:《心经说》,《紫柏老人集》卷一一,金陵刻经处本。)黜聪明,才能得智慧,有智慧才能有真观照。
正因为需要这一智慧之光,审美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智慧之光的过程。智慧之光和理性有矛盾,所以需要克服知识的束缚;智慧之光与欲望有矛盾,所以需要克服欲望的干扰;智慧之光和人之感受有矛盾,所以需要无苦乐感(大乐者无乐);智慧之光与人的经验世界有矛盾,所以需要自然而然,自在兴现,需要一种圆觉的世界;智慧之光只能在非主非客的境界中发出其本明,所以必须解除主客的分别(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妙悟作为审美直觉活动,是一种独特的直觉,它是“慧的直觉”,或者说是“性的直觉”,在直觉中发现自性,在自性中观照世界。点亮一盏生命的灯,照彻无边世界。
四
审美妙悟在中国美学中的独特地位,是天人合一哲学在美学中的体现,这也是中西美学的重要差异之所在。妙悟强调的是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之中的现实。
妙悟实现了由观物到照物的转变。妙悟的“观”和一般审美认识活动中的“观”有根本区别。在一般审美活动中,我是观者,物是对象,是我之所观者。当我们说物象的时候,就已经将物当作我的对象,与我对举而生,是我的世界中的现象。在审美妙悟的主张者看来,此一现象是一种非真实的存在,因为它存在于人的意念中,是被人意念改制的物象。物成为我心中的存在,物之存在不在其自身,物失去了自己的主宰,它无法自在自由地显现,物丧失了“自性”。在非妙悟的世界中,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灵也处于非真实的状态,它存在于世界的对面,它似乎不是这世界中的存在,它高高地站在观者的角度去打量对象,它将对象推到异在的位置上,处于身在世界中,心存世界外的尴尬之中。更有甚者,我和物还处于全面的“冲突’之中,物在我的“念”中生存,也在我的“念”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天光暗淡,天全丧失,物不见其物,人不见其人。有心观万物,万物改其性;有物撞我心,物我难相合。
在中国哲学中,妙悟是“一”,而非“二”,妙悟是不二之感悟。“不二”强调此悟乃是无分别、无对待之境界。无分别乃就知识言,以反逻辑非理性为其要义。无对待是就存在的关系性而言,从天人关系、心物关系看,其旨在于冥能所,合心境(外境),去同异,会内外。
我们说物,是个粗略的说法。物是和我对举的,因而物是我的对象,当我们说物象的时候,就肯定其作为对象的特征,我们是以自我观察的角度为物命名的。物的对象性的存在,不是真存在,因为在此有能取,有所取,有能诠,有所诠。有能所必有成对待之关系,必是分别;有诠解必有诠说者,有诠说对象,所说必以名,一落名诠即是假。能所分,诠说起,物则不能“如其自身之性”存在,即是虚妄之存在。作为物的真存在,就是佛学中所说的实相,即物如其自身之存在,不在我的感觉世界中存在,不是我的名辨之对应物,物没有彼此、大小、多少等分别,因为此分别本是人秉持之差别相所使然。这就是物如其自身之存在,就是真存在。所以佛学以“真如”为其名。
五代荆浩《笔法记》(注:《笔法记》,当为荆浩所作,据于安澜《画论丛刊》本。)中有关于物的存在特性的精彩辨析,这篇文章假托野叟和画家的对话,说明绘画之大法:“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同样一个物(并非二物),却有似与真的区别(并非两种表现)。物有其形,又有其性。从形方面说,它是客观的,是世界中存在中的现象,是人观之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物象。但作为一个山水画家,如果仅仅停留在眼中所观的物象,那么只能说是对物的虚假的反映,作者提出,画山水要画出山水的性,这个性就是他所说的“须明物象之原”。这个“原”就是山水之性,是山水的“本来面目”,作为“性”和“原”的山水才是真实的存在,才是如如之境。画家所要表现的山水正是此一真山水。真山水不是作为我之对象存在的山水,它是自在显现的。如何摆脱分别的虚假的感知,必诉诸妙悟。
荆浩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画出“如其自身存在”的物。朗照如如,如其真,如其性,如其实在。因为要“如”其“如”,人要有如如智,去观如如性。如如智,即为悟智,如如性,即为真性。如如智如何认识如如性,也就是说妙悟如何展开,中国哲学和美学将其称为“观照”(注: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代美学界,“观照”常常被用为审美观察、审美认识,和古典美学中的“观照”一语了不相类。)。
这里所说的“观”,当然不是外观,不是眼耳鼻舌身对外在世界的接触,而是“徇耳目以内通于心”(庄子语),是“内观”。它又是一种“反观”,这里的“反”不是反向的反,而是返回的“反”,返回到自己的生命真性,在虚假的意念中流连,带给人的是虚假的判断,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去体验,就是中国艺术家所说的“物在灵府,不在耳目”。从对外在对象的观照回到内在心灵的体验,由有念之心的体味回到无思无虑的心灵静寂状态。
与其说是观,不如说是照。以如如智观如如之性,这个“照”字最合“如”的特性了。“照”是整全的,不是从世界中切割出部分,以此部分去观照全体,以个别去概括世界,如一月普现一切月,并非存在一月和多月的关系,这样理解就落入了量论的陷阱。一月就是充满,就是全部。因此,照不作差别观。“照”是无二的,所谓“实相一相”……照就是捂起外观的眼,开启内观的心,去除心中的念,而显现智慧的心。照是一个比喻,如一帧琤亮的镜,如一渊清澈的水。重视妙悟的古人太喜欢使用镜子和水的比喻,意也正在于此(注:如《庄子》中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以镜子般的心灵去观照“物”(并非作为对象的物),就避免“伤”物。)。
在妙悟中,冥物我,合内外,物不在我心外,因此说以我心去照物只是方便的说法而已,因为在此已没有观照的主体和客体,物已不与心对待,哪来以心照物?如果说以心照物,也可以说以物照心,物我互照。所谓心印始归香象迹,妙悟全归无念中。照即是无照,即是镜照,即是空照,统合地照,自在地照。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妙悟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直觉活动,表达的是天人相合哲学的精髓。用佛学的术语表示,妙悟即如如。
五
进此,本文以为,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的妙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是一种以直觉为其特征的特殊审美认识活动,同时,又以智慧观照的特性与西方的直觉理论划然有别。鉴于妙悟在中国美学乃至在日本美学、印度美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认为:在世界美学中,应确立“审美妙悟”作为一个独特美学概念的位置;在未来的世界美学建设中,应注意吸收东方审美妙悟说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