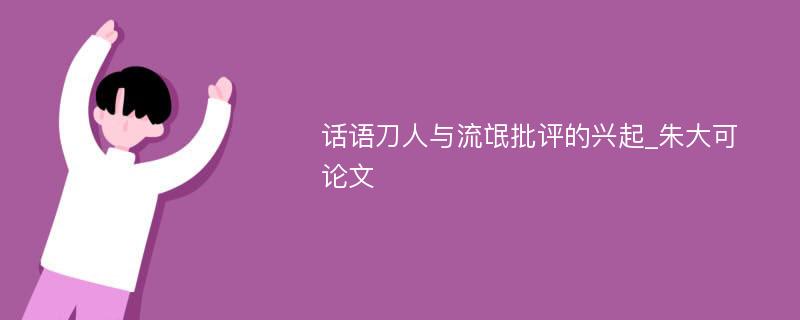
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刀客论文,话语论文,流氓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产生不出巨人的时代,往往是一个对巨人充满敌意和恐惧之感的时代,因为,巨人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引领人前行的积极力量,但也通过比照,彰显着一些人精神上的残缺和人格上的病态,带给他们的是横竖左右的不自在。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衰颓之雾遍被华林的世纪末,会有那么多人义无返顾地加入到否定鲁迅的行列中。而新近登场的这一位,则是澳大利亚的话语刀客、“口水”批评家朱大可先生。
朱大可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两年前,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的一帮话语刀客一起搞了一本对十位中国作家声罪致讨的《十作家批判书》,“一脸坏笑”地在中国文坛上亮了一次相,给中国的读者赠送了一支印有"Austrilia"字样的“文化口红”,搞得几个中国的“刀客功”的痴迷者,也“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无奈,“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的“细小命运”,注定是久长不了的,因此,它虽然成功地绑架了不少读者的想象力,有效地扰乱了一些圈内人士的判断力,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成了把聋子治成哑巴的“话语手术”事故。
其实早在《十作家批评书》中,朱大可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恶意攻击鲁迅的事业,他说,“……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和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
此后不久,人们就从网上,从著名的《书屋》杂志上,读到了他的题为《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的奇妙文章(注:见《书屋》2001年第五期,以下引文凡引自此文者,不再注明。)。这篇文章的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谣诼与诬蔑混和而成的气味,氤氲着挖苦和冷嘲构成的阴险毒雾,透过这些缝隙,你会看到面部表情狞厉而古怪的话语刀客,把用“情欲”、“性感”、“风骚”、“仇恨”、“劣质”、“欺诈”和“殖民地”等材料调制的外国口水,疯狂地吐到鲁迅的名字上,其情形有如一只蜻蜓向一架光荣退役的战斗机发起进攻,虽然显得勇敢而且无所畏惧,但是,让人可怜它的渺小和无力。
一般说来,话语刀客的“口水”批评与正常的批评的最大的不同,在于正常的批评是人的批评,就是说,它把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当作人,把批评理解为人与人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既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而且,因为批评者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也就怀了一颗富有同情的心,先来理解别人。话语刀客的批评就不同了:他把批评变成诅咒,变成审判,把一切都变成冷冰冰的“话语”,他所批评的人,因而也就不再是一个有个性、有忧伤、有爱憎的复杂的生命体,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一种手段,借助它,话语刀客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后资讯时代”的“放荡”和“风骚”,才得以表现出来。
话语刀客是喜欢谈“肉感”的。他们讨厌羞答答的遮掩和文绉绉的表达。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文字赤身裸体地在白纸上狂舞。他们的笔下频繁出现的是“情欲”、“性感”、“风骚”、“放荡”、“风情”、“爱欲”、“爱语”及“阳痿”之类的具有肉感性质的词汇。在灵与肉之间,话语刀客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后者。他们不惜学习流言家的手段和长舌妇的做派,虚构出一个被温香软语缭绕着的“情欲”场景和“风情”故事。所以,虽然“中年鲁迅”对“迷人的殖民地情欲”,“表现出来罕见的冷漠”,但这不是问题,这正好为朱大可提供了“惊骇地发现”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他“仔细探究”,却从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中,“找不到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注:无独有偶,有一个叫老侠的“刀客”,在同王朔对话的时候,也曾就这一点嘲笑鲁迅:“……《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而话语刀客“探究”到的秘密是“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刻。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一声凄厉的狂哭。”纯洁的师生感情,对被杀者的“记念”,对杀人者的“出离的愤怒”,都被话语刀客用“欣赏”这样一个含混的词置换成了暖昧的“爱欲”表达,对黑暗和暴政的愤怒抗议,被置换成了基于一己私情的“凄厉的狂哭”。这正应了《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段著名的文字:“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算不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尽管鲁迅说过,他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他未必会想到,“流言家”的种子竟会如此绵延不绝,竟会下作到如此地步,竟会从死亡和鲜血中,找寻“情欲”的根苗,编织“爱欲”的故事。而被“肉欲”主宰着的话语刀客是不会放过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剥光全身进行羞辱”这一细节的,虽然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这并不能赢得“话语刀客”的敬意,相反,话语刀客视之为“极其强悍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必然是“不谙风情的女人”,鲁迅与这样的女人的书信,也必然会“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话语刀客在寻找别人的“生活激情的迹象”上,具有猎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他终于找到了鲁迅“惟一的情感线索”,这条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遗憾的是这条线索并没有事实的支撑,因此,它也就没有办法满足把“肉感”和“情欲”等同于“内在激情的动力”的“口水”批评家的需要,没法让他利用“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他要让鲁迅万劫不复地“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
为了把鲁迅说成“远离爱语”的疯狂的“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朱大可是不怕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他把鲁迅《死》中的“写给亲属”的几句话,断章取义,深文周纳,上升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毫无疑问,这“七项基本原则”,体现着鲁迅先生的气质、人格和生死观等重要价值观念的。但我从中看到的不是所谓的“仇恨”,而是一个自尊、清醒、深刻、毫不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懂得真爱的丈夫,一个语重心长的父亲。
鲁迅“七项基本原则”中第一条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第三条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话语刀客朱大可即据此评判道:“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并将此列为鲁迅“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的大罪状之一。诚然,如果按照物质主义时代和腐败社会的尺度来衡量,鲁迅的这一原则似乎属于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但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附记”中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先生傲然“坚拒”的充分理由,而这,却是话语刀客们所不以为然的。“原则”中的第四条是讲给妻子许广平的:“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湖涂虫。”朱大批评家斥之为“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其实朱大可显然对鲁迅的思想知之未详、理解不深,早在1981年,鲁迅就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强烈反对要求女性“守志殉死”的节烈观,呼吁人们“要除去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鲁迅在这里,只不过将所提倡的道德原则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不存偏见的读者,从中见到的,是先生对妻子理性而深沉的爱的情感,而那位披着慈善家外衣的批评家,却显得无知而伪善,荒唐而可笑,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第六条,“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这是鲁迅讲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也许还包括所有那些善良而轻信的人。这实在是千古清醒人语,是看透了人间的伪诈,深味了人间的欺罔之后的无奈的慨叹。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现实的情况是,一诺千金的季布少,而轻诺寡信的刘邦多。鲁迅早在写于1927年9月24日的《小杂感》中就说过“防被欺”的话,他举的历史上的例子是:“刘邦除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因此,到终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法三章者,话一句耳。”(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1页,第533页。)岂只刘邦,他的精神遗产的继承者无不如此。这一条,实在是鲁迅吃了多少次亏以后总结出来的教训。朱大批评家说这是“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原素”,实在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人的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朱大可批道:这是“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鲁迅这句话的核心动词是“接近”,而它关涉的宾语是那些损人而又要人默无声息的人。鲁迅在题为《女吊》的文章中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食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9页。)鲁迅提醒“被压迫”者警惕那些言清行浊的人,免得受了他们的伤害,再受他们的欺骗。朱大可不分是非曲直,不看鲁迅所指涉的对象,是些什么样的人,而是将对象主体模糊化,似乎鲁迅无原则地恨一切人,主张“以牙还牙”地报复一切人。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第三种人往矣,但在“殖民地”摇篮里成长,在异国他乡“崛起”的话语刀客登场了。他适彼乐土,远离了“这一世界”,也遗忘了“这一世界”,只有对“这一世界”的难以消释的幽怨,被化作仇恨的火焰和诬蔑的利器,从遥远的澳大利亚,不断地射向另一世界之外的这一世界。然而,如此行径,无非“捣鬼”。遗憾的是,朱大批评家虽有“捣鬼”的勇气,但却乏术,“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注:《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6页。)不过,朱氏虽“捣鬼”乏术,但并不是没有老师和同志,只怪他智术短浅,没有学习和借鉴的能耐。事实上,陈西滢早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致志摩》中,就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这就是那种道术甚高的“捣鬼”。他并不明言确指,更不议论发挥,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远比朱大可式的赤膊上阵妄下雌黄要高明。针对陈西滢的诬枉之论,鲁迅先生在《无花的蔷薇》中替自己辩护说:“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这实在是无所遮掩的老实话,也许有违托尔斯泰式的隐忍和恕道精神,但心肠实在比朱大可一类的“句句落空,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注: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的话语刀客要仁慈、善良。
无疑的,鲁迅的性格中,确有坚硬、尖锐的一面,有时,在政府的审查、迫压与恶意的诽谤、中伤的双重攻击下,它往往会变得更加坚不可摧、锐不可当,但是,从整体上看,绝对不可用“仇恨”或“暴力”这样的词语,来简单地概括和评价鲁迅。无论是鲁迅的精神世界,还是他的杂文创作,都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正像李欧梵指出的那样:“爱、死、牺牲、希望、失望、时间、历史、人的状况、生命的意义等主题,成为他的杂文中的‘内在的声音’,不仅揭示了他作为创作者的内省的方面,也揭示了他在思想理性方面‘多方位’的复杂性。”(注:李殴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35页。)而无论多么“复杂”,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热望,对于社会痛苦的关注,对于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始终是鲁迅精神的底色和鲁迅杂文创作的灵魂。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2页。)而他的“恨”是他的“爱”的另一面,是是非分明的,是有着稳定的道德基础和人格支撑的,他说“文人是不应该随和”的,“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林毓生说,鲁迅对军阀政客的憎恨,对逮捕并屠杀青年学生的国民党的憎恨,对左翼阵营的“奴隶总管”的不满,都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正直的道德感”,而“他的正直的精神”,“仍然是人们至今尚熟悉的‘标准’”。(注:李殴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70页。)这才是对鲁迅的“仇恨”的正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
朱大可的这篇奇文,与其说揭示了鲁迅“仇恨政治学”的性质与内涵,毋宁说标志着“流氓批评学”的“崛起”和形成。“流氓”是朱大可批评话语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关键词。他在一篇题为《流氓的生命周期》的长文中,语无伦次地把从大禹开始,到徐渭止的中国神话、小说和历史中的多位长期受到称颂的人物,都谥之为“流氓”。朱大可对“流氓”的使命的界说是:“从一个沉重的本质里逃开,并用那种游戏的、平面的、没有深度的存在取代这个本质——流氓的使命就是如此。”(注:洪子诚编:《冷漠的证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话说得玄了一些,但大体意思无非如此:“流氓”也者,就是那些把一切都“游戏化”的“没有灵魂栖所的异乡人”。“流氓”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在他的眼中,没有可以依本的传统,没有可靠的价值观念,没有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的态度永远是拒绝,永远是嘲弄和挖苦。“流氓”是信仰和道德的敌人,尊严和正义的对头。他乐于把庄严和神圣化为一句笑谈。他因为仇恨一切,所以看一切都不过是“仇恨”。他蔑视内在的精神世界,把一切都看作“情欲”的奴隶。豪克说:“人能够忍受身体的饥饿感,却不能忍受无意义感。”(注:豪克:《绝望与信心》,李永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但对文学上的“流氓”来讲,这句话是无效的,他们能忍受“无意义感”,但不能忍受“身体的饥饿感”。他们的文学事业的基石,只有“情欲”。
依据“流氓”的精神语法展开的“批评学”,谓之“流氓批评学”,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偏执的“主观主义”。在展开批评的时候,“流氓”批评家的语气是独断的。他喜欢用“无疑”或“毫无疑问”,爱用“最”和“无比”,爱用“普遍”和“彻底”。他只下判断,不作分析。他更依赖随意的联想,而不是可靠的事实。例如,朱大可认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陡峭的楼梯,光线黯淡的走道、狭窄的空间、巴掌大的顶楼的晒台,遍布着油腻和房客的争吵声的厨房,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罪恶和亲情的混和气味”,总之,“阴暗的建筑成为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这实在是别出心裁的分析视角。我不知道朱氏的分析套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巴赫金的启发,但我知道巴氏的“文化建筑学”是基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事象的考察与分析之上的,而朱大可的判断则是任意的,结果和原因之间,缺乏起码的因果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朱大可的理论成立,即上海的“石库门”和“亭子间”果然能“古怪”地“支持”鲁迅及“各种势力”形成“仇恨政治学”,那么,人们想知道,另一些同样居住在“水性杨花”的上海的人(如朱大可先生),是否也曾在劫难逃地“陷入了上海的圈套”?是否也被这“绞索”“扭曲成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人们还想进一步弄清楚,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野心勃勃”的“口水”批评家的病态的偏执狂倾向,是否与澳大利亚的“文化建筑学”和“文化生态学”有关?难道生活在毒虫颇多的环境里,整日提防着毒蝎、毒蛇、毒蜂、毒蚁、毒蜘蛛、毒蜥蜴和带病毒的蝉螂的侵袭,不是更有助于形成更极端的“仇恨政治学”吗?不是更容易让一个人对远隔重洋的中国“充满乡怨与疑惧”吗?
在“流氓”批评家看来,既然“仇恨政治学”从鲁迅开始“崛起”,“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那么,此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暴力”现象,都与鲁迅脱不了干系。鲁迅的“仇恨政治学”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寒冷的北方窗洞里,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他在期待“毛语”与“鲁语”的“胜利会师”。朱大可说,毛和鲁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疑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但这并不妨碍“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不过,“鲁迅党人胡风”等人的遭到“严厉整肃或‘报复’”,却与“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爱意”的他人无关,而要由鲁迅来负全责,因为,“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迅党人的文化生涯”。——“流氓批评学”的流氓逻辑于此可见一斑。
“流氓批评学”的文体特征,是没有节制地运用夸张、比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流氓”批评家的语言是高度意象化的,华丽性的。他赋予自己的语言以含混的隐喻性和强烈的肉欲色彩,借以刺激并征服读者的想象力。例如,朱大可的批评文字的文体特征,就是轻浮、虚饰、俗艳、做作。它并不引人进入深在的意义空间,而是让你滞留在外在的形式层面:一方面让你欣赏“流氓”批评家炫奇弄巧的才华,一方面又让你佩服他披坚执锐的凌厉锋芒。他的语言在“轻快、轻浮、轻松、轻贱”方面绝不亚于为他所不齿的余秋雨。看看他的《书架上的战争》一文中的这些句子吧:“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段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今天,他(马克思)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女孩死亡的场面变成了一场恶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我们生命的血的联盟”(注:朱大可:《书架上的战争》,《南方周末》,2001年2月1日。)。“满含泪水”的“煽情主义话语策略”,比起余秋雨的《道士塔》里的“大哭一场”,不是更“轻浮”,更矫情吗?“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自己的神性”,比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中的“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不是更“甜蜜”,更“轻快”吗?“热烈的意义”、“缄默的信徒”云云,不是比余氏的《千年庭院》中的“我是个文化人,我的生命主干属于文化”更“轻贱”,更接近“软体哲学”吗?最后,朱氏的“书比刀子更危险”的高论,不是比余氏的《雨夜诗意》中关于“雨夜”的议论更“轻松”,更随意吗?这说明,“流氓”批评家所反对的话语和文体,往往正是“流氓”批评家自己“行凶”的利器,“煽情”的工具。
总之,“流氓批评学”乃是“欺诈性”、“劣质性”、“诽谤性”语境的产物,是一种其性质、特征及内部样相依然有待进一步认清和揭示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流派。“流氓”批评家的武器是“口水”。他“仇恨”一切。他通过诅咒“放荡”,“体验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他透过“情欲”的孔道观察世界,把一切纯洁与高尚的东西,都变成了长舌妇的谈资和流言家的消费性话题。他的事业一时还不会寂寞,因为这个时代用以区别真实与虚假、高雅与卑俗的尺度与标准已经非常模糊,留待“流氓”“崛起”的空间和舞台依然很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