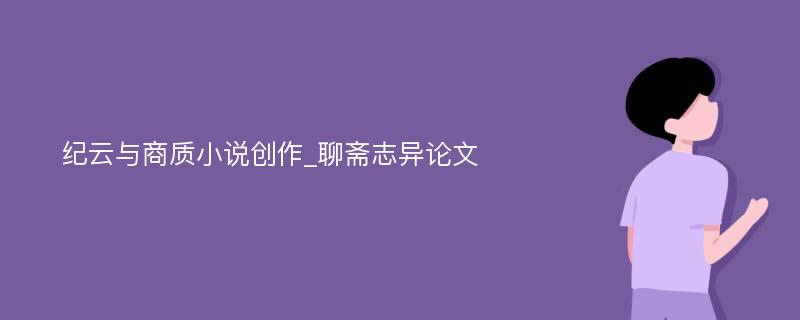
纪昀与尚质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言小说自唐人传奇后,于宋元明三朝滑向了低谷,历经数百年披沙捡金的积累,在清经过蒲松龄《聊斋志异》强大的驱动,终于又使文言小说这一艺术样式攀上颠峰。但在《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不仅从小说理论上批评《聊斋》者流的创作,而且抛出了自己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于是在清文言小说的创作中出现了“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和“体式较近于纪氏五书者”两种不同的创作追求,并且形成抗衡性影响。笔者无意评价《聊斋》与《阅微》二者的优劣,而是试图通过纪昀的小说创作,认识其渗透于小说中的思想,观照中国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小说意趣追求及由此带来的文言小说创作的不同艺术走向。
一
《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是纪昀晚年所著。从其创作的题材来源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基本相同,或来自于亲朋、同事,或来自于下层俚巷,或来自于见闻考索。内容上涉及到官场世相、民俗风情、评诗论书(画)、名物训诂、医卜星相、精怪鬼狐等等,细大不捐,包罗万象。纪昀仕途顺畅,31岁成进士,“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留庶子,寻擢翰林院侍读学士”,49岁为《四库》总纂10年,书成,“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卒,赐白金五百治丧”。[1]可以说受到了浩荡皇恩。加之治文出入《左传》,参用《公》、《穀》,故时人皆以严肃的封建文人或拘严的儒学大家论之。其实,在纪昀的小说创作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封建文人对封建文化的微妙心态。
的确,纪昀身为上层文人,在作品中对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揭露没有《聊斋》那么惊心动魄,但并不表明纪昀对此没有认识。《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中写“职官奸仆妇,罪止夺俸”,“康熙年有世家子挟污仆妇”,“主人调仆妇而妇自缢”。作者深感此类不平等现象,更认识到当时法制、吏治对此无可奈何,于是采用了因果说法的传统手段,指出此职官遭到阴谴,此世家子遭到报应,此主人为仆妇阴魂所索。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六)记录一妇人为人所污而亡,阴魂不散,托人具状告于城隍—正乙真人—上帝,然而这一敬畏的上层建筑,奉行的却是“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大事不如化小事”。面对于此,作者指出:“此鬼苟能自救,即无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既为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聪明而不正直乎?且养痈不治,终有酿成大狱时,并所谓聪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其认识是清醒的,其用心是良苦的。卷六《滦阳消夏录》(六)对于铺天盖地的黑暗势力网作了较为详切的分析:“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
封建社会进入清代,积弊几千年,沉疴难瘳。纪昀与历史上较为开明的士大夫文人一样,没有办法,也不可能为这一社会找到疗救的良方。但是纪昀却以自己的清醒,认识到了上层的积弊,给我们揭示出了某些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暴露出当时官场,特别是法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客观上有警策作用,这也显示出纪昀思想上较为进步的一面。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纪昀虽然对社会不合理现象有所揭露,指出吏、役、官之亲属、官之仆隶为天下之最大害,显然却忽略了根本上的原因,并且在暴露时难见痛快淋漓,只能“盛陈祸福,专主劝惩”,这正可见到传统文人欲有所言而又害怕贾祸的微妙心态,也难怪《笔记》在思想上不如《聊斋》那样脍炙人口。
“贞”与“孝”是封建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理学产生后,成为社会强大的规范标准,作为士大夫的纪昀极力鼓吹亦不足为怪。就孝而论,在纪昀小说中多处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子媳名义在,纲常便在。《滦阳消夏录》(四)记一妇人不堪忍受其姑之虐待而自缢,阴魂欲与父兄讼姑,作者训责道:“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忘巳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这与“君要臣死”、“父要子亡”似乎没有什么两样。就贞而论,在作品中表现为以是否节烈作为妇女立世的基本准则。《滦阳消夏录》(五)写一妇夫死再嫁,“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甚至歌颂一少妇甘被屠妇肢解作食物卖,有于心不忍者,“倍价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艴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滦阳消夏录》三)这岂不是活生生的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应该说,经过明代人文思潮的冲击,纪昀还持此种节烈贞操观,显然较为落伍。
然而,纪昀又并非顽固不化。在许多作品中,作者对理学的贞节孝道观感到困惑,发现它有着许多不尽人情事理乃至扼杀人性的一面。
《滦阳消夏录》(四)记一女子并父母为强人所絷,女誓不受污,贼便于其父母加炮烙,父母不堪苦刑命女从贼。女批贼颊,与父母俱死。纪昀评价道:“或谓女子在室,从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从贼矣,成一己之名,坐视父母之惨酷,女似过忍。……父母命为娼亦为娼乎?女似无罪。”
《槐西杂志》(二)记一妇一手抱儿一手扶姑涉河,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祀!”姑以哭孙不食而死,妇亦立槁。纪昀评价道:“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
可以看到,纪昀对于贞孝节烈这一道德标准有着自己的思考,他在整个《笔记》中记录了许多节孝与事理、物理的矛盾,甚至是节与孝本身的矛盾。在其评价之中看似首鼠两端,实则是通过殊难置评的种种现象,表明僵死教条的可笑。
尤为可贵的是在小说中并不回避人情人性,他虽没有明代人文思潮以情反礼那么尖锐激烈,然而却能够认识到情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而肯定之。《槐西杂志》(一):
某乡有少妇,夫死未周岁辄嫁。越两岁,后夫又死,乃誓不再适,竟守志终身。尝问一邻妇病,邻妇忽瞋目作其前夫语曰:“尔甘为某守,不为我守,何也?”少妇毅然对曰:“尔不以结发视我,三年曾无一肝鬲语,我安得为尔守!彼不以再醮轻我,两载之中,恩深义重,我安得不为彼守!尔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语塞而退。作者充分肯定女子的守与不守,皆是情之所使然,而并非为固守某一原则。这正如在《笔记》中描写一夭逝女子,一百年心如枯井,以贞魂自视,遇一别业太学生却为其所动,如此情状,也是人情人性的因素。纪昀虽然不时表明“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但又处处可见作者为改嫁寡妇鸣屈辨理,亦可谓用心良苦。作为身居要职的正统文人,能够认识到人情人性的不可遏制,认识到理学所倡导的道德原则与生活本身逻辑的某些悖谬,客观的暴露,恰恰是对所谓“天理”弊端的揭示,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整个《笔记》中,涉及道学家(或言讲学家)者流有四十余篇,而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作者肯定的正面形象,似乎皆是嘻笑怒骂,恣意鞭挞,故有人说纪昀与戴震同道。鲁迅评价纪昀时亦指出:“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
《滦阳消夏录》(一)记某老学究的亡友能从屋上光芒见所读之书及胸中学问。老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亡友评道:“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言罢大笑而去。《滦阳消夏录》(四)载:“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辨论天性,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纪昀在小说中嘲讽陋儒的夸夸其谈,聚讼不休;攻击迂儒的苛责而不知变通;鞭挞腐儒的龌龊之行,等等。虽然难见深度,但从思想上看,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然而,纪昀所反,又并非整个理学。他厌恶陈词滥调的理学信徒,但对理学的根本信条少见否定。用其学生汪德钺的话或可作些解释:“平生讲学,不空持心性之谈,人以为异于宋儒,不知其牖民于善,坊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于洙泗。即偶为笔记也,以为中人以下,不尽可与庄语,于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铎之声。乍视之,若言奇言怪;细核之,无非寓惩劝以发人深省者。”[2]
由此可知,纪昀之小说虽取材于街谈巷议,且自认为是消遣时日而无关于著述,但绝非是无关宏旨的琐事,我们从作品中的一点灵性,一种情绪,无不可以见到纪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热情。虽然他不如蒲松龄在谈狐说鬼之中寄寓“孤愤”,但他在“不乖于风教”的微妙心态下,寄寓了劝惩之意,而从这劝惩之中,又可见到士大夫文人积极的一面。
二
人们多认为纪昀对待小说的观念是保守落后的,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但细细考察其于小说创作的策略,我们既可看到作家独领风骚的艺术个性,亦或对当代小说创作有所裨益。
首先,叙议相生的策略,使作品之意义要旨释然,不必苦索。在纪昀《笔记》五种之中,或先叙后议,或先议后叙,或夹叙夹议。应当说,小说创作是以形象取胜,而非以说教见长,当是审美对象——审美感受,在感染之中体现其魅力,而纪昀“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3]处处板着面孔说教训戒,即使生动的故事,也有索然寡味之感。但是,其论说亦不乏警策、妙趣,在“资谈助”的审美需要中,一洗伪饰之态,令人莞尔一笑。再则,作品之议论,盖受史家职责之影响。史家著书,必褒贬善恶,孰是孰非,态度鲜明,我们所见之史书“太史公曰”、“臣光曰”等莫不如是。这也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文人创作古典小说,所见唐人传奇篇末喜发议论、《聊斋》某些篇目末尾也见“异史氏曰”。只是纪昀把这种影响发展到了极至,使作品外贴伦理教条,议论成份过多,就有了太浓的迂腐气,乃至喧宾夺主。但其直接劝戒,以理喻人的追求,又比《聊斋》中如《蛇人》、《犬奸》、《役鬼》等大量的纯为“志异”作品可取得多。
其次,“事皆摭实”的写实态度。对此,纪昀在总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中明确表示: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观纪昀《提要》,在子部中著录小说123部,存目196部,共计319部。且不说《三国》、《水浒》未收,即是相去不远、影响很大的《聊斋》也视而不见。重要原因是在于《聊斋》一类“诬谩失真”,“妖妄荧听”,且“猥鄙荒诞,徒乱耳目”,当然黜而不载。不能诬谩失真自然也是纪昀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要劝惩,首先要让人可信。述自身见闻,便言之凿凿;转述他人见闻,便著录某公所言,且标明故事发生于某朝某年某月某日。首尾齐全,因果必备。即使是众多的谈鬼说怪作品,也让人感到斑斑可考。严谨的学究气于小说作品中亦可见之。这种写实的态度,限制了纪昀小说的成就及其影响。追求作品不诬谩失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真,应是属于艺术的真,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不是对生活的实录,其魅力恰恰在于经过提炼后与现实的那种似可企及的距离感。纪昀小说力求靠事实去取得真实性,正是少掉了凝炼与距离感。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经过创作及理论总结的长足发展,到纪昀时,虚构已为众多作家所认同,但纪昀刻意以史家角度抵牾虚构,并从小说情节考证的角度提小说是叙事体,叙述方式取决于叙述者身份,叙述者身份就决定了小说情节可信与否,认为《聊斋》所写“媟狎之态”以及“燕昵之词”又非作者所见当不足信。所以他只写事状而避去心理活动和人物密语。这似乎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但这正是纪昀尚质小说创作中在写实追求方面形而上的思维表现。
纪昀在作品中忽略对情节的构想、环境的设置以及艺术形象的生动。然而他注重写实中的简约而准确,自然而又妙远,虽然缺少了静态的细腻描写,但其简淡数言,风致无穷,颇有雅室文人的神来之笔,自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面。兹举例可见:
……兰台言鬼之形状:仍如人,惟目直视,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与人稍殊。质如烟雾,望之依稀似人影。侧视之全体皆见;正视之则似半身入墙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苍,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则或瑟缩匿墙隅。……(《滦阳续录》一)对鬼之情状叙述可谓简言而栩栩如生,这其中当包含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只是作者没有以繁荣的藻饰去扬丽铺张,而是理质黜华,机趣尚在。特别是其中颇多作品诸如槐家镇马氏家宅之变异最后点出为老儒贿盗而为之、沧州无赖吕四淫人而终至妻为人所淫等等,经意点染而令人绝倒。其中虽有训导与教诲,但那一分睿智含蕴与机趣诙谐,令人深长思之,却又非实录可比。这或许是纪昀尚质追求中可采可取的一面。
再次,信笔为之,不拘一格的创作方法。
纪昀整个小说作品充分利用了中国古典文言小说在“小”之中表达的自由与洒脱。或追寻见闻(《滦阳消夏录》),或补缀旧闻(《如是我闻》),或置朋友异闻(《槐西杂志》),或时作杂记(《滦阳续录》)等等,即兴遣怀,细大不捐而包罗万象。让读者品味其“姑妄听之”的信手之作,从中去获取劝戒的教益,而不注重创作的一体化,张弛自如。与《聊斋》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相较,蒲松龄虽言是“妄续《幽冥之录》”,但实是“成孤愤之书”。[4]其所作小说是“永托旷怀”,所谓之借酒浇愁。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使蒲松龄在小说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在小说的创作之中必然注意“节成体载”,经营为世人所不容易理解的隐衷而泄愤寄慨,难怪蒲松龄自身也感叹在文言小说创作道路上的曲高和寡。另一方面,蒲松龄之创作如此,使中国古典小说“游心寓目”的美感享乐就要淡出的多。而纪昀创作是“文史以外无自娱”的笔墨游戏,不拘一格,即兴式的叙写中不乏文化意味。就其作品而论,虽然不求完整,不求巨制宏传,但挥洒自如,种种风致,猎收其中,不作端庄而以灵隽谐谑见之。清淡高远的意趣自由内现,又能让读者获得“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迭”[5]的美感娱悦,这又甚为可取。
三
纪昀比蒲松龄晚出,以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力诋蒲松龄。后人在评价二人时,对蒲松龄多溢美之词,而对纪昀则有更多的苛求与责难。实际上,纪昀与蒲松龄在文言小说创作上体现了中国古典文言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美学追求,都自有其合理性。
从关于“小说”的早期理论形态上看,就埋藏了上述分野的必然性因素。早期的小说,是“丛残小语”,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人们苦心地将它与社会政治作用突出的“史”相联系,这正如词曲在其兴起的过程中作为“诗余”对待一样,小说也就成为了“史补”、“史遗”。文人即使投入精力志怪志人,有荒诞不经的虚构,但都必称为著史。干宝《晋纪》是“咸推良史”,《搜神记》称“鬼之董狐”、“鬼之良史”,即或是唐传奇也称是“摭实”。正统的史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列小说入史部。影响所及,必然导致创作上对现实世界中因果片断的剪辑,对小说价值的认识也就限制在“补史之遗”,为正史“拾遗补阙”,“与史传相掺”等观念上。
若小说创作不仅仅停留在尚质的基础上,作史书的附庸,要摆脱这种窘境而独立,必然谋求艺术上的开拓与创新。这一时期的真正到来是“唐人有意为小说”。“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6]即情节的曲折,细节的委婉,辞采的华美开始上升为一种小说美学追求。寓意化、象征化、理想化为作家采用,虚构、夸张、想象、渲染等手段也普遍运用于作品,特别是对艺术形象的多角度描写,艺术魅力得以加强,于是脱离“丛残小语”而“篇幅漫长,记叙委曲”,在功能上也由因果报应的以理喻人而上升为具有情感特征的以情感人,从而使作品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对“史补”创作的突破,让小说锐意地走进了“文学”的正道。
有了小说创作认识的发展,并不等于述实尚质影响的消失。实际上,两种观念、两种不同的创作一直潜滋暗长,影响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或交融,或对峙,文言的、白话的、短篇的、长篇的,都是如此。例如,即使是在新兴说话艺术上产生的白话小说,虽然注重了情节、形象诸要素,有以情感人的审美特征,但前面的入话,后面的应证,仍然是从因果说法中以理喻人,尚质的特征并未消失。
一般讲,“史补”观念较重者,往往不以小说为正道,而是以“消闲自娱”为创作动机。常在诗文著述之余,公事之暇,游戏笔墨,戏作小说。这种情况虽然从小说出现时便存在,但在清代,却出现了以纪昀为龙头的群起相从之势。纪昀自称在“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昼长无事,追录见闻”著《滦阳消夏录》,“再掌乌台”,“公余退食”之暇著《槐西杂志》。王士祯于暇日与客“相与论文章流别,晰经史疑义”,“或酒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嗢噱”写成《池北偶谈·谈异》。袁枚在《子不语》各卷之首皆言“戏编”,并与“饮酒、度曲、樗蒲”相提并论。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也推崇“饭后茶余,尚可资以解闷”。以上情状,都可见到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致,书生积习十足的博雅之才。
受到真正文学意义小说观念影响较重者,则能视小说为正道,并且把小说与诗文同视为可以负载主体生命意识的工具或酒杯。因而在创作之中有着巨大的创作动力乃至献身精神,投入精力,用心思才学去研炼揣磨,这就使得小说创作与消闲的率意之行大异其趣。即创作上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沉淀,而且要有艺术上的充分准备。蒲松龄的“孤愤”之书自不待言,宣鼎“以无可奈何之身,当无可奈何之境,未能己之,奋笔直书”成《夜雨秋灯录》,王韬“诚壹哀痛悴婉笃芬芳之情,一寓之于书成《淞隐漫录》”等等,莫不如是。这样作品就不是只言片语,也非消闲中的机趣,而是由作家—社会多层面的现实因素构成,作品的功用就不是简单的劝戒,而是一种审美。
同样是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在观念上和创作上显出如此大的差异,与作家不同的生活体验有非常大的关系。
前者,作家大多属于仕途较顺的上层官僚文人。《池北偶谈》的著者王士祯是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子不语》作者袁枚是乾隆进士,虽然壮年辞官,但自筑随园,生活悠闲享乐,几达半世纪之久;纪昀更是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也只有他们,才能在诗文著述之暇,公事之余而戏作小说,以为消遣,同时,他们作为正统文人,劝戒则为其追求,在消闲之中又免不了板起面孔说教。
后者,多是仕途不顺或官阶较低者,中国文人传统的“发愤著书”在他们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蒲松龄一生地位卑微,生计艰辛,于是乎“子夜荧荧,灯昏欲蕊,潇斋瑟瑟,案冷如冰,集夜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7]虽炽昌虽学究天人,但仅客游幕府,为人作司笔,在“古稀已届,两耳塞绵”时,转而“力尽情坚”于小说创作,著《客窗闲话》。宣鼎为人作幕宾,后靠卖画为生,“归则僵卧,不语亦不哭”,转而奋笔直书成小说《夜雨秋灯录》。长期的生活积累成为创作的原动力,小说就非兴之所至,而是凝结为一种生命现象。差异的出现也就是势所必然。
综上所述,人们在认识中国古典文言小说时常分为藻绘与尚质两派,蒲松龄与纪昀各为其代表。但是,如果排除褒贬分析,我们应当认识到他们的出现与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也都有肯定与借鉴之处。
其二,纪昀的人生体验影响到了他对待小说的观念及创作,其出是在强大的激进人文思潮对传统文化体系的冲击之后,凝结于小说作品中的思想并不能与其落伍的乃至保守的小说观念划等号。
注释:
[1]《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二“纪昀传”
[2]汪德钺《四一居士文钞》卷四
[3]盛时彦为《姑妄听之》所作“跋”
[4][7]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志》
[5]毛晋《西京杂记·跋》
[6]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