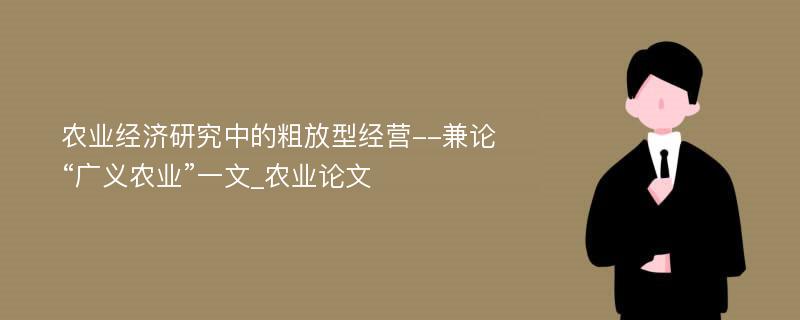
农业经济研究“粗放经营”的例证——对《最广义农业》一文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经营论文,农业论文,例证论文,广义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曾以讽刺的口吻向学术界公开指出,坚持“农业基础论(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属于经济学研究中的“粗放经营”(注:《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11月28日《经济理论研究中“粗放经营”》。)最近,笔者在《理论月刊》杂志1998年第4 期上读到了陈文科先生的《最广义农业: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基础论”的依据》一文(简称《最广义农业》),不客气地说,该文就是“粗放经营”“农业基础论”的典型例证。对此文,笔者谈点个人看法。
先从最明显的漏洞说起。《最广义农业》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一个动态概念”。在这里,“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由“农业”、“国民经济基础”两个概念加上判断词“是”构成的理论判断,所以不能叫做概念。即使是作者行文时发生了笔误,但读一读这一部分的内容,常识性错误也充斥于其中。其一,《最广义农业》中写到,以动植物生产为主的农业是原始农业乃至传统农业生产水平阶段的国民经济的基础。这说明作者对国民经济这个概念也没有完全理解。国民经济是近代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中才使用的概念,是同复杂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向自然索取(严格地说不属于经济活动)的原始农业阶段自不必说,就是在传统农业阶段,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几乎全是农业,生产者基本上自给自足,哪有什么国民经济而言?如果说农业就是国民经济的全部,那么再谈什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成了农业是农业的基础了。而且,在传统农业阶段,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也就没有国民的概念。既然没有国民,何来国民经济?欧洲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国民这个概念才出现了。这以后才可以说有国民经济。其二,《最广义农业》说“人们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至少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对照下文的阐述,这句话表述为“人们对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至少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可能更符合作者的本意。这姑且不论。这所谓的三个认识阶段,上面已经谈过了,第一个认识阶段就违反了常识。其三,《最广义农业》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含义不可能一成不变。即使“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按照科学研究的惯例,对于变化了的事物,要用新的概念去概括,用新的判断去阐述,进而构成新的逻辑体系。比如,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便产生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判断,而不再沿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旧说,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是不明白,“《最广义农业》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有发展变化,另一方面还要把“农业基础论”当成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呢?
《最广义农业》声称马克思有一个“最广义农业”观。寻着作者提供的注释,笔者查阅了《资本论》原文,结论是:马克思是在谈地租问题时,用了“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注:《资本论》第3卷,1997年版,第715页。)这个提法,作者把劳动一词去掉, 就说马克思使用了“最广义农业”这个概念。笔者认真学习《资本论》这部分内容,结论同《最广义农业》的看法大相径庭。马克思使用“纯农业劳动”、“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这些提法,不但不是要造出一个什么“最广义农业”观,恰恰相反,他是为了使读者在地租问题上理解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理论时,不要把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混淆在一起。马克思的理论是:工业劳动中的必要劳动在使用价值上也要表现为农产品,所以可以当作“最广义的农业劳动”来理解,而不是要求读者把已经分离出去的工业部门再拉回农业部门内,从而把所有与农业相关的经济部门都当作“最广义农业”部门来看待。稍微认真一点的读者都能领会到,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在谈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问题,丝毫没有阐述农业部门与其它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意思。而“农业基础论”不论正确与否,其理论功能在于表述农业与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则是明白无误的。到此来找“农业基础论”的理论根据,实在是误入歧途。作者自己认为存在一个“最广义农业”概念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在《资本论》中生拉硬扯。
但是,笔者不同意《最广义农业》中阐述的“最广义农业”观。按照作者的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注:《资本论》第1卷,1997年版,第551—552页。) 一段话是在肯定农工一体化,这未免过于牵强了。如果读者顺着这段话把马克思的论述读完,就会发现马克思对于作者所钟情的“联合”,从土地的掠夺性经营和农村劳动者受剥夺方面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实际上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者制造农工商一体化的理论根据,他是在谈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表现在雇佣劳动者代替传统农民上。笔者也是赞成农工(商)一体化的,但不一定非要到马克思那里找根据。而且,农工一体化并不是像《最广义农业》所主张的那样,把农业的产前、产后等非农产业部门统统纳入农业部门,构成一个所谓的“最广义农业”,以便农业与“二次、三次产业平起平坐”。农工一体化是在企业层次上的生产力组织问题。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正大集团,既搞鸡的饲养(农业),又搞鸡饲料的加工(工业),还要搞产品销售(商业)。企业跨行业经营,并不等于把行业界限抹煞掉。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当代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讲过农业作为一个部门要比其它产业部门矮三分,也就是没有讲过农业资本要比其它产业资本少得利润的规律。各个产业都处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某个行业受到歧视,肯定是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偏差。试图以最广义农业观来论证“农业基础论”,为农业争点利益,却给人以缘木求鱼之感。
《最广义农业》中声称,按“最广义农业”观,可以改变农业的弱质性,而使之成为强质产业,并且使农业成为获利最多、最有前途的产业。这说明作者同另外一些知名人士一样,对农产品尤其是主要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需求的收入弹性等市场农业概念不甚了了(注:参见《理论前沿》杂志1997年第18期《农业是弱质产业不是传统观念》。)。山东省寿光的农业产业化不能说发展水平不高吧,但据中央党校学者的调查,1997年寿光农民的纯收入仅仅比上年增加1.74%,1998年6 月份以来菜农普遍发生亏损现象,基本原因是蔬菜生产过剩。按我国目前流行的说法,日本农协领导农民搞农业产业化(但人家不用这类新名词)的水平也不算低吧,但据笔者一年半的实地考察,说日本农业是个风险小、获利大的经济部门,恐怕得不到日本农民、学者、政府的首肯。
令人费解的是,《最广义农业》主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开头和结尾又都言之凿凿地讲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的基础”同“国民经济的基础”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是相同的吗?同是“主席”这个概念,在其前面加上“国家”和“自治区”的限定之后,两个主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吗?
8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关于“农业基础论”是有一个论证体系的(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216—217页。)。但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基础论”的坚持者们越来越感到那个体系不能再用了,于是,便以印度学者的“农业贡献论”来论证“农业基础论”。印度学者是否同意中国的“农业基础论”不得而知。但在笔者看来,从产品、要素、市场、外汇等几个方面来论证农业的重要性或地位,实在也算不上什么高明。除了农业之外,莫非其它产业就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而且对照一下“农业贡献论”同原来的那个“农业基础论”论证体系,也不过是大同小异。“农业贡献论”救不了“农业基础论”。
笔者揣度,“农业基础论”的坚持者在学术上“粗放经营”,似乎是由于存有一份担心:否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重要性还怎么讲?农业的地位往哪里摆?这份担心多少同改革中一些人担心不讲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就搞不成社会主义相类似。关心社会主义当然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不知道恰恰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僵死的计划经济、难以全部做到的按劳分配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新标准。那些还在坚持“农业基础论”的人士可能还不知道,恰恰是这个理论几十年来一直把农业置于受剥夺的地位上。如果不是这个理论,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业的理论是什么?
据笔者考证,“农业基础论”是60年代初,毛泽东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把它论证为规律,是那个时代学术屈从于政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遗憾的是至今还有那么多的学者,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进军号在中国大地上吹响以后,具体地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以后, 邓小平再也没有讲过“农业基础论”。在概括马克思与邓小平关于农业理论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农业根本论”取代“农业基础论”的学术主张。(注:参见《理论前沿》杂志1998年第13期《论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所谓“农业根本论”,其完整的表述是: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农业根本论”与“农业基础论”的区别,不在于“根本”与“基础”的用词不同,在词典中这两个词的词义大体相同,而在于前面的限定词不同。邓小平讲过“农业是根本,不要忘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52、307页。)故而以“农业根本论”命名,取代“农业基础论”。
邓小平要求我们,学理论要管用。笔者认为,“农业根本论”在两点上是管用的。
第一,“农业根本论”要求国家考虑农业问题,首先不是着眼于经济,而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从国民经济的层次上看待农业的视角矮小问题。国家必须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角度看待农业问题,但并不等于要求农户也同国家一样看待农业。正常情况下,农户经营农业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是基于利益的考虑。所以,政府要获得自身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必须满足农户经营农业的合理利益要求。因此,“农业根本论”找到了政府保护农业的双方利益基点。
第二,打开了如何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思维空间。“农业基础论”的实质虽然是剥夺农业,但字面上却是要求人们相信“农业上去了,国民经济就能上去”的所谓道理。然而,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道理的。硬是按着这个方针指导经济发展,就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畸型发展现象。关于什么产业在现代经济中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52、307页。)显然,这段话中的“从何着手”、“起点”同国民经济基础的本来含义是完全吻合的,同时也说明邓小平在关于何为国民经济的问题上认真地借鉴了外国成功经验。1989年6 月邓小平又说:“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52、307页。)这里的“基础”也显然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是由与农业明确区分开的工业部门构成的,故称基础工业。由“宁肯欠债”一语也足见邓小平加强国民经济基础的决心。邓小平的这些理论观点本来都是明明白白的,但由于过时的农业基础论仍然处于被人们似是而非地认同状态,以致于常常在同一本书、同一个版面、有时甚至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说交通运输等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让人莫名其妙。有人把这里的基础产业理解成加工工业的基础产业,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难道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商业等等就不依赖交通、能源、通讯?就不以这些产业为基础?1997年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及政策选择——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地区分了农业与基础产业概念,令人欣喜。更有广大农民早就知道“要致富,先修路”的道路。总而言之,邓小平的理论是:在中国,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就要把农业农村稳定和发展起来;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和农村经济)要搞上去,就要先把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搞起来。从长远看,解决农业问题要靠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
责任编辑注:“最广义农业: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基础论’的依据”一文转载于本专题1998年第6期88页。
标签:农业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