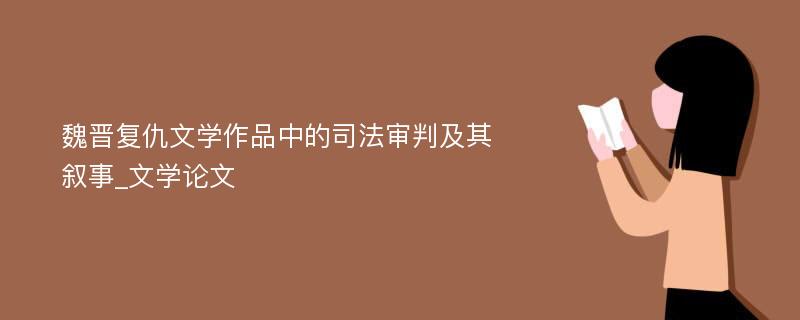
魏晋复仇文学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及其叙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文学作品论文,司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6)02-0045-07 复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由“父兄之仇”、“兄弟之仇”的血亲复仇到“交游之仇”、“弑君之仇”的非血缘关系的复仇故事,在各类史书中有淋漓尽致的记叙。魏晋时期,由于律法制度的进一步专门规约,复仇行为受到一定局限,但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仍有大量的以复仇为主题的叙写。 一、魏晋复仇司法审判的文学叙写 表面上,在一个有相关法律制度的社会,复仇行为与对复仇者的司法审判从意愿上并不趋同,采取复仇行为意味着置司法审判于不顾,审判则是为了对复仇行为进行以法律为准的裁决。然而,在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复仇与司法审判构成了一种相消相长的特殊互补形式,复仇者复仇的坚定意志与其复仇得以实现后所受司法审判的过程,往往都成为作品描绘的重心。以下将其基本模式分为两类进行探讨: 第一,复仇后的审判模式。 这种模式的创作内容大多有本事可考,多写前代之人、前代之事,创作手段上对音乐仍有一定依赖。 曹植《精微篇》中有苏来卿因复父仇受刑而亡与女休复仇得赦的叙写。 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 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1](P332) 左延年《秦女休行》写主人公女休“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杀死仇人,成功复仇。其后,诗歌对其复仇行为审判、服刑及结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写: 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辞:“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辞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2](卷六十一,P886)女休对自己复仇行为的申辩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复仇造成的生活影响。对于女休,杀人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她复仇前以“燕王妇”身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复仇后成“诏狱囚”,过着“无领襦”的艰难日子。倘若不复仇,就不会有如此落差。其二,不得已而复仇。女休复仇,是因为家族中再无人能承担如此重任,兄长只知郁闷忧愁,小弟浑噩无知,女休责无旁贷。其三,复仇无悔。虽然有上述落差与困境,女休并未选择放弃,而是更进一步坚定了复仇的决心,“为宗报仇,死不疑”。 与左延年所作不同,傅玄《秦女休行》一开始就着力强调仇之深、仇人与复仇者之间实力的强弱反差:“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以至于主人公为复仇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这种实力强弱对比下的复仇过程相当惨烈,傅玄在描写了复仇过程之后,也集中描写了审判过程: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今仇身以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法,义不苟活隳旧章。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2](卷六十一,P887)与左延年诗相比,傅玄《秦女休行》不但专写复仇者的申辩,还特地叙写了执法官吏听闻事件过程与主人公申辩后的态度和举动。前人多以傅玄诗模拟左延年诗,所歌咏为一事,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 左延年与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种传说——故事诗——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题”(Motif)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这个故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经是后期状态了,已是“义声驰雍良”以后的民间版本了。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人与自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3](P66)胡适正是以这两首诗中官吏对复仇者的态度与行为以及对复仇事件的审判结果作为诗所歌咏内容本事的判断标准之一。 从文学叙写与创作的角度,晋代类似的女子复仇故事流传很广,皇甫谧作《列女传》,将娥亲复仇的审判、执法官员的感动、娥亲欲伏法而不得的过程叙写得更为详细。然而,这些女子复仇的故事仅见于文艺作品的转述叙写,在魏晋史册中却几乎找不到。 第二,通过审判实现复仇的模式。 当复仇行动由于各种缘由无法实现时,司法审判又会成为实现复仇的中介。在这一叙写模式中,往往是复仇者受冤屈——包括在前期审判过程中受冤屈——从而引发带有复仇性质的申诉,最终实现正义审判,平复冤仇。魏晋时期这类文学叙写的着力点往往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终极审判的正义性,其二是复仇目标的转移。 干宝《搜神记》载东海孝妇故事: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旛。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旙竹而上极标,又缘旛而下云。”[4](卷十一,P421)故事中东海孝妇蒙冤,前任太守作为执法者未能伸张正义是极其关键的因素,因此需要进行一次具有正义性质的审判,也即后任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这虽然不是当事人本人对簿公堂,但后任太守以执法人的身份给予了一个正义的认证,从而取得了与审判同等效力的结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复仇并不是指向前任太守或某一个人,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向性,因此复杂方式为“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复仇成功,则一切回归常态,“天立雨,岁大熟”。此故事《汉书·于定国传》有记载,此处虽也出现“于公”,但侧重角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汉书》中,为了表现于定国的正义明断,故事的主人公是于定国;此处则以东海孝妇为主人公,又加入了“长老传云”的一段记载,进一步突出了周青“冤”的成分。这也是汉代史传文学中的复仇与魏晋时期诗歌小说类文学作品中的复仇的主要区别之一。 同样,谢承《后汉书·周敞传》对苏娥故事的记载非常简单:“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财物,埋置楼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此事《列异传》中记载略同。两处记载中周敞“杀寿”是执法官吏主动审理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在《搜神记》卷十六则变成了女主人公复仇的故事: 汉,九江何(周)敞,……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4](P443)通过细节叙写,已由前书所载的一件普通再审案例变为女子借执法官审判的复仇案:加入了女子在请求正义审判时的辩辞,着力刻画了周敞在获得主要案情后的验证过程,详细记载了案件审理的结果。足见,《搜神记》对这一故事进行的加工,主要集中于以文学描绘方式突出法律因素。 除了亲属复仇并受到审判外,魏晋时期复仇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执法官员的明断正义实现怨仇报复,而复仇方式也由手刃仇家转化为多元复仇。 当执法的官员能伸张正义,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平复冤屈,同时也就完成了复仇。如《列异传》载魏公子无忌审鹞杀鸠事[5](P12),《搜神记》卷十一载严遵闻道傍女子哭声不哀事[4](P423)。当执法官员不能伸张正义,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出现如《搜神记》卷一载汉阴生“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又械欲杀之”的情形,就会引发“洒之者家,屋室自坏,杀十数人”的复仇转移[4](P369),即便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复仇,也会通过天道获得正义支持。文学作品中还会出现主张正义的天或伸张正义的侠客来完成复仇,如《搜神记》卷二谢尚绝后就是因天道进行复仇式审判的结果[4](P377)。 由上述不难发现,魏晋时期复仇主题文学作品中所写审判的实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存有矛盾:一方面,司法审判是对主人公复杂进行以律法为依据的处罚——从效果上,往往反衬出主人公的复仇被宽恕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是以律法为依据的审判,执法者又在帮助复仇者完成复仇行动,也即复仇行动由于各种缘由无法实现时,司法审判能实现正义复仇。 二、魏晋复仇文学中的司法审判依据 魏晋复仇文学中,复仇往往与执法官员的审判裁决相联系,这与当时对复仇的频繁立法以及司法审理程序有关。 复仇杀人曾经是“在没有统一且强有力的公权力维持社会和平和秩序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和平的根本制度”[6](P61)。汉刘邦“约法三章”之一“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条[7](高祖本纪,P362),汉宣帝、成帝时对该条年龄的细化①,东汉桓谭上书:“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8](桓谭传,P958),都未将复仇杀人专列,复仇杀人的情形是否一定就包含于上述“杀人者”“相伤杀者”中,也有待商榷。《九朝律考》言:“汉时官不忌报仇,民家皆高楼鼓其上,有急即上楼击鼓,以告邑里,令救助。”[9](P107)认为汉代对复私仇并无任何法律层面的限制。 汉末“魏武重法术,天下贵刑名”,人们对律法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曹操《拜高柔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10](魏书·高柔传,P683)将“礼”与“刑”分立并列,实则强调并提升了“刑”的地位。王粲《难钟荀太平论》:“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谓之无者,‘尽信书’之谓也。”[11](P76)直指礼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性。人们不再一味强调礼至上,相反,开始关注法治的重要性。 明确禁止复仇的,当属曹氏父子。建安十年,曹操破袁谭、平冀州后,明确发出复仇禁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10](魏书·武帝纪,P27)复仇与厚葬本是大家族表现凝聚力的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曹操一并禁止。曹丕曾下《禁复仇诏》: 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残害者。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仇。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当相亲爱,养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11](P29)《太平御览·仇讐》载: 魏文帝《杂诏》曰: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杀害,昔贾复、寇询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12](P2208)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10](魏书·文帝纪,P82)曹丕所提及的汉代“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的复仇事件,都是皇帝权威裁断煎阻止复仇行为。“贾复、寇询”事虽然已构成“至怀手剑之忿”的复仇倾向,但结果却是“和”而不复仇。或因第三方施压放弃复仇,或因第三方协调而和解,这是当时避免复仇的典型处理方式。基于此,曹丕认为“宿有仇怨”其实都可以化解,实在不能通过化解方式避免的蓄意复仇行为,则可以用最为严厉的刑罚手段——“族之”——定罪,通过这种强制要求的形式进一步限制复仇。下《禁复仇诏》的第二年(黄初五年),曹丕又下《轻刑诏》,提出“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对比这两部有关刑罚的诏书,前者的目的在于“重刑”,后者的目的在于“轻刑”,貌似冲突,实则反映出有“慕通达”之称的曹丕虽然极力维护自己“圣”君的形象,但在复仇一事上,处罚不减轻反而加重,其通过法治杜绝复私仇的决心可窥一斑。 曹操和曹丕只是以通告方式宣布对复仇行为量刑定罪,至魏明帝曹睿则令人修改律法,制定《魏律》,在序言中正式提出复仇杀人的法律责任: 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13](刑法,P925)这可以算是对曹丕诏书的补充,非常明晰地规定了可以复仇与不可复仇的具体条件。允许复仇的条件为:其一,复仇前的命案是“贼斗”所致。“两讼相趣谓之斗”,“无变斩击谓之贼”[13](刑法,P928)。其产生的原因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等毫不相关。其二,有“劾”的过程。即凶犯已被告发于官,命案已经进入了法律审理的范围。其三,因“劾”而“亡”。凶犯不但没有自首情节,听闻官方通缉的风声后,反而逃亡。足见,从律法角度,这有三重罪:故意杀人、不从官令、出逃。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容许复仇。所谓“依古义”,也包括依《公羊传·定公四年》所言:“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逸,古之道也。”[14](P503)相应地,不允许复仇的前提为:其一,已经过法律裁判,明确认定应当赦免宽刑的;其二,过失杀人。二者具备其一,就不可再追究复仇。此时并不考虑“弗共戴天”或“不反兵”的礼之“古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人们之间再形成相互残害、复仇不已的恶性循环。这无疑从某种角度将律法的地位提升到了“古义”之上,体现出明显的法治精神。 《宋书》载,宋元嘉年间,任司徒左长史的傅隆对一民间案件做出初步审理意见时,曾提及“旧令”: 隆议之曰:“…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15](傅隆传,P1550)一般认为,此处所依据的“旧令”当为《晋律》内容。则“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而且“同籍亲近”可以“相随”,则是对复仇杀人“移乡避仇”的处理方式。这样既照顾了礼,又从客观条件上维护了律法的执行,对禁止复仇而言,无疑是一个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时的北方十六国也曾有类似禁令,姚苌统治前秦,曾担心战争时期人们因复私仇形成内乱,下书禁止:“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13](姚苌传,P2970) 这些律法禁令的颁发对两汉以来的复仇风气起到了明显的约束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期”,“应当视为历朝历代不断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16]。 魏晋时期不仅从立法角度明确禁止复仇,还进行相应的宣传,使律令人皆共知。晋武帝司马炎就曾在新律法颁布以后“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13](刑法,P928)。 除专门的司法组织外,当时中书省、尚书省官吏也兼管刑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都由地方官兼任,因此当时的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可以进行司法审判工作,复仇的民事案件的审判也是由乡县、郡州至朝廷依次上报裁决。 若遇皇帝临讼,皇帝的裁决便超越前期所有审判结果,成为最终审决。魏晋时期皇帝听讼的事很多,如曹魏黄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辨得失。”[10](魏书·文帝纪,P84)魏明帝曹睿于太和三年“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17](P146)。晋武帝司马炎颁布《泰始律》后,于泰始四年十二月“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又于五年春正月、十年六月分别“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13](武帝纪,P58)。桓玄称帝后也“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13](桓玄传,P2596)。 三、魏晋复仇文学中的司法审判叙写特点 其一,以现世流行的书写形式叙写非现世的题材。 由于魏晋时期对复私仇进行了明确而严格的律法规约,社会上属于民间复私仇的实例与前代相比少之又少,人们所谈论的有关复仇话题自然而然地逐渐聚焦于前朝旧事,这些古事一般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经过民间的口头加工,然后才成为文人笔下的文学创作素材。曹植《精微篇》写了7则故事,其中4则为先秦故事,2则为西汉故事,当代学界多以为女休事“极可能亦西汉事”[18](P154)。郭茂倩《乐府诗集》:“《秦女休行》,左延年辞,大略言女休为燕王妇,为宗报仇,杀人都市,虽被囚系,终以赦宥,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庞氏有烈妇’,亦言杀人抱怨,以烈义称,与古词义同而事异。”[2](卷六十一,P88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以为左延年所作也是“借古题以咏古事之类”,傅玄所作庞娥事“实为汉末魏晋间最流行之故事”[19](P180)。葛晓音《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新探》认为左延年诗本事当为顺帝阳嘉时的缑玉复仇事[20]。陶元珍《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认为傅玄诗本事当为酒泉庞涓母赵娥事[21]。干宝整理《搜神记》序言“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若使采访近世之事”[4](原序,P366)。可见,前人著作和时人采集是《搜神记》故事的主要来源,前文中出现的于公、周敞、严遵等,便是前朝古事改编的痕迹。 虽然所写素材为前朝旧事,却又采用在当时极为流行的文体叙写。沈约《宋书·乐志》以为曹植《精微篇》当《关东有贤女》,应归入《汉鼙舞歌》之一。曹植自己说这是“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②。左延年,李白拟《秦女休行》称其为魏协律都尉,《三国志·魏书》载其人“妙于音,咸善郑声,其好古存正莫及(杜)夔”[10](杜夔传,P807),他曾于魏黄初间“以新声被宠”,魏明帝曹睿时期颇受重用,太和年间改制杜夔所整理古曲,“更自作声节”,使“其名虽存,而声实异”[13](乐志,P684)。傅玄,晋初重臣,曾改制晋初雅乐,其乐府诗创作多拘于模拟,但也不乏新篇,《秦女休行》便是一例。魏晋小说流行,“志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多以短篇叙神怪之事,《列异传》、《搜神记》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 可见,魏晋复仇主题文学作品从选材上以古事为主要叙写对象,在创作形式上则往往采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体裁,也即以新辞书古事,其主要原因是人们欲借此寄托现世复仇的愿望。古事的主人公及其结局为魏晋时人熟知,而具体的过程却有可能少为人知。魏晋时期有关复仇的文学作品着力强调司法审判的过程,正是当时社会对复仇有所规约有所限制的时代特征的体现。 其二,注重塑造“知法”的复仇主人公形象。 成功复仇的主人公对自身复仇行为的后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左延年笔下的女休“明知杀人当死”,傅玄笔下的女休言“杀人当伏法”,皇甫谧笔下的娥亲言:“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主人公并非过失杀人或无相关知识,而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行为后果的前提下,故意杀人。但在复仇后,又往往归于理性,能依照法律程序报官处理。 主人公们大都成功复仇并受到了法律审判,虽然审判后受刑与恕刑的结果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专门的司法机构或最高审判权威得出结果。复仇后主人公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左延年笔下的女休复仇后西行归家,而傅玄笔下的女休则是“直造县门”,两人面对法律审判的时候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申辩。《列女传》中的娥亲不但报官,还强调了自己对朝廷法律的信任:“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乞得归法,以全国体。虽复万死,于娥亲毕足,不敢贪生为明廷负也。”坚信即便自己被处以极刑,朝廷法律也是绝对公正公平的,自己不会因为个体的生命而损害朝廷法律的威严。 主人公受到委屈,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法律去处理,《搜神记》中那些蒙冤的主人公,即便身亡,也要寻找到清正的官吏,以企图通过官方的明断是非,平复怨仇。他们基于清醒的认识,通过报官的方式寻找最终的解决途径,正是当时有律可循的反映。 其三,注重描绘司法审判过程的细节问题。 魏晋复仇文学注重描写审判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值得关注。 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下《禁复仇诏》,曹植《精微篇》明确点出创作时间为“黄初发和气”,黄初年号共计7年(公元220-226),当代学界多以此诗作于黄初六年[1](P332),二者相距极近。观曹丕诏书,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和解与严刑两个途径来制止社会中的复仇之风。观曹植《精微篇》中的两个复仇人物,显然是经过了筛选,除了勇气感人外,还特地突出对其行为的处理结果。诗中并未叙写两位女子复仇的具体过程,也未叙写二人明知杀人当死但死而无憾的坚决态度,相反,对于其伏法的处理结果,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调:苏来卿因复仇被处刑,名列“仙籍”;女休在已受刑伏法的过程中,在“白刃几在颈”时“逢赦书”,何其侥幸。 相比曹植笔下的人物,左延年《秦女休行》加入了更多的细节:首先,复仇不逃亡,诗中多次出现“西门”、“西上”、“西巷”等方位名词,就是刻意突出女休“明知杀人当死”,必然要接受法律处置,因此认为没有必要逃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而是选择归家。其次,“上山四五里”,“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强调进入司法审判过程的速度非常快,而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女休的态度是选择伏法,“死不疑”,而非逃避。再次,女休被审判时进行了申辩,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其复仇是否属于受刑范围。女休复仇前的争斗,是否为“贼斗杀人”,不得而知,但女休在受“劾”前后并无任何逃亡迹象,相反,却选择尽可能为自己申辩,通过审判程序为自己宽刑。既然这次复仇有准备、有预谋且非过误杀人,能救她的,只能是“赦书”,故而,女休最终被恕刑的结果,不只是与曹植的叙写达成统一,事实上也完全符合当时对复仇的立法与司法审判程序。 傅玄、皇甫谧生活时代相同、生活地域相近,故而在创作中以不同文体叙写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前代旧事,一诗一文。除所选题材相同,二者都极力刻画了仇敌的嚣张气焰,或曰“仇人暴且强”、“怨家如平常”,或曰“防备懈弛”、“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这与晋代律法对复仇相对宽松的审理方式又相应。仇人的彪悍与无所忌,恰恰是复仇者获得审判同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当时感动执法官员、获得广泛同情的基础。 《搜神记》中,对法律的审判程序也有非常明显的细节叙写,如卷六记载“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时,“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范虽然做出了初步判断,“此非人类,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但他也没有直接的决定权,于是“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卷十五写两家争复活的女子不决,“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强调了法律审判层层决断的特点。 可见,同样是对复仇事件的叙写,即便是同样的古事、同样的结果,由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具体的叙写过程和切入视角、细节处理方式也都有所不同,如曹植和左延年对女休这一主人公的叙写。作者叙写时着力铺叙和刻画之处,也是最能体现文学创作的时代之处。魏晋时期复仇主题文学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叙写,其实是当时立法与司法对复仇问题逐步完善规约历程的一个见证。在不修改前代结果的前提下,加入对司法审判过程的详细叙写,并非当下社会的实际反映,也并未刻意强调“礼”大于“法”,或突出“礼”向现有的立法内容、司法程序挑战,而恰恰是当时社会禁止复仇、复仇伏法现实的反映。 这些文学作品,不但不与当时的法律规范和具体执行过程相悖,相反,往往会得到朝廷的默许甚至支持,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这些作品以特定的细节处理方式,使其叙写的内容不但与当时的律法冲突甚少,相反,还能间接地起到宣传普及法律规定的作用。这或许可视为在一个有律法、很少有复仇事件的社会里复仇文学作品流传甚广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在一个有律法的社会中复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大都为官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原因。 注释: ①《汉书·宣帝纪》元康四年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汉书·刑法志》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1106页。 ②曹植《鼙舞诗序》:“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古曲,多谬誤。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房玄龄等《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