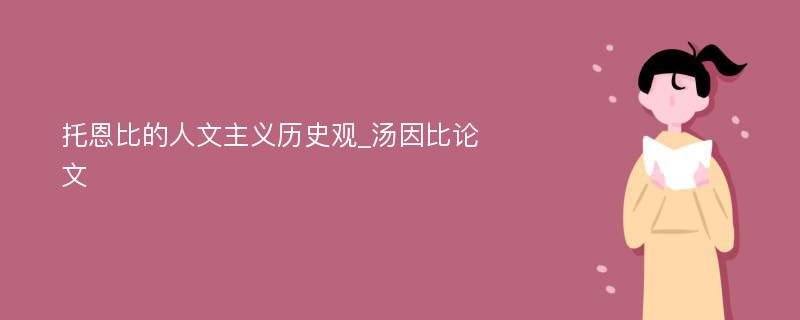
汤因比的“人本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诺德·汤因比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其十二卷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通过对于各种文化形态的比较考察,揭示了文明诞生、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系统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学说”。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包含着诸多的人本主义因素,笔者从人本的角度进一步检索其文化形态观中的人本主义因素。
一、“挑战应战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首先探讨了文明的起源问题。文明是如何诞生的?汤因比批判了近代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族论”和“环境论”解释。在他看来,是恶劣环境而不是安逸的环境构成了人类的挑战从而刺激人类起而应战的结果。汤因比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由此提出了五种形式的挑战或刺激,包括困难地方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遭遇不幸的刺激。面对每一种挑战,人们都会做出不同形式的应战。如果对于一种或几种挑战取得了胜利,那么文明就诞生了,否则文明就趋于夭折或流产。“挑战与应战”才是文明起源的规律,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然而,这种挑战与应战并不是无条件的。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就必须“适度”,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强度太大,超过了人们的应战能力,人们就会被压垮;强度太小,又不能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因而“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一个点上,这一点是在强度不足与强度过分的某一个地方”①。
从表面看,汤因比把文明的起源归因于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然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挑战与应战”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是人。汤因比指出挑战必须适度才可以激起成功的应战,那么挑战适度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显然挑战只能相对于人的应战能力来说是否适度。汤因比认为,不能指望人们对于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种应战做出相同的应战。正是人们具有不同的应战能力,才使得各种挑战具有了不同的结果。因而在挑战与应战这一相互联系的因素中,人的应战能力无疑占据着更为根本的地位。人的应战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先前过度的挑战到后来却被变成可以战胜的挑战了,一个挑战终究会遇到一个成功的应战。“对于同样一个挑战,一个应战者失败了,后来总会有胜利者出来证明它其实并不是不可战胜的”②。可见汤因比承认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的应战能力,而且人的应战能力会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这种能够不断发展和提高的人的应战能力才使汤因比对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精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汤因比并没有看到人的应战能力的本质,而仅仅把它归结于人的创造精神。汤因比宣称人类的关键装备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精神。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自控能力,没有这些为开发有利于人类的某些地理潜能的精神,那么再好的技术本身也不能使人类完成创造文明的任务。应该说,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主体作用也是汤因比思想的闪光之处。然而不能正确认识人的主体作用,未能看到人的应战能力的本质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能力,又暴露出汤因比认识上的片面性。
二、人的自决能力是文明成长和衰落的衡量标准
汤因比的人本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关于文明成长和衰落的衡量标准之中。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征服、地理扩张、统一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文明的发展进步,然而汤因比却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文明的成长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宏观领域来讲,一个文明的成长表现在对外在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控制,控制力量增强的标志则相应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和军事征服、地理扩张。虽然有些时候文明在宏观领域中的成长在时间上与一个文明本质上的进步相吻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是这样。比如地理扩张往往伴随着文明的衰落,这是因为地理扩张是与动乱时期和统一国家阶段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个时期实际上处于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阶段。动乱时期往往产生军国主义,成功的军国主义者会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伴随而来的就必然是地理上的征服和扩张了。技术进步同样如此,技术改进并不意味着文明成长,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既出现过技术进步与文明同步的例子,也出现过许多技术进步,文明停滞;技术倒退,文明反而进步的情况。因而汤因比认为,技术改进不是文明成长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技术改进反而是文明成长的结果。所以,对于外在环境的控制不能成为文明成长的标准。
从微观领域来讲,一个文明的成长表现为构成文明或社会的个人精神自决能力的增强或人格的进步。这指的是一个文明不是战胜外来的挑战,而是能够控制战胜外在挑战能力本身。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实现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转移,一个文明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成长。比如古代埃及人成功地控制了尼罗河,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面对的主要挑战已经不是外部环境的挑战,而是转移到了社会内部:埃及的统治者们如何利用建立起来的了不起的人类组织?显然这是一个来自社会内部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埃及统治者没有能够成功应战,而是利用它为自己建造了金字塔,给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汤因比进而分析到,既然文明成长的衡量标准是人类迈向自决的程度,那么不言而喻,文明衰落的标准也不能够从宏观领域去寻找,也只能转向文明的内部。
尽管汤因比承认文明的成长取决于人们自决的创造能力,可是在他眼里,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自决的创造能力,自决能力不属于“毫无创造力”的普通大众,而是他所谓的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超人”。这些“超人”大都经过一个“退隐和复出”过程——退隐是为了陶冶品德和情操,获得某种启示和灵感;复出则是他的最终目的——获得了创造能力,并进而把灵感和启示通过普通大众机械性的模仿行动转化为现实的创造能力,由此推动文明的生长。文明走向衰落则是这些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在变成统治者以后,日渐丧失了创造能力,从而失去了领袖魅力,开始采用粗暴强迫的方式压迫广大普通群众的结果。
三、宗教本质是一种人生态度
汤因比认为宗教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宗教是文明诞生的源泉,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且还是文明最终的“救世主”。他承认自古以来,创建文明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生产的剩余,就是说,人们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最低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依靠这些才能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事业,诸如建筑、艺术、文学、哲学、战争等等。然而这些创造性事业,如果没有群体的合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种群体的合作,必然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支柱。比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诞生的农业文明,如果没有群体协作,就不能修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荒漠就无法变成良田,文明就无从诞生。维系群体合作的精神上的纽带就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文明衰落的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但是汤因比并没有把宗教当作文明衰落的原因,相反认为宗教是文明的拯救者。这是因为宗教会增强信徒的社会责任感。一个真心对上帝充满爱的人,是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同胞、同类的,因而宗教不是一颗毒瘤,而是一种新文明的“蛹体”,总之,就文明而言,宗教是不可或缺的,是“使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③。应该说,汤因比理解的宗教信仰指的古今中外一切宗教概念所涵盖的一种人生信仰,是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包括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我在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对人生的态度,是鼓舞人们战胜人生中各种艰难的信念。这也就是宗教对于有关宇宙的神秘性和人在中间发挥作用的艰难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给我们所提供的精神上的满意答案;并在人类生存中给予实际的教训规戒,由此鼓舞人们去战胜人生旅途上的困难”④。可见汤因比的宗教观从本质上并不是如神学家所宣扬的神秘东西,他心目中的“上帝”是宗教本身包含的一种“爱”的情感,历史上每一次宗教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精神的一次升华。
四、人的“生命冲动”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从挑战应战说、文明兴衰的衡量标准和宗教方面理解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体系,只能说是理解了其表层意思。要触及汤因比史学思想体系的实质,还必须探讨汤因比的“生命冲动”“人格”等概念。人的精神力量即文明发展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是自发的还是上帝的启示?汤因比借助古典希腊神话阐释了它的源泉。根据埃斯库罗斯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宙斯战胜了天神克洛诺斯以后,坐上了奥林匹斯主神的宝座,从此除了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然而普罗米修斯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不得安宁,使他被迫起而应战。宙斯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处死了普罗米修斯,可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后者。在汤因比看来,普罗米修斯是一位永不知足的创造者和点火人,他具有不断探索的思想,是成长过程的一个神话般的化身,是一种“生命冲动”。在这里汤因比借用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柏格森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创造进化的过程,其动力来自生命冲动。生命冲动是一种精神性本原,它存在于世界之初,分为两个方向:上升和坠落。生命冲动就在这两个方向的相互作用中创造了万物,它不受任何规律制约,相反,如果有什么规律,也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物。汤因比的生命冲动理论与柏格森的思想并无二样。他把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看成是同一个人类灵魂的两种冲动,是不同的人类化身。正是人类的“宙斯”内心深处具有“普罗米修斯的火光”,而且永远不会泯灭,人类才得以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文明才能够成长。“如果文明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变成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柏格森的术语),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做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致无穷”⑤。汤因比使用了“人格”这一术语来标识“生命冲动”。他认为“人格”是少数创造者的灵魂,它具有创造性、超人性和神秘性,代表了最高的生命力,是创造新人种,改变文明社会精神面貌的力量,推动文明的成长。“正因为这样,文明社会的生长过程就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文明的生长实质上就是一种生命力”⑥。
这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到了人类的生命冲动,最终与主张把人的精神、意志、动机、本能等视为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人本主义殊途同归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可以称之为“人本史观”。他重视历史发展中的人的主体作用,能够认识到正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完成了文明之间的新陈代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历史进程中的物质因素,不了解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仅仅重视人的精神、本能和动机的作用,是不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的,这是一切人本主义者的根本缺陷。
注释:
①②[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173、177页,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④[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63、363-364页,荀春生、朱继征、陈国粱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⑤[英]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略本(A.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 Ⅰ-Ⅳ by D.C.Somerve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87.)
⑥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12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