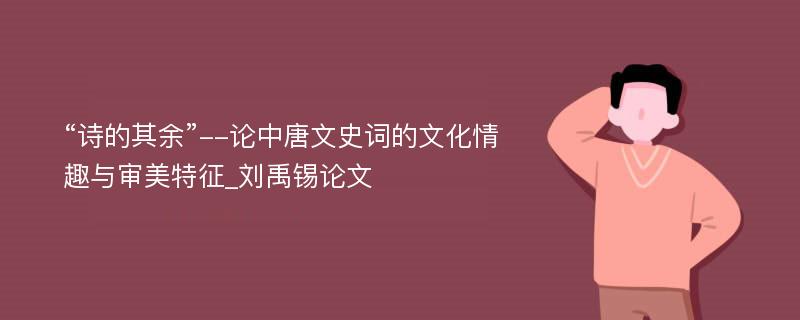
“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余论文,品位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唐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渊源悠远的“诗”相较,曲子词——通常简称为“词”,是一种受到声律音调更严格约束的新兴文学样式,自它出现以来,或由文体流变着眼、或因句式韵音立言、或依据题材内容的表现特点,被赋于多种别名异称。甚为流行的“诗余”一辞,最早产生在南宋孝宗赵昚乾道、淳熙年间,至明人张綖制订词谱,竟径直书之曰《诗余图谱》,遂为词学界广泛接受,视作词的又名。当然,明、清两代的不少论词者也曾力辨其诬,考析“词”与“诗”的若干形式、本质上大的区别,实足能卓尔独立于文学之林,蔚然自树大国,决非“诗”之“余事”、“余兴”、“余波”(参见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第七则“诗余”)。现在来看,这些说法皆有其合乎道理处,但是,它们往往忽略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时代文化属性,无视初生萌发期的中唐词和晚唐五代,即温庭筠、韦庄以后至两宋成熟鼎盛期的词相互间的诸多差异,而就后者统而代之,甚或遮蔽、掩盖了前者的存在。我这里无意于辞语本身的释义、考异、辨源等工作,而着重从文化生成、美学品味、功能取向及价值定位等方面,论述中唐文士词(因为同期敦煌钞本民间词的准确编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把据,故姑置之不依为据)所受“诗”的影响,其两端走势与中介关系等。
一
隋、唐之世,西域少数民族音乐——胡乐大量涌入中原,其间流行广泛、最具影响的是西凉乐与龟兹乐,这就是唐杜佑说的:“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它们与汉民族固有的民间音乐——俗乐相互融合渗透,逐渐形成为新的燕(宴)乐,以取代旧的雅乐和清商乐,“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燕乐的适时、实用性质和它的兴盛,直接刺激、鼓励着新歌辞的制作繁衍,于是,不同于传统声诗的、与音乐更关系紧密的一种新文学样式——曲子词便应运生成,并由民间向中上层社会推进扩展,在相当程度上征兆文坛嬗变代兴的消息。所以,它渐次引起某些创作思想活跃,具有敏锐审美感应的诗人文士的注意和兴趣,将之视为一试身手的大好领域。
从文学自身发展演进规律与具体时代文化风会说,历经千余年而到盛唐,传统的诗已臻极致,可谓诸体大备、众美咸集,后来者仰慕其辉煌,却势不得再循其原路,是以“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诗人无论于艺术手法、设意命思,抑或风神面貌,都崇变尚新,力图另辟蹊径,重造新境。那么,由“诗”衍化过来、又相对独立的“词”这种样式,对之更产生诱惑吸引力,也就毫不奇怪了。另一方面,早已经流行的民间词虽然提供很多的借鉴经验,不过,那种粗鄙俗陋的格调不适合宫廷公府樽俎筵宴间遣兴娱宾的需要,以及中上层社会普遍的审美取向,也促使他们按照自我为主体的兴味旨趣,从仿效到不断进行新的创制,流播在弦管歌喉中,娱人亦复自娱。反而言之,正缘因这批文士一般皆载具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表达能力,其介入便促进了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发展成熟,他们的制作,也相对提升了词的美学品位和社会影响度,从而有着示范导引意义,使词由粗糙走向精美,开拓出无限广阔的未来,勃发强大的生命力。
无待赘言,在这种流变过程中,还需要经历长时期的积累、实验。从隋到初、盛唐,文士们仅只偶尔为之,据《全唐五代词》所载者,自虞世南、长孙无忌等至李白以前的唐玄宗、崔国辅、王维等,不过二十人左右,所制作亦不足五十阕。更主要者,便是其体制不纯,仅初具“词”的面目,实质上很难同声诗区别开来,有的甚至截取乐府诗的一段,或者直接取诸近体诗,配以弦管歌唱罢了。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关于此二词的真伪,向有不同说法,遽难定论,本文仍按习惯系于李白名下),才属真正符合词这种文学样式规范的发轫之制,标志着在整个初生萌发阶段,词已由地下土中冒出地表,很快就要滋长张大了——那是中唐文士词。
二
曲子词,或称曲子,当时名词人曰“曲子诗客”,其所制作者,自然就是诗客曲子词了。乍看来,这是一个单纯的名称词语,其实于它之后,包含有深层文化背景与特定审美意蕴,暗示了与诗的血缘纽带,通连传统的本质走向;如果再进而比较代表着词体的完全成熟独立、揭开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花间集》,就能够显现得更加明晰透彻。
“花间”的鼻祖温庭筠,虽然也是著名诗人,成就不凡,但终究藉凭词人身份跻身文学史,两方面作品高下向有定论;韦庄情形类似,诗远逊于词。至于集中其他作者,可谓属于专业词人行列,多因词名世,否则早就湮没在尘封的浩瀚典册里了。中唐却大不然,善词者如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首先是诗人,发其余事存词数阕,即亦不妨他们在文坛的固有位置,世人或其自己,也均不以词家待之。这种带有本质性的文化环境,注定使之以“诗客”的艺术思维惯势、美学理想去制“曲子”,所作词也必然涂染上浓厚的诗化色调。
首先,体现在有关词的本体意识上。词为“艳科”,最早由花间词人标举宗旨:“《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诸》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庭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艳之词,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叙》)故而其题材范围和表现内容,多为恋情闺怨、伤春感别之类。社会文化功用在于满足迎合贵族官僚及上层文士们声色享乐的需要;艺术风格方面,则以“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的精丽绮华为尚,一句话,它“香而软”(王士禛《花草蒙拾》),立意在“娱人”,从而与兴观群怨、比物寄托的诗化传统分道并驰。缘前述者,中唐词作者显然还未具备这种独立的创作观念,他们仍然深受诗的熏陶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循言志抒怀的惯式心态去制词,依旧以“娱己”为旨,喟叹身世,就自我人生际遇和种种现实感受而发之。下面将分别举例作些论析,以便具体观察印证: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渔父〕
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
——张松龄〔渔父〕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秋。若问二妃何所处?零陵芳草露中愁。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刘禹锡〔潇湘神〕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忆江南〕
张志和是真正的隐士,词中描摹的春汛时节烟波垂钓的渔翁形象,正是他热爱大自然、淡泊名利的情趣襟怀与悠然世表、寄身五湖的闲适生涯的真实写照,物我两化,人词合一,随意凭清隽平易之笔致挥洒出来,绝无丝毫做作态。张松龄为志和兄,释晓莹《罗湖野录》说制此词以招志和还聚,“后家莺脰湖旁,仙去,吴人为建望仙亭”。仙去云云自是附会,但水上林下,生命归宿的选择却并没有实质区别,唯松龄词更为质率罢了。刘禹锡〔潇湘神〕系祭祠神祗之制,性质与屈原《九歌》相类,也有词的实用功能。不过,若结合他因参与王叔文革新活动,事败被长期贬逐南方蛮夷之地的现实背景来品味,则那种凄迷惝恍的气氛,那一派兴寄无端、不知由何所把握的哀婉幽怨情愫,无疑都融进了沉挚的沦落之感,极富自我排遣旨趣,不乏屈子迁客骚人的传统风韵。有关组词〔忆江南〕,基于白居易昔年游宦苏、杭的切身经历,是以深情贯注,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凸现出中唐士大夫文人真率坦易、又洒脱倜傥的精神面貌。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唐王朝亦国力蹙迫,从此由极盛峰巅跌落下来,除藩镇割据、对抗中央政权外,边患日渐严重,回纥、吐蕃等不断兴兵内侵,造成很大危害,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也体现到词里,构成沉咽萧飒的时代基调,已不复再有盛唐边塞诗苍凉豪迈、慷慨高歌的气慨了。请试味下列诸阕: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
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戴叔伦〔调笑令〕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
江南塞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韦应物〔调笑令〕
“边草”一首写久戍关塞士卒的浓浓乡愁,“河汉”一首则是戍卒与江南闺妇的相互思念,然更为凄绝,二者于性质上有共通处。中间的“胡马”一首不同,仅着力描摹塞上草原的苍茫荒凉风光,但是,大漠雪地里嘶叫回旋的迷途胡马,难道不是象征了某种日暮失路、四顾彷徨无计的命运沉落感?相较前辈诗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的昂扬高亢,自是荡然无存了。
相思离别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但到了《花间集》,却是空前膨胀,似乎从此以后,便成为词这种文学样式的专擅,乃至充耳盈目,占断春光。不过,那里面描述的女性,多为歌伎倡妇、宫人女冠之属,系正式婚姻家庭以外的感情,而中唐词从社会现实出发,另有其不同的着笔角度:
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
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
——王建〔调笑令〕
这里以中夜惊飞的鹧鸪为喻,描写独守空船的“商人少妇”的寂寞与相思之苦。中唐之际,江南以未受安史战乱祸害,生产力和生产水平迅速提高,成为国家财赋漕粮的主要供给地;而城市商品经济尤其发达,促进了金钱意识强化,流通运转加速,原属四民之末的商贾阶层身份地位显著提高,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估客行》、《贾客词》之类作品的出现,说明已是诗人的写作题材,现在又被引进新兴的词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家中怨妇空闺难耐,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应该承认,商人的活动有便利经济民生发展的一面,但这里仍然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纯感情角度出发,刻划出一位不幸的女性形象。
综上述者,可以看出中唐曲子诗客的创作视野,相对局囿在艳科范围的“花间”词人,较为宽阔。他们一方面受到传统诗教和文化功能取向的制约,另一方面主动包容现实生活的激扬牵发,而贯穿着十分典型的自我色彩及个性特征,乃致成为情性心灵的物化形式;反向言之,有些词章还富有现实感与时代精神,或者能据以考索其行踪境遇的具体情状。这就殊异于花间词的类型化和制作背景的模糊性,消解甚或泯除了自我现实存在在词中的位置,“以男子作闺音”,依流行的题材、内容促成之,仅着力于表现的技巧手法,遣语造句的新艳,即使寄寓了自我人生感受,也不过芳草美人,假委曲深隐笔致出之。如白居易〔忆江南〕的感事而作,直显胸臆,张志和〔渔父〕的自我外向表现,都只在《花间集》韦庄、孙光宪、李珣等少数词人那里有微波余音。直到后来的苏轼,改革词风,扩张词境,以提高词的品位与诗并行,才重新向诗化道路回归,但那已经不再是“诗之余”,而上升到新层次了。换句话说,一变中唐曲子诗客的“以词为诗”,而凭独立词人身份的“以诗为词”,从缘诗发作到随心驭使词为我所用。
三
其次,再进而论析有关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品味。如果由体制形式方面考察,第一,中唐曲子诗客的制作符合词在萌生初发阶段缘调切题的惯例,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述内容与调名曲牌相一致,像上节所引录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诸阕及后面将谈及的白居易〔长相思〕等,皆可复按,兹不赘述。在这里,曲调名除却代表音乐格律规定的范式——词的文体特点——之外,还兼具作品题目的意义,从而与诗题的性质类同。以后进入成熟阶段,较早期的花间词尚不乏此等现象,至南唐词便逐渐绝迹,入宋,词臻极盛,但题材内容和调名曲牌已经完全脱离,后者仅只剩下音乐格律的规范作用,不复有他了。
第二,中唐词多以篇幅简短,字数在二、三十字到三、四十字的小令形式出现,绝无同期敦煌民间词的长调,也不象后来花间词的用中调为主。“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辞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辞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辞〕、《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杨慎《词品序》)都说明了曲子诗客初为尝试,难免要依傍已经规范化且早就习熟的诗的声律形式,参酌而逐渐变化之,最后才能创为独立的新体。
与外在体制形式相表里,小令于表现手法、韵致兴趣上也带有诗,尤其是近体七绝的浓厚色彩,美学品味共通。都是以小见大,用尽量少的笔墨包容尽量多的意蕴,在有限的字句间传写无限的情致,或不言之言,言外见意,或烘托渲染,就曲笔出之,造成一种余味悠悠不尽的艺术效果与审美感受。张炎总结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又如冯延巳、贺方回、吴梦窗亦有妙处。至若陈简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之句,真是自然而然。”(《词源》卷下)其实,作为小令中之尤小者的中唐词,早已呈美在前,摇曳生姿了。如: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
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长相思〕
夏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频。
——刘禹锡〔忆江南〕
前者写离别相思之情,俞陛云评析道:“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楼一笑矣。”(《唐词选释》)但是,潘慎不同意表现女子念远人的旧说,认为上片从瓜洲古渡的男子着笔,因河水北顾而生思家之愁;下片倒装,始及女子月夜不眠,倚楼相思之情状,或为虚笔,系男子之悬想而已。然上片另解作女子倚楼南眺而揣测远行人踪迹及所在,下片实境,点明她的月下苦思,仍是倒装结构,亦可通。但无论如何解说,皆显示出善为起兴,因景及情,回旋贯注而下,沉挚绵邈之美。后者抒伤春惜之感,作于文宗李昂开成三年(838),时刘禹锡仕途蹉跎,年老多病,自难免惊心韶华递嬗、春秋代序,喟叹生涯的落寞迟暮,是以发为寄托,也未可知。他由春恋人的反向着笔,采取拟人式手法,情隐景中,物我两化,至结句始正面点题,于短章中颇极曲折宛转之致;情思蕴藉,虽惆怅伤感却不溺在哀婉悲恻,令人寻味其风神不置。诚如况周颐所说:“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如刘梦得〔忆江南〕云云。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蕙风词话》卷二)龙榆生又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说:“这样解散五七言律绝的整齐形式,而又运用它的平仄按排,变化它的韵位,就为后来‘倚声填词’家打开了无数法门,把文字上的音乐性和音乐曲调上的节奏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长短句歌词的发展。”(《词曲概论》上编)其实不独此阕,若再与前面所引录诸作互为参照发明,则那种言约意丰,语浅情深,含蓄委婉中余味悠悠无穷的风格类型和审美趣旨,正由其本人乃至盛唐李白、王昌龄等七绝圣手的风韵一脉承循而来,是唐音的另一种体现。
四
缘因中唐处于词的萌生初发阶段、制作的文士——曲子诗客的特定诗人身份,综前所论析者,“诗之余”,诗化倾向遂成为主导;不过,此时究竟已到了这个漫长阶段的后期(前期为隋至盛唐),正当渐发臻突变、量的积累衍作质的提升的前夜,更基于曲子诗客探索觅寻的自觉意识,所以,在其制作中必然也体现出词的新文体特征,为晚唐成熟阶段的来临预作铺垫,透露出那辉煌未来的最初消息。
上一节述及的刘禹锡〔忆江南〕,调名下原有其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说明他已经倚声填词,承认并遵循固有韵律音调的约束为制作新辞的前提,一变“选词以配乐”的初期原生形态为“由乐以定词”的规范模式,从此开风气之先。
除却上述纯形式方面对传统诗的超越,再考察刘禹锡词所写的内容,业已不再拘束于符合曲调本意的旧习,而是自在行事,径直凭任一己的感发命思去填制新辞。参照前一时期唐玄宗因避安史乱军,仓皇出长安逃奔南蜀,行至骆谷,悼念往事,“取长笛吹自制曲,曲成复流涕”的〔谪仙怨〕(王谠《唐语林》卷四),至“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之内,长卿遂撰其词,吹之为曲”(曹锡彤《唐诗析类集训》卷四),聊以寄寓其贬谪之怨慨。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岛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后来窦弘余制〔广谪仙怨〕,《序》文中说玄宗奔逃“次骆谷,上登高下马望秦川,遥辞陵庙,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听(张)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并对所制曲〔谪仙怨〕解释说,“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而“其旨属马嵬之事”。窦弘余认为刘长卿词“盖亦不知本事。余既备知,聊因暇日撰此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其不知音。”但是,康骈却说此曲调兼融思贤、悼亡两重意兴,窦弘余词“但以贵妃为怀”,未免缺少了“思贤之意”(《剧谈录》),故再另制新作,以图兼具之。由此可见,这种逆向的反复驳难活动,在于探讨曲调词牌的本意,俾使歌辞内容与之相符合,仍然属于前期缘调切题,曲调名即题目,从而先行决定词主题选择的旧传统。若与之比较起来,刘禹锡与白居易的“调同词不同”,说明词由初级尝试渐次迈向成熟独立,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再如前引〔调笑〕,曲名本含有戏谑、耍笑的意思,但戴叔伦、韦应物、王建三人都无视此原旨,而按照各自现实社会感受或创为边塞悲咽苍凉之音,或抒商妇离愁别怨。王建另有两首〔调笑〕: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
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蝴蝶,蝴蝶,飞上金枝玉叶。君前对舞春风,
百叶桃花树红。红树,红树,燕语莺啼日暮。
皆写宫女生活,前者描叙她被遗弃的不幸遭遇,结句尤为凄怨;后者摹画其歌舞宠幸之乐事,纯用比兴之笔,然结句托意遥深,暗暗透露出衰歇迟暮的迷惘惆怅,尤耐人寻味。综上所述,显示了曲名调牌仅只剩下标志声律音韵格式的纯符号意义,已不再具载指示、规定题材内容的作用;曲子诗客着意使这二者分离,从自我主体寓怀感兴的新的文化功能取向和“娱己”的审美角度,来看待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创作,因而将它牵领出诗的荫庇,以不同面目出现在文学之林。
纵观中唐文士词,虽然历时短暂,为数无多,但其过渡性质是很明显的,故它那承上启下、兼容诗词两端而预作征兆的独特价值也应重新予以评价。一般说来,“魏晋——盛唐”为中古,而中唐恰恰站在近古历史文化阶段的起始点上,于词这方面,又属正式成熟的前夕,所以贯注着诗化传统的强大惯性力量,同时显露了新的气象,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比照。或者说,它以词的外壳而展现了由诗向词交叉演变进化的痕迹。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仅只采用在体制形式上已具备较规范的词的特征,能与声诗明显区分的作品为考察、论析之例证,而不再涉及那些混淆于诗词两种样式间、左右皆圆通者,如《竹枝》、《杨柳枝》之类。这样较严格的选择,有助于更明晰、准确地描述处在萌生初发阶段后期诗客曲子词的真实面貌,及其错综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