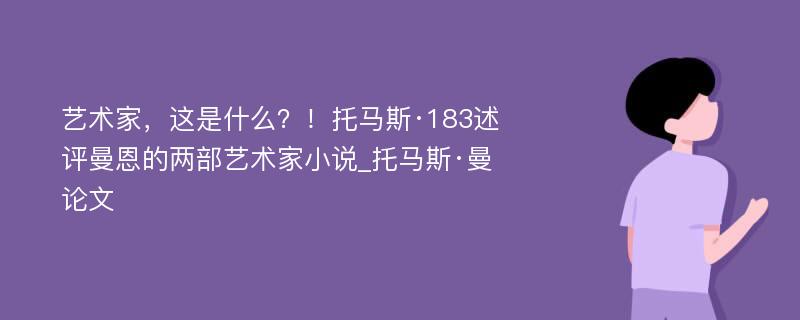
艺术家,什么东西?!——评托马斯#183;曼的两篇艺术家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艺术家论文,什么东西论文,两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家小说,顾名思义,就是描写艺术家的小说。如果说小说旨在刻划人生,刻划灵魂,那么,艺术家小说就专事刻划艺术家的人生和艺术家的灵魂,它是艺术家的文学自画像。这种小说的存在,首先得归功于文学艺术家的强烈自我意识,因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身职业,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复杂性,优越性之后,才会反观自身,表现自身。
德国的艺术家小说有辉煌的传统。它诞生于崇尚天才的狂飙突进时代,由歌德等人开下先河,再由浪漫派和诗意现实主义作家发扬光大,成为19世纪德国小说创作中的一股主潮,荟萃了许多小说艺术的精华。到了20世纪,这一传统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被两位小说巨匠——卡夫卡和托马斯·曼——推向一个新的巅峰。
托马斯·曼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艺术家小说,描写的是艺术家或者说他本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地位。在托马斯·曼研究中,艺术和社会的对立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有社会学眼光的人看出社会在扼杀艺术,富于哲学思辨者则高屋建瓴地指出物质与精神的永恒搏斗,给予我们不少形而上的启示。笔者在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时对一些形而下的问题倒是比较关注,尤其对他的创作与其个人心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紧扣托马斯·曼的生平和心理事实,分析《特利斯坦》和《托里奥·克吕格尔》这两部中篇杰作,以期对艺术家小说管中窥豹。
(一)
《特利斯坦》的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没有什么病,却为了什么风格而长住疗养院。他写过一部篇幅有限的小说并且热衷于写作,但从他那光出不进的邮件看,他的作品似乎在四处碰壁。他性格孤僻,在疗养院独来独往,但科勒特扬夫人——一个前来治病的商人之妻——却引起了他的兴趣。当他得知后者出身于一个走向没落的商人世家而且精通音乐之后,更是兴趣倍增。一天晚上,科勒特扬夫人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弹奏了瓦格纳的歌剧《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序曲。音乐造成的情绪激动使她肺部出血,不久便死去。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科勒特扬夫人临死之前,这位作家还给近在咫尺的科勒特扬先生写了一封信,以激烈的言辞分析和抨击了后者的低级庸俗,而当后者捏着信前来责问时,他又显得十分难堪、胆怯。他是一个怪诞、滑稽、缺乏正常人性的人物。不过,这个名叫史平奈尔的作家恰恰是早期托马斯·曼最为真实的一副漫画肖像。这绝非无稽之谈。
1906年,托马斯·曼在题为《比尔泽和我》的论文中写道:“不论一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多么对立,他们却都是创作主体的自我投影……夏洛克这个犹太人难道不令人生厌,令人害怕吗?难道莎士比亚没有大快人心地对他无情地鞭笞和践踏吗?可是,人们不止一次地察觉到莎士比亚和夏洛克之间深刻而可怕的一致。”〔1〕这番话旨在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手法作总结和辩护,但也同样适合于《特利斯坦》。在史平奈尔正式出场之前,作者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做了如下交待:“这儿甚至有一位作家,他是个乖僻的家伙,叫一个什么矿物或者宝石的名字,也在这里浪费光阴……”〔2〕细细对比, 我们就会看出托马斯·曼和史平奈尔是如何息息相通的。
史平奈尔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唯美倾向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十分地不人道。因为当科勒特扬夫人说她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弹钢琴时,他回答说:“要是你怕对你有害处,夫人,那么你就让那渴望在手指下鸣响起来的‘美’死去和沉默吧。”(第47页)。结果,他渴求的“美”鸣响起来了,而科勒特扬夫人却因肺部出血死去。科勒特扬夫人的死合乎医学法则。但是,托马斯·曼告诉读者的不只是史平奈尔为了美的享受而漠视生命、健康,他还提示人们音乐——确切讲是瓦格纳音乐——和死亡的关系。托马斯·曼也不是第一次在小说中描写瓦格纳音乐。回想起来,矮个子弗里德曼是在看歌剧《罗恩格林》时燃起了欲火,从而酿成一场爱情悲剧;汉诺在瓦格纳音乐中一点一滴地耗尽了他那原本微弱的生命,托马斯·曼让他在病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弹奏瓦格纳音乐。我们觉得瓦格纳音乐就像一个不祥之兆,像一团死亡的阴影。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他的音乐跟死亡有什么关系?
说到瓦格纳,不能不提叔本华,因为这两人都被托马斯·曼奉为精神和艺术先师而且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叔本华想用艺术、尤其是音乐艺术来启迪认识以拯救因为意欲而受苦受难的人类。当瓦格纳读到叔本华的理论时,他茅塞顿开,意识到救世重担落到了自己肩上。既然叔本华呼吁艺术家们要让“意志无阻碍地显现出来,以便它在这显现出来的现象中能够认识它自己的本质”〔3〕, 那么瓦格纳就有充分的理由按照“过把瘾就死”的逻辑创作他的歌剧《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让人们去彻底发泄激情,从而体验、认识并取消意欲。正因如此,托马斯·曼才说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最深刻的本质是性爱”,是“特利斯坦音乐的精神源泉”。〔4〕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背景下,音乐、性爱、 死亡便胶在了一起。
托马斯·曼对瓦格纳音乐领悟得如此透彻,以至于他不断在其小说中花不小的篇幅,用准确细腻的文笔去再现和分析瓦格纳音乐。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布登勃洛克一家》,《特利斯坦》以及中篇小说《女武神的儿女》(1905)就是例证。令人惊讶的是,音乐在这三部作品中都有不良的副作用:前两者的主人公都是病死的,《女武神的儿女》的主人公——一对孪生兄妹——却在歌剧《女武神》的音乐煽动下跌入了乱伦的深渊。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描写,一个问题油然而生:瓦格纳音乐有这么可怕吗?笔者凭朴素的经验观察,觉得瓦格纳音乐并不是对每一个人——当然是音乐内行——都有托马斯·曼所描述的那种效果。显然,托马斯·曼那种既爱又怕、既投入又怀疑的双重态度有其独特的个人背景。这里有两点要谈:第一,托马斯·曼是带着青春期的情绪和渴望听瓦格纳音乐的。我们不难想象,当一个春情萌动的少年听到像《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这种宣泄性爱的音乐,当他领悟了“你是伊索尔德,我是特利斯坦,但又不再是特利斯坦,不再是伊索尔德……”(第53页)这类极乐的呻吟时,他会有何感想,有何骚动。第二,如果只是引起一时的情绪骚动,那么这种音乐也没什么可怕的。音乐总是要唤起点情绪的。但托马斯·曼的感受之深已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托马斯·曼那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世俗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瓦格纳音乐的态度。他害怕自己跟汉诺一样沉溺于被动、消极的艺术享受,到头来一事无成。说白了,他是怕因为一种不良习惯耽误了他的写作“正事”。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唯美主义者,他追求和崇拜的是空灵的“美”,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阳痿的人。〔5〕但是他又偏偏陶醉于宣泄性爱的音乐。 毫无疑问,史平奈尔无论在音乐还是在性爱方面都不会有所作为的。托马斯·曼跟史平奈尔开这种恶毒的玩笑,其实是在鞭策自己,而他描写后者为了音乐不惜把别人推向死亡也是为了给自己敲警钟。
关于史平奈尔,托马斯·曼写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作家是这样一种人,写作对于他比对任何人都来得艰巨。”托马斯·曼不是那种兴来落笔如几雨的作家,他的创作方法十分理性,他几乎总是以蜗牛速度爬格子。他夫人回忆说:“托马斯·曼写得很慢。但是他写好的东西就不再改动了……他只在上午的三个钟头里写作。他全是手写。如果他一天写出了两页纸,那就算相当多的了。”〔6〕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发表使年仅26岁的托马斯·曼一举成名,他的文学航程可谓一帆风顺。同时,这种不可多得的幸运给他带来双重的压力。他很清楚,他未来的生活跟他的创作密不可分,这意味着沉重的使命感和创业心,意味着写作成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托马斯·曼一门心思探究自己的艺术家烦恼,顾不上左顾右盼,他似乎天真地以为只有艺术家才遭受此等厄运。由于大惊小怪,他便让史平奈尔去担当这种命运,给这个滑稽人物涂上了一点严肃甚至悲壮的色彩。我们看到,史平奈尔进疗养院是为了“风格”。他对自己的奇谈怪论做了如下解释:“为了保障起码的身心健康,非要它(指风格)不可。显然,在软绵绵、舒适到令人淫逸的家具当中,人们是一种感受,而在这种线条笔直的桌子、椅子和帷帘当中,又是一种感觉……这种明朗和坚实,这种冷酷的朴素和拘谨的严峻,给我力量和尊严。”(第33页)这些话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史平奈尔也在身体力行。他为此终日过着一种“守规矩,讲究卫生的严格生活方式”(第34页)。
作者又提醒读者说:“令人惊异的是,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没有写出第二本书来,虽然显而易见,他热衷于写作。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屋里写东西,寄出去许多信件,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封信……”(第30页)托马斯·曼又跟史平奈尔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跟其他场合一样,他是在鞭策自己。说到这里,必须谈谈《布登勃洛克一家》给托马斯·曼带来的另一重压力。托马斯·曼有着异常强烈的功名心。作为一个受到19世纪文化熏陶的人,他深知文化巨人离不开恢宏巨作,伟人首先得有数量的积累。因此,要当文学泰斗,就必须写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一炮打响。但他意识到这个起点太高,而他日后的创作又只能在其上,不能在其下,既要保质又要保量。这对托马斯·曼来说实在不轻松。他害怕跟史平奈尔一样,写完一部小说就气数已尽。这种心理不免使他有些操之过急,结果有些欲速则不达。反正他的第二本长篇杰作《魔山》是在时隔25年才问世的。对于这一现象,回首往事的托马斯·曼在1940年总结道:“最伟大的作品并不总是那些带着最伟大的意图写成的作品……不能在一开始,在动笔之前就雄心勃勃……再也没有比那种抽象的、不着边际的雄心,自在自为的、跟作品无关的雄心,作家自我的盲目的雄心更错误的了。”〔7〕
简言之,《特利斯坦》只是托马斯·曼谱写的作家受难曲的序曲和变奏。史平奈尔承认他“除了几个钟头的好时光以外,都是在创伤和病痛中挨日子”,抱怨他的整个内心生活,人生观及其工作方式“具有异常不健康、腐蚀和折磨人的效果”(第34页)。《沉重的时刻》中的席勒则替托马斯·曼感叹说,创作就是“负担、压力、良心的折磨,是吞饮不尽的海洋,是可怕的任务,是骄傲和苦难,天堂和地狱”〔8〕。他还痛苦地发现,如果为写作兴奋了一个晚上,其代价将是“一周的盲然和衰竭”〔9〕。《王爷殿下》(1909)是托马斯·曼的败笔, 但桂冠诗人马蒂尼和亨利希王子讨论什么是诗人那一段确是妙笔生花。马蒂尼总结说:“我可以保证,诗人的生活并不美妙,特别是因为我们并非时时刻刻都是诗人。为了不时地写出这么一首诗,谁会相信我们得经受多少闲荡,无聊以及忧郁的懒惰。给雪茄烟供应商写的一张明信片就常常是一天的劳动成果。我们睡得很多,昏昏沉沉地四处闲逛。哎,我们常常过着悲惨的生活……”〔10〕
最后,我们看看史平奈尔和科勒特扬那场较量,因为托马斯·曼再一次显示出他多么擅于通过漫画“走私”真理。这两个人一个笔头,一个口头,相互分析、咒骂,及尽攻击之能事,似乎要竭力给对方勾勒出一幅暧昧的肖像。不过,细细一读,我们会发现史平奈尔对科勒特扬的咒骂几乎全是陈词滥调,比如食客、村夫、厚颜无耻、自以为是、跟艺术绝缘等等。相比之下,关于史平奈尔的话,不管是他本人还是科勒特扬说的,却显得很有份量,很有来头。不难看出,说商人是虚,谈文人是实。托马斯·曼兼用分身法和讽刺笔法,通过这幕滑稽的对话来讲述自身的伟大和暧昧。
文人会观察、擅表达,这是妇幼皆知的。托马斯·曼却为此得意非凡。他把这条常识翻译成“精神与文学”这两个庄严的字眼,交到史平奈尔笔下,让他解释为文人——生活中的弱者——的“珍贵武器和复仇工具”(第60页)。有趣的是,托马斯·曼对于这个常识的体验是如此深刻,把它看得如此宝贵,所以他不仅要在此重复,而且还要尽情地发挥、阐述。史平奈尔声明,他“在世上责无旁贷的职务是照实反映事物,让它们倾吐,使不为人知的事物公诸于世”。既然责无旁贷,那一定是毫不妥协,因此他要对“四周的一切加以说明,申述,使它被知觉,不管这样做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带来慰藉和镇静,还是增添痛苦”(第59页)。指名状物不仅是义务,而且也带来快乐,因为恰当的表达可以带来预料的效果,给人以胜利感。正如读者所见,史平奈尔如愿以偿。虽然他在科勒特扬面前犹如小鸡见到老鹰,虽然他基本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但是他只纠正了后者二三个错别字就使之乱了方寸。应该说,这些思想、这等文字是有点抬举了史平奈尔,跟他的整体形象有些出入,人们甚至要问这是不是艺术上的疏漏。不过,这种疏漏是情有可原的。既然托马斯·曼把自己最珍贵、最光辉的东西——文字——赠与了史平奈尔,他不可能不沾点光,升点值。
不过,史平奈尔的光辉形象只是昙花一现。托马斯·曼凡事不忘“另一面”,他当然也不会隐瞒语言狂的阴暗面。如果说史平奈尔在宣言和别字更正中显示出一点价值和尊严的话,那科勒特扬的话和他本人随后的表现又使他的暧昧之处暴露无遗。“咬文嚼字你倒是有勇气!”(第3页)科勒特扬这话可谓一针见血。 因为史平奈尔只敢写信发泄愤怒,只会通过纠正别字体现尊严,他对女人也只是“斜着眼瞟一下”(第62页),然后提着笔杆去驰骋想象,以此享受“美感”。文字于他只有画饼充饥之效。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获悉科勒特扬夫人病危时的反应:消息传来,看上去粗鲁而轻率的科勒特扬“眼眶里噙满泪水,可以看出好像有一股温暖、善良、诚恳而高于人性的感情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第65页)。史平奈尔则表情木然。当科勒特扬嚎哭而去之后,他却自言自语地重复科勒特扬的错别字:“不可逃避的职务……”(第66页)显然,别字比垂死的人,而且比一个他熟悉的、客观上被他坑害的人更能触动他。因此,不论史平奈尔的文字如何,他的人格总是不足取的。他不仅是懦夫,而且缺乏人性。在他这里,表达高于感情,文字重于生命。他把热血洒向了文字,自身却成了冷血动物。他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唯美主义者,一个异化的文人。
托马斯·曼也是语言狂。他给人的印象是为语言而生,为语言而死,不惜为之赴汤蹈火。比如他在《比尔泽和我》一文中宣告:“妙语伤人……可一个真正热爱语言的人宁愿与世为敌也绝不牺牲一个绝妙的字句。”〔11〕至于托马斯·曼和史平奈尔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他本人是否异化或者异化到哪种程度,笔者不敢妄加断言。毫无疑问,托马斯·曼有着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否则他不会塑造史平奈尔这一形象。据说,认识了自我就不再可能依然故我,托马斯·曼也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一浸透着辩证思维的教义。但是,在并不那么强调知与行相统一的西方知识界,这一智慧论断很难说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二)
现在我们得评一评《托里奥·克吕格尔》(1903)。提起艺术家小说,熟悉托马斯·曼作品的读者大概首先会想到这部作品。同名主人公的思想和经历是如此动人,以至这部仅几十页的短篇小说拥有的读者仅次于《布登勃洛克一家》,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托马斯·曼都禁不住把他这篇得意之作比为20世纪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是为什么?
小说从主人公的少年时代讲起。托里奥和汉诺简直如出一辙。他们不仅有南欧名字,他们的相貌、气质都跟“那些淡黄色头发、深蓝色眼睛的斯堪的纳维亚型的同学”有所不同〔12〕,一望而知他们是特殊人物。两人所不同的是,汉诺奉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对随处可见的斯堪的纳维亚型同学避而远之,只跟那个性格虽野,但志趣相投的凯伊形影不离。托里奥则是“鹰勾鼻子爱狮子鼻”,偏偏喜欢两个最地道,最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型的少男少女:汉斯·汉森和英格博格·荷尔姆。可是,托里奥的爱没有得到回报。汉斯跟他在一起总是显得敷衍而又勉强,英格更是从来没注意过他。托里奥只有单相思。这原因似乎很简单: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走不到一起。于是托里奥努力寻求共同语言。由于他无意、也无法进入汉斯的自然领域,所以他试图把汉斯引入他的精神王国。但是汉斯不为所动,而托里奥也认识到,汉斯不应该变得跟他一模一样,因为他爱的正是汉斯的“不一样”。托里奥恰恰有“同类相斥”的倾向。比如在舞蹈学校也有一个名叫玛达莲·维梅雷恩的姑娘注意他,喜欢他。她跟托里奥一样喜欢诗歌,拙于跳舞,不时在舞场上摔倒。可托里奥对她又毫无兴趣。因此,托里奥陷入一个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别人欣赏的东西他没有,他拿手的东西别人不欣赏;他爱的人不爱他,爱他的人唤不起他的爱。托里奥的爱是无法实现的,他为此痛苦、忧伤,整篇小说都浸透着这种缠绵悱恻的情绪。
托马斯·曼说过,《托里奥·克吕格尔》兼有“忧伤和批判,热情和怀疑,施笃姆和尼采,浓郁的情绪和极端的理智”〔13〕。的确,托里奥并没有深陷于情感而不能自拔,他倒是很能痛定思痛。小说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托里奥的两个单相思经历,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绪。随后作者用寥寥数笔交待托里奥去了南方,体验了感性快乐,在艺术上也成熟起来。再接下来就是功成名就的作家托里奥和女画家的长篇对白(严格讲是前者的独白,因为后者不过是偶尔插话的听众)。他试图解释作家痛苦的真正原因。
托里奥认为,根子在于他是艺术家。他提出一个很有挑衅性的观点:做人与做艺术家,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人,就当不了艺术家;是艺术家,就无法做人。艺术家不是平常人,是异化了的人。托里奥的意思是,人是热血动物,都有七情六欲,而艺术的产生却以冷却和消灭炽热的情感为前提。他对此作了美学论证:“作家必须有些超乎人情和不通人情,对人情保持一种疏远和淡漠的态度,才可能,才会被吸引去表现它,戏弄它,成功而富有风趣地把它表现出来。风格、形式和表达方面的才能,首先就要求冷静和挑剔的态度,也就是某种人情上的贫乏和空虚。健康而强烈的感情,素来就没有什么审美能力。”(第94页)。众所周知,艺术存在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它要求艺术家跟作品保持距离,以便能够清醒地考虑如何制造艺术效果。因此,艺术家在创作时既要投入,也要冷却感情,他既在作品之中,又在作品之外。可是,托里奥偏偏要搞片面化,把心和脑,情感与理智,体验与表达对立起来。他力图告诉人们,创作时绝不能心跳,就创作而言,喜莫过于心死。这一理论是荒唐的,其炮制者自己就无法身体力行,因为不难看出,《托里奥·克吕格尔》的作者在写作时是动了情的,他的心是跳动的。更有甚者,托里奥还把冷若冰霜宣布为作家时时刻刻都无法摆脱的职业病。他即便放下了笔杆,离开了书桌也不能有冲动,不能生感情。为此,他必须回避春天、感官、社会,他只能当冷冰冰的艺术苦行僧,也必须承受孤独的命运。
简言之,是艺术害了托里奥。当然,他不只是在一个地方深受其害。托里奥跟史平奈尔一样,把精神与文字或者说认识与表达看作艺术家最本质的活动。如果说史平奈尔为之感到自豪与快乐,那托里奥则是怀疑和痛苦。托里奥说认识使人痛苦,指的是认识的内容令人痛苦。因为世界的根基是“滑稽和苦难”,所以一旦看破红尘,就会跟哈姆雷特一样“厌倦得不要活了”(第88页)。既然艺术家的眼光最为犀利,其痛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托里奥没有解释他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他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以及《悲剧的诞生》两本书中取来的经。至于表达,托里奥认为有乐趣,这种乐趣使他保持“清醒和开朗”(第89页)。因此,表达减轻了认识带来的痛苦,是对认识的必要的平衡。但是,托里奥也发现了一个很糟糕的副作用:“文学语言能够很快地而又较轻浮地使人摆脱感情……按照他(指文学家——笔者按)的信条,一桩事只要说出来,就解决了,倘若整个世界都能解释出来,世界也就解决了得救了、终结了……”托里奥对这一信条似乎嗤之以鼻:“文学家根本不理解生活在被表达和‘解决’以后,还照样会继续下去,而且不以此为耻。”(第101页)基于上述两点原因, 托里奥把文学家称为“无情、浮夸的骗子”。换言之,表达会使人变得无情、浮夸。
托里奥是一位无私的、彻底的思想家,他追求真理的勇气令人钦佩。虽然他一一列举了艺术的危害性,但是他又毫不留情地指出艺术和艺术家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艺术造就了艺术家,使之变得冷漠、孤独、虚无;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那种注定要献身艺术的人,那么艺术就不可能产生。既然如此,那这种注定要献身艺术的究竟是什么人?可惜托里奥没有把这个问题说穿、说透。他只是说“正直、健康、规矩的人压根儿不会去写作、演戏和作曲”(第95页),而没有进一步讲那些写作、演戏、作曲的人有不太光彩的起源,艺术家都是暧昧的人物。
既然艺术是如此糟糕,那托里奥反过来崇尚生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根据物极必反的原则,这位洞悉了艺术底蕴的艺术家把渴慕的眼光投向了美好、光明、简单的生活,他的爱只属于那些金发碧眼、心底单纯、快乐幸福的平常人,也就是汉斯和英格那样的人。成年托里奥和少年托里奥是一门心思,一种趣味,可惜他们的经历也一样。他们都是一相情愿的爱。每当功成名就的作家托里奥春风得意地站在讲坛上,他总是希望能在欢呼的听众中见到他的汉斯和英格。可是他不得不失望,因为满目都是他“熟悉的羔羊和信徒”,“这些人的笨拙的形体里隐藏着优美的灵魂……他们中都是一些受苦受难、期待渴望,可怜巴巴的人”(第102页)。正如舞场上的托里奥发现他感兴趣的人不理他、 他不感兴趣的人却关注他一样,讲坛上的托里奥觉得台下的人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偏要来。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得不到的总是美好的。由于托里奥对生活望洋兴叹,所以他起劲地美化生活,作践精神。生活“正常、规矩,亲切……平凡得诱人”(第101页),生活是田园,是牧歌, 艺术是冰川,是受难曲。天生丽质者不会去写作,写作者必定先天扭曲;四肢发达者头脑简单,头脑复杂者形体笨拙;自然人翩跹起舞,文化人跳舞跌跤;凡人美貌,文人丑陋。生活捧上天,精神罚下地,精神求生活如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托里奥在心里默默地对可望不可及的英格说:“在我跳女士们的四组舞步,当场丢尽了脸时,你笑我了吗?现在我算是成名了,你今天还会笑吗?……即使我独自创作那九部交响曲,写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画出《最后的审判》,——你若笑我,也总会是对的。”(第132页)就是说,贝多芬,叔本华, 米开朗基罗这三个文化巨人合起来也配不上一个普普通通的金发碧眼的英格!精神自虐到如此地步,已谈不上有多少的严肃与痛苦,倒是成了登峰造极的玩笑。
托里奥的上述思想并非全都有说服力,不是都能自圆其说的。这些观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杂然纷呈。这中间不乏勉勉强强,以偏概全乃至自相矛盾、荒唐错误的东西。艺术的“冰镇”效果是他制造的神话,而所谓认识使人痛苦的说法,则是他从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武库中信手拈来的,充其量只能起点缀作用,满足一下艺术家的虚荣心,与正题没有多大关系。至于艺术的暧昧起源,他欲言又止,说一半吞一半,令人遗憾。不过,之所以这样,绝非因为托马斯·曼一知半解或是头脑糊涂。恰恰相反,他倒是故意片面,假装糊涂。这些问题与其归咎于他的思维,不如说根源于他的态度。这点可以从小说对人们交口称誉的所谓中心思想的处理上看出来:托里奥反复声明他热爱生活,向往生活,渴望跟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谋求艺术和生活和解的良好意愿当然获得了众人的赞赏和共鸣,但是,托马斯·曼的真诚必须打点折扣。就在托里奥主张精神与自然融合的同时,小说又通过实例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那个苍白瘦削的玛达莲姑娘本该呆在家里读书写诗,她却偏偏去了舞场;托里奥碰到的军官和商人应该本本分分地习武经商,他们却偏偏要嘲风雪弄花草。结果,都没有好下场。前者改不了笨手笨脚,所以总在舞场上摔跟头,后者的诗“感受深、效果差”(第103页), 所以在文坛上栽跟头。他们的前车之鉴是:文学求生活必然出丑,生活沾文学势必酸不溜秋。托马斯·曼似乎在向所有想脚踏艺术和生活两只船的人耳语道:死了这条心吧!
既然愿望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距十万八千里,那么托马斯·曼又何必让托里奥来如此表白呢?其实,托马斯·曼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不在于作什么思想上的发现,更不寻求弥合什么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鸿沟。他无非是借着这些抽象的议论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情绪,说具体点,是他那惆怅的同性恋情绪,对于这个颇为新鲜的问题,我们得多扯几句。
托马斯·曼是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虽然跟卡佳·普林斯海姆结了婚并成为六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始终没有摆脱同性恋倾向。这是他平生最大的秘密,最大的心病,也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由于他的同性恋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由于他不断感觉到同性恋给他带来的诱惑,恐怖,烦恼,所以写作对他来说具有双重功效:既是画饼充饥,又是自我审判。他的作品记录和分析了他的同性恋冲动,同时以优美而热烈的文笔流下了一个个让他怦然心跳的英俊少年的音容笑貌。托马斯·曼的同性恋倾向似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直到70年代中期,托马斯·曼的日记发表之前,人们好像对此一无所知,反正评论界是无人谈及此事。托马斯·曼的遮羞布实在编织得太巧妙,他确实给他的秘密套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装,使评论家们只能当事后孔明。老实说,笔者若是20年前评这篇小说,也必定是睁眼瞎。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得知真相之后回过头来看托马斯·曼是如何为他的秘密套上皇帝的新装的。
《托里奥·克吕格尔》是以托马斯·曼和保罗·埃伦堡的关系为背景创作的。后者是一个擅长画马的年轻画家,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和他交往甚密并且逐渐对他产生了恋情。但是,他的感情不敢表露,更谈不上实现。因此,埃伦堡对他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为此感到痛苦、绝望。他在小说中就是要描写和分析这一经历。前面我们曾笔酣墨饱地跟着托里奥讨论了精神与自然,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结果发现他好像在说废话,而且是有意识地说废话。现在有了背景知识,事情总算豁然开朗。事实上,托里奥的形而上的翱翔是由他的形而下的动力助成的。并不是什么艺术跟生活无法沾边,无法结合,而是托马斯·曼无法“体贴”埃伦堡,甚至不能碰他一根手指头。托里奥也并没有物极必反,不是他腻味了精神才转向自然,讴歌生活,而是托马斯·曼对埃伦堡一往情深,把这颗摘不到的禁果想象得无比甜蜜。当然,托马斯·曼本人很清楚小说中说的是什么,指的又是什么。当他谈到“那隐藏的、折磨人的渴望……那对平凡的事物所引起的快乐的渴望”(第101页)时, 当他抱怨自己“专事刻画人情,而偏偏对人情没有份”(第95页)时,他是在对埃伦堡望背兴叹。当他声明他看到“在整个艺术领域,在所有的不平凡的事物和一切天才中,存在着一些极为暧昧、极为丑恶、极为可疑的东西”(第135页),当他质问“艺术家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第95页)的时候,他是在反思和批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说到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当他讲到在故乡险些被警察误抓起来的经历时为什么又在内心深处“认为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第117页)。 如果托马斯·曼生活在同性恋日趋“正常化”的当代德国,他或许犯不着在作品中使劲抽自己的耳光。但在他生活的年代,同性恋者深为大众所不耻,类似于罪犯,在第三帝国还免不了进集中营。因此,他只好拐弯抹角地讲述这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其实,《托里奥·克吕格尔》通篇都在玩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把戏,其文字始终有一种“能下能下”、一语双关的魅力,象征和现实两个层次在里面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最令笔者击掌叫绝的是小说的结束语。托里奥在给那位专听他独白的女画家的信中总结说:“别责骂这‘爱’,丽莎维塔;它是美好的,也是丰硕多实的。在它里面有渴慕,有辛酸的妒忌,还有些蔑视和一片贞洁的幸福。”(第136页)现在, 我们就拿这段话来“淘淘金”:给爱打上引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既不是抽象的人类之爱,也不是寻常的男女之爱,更不是得到满足的爱。说这种爱美好,那只是作者的个人趣味;说它丰硕多实,也是事实,因为要是没有这种爱,要是托马斯·曼不画饼充饥,恐怕就产生不了这么多、这么好的文学作品。这种爱包含渴慕,这是不言而喻的,有辛酸的妒忌,是可以理解的,谁见到自己求而不得的人跟别人走都会眼红的。至于蔑视,这不可避免,因为这位单相思者心底里并没有放弃精神的自尊自傲,他偶尔也会居高临下地审视精神显然没有他发达的埃伦堡。托里奥最后提到“贞洁的幸福”,这更是显出托马斯·曼艺高胆大。所谓贞洁,自然是指不接触,没玷污,就是说,托马斯·曼既为无法“体贴”埃伦堡叫苦,又因后者近在咫尺庆幸,他有一种苦中带甜,或者说又苦又甜的感觉。
综上所述,托马斯·曼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包装大师,他擅于拿形而上的东西来包装形而下的东西,不露声色地把个人的问题上升为、装扮为普遍的问题。这种做法或许要引起伦理上的争论,但这在美学上是值得赞赏的。试想,如果托马斯·曼在《托里奥·克吕格尔》中一五一十地去描绘他和埃伦堡的关系以及他那平平常常的单相思,绝口不谈精彩的玄学哲学问题,那我们一定会觉得乏味得要死。正因为有这些动人的玄学哲学议论,这篇小说才吸引了众多“内秀”的、档次极高的青年人。据莱希—赖尼斯基统计〔14〕,爱读《托里奥·克吕格尔》并且愿意跟主人公认同的有卡夫卡,卢卡契,施尼茨勒以及法国女作家萨洛特,波兰诺贝尔文学将获得者米沃什等等。当代的高雅青年也在捧读这本书。当然,主题并不是该书成功的唯一原因。小说中的思想、逻辑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关键在于小说中贯穿着“高贵者最痛苦”的主旋律,反复述说精神的烦恼与羞愧,一下子就攫住了那些多多少少也被青春期烦恼所困绕的高雅读者,给后者的思维和情绪定了调,使之来不及反思、批判,注意不到作者如何偷梁换柱。他们只感受到小说的忧伤、严肃、悲泣,没有看出隐蔽的玩笑、讽刺、微笑,总之是没有看出小说的双重视角。可以想象,如果读者觉察到小说的双重视角,双重层次,那么他也许会更加喜欢这本小说,但是他恐怕不再轻易去跟托里奥认同了。
在托马斯·曼这里,生活稍有风吹,艺术必有草动。当他自悲自怜的时候,他写出了《托里奥·克吕格尔》,把孤独与失落宣布为艺术家的符咒和命运。可是,小说发表不到一年,他爱上了卡佳·普林斯海姆并在1905年跟她结婚。他终于体验到生活的光明和温暖,在他笔下,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也随之解冻。他在短篇小说《和预言家聚会》(1904)中就把自己写成一个“跟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一本书在市民圈子里广为流传”〔15〕的小说家,同时以嘲讽的、怜悯的、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那些号称不食人间烟火的青年艺术家、思想家,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人的性格是“残忍和软弱的混合”〔16〕。在剧本《菲奥伦察》(1905)里,基督教禁欲主义露出吃不上葡萄就骂酸葡萄的原形。〔17〕新婚燕尔的托马斯·曼似乎在告诫人们,精神与自然,艺术与生活的对立是一种错觉,一种误会,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但是,幸福的婚姻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它解除了一个单身汉的烦恼,但还远不足以根除一个艺术家的其他痛苦。正因如此,托马斯·曼虽然在《沉重的时刻》(1905)中戴着席勒的面具对卡佳表示了爱抚和感激,但他最后还是默默地向后者承认:“我不能完全属于你,我永远不可能在你这里得到彻底的幸福,为了那构成我的使命的一切的缘故……”〔18〕。就这样,托马斯·曼带着幸福和满足,也带着矛盾和遗憾告别了自己的青春。
注释:
〔1〕〔11〕Thomas Mann,Gesammelte Werke, AufbauVerlag Berlin 1956,Band 11,S.11、17.
〔2〕《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刘德中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3页。以下凡出自此书者只注明页码。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 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9页。
〔4〕〔13〕Thomas Mann,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Fischer Verlag 1983,S.74、91.
〔5〕Hans Rudolf Vaget,Thomas Mann:Kommentarzu smtlich-en Erzahlungen,Winkler Verlag München 1984,S.91.
〔6〕Katia Mann,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4,S.87.
〔7〕Hans Wysling,Dokumente und Untersuchungen,Franke-V-erlag Bern 1974,S.78.
〔8〕〔9〕〔15〕〔16〕〔18〕Thomas Mann,Die Erz hlunge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10〕Thomas Mann,Gesammelte Werke,Aufbau-Verlag Berlin1956,Band 7,S.182.
〔12〕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20页。
〔14〕Marcel Reich-Ranicki,Thomas Mann und die Seinen,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7,S.101-103.
〔17〕Thomas Mann,Gesammelte Werke,Aufbau Verlag Berlin1956,Band 9,S.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