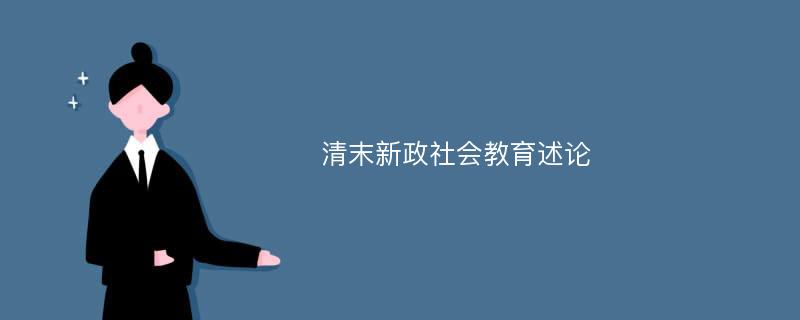
杨晓军[1]2005年在《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地区新式教育述论》文中提出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于1901年颁布召旨施行新政。东北地区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和边陲重地,在日益严重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也推行以“启民智”和“兴新学”为宗旨的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史学界关于清末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存在着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模式单一、研究范围狭窄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报刊杂志、地方档案等资料的基础上,拟对清末东北地区的教育改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的分析,并给予清末东北教育改革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首先叙述了东北地区新式教育管理机构的建立及运作,并对东北地区新式教育机构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其次阐述东北地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社会教育、外国教育等方面加以论述,并对各种新式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简单的评价。最后总结了清末新政东北地区新式教育改革的特点、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认为: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地区兴起的新式教育是一场不彻底的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封建教育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东北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各类新式人才,从而加速了东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当然,由于政局动荡和地理位置的局限,这时期东北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还很不完善,甚至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但从总体来说,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地区新式教育得到了发展,并对东北地区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裴文玲[2]2000年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清政府逐步认识到仅靠推行学校教育,不足以开启民智,挽救濒临崩溃的封建统治。在继承我国社会教育的历史传统和借鉴外国社会教育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办了半日学堂、宣讲所、阅报社、图书馆、简易识字学塾等近代社会教育机构。 为全面反映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及其臣民创办近代社会教育的状况,并予以恰当的评价,本文试图从三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论述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源起。 “社会教育”一词虽至民国元年才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但类似社会教育的社会教化在中华大地上却是源远流长,本部分首先对社会教育加以界定,并概述了社会教化的发展历史。接着分析了清末新政时期,促使社会教育萌芽并得到初步发展的诸种因素。近代社会教育是在清政府的倡导下出现的。为推行社会教育,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另外,时贤学者的鼓吹提倡也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第二部分,全面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国人创办近代社会教育的状况。 近代社会教育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论述了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宣讲所、阅报社、图书馆、近代报刊等六种形式。本部分对这六种社会教育形式在清末新政时期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第三部分,历史评价。 近代社会教育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其影响面也就比较宽泛。它的出现及初步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近代化。首先,清末新政社会教育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以后社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它在西学的传播、社会风气的改良以及开启民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是封建统治者推行近代社会教育,在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如过于重视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忽视女子社会教育等等。最后,本部分剖析了清末新政时期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
王脉生[3]2009年在《清末民初黑龙江近代教育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清末民初,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或者颁布召旨施行新政,或者颁布新的政策,所有的国家政策当中教育政策实行的意义最为深远。黑龙江省地区作为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和边陲重地,在日益严重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也开始推行以“启民智”和“兴新学”为宗旨的新式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史学界关于清末民初黑龙江省教育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是对于黑龙江省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却存在着研究方法非常简单、研究模式单一、研究宽度狭窄等问题,这就有待于进一步得深入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各种报刊、杂志、地方档案和地方志书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地区的新式教育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分析,并给予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省的新式教育改革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首先叙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成果,包括: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社会教育等,其次阐述黑龙江省新式教育发展的促进因素,再次对黑龙江省新式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最后总结了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地区新式教育改革的特点、对黑龙江省社会的影响及黑龙江省的新式教育发展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省地区兴起的新式教育是一场不彻底的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黑龙江省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新型人才,从而加速了黑龙江省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当然,由于黑龙江省政局的动荡及地理位置的局限性,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省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还不完善,甚至存在一些严重的局限性。但从总体来说,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省地区新式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为黑龙江省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吕晶[4]2010年在《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以及预备立宪的实行,教育改革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教育开始关注广大下层民众的需求,社会教育逐步进入历史舞台。作为推进社会教育开展的大省之一,直隶社会教育的兴起有其自身缘由。直隶较早确立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作为推进新式教育开展的县级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严修在直隶首创。然而新式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缺陷,尤其是小学教育不能得到完全普及,致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愿望不能实现。维新运动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要求“大开民智”,教育理念实现了从学校教育人才观到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的转变,促使以“开民智”为目的的社会教育出现。“开民智”引起直隶各级官绅重视,他们身体力行,自上而下悉心推行,保障了社会教育的开展。直隶社会教育各项设施地筹办形式多元化,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图书馆、宣讲所、阅报社的兴办更为突出,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们的需求,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清末直隶社会教育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迅速,伴随着多元化发展,成效非常明显,位居全国之首,并且创办各项设施形式灵活、功能多用。由于清末复杂多变的大背景,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经济落后、资金不足、经验缺乏,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以及直隶特殊的自然环境,致使直隶社会教育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社会教育早期发展没有固定机构,各地社会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内容上保留了许多封建伦理思想。
唐彬源[5]2017年在《清末半日学堂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分析和梳理清末新政时期推广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一一半日学堂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聚焦于半日学堂与普通中小学堂在初等教育领域的关联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当中的地位。由此本文认为半日学堂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重要作用,极大推动了普通群众的识字扫盲水平,并为建国之后的扫盲教育积累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同时也可以视作清末社会各阶层社会改良的一次重要尝试。现将本文各章节主要内容观点摘要如下:第一章通过对半日学堂在清末时期起源的考察,以及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当中的地位,表明半日学堂的产生深深根植于近代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清末新教育思想的传播、日本的文明开化观、德国国家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新政教育改革当中对于初等教育的重视、学部劝学所的成立都对半日学堂这类社会业余补习学校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章集中探讨半日学堂在清末几年当中产生和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情况,指出半日学堂填补了官办中小学堂未给普通民众识字教育的资源空间,这一新式学堂因而获得巨大的成功,短短数年时间就由直隶扩张至全国各省。并且通过具体统计数据,勾勒出清末半日学堂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为各省行政长官和当地官绅阶层对于新式教育的开明程度决定半日学堂在当地发展水平的高低。第三章主要分析半日学堂的办学特征。基于半日学堂招收"贫家子弟"和"年长失学者"的教学理念,教育对象上十分多样化,均保持十分宽松的入学条件;教学设施上充分利用当地简陋的公共场所,师资来源上则充分挖掘各类有志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人群。学制和教材运用上也十分灵活,能够半日读书,半日营生。第四章就半日学堂与近代中国社会改良之间的关联展开探讨。认为半日学堂率先采用的拼音识字法对快速提高国民的识字率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直到今日,此种识字方法依然被广泛采用。在近代社会移风易俗上也有突出贡献,半日学堂的宣讲、阅报活动与劝学所共同举办,宣讲员多兼任半日学堂的师资,其学员也多是积极参与者,这些举措都十分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文明开化。第五章对半日学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联展开综合评述,着重探讨半日学堂兴起的原因,对初等教育的贡献以及整合地方教育资源的贡献。认为其对落后的中国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于今日边疆落后地区的扫盲教育依然有现实价值。
徐振岐[6]2013年在《民国时期黑龙江高等教育述论》文中指出近代以来的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多有变化,本文所阐述的黑龙江高等教育是指现在黑龙江省的区域,因为当时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主要分布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故以这些城市的高等院校为主要考察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近代化历程,东北社会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末新政前后,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学习日本经验,黑龙江地区也逐渐出现高等教育雏形,但在此期间,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沙皇俄国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尤其是哈尔滨地区开设了一些教育设施促进了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该地区的高等教育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北洋政府时期,实际上长时间控制黑龙江地区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于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倾注了一定心血,但由于基础薄弱,民国初年黑龙江地区仅有黑龙江法政专门学校、黑龙江优级师范学堂、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等为数不多的高等院校,而且办学规模小,入学学生少。20年代后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当局为俄国移民创办的高等院校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超黑龙江当地政府,实际上构成了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主体。此期间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虽然比不上关内一些省份发展迅速,却一直在逐步发展建设当中,至九一八事变前,黑龙江地区已经建成了东省特别区法政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东省特别区俄文师范专科学校、东北商船学校等十几所高等学校,学校规模和入学学生人数都大大超过民国初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黑龙江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一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东北,黑龙江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殖民地。随着1935年3月23日,苏联与伪满双方在东京签订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原先中东铁路局创办的学校很快失去依靠,很快被日本接收,整个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已经没有俄国侨民教育的痕迹,而黑龙江地区其他高等院校除内迁外,均已被日伪强行接管,高等教育完全受到日伪的控制。在日本殖民统治的这一段时间内,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作为奴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高校教学中强化日语教育,抹杀学生的民族性;宣扬皇道主义,忠君思想;强化实务教育,轻视文化教育;抬高高等教育门槛,高等院校中的中国学生只占少数。通过这些方式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磨灭中国青年的民族性。日伪当局在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同时,也在黑龙江地区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高等学校:哈尔滨农业大学(1940年创办)、佳木斯医科大学(1939年创办)、北安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龙井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等等。日伪虽然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但是规模不大,学校招生人数并不多,而且学科偏废,以工科、医科、农科为主,突出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高等教育方面采取急功近利违背规律的政策和措施,为其殖民掠夺目的服务。在抗战胜利之后,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在日军投降后由苏军占领,国民党军接收不久便被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赶走,实际上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开始之前整个黑龙江地区便处于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直接控制之下。此后中共对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造与建设,在1948年8月之前,中共以原先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来改造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将其变为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共改造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批新的高等院校: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东北行政学院、东北铁路学院、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专门学校等等。1948年8月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整个东北地区即将解放,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而从事建设必须拥有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因此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开始了新型正规化的过程,逐渐确定了新的学制、新的课程标准等等,在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新型正规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在高等教育的改造过程中,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在具体学习方面,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切制度都要采用苏联高等学校的制度,本科教学计划及课程也全部按苏联高等学校决定,并全部采用苏联高等学校的课本。并且要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实行苏联教育制度的全部经验和采用的教材有系统的全部介绍给全东北的高等院校。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在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绩显著,从几乎零基础发展到具备一定规模,在这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1912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为第一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寇投降为第二阶段,1945年日寇投降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在这几个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特征完全不同。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除了受到政治的影响外,还受外来因素影响强烈,早期受俄国教育影响,后受日本影响,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高等教育的改造与建设又借鉴了苏联模式。1912年至1949年,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看成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政府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总体上是伴随着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产生,呈现出强烈的近代化趋向,并为近代化服务。
高俊[7]2012年在《清末阅报社团述论》文中认为阅报社团在清末新政时期的兴起,是近代以来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产物。戊戌之后白话报刊的崛起促进了以底层社会民众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活动,在官方和民间人士的共同提倡之下,阅报社团在各地得以广泛组建,其所从事的阅报、讲报活动在清末最后数年间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在增进民众智识与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一定成效。阅报社团所采用的种种社会动员策略,也为之后的历次民众运动所借鉴,至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舆论宣传模式。
仲兆宏[8]2010年在《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文中指出常州所在的江南地区是我国古代宗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宗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宗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明清时期,常州地区的宗族众多,声名显赫。晚清,时代急剧转型,常州宗族竭力适应社会变迁,寻求自身的生存之路。作为恢复被太平天国战争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慈善事业,政府呼吁地方社会的配合和协助,常州宗族及其士绅在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下,利用政府经意不经意让渡的制度空间,修建和创建了大量的慈善组织,使常州慈善组织的规模达到了历史顶峰。慈善组织救助了大批的弱势人群,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社会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宗族提升了社会地位和声望,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宗族的生存和发展。晚清,常州宗族通过对宗族成员的族内教育,不仅提升了族人的自身素养,使之成为维持宗族秩序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宗族及其士绅依靠国家进行社会重建的制度性空间,极力恢复和维护传统的社会教育资源,重建和新建了府学、县学、书院、义塾等各类教育机构,以恢复传统的地方社会秩序。这实际上是宗族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采取的一种维护和振兴宗族的重要举施。在“清末新政”期间,在国家法理层面上,宗族和士绅兴办新式学校,任职于新式教育的各类管理结构,为常州的新式教育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晚清常州宗族寻求生存空间,调整生存策略的过程。如果说祭祀事业在于调适地方民众的心理状态,以求压抑情感的有效释放,那么河道疏浚、修桥铺路、清道路灯、公园、图书馆等公共事业则在于关注地方社会百姓的日常生计,关注他们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利益。晚清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情势使得地方政府关注公共事业的精力和财力不敷,治理不善。在这一历史的转折时期,常州宗族及其士绅完全或部分代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公共工程事业建设,客观上完善了地方官员的部分职能,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秩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宗族的褒奖和依赖大大提高了宗族的名望,地方民众的感德之意也激发了对宗族的钦佩与仰慕。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宗族掌控地方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说是宗族求得生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晚清常州宗族及其士绅依靠宗族的社会关系、经济实力和个人能力,利用国家自觉不自觉的让渡社会事业的操作空间和法理性的制度性空间,重建和新建地方社会的慈善组织、重建地方社会的传统教育体系、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从事地方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在造福桑梓、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同时,宗族努力寻找着自身的生存空间。宗族扮演了社会事业发展与转型的主角,社会事业提供了宗族生存与变迁的舞台,宗族和社会事业双向促动、双向构建的视域交融,表明晚清常州宗族能动地适应社会变迁的同时促进了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果我们仅把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在地方社会事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宗族的长袖善舞留给了历史亮丽的色彩。
王曙明[9]2009年在《宁夏近代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教育界、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倍为关注,在深入探讨各民族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同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回族教育,因其人口众多、分布甚广,且较好地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而更受重视。近代宁夏,作为回族之乡,无论是就其传承伊斯兰教文化为主的宗教教育而言,还是以其普及大众文化知识的国民教育而论,都在西北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研究宁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为近代回族教育研究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提供了典型范例。对于今天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立足于发掘和整理近代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试图对宁夏近代教育进行全面研究。按照宁夏各民族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将全篇分为五章,加以论述:第一章,清末新政前的宁夏社会与教育状况。同治年后,宁夏人口锐减,清政府为加强对宁夏回族的统治,强行迁徙众多回族到宁夏穷山僻壤之地,造成宁夏回民聚居地区教育严重落后,以及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等问题。清末新政前,宁夏府州县学、书院、社学、义学以及私塾都是为科举服务,注重伦理道德教育,轻视生产技能培养。宁夏经堂教育重在为清真寺培养宗教职业人士,小学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和一般宗教知识,大学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和教法等。教会教育,围绕经言要理,实施汉语识字教育等。这时期,宁夏回族子弟就学经堂教育的多,去官学、社学、义学的少,这样使得宁夏回汉各民族接受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的距离拉开了。第二章,从清末新政到1929年宁夏建省前,宁夏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宁夏改满城书院为驻防满营两等小学堂,开启了宁夏近代教育的先河。此后的近30年,宁夏普通教育,尤其是宁夏回族普通教育在多方人士的推动下,近代化教育逐渐开展。这一时期宁夏兴办学校,无不渗透着回汉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创教育未来的新气象。许多清真学校聘请汉族教员任教,学生入学也是回汉兼收。同时,入读普通小学校的回族学生也有增加。与此同时,宁夏经堂教育虽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变革大潮中,但因其教育自身的封闭性而一时难于适应性地向前变化发展。第三、第四、第五章,以专题形式,分别论述宁夏建省后的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讨论建省后宁夏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探讨建省后宁夏学校式社会教育、变革的经堂教育与教会教育。1929年宁夏建省后,作为边疆省份,其教育政策主要倾斜于边疆教育政策与义务教育政策。边疆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化特殊为相同,以期达到各民族教育的平等、统一发展。义务教育政策,是逐级将普及一年、二年乃至四年儿童义务教育与推广民众识字、扫除文盲等的社会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教育政策的正确制定不能代表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教育行政管理的作用。建省后,宁夏教育行政机构虽逐步建立健全,但因教育经费极其有限,所谓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也只能是巧妇难于无米之炊。宁夏国民教育,以其建省后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人数来看,呈现金字塔式的发展状况。初等教育,以普及义务教育为中心向着规模化方向发展,施教对象不仅面向学龄儿童,而且辅助广大失学民众受教育;中等教育,发展空间不大,仅拓展有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及中学教育等;所谓高等教育,只是宁夏当地政府利用外在教育资源培养本地学生接受国内留学与国外留学教育,而宁夏本省内并未建立起实质性的高等院校。就学校式的社会教育而言,宁夏建省后入学民众虽年有增加,但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宁夏经堂教育在变革道路上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变革的结果使宁夏经堂教育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与此同时,宁夏教会教育也适时调整了教育方针、办学形式和方法,进而得到发展。总之,宁夏教育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既体现有与西北乃至全国其他省份相类似的教育共性,同时又因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背景而独显其近代教育特色。
刘福森[10]2008年在《劝学所探析》文中提出清末革新教育,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标志着中国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劝学所由严修于1905年在直隶首创,后推广全国,历经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直至被教育局所取代,存续18年。其间多有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筹款是劝学所的首要职责。劝学所面对教育财政的极端困顿,实行“就地筹款”原则,采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诸如发动社会捐助、整旧从新、增加教育捐税、征收学费等手段。劝学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近代初等教育,包括一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劝学所作为基层教育行政机构,除了主动劝办新式小学堂、发展社会教育设施外,就是通过贯彻学部的法规、命令等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劝学所的设立促进了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劝学所作为民间私塾的主管机构,面对新式学堂与旧式私塾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由困顿转而力主改良私塾。通过调查、劝导、培训,增设新式课程,采用新式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等,积极促使旧式私塾的近代化转型。劝学所作为地方教育行政的组成部分之一,与作为其咨询辅助机关的教育会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存在劝学所对教育会的设立扶持,又有妨碍教育会成立的事实;既有教育会对劝学所的行政辅助,又有对劝学所行政权的侵占。总之,劝学所与教育会是一个既合作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
参考文献:
[1]. 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地区新式教育述论[D]. 杨晓军. 吉林大学. 2005
[2]. 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D]. 裴文玲.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3]. 清末民初黑龙江近代教育述评[D]. 王脉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4]. 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D]. 吕晶.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5]. 清末半日学堂研究[D]. 唐彬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6]. 民国时期黑龙江高等教育述论[D]. 徐振岐. 吉林大学. 2013
[7]. 清末阅报社团述论[J]. 高俊. 社会科学. 2012
[8]. 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D]. 仲兆宏. 苏州大学. 2010
[9]. 宁夏近代教育研究[D]. 王曙明. 西北大学. 2009
[10]. 劝学所探析[D]. 刘福森.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标签: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教育论文; 清末新政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大学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东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