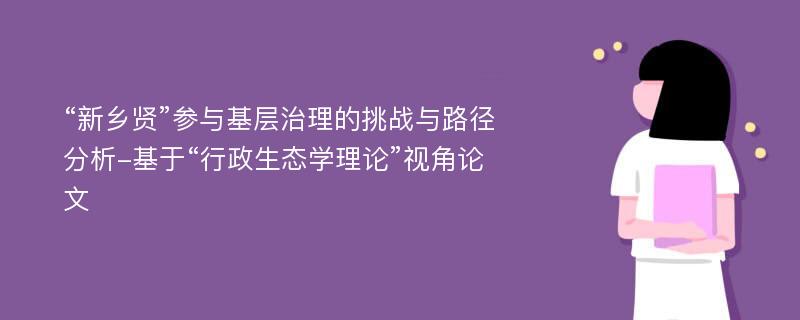
“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与路径分析
——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视角
张志明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新乡贤”有知识、有道德信念、有理想追求、有资源优势,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良好发展带来了新动力。“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和发展,其在参与基层治理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本文从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视角中“社会因素、符号系统、政治架构”三个部分分深入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路径对策。
关键词: 乡贤文化;新乡贤;基层治理;行政生态学理论;乡村治理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1]政策上的支持引导“新乡贤”的发展,为“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制度基础。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全国多地积极开展融合“新乡贤”力量,推动乡村振兴在基层农村扎根壮大。
《政府会计制度》要求高等学校会计核算应当具备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双重功能,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在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当进行预算会计核算;对于其他业务,仅需进行财务会计核算。同时要求高等学校对基本建设投资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的规定统一进行会计核算,不再单独建账,但是应当按项目单独核算,并保证项目资料完整。
一、“新乡贤”传承发展和行政生态学理论阐述
(一)“新乡贤”传承发展
新时代的乡贤继承“传统乡贤”参与基层自治、维护乡村稳定和谐、传递家庭美德与礼俗教化德治的传统,又具有现代法治理念,能弘扬践行优秀乡贤文化的礼治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村民、发展农村经济,振兴乡村。“新乡贤”成立的组织是基层民主协商的组织,可以在基层多元治理中发挥“智库角色”,辅助村两委,发挥补充和协同作用,推动乡村基层的振兴发展。目前,基层组织里的“新乡贤”成员构成主要:有经商成功的企业家,有德高望重的退休公职者,有专家学者,有基层农村致富的精英能手和有工作经验的回乡务工者。“新乡贤”从理论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2]“新乡贤”成员要有责任担当、使命担当,发挥智力才干和资源优势来振兴乡村。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激励、劝勉乡民,教化乡村社会,它还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为了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发展这一难题,尤其后者,是当代新乡贤文化建设所肩负的全新的历史使命。[3]“新乡贤”秉守着乡贤文化的道德标准及自身爱家爱乡情结,以政府“元治理”的引导来实现“新乡贤”的自我价值和社会的尊重。
(二)“行政生态学理论”阐述
行政生态学首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提出,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对该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行政生态学是生态学与行政学交叉融合所生成的。[4]里格斯对法对美国、泰国、菲律宾进行比较分析,从生态学角度对公共行政与政府行政环境间相互影响进行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行政生态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主要包含:三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基本行政模式以及五种行政生态要素等。里格斯用结构功能研究“融合-棱柱-衍射”模式,分别以经济、社会、沟通网、符号、政治架构因素加以分析,这种方式奠定了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基础。新时代振兴乡村经济、治理乡村社会,借鉴里格斯对三种社会形态的行政模式转变中总结的五种因素分析“新乡贤”,以便“新乡贤”更好地助力乡村经济振兴、社会发展。“新乡贤”吸收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治理理念,又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繁荣乡村经济、增进乡村生活和谐、实现村民自治民主有序、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上,形成“有尚德富民之心”的“新乡贤”。基层治理中如何衔接融合好“新乡贤”力量,实现“新乡贤”与村民之间经济双赢、利益兼顾,基层组织内社会成员之间信任与沟通理解,协同好“新乡贤”与村民及村委会之间的合作治理,这些是治理的关键。
二、“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因素”对“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以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并称其为“社团”;这些“社团”与国家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5]“新乡贤”是以群体组织为依托,以血缘地缘的“乡愁情怀文化”关系为纽带,汇聚“新乡贤”回乡富村的力量,凝聚彼此间信任关系。“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存在的相互信任挑战:一是“新乡贤”与村民之间存在心理上认知偏见的信任挑战。“新乡贤”与村民以往沟通联系较少,两者初期磨合由于知识构成、视野经历不同,易产生意见分歧和不信任偏见。初期村民关注现实的实惠,有些村民认为“新乡贤”是有影响力的“势派”、又是投资方,会着重关注企业利润及长期发展利润;也有村民考虑“新乡贤”会不会出现“损公肥私”。“新乡贤”在积极承担家乡的社会责任、回馈家乡村民福祉时,会考虑资金成本、技术水平、规模效益、涉及村民利益的协商难易程度等方面,推迟或减少家乡建设的福祉规模,达不到村民眼里的“乡贤义举善举”行为,此时,村民会对“新乡贤”有不信任的感受。二是“新乡贤”与政府、村委会之间协同治理的信任挑战。同时“新乡贤”与“村委会”之间关系仍需明确界定,厘清二者事务方向。一些村干部官本位意识强,民本位意识淡漠,认为“新乡贤”能力强,会削弱自己的权威、地位、话语权,甚至会阻碍自己谋私利。[6]对待“新乡贤”信任的态度上不冷不热、不主动积极配合“新乡贤”工作,使“新乡贤”积极热情度锐减,影响基层治理绩效。
(二)“符号系统”对“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
该要素强调政治与行政应相对分离,政治领导着行政,而行政则实现着政治的目标,二者存在着一种“功能依存关系”。[7]在中国的政治下政治与行政是有分工且又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具有重要的特殊作用;这就决定“新乡贤”参与基层自治时,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村两委”协同治理基层、振兴农村经济。“政治架构”的独特性对“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有:一是乡村“强势势力”与县域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双向利益契约“耦合”上的挑战。在乡村治理内部场域,乡村自治事务一定程度上被“宗族势力”“强势能人”所控制,更有甚者被“村霸势力”控制,一些存在巨大利益的乡村,暴选贿选等违法现象层出,目的是便于获得好处,也使乡村的村规乡约被破坏。县域乡镇政府派驻人员参与乡村,干预指派村委会人选,乡村“宗族势力”“强势能人”“村霸势力”等以多种手段和力量参选成功、只等着乡镇政府认定后就可以确定了,乡镇政府选取符合心意的管理乡村的“代言人”,以便于当选村两委人员配合自身的工作开展,完成或者满足自身政绩利益的需要。这种双向利益的“耦合”破坏了村民自治制度,也使得“新乡贤”运用村规乡约文化进行乡村治理的实效受损。二是避免“精英决策”对“乡村大众决策”控制上的挑战。乡村精英可以分为“在村精英”和“离村精英”。长期实际参与的且又具有资源优势的“新乡贤”是“在村精英”的组成部分,“在村精英”参与基层治理决策时会有“隐性的势”权威与话语权,逐渐产生“精英决策”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偏离村民大众的决策。
(三)“政治架构”对“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挑战
符号系统提供的“共同意识”是形成权威的必要物之一,这种“共同意识”通常潜藏在政治神话、政治准则或政治法典内。[7]“符号系统”对“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上的挑战:一是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人情冷漠,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对基层治理理念意识上的挑战。当下,“对外开放”政策的继续深化,以及外来多元文化的交织影响;城镇与农村发展差距拉大,商品发达与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人皆往之,导致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就业、务工、定居,乡村优质人力资源不断流失,农村发展衰败,乡贤美德文化和符号系统受到冲击,传统乡贤文化日渐淡薄凋零。现有的乡村文化基本上是“利益导向、金钱至上”的文化,将乡村事务建立在利益衡量之下,基本上丧失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也没有有效吸收现代优秀的核心价值文化,更没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使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沙漠”。[8]二是“乡贤情怀文化象征的符号”流失对基层治理带来挑战。“乡贤情怀文化象征的符号”:如“宗族家谱”是血缘脉连印记的文化符号,“宗族祠堂”是缅怀先祖、慎终追远的文化符号,“先贤庙宇”是尊敬先贤、传承精神的文化符号,“古城”与“古房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手艺”都是历史智慧文明的“活化石”及浓浓的回忆乡愁情怀的文化符号;这些象征文化符号在现代文明和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渐渐走远没落了,也使“新乡贤”内心“趋同回归感”减弱,不利于发挥优秀乡贤文化教化作用,也不利于相关“乡贤文化象征的符号”保护与经济链的开发。
传感器俯视图如图2(b)所示,磁通门传感器两个励磁绕组均匀绕制在磁芯通孔的左右两侧,绕组匝数相等且方向反向串联。励磁绕组产生的励磁磁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围绕通孔组成闭合磁通路径。外部激励源产生频率和幅值稳定的高频方波,使励磁线圈中的磁通产生周期性变化。因此,当激励电流达到峰值时,相应的磁芯中的磁场接近最大值。忽略通孔两边微小不对称,假设通孔左右两边几何参数和电磁参数完全相同,则在检测线圈的感应电动势将互相抵消,因此激励电流只起到调节磁芯磁导率的作用。
“新乡贤”、村民、村委会成员、政府(尤其县镇政府)以地缘间的乡贤文化为向心力,乡土情怀与乡愁基因文化为纽带,形成的社团精神、信任关系。首先,培育“乡贤文化”价值,倡导团结信任关系理念。乡村开展节日活动增强家乡情怀与乡贤文化团结共鸣感价值,举办非正式的联欢会以及“新乡贤”入村后的生活文化欢庆会,增进心理融入感、尊重与信任价值,重塑包容团结的成员间信任关系。其次,增强“新乡贤”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所产生的农村“经济共生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内没有达到,村民要理解且远见卓识地看待与信任;“新乡贤”既要做好眼前真诚服务工作和实惠之处,又要与村民协商交流长远发展实效目标。这样才能消除二者的怀疑与不信任感,增强乡贤文化的内聚力。最后,根据制度建设实行县镇政府、“新乡贤”、村委会成员、村民的多元间协同治理的信任理念。在政府“元治理”下,多元主体间是多中心的、各有分工、相互信任合作、协同治理,增强基层农村自治实效,逐渐磨合形成一套具有乡贤文化基础的价值观,来提高信任程度,同心协力发展农村经济繁荣。
三、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培育“新乡贤”社团精神,重塑社会信任关系
此次,安徽省启动无违建县(市、区)创建,明确考核标准,主要包括存量违法建设治理到位、新增违法建设管控有效、防违控违长效机制、拆后土地充分利用、社会平安稳定等五个方面。定性考核方面,亮出3条“红线”,即对“存量违法建设治理到位”“新增违法建设管控有效”和“社会平安稳定”三项考核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创建工作将治理存量违法建设,严格禁止新增违法建设,形成防违控违长效机制,实现违法建设零增长,提升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二)创新“符号文化”治理。发展“新乡贤”回乡建设乡村要传承美德、凝聚共识、创新新时代乡村“符号文化”
一是建立表彰为村民作出贡献的“新乡贤”的物质载体,赞颂其功德。在乡村或者乡镇上建立新时代的“乡贤馆”、“乡贤牌匾”、“乡贤美德事迹照片或绘描像展”、“乡贤功德载入志记”等物质载体记忆,赞扬其服务精神、传颂其功德。在过年过节举行庆祝活动时,先从“乡贤馆”或“乡贤祠”处开始,以表达对“乡贤”的缅怀、敬重、传颂与继承;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宣传“乡贤功德”,以及在报社或电台新闻上宣传“乡贤功德”,实现“新乡贤”的人生价值与社会评价相兼得。二是保护与修缮“物质符号实体”,发扬“物质符号”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中的“物质符号”,如“家谱祠堂”、“先贤庙宇”、“古房屋”与“老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手艺”等,这些都是“同源乡土乡愁物质符号”的象征,强化“新乡贤”内心情感价值观共鸣的回归和身临其境回忆的思绪情怀。保护与修缮“物质符号”可以保护文化资源,发展乡村适度的“文旅”效应。
(三)加强制度建设,深化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
首先,健全基层民主协商与村民参与制度。用制度保障村民有序参与利益表达机制,以及政府、“新乡贤”、村委会成员、村民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方式。其次,完善基层多元监督举报与县域政府(包括监察委员会)的严查处理制度及信息公开制度。“新乡贤”成立“议事监督会”组织,监督“新乡贤”自身成员及其他主体的违法行为;依法监督查处及信息公开制度保证村民选举的公正公开性,治理乡村“强势势力”与县域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双向利益契约的“耦合”现象,切实构建一个村民自治的良性的乡村社会。最后,明确“决策商议上”是基层多元民主协商,裁定“决策方案上”是基层“新乡贤”、村委会之间为“主辅”、“谋断”的关系。基层多元参与主体间协商决策乡村事务,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界定“新乡贤”“是辅、是谋”,村委会“是主、是断”,二者是协同的、多元共治的、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新乡贤”作为精英成员可以发挥其“智库方”角色,帮助“村委会”
协同治理的实效更符合村民的愿望,增进村民的认同感。“新乡贤”弥补“村委会”治理过程中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也进一步拓宽了村民自治实践的治理主体范围和治理形式,“村委会”也可以协调动员村民配合“新乡贤”发展企业所需的相关资源,振兴乡村经济。
[ 参 考 文 献 ]
[1]中共共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2018-02/ 04/ content _ 5263807. htm,2018-02-04.
[2]李思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J].人民论坛,2018(03):29.
[3]季中扬,师慧.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18(01):185.
[4]黄爱宝,吴頔.国内生态学研究概览及其检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39.
[5]陈婕,孙国峰.共享经济对我国公共行政的挑战及应对路径——基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J].行政与法,2018(02):22.
[6]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6(08):89.
[7]王力,朱良.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与转型中国公共行政环境分析[J].理论研究,2016(05):55.
[8]李金哲.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J].求实,2017(06):89.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 (2019 )18-0127-03
作者简介: 张志明(1989- ),男,汉族,河南周口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