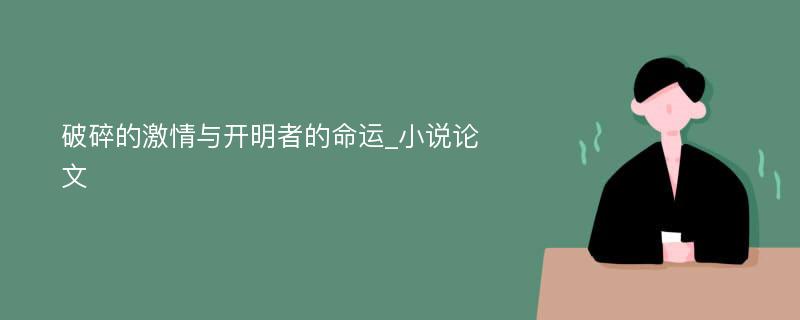
破碎的激情与启蒙者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运论文,激情论文,启蒙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问张梅:你的小说里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这很特别,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想起要这样写?听了这话,张梅似乎有点吃惊:我的小说有超现实主义?我怎么不知道?
对张梅的回答我并不太奇怪。有不少作家都是这样的,他们迷恋写作如同探险家迷上了探险,尽管伴随着探险免不了会有种种和探险无关的啰嗦和纠缠,免不了会有种种以探险为名却实际上要你偏离探险的诱惑,但探险的冲动最后还是压倒了一切,让他们一如飞蛾扑火一般向目标扑去,至于结果会如何?他们并不很清楚,也没法儿把握。不过,这样傻气的作家今天已经不多了,因为如同探险本身如今已经成了实现金钱效益的商业行为,写作也被织入了追求“经济效益”的历史过程之中。飞蛾们已看不清那迷人的灯火在何方,他们面对的是一张金光闪闪的大网,投身于上的每一个飞虫都在似真似幻地发出片片光彩,有如霓虹。
如果不留心,《破碎的激情》(以下简称《破碎》)这个长篇小说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并不能一眼就看清楚。在张梅的叙述中,它们不是以形成整个小说的结构框架的形式出现的,相反,它们是零散的,断断续续的,像一群散兵游勇,随随意意地出入在人物、情节、细节、景物描写等层面里,不仅使小说有了一种诗意,给叙述带来一种抒情散文的格调,而且还使故事获得一种梦一样的气质。这使我在阅读中,时常想起孙甘露的小说《访问梦境》。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阅读这篇小说时的那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迷离恍惚的感觉。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感觉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每忆起仍然新鲜如昨。但是拿《破碎》与《访问梦境》相比,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在孙甘露那里,超现实主义是小说叙述的主要技术和框架,这主要表现在《访问梦境》里不仅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而且没有具体的社会环境,没有时代特征,有的只是惟有汉语(应该强调,是现代汉语)才能营造出的种种华丽的意象,正是这繁密华丽的意象激流构成了一个虚幻的梦境,这梦境引诱每一个迷恋语言魅力的读者去访问它。《破碎》则不同,张梅无意讲一个超越具体时空,没有具体社会环境的梦幻故事。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有人物和情节,还有具体环境:广州,有具体时间——八十至九十年代。但是,几乎小说中的一切叙述因素都被巧妙也可以说是微妙地偏离了现实,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快餐文化”迅速兴起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之后,没有耐心是当今阅读的最显著的特征),读者在表面上相当“写实”的故事中,不仅时时能够发现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事情,而且还能与种种奇迹甚至是神迹相遇。对于喜爱阅读的人,特别是喜欢在阅读中有奇遇的人来说,这恐怕是一种难得的愉快经验:你本来是到一条相当熟悉的小路去散步,不料意外地在路边看到一些奇花异草,虽然稀稀落落,可是它们一下子使这小路变得可爱而且陌生。
在《破碎》中展开的故事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故事里的一群主要人物都在八十年代有过一段激情迸发的浪漫经历,并由于都自认为是一些“不屑于陈腐而追求真理的人”,他们聚会,念诗,唱《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谈恋爱,办杂志,“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为“开拓思维”“吵得天翻地覆”,立志要成为“社会的前驱”。但是很快(小说并没有指出确切时间,似乎是八十年代末),这伙人的“教父”圣德, 在一天的傍晚看到两群十三岁左右的女孩子告别时互相挥手叫“byebye”之后,立刻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随即宣布:“新一代以他们全新的感受方式,正绕过我们至今还未完成的裂变去拥抱新世界”,“他们将比我们快二十倍地掌握打开这个新世界的金钥匙”。鉴于“他们今后都将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圣德发问:“我们这些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字游戏,自以为探索灵魂的人的出路在哪里?”他的回答很干脆:“我们必须更新自己,重新入世。”《破碎》的主要篇幅都是以圣德为“教父”的这个群体,在九十年代怎样“更新自己,重新入世”的一幅幅图景。这些图景构成了我们并不陌生的一卷当代生活风俗画:美容院、公关小姐比赛、到处行骗的气功大师、由于仅仅用了“秋天落叶”这样一个怪笔名就红起来的女作家、渴望过做贵妇人的女老板、挤满了“大大小小寄生虫”的桑那浴室、为“一夜偷欢”而努力积攒激情又屡屡失落的男男女女。这真有意思,昨天还在“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的圣德们,此时已经成为“一个个有钱有闲”地隐没于这画卷中的主人公。这当然充满了讽刺意味。从一定意义上,张梅的这部长篇小说,也真的可以当做讽刺小说来读,只是张梅的讽刺很少表露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像一个淡淡的影子,无时无刻不跟在几位主人公身后。例如,小说描写在九十年代“更新”了自己的圣德(他此时不仅当选为广州十大杰出青年,而且成了腰缠万贯的青年企业家,广州市蓝箭公关学会的会长)走进一个桑那浴室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身穿西服打着黑领带的年轻侍者把他带到房间后,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句:先生请慢用。这句话让圣德陶陶然,“他很喜欢年轻男人说的‘慢用’这个词。他想,要是我是他的老板,我会给他加工资”。联想到这人在八十年代曾是无数“追求先进思想”的青年的“教父”,他住的那间破旧的铁皮屋曾被他的崇拜者视为“圣殿”,这个细节的讽刺其实是很辛辣的。由于圣德们在九十年代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八十年代的信仰追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时不在,我们在阅读《破碎》的过程中,时时可以和这种不动声色的讽刺狭路相逢。而且,对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说,特别是对一个敏锐的批评家来说,在与这样的讽刺反复相遇之后,他不能不认真考虑这讽刺所指向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不能不把这讽刺和在八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个事实联系起来:不是在小说里,而是在现实里,为数相当不少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当中转换了身份,成功地变成了企业家、老板、大腕儿、百万或千万富翁,这些人中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当年“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本来,这一转换早已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结果,这有什么可说的?但是阅读《破碎》却使我们突然看到这个司空见惯的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回想八十年代的许多往事,回想往日的那种种激情,以及那激情在当时所指向的目标,同时还不禁要拿这些和今日相比,特别是和那些昔日为“追求真理”、探索“新观念”而激动,今天已经是大腕儿、老板的人相比,我们不能不想到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这里有某种讽刺。当年成为思想界“前驱”的人们,他们曾想到日后他们会变成企业家和老板吗?他们曾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吗?或者预见到他们昔日的激情一定会逻辑地导致今天的结果?我觉得事情不是如此。那么,今天这样的情势又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引出这样的历史讽刺的动力?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一历史的讽刺?感谢张梅,是她的《破碎》迫使我们重新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讽刺还不是张梅这个长篇的最重要的特色。尽管讽刺因素使得《破碎》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张梅的叙述激情似乎并不想太多地依赖讽刺,她对某种超现实主义的可能性更感兴趣。这些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形成小说叙述更重要也更有趣的特色,它使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总是和种种超验的神迹,一般逻辑不能解释的怪事,以及形形色色的荒诞纠缠不清。读者在小说里可以碰到米兰这样的女人,她除了偶尔和情人们热情奔放地做爱之外,主要事情就是睡觉,每睡必数天数夜;读者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个瞎眼的富婆四处张贴寻求“读书伴侣”的广告,只是每一个应招来读书的男性“伴侣”还得为她提供性服务;小说的第一号女主人公黛玲则有奇迹在身:她的额头上经常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紫色唇印,而且每当这唇印出现,她就会重新获得美丽和青春;我们还能与这样的场面相逢:为了制止黛玲和她的情人厮打,子辛(小说中的一位现代都市中的漂泊者)忍不住用英文喊了一声“STOP”,结果这“STOP”的喊声遍及广州城,连出租汽车的司机们也都加入了高呼的行列,一时响彻云霄。这些超现实的叙述因素给小说的读者一种新奇的经验。《破碎》中展开的生活场景本来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特别是那些与市场经济的蓬勃相联系的九十年代都市生活(这在小说里占了大部分篇幅),无论其中的许多人或事是多么荒唐,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经张梅叙述,这些我们天天经验的当代都市生活突然和我们拉开了一个距离,变得有点陌生,我们有兴趣去把它当成一个新鲜东西再仔细看一看、瞧一瞧,没准这里有什么事有什么人值得琢磨一下。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张梅在把现实生活加以夸张、歪曲、变形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变成完全脱离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可怕的梦魇,或者是一个脱离九十年代具体时空的荒诞世界。张梅的世界并不让我们联想起达利或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这些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 她对人的潜意识世界,以及从潜意识和梦境出发去阐释世界似乎没什么兴趣。《破碎》中展现的一幅幅画面,倒更容易使人联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凯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或迪克斯(Otto Dix)描绘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它们是本世纪初德国人所熟悉的德国的都市生活景象,人们很容易从画面中认出柏林的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但画家通过歪曲和变形强调了他想强调的东西,也在这强调中批评了他想批评的东西。张梅在《破碎》中描绘的当代广州生活,同样有这样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效果。问题是张梅通过这种苦心经营的“似与不似之间”想干什么?或者换一个想法:读者和批评家能在这苦心经营中读出什么?我想,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主题上来,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中社会角色的转换。
有意思的是,张梅并没有直接去写这一转换,非写实主义的写作使她在观察和再现这个转换的时候有了另一种可能。在似真似幻的叙述里,《破碎》中的人物个个都不同程度上像是梦游人,他们有热烈的追求,但那追求可以突然放弃;他们有目标,但那目标虽十分绚烂却变幻不定;他们总向往一种“如火如荼的生活”,但不能有持久的热情;他们不仅总在梦想另一种更美的人生,而且还以假乱真地就在这梦想中生活。这是一群色彩十分驳杂的人物,其中不但有圣德这样的“教父”式的充满象征味道的形象,还有诗人、大学生、爱好文学和文化的老板、崇拜名人的闲人,甚至还有“蔑视工作”、以专门大谈哲学骗吃骗喝的职业骗子,以及身兼“新潮发型师”和“现代西门庆”双重身份的今日都市浪子。就是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听凭“理想主义”的引召形成了一个群体(经历八十年代的人大约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吧,那时候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多这种群体),并且在“教父”圣德的率领下一时成为“社会先驱”。然而在九十年代,同样是这些梦游人,又毫无障碍地滑入另外一个生活航道,开始了另一种梦游生活。黛玲开了一家美容院,不但生意火得不得了,而且如同八十年代的圣德,有了无数崇拜者,只是崇拜者们崇拜的不再是理想和真理,而是黛玲保持美容使青春长驻的秘密。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面:“等调音师把琴调好了,黛玲穿上黑色缎子做成的旗袍,坐在白色的钢琴前,弹起一首江南小曲《茉莉花》来,几百个女黄褐斑患者随着她的琴声,像幼儿园的小孩那样齐齐排着队坐在她门前的木楼梯上,拍着手整齐地唱起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又白又香人人夸,又白又香人人夸。’”这是一个三分真实七分荒诞的场景。由于小说还告诉我们,此处的几百位“女黄褐斑患者”不是等闲人,她们也都是老板级的富人,这个场面的象征意义就更耐人寻味。真是时代变了,不再是一群杂牌军跟在“教父”圣德之后去争论什么存在主义,而是老板们集合起来跟随美人黛玲合唱“美丽的茉莉花”。与此相映,“内心万分痛苦”的圣德在九十年代的“梦游”显得更符合梦的性质,混乱、破碎、前后不连贯、乱七八糟又在深处有一种和谐。他拒绝了崇拜者们为他在高级住宅区买下的电梯洋房,继续住在那间和他的名声紧紧相连的破旧的铁皮屋里,因为他还想“在这个享乐主义弥漫的城市里坚守思想者的大本营”;但是他又厌烦生活里“有太多的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乐,现行世界都奉行一种叫做快乐原则的东西”,于是又安心地去大酒店和经理们相会,去桑那浴室享受。他在老板和经理中寻找旧日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在理想主义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对今日这个物质社会充满了不满和鄙夷”,但是他和他们凑在一起热心商量的却是“要建立一间铸造完整人格的贵族学校”,还设想这学校的学生“第一本要读的书就是《格瓦拉传》”。复杂之处还在于,圣德在梦游中还有一份难得的清醒,知道自己是在从一个梦里向另一个梦里堕落,“他特别喜爱在黑夜里灿烂的东西。在这些灯光下,他的思维像充了电一样活跃,有时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些黑夜的灯光。而黑夜要是没有了这些灯光会有多么寂寞呀。这些灯火辉煌的建筑物在黑夜里散发着他所喜欢的糜烂的气氛,好像在说:来吧,来吧,来清醒一下吧,来快乐一下吧。他就会抑制不住地走进去”。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清醒地走进糜烂,并且享受在两个梦中游动的乐趣。发了一阵小财的子辛成了终日混迹于夜总会的无赖,睡美人米兰患了精神分裂症,而红极一时的老板娘黛玲最后发狂,成了疯子。难怪圣德在一次讲课中宣布:“这一代人完结了。”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台下面寻呼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圣德的这句包含着痛苦激愤的话就被淹没在现代传呼工具的噪音之中。”这倒不是梦,是我们常见的场景,司空见惯。
张梅这部长篇小说当然不是对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命运变化的全面概括,她似乎也从没有想过要做这样一件事。但是,《破碎》对圣德为首的这群梦游人的描写,无疑表达了作家对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近二十年中社会角色的变化的某种看法。这些看法读者们是否会同意,那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法子一致。不过张梅至少以她的小说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弄潮儿”们,面对九十年代的巨大社会变迁却不仅丧失了思考和批判的锋芒,而且其中很多人那么容易地认同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近两年思想界和理论界已经对这类问题展开了讨论,而且导致相当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一个焦点是对八十年代在知识界中进行的知识建设和话语建构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当前的社会状况是推行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结果,但是他们忽略了: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得到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的支持才能合法地进行,何况,这一知识体系不只是被动地提供“支持”,它还必定会渗透到变革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因素。从这一点说,追究九十年代物质主义的盛行,不但要分析它和商品经济的复杂关联(可以大胆提出这样的问题,商品经济是否必然要导致物质主义对全社会的支配?),还要研究它和八十年代知识建设和话语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追究是那个时期的哪些“新观念”为今天的物质主义盛行提供了框架和资源?这些“新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等等。如此提出和讨论问题,势必引出对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种种质疑,事实上,当前思想界种种争论也都和这些质疑密切相关。这些争论恐怕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有意思的是,张梅以她的《破碎》加入了这场论争,她的写作为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破碎》中充满了对八十年代激情的感伤和怀念,但非写实的立场使张梅不可能具体地描写圣德们“开拓思维”的具体内容,她集中笔墨写的是那些为“开拓思维”而聚集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正是这些人给我们以启发,使我们在检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国家的领导作用,国家和知识界的互动关系,不仅要注意少数思想家和理论家,注意那些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和文学著作,还要注意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集合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在“思想解放”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仅仅是些消极地等着被人家“启蒙”的庸众吗?还是有自己的利益并想利用“启蒙”的特定社会阶层?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当前的讨论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压根儿就没提出来。阅读《破碎》给人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圣德麾下这拨人是多么驳杂、多么混乱。“他们当中有工人、小学教师、车间检验员、银行小职员、秘书等等,他们有许多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而又热衷理想主义,他们急需一个地方说话和施展才能。”所有这些人都是圣德的理想主义河床中的浪花和泡沫,不只是圣德在影响和引导他们,他们也在影响和塑造圣德——这在小说中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张梅的小说不是八十年代思想界的“真实反映”,相反,那是一个哈哈镜,人们熟悉的一切都在这镜子里被歪曲和变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隐喻层面上把相当肤浅的圣德(至少作家的讽刺笔法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和他的崇拜者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八十年代思想运动复杂性的一个暗示。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那一时期思想界的构成,以及它和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还有它和当时社会各个成份在思想方面相互影响的方式,我相信它会比小说里描写的要混乱和复杂千百倍,可能也更让我们沮丧。我们也许会发现,什么是八十年代“思想界”本身就值得分析,至少从它内部鱼龙混杂的情况来看,当前那么多文化人和知识人热衷物质主义是一点儿不值得奇怪的。
最后要说几句的是,要是挑毛病,《破碎》的毛病实在不少。看得出来,张梅写得有些马虎,无论小说的整体结构,还是细部的语法修辞,都有很多疏漏之处。特别是,张梅尝试以一种有她自己特色和创造的超现实主义写作介入社会现实,使文学和当代社会变迁发生关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重要的文学实验,可惜的是,作家的想法和构思没有被充分实现,给人以意到笔不到的感觉。这真是太可惜了!
(《破碎的激情》,张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11.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