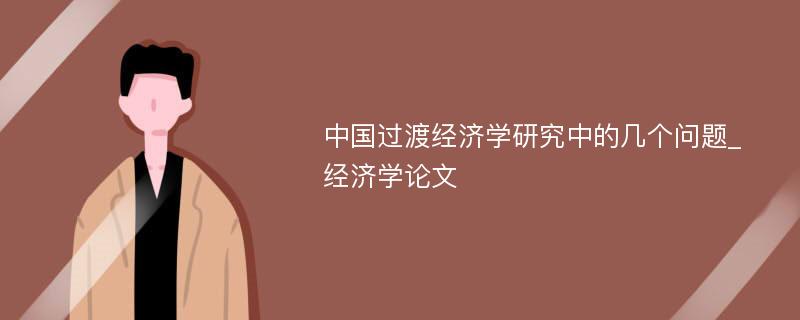
关于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李晓博士最近就“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以信函形式分别采访了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学经济系徐滇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盛洪研究员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现将采访提问和四位学者的回答综合刊于下。利用信函采访,意在更有针对性地“寻找”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理论研究问题,征求专家解答,以期获得有益的启迪。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
* *
尊敬的徐滇庆、周其仁、盛洪、张宇燕先生,你们好!
围绕现阶段“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想知道先生们的高见:
李:过渡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作为前提假定,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研究没有具体目标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否有意义?换言之,过渡经济学是否需要人为地设计一种或几种目标模式?如果需要,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徐:在我个人看来,这一类问题是没什么意义的,理论研究的实践很能说明这一点。
周:我向来只对某些问题有兴趣,至于用什么“学”来理解这些问题,我好象从来没有清楚的概念。对“过渡经济学”也没有更多的考虑,似乎是“转型经济学”还有一个tevm,(transformation Econ?)只强调“转型”,而不是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
张:首先,我不赞成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作为过渡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经济学家论谈“好坏”问题,标准只有一个,即效率原则。同时,效率本身又是有条件的,即应以所处的约束条件而定。由此而推出的一个结果便是,条件不同,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效率结果也不一样。有时前者更有效些,有时恰恰相反。过渡经济学,依我粗浅的理解,原则上讲是在考虑现实条件的前提下向更有效的体制转化。就今天的条件而言,市场经济相对更有效些。
其次,过渡经济学是否需要人为设计的目标模式问题,我大致认为重要的是方向,而不是具体的目标。在操作意义上,也许更有意义的还在于让经济当事人自己选择适合自己利益的组织或制度形式,让不同层次、选择各异制度安排的经济当事人之间产生竞争,从而促使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得以生存、拓展并发挥功能。
盛:过渡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作为假定前提,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不然的话,应首先讨论“谁好”的问题,接下来又要讨论“为什么一种经济制度比另一种更好”,以及“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怎样发现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在经济学中、以及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所讨论,并且改革实践也给出了经验上的判断。过渡经济学第一并不想假定存在几种目标模式,它的假定其实是有着经验基础的;第二承认以往的讨论已经得出了某种结论,它不过是简单地接受了经济学已经作过的工作。它强调的是,如果不考虑过渡过程,谈所谓的“谁好”、“谁坏”,那是没有意义的。
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其首要目标。因此,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那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同发展经济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具体些说,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是目的还是手段?
张:过渡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区别显而易见,这首先表现为经验起点不同。即前者讨论的是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后者关注的主要是位于南北纬30°之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以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及产权经济学等为分析工具,后者则主要运用一套发展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独立概念体系对发展问题加以讨论,如二元结构、工业化等。
当然,两者之间同时也存在有许多的相似或共通之处,比如说,发展经济学的几乎每位老师均对制度安排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眼中,决定经济发展的序参量中,制度安排,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背景,多排在相当靠前的位置。而这一思想倾向,与过渡经济学家们的偏好如出一辙。说到目的和手段,两者大体也近似,即均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制度安排视为实现经济发展或导致更为有效结果的手段。
盛:制度经济学其实一直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因此从来不存在这两者脱节的问题。所谓“制度是重要的”,其含义就是制度会影响经济效率,制度变迁会导致经济发展。而所谓发展经济学,是一种将一些技术因素,如技术进步、投资率、迂回生产方式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因,而这些,在诺斯教授看来“乃是发展”。“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显然是比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更能解释经济发展原因的一种理论。
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讲求特色,这也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突出特征之一。但目前它对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仍止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水平。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眼中,理性化的新教伦理是一种既定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经济学研究的既定理论前提,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只是注重了对习俗、某些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微观层次的研究,对宏观层次的非正式约束如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却着力不足。“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此将做怎样的拓展?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否认为用“非经济问题”解析经济问题具有理论新意?
张:中国的位置很独特: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曾是计划经济国家。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或许能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来,原因便在于此。换言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融合,即把制度变迁与人口问题、积累问题、人力资本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等等兼收并蓄,或许是中国过渡经济学对经济学有所贡献的地方。
关于“非经济问题”,我在这里打算简单说几句。这里首先涉及一个定义问题。何谓“非经济问题”?如果用经济分析工具去讨论人的行为,那么所有关于人之行为的问题便都是经济问题。文化在许多人眼中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当我们读文化功能主义的推崇者的著作时,我们便会发现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而后者无疑又构成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之一。中国的文化有其特性,更一般地,用马克思的概念讲,中国的上层建筑有其特殊性。如果承认它至少有时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话,那么,对通常被认为是“非经济问题”的问题进行经济分析,对经济学、至少是对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而言,则可能是有些理论新意的。
盛:这个问题很好,诚然,“中国特色”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对于文化,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韦伯的理论,我觉得都还太肤浅。新制度经济学,诺斯教授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但还没有看到专门的研究;韦伯只提出了新教伦理中的勤奋、节俭等品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却很少强调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如何减少了市场活动中的欺诈,如何阻止了政府的扩张,如何约束了人们心中的恶欲。所以对文化(不独是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翻译成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文化(狭义的)就是无形的规则。正因为“无形”,所以它以往一直受到忽略。但正是这些无形规则,与有形规则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制度结构,使得社会得以运转。如果我们忽略了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或“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当然,经济学并不认为有关文化的分析是“非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