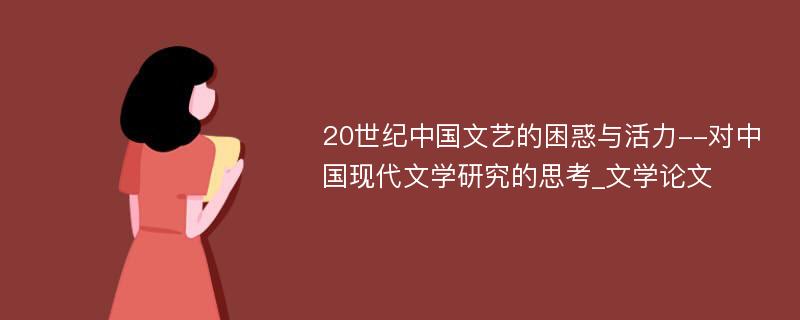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困惑与生机同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代文学论文,生机论文,困惑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读到《文艺争鸣》上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危机的笔谈(见《文艺争鸣》,93年3~4期),不期然地引发起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联想。
总体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历时的流程时,本身便是一条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始终呈展出承传、演化、发展的势头。真可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或者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这说明历史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但是,历史研究却无妨大处着眼,也可以小处落墨。宏阔的历史流派需要梳理,细微的作家作品也呼唤史家观照。通体研究历史的流变与发展,需要;切割成断代,着眼于专史乃至作家论、流派论、思潮论,同样是社会的需求。科学的发展由简趋繁,在宏观与微观中延伸嬗变,本属常态的事。《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自然是就文化、文学的本体说的,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也大抵如此。如果说,“五四”文化、文学革命给予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赋予文学历史的研究以冲击力量。从史的踪迹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史的端绪,可能始于刘贞晦、沈雁冰著《中国文学变迁史》(1921年12月上海新文化书社版)。其中刘著的《中国文学变迁史略》共分十一篇。从唐虞以前的文学说起,最后一章便是“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就现在的眼光审视,所述范围大多属于近代文学现象,但显然也包溶着新文学的业绩。比如对旧文学家引车卖浆者流的话的拨正,新体诗的提倡、“文明新剧”演出的评述,无疑都蕴纳着“五四”新文学的诸多现象。只是这时的文学变迁史依然是通体的,“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只是它的组成部分。继之问世的胡适著《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2月版,初载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所论“活文学的白话小说及文学革命运动”等内容的框架,亦莫不如此。只是,新文学的业绩,已逐步得以扩展。在结构形态及内蕴上具备学科的独立品格的,当推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其中的八章:背景、经过、“外国影响”与现在分野、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现代目光。这是朱自清从1929年起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所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教学大纲。其中许多论点,仍为今人所参照。如讲述茅盾时所陈:a、“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b、“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c、“恋爱的外衣与阶级的意识形态”;d、三种女性的型;e、都市女性心理的剖析,等,在历史的沉淀中仍不减其理性的光采。只是当时并未被更多的学人所认知。到了1982年才经赵园整理,王瑶介绍刊于《文艺论丛》上。
开国后,王瑶、丁易、张毕来、刘俊松、唐韬诸版本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以一个独立的学科,以自我的体例范式,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无疑地具有着开拓性的奠基意义。作者在1951年初版的这部文学史,正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的产物。因之,无论教学,或者著作,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一门新学,容纳着新知,同时颇有几分革命气息。影响所及,到了1957年在众所周知的“右派”案中,某些戴上帽子的人,则不能再教此课,理由之一是该课革命性强。为此演化发展,拓展变异,几经风雨,到目前为止,据《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慨览》统计,已达89部。(这个数字远不够准确。例如前述的刘贞晦、沈雁冰本、胡适,其他的赵景琛、陈炳坤(子展)、谭正璧、周作人等版本,均被遗落)。但已大体见其发达的状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史、断代史、专史、作家研究专论迭出,更为这块研究的领地,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势头。影响所及,台港与国外学人,也挤身此林,构成中西互补、对话的趋势。应该说,中国新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至于它的性质、任务与研究空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来,逐步为学人所充实,并获得了学科上相对稳定的共知。这种历史的界定,是否完全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尽度呢?也不尽然。文学作为时代、社会的反映,它在相当程度上,“染乎世情”、“系乎时序”,这是吻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却它的自律性。例如说,“五四”文学革命的起点,大多认定为1915年至1917年。这时间,正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便是文学自律性的自觉呈现。这说明,文学的轨迹,总是在自律与他律之间运行的。它的下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讫止,既注意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也瞩目于文学发展的性质、任务自身的变化。
2、自然,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具有多种多样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这不仅缘于文学历史的丰富,也来自于史家目光的变异。按照克罗齐的说法: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描述的是过去发生的文学事件。它是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它要发展,也要承传,而文学史家总是在时差中呈现出自己的理解和富于当代性的审美品评。这从解释学来说,就更看重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的双重因素。按伽达默尔的见解:理解的东西,既不完全地是其全自身观点的产物,也不完全地由本文原初观点所决定,它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①有人甚至说,历史事件从来就不会“自己讲述自己”,使事件语言化,构成史的行为,造成物化形态就意味着有识者、撰写者的介入,或者说“事实的历史”唯有以“创造的历史”为中介,才能构成“叙述的历史”。②这说明,作为原生态的历史事件,经过史家的介入,经过带有特定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的滤过,纳入到某种思维范式和历史框架中去,才能呈现出它的意义。所以文学史,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别,时时出现异议或差误,这是很自然的事。
目前,遇到的困惑之一是所谓“生存空间”问题,也有人称之为“空间狭窄”。是的,无论与它之前的近代文学,或之后的当代文学比较,它的年代确乎有些过于短暂。如果从《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发刊,倡导文化革命作为起点,至第一次文化大会迄,也只有30余年。就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巡视,它只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有人担心过不了多久,学科的格局或许要有变化。甚至有人说,过上一百年或二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经过历史的筛选、沉淀,也许只剩下鲁迅了。1985年,黄子平等曾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以“整体化的构思”,把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文学作为通体现代化的建构加以考虑的构想,无疑是有建设性的。在提倡者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蕴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分期问题”,它涵盖着“走向‘世纪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而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等。因此,至今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仍为学术界所探讨着。但是,在研究中,也对“20世纪”的概念,存有疑议,例如说,到了21世纪,它是否就将斩断;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操作性问题。试想,在贴紧现实,还未来得及沉淀的诸多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如果融通起来,将怎样完成?提倡者也意识到“匆促的‘全景镜头’的扫描难免要犯过分简化因而是武断的错误,必然忽略大量精彩的‘特写镜头’而丧失对象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特别是操作起来,放在那一个人肩上,都难能胜任。仅以当代的小说创作来说,就很难跟踪披阅、赏析,何况20世纪中国文学通体观测呢?有人曾设想,新时期的文学可以不设史,以文学批评取代。这自然不失一种构想。但是,今天不设史,不等于永远不设史。一但入史,仍需清理、把握、披阅。现代读到了几部以20世纪命名的专史,也大都是共同完成的。因此,我想文学历史的发展走向,自然应该纳入史的视野,但又不宜操之过急。目前,可以多种形态并存着、发展着。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等。待时间拉开距离,诸多文学现象经过历史筛选,客观的价值取向日益清明,纳入史的框架,便自然形成。据我所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时间边界”,并无人匆忙划定,而是在教学与研究中自然形成的。80年代初当时的教育部曾组织高等师范系统起草一部中国现代(含当代)文学的大纲,但是也很少有单位执行。在广州起草时,就分别由现代、当代人研究人员主持,并分别开会形成的。但是,在开国之初,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是从“五四”贯通到现实的。例如王瑶的《润华集》中所收的《建国初期的文学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便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当时“尚无独立的‘当代文学’课程”。以后,由于历史的更移,时间延伸,更为主要的是文学事件,作家作品日益丰富,而难于疏理,便自然地形成两个文学史的格局。
目前,遇到的困惑之二是课题重复说。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空间范围审视,只有30余年。多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许多课题都已研究过了,有的已形成研究的“高原区”,因此需要拓展空间,造成宏观的研究视野,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应该说,吸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造成宏观的全景式的研究框架,是完全需要的。例如原型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派研究等,都以宏阔的态势冲开时间的格局,寻取时隐时现的历史脉络。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理当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显示出多样统一的特征。
但是,认为许多课题已经重复了,却并不尽然。目前研究的课题,固然有许多“熟地”,但仍有许多“生地”和尚待开垦的“处女地”(空白)。例如台港文学、各个沦陷区的文学、通俗文学,许多第一手资料尚待理清品析。据说仅张恨水全集,就要印行70卷;现代新诗集的出版也在1500部左右。1992年沈阳出版社着手准备印行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大系》预计是13卷600万字的样子,上述许多篇章,也许我们尚未来得及阅读。所以有人认为“空白”还很多,很多领域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
仅以“熟地”来说,作品的含意与意义,在历史的嬗变和认知的反省中,审美价值的更移与深化是屡见不鲜的。由于诸种因素误读或认识上的谬误,也不时需要拨正,至于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中,研究领域的发现与创新,更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以活力。就此来说,文学的历史,是在曲折的嬗变中螺旋式的发展着。鲁迅的《呐喊》与《仿徨》现在大抵是有口皆碑了,但在它出世的时候,那情况也颇纷纭不一。当时“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这是事实,但其中不独有摇头,而且有人用“恶骂来欢迎它”,乃至畏之如“洪水猛兽”,也不乏其例。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曾谈到:“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一部作品的含意从它诞生起便构成非个人的、客观的、自主的精神生命;但是基于文本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人们的解读也会经常出现差异。特别对于伟大的作品,由于它的蕴涵的深邃与丰富,就更难一次性的破译它的意义。所以有人认为“本文含义是随着一次次的阅读而发生变化的”。③读不完的《哈姆雷特》,说不尽的《阿Q正传》,这是吻合实际的。有些含意被读者所理解,构成显价值;有些尚没有被理喻,依然是潜在价值,因此作品会常读常新,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也大抵如此。
至于,由客观的因素所造成的误读或研究上的失误,随着历史的变移,也理应得到拨正。冯雪峰、胡风、丁玲、艾青、沈从文等作家,都在不同历史阶段,难于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是,历史终于现出公正的态度。1992年2月26日《文艺报》消息:《王实味已获平反昭雪》。王实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一定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王的托派案经过了49年,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断。50年代初,我们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抵是否定的。“改良主义”是论点之一。影响所及,语言上的“文学改良”便是论据的佐证。当我们冷静地翻阅这段历史资料,便会看到:从1915年9月到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胡适曾不止一次地也在书信、诗作或文稿中反复论证“文学革命”。1915年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的诗中,便提出“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见解。1916年在《答梅觐庄》诗中,仍在坚持“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有话便要说,不说过不得”。④该年的10月5日胡适得陈独秀信,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这结果便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出世。事实上,改良、革命,在“五四”时期都是革故更新的涵意。进化论在当时被许多新派的人物作为文学革命立论的思想武器。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困惑与生机并存的。困惑与生机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作用于同一母体中。困惑的出现为机体的发展,增加了难度,但也为生机的寻取构成了促进的动力。
注释:
①见赫施《解释的有效性》293-294页。
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72页。
③《解释的有效性》15页。
④《藏晖宅札记》卷19。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20世纪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文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王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