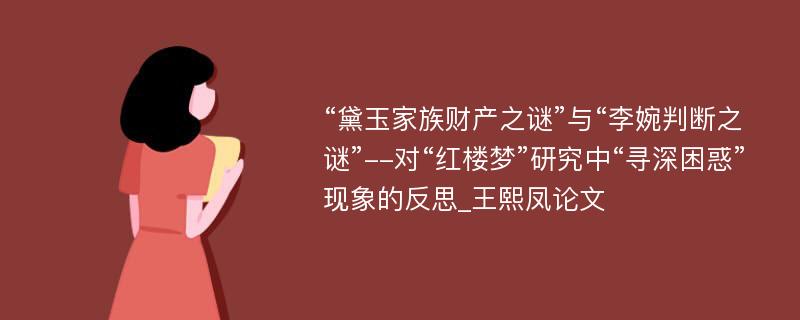
“黛玉家产之谜”与“李纨判词之谜”平议——红楼研究“求深反惑”现象之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判词论文,家产论文,黛玉论文,红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楼梦》因其复杂的内容、特殊的成书过程,在其阅读史中留下了一系列疑难问题。而在求解这些疑难的种种尝试中,可以说,留下的教训与取得的成绩,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深长思考。本文拟平议红楼二谜——“黛玉家产之谜”、“李纨判词之谜”,乃因论者皆从经济角度对其中有关细节进行解读,并由此导致对人物评价、情节结构诸方面的理解出现歧异,而这种歧异己影响及于对《红楼梦》整体构思的认识。本文在梳理前人观点时将择要对其中误解进行辨析,并从学理上追究屡见不鲜的此类“求深反惑”现象的成因。
一、“黛玉家产之谜”的提出与疏解
最早提出黛玉家产问题的是清人涂瀛。他在刊行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红楼梦论赞》的附录《红楼梦问答》中记载:
或问:“凤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则何也?”曰:“不独凤姐利之,即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凤姐领之。脱为贾氏妇,则凤姐应算还也;不为贾氏妇,而为他姓妇,则贾氏应算还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则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
或问:“林黛玉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有明征与?”曰:“有。当贾琏发急时,自恨何处再发二三百万银子财,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或问:“林黛玉聪明绝世,何以如许家资而乃一无所知也?”曰:“此其所以为名贵也,此其所以为宝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将数百万家资横据胸中,便全身烟火气矣,尚得为黛玉哉?然使在宝钗,必有以处此。”①
《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到荣国府经济每况愈下,偏偏宫中太监又不断来打秋风,不禁让贾琏抱怨“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并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②所有关于黛玉家产问题的议论即由此生发。因为持论者众口一词地指出,这“三二百万的财”乃源于黛玉家产。涂瀛阐论此事虽夹杂有后四十回续书的内容,但因系先发依然在后世激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
1987年,邓云乡先生所著《红楼风俗谭》出版,书中《林如海和“盐政”》一文引述俞平伯先生的信件也曾谈及黛玉家产之事:
太平湖风景至佳,又得雅吟信美。只是潇湘俭妆上船,未免被作者瞒过。盐务是最阔之差,屡见记载,兄必知之。比北京之破落侯门为远胜矣。如此用笔,一洗熟套,以豪富骄人,尚得为潇湘女耶!偶发狂言,聊博一笑。③
俞平伯先生此信中正面表达的观点,实际不出涂瀛的范围。不过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俞先生并未以一种严肃的学术腔调阐发此论,而是出之以“偶发狂言,聊博一笑”的游戏态度。这正是晚年的俞先生对红学问题抱以审慎态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2005年12月,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梦》“揭秘”系列第二部中,提出黛玉未得到父亲的巨额遗产,是因为贾琏从中做了手脚,他“略微往总账房——也就是官中——交出一部分,其余的绝大部分就贪污归己了”;而考虑到王熙凤不会容忍贾琏独吞这笔巨资,所以“应该是他们两口子,联手鲸吞了黛玉应得的绝大部分遗产”。④2007年7月,刘先生在《红楼梦》“揭秘”系列第三部中,吸取历来一些读者的意见,即“林黛玉应得的那份遗产肯定是在兴建大观园的时候被贾府挪用了”,同时认为黛玉应得遗产并非全部用于兴建大观园,因为“贾琏既然经手此事,必然从中贪污”。总之,刘先生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贾琏把这些银子拿回来之后,有可能形式上往官中交了一点,其它的就和王熙凤私吞了。”⑤而这形式上往官中所交部分,即被挪用为大观园的建造费用了。这可以视为刘先生经修正后的最终的观点。
法律界人士也满怀热情地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立足于自己的专业背景,他们主要从继承法角度切入,不过具体认识却不尽相同。李俊律师在2006年7月所出专著《红楼梦证悟》中,在确认林如海遗产丰厚的基础上,根据清律关于立嗣顺序的规定,即“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结合书中对林如海子嗣的介绍,指出林黛玉是林府遗产的惟一继承人,而这笔巨额遗产,即第七十二回贾琏所称“三二百万的财”,被贾琏侵吞后充作大观园建造费用了。⑥《南都学坛》2007年第3期所刊李俊论文《林如海的家产被贾琏侵吞挪用稽考》,内容与其专着完全相同,此不赘述。2007年7月,尹伊君先生在专着《红楼梦的法律世界》中,同样征引了李俊律师提及的上述法律条文,不过尹先生却称其为“强制侄子继嗣”的规定⑦,即清律将近亲的范围扩大至四世以内的所有侄子,由此导致女儿的继承权实际被剥夺的局面。落实到《红楼梦》中,林家遗产应被第二回交代的几门“堂族”中的“堂侄”所继承,林黛玉的继承权则被完全排斥。尹先生据此进而指出,第三回中林如海托贾雨村将黛玉送往荣国府,“其中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那就是他要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乘机转移到荣国府,以供黛玉将来之用”;而被转移的这部分财产,亦为第七十二回贾琏所称“三二百万的财”。⑧2008年10月,专治法制史的郭建教授在其著作中,则根据明清法律的有关规定,指出“林黛玉无可争辩的是林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不要说她那几位堂房的兄弟,即使是林如海有亲兄弟、亲侄子,也没有任何参与继承林如海遗产的可能”。⑨至于郭先生有关黛玉家产问题的其它论述,则与下面将要评介的陈大康先生的见解完全相同。
陈大康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红楼梦》中的经济事象。关于黛玉家产问题的论着,则有《黛玉的家产之谜》(载《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1期),及同年出版的《说红楼》一书“经济篇”第一集“黛玉家产之谜”。陈先生对黛玉家产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细密的论证,而其中易于引发争论的观点也相应地增多了。对于这些观点本文不拟作全面评述,而仅列举其中若干要点加以讨论。一是关于黛玉父亲林如海的家底问题。陈先生指出林家传到第五代的林如海时,“仍是相当有钱的人家,其证明便是林如海与贾敏的婚事”,而这不能不归因于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能将这样的千金小姐娶进门,林家不是很有钱怎么行?”⑩可是在第二十九回的描写中,作者让贾母明确地否定了这种世俗观念。该回写贾母在清虚观嘱托张道士为宝玉物色配偶时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对于宝玉的配偶,贾母只强调两点:“模样”与“性格”,而“根基富贵”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11)二是潇湘馆月钱的背后是否存在隐情的问题。陈先生注意到书中这样一个经济细节:第二十六回透露出潇湘馆的月钱是由贾母处送来的,而不像其它地方均由王熙凤负责分发。陈先生由此推论“贾母那儿有一笔专门的钱财,林黛玉的‘一应日费供给’都从其中开支,似乎有点专款专用的意味”,而“这笔专项经费就是流入荣府的林家财产”。同时,陈先生考虑到第五十五回王熙凤曾说过“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这里凤姐又把专款专用的那笔钱财称为贾母的梯己,“使人感到林家的财产流入荣府后并非完全是被独立监管,而是含含糊糊归贾母支配,林黛玉的一切费用则都由贾母承担”。林家财产流入荣府后,正赶上元妃省亲这一关系家族最高利益的大事,而“贾府根本没有建造大观园的经济实力”,于是只好将林家财产挪用为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妃省亲的费用了。不过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挪用林家财产并不能算作侵吞行为,因为贾母是支持宝黛婚姻的,而黛玉留在荣府做媳妇的话,她的嫁妆亦即林家财产“就应该成为荣府财产的一部分,于是贾府的动用只是提前使用而已”。(12)在此我们只提出一点加以讨论:第十七回大观园便已宣告竣工,第十八回元春省亲完毕,依陈先生之说,则此时流入荣府的林家财产便应消耗殆尽了;可是第二十六回由贾母处送至潇湘馆的月钱,仍被陈先生认定为流入荣府的林家财产,第五十五回中这笔钱财又被称为贾母的梯己,是则林家财产流入荣府后被一分为二了:一部分挪用来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妃,一部分以贾母梯己的形式供黛玉日常所需。真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帐啊!
陈大康先生在其论著中多方考察了黛玉的经济意识。在《黛玉的家产之谜》一文中,陈先生指出:“黛玉自认是‘旅居客寄之人’,还自称‘一无所有’,其实她心里对‘一无所有’是有所疑惑的,至少她曾亲耳听到过王熙凤无意间提到过林家的家产,尽管那说法是相当间接的。”然后陈先生提示第二十五回中凤姐对黛玉说过这样一段话:
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
陈先生分析这段话中提到“家私”的一句道:“王熙凤最后又讲到了‘家私’,即两家的家产,按照王熙凤的意思,两家仍是相配的。”也就是说,凤姐无意中讲漏的这句话,暗示了林家曾经拥有巨额家产。尽管黛玉在成长过程中曾因家产问题而困惑过,可是她又逐渐地走向了超脱,陈先生在《说红楼》中对此作出了升华性的概括:“无端失踪的百万家产,最终没能成为黛玉心灵上的枷锁,她始终不渝坚持的是对自己的‘知己’,即宝玉的相知相爱。用五世先人积累的家产,换取一个可以和心上人共渡少年时光的大观园,也是种不错的选择吧?这才是在曹雪芹构思中的‘绛珠仙子’。”(13)追根溯源,陈先生此论显然接受了涂瀛《红楼梦问答》的启发,只是其中的“换取”、“选择”等语汇,使黛玉沾染了更多的现代浪漫色彩。
在回顾有关黛玉家产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之后,以下就前人未多加注意之处及未作正面评判的观点加以论列。
(1)第七十二回中贾琏所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在不同版本中是存在异文的:
“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庚辰本、甲辰本、梦稿本、程甲本)
“这会子再发三二万银子的财就好了”(戚序本)
“这会子再发了三二万银子的财就好了”(蒙府本)
“这会子再发个三二万银子财就好了”(列藏本)
“这会子再发个三五万的财就好了”(程乙本)
八种版本在数字上存在三种说法:“三二百万”、“三二万”、“三五万”。选择不同的数字自然地会影响学者的立论。如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中便取程乙本“三五万”之说,并将其与有关记载中盐政的通常收入作比道:“出口只是三、五万,便算发财,比起盐政一年数十万的收入,那太不成比例了。”(14)显然,邓先生没有将程乙本的“三五万”与黛玉家产联系起来。至于八种版本的三种数字孰为作品原貌,迄今未见专门论及者。(15)我们仅知主张黛玉家产流入贾府的论者,无一例外地信从了庚辰等本的“三二百万”之说。有的论者尽管注意到了不同版本的差异,但为了坚持黛玉家产流入贾府的既有观点,指出较小的数字乃是出于传抄者的妄改。(16)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假如这里的数字不是庚辰等本的“三二百万”,而是其它版本的“三二万”、“三五万”,黛玉家产问题可能压根就不会被提出来。
(2)假设林如海去世后真的留下了巨额遗产,那么它被管家夫妇贾琏、凤姐私吞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众所周知,贾琏、凤姐都是极端爱财之人。凤姐自不必说;贾琏也是“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的主儿,难怪会有贾琏料理林如海后事必乘机侵吞其遗产的猜想。然而,这种猜想实在是高估了贾琏、凤姐夫妇的胆量和能力,同时也就严重低估了作为百年望族的贾府的管理水平。不要只看到凤姐行事雷厉风行、似乎无所不能的一面,其实她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就证明她依然处于家族的监控之下,而远未达到为所欲为的失控状态。(17)我们看她在挪用月钱放债一事上是何等小心,就会明白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贾琏、凤姐夫妇当真私吞了林家巨额遗产,首先他们在“老祖宗”贾母那里就很难蒙混过关。“老祖宗”贾母绝非一味闭眼享乐的糊涂老太太,关键时刻她所表现出的魄力实不在凤姐之下,这一点已经是广大红楼爱好者的常识了。第二十五回甲戌本眉批以“神明”一词称许贾母,第三十五回宝钗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都是对这一常识的绝好说明。贾母会容忍贾琏、凤姐夫妇私吞她的宝贝外孙女黛玉的家产吗?我们实在没有如此“大胆假设”的勇气。其实,推敲第七十二回贾琏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的上下文,完全可以断定曾经发过这笔财的是贾府,而非落入贾琏、凤姐夫妇私人之手。这里的道理依然很简单:贾琏、凤姐打发不断来打秋风的宫中太监,自然是动用官中的钱,而绝非夫妇二人的私房钱。我们看贾琏抱怨太监“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并举例说“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这次来“借”二百两银子的夏府小内监,还承认“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贾琏、凤姐夫妇打发这些没完没了的“外祟”,可能傻乎乎地拿出他们的私房钱吗?第四十四回写到贾琏因鲍二媳妇自杀,“许了二百两发送”,可是他随即“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帐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为了省下区区二百两银子,贾琏还要作弊让官中负担,更不必说自承太监们动辄千两的勒索了。总之,第七十二回中贾琏说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是:这会子官中要是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该多好,那样的话就可以应付太监勒索之类正常花销以外的开支了。其中并未透露琏凤二人曾经私吞过黛玉家产的任何一点信息。
(3)假设林如海去世后真的留下了“三二百万”的巨额遗产,而且这笔遗产真的被贾府侵吞了,那么这笔遗产是否被挪用为大观园的建造费用了呢?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参加大观园模型问题的讨论时说过:“大观园虽也有真的园林做模型,大体上只是理想。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其为理想境界甚明。……大观园即太虚幻境。果真如此,我们要去考证大观园的地点,在北京的某某街巷,岂非太痴了么。”(18)大观园本是作者精心建构的理想世界,就像我们不能考证出大观园的模型在哪里,我们同样不能追问建造大观园的总费用是多少。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从未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仅在第十六回中提到两笔具体花销:一是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需银三万两;一是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需银二万两。对于这些具体的花销作者尽可将其坐实,至于总费用他却不会胶刻地将其定为“三二百万”,更不可能在相隔五十多回后的第七十二回让贾琏冷不丁地说出这个数字。“三二百万”既然不能视为建造大观园的总费用,那么它的资金来源又在哪里呢?有的学者提出其资金应来源于贾府历年的积蓄。(19)结合书中有关描写看,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第五十三回写贾蓉向乌进孝解释荣府经济拮据的原因时说:“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体会贾蓉说话的语气,“省亲连盖花园子”的花费应出自荣府本身财政,而非发了黛玉巨额家产的外财。须知荣宁二府的经济都是靠庄田地租维持的——第五十三回中提到宁府庄头乌进孝的兄弟现管着荣府八处庄地,宁府的贾珍、贾蓉等主子对荣府的收入大体上是清楚的,就像第五十三回中贾珍所说的“我心里却有一个算盘”。如果“省亲连盖花园子”全仗外界注入的“三二百万”的黛玉家产,贾珍等人自始至终竟会毫无察觉么?第十六回中交代的很清楚,盖造省亲别院是“借着东府里花园起”,“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于是省亲别院将原来隔着一条小巷的宁荣二宅连接了起来,而“两处又甚近,凑来一处,省得许多财力”。第十六回中还清楚地交代,宁府主子贾珍与宁府大总管来升,都亲身参与了省亲别院的筹建;宁府主子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往姑苏采买女孩子等事务则由宁府正派玄孙贾蔷负责。宁府这么多重要人物参与了省亲的筹备工作,他们对突然注入的“三二百万”的巨资会麻木到无知的地步吗?不少论者之所以认为贾府根本没有建造大观园的经济实力,不过是因为第二回中冷子兴说过“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话。其实对于冷子兴这两句话,不宜理解得过于绝对;而且在说这两句话之前,他还说过几句不太引人注意、然而却是很有分寸的话,正需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不仅如此,冷子兴在说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之后,有一句过渡性的话引起后文:“这还是小事”。可见在冷子兴看来,贾府经济上的危机“还是小事”,还远未达到动摇根本的严重程度;“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对贾府来说才是最为致命的。这与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凤姐时对贾府现状的观察并无不同。而秦可卿用什么语言描述当时贾府的经济状况呢?是“如今盛时”,是“今日富贵”。
行文至此,我们依然无法答复第七十二回“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处姚燮眉批的两个疑问:“试问从前三二百万是那里发来的?如今又那里去了?”(20)我们同样无法回答林如海去世后是否留下了巨额遗产的问题,因为前八十回中找不到与此有关的任何一点信息。我们只能较为明确地提出几条否定性结论:一,“三二百万的财”不能视为建造大观园的总费用;二,大观园的建造费用不可能来源于黛玉的巨额家产;三,贾琏、凤姐夫妇私吞黛玉巨额家产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二、“李纨判词之谜”的提出与疏解
所谓“李纨判词之谜”,乃指因释读第五回中李纨的判词及《晚韶华》曲,而产生的对李纨为人行事的歧异认识。又因其中一些争论涉及八十回后的内容,致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增添了若干的曲折。
第五回中李纨的判词是:“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对前两句的理解学界向无分歧,后两句则迄今仍被视为《红楼梦》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而第五回综括李纨一生的《晚韶华》曲中的几句话,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有名难点:“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而随着对判词与曲子的不同见解的陆续发表,突然有一天我们竟然发现,为无数红迷所熟悉的那个“大嫂子”李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嫉妒、吝啬与冷漠诸恶德于一身的李纨。
陈大康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李纨判词之谜”的破解。其成果主要有《论李纨判词之谜》(载《社会科学家》1986年第2期)、《月钱:李纨与王熙凤的经济过节》(载《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4期),以及2007年出版的《说红楼》“经济篇”中的相关论述。陈先生是从李纨与凤姐存在“经济过节”的角度,来阐释李纨判词中“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这两句的。陈先生注意到,贾母提到李纨时总说她“寡妇失业”,而“‘寡妇’与‘失业’两词相连,实际上正寓示着李纨遭受过的两次打击。第一次是贾珠之死,第二次则是她失去掌握治家大权的‘业’”。陈先生指出,荣府治家权本应属于大嫂子李纨的,但不信任儿媳李纨、不喜欢孙子贾兰的王夫人,却将治家权转交给了内侄女凤姐。李纨对凤姐的不满与嫉妒因而不可避免。尽管第六十五回写兴儿向尤二姐介绍李纨时曾说过:“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但陈先生认为这项规矩其实并不成立。(21)关于荣府治家权到底该归谁的问题暂置不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更有能力行使治家权?毫无疑问,“脂粉队里的英雄”凤姐是弊窦丛生的荣府得以按常规运行的不二人选。李纨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也不乏精明之处,主持诗社活动也有组织能力,但在需要杀伐决断方可有效行使治家权方面,她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望凤姐之项背的。第五十五回中说李纨“素日原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是个尚德不尚才的”,都是对其缺乏杀伐决断能力的委婉表达。贾母、王夫人支持强悍的凤姐治家,是着眼家族整体利益的明智之举,其中并不存在排斥李纨的主观故意。至于“寡妇失业”中的“失业”一词,是否寓示着李纨失去本属于她的治家权,也是大有商榷的余地。第四十三回写贾母发动众人凑份子为凤姐贺寿,李纨提出要出十二两银子,这时贾母忙和李纨道:“你寡妇失业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吧。”在妻视夫如天的封建时代,失去赖以终生的丈夫,就意味着处于“失业”的状态;换言之,“寡妇”与“失业”本属一事,而非意指李纨既做了寡妇,又失去了治家权的“业”。再说贾母在充满愉悦情绪的众人面前,也不可能揭出失去治家权这一让李纨难堪的事。
对于李纨缘何招来凤姐的嫉妒的问题,陈大康先生的解释则是切合实际的。在对月钱按等级发放的情况进行一番精密的考察后,陈先生指出凤姐的月钱是四两银子另加二吊钱,而李纨“按定例她该领取四两,但实际上却领取了二十两。正是这个特例,造成了王熙凤的心理不平衡,她对李纨的妒忌,也由此而来”。(22)另据第四十五回凤姐在玩笑中替李纨算帐的那段精彩描写,可知李纨还有“园子地”的租子、“上上分儿”的“年例”等进项,加上月钱的累积,“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利心极重的凤姐对李纨产生妒意正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李纨因失去治家权而嫉妒凤姐的观点还难以确立,故而从“经济过节”角度阐释判词后两句,也就存在诸多难以得到圆融解释的困难。陈先生说,李纨判词后两句“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从字面意义上看,乃谓“‘冰’与‘水’作无意义的互相妒嫉,结果是白白地给世人作谈资笑料”;而第三句中的“冰”,系喻指王熙凤,“水”则喻指李纨,全句即喻指“久已心存芥蒂的李纨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而“这也应该是后来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身陷危难,李纨却不愿援手相助的重要原因”。(23)也就是说,凤姐与李纨之间的矛盾在佚稿中殃及到了下一代的巧姐身上。
让我们引入《红楼梦》判词在图画、谶文的配合规律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审视从“经济过节”角度阐释判词后两句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辑所刊何卫国先生《金陵十二钗册子蠡测》一文中指出,金陵十二钗册子中的图画、谶文风格与《推背图》类似。而金陵十二钗册子中的图画,可以分为风格不同的两组,其中写实性较强的第二组均以一女子为构图中心,有探春、迎春、惜春、巧姐、李纨、秦可卿等人,而图中女子所处环境均为其悲剧命运最相关切之物,如迎春是“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巧姐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而隐喻李纨命运的图画“一盆茂兰,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则指李纨一生命运与其子贾兰密切相关。如果作者用四句判词中的末两句隐括李纨的命运,而末两句又喻指李纨与王熙凤之间的矛盾关系,则王熙凤对李纨命运的重要性应不在贾兰之下,那么判词旁的图画中按理应有象征王熙凤的物事出现,可是我们并未看到这方面的任何描述。而且,为了进一步揭示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与结局,作者又以《红楼梦》十二支曲与图画和判词相互补充,可是在综括李纨一生枯荣变化的《晚韶华》曲中,也很难将其中的“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指实为与王熙凤有矛盾的李纨不愿搭救巧姐的佚稿情节。尽管《晚韶华》曲中的这几句话迄今尚无圆融的解释,不过从总体上看,该曲前两句已经将中心意思点明了:“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用梁归智先生的话来说,该曲乃是写李纨一生的两大悲剧:“青年丧夫,晚年丧子”(24),而非意在指责李纨亏欠了阴骘;否则,曲子末句“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中的“钦敬”一词就不好解释了。
《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4辑所刊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王湘浩先生化名黄鹤乡的论文《从荣府内争看贾兰和巧姐》,则是从荣府内争的角度阐释李纨判词后两句:“荣府的骨肉相争如冰水有同根之好而相妒不能相容,结果家亡人散一场空,只不过让他人作为笑料来谈论罢了”,而“判词第二句说的是贾兰,后两句却说到荣府的内争上去,可见他在内争中并不是旁观者”。据说在家族、朝廷的战场上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后,皇上特旨将荣府世职赐还嫡孙贾兰。由此可见“贾兰的乌纱帽不是好来的。正因为如此,判词才把他母亲的凤冠霞帔同贾府的内争相联系,并说这不过让人作为笑谈而已”。在王先生看来,作者塑造李纨形象的本意乃是借用她来“写荣府的骨肉相争、无情无义”。王先生对李纨判词后两句的阐释虽与陈大康先生不同,但从矛盾斗争的角度立论却并无二致。王先生阐发此论的关键在于确认贾兰为巧姐《留馀庆》曲中的“奸兄”,对此下文将专门予以评判。
据陈大康先生研究,第五回《晚韶华》曲中的“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乃是作者对李纨的批评:“当贾府败落之后,惟有李纨在经济上还拥有较强的实力,但她却不愿积阴骘,帮助某人摆脱困难。”(25)李纨为何不愿助人于危难之中呢?陈先生说,是因为她要为儿子日后的前途着想,于是想方设法多积攒些钱,结果不可避免地养成了小气与吝啬的毛病。“自己的钱决不用在他人身上,这可以说是她奉行的铁定原则。”(26)为了说明李纨的吝啬已达到久而自然的程度,陈先生从第四十三、四十五、四十九诸回中进行了举证。尤为典型的是第四十五回写探春、李纨等向凤姐拉赞助,凤姐以开玩笑的形式替李纨算了一笔收入帐,最后还趁机将了李纨一军:“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陪他们顽顽,能几年的限”,“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他们来闹我”。凤姐的长篇大论激起了平日以和善示人的李纨的猛烈反击,其中使用了“无赖泥腿市俗”、“下作贫嘴恶舌”及“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等骂詈性语言;而为了增强进攻的力度,李纨还提起平儿无辜遭打的事,愈发让凤姐陷入理屈词穷的境地。陈先生就此认为凤姐的话确实触痛了李纨的吝啬真病:“确实,李纨就是拿出点钱供诗社活动,又能花费多少钱呢?曹雪芹通过这一情节的描写,暴露了李纨吝啬小气的一面。”(32)其实前人也曾这样看待过李纨,如第四十五回有洪秋蕃回评云:
按凤姐虽分斤掰两,为李纨作算博士,意在笑他鄙吝,不肯出钱做东,与诗社尚有关合;李纨之言则纯责其不应与他会计,与诗社毫不相干,语虽趣而理则欠。(28)
盖有钱之人,最怕人家说他有钱,凤姐犯其忌故也。至提昨日打平儿之事,则去题益远矣。闺中斗口,正理说不去,往往摭拾别事以怄之,真有此情理。(29)
作者曲折有致地描写凤姐、李纨唇枪舌剑的交锋,难道其意即在暴露李纨吝啬的性格特征吗?考虑到作者结构小说情节的苦心,这样理解不免有简单化之嫌。如果我们承认余英时先生在《眼前无路想回头》一文中提出的凤姐实为“大观园理想世界的一个中坚分子”的论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30),那么李纨等向凤姐拉赞助正为后者提供了加入大观园群体的机会,而凤姐在与李纨理论一番后还是抓住了这一机会:“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如果诗社活动经费由李纨个人承包了,试想作者还怎么安排凤姐加入大观园群体呢?而如果凤姐失去了加入大观园群体的机会,诸如凤姐体贴家贫命苦的邢岫烟、抄检大观园时维护园中人物等情节又怎能展开呢?凤姐“一夜北风紧”的名句不也因此而无法出炉了吗?而据余英时先生所论,凤姐这句诗在表现她与大观园群体的关系上意义重大:“凤姐加入了诗社,并且写下了一句诗,她和大观园的认同便达到了完全的境地了。”(31)总之,为整体情节构思计,第四十五回中的李纨是非“吝啬”不可的了。《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辑所刊周五纯先生论文《李纨三题》第二题“李纨吝啬吗”中,便曾针对书中有关李纨存在吝啬嫌疑的事例,指出“这样的材料,转了几个弯,间接性太强,不免沾上一点索隐派的味道”,从而审慎地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而周先生对以“不写之写”的艺术手法表现李纨吝啬的观点,也有非常辨证的看法。凡此均可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客观认识。
陈大康先生曾经指出,李纨《晚韶华》曲中的“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乃指贾府败落后惟有李纨经济状况独好,但“她却不愿积阴骘,帮助某人摆脱困难”。而这里的“某人”据说没有比凤姐的女儿巧姐更合适的了。因为第五回中李纨的判词与《晚韶华》曲的上面,恰好都是巧姐的判词与《留馀庆》曲;而巧姐判词“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以及《留馀庆》曲中的“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与李纨《晚韶华》曲中的“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凤姐因救济刘姥姥“积得阴功”,终得刘姥姥解救巧姐之报;李纨则是亏欠了阴骘,因为她不愿“济困扶穷”,对落难的巧姐漠然置之。据此推断,巧姐《留馀庆》曲中的“奸兄”只能是李纨的儿子贾兰;而贾兰既然做了“爱银钱忘骨肉”的缺德事,对其为人行事影响深刻的李纨自然难辞其咎。拿王湘浩先生《从荣府内争看贾兰和巧姐》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李纨正是在巧姐遇难这个问题上,‘爱银钱,忘骨肉’,损了阴德。母子一体,事情是商量着办的。母亲如此,儿子自然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损事”。
巧姐《留馀庆》曲中提到的“奸兄”到底指谁,学界曾提出贾蔷、贾蓉(32)、贾芹(33)、贾兰诸说。梁归智先生曾比较过被怀疑为“奸兄”的贾蓉、贾兰和贾蔷三人,认为“贾兰是奸兄的合理度更高”(34)。在证明贾兰为“奸兄”的诸多论说中,以1989年问世的王湘浩先生《从荣府内争看贾兰和巧姐》一文用力最大,且其中若干论断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被某些论者所承袭,故仍有加以客观评判之必要。王先生用来论证贾兰为“奸兄”的典型事例,是第九回所写顽童闹学堂的混乱场面中,与贾兰同桌的贾菌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砚来打宝玉的书童茗烟,不料却将贾兰、贾菌的书桌砸得狼藉不堪;“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贾菌抓起砚砖就要反击,“省事的”贾兰却极口劝阻道:“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王先生就此得出结论:贾兰与亲叔宝玉“极其不睦”,因为“亲叔要被人抓打了,却说这事不与他相干,这不正是‘忘骨肉’吗?”陈大康先生则将贾兰的表现与母亲李纨的影响联系起来:“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从中不难窥见李纨平日是如何教导贾兰的,而其出发点,却是怕在贾兰身上‘生事’。”(35)梁归智先生在2008年新出著作中大段转引了王先生论证贾兰为“奸兄”的部分,并称其说是“颇有吸引力的”(36)。贾兰难道真是一个从小就缺乏应有的同情心,长大后又干出“爱银钱忘骨肉”的缺德事来的“奸兄”吗?
《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所刊刘世德先生论文《这贾兰不是那贾兰——〈红楼梦〉版本探微之一》,通过对《红楼梦》的版本及成书过程的细致考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第九回中与贾菌同桌的那个“贾兰”乃是贾府族人,而非我们最熟悉的贾珠和李纨的儿子贾兰。(37)而刘先生此论一出,王湘浩先生以第九回中的“贾兰”所作推论也就失去了依据。
王湘浩先生论证贾兰为“奸兄”的另一典型事例出自第二十六回。书中写宝玉无精打采地出门闲逛,
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其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作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把牙栽了,那时才不演呢。”
粗粗看去,这不过是宝玉和“淘气”的贾兰叔侄俩的一段家常对话。王先生则将其视为一种隐喻:“暗示贾兰也要‘逐鹿中原’,参与夺嗣之争,看看究竟鹿死谁手!”并从贾兰答对宝玉的话中抽绎出三层深意:“一是堂皇正大,标榜自己不习文便练武;二是以此讥刺宝玉不是‘出门去’便是在家里‘闲着’;三是坦然为自己无故杀生辩解。”王先生就此判定此时的贾兰“其奸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在王先生看来贾兰天生就是“奸雄”的材料,因为“根据贾宝玉的定义,凡热衷功名讲究读书上进的人谓之‘禄蠹’,而‘禄蠹’一定不是好人”,所以贾兰“小时即奸,等到做了官,必然成为象贾雨村那样的奸雄”。贾兰难道真是《红楼梦》中一个奸诈无比的漏网“禄蠹”吗?按第二十六回在贾兰所说“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处甲戌本有夹批云:
奇文奇语,默思之方意会。为玉兄毫无一正事,只知安富尊荣而写。
庚辰本有夹批云:
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之至。(38)
可见脂批认为此处描写意在以贾兰的有为反衬宝玉“毫无一正事,只知安富尊荣”;用来反衬宝玉的贾兰也没有一丝“奸”相,而纯粹是以正大光明的形象予以表现的。此其一。其二,是否像贾兰这样演习骑射、追求上进的人也得归入“禄蠹”之列呢?不可以的。第七十五回写贾珍居父丧期间,按礼制不能放荡游玩,乃巧生破闷之法,“以习射为由”,请来一干纨绔子弟较射。不知就里的贾赦、贾政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于是赦、政兄弟也命贾环、贾琮、宝玉、贾兰四人加入贾珍习射的行列。此处宝玉、贾兰叔侄尽管是奉严命加入习射行列的,但在借机“一味高乐”的贾珍的映照下,习射活动的正面意义是十分显豁的,而与宝玉素所痛斥的“禄蠹”现象全无关涉。第二十六回中贾兰的演习骑射亦当作如是观。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贾兰是一个勤苦攻读,性格拘谨,偶有淘气表现的,并初步崭露出文才武略潜质的,深受贾政等长辈喜爱的小孩,而绝非巧姐《留馀庆》曲中提到的“奸兄”。清人涂瀛《红楼梦论赞·贾兰赞》的见解无疑是可取的:“习于宝玉而不溺其志,习于贾环而不乱其行,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矣。”(39)
巧姐《留馀庆》曲中提到的“奸兄”既非贾兰,所谓不救助巧姐的决策乃由李纨作出的看法也就站不住脚了。让我们引入梁归智先生富有启发性的论断,进一步驳斥李纨因巧姐而亏欠阴骘的主张。为了说明由元春致黛玉于死地的设想不合作者原意,梁先生指出作者设置金陵十二钗内部关系遵循一条总体原则:“细察前八十回,似乎有一个总体原则,即金陵十二钗内部不会互相严重伤害,她们都属于‘薄命司’,都是薄命女儿,曹雪芹不写她们自相残杀。即使有些纠葛,也无伤大体”(40),“看前八十回的写作风格,曹雪芹一般不写十二钗内部自相残杀,主要写这些‘薄命’的女儿惺惺相惜”(41)。梁先生归纳的这一总体原则是符合前八十回文本实际的。据此我们即可判定李纨不可能对同在十二钗之列的巧姐冷漠无情,何况在八十回后的佚稿中,作者可能压根就未设计巧姐需获李纨救助的情节。再者,如果李纨对危难中的巧姐置之不理的话,则与前八十回中作者对李纨的性格设定正相反对,而这是违背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和谐统一的基本规律的。前八十回中作者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李纨的性格特征呢?是诸如“尚德”、“第一个善德人”、“贤惠”、“老实”、“厚道多恩”、“大菩萨”、“佛爷”等褒扬性词汇;第四十八回“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处庚辰本夹批谓香菱“端雅不让纨、钗”(42),该批明署“脂砚斋评”,是则深悉作者创作意旨的脂砚斋亦以“端雅”二字称许李纨。林冠夫先生曾从原型考察的角度指出,《红楼梦》中的李纨之所以未被赋予任何缺点,乃因她的生活原型是曹颙的遗孀马夫人,也就是作者曹雪芹的母亲。(43)
不少学者之所以将李纨与凤姐的关系视为相互嫉妒,并推测李纨、贾兰对巧姐冷漠无情的佚稿情节,从深层原因考察仍是传统斗争哲学在起决定作用。无独有偶,早在1948年,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公孙午的短文《史·王·薛》,即将《红楼梦》视作史、王、薛三大贵族先后把持贾氏家政而类似宫廷斗争的政治小说,文末一段并进而引申道:“史、王、薛先后把持贾氏家政,全书述事一贯,不问作者为一人,为二人,吾谓其意识如是。宝钗尚有腹中一块肉,前途颇有希望,然李纨正养晦待时,兰一长成,贾氏或可中兴,李氏必可得势,未知其时李、薛两家,谁胜谁负耳。使吾为续书,当着眼于此。”(44)公孙午意识中的李纨与不少学者所阐释的李纨形象,难道不是存在某种精神上的相似之处吗?
三、“求深反惑”:教训与启示
饱经沧桑的俞平伯先生在晚年之作《乐知儿语说〈红楼〉》中深有感触地说:
夫不求甚解,非不求其解也。曰不即不离者,亦然浮光掠影,以浅尝自足也。追求无妨,患在钻入牛角尖。深求固佳,患在求深反惑。(45)
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46)
俞先生所揭示的红学研究中屡见不鲜的“求深反惑”现象,在“黛玉家产之谜”与“李纨判词之谜”的探讨中表露无遗。而从学理上追究其成因,似可归结为以下二端:
一、“自传说”的阴影依然在徘徊。黛玉的父亲曾官巡盐御史,而此职在明清时期是肥差,加上现实中的曹家曾有人担任此职,脂批又说借元妃省亲事写康熙南巡,而接待康熙的花费系挪用盐政官银;更刺眼的是贾琏透露贾府曾发过“三二百万的财”,而当年料理黛玉父亲后事的正是贾琏。如此之多的巧合因素凑拢在一起,难怪黛玉父亲身后留下了“三二百万”的巨额遗产,这笔巨资被挪用来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妃等“发现”,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推演出来。只可惜貌似严密的逻辑推演,终究无法取代艺术描写本身留给我们的真实印象。大批以“自传说”为学理依据的考证成果,在曹雪芹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处处碰壁,难道不是理有必至的当然之事吗?
二、长期斗争性思维的持续影响。这一点在对“李纨判词之谜”的探讨中体现的尤为深刻。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人们对很平常的小摩擦、小矛盾,却看得相当严重;而将这种思维方式坚决贯彻到底的话,又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些保持和谐面貌的细节,最终得出表面上新意十足,实则严重背离作者本意的论断。大量历史教训早已警示我们,斗争性思维最易催生偏见,而偏见往往会伤及无辜。
前人的失误给后人带来宝贵的启示。而我们在辨析前人种种失误的过程中,对曹雪芹非凡的艺术思维获得了深细体察的机会。吴组缃先生在《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一文中论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成因时说过:“作者是努力从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的极其复杂深邃的关联和发展上来连根地‘和盘托出’这个悲剧的。”(47)此语对廓清上述二谜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面对曹雪芹建构的复杂而深邃的艺术世界,单向度的致思往往会陷入迷津而难以自拔,综合考量才是深入红楼艺术世界的惟一可行之途。
注释:
①(39)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45、133页。
②本文所引《红楼梦》正文,除特别说明者外,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③(14)见邓云乡《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338页。
④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⑤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三部),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
⑥参见李俊《红楼梦证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47—156页。
⑦对此,专治中国法律史的美国学者白凯的见解与尹伊君先生相同,她说:“对女儿来说,强制侄子继嗣的立法意味着她们对绝户财产权利的收缩。明代(然后清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当一户绝嗣时,应在同族合格的侄子中立一嗣子。只有当没有合格人选时,女儿才可以继承财产。女儿对绝户财产的权利由此落到她所有族兄弟之后。”见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6页。乾隆年间另一巨著《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中,写惟有一女的鲁编修去世后,“众亲戚已到,商量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过来,然后大殓治丧”。其事虽与《红楼梦》的描写不尽相同,但仍有助于说明法律规定在生活中的落实情况。
⑧尹伊君《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6—83页。
⑨参见郭建《古人的天平——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法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151—158页。
⑩(12)(13)(21)(22)(23)(25)(26)(27)(35)参见陈大康、胡小伟《说红楼》,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7、17—22、27、9—11、30—58、78、89、68、86、84页。
(11)刘心武先生认为,准确解读贾母不管根基富贵的言论,意义重大,因为“读《红楼梦》,读不懂贾母这些话,那真是白读了”。在刘先生看来,“贾母的话都是‘黑话’,话里有话”:贾母宣扬此论是在向在场的薛姨妈、未在场的王夫人等“金玉姻缘”的支持者表态,即贾母是坚决支持宝黛婚姻的,尽管黛玉没有得到父亲的遗产,但贾母可凭梯己钱做黛玉的经济后盾。贾母在子女婚配问题上实际是非常讲究根基富贵的。参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三部),第8—12页。贾母的言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周思源先生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参见《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中华书局2006年,第47—48页。
(15)漓江出版社2009年出版周汝昌先生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在第4册第1091页独取列藏本,将贾琏的话校订为“这会子再发个三二万银子财就好了”。不知周先生何所据而作此校订。
(16)刘心武先生说:“在有的古本上,三二百万写做三二万,可能是抄书的人觉得三二百万这个数字未免太多,就给改了,但缩水一百倍,似乎又显得过少。”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第140页。
(17)荣国府有一套严密的财务与人事管理制度,也就是书中所谓“祖宗旧例”,一般情况下凤姐是必须遵照这些“祖宗旧例”,来行使其有限而绝非失控的权力的。对此,陈大康先生有十分全面而客观的解析,可参见《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一文(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辑)及《说红楼》第98—114页相关论述。
(18)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六《记嘉庆甲子本评语》中语。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3页。
(19)陈大康先生在早年的论文《论贾府的经济体系及其崩溃》中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济上的打击竟伴随着政治上的荣耀而来,元春的省亲几乎耗尽了贾府历年的积蓄,于是第二年一歉收,贾府便立即陷入了危机。”(见《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辑)可见陈先生在1990年时认为大观园的建造费用来源于贾府历年的积蓄,不同于2007年出版的《说红楼》中主张大观园的建造费用系挪用黛玉“三二百万”的家产。胡小伟先生在《说红楼》“政治篇”第五集《三朝恩怨录》(上)中,指出大观园的建造费用系贾府的“历年储蓄”与“亲朋挪借”,而未将其与黛玉家产联系起来。可是胡先生又据第七十二回贾琏所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指出“大观园造价起码会是二百万银子以上”。(见《说红楼》第192页)贾府的“历年储蓄”与“亲朋挪借”,怎能算作贾府曾经发过的“三二百万的财”呢?胡先生的两个主张之间无疑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
(20)笔者曾就如何理解“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这句话,向中央民族大学的曹立波教授请教。曹教授在回函中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释:贾琏说这句话是一种假设语气,“再”字大体相当于“要是”的意思。也就是说,贾琏这句话不过表示一个美好的愿望,而非透露贾府以前真的发过“三二百万的财”。
(24)参见梁归智《红楼探佚红》,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28)(29)见冯其庸纂校订定《八家评批红楼梦》中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772、1779页。
(30)(31)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1、102页。
(32)参见张宏雷《从巧姐结局说到“奸兄”》,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
(33)参见《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第167页。
(34)(35)(40)(41)参见梁归智《红楼疑案:红楼梦探佚琐话》,中华书局2008年,第184—185、221—223、116、250页。
(37)参见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第284页。刘先生该文后收入《〈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42)见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481、600页。
(43)参看林冠夫先生演讲稿《由李纨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同现实“模特儿”之间的关系》,见傅光明主编《插图本新解红楼梦》(续),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230—233页。
(44)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1—1372页。
(45)(46)见《俞平伯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04、412页。
(47)见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6—147页。
标签:王熙凤论文; 林如海论文; 红楼梦论文; 李纨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贾母论文; 大观园论文; 曹雪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