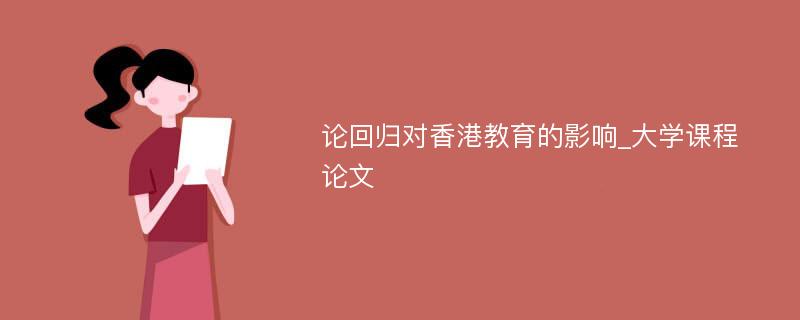
香港学者论回归对香港教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两地间的教育对接与互补已成为当前一项迫切的研究课题。在香港,早在中英联合声明草拟之际,有关的学者就已关注这一问题。随着回归的临近,研究也逐步深入。本文拟对香港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加以介绍,以提供参考。
一 教育在过渡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香港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认为,教育在转换期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若不发生军事行动的话,教育就是最为重要的了[1]。教育可以帮助形成1997年以后新一代的思想,影响政府机关录用人员的标准,维持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以及作用于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形成对于祖国文化的认同等。
香港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李荣安指出,教育有两种功用:一种是保守的,另一种是创新的。前者旨在维护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特点。在此方面,香港教育与大陆连接,考虑到中国大陆将对香港教育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可以预见,普通话教学会增加,一些学校甚至会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在教育的创新功能方面,教育变革仍将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香港应有意识地提高教育水准,继续实行教育改革,增进国际联系,从而充分实现创新功能,以便为中国未来经济和教育发展提供动力与范例。如果香港能充分地利用好教育的创新功能,它将一定会在教育的试验与开拓性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有利于香港和中国大陆两地的未来发展[2]。他坚信,只要中国仍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关注于提高教育,香港教育对大陆未来经济与教育发展必将作出贡献。他认为香港教育制度将会在50年保持不变是不现实的,社会在变,教育制度也会变,即使能够认识到香港将日益同大陆的制度相统一,但想精确地预计其变化也不容易,因为在中国不同地区已有各种不同的改革。
二 “九七回归”使得香港教育发展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白杰瑞指出,东欧和香港都面临着转换,东欧需要适应西方体系而自身并不一定完全资本主义化。香港则需要适应中国大陆而并不是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有大量人移离香港,中资的影响日益扩大,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日多,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接受教育的,这些因素使香港的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socialist bourgeoisie),从而改变香港教育的背景条件,对香港学校气氛形成较大影响。同时,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方面的国际化又是1997年以后被用来抵制大陆影响的一种途径。由于香港于2047年成为社会主义时的公民是现在的中小学生,所以教育应开始考虑如何培养这些学生的问题。在白杰瑞看来,回归所引发的教育社会背景的变化使香港教育陷入二难:一方面要求教育变革以应当代当地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担心平稳与繁荣。
曾担任过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之职的Paul Morris教授认为,同其他大多非殖民化的情况不同,香港回归中国在许多民众看来将不是以解放和自我独立为结果,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定与疑惑[3]。回归导致了对培养学生成为未来中国公民的压力。一方面,产生出了主要来自于政府的对课程的影响,其基本目标是保证回归顺利,途径是通过修正学校课程内容以促使学生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转。另一影响主要来自当地社区,目的是通过课程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程度,从而保证香港民众具有主动的政治认识以保障1997年以后相对自发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特别是运用课程支持促进香港政府成为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尽管香港中学课程一直都受到对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的影响,但回归的影响却更加显著。首先,它影响了学科范围;其次是内容以及对内容的处理方法;再次,回归使得香港政府建立起新的德育指导原则。
但是,也有人认为回归并没有给香港带来什么特别的社会背景。香港大学课程系教授Anthony E.Sweeting就坚持认为,香港一直就是充满了转换(transition)的地方,不仅仅表现在居民转换这一点上。变化从来都是香港生活的重要事实,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都如此。香港课程一直都被政治因素影响,尤其是大陆的发展,教育的各个方面一直都由内外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尽管即将来到的转换占满了今日几百万港人的思想和情感,其实情况并无独特之处,过去长期以来影响港人的趋向和各种因素仍将在转换期间以及之后影响香港社会[4]。
三 香港地区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影响香港教育在回归前后的作用与发展
白杰瑞指出,香港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经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具有很长的历史,却又是殖民地,既有中国的传统又与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都不同,这种独特的香港社会文化是战后香港的一大特点,对于“97回归”意义很大。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反映在教育上,存在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归属方面,如文化、社会、政治等。例如教学语言是英语还是汉语、学校与之相联的各种组织以及学校内的社会阶级组成等。另外,香港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市场力量占统治地位,传统价值观式微,以致缺乏道德精英,形成道德和文化上的责任匮乏等特点,加上与英国传统的英才教育、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在8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严格管理体制和监控机制的学校教育系统。这样营造成了一种香港所独有的现象,即尽管香港人口拥挤,许多学校都处在居民区之内,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融合却很少。这种距离既由于教师和家长之间缺少沟通,也由于学校领导同社区之间的隔膜,各种学校管理委员会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向所在社区直接负责的团体,而只向教育署负责,因为他们的经费分配及视导是由教育署负责的。
另外,也有学者根据香港的社会文化属性而得出了其独特的对于回归前后教育特点的认识。Sweeting认为,由于香港人中的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其文化归属是中国,对于他们来讲,英国的殖民几乎近于不相关,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如子女教育等都反映了中国的传统。香港早在英国殖民以前就已经有了学校,这种建基于中国模式的学校一直都在发展延续着。所以,香港在过渡时期并不存在许多在其他殖民地中的那种殖民传统与回归后民族价值之间的冲突,而只是中国教育之内的不同变异之间的统一问题[5]。
香港的政治情况对教育也施以显著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香港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真正的民主。香港的主要政治要素就是集权、施仁和法律典章。香港没有像其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拥有民主,而且港人对选举的兴趣一直不大。香港的学校从未在香港的民主化中起过作用;若有的话,也只是阻碍的作用。直到80年代末以前,课程一直都对增长中的政治意识不予理睬。尽管回归使课程稍有修正,但政治民主化仍然是一个尽力避开的话题。
刚刚辞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而赴美国荣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程介明博士,则从理论高度分析了香港教育政策的合法性问题。他指出,香港政府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的两个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其经济上的成功和有意识地制造出决策中的居民可信度。实现后者的两个主要途径主要是雇用专家和进行咨询。各种咨询委员会一方面显示出其代表群众的性质;另一方面为政府制定政策合法性提供根据。政府官僚机构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咨询委员会而制定政策,它同时设法控制这些委员会,从而使这时的合法性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几乎无任何关联。
香港政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现存政府合法性所依赖的背景条件正在改变;二是政府合法性本身正遭到威胁。今后,选举无疑将成为进入制定政策机器中的主要途径,一旦当选举中的投票成为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手段时,专家和咨询的作用就会变得微弱了。在他看来,专家和咨询是否将成为维持政策制定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是令人怀疑的。但合法性的变化则会增加对政治权力的强调,并减少对知识理性和日常专家咨询的依赖。一个不拥有未来的政府不可能去关注培养其合法楔性的,而不幸的是目下的香港政府正如此,当“97回归”,在即,它可能继续努力维持殖民地的稳定与繁荣,但若不在合法性方面下更大的本钱将会陷入困境。当前的政府显然已忽视政策制定的程序及合法性问题,因此遇到了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夕阳政府并不惊讶,但对香港未来却是有害的。合法性的变化或可使未来政府丧失公民的信任,或给未来新政府遗留下推行教育政策方面的官僚化与政治操作上的一种宽松状况[6]。
四 回归使得香港教育界长期以来的英才教育与平等主义之争更加引人注目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专业来自香港的博士生李君贞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德新指出,香港自70年代中期始包括整个80年代都在试图改革中等教育以减少升学竞争的不良后果,因此平等主义与英才主义的冲突就成为民众争论的中心。面临“97回归”,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并与过渡期的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政治上,香港政府正在致力于全面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在英国1997年退出时能够发挥作用。与此相应,出现了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地区性和中心政府机构,以及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组织和一些半政治性团体表达了许多公共问题。在这种香港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对平等主义的呼吁,便成为对形势的一种正常反应。
在经济方面,由于大量香港人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间阶层管理人员移居外国所造成的人才流失,引发人们对教育制度的质量更加关注。香港人才质量一直是并仍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尽管教育中的英才主义过去一直与英国的传统相联系,但英才主义政策仍是过渡期之间保证教育质量的因素。简言之,英才主义与平等主义在80年代的争论在“97回归”前后的过渡期内仍将继续下去[7]。他们认为,鉴于“97回归”在望,以及严峻的人才外流的状况,香港政府教育政策似乎更应强调教育的质量而不是平等问题。
白杰瑞认为,传统的英才教育系统将会使得英国通过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成为社区领袖而继续施以影响,这也会使英国在撤出香港后继续保持有利的联系。他指出,香港教育委员会看起来正在努力延续英式高等教育,其最有争论的教育改革计划对非殖民化问题具有直接影响。改革内容是在中六方面,但却对香港大学有重要影响,改革所陈述的目的是使中六教育标准化,减轻考试压力,统一大学入学计划,其影响却使得大学教育年限问题被推到了议论的中心[8]。
五 教学语言一直是香港学者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
对于教学语言之争可追溯至二战后。政府虽然承认普通话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在实践中却没有加以推进,不作为真正的要求,因此目前香港仅有2所中学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但香港有学者认为,普通话无疑将成为官方语言而取代广东话和英文,所有人都必须学会普通话。可是,大多数的香港本地教育工作者强烈反对用普通话作为学校教学语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话是他们的母语[9]。用英语作为中小学的教学语言给学生带来很大的负担,因为多数学生几乎没有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过接触。由于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念书对于将来进入政府部门有利,许多人和家庭都争取送孩子进入英文学校,而政府并未对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给予关注,相反却可能会由于政府某些政策而加剧,一项新的政府语言政策计划是使进入英文中学的入学考试建立在中六以后考试的基础上。该计划的公开目标是提高至少一种语言的能力,减少中文式的英文。计划的结果将会扩大教育制度中的英才性因素,限制人们进入香港大学及政府部门的机会。
总体上,香港教育决策者只是鼓励而不是强行推广普通话,而过去,他们对广东话则是从制度上硬性要求的。但是,正如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Herbert Pierson指出的,随着回归的到来,大陆官方语言普通话将成为有力竞争者。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两地经济联系日多,学习普通话的人也日益增多。回归后,现在用得很少的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地位将超过英语和广东话。这样将会出现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语言现象,即一个社区存在着两种高位语言和一种低位语言。普通话为政治和管理语言,英文为技术、商业和金融语言,广东话为家庭内和熟人间的使用语言[10]。他主张通过把普通话学习与学生的考试挂起钩来,从而建立起激励机制。同时有些关于中国的主干课程可以用普通话教学,以便让学生有更多接触和学习普通话的机会。他援引语言学家Bauer的论述,指出普通话将取代英文,也可能会取代广东话,从而成为权力者的语言和官方使用语言,所以每个人都应学习它[11]。Pierson认为,使用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将会是使香港这个讲广东话的小社会在1997年以后保持稳定和繁荣的一项实质性的投资。
香港大学课程系讲师过伟瑜更具体地罗列出了必须推广普通话的几大理由:第一是政治因素。随着回归问题的提出,普通话已在使用,回归后会更多地使用,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必然扩大,因此应学习普通话。同时,与中国大陆打交道不可能寄希望于大陆官方学习广东话。她援引一位香港中学理事的话指出,如果香港仍限于广东话的话,它则冒险被大量大陆与台湾讲普通话的人所孤立[12]。第二是经济因素。中国大陆开放政策使香港贸易额飞涨,讲普通话者在做生意时会有很多好处与方便。同时讲普通话还将有利于同其他讲普通话的国家做贸易,如“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国都是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第三是教育因素。长期以来,香港学生中文写作水平一直是个问题,一些教育家建议通过推广普通话来提高。因为讲广东话常常对提高中文写作不利,虽然孩子可以学会中文写作而不懂普通话,但这样做的难度却加大了许多。
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Keith Johnson指出港大的情况是香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用广东话,与大陆交流时用普通话,与国际交流时用英语,这一状况也适于其他学校。尽管未来一段时间学生仍主要来自本地,但来自大陆各地的优秀学生会增多,普通话应予强调。三种语言的使用使得学校在录取学生时要更多考虑语言能力,而学生为了提高语言而花上大量时间精力会影响其学术进展从而降低入学水准,同时大陆学生的增加也使本地学生学习普通话的需要更加迫切[13]。
但是,维持一种高水平的英语知识对于香港维持国际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贝磊(Mark Bray)所指出的,英语知识将使香港人继续与国际社会和文化保持沟通,其中最明显的意义是香港将保留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范围之内,尽管其同时将会更加对大陆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表示理解[14]。
六 回归引发了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本土化问题的争论
在香港,自英国占领香港岛之后的约100年时间里,殖民地学校中教师职业都是由英国人、其他欧洲人或美国人充当的,正是这些人计划、发展、落实课程,控制着教育。与其他一些殖民地一样,香港课程只是模仿他人的结果,其主要的学术课程如物理、生物、历史、经济学等同英国"0"水平和"A"水平相似,初级中学的综合科学课程是根据苏格兰的同样性质的课程计划制定的。社会科学课程虽不是直接模仿英国,但仍是西方式的,主要是受到加拿大课程计划的影响[15]。80年代期间这种对外依附性明显减少,主要是由于许多当地问题的出现对课程产生了影响,人们逐渐意识到由于政治的变化给课程管理、制定等带来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香港教育中正规教育与本土需要不尽吻合的情况。所以,程介明教授指出,香港教育的困境是西方观念与传统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16]。
近年来,香港有意识地实行教育政策的本土化,教育署自1984年起有了本地人做主任。但是,根据贝磊的论述,政府高层仍为外籍人士控制,而且在本地人中,有不少都在西方接受教育,持着西方式价值观,甚至拥有外国护照。这种状况对于教育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贝磊还指出,香港教育制度也受到外界咨询人员的重大影响。比如七八十年代人力资源计划是由Peter Williams和伦敦大学做的,香港大学成立听说科学系时就从英国邀请了一个小组咨询其对课程与师资的建议。198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组建的影响很大的小组负责人Sir John L.Lewellyn是英国人,成员中Greg Hancock博士是澳洲人,Michael Kirst教授是美国人,Korl Roeloffs是德国人。
香港的高等教育机构喜欢把自己看成是具有国际地位的,这一点具有模糊性,而且反映出强烈的西方式偏见。例如,机构很少将自己与南亚、非洲或拉美的高校相对比,它们的目标模式是根据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而制定的[17]。香港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偏见,在1989年8月,61%的成员是西方人,其中不少甚至不是居住在香港,包括英国莱斯特多科技术学院负责人、一位利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伦敦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和利兹大学校长、澳洲的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负责人、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以及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和澳洲新南威尔士技术学院的前任校长等。
香港高等学校教师中西方人的比重也极大,最典型的是港大,其教学语言是英语,并且以其从全世界聘请师资而骄傲。所谓国际聘请其实主要是从英国,其余的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文大学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其主要是用中文讲课,因此不需要那样多的外籍教员,但即使是香港当地人,其背景也仍是西方的,在西方获得的高级学位。其他几所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香港有大量学生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其数字远远大于在本地的学生数[18]。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好,一来昂贵,二来不切合香港实际。但在贝磊看来,这也有好处,如海外生活经验可促使港人更加开放。
七 香港人才外流现象是香港教育界学者积极探讨的现实问题之一
香港国际教育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Glenn Shive指出,香港缺乏自然资源,唯有依赖人力资源。即使没有人才流失,也存在人才短缺。大量技术人员移居海外,在香港向高技术信息经济转型时更加重了人才的匮乏。1989年中期,香港劳动力共2,757,800人,占总人口的47.9%,平均年龄34岁,一半以上具有中学教育水平,7.4%具有高等教育水平,5.9%拥有学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为7.4%,3.8%为管理人员[19]。根据政府1990年的综合人力调查,在所需的286万劳力中,29%将不得不由回港的学生充当,37%由现有劳力担任,28%由当地毕业生充入,5%以移居外国再次回港者和新移民补充。政府认为90年代中期因在海外学习而流失的人数达118,400人,移居海外者达427,000[20]。这种移居海外的趋势对一系列职业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律师、法官、系统分析员、程序设计员、会计、审计员、调音师、医生、牙医、护士、助产士、工程师、建筑设计师、测绘员,以及各种经理人员。这些人一般都是年轻而且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专业工作者、管理人员、经理等。他们的离开还给那些决定留下来的人带来了低效率和低生产率,引发大量人力资本的丧失,并因而导致香港资本的外流[21]。移民国外的回港率少于10%,在他们中间,只有不到1/3的人愿意在1997年以后仍滞留香港。
香港当时所做的人才流失的估算是,假如大陆一切问题都圆满地获得解决、香港经济稳定的话,则1990-1994年每年离港人数约在7.5万人左右,到1995年由于回归在即再次出现高峰。按此估计,香港可能失去约70万人,占总人口550万的近13%,其中至少1/4的人被认为是对于香港的社会与经济非常重要的人才[22]。目前,香港已经遭受了人才流失的影响,在1996年前必须拥有93,400名新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这些职位中的绝大多数只能由拥有学位或较高资格证书的人担当。然而,调查显示在1996年将会缺少36,700名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员,考虑到将会有27,300名研究生毕业,仍将缺9,400人[23]。
八 香港回归能否在提高妇女教育方面有所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麦肖玲认为,总的来讲,香港妇女从教育扩展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在男女平等的教育政策方面仍存有不平等,尤其是在较高级的教育目标方面更是如此。在水平差异减少的同时,平行差异仍很严重。传统上认为属于女性的职业和专业中女性过多,而传统上的男性学科和职业中则女性太少。尽管女性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对妇女教育的投入大大少于男子。经济发展结构升级和大量人才流失使得女子将成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要求人们对传统看法加以改革[24]。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香港各大学女生比例都在25%左右,1963年猛升,原因是中文大学建立起来了,这年港大本科生中女生比例为31%,而中文大学达36.3%。从那时起,女生比例一直在上升,到1988年已达42%。1988年,港大女生在各科的比例为:艺术68%,法律55%,社会科学44%,建筑31%,医学19%,牙科18%,自然科学15%,工程3%。中文大学的情况也类似,分别为艺术73%,社会科学68%,商业管理62%,医学26%,科学24%[25]。尽管香港妇女从教育大发展中获得益处,但无论是在各种机构还是在家庭中受歧视的情况仍很普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仍阻碍许多女性的自我实现。
“97回归”将怎样影响香港女性的地位仍不被人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都认为香港女性已赢得了平等、歧视女性现象已不存在。香港回归不太可能终止目前的女性不平等状况,也不太可能引发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由于社会上对这一问题不甚关心,为数不多的香港女性组织不太可能从未来政府那里获得太多的鼓励。
九 香港回归之后最主要的教育工作是两地的学术交流
白杰瑞强调,现在经济上与大陆的相互依赖并未与教育或学术上的相互依赖相匹配,实际上,在两种教育制度之间至今尚无结构性的相互依赖,两地高校间的正规协定不多,香港地区高校与内地的正式学术交流主要是由大学中各系、院教师利用学校的学术交流经费在个人之间进行的。就发展来看,自80年代初始,两地学术交流开始增加,但科技工程方面远远多于其他方面。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等以及在香港的其他一些机构如中港学术交流中心等在把各大学联系起来中起了一定作用,学生交流也日益增多,奖学金计划使得许多香港学生进入大陆高校学习,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其他学生则多在广东上学。
贝磊则做了以下的分析,他指出,正如阿尔特巴赫和凯利所认为的,殖民地学校在语言及其服务宗旨上都与当地相背离[26]。香港在开始时曾帮助乡村学校和古典汉语学校,后来逐步以西式教育为主了。采用西式教育使得香港走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使之建立起国际依附关系。虽然香港学校从中国分裂开来,但大陆当前却走上了一条相似的路径,西式学校在中国大陆也已根深蒂固了,从而使得两地在相互可资借取的方面大大地增加了。展望未来,香港有不少可以为大陆提供如课程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技术、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经验,香港也可向大陆学习,例如推广普通话教学以及通过学校系统树立祖国的归属感等。目前,两地之间的联系正在迅速加强,香港与大陆间的各种官方代表团互访日多,香港各大学都设有鼓励与内地联系的专项基金。香港政府不承认内地学历、学位的做法一定不会长久。一旦政策改变,将鼓励更多人去内地学习,同时更多的内地学生将来港学习,当前的人数虽不多,但其增长速度却是极快的。
香港大学课程系副教授梁一鸣指出,对两种教育制度的仔细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特点,如在管理和课程方面都是高度集中的;二者都在早期进行学生分化;专业狭窄;在文科与自然科学间都有显著的区别;二者都比较轻视社会科学,以及二者都重视高等教育而牺牲了初等和学前教育等。总的来看,香港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社会,与大陆有着很强的文化认同,香港保留了大部分的儒家教育传统,像尊重学校权威与规则,重视考试成绩等,现有情况已说明在大陆与香港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并将继续加强。历史上,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自19世纪早期以来一直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随着回归逼近,两地交流增加,大陆学生来港攻读高级学位的日多,很多香港学生到大陆高校学习尤其是医学、中国文学、法律和工程等。其它形式的交流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树人学院的中国法律证书,中文大学的生物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同行在香港和国际上的革新合作等。在其他方面如香港吸引了不少大陆技术人才来港成为合法移民或工程师,尽管这些人的资格并未得到正式的认可。鉴于香港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人才流失现象,香港教育委员会倡导大陆学者访港的短期合同的做法。同时,大陆正积极地利用香港学习西方管理技术,如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对两地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技术交流的促进,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派遣大量中学校长和师资培训人员到港大进修学习等。
他最后强调,从经济上看,将香港与大陆隔开是不可能的,其实二者已融合在一起了。在教育方面,可以预见到二者在过渡期间的相互依赖和互惠互利;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制度也将保持其独特性与独立性[27]。
十 回归对教育影响的展望
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回归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教育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底其对于回归是起着支持的作用还是抵制的作用,不少学者仍认为尚难肯定。白杰瑞就曾指出,教育既可用于支持过渡,也可通过培养香港的英才和领导者用来继续英国的影响与控制。他认为,中国政府把影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围之内的想法令人怀疑,而且香港学生也因社会变革而变得更加政治化,他们对伦敦和北京的影响都可能会采取不尽合作的态度。“97回归”使香港处于困境,有了归属感却失去了教育发展的方向,也使政府在控制文化传播机构时其合法性权威(Legistimacy)处于危险的境地[28]。但是,无论如何,与大陆其他地区保持一种独立性对于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改革过程的影响都将具有重要的潜力。中国大陆对于香港教育发展的影响将取决于它是以一种民主化为实质的教育改革过程为中介,还是重新建立一种谘询制度以使教育发展与大陆的要求相一致。即使大陆做出了不太可能的努力,企图使香港政治保持现状,目前的发展趋向也难以维持。香港当地领导人将会受到很大压力捡起殖民者所遗留的传统,而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以政府为牵动的教育变革。
也有一些学者直接表示对回归后发展前景的悲观态度。Sweeting的观点是,转移(transition)对香港今后教育的影响在总体上是负面的。香港人口的不持久性常常被用来作为避免长期规划尤其成为拒绝提高教育质量与数量的理由,转换所带来的变化将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同时,转换也提高了教育在授予学位方面的重要性,从而可能会出现学位增多而质量下降的现象。另外,转换对于当地文化发展也有着负面的影响。
Sweeting认为,转换已给香港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多是涉及到共同体和归属方面的缺乏。如果有什么益处的话,它们或与物质财富的增加相联系,伴随着快速移动的资本和劳力;或与由来来去去带来的城市化有关。由于一些人刚刚从外地到港,一些人马上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他们将对外界国际性趋向保持警觉,这一点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开始日益依赖于第三产业的社会上所存在的力量[29]。
历史地看,香港除了在近代一个短暂时期内在政治上对大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外,其贡献都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回归之后,香港能否利用自己的国际化特点和中国教育正在努力融入国际教育圈的现实情况下作出其独特贡献呢?贝磊认为这一点是应予以肯定的。他提到,Lugard在最初设立香港大学时就要求香港大学像为香港服务一样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服务,这一宗旨在港大后来长期的发展中未被重视,更不能获得实现。现在随着香港回归,应对这一问题予以认真的考虑了。
注释:
[1][2][3][4][5][6][7][8][9][10][14][15][17][22][24][27][28][29] Gerard A.Postiglione,ed.,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Kong:Toward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P7,P248-249,P117,P72,P41,P113,P149-151,P15,P208,P183-184,P91,P120,P85-88,P226-227,P167-168,P267-268,P32,P68-69.
[11] R.Baucer,"The Hong Kong Cantonese Speech Community",manuscript,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er of Asian Studies,1984.
[12] Hong Kong Standard,April 13,1987.
[13] Keith Johnson,"Medium of Instruction:Policies and Options",Interflow,University of Hong Kong,Issue49 (1986).
[16] K.M.Cheng,"Traditional Values and Western Ideas:Hong Kong's Dilemmas in Education",Asian Journal of PublicAdminist ration,Vol.8,No.2 (1986),P199.
[18] G.Postiglione,"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the Labor Market in Hong Kong:Functions of Overseas and Local Higher Education",International Education,Vol.17,No.1 (1987),P51.
[19]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Labor ForceCharacteristics,Quarterly Report,1982-89(April to JuneQuarters)(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
[20][23] Hong Kong Government Manpower Survey,1990,unpublished.
[21] Paul Kwong,Pak-wai Liu,and Stephan Tang,Functional Core of the Labor Force:Toward the Retention of KeyPersonnel in Hong Kong (Hong Kong:December,1989).
[25]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Annual Digest 1989,P211.
[26] P.G.Altbach and G.P.Kelly,eds,Education AndColonialism (New York:Longman,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