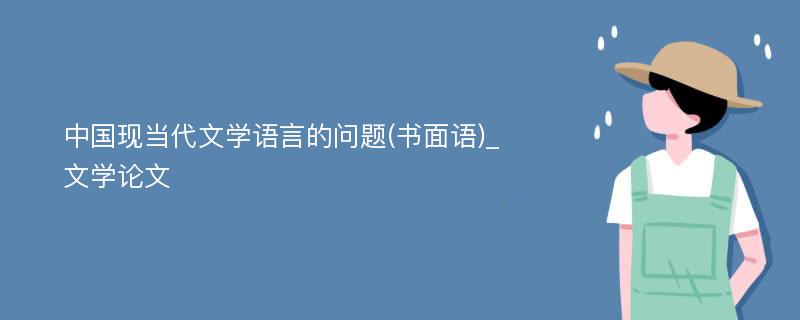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现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想不出题目,现成借用一下。 这次会议是雅集,也是盛事,但到此也就将告结束。两天密集的会议,有来自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内地32位学者参加,各位都提供了自己关于语言方面最新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大家也都和我一样感觉获益匪浅。这里不敢说总结,只谈几点肤浅的感想。 本次会议第一个特点是涉及面广,研究方法多元。 比如,陈建华(以下一律直呼其名)将现代“香艳(私密)”小说与民国初年的共和主体及文化转型联系起来,细致考察现代汉语书面语在报刊(尤其是小报)文体上的呈现。张卫中系统梳理了晚清科幻小说大量出现的“新词语”并将之归属于作家的科幻想象——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想象与设计。 关于“五四”文白之争和周氏兄弟、胡适白话文理论与实践之重审,仍然是学者们不约而同属意的对象。王风从周氏兄弟的杂感与小品出发,关注现代文体建构与语体的养成;朱晓进研究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虽为旧文,仍有新意;寇志明梳理了鲁迅早期文言文在海外流播并对其重要性进行新的探讨;张业松从“祥林嫂的声音”来探讨鲁迅语言世界的一个或许长期被忽略的方面,即鲁迅小说的语言如何随人物的身份与命运而展开;范钦林以《沉沦》中大量使用西方人名、地名为例,探讨了西方语汇与中国现代小说创生的关系;张宝明重审百年“文白之争”,尤其关心语言作为最深层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坍塌之后所带来的现代性偏至以及今人所面对的大量工作;段怀清则将胡适白话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和评价与白话文学的实绩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曹清华对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进行了反思,提出这到底是意识的危机还是语言的危机这样或许很难有结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现代新诗格律化的物质基础和当代诗歌个体言说的可能性也为与会者所注意。王雪松认为现代诗歌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物质基础”造就了现代格律诗独特的命名和构型;何言宏把个体语言与个体经验相联系,指出正是它们与公共经验、公共语言之间的对抗造就了个体语言可能的表达策略。 更深层次的挖掘,如中国现当代小说、散文、戏剧和日记等各体文学语言问题的历史脉络,也令研究者倾入了更多心力。小川利康从周作人的《小河》到《老虎桥杂诗》梳理了一条作者从欧化白话诗到文白夹杂的打油诗的发展历程。千野拓政则从现代文学伊始的“三篇日记”来探讨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文与本土固有的白话文之间的差异,力图寻找现代文学诞生时的关键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今天的遭际。祝克懿对文革“样板戏”文本的异域收藏与认知范式进行了研究,视野十分开阔。 与现代汉语联系紧密的日语问题也受到关注。林敏洁从鲁迅的日语学习考察了日语汉语教育与中国作家的语言习得之关系,藤井省三则研究了在此相关背景下日本读者对现代中国作家的接受。除此以外,文贵良谈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西学与中国传统的资源,高玉涉及当代文学的整体语言品格和语言优势,吴俊着力于现代中国语言转向与文化权利运作的关系,郑亚捷追问当代文学“边疆叙事”对文学语言可能存在的影响……所有这些课题的论述都十分精彩。 文学语言本来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如何选择课题,如何确立相应的方法论,都很难定于一尊,今后恐怕还会保持这个势头。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涉及面广,方法多元,但也凝聚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话题。 比如,这次许多专家都谈到方言,但角度各不相同。有小说家的方言,如罗鹏谈阎连科最新几部小说里的方言;有散文家的方言,如黄维樑谈香港作家黄国彬的“四合语”特色;还有诗歌的方言,刘进才就从《歌谣周刊》到《新诗歌》的梳理中,看出方言的“发现”与诗歌体式的探索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单独讨论方言问题,更多则将方言和其他语言要素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比如与方言有关的“声音”和“听”的问题。前述张业松描述了声音中的“祥林嫂”,贺昌盛谈论了“声音”在现代性进程中的隐性作用。应该说,方言是现代汉语研究界的一个核心问题,涉及整个现代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而方言在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写作各个不同时空更有异常复杂的呈现,今后研究空间还会很大。这次许多专家在梳理“五四”和整个现代时期提出(刘进才教授称之为“发现”)方言或“方言文学”的脉络,较之以往,更加深入而清晰。 方言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但本次会议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其他语言要素也有出色的研究。比如,不断成型而又变动不居的占主流的普通话书面语(黄维樑引余光中所谓“白以为常”),欧化和其他方面的外来语(坂井洋史所谈“新感觉派”与陶晶孙的语言突破、张卫中列举晚清小说中的新语词),文言的采用,还有黄维樑谈到的网络“潮语”,以及这四者的混搭与和合现象(“三及第”、“新三及第”、“四合语”、“五行无阻”)……从“五四”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展开之初以迄于今,始终就是贯穿性和结构性的主题,与文学界之外的语言政策、语言计划以及来自教育和文化部门的权力运作,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方言,不能不经常触及上述诸多语言要素。 尽管如此,作家个体存乎一心的选择和创造,更需慎思明辨。这就不得不提到本次会议第三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会议收到的29篇论文中,竟有15篇专论一个作家一部或多部作品的语言问题。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趋势。 这或许跟去年华师大会议闭幕式上一些专家的倡议以及本次会议通知的某些建议性问题设计有关,但大家提交的论文绝非应景之作,都是各自学术研究计划长期积累苦心孤诣的结果,因此作家语言问题的凸显就更能反映当下一种学术兴趣的转移与深化。 除了鲁迅仍然是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千野拓政、朱晓进、张业松、林敏洁、金河林、寇志明、藤井省三都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川利康所谈周作人,千野拓政所谈周瘦鹃,范钦林所谈郁达夫,坂井洋史所谈陶晶孙,洪昔杓所谈张爱玲,王彬彬所谈高晓声,黄维樑所谈黄国彬,罗鹏所谈阎连科——这些作家的语言问题,包括与语言有关的诸如王风所谈周氏兄弟文集编纂方式和“杂文”概念的流变——都在15篇论文中有极富启发性的论述。 当我们说“语言是活的”,这还只是一个抽象、宏观、甚至停留在常识层面的描述。语言之所以是活的,乃因为有无数活人的生命投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个时代的作家们的语言实践与语言创造。作家的语言实践与创造无疑受制于给定的语言环境,但反过来又深浅不同地在语言环境中留下各自的印痕。究竟是语言在说(写)人,还是人在说(写)语言,久已是困扰哲学家们的难题,而对研究文学语言的学者,却正是最有诱惑力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前两天在罗鹏教授主持的“昆山杜克大学”一次别开生面的工作坊中,一位学者说,你们又要召开语言文学的会了,那可是个高深的问题啊。我想这言下之意,该是说语言问题容易流于玄虚,也许早就很玄虚了吧。 毋庸讳言,研究文学语言,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是很容易流于玄虚的。但文学语言问题无论如何容易流于玄虚,只要和作家具体的语言实践和语言创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顿时就会滋味无穷,绝非“触不可及”。当然,作家作品的语言研究,也只有不断拓展文学语言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才能更上层楼。这个局面今后恐怕也会继续保持下去。 “五四”新文学初期所谓“语言工具的革命”,主要还是宏观历史与理论层面的文白之争,当时尚来不及深入考察个别作家的语言实践。这个局面一直要到现代文学语言本身日益成熟、壮大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作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语言风格之后,才引起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关注。 从40到80年代,个别作家或某一流派作家的语言风格问题一度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但这种研究取向不知不觉慢慢脱离了现当代中国文学语言转型的大背景而被孤立起来,收缩为文学研究内部的一个领域,而失去了应有的历史感。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五四”新文化及其内涵的白话文运动的再反思,作为文化选择和文学创造过程的语言现象再次被强调地提出。在此学术背景下,文学语言问题不得不冲破单纯的文学研究、作家研究尤其是作家语言风格研究的狭隘范围,重新回到语言、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巨大历史现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无限可能。 但物极必反,到了新世纪又趋向另一个极端,就是研究文学语言,历史和宏观的视野固然不断被拓展,然而对于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历史变迁中作家个体语言实践的细部考察,又经常被忽略;而缺乏对作家个体语言实践与创造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谓宏观历史的语言问题的考察就会脱离文学这个须臾不可相离的活的语言本体,就不能在活生生的作家语言的实践过程中触摸到语言历史的深度奥秘。 作家语言观念、语言探索和由此形成的语言风格,在将近一百年的文学语言研究中似乎走了一个“之”字形载浮载沉的曲折道路。因此可以说,今天作家作品的语言研究不是简单的返顾,而是带着以往宏观历史与理论问题考察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而在更高水平上完成的回归。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者说问题,是关乎文学语言的学术课题实在太多,许多研究者一开始专门研究文学语言,后来逐渐伸展开去,花了更多功夫去探究造成某种文学语言现象的更深的社会文化尤其是文化制度的问题。推其用心,大概就是知其然,也欲知其所以然吧。唯其如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才每每令单纯研究文学语言的人惊叹不已。但也要看到,文学语言毕竟是文学的,倘若这些远行者们愿意时时返顾“旧乡”,则他们的探索对于文学语言研究水平的提高,一定功莫大焉。 此外,还有一篇论文和一个临时增加的学术报告,专门对近三十年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方法和存在的问题做出深入思考,这就是夏莹、王泽龙和范钦林的两个报告。当然,许多精彩的评议和报告、评议之后热烈的讨论,也包含了许多反思以及未来研究的可能。 必须承认,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论著出来,更加深入而切实地反思与梳理“五四”以来文学语言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促进我们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自觉。 一次学术会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深入触及哪怕一两个小问题,就非常不易。而如上所述,本次会议同时摊开了偌多的问题,又将这些问题彼此联络为紧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系统,极大地提升了学术对话的有效性,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已经有好几所大学表示愿意承办明年的语言研究会议,我们也期待着,能在下次会议上再如此美好地“谈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