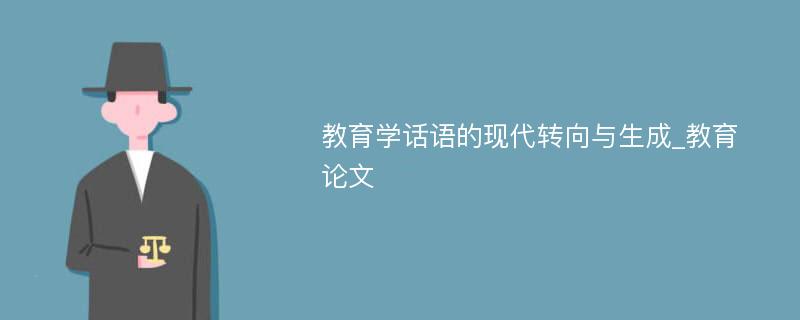
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教育学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学现状,力求走出“思想的贫困”,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教育理论的生成做些实实在在的拓荒的努力。任何研究都在一定的话语之中展开,表面上看,是研究者任意使用话语,但深入下去却发现,话语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支配着研究者,好比空气,研究者不知不觉地置身于话语的影响力之中,受话语的左右。深入考察教育学话语,或许会引领我们触及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一、“说”什么“话”:公共性话语的滥觞
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说”教育学的“话”。或许,我们并没有仔细地思考过我们究竟“说”的是什么“话”。
自从五十年代凯洛夫教育学引进我国,其话语框架便成了我国教育学话语的基本框架,并沿袭至今而无根本性突破。这似乎预定了我国当代教育学话语的整体命运,是植入的,不是原生的;是先见的(即先有一套话语再去“说”),不是“面向事情本身”的(即先有“话”要“说”,再去寻找合适的话语)。我们在“说”自己的教育学“话语”之先,必须习得这些先见的话语模式及话语规则,成为我们“说话”的“话语准备”。这样,我们在“说”“自己”的“教育学话语”之先,实际上大脑里装满的是这些被公认的众所必备的公共性话语,以及由话语规则所产生的各种潜在的“暗示”、“指令”。比如,我们把教育学分成几大块,“教育基本原理”、“教学论”、“德育论”、“教育管理论”,你在“说话”之先,得确定你属于哪一块,你必须遵循你那一块话语的规则,谈德育就是谈德育,谈德育的“规律”、“功能”、“原则”、“方法”,如果你越出了基本的话语框架和规则,那叫“不伦不类”。这一套先见的公共话语框架左右了我们的话语,在“说话”之前这套“话语”先“说服”了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顺着这套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话语的指引去“说”教育学的“话”。如果把这些话语全部“括起来”(胡塞尔),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多少“自己”的“话”,我们“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人家的,话语的“贫困”便立刻显露出来。
当然,我们对引进的话语框架并非照搬不误,我们同样经过了自己的加工改造。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加工改造”的呢?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话语对于我们可谓“根深蒂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等,这些命题当然是正确的,现代教育不可能关起门来背诵“之乎者也”,如果不联系实际那就根本产生不了理论,关键在于何谓“结合”。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高呼这些个“结合”时,“结合”就成了大话、空话、套话,成了“大帽子”随处可戴,成了“万金油”随处可擦。当这些充满着权威(权力)性的先见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里扎根的时候,又成了另外一种无形的“力量”、“命令”,潜意识地指挥着我们“说话”。在原本不能跟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便“凑出”一条理由来人为“联系”,在原本理论都没谈清楚的地方我们先要考虑“联系”一下“实际”。
现代教育应充分注重其政治、经济功能,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于是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便成了教育学的“权力型话语”。谈德育要谈“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谈美育也要谈“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谈素质教育更要先谈“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学生读《红楼梦》也似乎非要首先“研究”出来一些“政治”、“经济”的“功能”不可。
八十年代,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说,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富于远见卓识的教育命题。但战略性指导思想不等于战术性的行为方略。问题恰好在这里。“三个面向”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到底言称什么?是不是任何时候都要牢记着如何去“三个面向”?如果我们随意就打出“三个面向”的“牌子”,“三个面向”就成了教育学话语中的“权力话语”。
九十年代,“素质教育”应该算得上一个生成性概念,是不是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成了中国教育话语转向的一个契机呢?在我看来,回答是否定的。一方面,素质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上下推动的“热潮”,从而使“素质教育”成为新的“权力话语”,人人都大谈“素质”、“素质教育”,似乎不谈此就跟不上时代、潮流,浮躁有余而冷静不足。另一方面,为赶潮流,大家又重新拿出了原有的话语框架,来“说”“素质教育”。由于基本话语并没有改变,只有增加了几个“××素质”而已,如果我们把原来的话语一一“括起”,素质教育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属于其自身的话语。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植入性的教育学话语的根基不牢固、不扎实,所以我们的话语才很容易“风吹草动”。我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话”?人云亦云的公共话语、政治性话语、习惯性话语、权力性话语,我们“说”来“说”去大都未逃出这些预置性话语的“手掌心”,“说”了许多,不过是这些先见性、预置性话语的延伸,唯独缺少“自己的声音”。
2.怎样“说话”:我们说话的态势
自五十年代以来,教育学的话语框架并没有质的飞跃,只有现成话语的不断完善,却并没有话语框架本身的突破和话语的转变。我们实际上是先在地默认了现成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就代表了教育本身或中国现实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而理所当然地充当我们继续“说”“教育的话”的起点。由于现成范式的根深蒂固,我们在新的研究过程中,便始终潜在地有一个研究者集体的“说”、他者的“说”。这种集体性的话语先在地被寄予了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便不自觉地转化成一种“命令”,从而制约、牵引着“我”的“说”,“我”是在看他者怎样说,“我”再接着他者的“说”继续“说”,表面上“我”“说”的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话”,实际上却只是“他者的话”的延伸。“我”“说”的不是“我”的“话”,而是虚拟的他者在“指令”“我”,“令”“我”“言不由衷”。我们本想“创造”出一些新的“思想”来,却不知不觉地落入原有的、先见的、外在的话语框架,成为传统话语、习惯话语、权力话语的延伸。“思想”的“贫困”即“话语”的“贫困”,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言不由衷”、“话不由己”。
而我们实际上习惯了“说”他者的“话”。因为他者的话、公共性话语、集体话语、权力话语总是“对”的,而我们从来就怕出“错”,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云亦云”最保险,即使“错”了也不干“我”事。我们在研究之中想的并非怎样使理论按问题本身的“方向”、“道路”深入下去,让“思路”通畅,而是怎样在现成研究范式和话语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怎样与实际相结合,怎样与“三个面向”结合,怎样与素质教育结合……众多“结合”的潜在“指令”“先入为主”地制约着我们的思考路线,无意中削弱了理论深入的勇气与可能性,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突破这些先在的话语框架而真正深入到“事情本身”或问题本身之中去“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没有作为个体在“思”、在“说”,“思”那“事情本身”,“说”出我们作为个体的“思”,让我们的“说”成为我们作为个体的“思”的结晶。
3.问题的症结:个体性话语的缺席
我们确定在不断地“说”,为什么我们“说”的“话”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言不由衷”、“话不由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个体性话语的缺席。缺席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事教育研究,何谓“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当然是研究教育,何谓“教育”就成了研究教育的起点和关键性的问题,任何教育研究都必然地是在一定的“教育观”的基础上展开。但“何谓‘教育’”本身即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教育是人的活动,人是“生活世界”中的人,任何教育都发生、包容在“生活世界”之中,教育本身即构成人的生活,教育生活,任何教育都是人的“生活的事件(事情)”。“生活世界”以物质世界为基础,但“生活世界”却不是,也不可还原成单纯物的世界,不可完全客观化。包容在生活世界之中的教育生活同样不是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纯客观的世界,作为“生活的事件”而不可被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而整齐划一(并不排除适度的标准、规范、模式,而是指不能彻底地“化”)。“我”研究教育、“我”看教育、“我”把自身“沉浸”在“教育的事件(事情)”“之中”,去体验那“教育事情”之中的“教育”之发生。“我”在教育中,“我”在教育的“体验”中,“教育”向“我”渗透、启迪、暗示,“我”沉浸其中并且谛听,对教育生活的理解成为“我”的生存方式。然后“我”表达,表达“我”“在教育中”“教育生活事件”向“我”的暗示、启迪。“我”并不是表达纯客观的事实,而是表达“我”“在教育中”的体验、态度,换方之即表达“我”“在教育中”的生存方式,表达“我”的“在”。“我”展示“我”“在教育中”的生存,亦好敞亮“我”“在教育中”的“思”、“理解”。什么是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即“我”“在教育中”的生存的表达与再现,“我”是“教育生活”与“教育研究”的载体、中点,“教育生活”使“我”成为研究者,“教育生活”与“教育研究”在“我”中续接,得以统一。
不同的研究者看同一个“教育事件”,“看出”的是不同的“教育”,获得的是不同的“体验”,得出的是不同的教育“观”。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说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我”表达、言说,“我”“说”的“话”都是“我”的“话语”。“我”的“话语”植根于“我”的生存,是生存论上的“言说”,本真的“言说”,不是技术性的、手段性的、外在性的,而是本真性的、目的性的、内在性的;不是纯知识论层面上的“我认知—故我说”,而是生存层面上的“我在—故我思—故我说”;说透彻一点,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是“我”所经验的那“事情本身”“让”“我”“说”。“我在”故“我说”,“我”表达“我”对教育的态度,也是表达“我”对人生的态度,“我”的生命(生存)在我的言说中得到阐明、张扬。
恰恰我们的教育研究大量地是在对起点毫不置疑的基础上展开,许多研究是在无(自己的)“教育观”或默认集体的、公共的教育观的引导之下展开的,原本就缺少了对作为起点的教育的测度与审视(比如,研究教学规律,研究者并没有去寻找教学规律之“根本”从而测度一下所研究的“规律”是服从于怎样的“教育观”,并为研究提供方向的保障,而是停留在教学层面上作表浅思考)。源于近代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思维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蒂固根深,我们始终把教育作为知识的对象,主客体分明,“我”作为主体,以研究者的态势去审度是非,裁决曲直,去“研究”教育。生动的教育生活成了单纯客体、静观的对象,规范而标准,我们可以凭借各种手段从中得出统一、精确的规律、原则、方法,建立规范的教育学以及标准、规范、严密的教育学话语体系,众多研究都以趋同为指向,无疑现成话语体系便成了这一“指向”的代表,我们潜在地相信或默认这一话语体系代表或预示了教育的真理,这样,我们在“说话”之先,就已预定了话语的方向与基本准则。我们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上只是为了现成话语的完善,而不是面向教育生活去“说”那“教育事情本身”的道理,我们并没有把“我在”纳入到事情本身和研究之中,我们的研究始终陌生或外在于“我在”。我们的研究态势是“我说话”,“我”原本“无”“话”可“说”,故“我”四处找“话”来“说”(名曰“查资料”),找来的都是“他者的话”;而不是“话”“说”“我”,那植根于生存的个体性体验的“我在性话语”在“心”中,通过“我”“说”出“口”来。这样,个体在性言说便始终没有到场。
4.现代性期望:教育学话语的转向
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对话与交流成为普遍趋向、权力话语的预置受到消解(并不是消解权力话语本身,而是消解其“预置”——如果在说话之先就已预定了其不可动摇性,那还有多少说话的必要呢?——换言之,权力话语也必须平等地参予到对话之中来)的现代性话语走向进程之中,教育学话语向何处去?
中国社会的现代知识进程大都是从引进西学开始的,引进之后再“本土化”成为知识转变的重要范式。时至今日,许多学科已不满足于“本土化”,而开始试图走出西学“说出”华厦学术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本土化”,它就是“本土”。或许,我们目前的教育学还是处在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学的“本土化”阶段或“本土化”完成阶段。如果说,“本土化”的教育学尚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那么“中国教育学”就决不是“中国本土化的教育学”。如果西方教育学中表达了人类教育的普通性的话语,那么它理应涵括了中国教育,不必“化”而“是”。如果西方教育学的只是西方教育的独特性话语,那么它就不是“中国本土化”,那么中国教育学也应从、而且只能从自己的土壤上生发出独特性的话语。归根到底,中国教育学是在中国教育的现实存在处境中生成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学话语并不是把西方的话语“中国化”,而是直接在“中国本土”生成,不是植入性的(从别人那里拿来),而是生成性的(并不排除借鉴他人)。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就是要从植入性转向生成性,从“本土化”转向“本土”,植入性、“本土化”可谓教育学话语建设的初始阶段,生成性、“本土”是教育学话语建设的深入。
要实现植入性话语向生成性话语的转变,需要我们暂时把植入性的传统话语框架“悬置”起来,不让其以先在的合理性“预置”在那里,真正面向我们教育的现实处境,用我们自身的智慧来思想中国现代教育的问题,把虚拟的公共性(集体性)言说转变成个体性言说,让我们自身沉浸于“教育问题”之中,“一心一意”地去“说”我们该“说”的事情,把外在性的话语转变成内在性的话语,手段性话语变成目的性话语,技术性话语变成本真性话语。
现代性话语反对权力话语的预置,它本身同样不以权力话语自居,不是一个确定的高高在上的话语框架,而是一个生成性概念,模糊概念。与其说现代性是一种“设定”、“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期望”、“理念”。话语的现代性转向并不是简单地虚构一个现代性的话语场(体系),引导大家向其“就范”,而是回复到话语的本原之所,回到中国教育的现实存在处境之中,去谋求中国教育学现代性话语的生成。并没有一个虚拟的“现代性”“等在远处”让我们去实现,但有一点,中国教育学要向前走,即使频频“回首”传统,但“路”却总在前方。
5.在“异”与“同”之间: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生成
也许,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确实应该尝试着努力走出那种人云亦云的公共性、群体性话语框架,更多的走向个体性言说,当个体性话语逐渐转变成公共话语时,依然保护个体性话语的存在与个体性言说的可能性,使整个教育学话语充满开放性与活力,这意味着教育学的开放性与活力。
个体性言说的转换意味着话语规则也要跟着转换。传统的话语规则是“求同存异”。“求同”是首要的、根本的,我们在说话之先,所想的就是如何去“求同”,如何把自身纳入公共话语框架之中,去“说”群体的“话”,我们的个体性言说之路一开始就被限定。这是公共性话语模式的基本规则。我们是在“求同”的大前提之下“存异”,其结果是“大同小异”,这或许是我们教育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其实,既然是“求同”,意味着这个“同”是“求”出来的,只有原本“不同”,才有必要与可能去“求”,如果大家一开始就趋同,那么“求”也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所以,在“求同”之先应该极力倡导“求异”,即让大家都把原来的公共话语框架暂时搁置一旁,每个人都尽量倾听自我内在的声音,都说自己“由衷”的“话”,说长说短、说三说四,都是各自所说,话语各“异”。当然“异”中又有“同”,那就是对教育之真的渴求,对教育(学)之现代性的期望,每个人都话语“由衷”,“真诚宣称”(sincerity claim,哈贝马斯),这就是求同的基础, 这就是“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各“异”,“同”在其“神”,这是高层次的“同”。“求异存同”,各异的话语生成,这是个体性言说的根本。“求同存异”,话语聚集、整合,意味着公共话语的实现。可见,“求异存同”是比“求同存异”更基本、更优先的话语规则。
人人都有“异”的“说”,再通过广泛交流来“求同”,达成共识。有了“共识”,并不意味着永久,一成不变。每个人还得继续去“思”,去“说”,不断地“破”又不断地“立”(这或许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教育学的“话”是说不完的。话语的交流,首先是教育学科内部的对话交流,是先“异”后“同”,以实现话语的整合、新生成话语的普遍认可与深入。其次是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交流。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需要不同的学科间形成有效的对话、交流机制,从而实现全面地阐释、引导、建构整个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生成与发展。不同学科植根于同一现代性社会之中,以不同的方式共同面对,“异”中也有“同”,使不同学科之间的话际交流成为可能。而教育学话语跟其它学科之间的阻隔似乎太深,过于封闭,所以当前保持教育学话语的开放性、对话与交流的普遍性尤为重要。
教育学需要开阔的话语空间,不仅如此,还要保持其话语空间的宽容性。没有一种标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只有各自不同理解的“教育”。同样,没有一种标准、严格、规范、精确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只有包含着各自不同经验的“教育学话语”。承认对教育的理解的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在“求同”的过程中尊重这种差异性。理解并且宽容差异性的存在,不让群体性话语淹没了个体性言说的声音,让大家更多地话由“己”出,言从“衷”来,让众人“土生土长”的“言说”逐渐汇成中华教育学术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