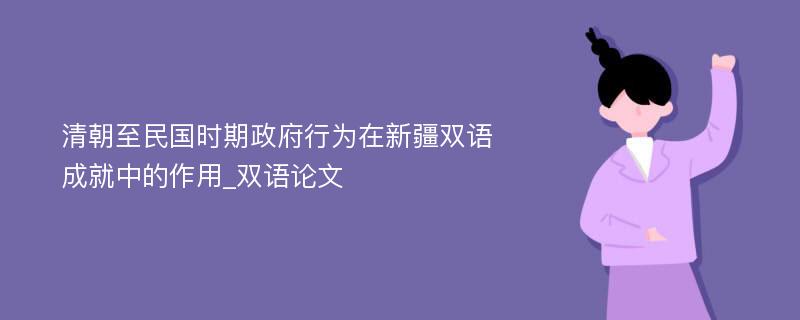
清至民国时期政府行为在成就新疆双语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双语论文,成就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沟通语言是我国历代政府的规定性工作之一,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参与政府、经济、文化活动的途径之一。本文选择清朝至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在新疆实施的语文政策和语文实践作为论述内容,以说明政府行为在成就新疆双语现象中的作用。
清朝政府的语文政策及其实践与双语现象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后,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军事措施有:军事机构地位的确立,指挥系统的构成,兵力的配备,对战略要冲的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交通联系;政治措施有:确立行政建制,制约地方封建势力;经济措施有:屯垦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商业政策;文化措施有:宗教政策,语文政策。[①]
清朝是以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为主建立的政权。明朝末年,汉语、汉文已成为满族统治阶层和商业领域通用的主要交际工具之一。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按他们的文化水准,加上人口相对较少,在文化上很难与汉民族匹敌,尤其在语言、文字方面对汉语汉文作根本性的变革,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在汉族地区,清朝政府认可了汉族语言、文字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清朝再度统一天山南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最终也确认了维吾尔等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征集粮赋、催办差役的行政活动到审讯判决等司法活动中,维吾尔语言等各民族语言都是当地的通用语言。
1815(嘉庆二十年)年喀什噶尔发生孜牙墩案件。从案发到结案,清朝官方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孜牙墩出身于维吾尔宗教世家,不懂汉语,而全部案情的审讯记录和说明却只有汉文文本。此项工作是由一些兼通维汉双语的翻译完成的。这是维吾尔语使用于司法的证据之一。与孜牙墩案件相牵连的图尔第·迈莫特毕是一位柯尔克孜族首领。无疑,图尔第·迈莫特毕案件的审讯记录和说明文字是由柯汉双语翻译完成的。这当然可以被看成是柯尔克孜语使用于司法的证据之一。
1826年(道光六年)7月至1828年(道光八年)6月发生的张格尔之乱,是当时新疆最大的政治事件。张格尔被活捉,对其审讯后在喀什噶尔、北京等地形成了大量的汉文审讯记录和各种文字取证材料。这个漫长的司法过程是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共同完成的。
维吾尔语言通用于官方活动的事实还反映在官职称谓上,仅清朝军机处制定的《补放伯克条例》所认同的就有十四种职官术语采用了维吾尔语,如: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商伯克、噶匝纳齐伯克、茂特色布伯克、纳克布伯克、哈孜伯克、密喇布伯克、什和勒伯克、巴克玛塔尔伯克、明伯克、阿尔巴布伯克、都官伯克、巴济格尔伯克等。同时,清朝政府在赐封维吾尔封建贵族中显赫人物以特殊荣誉时,并没有忘记使用满语以及满族已经习惯的汉语专门术语,如清朝政府封吐鲁番的额敏和卓为贝勒(满),赐郡王衔(汉);库车鄂对曾被封为辅国公(汉),稍后,又晋升为贝子(满)赐贝勒品级;封哈密的玉素甫为贝勒(满),赐郡王衔(汉);封阿克苏的霍集斯为贝勒(满),赐郡王品级(汉);授于拜城的噶岱默特以公(汉)的品级;封和田的和什克为辅国公(汉)。[②]
清朝政府对维吾尔语言、文字的认可还表现在将维吾尔语言、文字应用于这一时期新疆各地铸造的钱币上。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朝政府用军队进疆所携带的备用余铜,在叶尔羌开炉铸造了第一批新币,约五十余万枚。新币完全模仿清朝制钱式样,钱的正面铸有汉文“乾隆通宝”字样,以示铸造时间,背面铸有满文和维吾尔文“叶尔羌”字样以示铸造地点。新币在维吾尔语被称作“雅尔玛克”。除了在叶尔羌开炉铸造外,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阿克苏,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在乌什开炉铸造过。这些地方铸造的清朝法币,也无一例外地都缀有维吾尔文。
维吾尔语言文字还被收到《五体清文鉴》中,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清朝政府视维吾尔语言、文字为我国法定语言之一。[③]
清朝政府对维吾尔语言的重视还可以从其它方面略见一斑,清朝政府将维吾尔文使用于京城,至今仍散见于北京城里名为“下马石”的石碑上。清朝皇帝避暑山庄的正门匾额上,也都附有相应内容的维吾尔文。
不论是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审理,还是《五体清文鉴》的完成,都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清朝的新疆地方当局,因为拥有一批兼通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人才,才得以完成诸如张格尔案审理的工作。特别是由于完成了像《五体清文鉴》这样高难度的语文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从而显示出当时新疆地区双语人才的整体水平。
但是,就数量来讲,这一时期新疆地方双语人才是极为有限的,最早的一批高水平的新疆双语人才主要出自哈密、吐鲁番、库车、乌什、拜城、和田等地的膺获清朝爵位的维吾尔王公贵族家族。赴北京晋见清朝最高统治者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学习汉语的主要机遇和环境。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较早奉调迁居北京的霍集斯家族,是较早熟练掌握汉语的家族群体。
清朝对于双语人才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864年(同治三年)以后,清朝政府在反省它在新疆的种种失误时,从中央到主政新疆的封建大吏更加明确了对新疆语文的认识,认为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语言上的不沟通。
左宗棠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持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④]
继左宗棠之后主持新疆事务的刘锦棠说:“缠回(维)语言文字隔阂不通,民怒沸腾,而下情无由上达。”[⑤]
曾负责筹建新疆行省的陕、甘总督谭钟麟说:“官与民文字不同,言语不通,即传回民当堂面谕,而阿奇木等从中播弄,传语恐吓,故往时缠回视官如寇仇。”[⑥]
清朝中央政府赞同了他们的看法,把与当地维吾尔百姓沟通语言作为一项政策性的工作加以实施。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礼、户、吏、兵、刑等各工作部门,配备维吾尔族官员,并要求这些工作部门的汉(满)、维官员“互授文语,期于相观而善。”[⑦]
二、在各个部门配备一定数量的翻译人才。[⑧]
三、招示于公众的各种文告,一律使用汉、维两种文字。尤其是“征收所用券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维)字,令户民易晓。”[⑨]稍后,清朝又进一步规定,各种官方印信一体兼铸回文。[⑩]于是维吾尔语文具有了新的更加明确的法定地位。其基本特点是:极大地扩大了双语人才的使用范围。由于这项措施是以政治需求为基础的,所以它有着明显的实施力度,并且有明确的取向。这种取向表现为着力造就通晓汉语的普通百姓人家的子弟,其着眼点是在清朝行政机构的基层形成沟通语言的固定的通道,以保证清朝政令直达百姓,也保证社会民情上达各级官员。清朝将在维吾尔族儿童中强力推行汉语教育作为它实施上述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
1880年(光绪六年)5月25日,左宗棠向清朝中央政府报告新疆善后事宜的时候,将教育(义塾)列为善后工作的七大要点之一。(11)在报告中左宗棠把主张教育的理由归为:“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籍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12)说到实践过程的时候,他说:“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13)说到未来设想的时候,他说:“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讲求经义。”(14)说到社会效益的时候,他说:“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既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15)
稍后,刘锦棠向清朝中央报告他主持新疆事务以来的工作情况的时候,特意将义塾列为所承办的第三项工作。
1883年(光绪九年)8月,刘锦棠在他向清朝中央呈送的题为《关外各军行粮坐粮章程善后台局一切应发款目缮清之案折》的报告中,对新疆实施教育措施的情况作了论述,根据他的叙述。当时新疆已经有七十七处义学。(16)
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锦棠建议,将维吾尔族学童中能诵经书,讲解文艺者,取作佾生,(17)同年十月一九日,光绪皇帝批准了刘锦棠的这个建议,从而开辟了维吾尔族学童“学而优则仕”的途径。
尽管在维吾尔族儿童中强行推广汉语教学的措施一度遇到一些维吾尔族儿童家长的反对,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许多维吾尔族儿童接受了这个现实。清末民初成为维吾尔族社会名流的许多人,都造就于这些场所。甚至有些人阴差阳错,代替别人入读汉语而后来却身居高位。
这一时期新疆双语人才的培养有了规范的途径和方法。双语人才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的经济待遇普遍有提高,也有了明显的吸引力,于是双语人才的人数超过了有清一代的任何时期。
杨增新时期的语文政策及其实践与双语现象
悬挂在杨增新的办公地督署花园镇边楼上的一幅长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增新主政新疆的政治态度:“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这幅长联所阐发的基本政治目标是作“太古民”,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主要方法是“扭南回北准”。不论是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百姓,还是天山北部的准噶尔部众,他们同杨增新都有着明显的语言隔膜。因此,进一步拓宽维吾尔等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沟通,成为杨增新主政新疆的一种特殊需求。
杨增新对于维吾尔语言地位的认识起始于他协调哈密王室同托尔帕克起义关系的那个时期,当时,杨增新的工作是听取双方的申述,说服双方退让并接受对方的条件。交涉双方使用的都是维吾尔语。他们互相诘问,指责甚至讥讽,唯独处于调停地位的杨增新只能通过翻译去了解双方交涉的基本内容。这次经历,使杨增新对双语交流有了这样两条印象:一、翻译(当时官方的称谓是“通事”)在新疆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二、造就兼通双语的官员是处理好新疆政务的主要手段之一。
杨增新正是本着这种思想走上新疆政坛的。不久,杨增新便对双语交流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当省府上下对铁木尔领导的哈密农民起义一筹莫展的时候,杨增新选派通晓维吾尔语的张采庭团长率部进驻哈密。这一举措,反映了杨增新已将语言沟通列为政治手段之一。
稍后,由杨增新亲自主笔的《征收粮草规则十四章》的第三章,将沟通与维吾尔族语言列为章程之一。其具体内容为:“三、南路缠民不识汉字,……须由主计员会同地方官将粮草串票,用汉缠(维)合璧文字载明银量数目。”(18)
杨增新还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新疆特殊的语言环境,甚至一度成为他拒绝中央向新疆派遣军校毕业生的重要理由。(19)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增新最终将语言沟通的问题上升到了能否实现吏治整饬的高度。他认定那些掌握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吏能够更好地贯彻政府政令、体察民情、掌握民意、并最终密切百姓与政府的情感联系,因此,在杨增新实施的双语政策中。培养掌握民族语言的汉族官吏成为主要的措施。在他提交中央政府的题为《呈请将缠(维)文研究所毕业员以委任存记文》的报告中,郑重其事地说,“窃增新前以新省本系回疆,文字语言迥异汉俗,欲期吏治宏通,端赖通晓缠回语文(20)。
杨增新向中央政府提交的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要成立“缠(维)文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学制为两年,学员由军务厅和政务厅科员中选派,年龄上限为三十五岁,学员的学籍及学历由教育部和内政部核准立案,考试试卷和答卷由教育部查核,内政部注册。研究所经费由省府开支,学员毕业后,择优委以职务,研究所就设在杨增新办公署院内(21)。
这个举措实施以后,杨增新便有了一批双语的汉族干部。其中的一部分原来就通晓维语,投考研究所以后,提前准以毕业,委以新的职官。另一部分经过两年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维吾尔语言的必要知识,也相继委以新的职务。由于杨增新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列为走向仕途的一种方式,从而不仅对那些奋发上进的年青人是一种激励。而且也给那些期望继续升迁的在职官吏提供了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上自省府下至县区,配置了相当数量的兼通双语的汉族官员。他们借助语言的条件,为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强调汉族官员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的同时,杨增新继续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推行学习汉语。过去,由于语言隔阂以及强迫维吾尔儿童直接接收汉语授课,致使维吾尔学生学习汉语越来越带有强制性。杨增新本人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同时,认为此举已经是进退维谷,与其功亏一馈,不如逆流而上,继续推行学习汉语。(22)
从历史的角度权衡杨增新的语文政策,应该说其正面的效应是明显的。首先,杨增新延续了以沟通语言为主的政府行为;其次,特别强调了汉族官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意义。第三,用常规的,或超常规的办法在少数民族学童中间继续推行汉语教学,使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双语人才继续保持了相应的规模和速度。并且确实为新疆各少数民族造就了近代史上较早的一批知识分子。
盛世才时期的语文政策及其实践与双语现象
1928年7月7日,新疆发生了“七·七”事变,镇迪道尹樊耀南刺杀了杨增新,省政务厅长金树仁取代了杨增新的地位。相隔不到五年的1933年4月12日,新疆又一次发生了政变,金树仁的政权被推翻,盛世才攫取了新疆的最高权力。由于盛世才与杨增新、金树仁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所以,他的双语举措有着自身的特点。他更喜欢在官方场合里用广泛使用翻译的方式来表示他对各少数民族的重视,而求得各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的上层的好感。此外他还给政府各主管官员配备有各种语言的专业翻译人才,在各主管机关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
1934年4月12日,即“四·一二事变”一周年时候,盛世才发表了《告全疆民众书》,即“八大宣言”。
不久,盛世才又以《新的主要任务》为题,在保持“八大宣言”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排列了“九项任务”。不论是“八大宣言”,还是“九项任务”,都包括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并特别强调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的必要性。在“八大宣言”中,文化教育列为第六位。盛世才阐述其内容时说:“想要建设新新疆,则必须扩充教育规模,一方面应该用各族固有语言、文字开办各族学校和力谋增加教育经费,增加各级学校教量;一方面则造就师资队伍、编审一般教材、教科书和用各民族固有语言文字编成课本,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必明此办理,方易奏效。”(23)
在“九项任务”中,教育升为第二项任务,盛世才在阐述其内容时说:“想要迅速地提高这个落后的新疆的文化,在各民族学校中必须用各民族的固有文字语言来教授。各种出版物与各项印刷品必须用各族固有的文字来印刷。必得这样去做,才能很快的达到提高文化的目的,才能达到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目的”。(24)
盛世才在培养双语人才中的具体措施是:其一是增加学校的数量;其二是造就教师队伍;其三是编译一般教材;第四是用本民族固有语言文字授课。实施的结果表明,不论是增加学校的目标,还是造就教师队伍的目标,用本民族固有语言文字授课的目标,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25)
政治上善于投机的盛世才伪装革命时,他试图把大量的革命的、时髦的新词汇融进新疆地方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迫使从事语言沟通工作的专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各级民族学校也成为推行这些新词汇的主要场所。学生们通过教材的途径自然地接受了这些新的词汇,并且成为新的双语人才的预备力量。
事实上盛世才并不满足于这种渐进式的办法。在其后设立的各种军政警学校以及农林医等专科学校中,汉语被列为少数民族学员的必修课程,尤其是军政警学校各种口令均采用汉语,使这些未来的军政警官员从一开始便掌握了基本的汉语术语。
这时期的双语人才主要是在各种专门机构培养的。它们通常称作翻译班,附设于各军政警学校。
由于盛世才使用来自苏联的许多新的概念、词汇,因此,新疆的语言沟通中又增加了俄语同汉语,俄语同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沟通的内容。
1934年11月至1936年11月,新疆地方当局共向苏联派出公费留学生307名,其中维吾尔族学生140名,汉族学生130名,其余为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学生。
这批留苏学生除了负有学习各种专业技术的重任外,还负有掌握俄语的使命。事实上他们学成归来之后,在沟通俄语同汉语、俄语同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双语人才的增多,拓宽了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同其它民族语言尤其是同汉语还有俄语之间沟通的渠道,推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应提及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借助语言的沟通,维吾尔族的一大批文学艺术家热情地投入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造就了维吾尔现代文学史上最具辉煌的抗战文学,出现了大量的维吾尔话剧、歌剧、长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抗战为主题的“五大长诗”。
结语
应该说,双语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受着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新疆范围内双语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与新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由于政府行为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向心力、凝聚力,所以它常常为双语现象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由政府行为带来的双语现象有极大的普及性,完善了汉维等语言文字的交流职能,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促进了新疆的社会发展。
注释:
①《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6、18、20、32;《回疆通志》卷7。
②《西域图志》卷31。
③《西域图志》卷7。
④《左文襄公奏稿》卷53,第34页。
⑤《光绪朝东华录》卷74。
⑥《平定陕、甘、新方略》卷315。
⑦ ⑧《新疆大记补编》卷9,第8页。
⑨《左文襄公奏稿》卷53,第34页。
⑩《刘襄勤公奏稿》卷5,第11页。
(11) (12) (13) (14)《左文襄公奏稿》卷56,第20页,21页。
(15)《左文襄公奏稿》卷56,第22页,23页。
(16) (17)《刘襄勤公奏稿》卷5,第64页下,第65页上。
(18) (19)《补过斋文牍》壬集(上),甲集(下),第47页上。
(20) (21)《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第19页,20页。
(22)《补过斋文牍》,甲集(上),第51页。
(23) (24)盛世才:《政府目前主要任务》,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迪化版,第2—4页。
(2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23页。
标签:双语论文; 盛世才论文; 五体清文鉴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维族论文; 杨增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