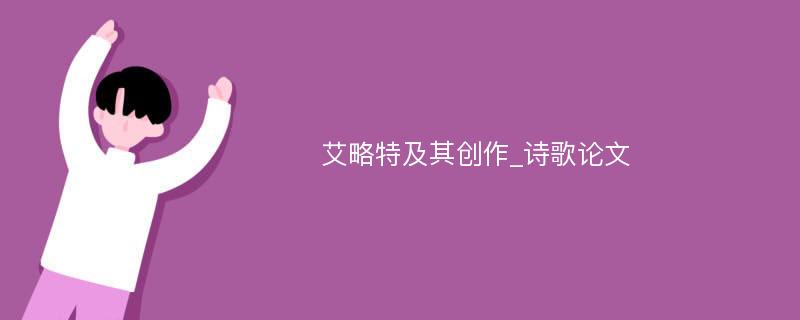
艾略特与他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略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荒原》的作者,艾略特在我国已经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作家了。我国学者陈嘉的《英国文学史》和王佐良、周珏良的《英国文学史·二十世纪卷》都对此诗人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另外在国内出版的各种英国现代诗歌选集都含有关艾略特的简介和说明。袁可嘉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对艾略特作品在中国的引进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裘小龙的《四个四重奏》前言对艾略特生平和作品的介绍较为详尽。本文不再仅仅介绍艾略特的生平,感兴趣的读者更可以参考西人所作的艾略特传记,我在这里要特别推荐彼得·阿克洛依德的《T.S.艾略特》和林德尔·戈登的《艾略特的早年生涯》和《艾略特的新生》。本文将把着重点放在艾略特生活中的重要片段和与他诗歌有关的细节上。
一
艾略特于1888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他的家庭算得上是名人世家,其十一世纪祖先威廉是曾经参加征服英国的诺曼底贵族。其十七世纪祖先安德鲁是早期移居美国的英国人,居住在当时为十三殖民地的马萨诸塞。祖父威廉是北美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神父,为传播福音才来到当时为文明边缘的圣路易斯,在那里他倡导创办了史密斯学院和华盛顿大学。父亲亨利弃教从商,在圣路易斯建立了显赫的砖瓦制造公司。母亲也出自名门望族,笃爱文学,创作有诗歌和传记,对幼年的艾略特影响颇深①。
少年艾略特进入了与他家有密切联系的史密斯学院和密尔顿学院学习。他的第一首诗《抒情诗》就创作于史密斯学院。190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又创作了几首以浪漫主义为模式的诗歌。当时的哈佛尤以研究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东方哲学和印度神学而著称。反浪漫主义的先锋欧文·贝比特(Irving Babbitt)也在这里任教。这种情况对艾略特的思想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他影响更大的是1908年他在书摊上购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于勒·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诗歌全集上下两册,他立即被其语言风格所吸引。拉福格很快就征服了他的心灵,而他也从拉福格诗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从此他的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的《歌》和《早晨之前》逐渐被《风夜狂想曲》和《序曲》等所代替。
在大学期间,艾略特是校报《哈佛倡导者》的编辑,他青年时代的诗歌和评论多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他还参加过亲朋好友组织的业余剧团的演出,在演出中他认识了对他今后生活影响很深的爱米丽·赫尔(Emily Hale)。他还利用假期常去波士顿附近航海,《荒原》和《四个四重奏》里的大海都来自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在波士顿,他与朋友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常去光顾贵妇人阿得雷恩·莫发特(Adeleine Moffat)的客厅,后来这段经历启发了他的《一位女士的肖像》②。
1910年大学本科毕业后,艾略特来到巴黎大学进修一年,亲临他崇拜的诗人拉福格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并聆听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讲座。1911年他回到哈佛研究生院攻读学位,研究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F.H.布莱德利(F.H.Bradley)。由于课题的需要,他又于1914年获奖学金去布莱德利的母校英国牛津作研究。在牛津、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生活,写下了《海伦姑妈》和《南茜表妹》等诗歌。他又见到了曾在哈佛讲学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后来他还完成了一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F.H.布莱德利哲学中的认识和经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阻止了他回到美国去接受他的博士学位。
从到达英国起,艾略特就一直企图发表他的诗歌,但他在伦敦四处碰壁,当时的学术界名人哈洛德·门罗(Harold Monro)称他的诗歌为“绝对不正常”③。但幸运的是,不久他就在伦敦见到当时为美国《微型评论》海外编辑的埃兹拉·庞德。在他的极力推荐下,美国芝加哥的《诗刊》杂志才同意接受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从此艾略特开始了与庞德的密切合作,并在庞德的帮助下逐渐在伦敦文学界崭露头角。
1915年,艾略特结束了在牛津的研究工作,到伦敦的一所中学以教书为生。同年,他结识了英国女郎维维安·海伍德(Vivien Haigh-Wood)并与她结为伉俪。婚后他继续以教书为生,直到1917年他才进入洛埃德银行(Lloyds Bank)当职员。《荒原》中的上班族和职员的描写都与艾略特的银行生涯有关。然而,艾略特的婚姻生活经过一段平静的航行很快搁浅,等待他的是无尽的悲伤。维维安身体虚衰、神经脆弱、疑神疑鬼。艾略特则需要一定的独立性,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人生。总之,他需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两人的道路就越走越远。《荒原》中充满了扭曲的两性关系绝不是偶然的。
1917年艾略特成为伦敦《唯我主义者》杂志的助理编辑。庞德认为英国的“自由诗”已经走过了头,应该用严格的韵律来予以纠正。他建议艾略特阅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特俄菲勒·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的“四行体”诗歌④。其结果是艾略特写了一组包括《斯温尼在夜莺中间》和《河马》在内的“四行体”诗歌。它们工整押韵,但又充满了戈蒂埃式的讽刺。
1920年,艾略特完成了《小老头》。在庞德的提议下,艾略特在巴黎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后者给他的印象是才气横溢,但过于自信。1921年《尤利西斯》陆续在《唯我主义者》杂志连载。作为此杂志的助理编辑,艾略特先睹为快。他写信告诉乔伊斯说,我对你的作品“没有别的,只有羡慕”⑤。对于正在写作《荒原》的艾略特来说,乔依斯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同年,艾略特由于工作繁重,创作不顺,精神状况一落千丈,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虽然他已发表了不少诗歌,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文论集《圣林》,但他仍然没有一篇有足够分量使他立足文坛的大作。同时,他感到自己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为了恢复精神状况,他决定去瑞士看精神病医生。临行前,他没有忘记带上他正在创作的一首长诗。在瑞士洛桑的雷蒙湖畔,他完成了长篇巨作《荒原》。
在回国途中,艾略特将手稿交给了已经移居巴黎的庞德,请他予以斧正。庞德一挥大笔砍掉了原诗的二分之一,只剩下四百三十三行。庞德建议不用《小老头》作序诗,去掉来自康拉德《黑暗的心脏》的引言⑥。虽然如此,庞德仍然认为这是艾略特到此为止的最重要作品。1928年《荒原》发表时,艾略特将此诗献给了庞德,并称之为“更优秀的匠人”。
在伦敦,艾略特结识了贵族夫人奥托琳·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她是文学艺术爱好者,也是作家的赞助人。经常光顾她的嘎星屯别墅的有阿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李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tchey)、D.H.劳伦斯(D.H.Lawrence)等作家和艺术家。1922年,由报业大亨太太罗特米尔夫人(Lady Rothetmere)赞助,艾略特创办了他自己主编的《标准》杂志,《荒原》在英国就首先发表于这个杂志上。
1925年,《空心人》发表。这首诗在众多方面沿袭了《荒原》的思想模式,它对现代人的精神贫乏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也就是在这一年,艾略特离开了洛埃德银行,加入了费伯出版社。他的加入使这个出版社逐渐声名大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艾略特编辑出版了英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奥登(Auden)、斯宾德(Spender)、麦克尼斯(MacNeice)、巴克(Barker)、休斯(Hughes)等人的作品。正如庞德当年扶植艾略特一样,一代新诗人在艾略特的扶植下成长起来。
二十年代后期,艾略特的家庭不幸使他逐渐抛弃了在哈佛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并向基督教靠拢。他此时所交的朋友包括牛津的牧师威廉·福斯·斯泰德(William Force Stead)和基督教哲学家P.E.莫尔(P.E.More)。这些人的影响对他最终成为基督徒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斯泰德为艾略特施洗礼使他正式加入英国国教。第二年,他在文集《给朗斯洛·安德鲁斯》中自称是“文学中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主义者,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
与此同时,艾略特写下了《三贤哲的旅程》等一系列宗教题材的诗歌。其中以《圣灰星期三》最为成功,它体现了作者成为基督徒后突出的思想想法。1932年,艾略特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诺敦”客座教授的职位到美国讲学。他的讲稿最终被出版为《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他在美国进行了巡回演讲,并与他青年时代的女友爱米丽重缝,从此过去的友谊又复活了。
艾略特与爱米丽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艾略特回到英国之后爱米丽每年都去英国度假。名为看望亲戚柏金斯夫妇(the Perkins),实为创造机会与艾略特见面,在艾略特的书信中,只有给爱米丽的仍未公开,读者要等到下一世纪才能查阅。爱米丽还拥有几本由艾略特亲笔签名的第一版诗集。两人虽然感情很深,但最终未成眷属⑦。他俩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恋爱”,可与但丁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的关系相比拟。这特殊的关系为艾略特谱写了一曲新的《新生》。《空心人》中的“那双眼睛”和《圣灰星期三》里的那位“沉默的女士”似乎都有爱米丽的影子。
艾略特从美国归来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而是住进了教堂。他从此单方面与维维安分居,直到1947年精神失常的维维安去世。在以后的几年中,维维安疯狂地寻找艾略特,调查他的行踪,甚至在报上登广告要他回家,而艾略特始终没有回去。他后期戏剧里的人物在“报仇神”的追逐下四处躲避的情节是否与这事有关就很难断定了。
此时,艾略特与教会的联系逐渐增多,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他结交了好几位大主教,参加了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举行的“兰伯思会议”(Lambeth Conference)。在费伯出版社,他被称为“罗素广场的教皇”(罗素广场是费伯出版社所在地)。他还为教会写作,《岩石》就是为教会节日所写的庆典剧,《大教堂惨案》写的是圣人托玛斯·贝克特的事迹,1935年发表的《烧毁的诺敦》也与宗教有关。
“诺敦”是一座乡间庄园,位于英国中西部的格洛斯特郡,艾略特曾在1934年与女友爱米丽到此游览。《烧毁的诺敦》以无限优美的语言描写了“未走的路”、“孩子的笑声”和“永恒的可能性”。诗人把自己走过的路和“未走的路”并列起来,看作同样存在的事物。如果他与爱米丽关系已象眼前这座庄园不可恢复,那么,那些未出生的“孩子的笑声”也就成了一种“永恒的可能性”。《烧毁的诺敦》还有一个精彩的片段描写伦敦地铁,把地铁的行驶比喻为时间的流逝。三十年代的艾略特每天乘地铁去出版社上班,在他乘座的地铁线路上仍能找到那段描写的细节⑧。
在费伯出版社,艾略特有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包括出版社的杰弗里·费伯(Geoffrey Faber)和弗兰克·莫理(Frank Morley),《新英语周刊》编辑菲力普·梅瑞(Philip Mairet),和他的同房好友约翰·赫伍德(John Haywood)。他们在一起聚会、开玩笑、阅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柯南·道尔的一些词语后来进入了艾略特的《东科克》。1940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国开始了对伦敦的“闪电战”和空袭。艾略特当时兼任教堂的看管员,夜间值班时目睹了轰炸所造成的火灾和对建筑物的破坏。在《小吉丁》里有一段非常出色的描写给我们勾画出轰炸后的死寂和幽灵出没的景象。
三、四十年代的艾略特过着相对稳定的文学生涯,除二战期间他为躲避轰炸曾寄居在作家霍普·默利思(Hope Mirlees)乡间住宅外,他只偶尔外出。1936年他访问了具有宗教意义的小吉丁,1937年他回到了祖宗居住的村庄东科克。他还常去柏金斯夫妇家看望爱米丽,有时也去费伯或莫理家度周末。他非常喜欢他们的孩子,1939年出版的《老负鼠的实用猫手册》就是为这些孩子写作的。
从三十年代开始,艾略特的文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论文中大概有一半是关于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它们发表于《基督教通讯》、《神学》等杂志上。1939年他出版了小册子《基督教社会的构想》,1948年他又出版了《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这时,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也逐步提高,他常常应邀在BBC作广播演说,宣讲文学。1943年,他在女王出席的一个会议上绘声绘色的朗读了《荒原》的第五部分⑨。
1941年艾略特回忆起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写下了《干燥的塞尔维吉斯》,1942年,他又完成了《小吉丁》,这样《四个四重奏》就大功告成。这个系列描写了艾略特亲身体验的“神秘经历”和对这个经历的哲学思考。当然,这样的长诗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但艾略特承认他是受到贝多芬的室内乐《a小调四重奏》的启发而创作的,诗里使用了音乐里的变奏等手法⑩。
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后期,艾略特的创作生涯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1939年发表的《家庭团聚》使他的戏剧创作日臻完善。这出戏写一个贵族青年受良心的折磨,逐渐发现了这个折磨的根源,最后通过接受折磨以赎罪,开始了他的新生。艾略特所有的戏剧都与独立的个人的灵魂自救有关。
1938年艾略特结识了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G.M.Trevelyan)的妹妹玛丽·特里维廉(Mary Trevelyan)。在同她接触的十年中,艾略特感到轻松自如,无拘无束,毫不压抑。她逐渐成为艾略特能够信赖和倾诉苦恼的人。1949年,玛丽以书信形式向艾略特表达了爱慕之心,艾略特婉言拒绝了她。他解释道,经过一场失败的婚姻他自己已不能对任何人回报如此的感情,并暗示他对一位故友的感情使他无法接受新的恋爱关系。他指的是爱米丽(11)。
在四十年代,艾略特进入了他的“名人阶段”。除了在出版社工作外,他还常常被邀请去外地演讲和朗读诗作,几乎他后期的所有论文都是讲稿。1940年他应邀作了第一届叶芝纪念演讲,1948年他又继叶芝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人们联想到叶芝去世之后,艾略特是当之无愧的诗圣。接着等待他的是一系列至高无尚的荣誉。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获得了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章”,德国的“汉萨-歌德奖”,和意大利的“但丁金奖”。最后这一项是奖励艾略特在但丁研究和对但丁的继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早在1933年艾略特就说过,诗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戏剧就是诗人介入社会的最佳方法(12)。1942年《四个四重奏》发表以后,艾略特实现了这个诺言。他的创作完全转向了戏剧,只写了几首零碎的抒情诗。1949年,《鸡尾酒会》在爱丁堡文化节的一片赞扬声中落下帏幕,剧中描写的都是艾略特所熟悉的沙龙生活和上层社会中有时间进行自我灵魂审查的富贵人家。1953年《私人秘书》又在爱丁堡文化节上演,虽然这次赞扬呼声仍然很高,但对艾略特本人的兴趣可能超出了对他的戏剧的兴趣。剧中的某些巧合(如母子失散多年后相认)使人想起了狄更斯小说中的戏剧性情节,但评论界对艾略特将宗教题材糅合到这样一个故事中的贴切性表示怀疑。
1957年,艾略特向年轻的秘书瓦勒利·弗莱彻(Vaierie Fletcher)求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这次婚姻中,艾略特找到了他的幸福,这是1927年他入教后一直遵循的禁欲主义的第一次松动。瓦勒利十四岁就开始崇拜艾略特的诗歌,后来她竭力与艾略特接近,直至最后成为他的秘书。婚后,艾略特写了一首赞美爱妻的诗歌,又将他最后一部诗剧《老政治家》献给了瓦勒利。这出戏写一位退休的政治家因悔恨青年时代的过错,而受着良心的谴责。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他的女儿,他的爱把他从折磨中解救出来,在平静中死去。虽然剧中有很多宗教成分,但这位女儿的形象很可能与瓦勒利有关。
1965年1月4日,在重病三个月后,艾略特在伦敦的家中去世。尊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祖宗的故乡东科克的圣麦克尔教堂。他的幕碑上写着“记住T.S.艾略特,诗人”。在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的“诗人角”有一块艾略特的纪念墓碑,与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伟大诗人安放在一起,这是对艾略特和他的诗歌的最后肯定。
二
艾略特对英国诗歌的贡献是卓越的,他通过自己的诗和文学批评改变了一代人的文学趣味,创立了一整套新的鉴赏标准。他的诗歌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英国诗歌的发展史,迫使他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十六世纪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和十七世纪的玄学诗派。同时他的作品更加深了人们对法国十九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认识,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借鉴别国诗歌的巨大可能性和对本国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艾略特把继承传统和个人创新相结合,振兴了二十世纪的英国诗歌,使当时萎糜不振的英国诗坛重新充满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他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等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诗歌杰作,他的《传统与个人天赋》和《玄学派诗人》等已成为二十世纪的文论经典。
西方关于艾略特的评论和专著非常繁多,几乎可以装满一个小型图书室。最早的有一定分量的艾略特评论来自I.A.理查兹(I.A.Richards)《文学批评的原则》,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阿克梭的城堡》,F.R.利维斯(F.R.Leavis)《英国文学的新方向》和克里恩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现代诗歌和传统》。这些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著作显然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艾略特的认识。可以说是这些人开拓了文学界对艾略特的兴趣和理解。
艾略特的诗歌难度比较大,并常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在时空上前后跳跃,结构松散,缺少连贯性。因此,前期的艾略特评论多集中在诠释上:对疑难点的解释和对内部结构的探索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批评方法上受艾略特本人观点的影响。F.O.麦息生(F.O.Matthiessen)《T.S.艾略特的成就》不但为我们阐明了艾略特诗歌的内部统一性和对传统的发展,而且遵循了艾略特一惯主张的原则:批评家“必须把〔诗歌〕首先看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13)。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T.S.艾略特的诗艺》试图用艾略特所接受的基督教模式来解释他的诗歌的整体性。她把《荒原》以前的诗歌都看成《四个四重奏》的准备或前奏,描述了艾略特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休·肯纳(Hugh Kenner)《隐形的诗人》将作者的心灵看作其诗歌的构架,把《荒原》等结构零碎的诗歌统一于作者的意识和人格之中。肯纳引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对诗歌和戏剧进行了“细读”(close reading),理解深刻而透彻。格罗弗·史密斯(Grover Smith)《T.S.艾略特的诗歌和戏剧》也极力探索艾略特诗歌的原引资料,试图通过对引文的研究来解释艾略特诗歌的意义。
艾略特对这个时期的影响还在于他几乎使评论界完全接受了他对浪漫主义的批评。以上这些评论家几乎都把艾略特诗歌看作对浪漫主义的反叛和对十七世纪“玄学诗歌”的继承。利维斯认为玄学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一些诗歌特质在“艾略特的诗中重新出现”。布鲁克斯认为,“现代主义诗人与十七世纪机智诗人的重要联系就在于此——他们在运用比喻上的共识”。麦息生也认为,“多恩的思想的支离破碎在我们的时代激起了共鸣”(14)。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逐渐抛开了艾略特文学批评的影响,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在《浪漫意象》中认为艾略特的叛逆是一种需要,并用大量事实说明艾略特、庞德和叶芝的象征主义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接着,罗伯特·朗鲍姆(Robert Langbaum)的《经验的诗歌》和C.K.斯泰德(C.K.Stead)的《新诗学》都把现代诗歌与浪漫诗歌相比较,并得出现代诗歌为浪漫主义第二阶段的结论。
随着人们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评论界开始了对艾略特的重新估价。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在《表达的力量》中认为英国诗歌的传统在于它的达意性和明确性,他对艾略特等人的创作手法和暗示性写作表示深深的怀疑。格雷厄姆·赫夫(Graham Hough)在《意象与经验》中对艾略特和庞德诗歌的不连惯性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偏离英诗发展的主干线。对他来说,现代派只不过是英诗的一支小小潜流而已。然而,对艾略特的最大冲击还来自美国。早在三十年代,爱佛·温特斯(Yvor Winters)就说《荒原》是用混乱的形式来表达混乱的心理,它无法与《恶之花》等一流诗作相提并论。在五十年代,W.C.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又称《荒原》为一大“灾难”,而在七十年代,哈洛德·布罗姆(Harold Bloom)则称艾略特的诗歌缺乏创造力,充满陈词滥调和宗教说教(15)。这位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在他所定义的“更强大的诗人”的行列里竟把艾略特排斥在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指责艾略特剽窃的,怀疑他有法西斯倾向的,讨厌他的宗教思想的,都大有人在。但是在批评声中艾略特并没有消声匿迹。冷静的批评家们在接受艾略特的种种偏激之后,更加意识到他的诗歌的重要性和独创性,他们从艾略特诗歌中找到了无穷无尽的意义。有关艾略特的书籍继续在出版,有关艾略特的文章继续在发表。J.D.马戈利斯(J.D.Margolis)《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和皮尔斯·格雷(Pierce Gray)《T.S.艾略特的思想和诗歌的发展》分别用艾略特所编辑的《标准》杂志里的材料和艾略特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对他的思想发展作了详尽的介绍。A.D.穆迪(A.D.Moody)《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诗人》和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T.S.艾略特:性格和风格的研究》运用了七、八十年代的最新发现对其诗歌作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莫德·爱尔曼(Maud Ellman)《T.S.艾略特和非个人化诗学》和格里高利·杰(Gregory Jay)《T.S.艾略特和文学史诗学》把艾略特的文艺理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艾略特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和解构学的有机联系。
后期的艾略特评论有明显的两个变化。一是我们已经提到的评论界逐渐对艾略特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发生兴趣。二是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艾略特诗歌背后的作者。七、八十年代的评论家抛开了艾略特“诗歌非个人化”的理论的束缚,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他创作的根源。瓦勒理·艾略特(Vaerie Eliot)编辑的《荒原》原稿和海伦·加德纳编辑的《四个四重奏》的原稿激发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唐纳德·盖洛普(Donald Gallup)的《T.S.艾略特:图书目录》更提供了评论界所需要的有关信息。随之而出现的是结合艾略特生平而写作的专著,最值得推荐的专著有斯蒂芬·斯宾德(Stephen Spender)的《艾略特》、詹姆斯·E·米勒(James E.Miller)的《T.S.艾略特的私人荒原》和凯尔文·比迪恩特(Calvin Bedient)的《他用不同声音装警察》。
以上这两点——艾略特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和艾略特诗歌与他个人经历的联系——是七十年代以来艾略特批评的发展趋势。然而,有关艾略特的研究是多种多样的,纷繁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纳为几大类。比如南茜·哈格洛夫(Nancy Hargrove)在《艾略特诗中作为象征的风景》中就把艾略特诗歌同他的景物描写结合起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艾略特在景物描写上的用意;埃里克·西格(Eric Sigg)的《美国的艾略特》把诗人放在美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来研究,并把他看作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以下这些题目几乎暗示了它们的内容,斯坦利·苏丹(Stanley Sultan)《艾略特、乔伊斯和同行》,路易斯·门南得(Louis Menand)《发现现代主义:T.S.艾略特和他的背景》和桑福德·史瓦兹(Sanford Schwartz)《现代主义的起源:庞德、艾略特和二十世纪初的思想》都试图把艾略特放在本世纪初的历史背景里来研究他的成就;罗伯特·克洛福德(Robert Crawford)的《T.S.艾略特诗中的野人和城市》、保罗·莫里(Paul Murry)的《T.S.艾略特与神秘主义》和克利欧·科恩斯(Cleo Kearns)《T.S.艾略特与印度传统》都试图从特定的角度——艾略特对人类学、对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对印度教的兴趣——来解释他的诗歌。
有关艾略特的书籍和文章还很多,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一书单可以继续写下去,令人目不暇接。但对于想了解艾略特的人,以下这几本书可能会很有用。B.C.索萨姆(B.C.Southam)的《T.S.艾略特诗歌选集学生指南》对艾略特前期的诗歌作了逐行的解释;C.B.考克斯(C.B.Cox)和阿诺德·星奇利夫(Arnold Hinchliff)编辑的《荒原手册》和伯纳德·伯贡兹编辑的《四个四重奏手册》汇集了有关这两首诗的资料和论文;阿伦·泰特(Allen Tate)编辑的《T.S.艾略特:生平和著作》和伦纳德·昂格(Leonard Unger)编辑的《T.S.艾略特:论文诗集》分别收集了美国两家重要杂志《南方评论》和《斯宛尼评论》中的论文,其中有艾略特的朋友和熟人写的文章;另外,在《荒原》问世五十周年之际,大西洋两岸都出了纪念文集,它们是A.W.李茨(A.W.Litz)编辑的《艾略特在他的时代》和A.D.穆迪编辑的《荒原的不同声音》。最后,格雷厄姆·马丁(Graham Martin)编辑的《T.S.艾略特透视》汇集了八十年代的最新论文。
三
在我国,艾略特研究可以说从1980年才真正起步,主要成绩表现在翻译方面。最早的译文可能是查良铮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赵萝蕤的《荒原》。1985年,赵毅衡在《美国现代诗歌》中重译了《荒原》,又增译了《小老头》和《空心人》等。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裘小龙翻译的艾略特诗歌全集,取名为《四个四重奏》,这个集子是到目前为止最全的艾略特诗集,它还收进了《荒原》原稿里的一些弃置未用的诗歌。尽管1988年艾略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紫芹编选的《T.S.艾略特诗选》,但它只收集了艾略特最主要的三首长诗。其中《四个四重奏》选用了张子清的译文。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收集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英美批评家写的评论。
对艾略特的兴趣在我国还是比较浓厚的,几乎所有英国文学的研究者都对艾略特有一定的了解。从八十年以来,已有数篇论文发表。扬周翰在《世界文学》发表了“艾略特与文艺批评”,介绍诗人在文学批评上的主张和他在西方批评界的影响。1983年《外国文学研究》刊登了毛敏诸的“《荒原》浅析”,1984年又刊登了郑敏的“从《荒原》看艾略特的诗艺”。这两篇文章对《荒原》作了基本的分析,有助于读者对此诗的理解和对艾略特创作方法的认识。1985年袁可嘉的“象征派诗歌”(后来被收集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也多次提到艾略特,并把他的创作看作象征主义的一部分。
1988年,张子清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了题为“把握时代精神,开辟现代派诗歌道路”的文章纪念艾略特诞辰一百周年,文章介绍了艾略特的生平、创作和历史意义。1989年,裘小龙的《现代主义的缪斯》有两篇有关艾略特的文章,其中一篇从意识流的角度分析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92年《外国文学评论》刊登了陆建德的“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艾略特、多恩和《荒原》”,作者从玄学诗派的角度,对《荒原》加以论证,使我们对这首名诗有了新的认识。同一期刊还刊登了张炽恒的“智慧的映照——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文章对这篇杰作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介绍,有助于进一步研究。1994年《外国文学研究》刊登了刘立辉的文章,题为“生命哲学的诗化耗损——有关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新探述评”。作者以《四个四重奏手册》一书为基础,介绍了近三十多年来西方对这篇杰作的评论。
总的说来,我国对艾略特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成绩是可喜的。但历年来评论的内容集中在艾略特为数不多的几篇名诗上,缺乏对艾略特诗歌发展的认识,并且常常依赖于翻译西方评论家的文章。所以,这个领域还有很多空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们把以下这个专栏献给大家,望能重新激起研究者对艾略特的兴趣,望借此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赫伯特·霍华斯(Herbert Howarth)《T.S.艾略特背后的一些人物札记》,波士顿,1964,第一章。
②参见康拉德·艾肯《厄星特》,波士顿,1951,第173页。
③参见康拉德·艾肯《厄星特》,波士顿,1951,第173页。也见彼得·阿克洛依德《T.S.艾略特》,伦敦,1985,第55页。
④埃兹拉·庞德:《斯文文集》,伦敦,1937,第14页。
⑤艾略特致詹姆斯·乔伊斯书信,1921年5月12日。
⑥埃兹拉·庞德:致艾略特书信,1922年1月,见D.D.佩奇编《埃兹拉·庞德书信选》,伦敦,1951。
⑦参见林德尔·戈登:《艾略特的新生》,牛津,1988。作者对艾略特后期生活,特别是他与四位女性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描述。
⑧参见海伦·加德纳《四个四重奏的写作》,伦敦,1978,第86页和休·肯纳《隐形的诗人》,伦敦,1959,第255-257页。
⑨彼得·阿克洛依德:《T.S.艾略特》,伦敦,1985,第267页。
⑩彼得·阿克洛依德:《T.S.艾略特》,伦敦,1985,第189页。
(11)彼得·阿克洛依德:《T.S.艾略特》,伦敦,1985,第306页。
(12)艾略特:《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伦敦,1933,第154页。
(13)艾略特:《圣林》,伦敦,1928,第×页。
(14)利维斯:《英国诗歌的新方向》,伦敦,1950,第81页;布鲁克斯:《现代诗歌和传统》,纽约,1939,第11页;麦息生:《艾略特的成就》,纽约,1958,第11-12页。
(15)参见温特斯《为理性辩护》,丹佛,1947;威廉斯《自传》,伦敦,1951;布罗姆《塔上的钟敲人》,芝加哥,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