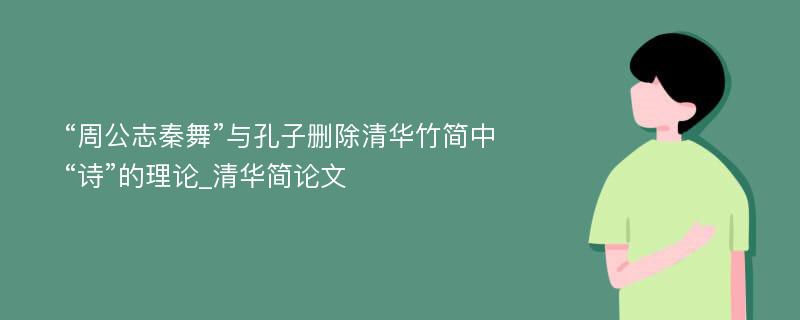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清华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孔子删《诗》”之说,汉至隋代未有异议。初唐孔颖达开始怀疑,之后踵其说者渐多,怀疑者提及的最主要论据有二:一是从古文献逸诗存留的数字看,认为孔子不可能删掉两千七百多首诗。如孔颖达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①二是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诗乐编排顺序看,认为已与今本《诗经》大体一致,证明当时《诗经》已基本编定,其时孔子年方八岁,不可能删《诗》。如宋人郑樵云:“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②长期以来这两条被视为否定孔子“删《诗》”的最有力证据,以至为一些文学史所采用,成为千年公案。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问世,厘清了《诗经》流传和编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为准确理解司马迁之说颇有启发意义。 一、现行本《诗经》确实对古诗删削过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周公和成王所作的乐诗,内容大体是周公对“多士”的劝诫和成王对自身的儆戒。李学勤先生说:“《周公之琴舞》是由十篇诗组成的乐诗,性质同于传世《诗经》的《周颂》。”③此说非常准确,当毫无争议。这不止是因其“琴舞”的形式,还因为简本成王“元内(纳)启曰”下面一段与传世本《诗经·周颂·敬之》极为接近,该段是: 敬之敬之!天隹(惟)(显)帀,文非易帀。母(毋)曰高高才(在)上,劯(陟)降亓(其)事,卑蓝(监)才(在)兹!乱曰:讫(遹)我夙夜不兔(逸),敬(儆)之!日就月将,教亓(其)光明。弼寺(持)亓(其)又(有)肩,视(示)告余(显)惪(德)之行。④ 大意是:敬慎啊,敬慎!上天是昭著明察的啊,美德是不易获得的啊!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掌管人间赏罚升降,监察着我们就在身旁。乱曰:我日日夜夜不敢懈怠,敬慎啊!日有所得月有所成,就会渐渐达到光明。请辅弼我担此重任,示我以光明的德行。 传世本《诗经·周颂·敬之》如下: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⑤ 现存本《诗经》大意是:敬慎啊,敬慎!上天是昭著明察的啊,承受天命实在不容易啊!不要说老天高高在上,它掌管着士大夫的黜罚升降⑥,每天监察着下土在这个地方。想我这个小孩子,不够聪听敬慎啊(或“岂敢不聪听而敬戒呢”),我期待着日有所得月有所成,奋发学习,坚持不懈以达光明。请辅弼我担此重任,示我以显明的德行。 上面的引文中,加点部分是文字上有出入的。不难看出,二者很多地方句子相同,诗意也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有一个问题,现行本《诗经·周颂·敬之》全诗仅此一章,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明示成王所作共九章,这九章很明显是一个整体,文气连贯,一气呵成,绝对不是乱简的结果。即在传世本《诗经·周颂·敬之》中,《周公之琴舞》的后八章都没有出现(这还不包括最前边周公所作的半章)。所以毫无疑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现行本《诗经·周颂·敬之》是繁本和删节本的关系。这一现象表明,传世本《诗经》确实对原始诗作进行过删节,司马迁说的孔子删诗并非无据之言。 二、周代一直有与传世本《诗经》不同的“诸侯本”诗篇存在 研究表明,这批包括《周公之琴舞》在内的“清华简”是大约2300—2400年之前,即战国中晚期楚国的东西⑦。但是简本身呈现的年代不等于简上书写的文献本身的时代。就《周公之琴舞》来说,它叙述的是西周初期周公、成王的事情,李守奎先生通过对其语言及用韵风格等考察后说:“《琴舞》的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懂,用韵很不规则,其词汇不仅与周初部分的《诗》、《书》,西周金文密切相合,而且沿袭商代的一些词语,有些词语后代消失了。第四首诗中的‘昼之才视日,夜之才视辰’直承商书旧语。清华简《说命》下记载商王之命:‘说,昼女视日,夜女视辰,寺(是)罔非乃载。’诗中的‘才’当与《说命》的‘载’用法一致,《周颂》的语言与《商书》之间的传承关系非常明显。”⑧李守奎先生的意思是,《周公之琴舞》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还保存着西周初年的语言风格,笔者认为其结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当是在早于战国中后期的某个时候(至少应在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之前,详见后文论述),以大体保留该舞曲在西周原始面貌的形态传入了楚国,之后被楚国史官或某一权势人物收藏,最后随收藏者下葬,即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较原始的西周之“诗”单篇流传下来的一个典型。由此可见,在孔子时代,甚至西周至战国的漫长历史时期,某些诸侯国一直有与传世本《诗经》不甚一致的“诗”的藏本或藏篇存在,笔者姑且名之为“诸侯本”。这些诸侯本的“诗”的藏本或藏篇或成集或不成集,与现今看到的《诗经》定本在文字上(甚至篇章上)多不完全一样。 笔者认为,就单篇而言,这种“诸侯本”藏篇可分两类,一类是与传本《诗经》同一祖本,在之后的流传中,因传抄或其他原因,文字甚至篇幅发生歧异,遂衍化成一篇诗的两个或几个版本,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经·周颂·敬之》的关系属于此种。另一类则是没有被传世本《诗经》收入、被后代称之为“逸诗”的诗篇。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左传》、《国语》、《战国策》乃至《荀子》、《墨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一些今本《诗经》中没有的诗句,当多属于此类。 三、僖公二十二年之前周王朝曾整理过诗 不少研究者认为,《诗》的编定不止进行过一次,但都认为孔子之前,周王朝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诗”的编辑工作。笔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总觉得尚且缺少更具体的材料证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现,进一步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佐证,其证据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一段记事: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⑨ 邾人出兵攻打鲁国,鲁僖公小看邾国,不做防备。臧文仲批评鲁僖公时引用了《敬之》,文句与今本一样。《左传》所引的“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与传本毛诗《敬之》仅“惟”字不同,毛《诗》作“维”,二者系同音通假;而与清华简本《周公之琴舞》中相对应的诗句“敬之敬之!天隹(惟)显帀,文非易帀”有一定差异。 显而易见,如果说传世本的“天维显思”与简本的“天隹(惟)显帀”中字的不同是音或者写法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论的话,那么传世本的“命不易哉”与简本的“文非易帀”的差异就不那么简单了。固然从文义上看,只有“命不易哉”的“命”与“文非易帀”的“文”字不同(“不”与“非”可用二者同义转换解释,“哉”与“帀”可用音近通假解释)。但是“命”当是“天命”之义,“文”当是“文德”之义,二者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上,似乎都不易混淆搞错。更重要的是,结合传世本《周颂·敬之》对简本《周公之琴舞》的大刀阔斧的删节⑩,似乎不能说是抄手误将“文”字抄成了“命”字,也不能说是传世本毛诗的经师用汉隶转写古文时造成的异文。 退一步说,说它是传抄过程中抄手的误抄也好,有意改动也好;说它的意思有变也好,无变也好,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今天看到的传本《周颂·敬之》是从当年鲁国臧文仲所看到的《周颂·敬之》本一脉下来的(11),与简本《周公之琴舞》不是一个版本系统。鲁僖公二十二年是齐桓公之子齐孝公五年、公元前638年,其后八十七年孔子出生。这就说明,鲁僖公二十二年之前周王朝曾整理过“诗”(也许还不止一次),在某一次整理中,以《周公之琴舞》形式呈现的文本被“编辑”成了与传本《周颂·敬之》文本接近或者相同形态的本子,之后这种形态的版本就成了“流行本”,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外交舞台上广泛使用。而楚国本《周公之琴舞》由于先此传入楚国,没有被编辑整理,得以较为原始的面貌保存了下来。 当然,这个结论必须排除如下可能:《左传》的最后编定者或汉代经师曾依据传世《诗经》对包括《周颂·敬之》在内的《左传》全书用“诗”进行过“整齐”(12)。不过笔者考察后觉得此种可能不大。因为第一,《左传·宣公十二年》将传世本《诗经》中分为三篇的《赉》、《桓》、《武》说成是《武》一篇诗的三章;第二,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次序上仍显示着与传世本《诗经》差异;第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其中的“何以恤我”,传世本《诗经》中没有,杜注以为是逸诗。杨伯峻考证后说:“‘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实则《周颂·维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之变文。假即遐之借字,何也。遐之训何,例见《词诠》。恤,《说文》、《广韵》引作‘谧’,《诗》作‘溢’,皆声近相通,实皆为‘赐’之假字。诗意谓何以赐与我,我将接收之。”(13)第四,《左传·昭公六年》:“叔向使诒子产书,曰:‘……《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而在传世本《诗经·周颂·我将》中这两句里边的“德”字是“典”。这几例与传世本《诗经》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左传》中有关诗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经过《左传》最后编定者或汉代经师的改动。因此,说僖公二十二年之前周王朝曾整理过“诗”是靠得住的。 四、“诗”传抄中的常用删削之法 大家都注意到了,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有点问题。为了便于阐述,抄录简文如下: 周公作多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卒)。 元内(纳)启曰:无悔亯(享)君,罔坠亓(其)考(孝)。享隹(惟)慆帀,考(孝)隹(惟)型帀。 成王作敬(儆)怭(毖),琴舞九絉(卒)。 元内(纳)启曰:敬之敬之!天隹(惟)(显)帀,文非易帀。母(毋)曰高高才(在)上,劯(陟)降亓(其)事,卑蓝(监)才(在)兹! 乱曰:讫(遹)我夙夜不兔(逸),敬(儆)之!日就月将,教亓(其)光明。弼寺(持)亓(其)又(有)肩,视(示)告余?(显)惪(德)之行。 通(再)启曰:(略)(14) 乱曰:(略) 参启曰:(略) 乱曰:(略) 四启曰:(略) 乱曰:(略) 五启曰:(略) 乱曰:(略) 六启曰:(略) 乱曰:(略) 七启曰:(略) 乱曰:(略) 八启曰:(略) 乱曰:(略) 九启曰:(略) 乱曰:(略) 从开头的文意看,本来周公是应该作琴舞九遂(章)的,可是实际上他只作了半遂(只有“元启”而没有“乱”)就转向成王所作的九遂了。也就是说,成王的九遂很完整,而周公所作的缺八遂半。对此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周公作’的诗缺失了八篇,而‘成王作’的诗完好无损。通过仔细绎读,可知现有的十篇诗前后呼应,‘周公作’之下的一篇固然是周公儆毖多士的口吻,并且适于作为全诗的领首,但在‘成王作’之下的九篇,却有一些不可能出自成王。”李先生通过对《周公之琴舞》逐字逐句的释义后说: 《周公之琴舞》全诗十篇,如以内容实际来说,以君臣口吻划分,是这样的结构: 所谓“周公作” 元入启 臣 所谓“成王作” 元入启 君 再启 臣 三启 君 四启 臣 五启 君 六启 君 七启 君 八启 臣 九启 臣 其分布很有规律,显然是有意编排的结果。 最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在此不妨试作一大胆的推想。《周公之琴舞》原诗实有十八篇,由于长期流传有所缺失,同时出于实际演奏吟诵的需要,经过组织编排,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结构。”(15)与李学勤先生看法不同,蔡先金先生则认为:“从第二遂的记载看,记载者十分清楚地载明从第二遂的第二启开始,是周公与成王共同的‘启’了。简文记载第二遂的‘启’文为‘通启曰’,而非‘再启曰’,简牍整理者皆认为这是字误……其实‘通启曰’的‘通’字并非为‘再’字之误。……”而“通”是“共”的意思,即“第二遂的‘启’开始了共同之‘启’了。……为何如此?因为第一遂的‘启’是由周公与成王分开的两‘启’,而到第二遂则成为了同一之‘启’,故曰‘通启曰’,而非‘再启曰’,但是仍然属于第二遂,所以后面紧接着是‘三启’,一直顺序下去,没有任何紊乱问题。”“该诗有两个序,让人疑为两篇乐章。但两‘序’又都指明该乐章是‘琴舞九遂’。这从乐的角度看,该‘颂’为通体‘九遂’,这是讲得通的。也许是作序者有意为之,表明无论是‘周公作多士儆毖’还是‘成王作儆毖’,总归都是一个‘琴舞九遂’而已。是故‘琴舞九遂’书写了两次,以作强调。”因此“可以基本断定出该颂诗乐为一完整的篇章,既非拼凑,亦非误抄。”(16)总之,研究者们都力图对《周公之琴舞》的结构给予符合逻辑的合理解释。 笔者认同李学勤先生的看法,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绝非其原始面貌。原诗实有十八篇,现状是被删节和重整的结果。与李先生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这种删节更多不是“由于长期流传有所缺失”,而多数是抄写者主观上有意为之的。换句话说,即使是“长期流传有所缺失”,缺失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辗转流传中某一中间环节的有意“漏抄”造成的——因为文字太长了,就当时的书写工具而言,写起来太费劲了!而就“实际演奏吟诵的需要”看,似乎留下的部分也足够了,于是乎,周公那八遂半就给删掉了。但是,毕竟删掉之后逻辑上不太顺畅,为了使文气连贯,抄手就对诗的文字作一些改动。因此李学勤先生才会感到“其分布很有规律,显然是有意编排的结果”。 蔡先金先生敏锐地发现了简文第二遂的“启”文“通启曰”的“通”字并非为“再”字之误。认为“通”是“共”的意思。对此笔者很认同。但是在结论上笔者与蔡先生有一点儿不同。蔡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是《周公之琴舞》最原始的面貌,“也许是作序者有意为之”的;而笔者认为这并非最原始的面貌,而是后来某一抄手所为。 笔者认为,这种压缩篇幅,取其所需的“删诗”,并适当改写部分文字,以顺通删节后的诗意的做法,并非个案,当为当时“诗”传抄中的常用之法。否则简本《周公之琴舞》不可能做得那么自然和纯熟老练。 五、传世本《诗经》使用的几种“删诗”法 根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其他可靠文献,目前可以推测出古代删诗方法有三: 1.删掉一部分。本文所论的《诗经·周颂·敬之》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关系就是例证。 2.整篇删掉的。《左传》、《国语》以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可以看到的一些“逸诗”多属此类,这些被称为“逸诗”的,除了有部分可能是自然散失或某些诗篇的逸句之外,应该是被有意删掉的。 3.把一篇分成几篇。《左传》中有一个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国胜利后,楚臣潘党劝楚庄王“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不同意,他的一番议论中引用了《诗经》,具体如下: 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7) 楚庄王提到的“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见于现行本《诗经》的《周颂·时迈》,简本与现行本一个字不差。“耆定尔功”,见于今本《诗经》,是《周颂·武》的最后一句;“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见于现行本《周颂·赉》篇,只是“铺”字,在现行本中做“敷”,当是通假字,“遍”、“普遍”之意。“绥万邦,屡丰年”在今《周颂·桓》篇。按照《左传》所记楚庄王的说法,后边的几句原本都出于一篇,即《武》篇,顺序是: “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传世本在《周颂·赉》篇,《左传》说是出于《武》篇第三章。 “绥万邦,屡丰年”——传世本在《周颂·桓》篇,《左传》说是出于《武》篇第六章。 “耆定尔功”——传世本是《周颂·武》的卒句,《左传》说是出于《武》篇卒章。 在传世本《诗经》里,明明是三篇诗歌,但《左传》却说是分属于一篇诗歌的三章。虽然都是《大武》舞的乐章,但是在现行本《诗经》中它们被分开了,而且三篇的顺序并不都连着。 《武》在现行本《诗经·周颂》“臣工之什”的第十篇;《赉》在现行本《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的第十篇;《桓》在现行本《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的第九篇。即现行本中,《武》与《桓》中间隔着八篇,与《赉》中间隔着九篇;而《桓》和《赉》虽然挨着,但前后顺序颠倒了。 对这种现象,杨伯峻一方面说“(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句今在《周颂·赉》篇,《左传》以为《武》之第三章”;“(绥万邦,屡丰年)句在今周颂《桓》篇,此作《武》之第六章”;接着又说“盖古今《诗》之篇次不同之故”(18)。这种解释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所谓“篇次”只是篇章排列顺序,而这里明显见《左传》不是颠倒了“篇次”,而是把今之三篇给合成一篇了!或者说是传世本《诗经》把古之一篇给分成三篇了! 孔广森《经学卮言》说《左传》所叙未必非周乐之正次(19)。认为《左传》所说可能就是原本周乐的顺次。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现可以说明,《左传》所说确实可能就是周代诗乐的原貌。因此笔者推测,在古代的删诗中,还有一种删诗法,即把一篇乐诗分成几篇。我们说的《左传》的例子当属于此种。 六、结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孔子“去其重”不诬 经过上面的分析,对司马迁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以及“去其重”的意思就容易理解了。本文前面已经论证了,从西周开始直至传世本《诗经》问世之后的战国时期,一直有与传世本《诗经》不同的“诸侯本”诗篇存在;僖公二十二年(前638)之前周王朝曾整理过“诗”(而且可能不仅仅整理过这一次),而压缩篇幅,取其所需的“删诗”,乃至修改诗句,是当时“诗”的传抄和整理中常用的方法。这样每整理一次,就会产生一些与老版本诗在文字或者篇幅等方面不完全相同的新版本诗篇;在一些诸侯国中,可能是一个甚至几个新老版本并存和并传。在从西周初年到传世本《诗经》编定的几百年中,随着“诗”的不断增加补充和辗转抄写,同一篇诗在各诸侯国必定会产生各自不同的“诗”的版本。加上一些产自本国而未能及时传入外诸侯国的“风诗”陆续出现,时间久远导致的断简错简,传抄中无意的漏字错字,为了书写简便的随意“通假”,不同地区方言产生的同言异字等,到孔子之时,同篇异名、同名异篇、多本一源、残简断章、舛误错乱的诗,加起来有三千多篇实在不足为奇。孔子对这三千多首诗,剔除重复舛误的,合并内容相似的,厘清归类混乱的,校理篇章窜乱的,订正字句讹错的,使它们各归其类,最后,编成了一部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所谓“古者诗三千余篇”以及孔子“去其重”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说得没错! 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十一篇《周颂》,几乎篇篇都那么短,失去了《周公之琴舞》所昭示的颂诗应有的磅礴气势,其根源就是“周室微而礼乐废”导致了“《诗》、《书》缺”;而罹“礼乐废”之最大灾难的必然是《周颂》。无法还原《周颂》原貌的孔子,只好在他所搜集到的舛乱残缺的简牍中爬梳钩沉(20),尽可能使“雅颂各得其所”;甚至采用对原诗“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等形式,在颂诗的篇数上,找回周天子的尊严(21)。 注释: ①孔颖达《诗谱》疏,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3页。 ②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八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3页。 ③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33页。 ⑤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8页。 ⑥“陟降厥士”也可以看成与简本“劯(陟)降亓(其)事”同义,“士”与“事”乃同音借字。 ⑦李鹏《清华简:发现中国最早史书》,《北京科技报》2008年11月3日。 ⑧李守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文物》2012年第8期。 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5页。另,《左传·成公四年》(前587)也有相同引文字: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⑩当然这种删节未必是一次完成的,可能中间几经曲折。 (11)因《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引文仅此三句,看不出当时《敬之》的全貌,无法断定当时的《敬之》是否与传本《敬之》全部相同,因此只能说“今天看到的传本《周颂·敬之》是从当年鲁国臧文仲所看到的《周颂·敬之》本一脉下来的”。如果当时的《敬之》全篇都与传本一样,说明孔子之前就被删成如今的样子了;否则,说明到后来又进行过整理。 (12)一般认为,《左传》成书下限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即孔子去世后的八十到一百五十年。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136页。 (14)“略”表示本文作者对《周公之琴舞》原文的省略。 (15)李学勤《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笔者对李先生观点的引用,主要是赞同其方法和结论,并不意味着对其琴舞结构的一切解释都认同。 (16)蔡先金《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与乐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先秦经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22页。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44—745页。 (18)(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45页。 (20)笔者认为,孔子肯定没有看到简本《周公之琴舞》。 (21)当然,孔子的这种“删诗”,不是有意压缩篇幅,而是文献不足的无奈之举。标签:清华简论文; 孔子删诗说论文; 孔子论文; 周公论文; 春秋左传注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诗经论文; 国学论文; 周颂论文; 儒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