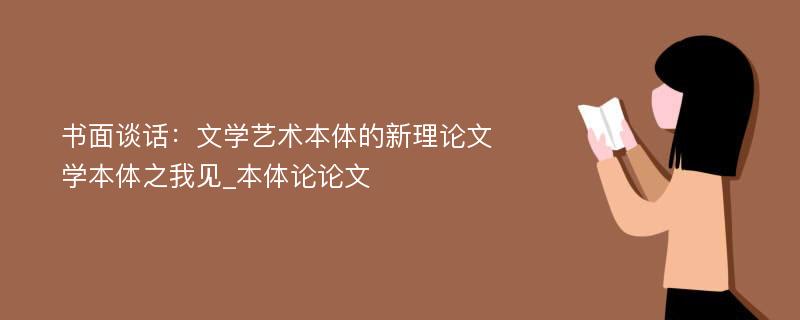
笔谈:文艺本体论新论——1.关于文学本体论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笔谈论文,新论论文,我见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本体论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但学界研究还相对不够、相对薄弱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话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
讨论文学本体论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要弄清“本体论”的哲学含义。长期以来,学界、特别是文艺理论界常常在本原论、本质论、本根论、本身论等意义上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术语),笔者认为这里存在某些误解或误用。这就有必要追本溯源,首先对本体、本体论等概念的历史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
据现存资料,“本体论”(英文Ontology,德文Ontologie)这个词最早是由德意志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于1636年首先使用的。他将希腊词On(ον即Being)的复数Onta (οντα即beings,指“存在者”、“在者”或“是者”)与logos(ονοδ,意谓“学问”、“道理”、“理性”、“论证”等)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e,可译为“存在学”或“存在论”。1647年,另一位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又将Onta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 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 Baptiste Duhamel)也使用了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此词指专门研究存在本身及其规定的学问,属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最早为“本体论”(Ontologie)下定义的则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弗(Christian Wolff),黑格尔曾引述过这个定义:“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ον)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1]189。这个定义对本体论作了重要的界定:(1)本体论是专门研究“有”(即“存在”,或译“在”、“是”)和“存在者”的学问;(2)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有”或“存在”的各种普遍的哲学范畴,其中包括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3)本体论认为“有”或“存在”是唯一的、善的,因而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普遍、最高的范畴,其他范畴均可从中推演出来;(4)本体论是抽象的、以逻辑方法构造的哲学,属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界定表明沃尔弗对该词的理解显然比之前三位更早使用本体论一词的哲学家全面、准确、深刻得多了。应当说,沃尔弗是借用Ontologie一词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逻辑概括,使原来被淹没在其他许多哲学问题探讨中的存在论研究的内涵鲜明地突现出来。自此以后,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就十分明确,本体论一词很少再被当作本原论、本质论、本根论等意义来理解和使用。直到今天,沃尔弗的本体论定义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有效性①。
对于用“本体论”来对译Ontologie(Ontology)一词,学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比如我国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在探讨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时,就不满意“本体论”的中译法,曾改译为“万有论”。他说:“万有论(OntOlogia,旧译‘本体论’,但不精确)成为一学科始自亚里士多德;但本篇(按:指《巴曼尼德斯篇》)已为这个学科奠定基础。它指出来,‘是’(ονσια)分为一切的‘有’(οντα),‘割裂为最可能小的和最可能大的以及各种各样‘有’,那么万有有一共通点,即分有‘是’……”[2]181
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第一,希腊文ονσια与ον一样,是系动词ειμι的动名词形式,相当于英文Being,陈康译为“是”,也可译为“有”、“存在”、“本体”等,笔者采用“存在”的译法;ονσια的词性是动名词,是从系动词ειμι或其不定式ετυατ(相当于英文be及其不定式,to be)演化过来的,系动词ειμι原本就包含“是”、“有”、“存在”等意义;而陈康先生译为一切的“有”的οντα则相当于英文中的 beings,它是ον的复数形式;ονσια(译为“本体”、“实是”、“实有”或“是”、“有”、“存在”等)的词性原本为分词(ειμι的现在分词形式是ουσα),但亦名词化了,所以在语法上指“分有”系动词ειμι(be)动、名双重意义的词;同样ον也有名词、分词双重功用,故陈康此处译为“有”,也可译为“是的”、“是者”、“存在者”等。第二,ον(“是者”、“存在者”)在语法上“分有”了“是”(“存在”,ονσια、Being),兼具系动词的功用。而在哲学范畴上也“分有”了“是”(“存在”)的意义,也即“存在者”范畴是从“存在”范畴中“分”出来、推演出来的。第三,“本体论”或“万有论”主要是研究存在(Being)和统称为存在者(“是者”,beings)的各种范畴之间关系的学问,陈康先生正是据此而把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看作西方本体论的始作俑者。
由此可见,本体论概括起来应当是主要研究存在的学问,可以而且应当用“存在论”加以概括。
二
西方的本体论研究在笛卡儿之前一直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课题和内容,自笛卡儿开启了近代哲学的新路子后,认识论研究上升到形而上学的中心位置,本体论研究的地位则在降低。笛卡儿最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就明显使本体论(存在论)从属于认识论,但是,他对本体论主要研究存在论的基本理解并没有改变。这里还想重点谈一谈康德对本体论(存在论)的看法及其新的发展。
康德曾就本体论(Ontologie、Ontology)指出:“较狭窄意义上的所谓形而上学是由先验哲学和纯粹理性的自然之学所组成的。前者只考察知性,以及在一切与一般对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的系统中的理性本身,而不假定客体会被给予出来(即本体论)……”[3]638可以看到,康德的Ontologie(本体论)即先验哲学,它与人(主体)的知性相关,研究人先天的知识形式(理性本身),这些知识形式是非实体化的,即不是存在者(即实体或实存)。因此,在康德思想中,Ontologie(本体论)实际上探讨的仍然是“存在”或“是”(sein)的问题,但这里“存在”不是如传统本体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与人无关的客体,而与人的知性、更广义的理性相关。这一点从康德对“存在”概念的理解中可以看出来。他指出:“‘是’(即‘存在’)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逻辑上,它只是一个判断的亲词……系词‘是’并非又是一个另外的谓词,而只是把谓词设定在与主词的关系中的东西。”康德具体举例说,当我们说“上帝存在”时,“那么我对于上帝的概念并没有设定什么新的谓词,而只是把主词本身连同它的一切谓词,也就是把对象设定在与我的概念的关系中”[3]476。这实际上颠覆了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关于上帝存在的探讨。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康德看来,存在作为谓词的规定性“少于”其他的实在谓词,也就是说,“存在”如果作为纯粹指向客体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康德明确指出,引入存在概念本身就产生了矛盾。他认为:“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在谈论那绝对必然的本质,而且人们并不努力理解是不是和能够思考这样一个事物,而是努力证明它的存在。尽管这样一个概念的名词解释是非常容易的,即它是某种这样的东西,它的不存在乃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这样的做法人们丝毫没有变得更聪明,同样看不出怎样可能把一事物的不是看作绝对不可思考的东西,而实际上人们想知道,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究竟是不是可以普遍地思考某种东西。”[4]400当然,康德并不是要取消“存在(是)”的概念,他认为“存在”不是指向“某种东西”即“存在者”,而是表达出某物完全符合“我”(理性主体)关于某物的概念,因而指向的是某种关系,即概念与对象的关系。而概念在康德看来,是人的先天的知性能力,因此,对“存在”的探讨就与人本身(知性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毋宁说,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人本身,认识了人的知性能力的界限,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存在”。在这一点上,康德的思路与海德格尔从Dasein到sein的思路颇为一致。事实也正是这样,康德可能最早在存在论意义上使用了Dasein(可译作“此在”、“限有”、“定在”等)这个词或概念。康德将Dasein解释为:“是被给定的”(ist gegeben)存在②。这个词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对“确定性”的强调,它指的是对象的确定性。在康德看来,存在只能是具体之物的存在,也就是存在者之存在,更具体地说是此在,是对象性的存在,是处于与人(主体)的知性能力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可见,Dasein的本质是对象性,所谓存在,就是对象性的存在,因为只有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与现实性、确定性、当下性,即与人具体的知觉和具体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存在问题就被康德置入“与我们知性能力的关系中”得到了思考。这样,康德关于“存在”的思想就与传统的本体论有了如下的不同:
第一,传统本体论认为,本体或存在实际上是某种最高的存在者;而康德认为“存在”不是“存在者”,而指向了某种关系。
第二,传统本体论认为,最高的存在者是外在于人的;而康德认为,“存在”与人的知性能力相关,是作为人的知性能力的对象的存在(定在/此在,Dasein)。
第三,传统本体论认为,由最高存在者可以推出现实的事物,如柏拉图的理念的床和现实的床,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注里警告说,“不要从概念的(逻辑的)可能性马上推出事物的(实在的)可能性”③。海德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现实性(实存)就是该物同时与知觉的结合,现实性、实存(定在/此在)是绝对的断定,相反,可能性则是相对断定”[5]40。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所谓存在,就是对象性的存在(定在/此在),因为只有对象性的存在是与现实性、确定性、当下性,也就是与人的具体的知觉和具体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是建立在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上的。
据此,笔者认为,康德哲学确立了主体(人)的存在论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存在论模式,达到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统一,从而使近代以来的“认识论转向”重新获得了存在论的基础。
另外,从康德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康德认为理性的兴趣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即我能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而倒过来看,“人是什么”又恰恰可以分解为这三个问题,这样,这一问题所问的就不是人的实在(存在者),而是人的存在,即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中,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即显现自身。在第一个问题中,康德试图通过对人的知性能力的批判和澄清,拯救形而上学,由此就通向了先验哲学,即本体论。可见,从康德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本体论同样也具有存在论的内涵。
20世纪以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哲学问世,本体论研究重又获得普遍重视。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明显受到上述康德存在论思想的深刻启示和影响,但又超越了康德主客二分的存在论模式。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人的存在就是“此在(Dasein)在世”,也就是“人生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把人和世界看成是一体的,人的变化带动世界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带动人的变化,而不是像认识论思维方式那样主客二分,认为世界外在于人。按照“此在在世”的观点,人跟世界是不能分离的:一方面,人生存在世界之中,世界原初就包括了人在里面,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世界只对人有意义,如果没有人,这个世界也就无所谓意义。而“在世”就是人与世界打交道,人一直处于跟世界不断打交道的关系中。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人就现实地生成了。这种打交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与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其实就是实践。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来阐释和改造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的观点,实践活动显然就是人的在世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生在世的基本方式就是实践。这应当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存在论)的基本含义。
综上所述,从西方本体论发展史来看,关于本体论研究应当聚焦于存在论上,而主要不是讨论本原论、本质论、本根论、本身论等问题,虽然它们之间并非没有关系。文学本体论研究亦不例外。
三
关于国内文学本体论研究,王元骧先生在2003年撰写的《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6]一文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评析。最近苏宏斌博士的新著《文学本体论引论》[7]则从哲学到文学、从概念到实际、从历史到现实作了更加系统的概括和评述,虽然其中不无可以进一步商讨之处,但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读后颇受启发。
笔者曾在1988年发表的《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一文中提出,应当把“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论”提问方式转换为“文学怎样存在”的本体论(存在论)的提问方式,即寻找和论述文学的存在方式。笔者在该文中指出:“文学既不单纯存在于作者那儿,也不单纯存在于作品中,还不单纯存在于读者那儿。文学是作为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8]苏宏斌把这种“活动本体论”概括为新时期四种文学本体论(另外三种是形式、人类、生命本体论)之一种,并给予了较多的肯定,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
现在看来,笔者的上述看法在思路和方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还停留在“文学”活动、“文学”的存在方式这一比较浅表的层次上,还不够深入。如果更深入一步思考,文学本体论应当提升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即把文学活动(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一种)看成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看成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如上所述,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学习、工作、生产、经济、政治、宗教、道德、交往、休闲、体育、艺术、审美等等活动在内,都是人生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实践活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也就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我们说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而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是种种人生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首先,人通过实践成为人,也通过实践得到了发展,其中就包括艺术和审美实践的作用在内。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在内的无限丰富的人生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的文明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建构和提升,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也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反过来,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推进了人类实践整体的发展,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建设。其次,艺术和审美活动是人走向全面、自由发展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因素。人如果只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而没有审美活动,那么其实践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这种实践造就的人也是片面的、不自由的。再次,艺术和审美活动总体来说是一种精神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精神生产”,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精神性的对话和交流,跟物质生产劳动相比,它的精神性更强。因此,审美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精神性更高一些,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是最超越于个体眼前的功利性的。总之,艺术和审美活动不仅是人的一种高级的精神需要和交流方式,而且是见证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是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和基本的人生实践活动之一。
据此,笔者认为,文学本体论应当在上述实践存在论思路下对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展开研究,应当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活动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才是文学本体论研究的任务。而不应当把文学本质、文学本源、文学本身(形式)等问题都归于或都当作文学本体论问题来思考,这样反而有可能把文学本体论的存在论这一核心内涵给遮蔽了。当然,对文学本体论展开具体的论述,已经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收稿日期]2007-05-2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如1989年出版的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中“Ontology”条目就明确指出:“研究Being本身,即一切实在性的基本特性的一种学说……这个术语在近代哲学中的知名则是由于德国理性主义者沃尔弗,他把本体论视为导致有关Beings的本质必然真理的演绎法。”
②引自陈嘉映先生在《存在与时间》(康德著,陈嘉映、王太庆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书的附录中所作的说明。
③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注。
标签:本体论论文; 存在论论文; 康德论文; 文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