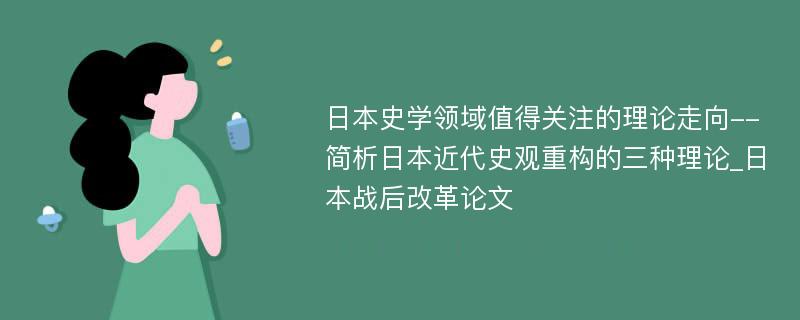
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动向——阐析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三种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现代史论文,三种论文,日本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史学界对日本现代史的基本认识,主要有两种传统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现代史是“接续”的历史,即认为日本在大正时期(1912—1926年)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建立的、以超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强权体制,将日本纳入了战时动员的轨道,从而阻断了这一民主化进程。日本1945年战败后开始的战后改革,是使日本历史复归大正时代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如三谷太一郎提出:“在大正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与战后民主主义直接相关的政治传统。”(注:三谷太一郎:《新版大正民主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357页。)松尾尊兊也认为:“应将大正民主视为日本社会在战后走向民主主义的前提。”(注:松尾尊兊:(大正民主),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2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现代史是“断截”的历史,即认为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使日本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之告别了历史,重新获得新生。这种观点在日本史坛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中国史学界也基本采纳这种观点,如彭树智认为:“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注: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但是,这一传统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已受到质疑。1977年,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提出了“支撑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的“假说”。(注: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中央公论》1977年第8期。)1988年,山之内靖提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注:山之内靖:《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 本》,《世界》1988年第4期。)但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和平稳增长时期,上述观点未引 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政治遭到普遍怀疑、经济陷入重重困境为背景, 认为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观点开始受到充分关注。包括野口悠纪雄和 山之内靖在内,不少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性考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 值得关注、颇有见地的理论。“总体战体制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19 40年体制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对日 本战时和战后体制“连续性”的研究,打破陈说,重构日本现代史。其共同目的,就是 寻找当今“日本病”的病根。这些理论不仅在日本学术界影响日广,而且波及海外,引 发了西方学者研究日本现代史新的学术兴趣。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对拓展认识日本现代 史的视野,进一步认识现行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均不无裨益。但是,迄今为止, 这些理论还未见有学界同仁予以评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特依据从日本所获最新 资料撰成此文,分别对三种理论及其影响进行阐述,并略发表个人浅见。
一、“总体战体制论”
“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是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于1995年主编的、作为13位日本和美国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依据明确的立论宗旨和方法论原则,通过对战时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系统而实证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日本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延续,并将他们自己提出的理论称为“总体战体制论”。
“总体战体制论”的立论宗旨,具有明确的针砭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批判性。对此,该书在绪言中即阐述得非常清楚:“本书所有论文的作者均有意识地同具有战后日本革新政治特征的历史意识保持距离。因此,其中有的论文必然会被认为存在保守和右翼倾向。例如,否定将战时‘黑暗的森林’和战后‘拂晓的启蒙’作鲜明对比的立场,或许可能被理解成是为战时体制开脱,为战后出现的重整军备和权威主义化倾向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明确理解本书所有论文的意图均与之截然相反就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几乎所有执笔者撰文的目的,都是对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进行批判”(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绪言”,柏书房2000年版,第3页。)。
同时,该书的立论宗旨还具有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明确意向,并将矛头直指构成战后日本史学主流的“战后历史学”派,特别对战后史学派重镇丸山真男、大塚久雄将战 前日本社会视为“后进的、封建的社会”,即认为日本社会是“前近代社会”的理论观 点提出批评,试图取“战后历史学”而代之。该书写道:“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 修正主义的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 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 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作为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 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批判性对立物成长起来的。”(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 、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第1页。)
在方法论原则上,“总体战体制论”的倡导者通过比较政治分析,对将二战时主要参战国的体制分为美、英、法等“合理的民主型体制”以及德、日、意等“非合理的专制型体制”的两分法提出了批评,指出:“无论是民主型体制还是专制型体制,在战时总动员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民社会虽然复归了和平的日常的体制,但是这种复归并不意味恢复至大战以前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国民社会,均选择了沿着由总体战体制促成的社会重组的新的轨道继续前进的方向。”“基于这一立场,本论将持因总体战而得以实现的社会重组的特征,视为‘从阶级社会向体制社会变迁’的观点。”(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38页。)毋庸赘言,基于这一立场所采取的必然方法,就是比较和分析战时的总体战体制是如何在战后得以延续的,即探讨战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
按照上述立论宗旨和方法论原则,该论著分“总体战和结构变革”、“总体战和思想形成”、“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三个部分,对“总体战体制论”及“总体战和现代化”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本书第一部分“总体战和结构变动”里,作者分别论述和比较了德国、美国、日本在战时发生的变化。在有关德国的论述中,作者强调:“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对德国社会结构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在有关日本和美国的论述中,作者对两国的“战争行为和国家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考察,指出:“若要了解为何现代日美两国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特别是了解日本政府如何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则必须考虑两国战时动员的不同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向非侵略性的通商志向型的国家转变的决定性契机。”(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108页。)
在第二部分“总体战和思想形成”里,作者通过对大塚久雄、内田义彦、三木清、阿 部重孝等人思想和理论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战时和战后的体现、“市民社会 论”和战时动员的关系、战时女性的“国民化”及指导思想、战时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 践同战后教育体系的关系。作者进行这种微观分析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 体制的连续性,并同样具有现实批判的含义:“本书在战前、战后的连续性中理解现代 世界,并不是为了拯救过去,而是为了批判现实。”(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 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206页。)
在第三部分“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作者首先分析了由“反动派”、“国民国家派”、“社会国民主义派”、“自由主义派”构成的四大政治潮流的交互作用引起的战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这些潮流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的“翼赞体制”的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论证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因战时经济而得到发展及在战后得以延续的状况;然后阐述了日本劳资关系因总体战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改变的状况;最后介绍了战时在思想战的呼声中整理统合的大众传媒和情报体制,几乎原封未动地被纳入了占领体制的情况,提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统制体制能够为占领军的情报管理所用,那么这一体制当然也适用于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332页。)总之,按照山之内靖等人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史的“起点”,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着“连续性”,日本的现代化是由“总体战”促成的。
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
“总体战体制论”主要强调的是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连续性”的政治和社会侧面,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强调的则是二者经济体制的侧面。这一理论的代表作,是冈崎哲二、奥野正宽于1993年编纂的、作为8位日本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
一般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同欧美,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各国的经济体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日本型”经营方式有“三大法宝”或“三大神器”,即终身雇用、年功工资序列、企业内工会。第二,在“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方面,主要不是通过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融资,而是主要通过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间接金融”获取资金,与此相关,在开展经营活动时,重视从业人员而非股东;第三,在“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方面,二者通过产业界团体相互依存,构成封闭的格局。按照中日史学界的传统观点,具有上述特征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是战后形成的。中日两国学者就以下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经营方式。战后形成的日本经营方式主要包括长期雇用制、年功工资及晋升制、企业工会及以主力银行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注:陈建安编:《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劳动问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然而,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宽等提出的“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对传统观点进行了明确的否定。他们通过实证性考察后得出结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是在战时形成的。按照他们的分析,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Corporate Governance),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对此,《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一章作了明确论述:“按照历史的观点,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即构成这种体制的诸多重要要素,都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经济的重化学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残留着某种程度的后进性,但基本上是同欧美诸国相似的正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市场型经济体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30年代政府构筑战时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变化骤然得以加速。”“现代日本的社会经济体制,从历史上来看是比较新型的体制。”(注: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年版,第2、3页。)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该论著通过图表和资料,对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项特征在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逐一进行了阐述和论证。(注: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6—13页。)
首先,他们指出:“现代日本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以长期固定的雇用作为理想的。”通过对日本和美国、联邦德国的同期状况的比较,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宽指出:“日本 企业的雇用调整方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期,为了保存熟练劳动力而开始 采用的。但是至30年代前半期,雇用调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尽量留用熟练劳动力这种 变化的产生,是在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战争时期。”
其次,他们写道:“现代日本企业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是股东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非常小。这特别在董事会的构成和股份的持有两种现象中得到典型表现。股份公司建立董事会本来的意义,如商法所规定的,是反映股东的意向监督企业经营。但是现代日本企业的董事会席位,几乎均为内部提拔者占有。拥有代表企业外部、特别是股东意见的董事的企业,除了外资企业,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股东权限的低下,主要同企业获取资金的方式有关。“在现代日本,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是通过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向作为资金供给者的储户借贷资金的,即‘间接金融’的机制,是资金循环的主流。”但是,“企业主要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形式成为主体,是自1936年前后开始的。战前,则是以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融资的直接金融作为主体。”
第三,他们同样认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最后的要素,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同的产业由单一的行政当局进行纵向监督,并通过以行政指导为主的管理手段左右产业的‘发展’和‘秩序’。具有目的性地控制制造业(或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典型,是通产省制订的‘产业政策’,而控制‘秩序’的典型,则是以金融机构为对象的大藏省的‘护送船团行政’。”他们强调,“这种由政府承担的‘竞争的管理’和‘计划的分配’,是对战时计划、统制体制的继承。”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不仅对“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的历史经纬作了探讨,而且对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另外两大方面,即以所得税和法人税为基干、集权和分权相结合为两大特征的“日本型”财政税收体制,和以粮食管理制度和农业协会(农协)为两大特征的农业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因战时经济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需要制定的。”(注: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274页。)
三、“1940年体制论”
1995年,曾提出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延续性“假说”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 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一书,提出了“1940年体制论”。关于为何要将 日本战时体制称为“1940年体制”,野口悠纪雄在书中作了明确解释:“‘1940年体制 ’这一词汇,最初是在自民党一党体制崩溃的1993年夏,由《日本经济新闻》的专栏文 章首先使用的。该文章指出‘55年体制已崩溃,但40年体制仍留存’。为什么不选别的 年份而选40年?有人着眼于《国家总动员法》提出的年份,提出称之为38年体制应该更 加准确。也许真是这样。总之,选择1940年并无特别的理由。”“我认为,当今的日本 经济体制仍是战时体制,故称之为‘1940年体制’。”(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 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东洋新报社2002年版,第4页。)事实上,这种理由还 是存在的。因为1940年正是第二届近卫内阁为适应“总体战”需要建立“新经济体制” ,对经济实行战时统制那年。
《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以十章的篇幅,考察了“1940年体制”的形成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面向未来 的选择等几个方面,对涉及日本经济发展的企业、金融、官僚体制、土地改革、贸易摩 擦的调整等在战时和战后的变化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之后,“为了考察1995年以后的 变化和‘1940年体制论’在现阶段的意义”,野口悠纪雄在2002年该书再版时,又增添 了第十一章“当今的1940年体制”。
毋庸赘言,野口悠纪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连续性”,就考察和分析的范畴而言,该书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亦基本相同。但是仔细作一比较,我们仍可发现他的论著具有一些新的、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和特征。
首先,野口悠纪雄强调,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战时的产物,并不是根深源长的历史产物,应该并且可能进行变革。他这样写道:“日本型经济体制植根于日本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往往容易直接导致‘因此不可变革’的宿命论,即有陷入现存的体制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主义的贫困’的危险。”“本书认为,当今的经济体制即便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特殊的例外,因此在理论上具有变革的可能。”(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18页。)
其次,野口悠纪雄明确指出,“1940年体制”曾经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目前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桎梏。按照他的观点,一方面,“‘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若采用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制,可能无法实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成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96、105页。)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日本仍无法实现体制转换。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当今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摆脱1940年体制的束缚。但无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围绕这些经济政策的争论,均同‘结构改革’的口号背道而驰。”(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155页。)
最后,野口悠纪雄认为,对决定战时和战后日本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有着重大意义的战后改革,必须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各样的文献,印象较深的是,对于在战后改革的风暴中为什么战时体制仍得以留存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关注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的事’似乎不会成为研究对象。对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关于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实际进行过的改革,已有了不少论著。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哪些领域没有经历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讶。”(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序言”,第5页。)
按照他的观点,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主要体现在“构成日本经济中枢”的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存续。他指出:“经过战后改革,日本经济的结构当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官僚制度,特别是经济官僚机构,虽然由占领军进行了‘大改革’,但基本上没有受到损伤的保留了下来,并迄今仍对日本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和官僚制度一起,40年体制的主要要素仍得以留存,其代表就是金融制度。”(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78、87页。)他在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残存的战时体制”的第一部分“战时体制仍然继续的日本金融”的标题下,首先引述了《日本银行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紧接着写道:“这不是战时的旧文书,而是处于现代日本经济中枢地位、决定日本银行存立的《日本银行法》。以1939年纳粹德国制定的银行法为蓝本、作为战时金融统制的总则于1942年制定的这一法律,今天依然是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法。或许没有比这个法律更能象征性地显示现代日本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进行国家总体战而导入的体制,现在依然构成经济的核心。”(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3页。)野口悠纪雄强调重新评价日本战后改革的观点,对重构日本现代史观,无疑具有突出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野口悠纪雄在该书的最后呼吁:“欲搞活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不是由政府推行新的政策,而是不要依赖政府。‘依赖政府’是1940年体制的基本精神。重要的是,不是等待政府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每个人开拓前进。我认为,日本新生的第一步,将从这里开始。”(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235页。)
四、三种理论引领的学术潮流
上述三种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基本观点和目的显然异曲同工,即通过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由于这些理论发表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面临种种难题的20世纪90年代,因此在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上述理论和这些反响,现已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涉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1996年,栗田健发表了专著《日本的劳动社会》,提出在战时体制下,在经营者和劳动者均被视为服务于国家的对等的劳动者的氛围中,工人和职员“作为从业人员应得到一视同仁”的意识、“废除工人职员差异”的意识得以产生,将“白领”和“蓝领”一 律视为“从业人员”的意识开始确立。正是这些意识,构成了战后按行业成立工会的思 想基础和历史背景。(注:栗田健:《日本的劳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19页。)他的这项研究,不仅支撑了“重构理论”,而且从“意识”的层面对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探讨。
1997年,雨宫昭一发表了《战时战后体制论》。他在书中将战时的总体战体制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联系起来放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分析和考察,同样得出了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结论。雨宫昭一指出,在总体战的“战时体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 体制”时期,劳资间、农民间、其他社会阶层间的“社会均质化”的不断演进,推动了 日本现代社会的形成。他在分析了日本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 “翼赞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各地国民重组的实态和功能后指出:“政府、市町村、最 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 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在 ,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进而,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 致无产阶级的形成;因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引起工业化的发展;通过 强制推行,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 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注:雨宫昭一:《战时战后体制论》,岩波书 店1997年版,第199页。)
1998年,女性问题专家上野千鹤子发表了专著《民族主义和性》,对战时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了重新考察。她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注:上野千鹤子:《民族主义和性》,青土社1998年版,第93页。)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上野千鹤子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即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作为一种延续的过程加以把握。她的这项研究,不仅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而且为认识“现代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或参数。
2001年,前田裕子在《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一书中,以三菱重工为例指出,在战争期间生产现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工厂制造产品的技术”和“工厂的经营管理”开始得到统合。换言之,按照她的观点:“生产和管理相结合”这一作为“日本型生产管理体制”重要特征的“现场主义”,就是在战时形成的。(注:前田裕子:《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2003年寺西重郎发表了《日本的经济体制》。在该书中,寺西重郎提出,冈崎哲二的著作中涉及的战时共同融资团就是战后银行体制的萌芽;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经济体制,正是在昭和战争时期出现了转变;正是在战时而不是战后,日本经济界乃至经济体制开始了从战前以财阀为中心,向战后以银行为中心的巨大转变。(注: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岩波书店2003年版。)
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影响,还波及到美国。美国的《日本经济研究》(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在1996年5月和6 月号、1998年5月号分别刊载了题为《告别1940年体制,跨入一个新体制》(Leaving The “1940”System and Moving into a New System)和《1940年体制:日本依然处于 战时经济时期》(The 1940 System:Japan Still under the Wartime Economy)两篇论 文。1998年,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发表了专著《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 的文化》。他在该书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使用‘总动员’一词,阐述日本社会给予满 洲国的广泛而巨大的冲击。”杨格通过对大众传媒、官僚制国家、利益集团、乌托邦意 识形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介入等“总动员”各个层面的探讨,批判了认为战时的日 本帝国产生于“未成熟的前近代国家”的传统观点,指出当时的日本是由支撑新型帝国 主义的现代产业、大众文化、政治的多元主义、新颖的社会组织创生的。(注: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7—9.)
另一方面,上述理论也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批评。1995年,原朗在《战后50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一文中提出,应该充分关注战前和战时(1937年以后) “连续和断绝”两个方面以及从战时至战后初期(20世纪50年代)一以贯之的经济统制期 (战时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时期和旧金山体制时期)。他认为,在经济统制时期,更 应重视战后改革,而不是战时变化的决定性意义。按照他的观点,“正是通过战后改革 ,日本才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生活方式同战前相 比出现了显著变化。”(注:原朗:《战后50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 ,《年报日本现代史》1995年创刊号。)1999年,大门正克发表了题为《探询历史意识 中的现代》的论文,针对雨宫昭一等“总体战体制论”的拥护者将统治者单方面对民众 进行统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社会“均质化”或“平准化”,视为所谓“现代现象”的 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该论文中写道:“所谓现代,是社会愈向前发展国民的团结 更加紧密的时代”,因此“只能将现代历史作为国民团结的历史加以描述”,“强制的平准化不是团结”。(注:大门克正:《探询历史意识的现实》,《日本史研究》1999年9月号,第98页。)2002年,泽井实发表了《战争对制度的破坏和革新》一文,为大门克正提出的、将战时和战后时期均视为“经济统制时期”的观点进行了申辩。他指出:“所以将贯通战前战后的统制时期视为一个持续的时期,不仅因为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存在差异,而且因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两个军部’(日本战时的军部和和盟军占领军总部)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相续存在。”(注:泽井实:《战争对制度的破坏和革新》,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的课题和展望》,有斐阁2002年版,第145页。)
五、余论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后,对日本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考察日本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使战时体制研究这一几无新意的课题,重新获得青睐。然而,形成这种繁荣的背景,却是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陷入了重重困境。不言而喻,学者们意欲以历史的眼光,通过对战时和战后体制相关要素的追溯和分析,探究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难题的历史根源。这种探究不仅就学术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均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依笔者管见,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90年代后,长期占日本史坛主流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日本现代史观,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中心、以鼓吹“自由主义史观”为幌子、以歪曲历史为手段、以否定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历史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现代历史学”。两方面的挑战使日本史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格局的形成昭示了日本历史学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以歪曲历史重构现代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努力”,我们当然应嗤之以鼻。但是对通过实证和还原历史来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努力,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因为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了历史学的真谛,而且有助于探寻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为何面临困境的深刻根源,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价值。
其次,正如《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所写道的:“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其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术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第7页。)毫无疑问,上述理论有助于启迪我们研究日本现代史新的思路。如上述野口悠纪雄关于目前战后改革研究仍存在很多“处女地”的一番论述,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次,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创造“日本奇迹”的基本要素。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涉及“企业内部关系”、“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都曾被视为创造“日本奇迹”的基本要素。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发表名噪一时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的《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等论著,均表明了这种观点。(注: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谷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埃德温·赖肖尔、马里厄斯·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不过,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三种理论的倡导者所采用的方法和批判现实的立场,均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存有对传统或正统历史观进行解构的偏向,并因此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缺乏足够的理性。对于这种缺陷,我们同样应有客观的认识。
首先,如“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的标题所示,在“总体战”和“现代化”之间构建一条笔直的桥梁,认为战时政治经济体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和日本现代“体制社会”形成的结论,在逻辑上给人以为战时的“总体战体制”歌功颂德之嫌,尽管他们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病。另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认为战时体制是“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的观点以及“1940年体制论”认为战时体制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最大的原因”的观点,也存在显然的偏颇。不可否认,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国际国内多种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不是因为战时经济体制的维持。
其次,雨宫昭一等强调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并认为战时的“强制均质化”使现代社会得以形成的观点,同样存在偏颇。应该看到,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战时的“强制均质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工人和职员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趋向“均质”。所谓的“社会平准化”理论,就是依此认为这种“均质”为战后民主平等的逐步形成,即“社会平准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时的“强制均质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趋同”,有着本质差别。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确,这种“均质化”是随着日本1939年以后国民生产力的衰退而日趋下降的“均质化”,和经历战后改革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出现的“平等化”趋向性质迥异。另外我们必须明确,战时的“均质化”程度在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扩大中日趋缩小,相反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包括经济差异在内的人们各方面的差异则日趋增大。例如在工厂里,不在编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包括被强行押解到当地的朝鲜人、中国人等殖民地劳动力在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在战时不仅显然存在,而且日趋扩大。不能不指出的是,认为战时体制下民众趋于“均质”的理论,是 不符合史实的,是片面和错误的。
概而言之,日本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既不是像“总体战体制论”、“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1940年体制论”提出的那样,仅限于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也不是如“战后历史学”始终坚持的,是因为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战后改革才得以形成。我们应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把握日本社会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运动、政治统治的变迁;应从社会诸要素的连续和断绝 、承袭和扬弃两个方面,通观不同阶段统一地把握上述变化。如果我们将战时和战后的 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范畴中加以透视,或许能够对日本从近代走 向现代的历史转折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理论。
(本论文撰写获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