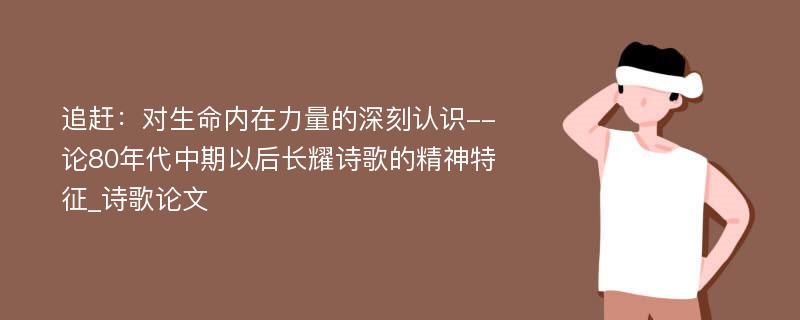
赶路:生命内力的深度领悟——论昌耀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精神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力论文,特质论文,诗歌论文,深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03(2004)06-0451-04
从表面上看,昌耀通过诗歌体现出来的精神状态,1980年代中期以后猝然由峰值跌落 到了底谷。但在深层次上,就精神主脉来看,这一时段昌耀的诗歌不是前期的断裂而是 延续;并且,昌耀还将其投放、伸展进了一个新境界、高层次。一方面,是诗歌悲剧意 识的膨胀、扩大和深入、内化;另一方面是随着悲剧意识的升华和跨越,作品内在生命 张力的升华和跨越:生命所具有的抗争宿命、拷问生命终极价值的强大内力,通过形而 上的“赶路”而得以深度张扬。
昌耀精神下滑的信号,首先是短诗《斯人》发出的:“静极——谁的叹息?//密西西比 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这是一种怎样的大孤 独、大荒凉啊,整个地球就一人无语独坐。接下来,昌耀的许多诗作,都是以一种深悟 了“人(人类)自身”和“超自然”[1](P40)悲剧实质的悲剧精神,来观照人的“内生命 ”:《回忆》表达了生命的大忧虑、大焦灼:“大漠落日,不乏的仅有/焦虑”,“心 源有火,肉体不燃自焚”;《生命体验》表达了生命的大苦闷:“人生有不解的苦闷” ,“无话可说/激情先于本体死去”;而《诗章》里的“我感觉疲倦……/我为追求新生 而渴作金蝉蜕皮/明天不属于每一个人”,则表达了生命的大疲倦、大沉重;《燔祭》 里“死有何难?只需一声呜咽便泪如雨下”传达的仍然是生命的大哀悯、大悲怆,等等 。
然而,当紧紧把握住昌耀诗歌的一个命题——生命、两个质素——悲剧精神和张扬生 命力(结合起来说就是,昌耀诗歌是在悲剧中张扬生命力的生命意象)后,就不得不承认 ,1980年代中期以后,昌耀诗歌精神指向与前期完全一致,精神理路是前期诗歌的延续 而不是断裂。昌耀诗歌中的生命,首先具有悲剧性一面,在1957年以前,昌耀在铸造生 命形象时,注目到了生存空间的凶险、艰辛、蛮荒和恶劣等悲剧的因子。而在1957年以 后直到1980年代前期的诗歌中,昌耀更是以自身苦难经历和不幸命运为“模本”,把生 命塑造成带荆冠的“囚徒”、罹难的流放者。就是1980年代中前期精神达到饱和而为西 部高原造型时,也是以浓郁的悲剧色调打底的。这些诗作,有的呈示“大生命”生存环 境的艰辛,如《旷原之野》;有的展现“大生命”历史道路的踬踣,如《寻找黄河正源 卡日曲》;有的揭示生命向往的虚幻和缈远,如《圣迹》《阳光下的路》。较之以前, 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的悲剧意识似乎膨胀了、扩大了,也更明显、直接了。那么,这 种透过诗歌蒸腾出来的心灵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可以从诗人的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 两方面找到原因。
其实,历经大劫大难、大苦大悲,生命帆船航行到这里,昌耀早已饱尝了命运打击和 生存磨砺,早已领悟到了“生命的本性具有先天的沉重”(《艰难之思》),生命的悲剧 性早已是他系于生命的明显标志。然而,在此之前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更多来自昌耀 外在生命经历、生活处境、生存情状,并用他自身外在生命经历、生活处境、生存情状 去比拟、参照那座荒原、那个民族,得出关于群体生命的悲剧意识。而此时,一方面, 他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也有来自于当下生活处境和生存情状的,比如“金钱拜物教的 倡行”、“渐显端倪的家庭关系的恶化”、“个人诗集出版上的屡屡碰壁”等等;但另 一方面,更多却是来自于内在生命——心灵和灵魂,主要是“庸常”和“不能唤醒激情 ”的精神状态,而由这“庸常”和“不能唤醒激情”引发的,只可能是心灵的焦灼、烘 烤感和悲怆、苍凉感。也就是说,外在生存景观的改善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换,不是减 弱、剪断、去除了对生命的悲剧性感受,而是沿袭、加深、内化了悲剧性体验。
然而在看到昌耀本时段诗歌中膨胀、扩大并深入、内化的悲剧意识时,绝不能忽视甚 至掐断另一条精神主脉,那就是对于生命力的张扬。当时昌耀诗歌悲剧意识膨胀、扩大 并深入、内化暗含的是生命力张扬的膨胀、扩大和深入、内化。这个时期昌耀所张扬的 是生命的强大内力,是立足于存在意义上,通过对人生命题形而上思考和把握,喷发出 来的抗争宿命、拷问生命终极意义的提升力;是内在生命和灵魂的毅力和意志力,是“ 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和“对生存悖谬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绝望搏击”。当然,这种内力的表现方式较之以前显得内敛、沉实、厚重,并且伴随着 巨大的焦虑、疼痛、疲倦和惊悚。概括起来说,昌耀采用了以下几条途径来“张扬”这 种形而上的生命强力。
一 从荒原高地领悟生命内力
当昌耀把诗歌触角再次伸向既是他九死一生的落难之地,又是灌注了他生命与灵魂以 再生的荒原高地时,其诗思是前一阶段(1982—1985年)的延伸。前一阶段他的诗歌是有 特定所指的,那就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而此时,他是把这片十分熟悉的特殊土地, 和生存其上的特殊生存景观,作为揣度生命悲剧实质、追问生命永恒意义、探究生命终 极价值的诗歌背景;他从中剪裁素材、捕获意象,目的是要呈示普遍意义和抽象意义的 、形而上生命的强大内力。此时段他“写”的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但要“说明”的 不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而是作为个体和类的生命本体和生命本身,是哲学意义的生 命。这片土地、这个民族不过是一个载体。比如《回忆》里,昌耀首先提供出一幅大漠 景观:“白色沙漠。/白色死光”,然而这样荒凉、悲怆的大漠景观并不能阻止“西域 道/汉使张骞凿空/似坎坎伐檀”,纵使“晋高僧求法西行,困进小雪山的暴寒,/悲抚 同伴冻毙的躯体长呼——命也奈何”,然而“红尘落地,/大漠深处纵驰一匹白马”。 显然这里有一种巨大的、强劲的生命力在张扬,但诗歌所指明显不是诗中的具象本身, 诗歌意象有着巨大的象征势能,直指抽象意义的生命本体;这里的生命力,是形而上和 普遍意义上挑战宿命、抗争生命所具有的必然悲剧性的坚实生命内力!
这里应该提及昌耀在1989年故地重走后写就的关于生命的大诗《哈拉库图》。“城堡 ,这一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作为全诗的情绪基调,确立了昌耀在诗中要传递的是关于 生命的悲剧性认知。诗中布满了这样一些意境和意象:“造物总以这灼灼的、每日采自 东方的花冠/冷眼嘲弄万类”、“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我每攀登一级山梯都要重 历一次失落”、“没有一个历尽沧桑者不曾有落寞的挫折感。/没有一个倒毙的猛士不 是顷刻萎缩形同侏儒”。然而人类生命和历史生命正是在这明知败北的艰难“博弈”中 实现价值和体现意义的,而其内在依据正在于生命有着无穷的生命力要张扬!于是,昌 耀在灰色生命总场景中看到了这样一些明亮色彩:“衰亡的只有物质,欲望之火却仍旧 炽烈。/……/被烧得高热的额头如一只承接甘露的黄金盘,/仰望那一颗希望之星/期待 如一滴欲坠的葡萄”、“竟又是谁在大荒熹微之中嗷声舒啸抵牾宿命”、“历史啊总也 意味着一部不无谐戏的英雄剧?”由此可以说,这首诗的主旨不在对生命悲剧的描摹和 渲染,而是对处于大悲剧中的生命强大内力的讴歌与抒写。诗歌的精神状态是在大悲苦 中亢奋,大沉郁中勃发;诗歌的基本使命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 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1](P20)是使人们领略生命固有的崇高 和悲壮。
二 从普泛生命情状感知生命内力
对生命形而上命题的终极思考和追问,成了贯穿昌耀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诗作的精 神主线。除了在“爱得最深”的“这土地”(《巨灵》)上营造生命意象以张扬生命内在 强力外,昌耀还从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普泛的生命情状里选取“素材”,构筑他有着 强大生命内力这种“内在一致性”的生命意象。《午间热风》里的“举旗者”;《我们 无可回归》里的“我们”……自然是这种抽象生命的象征本体;而《听候召唤:赶路》 中的“将一切弥合,而你已被孤独激怒穿越恐惧,终于攀登在明月的海岬,感觉海洋铜 管乐搏杀的节拍长短参差闪击/织为黎明之皇冠”的悲壮和激越,《干戚舞》的“时不 我与,是前行还是却步?/嗅着山的气息有如老虎的气息。/我们也将开始我们的睡眠。/ 醒来我们已是子弟”的犹疑和激愤,也正是这种生命内力的强烈爆发和张扬。那些揭示 生命之于世界深刻荒诞感的作品如《幻》《我见一空心人在风暴中扭打》《火柴的多米 诺骨牌游戏》等,也是诗人深刻领受了生存荒诞感后,呈示生命抗争、冲杀、战胜生存 荒诞感时爆发的内在强力和意志力。
三 对理想的坚守
昌耀所体认的生命内力,还表现在“理想主义”“成了一个虚词”、“一个诗人的生 命理想”“被看作不合时宜的象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存更进而被庸常日子中鸡 零狗碎的压力所研磨”的生存处境中,对自身灵魂和理想的坚守与操持。《僧人》中那 个僧人可谓是这种操守灵魂和理想的典型“化身”。他深知“无信仰就属于麻木”,所 以虽然在“惶恐的高度”上“感觉呼吸困难”并且“孤立无援”,但他“挣扎”并“强 化呼吸”,最终感觉到了“光明之顶被罩在”“放大的瞳孔”和“抽筋似的快意”,而 且“又向前趔趄了半步”;同样,《江湖远人》里的“江湖远人”、《圣桑<天鹅>》里 的“天鹅”等等,都是通过坚守灵魂和操持理想张扬生命内力的生命意象。
昌耀生命意象所张扬的强大生命力,“呼应”和“落实”到昌耀身上的一个表现形式 ,应该是在诗歌道路上进击、拼杀和冲刺。“以诗歌年龄划线,昌耀确实不够‘先锋’。但其诗歌艺术的超前性质,则理所应当地属于‘先锋’的范畴”。[2]在诗歌征程中血路冲杀,是昌耀诗歌得以总是游离、高蹈于时代公共规范框架之外,卓尔不群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始终处于当代诗歌最前沿和“先锋状态”,是昌耀生命力的遒劲张扬,然而,这又绝对不是对其他“先锋”和“前卫”的简单认同和趋附,而是自身诗歌艺术秩序和思想轨迹的延伸与递进。所以,完全有理由说,昌耀诗歌视线“陷入”生命哲学这一形而上命题的同时,许多本时段的先锋诗人也在“问津”这一“迷宫”,纯属一种巧合。而且,昌耀与他们的诗歌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除了表现在诗歌艺术传达方式上外,如在语言上他所独具的标志性特征(古奥和滞涩,诗歌语象“采集”、“获取” 的本土经验、原生态特征——高地生态气韵和异质异族色彩)等,根本地还表现在,昌 耀与先锋诗人们一同“笔耕”于生命哲学这一形而上平台时,主旨动机、思想立场和精 神姿态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
对于生命本身,昌耀与许多生命哲学诗人在重要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的,那就是 如同诗人欧阳江河写的那样:“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 者列在一起/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2]——生命是宿命的存在,生命挣 不掉宿命的攫取。这也是他们的诗歌在形态上都散发着深灰悲剧气韵的共同原因。然而 ,正如前文所论,这个时期昌耀的诗歌主题和主旨动机,仍然是张扬生命的强大内力; 诗歌形象是“永不懈怠,持续以恒,于终极意义上是悲剧性的可怜挣扎”的、“在过程 瞬间中却体现出某种正剧喜剧的光彩”的生命意象。尽管,这种内力的表现方式显得内 敛、沉实、厚重,并且伴随着巨大的焦虑、疼痛、疲倦和惊悚——这是因为,这是一种 抗争宿命的强大内力,而宿命,是“理想的实现和苦难的阻遏”这一对“孪生兄弟”形 成的“人类永远解不开的生存悖论”,本身就是生命的大悲哀。所以在本质上,昌耀通 过此时段此类诗歌表现出来的思想立场和精神姿态,依旧是他一以贯之的积极、向上、 奋发和激进,创作心理依旧是健康、昂扬、正常的。而此时其他许多诗人呢,在面对宿 命和命运时,状态就不是全如昌耀了。他们中有的选择了庸常化生命哲学和“冷态抒情 ”,认为既然“命运如血液般流淌在我们的肉体”,又还谈何人生与生命的意义呢;[3 ]有的则“在对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的书写里,“透出个人日常生命的本真体验: 生存的恐慌感”[4]以及对崇高、价值、意义、英雄、文化的反讽、颠覆,从而呈示生 存的真实景观和作为凡夫俗子的人的真实姿态:“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总 之,这类诗歌在人格塑造上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渎、自虐与自伐;在精神指向上是积极 向“下”、消极颓丧的;写作姿态是在悲剧中悲泣。写诗动机和主旨,恐怕也在于使本 已消极、无聊、庸常的人类更消极、无聊、庸常了——然而,事实上,对于命运和宿命 ,灵魂需要的是拼搏、抗争,精神需要的是提升力,而不是顺从听任无奈的叹息。这正 是昌耀区别于他们的地方所在。
收稿日期:2003-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