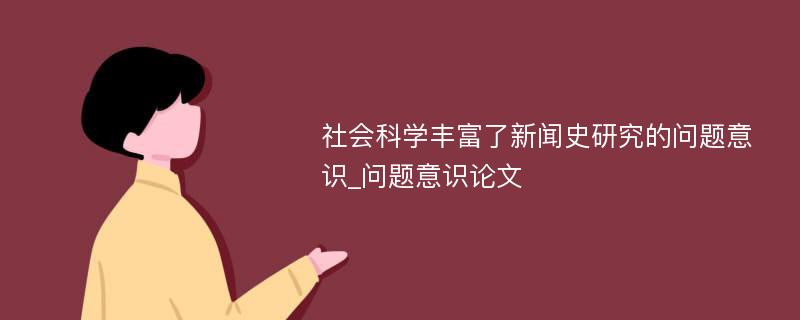
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意识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站在这儿,十分忐忑。我对新闻史有兴趣,但没有下过工夫,是个外行人。陈昌凤老师和邓绍根老师怂恿我来说些外行话,我就姑妄言之,可能以偏概全,许多观点也在其他文章或访谈表达了。我要说的是新闻传播史能够从社会科学里汲取到什么养分?这是社会科学与史学双向交流的问题。当今的社会科学往往是脱离历史语境的,不太好。但我也不是主张要把史学社会科学化,史学本身有本身的能动性,不是为社会科学而服务的。重要的是怎么从社会科学里面得到启示,有助于史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推进。 我对一般新闻史的写作有三个印象。第一,缺乏问题意识,材料如何取得,信度、效度和代表性如何,交代不清,甚至没有交代。第二,叙述单线条,不从多视角看问题,也不多方求证。有时更先有结论,再找例子权充证据,实在缺乏说服力。我在阅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既有正史,又有笔记、日记、通信、家谱、墓志铭,旁敲侧击,层层推进,直捣问题的核心,感觉有柳暗花明的乐趣。历史研究者必须向前辈学习考据的能力,并适度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第三,我不喜欢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这些话语尽是想当然耳,与材料未必有关联。我对“进步的”、“反动的”这些词语特别反胃,貌似进步的可能是很反动的,貌似反动的可能是进步的。人是复杂的,在各种情景下有不同的表现,不能先入为主戴帽子。我告诉学生多分析、少议论,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中国注重直觉的智慧。常有精辟的结论,有好的洞见,却不太交代推理的过程。因此有轮廓,但缺少细部的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则重分析,连结概念、逻辑和证据。每篇文章有论旨、推理和论据,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较倾向于归纳法。这个题目很复杂,这里不展开来讲了。 新闻史可以向社会科学借鉴什么?首先是活络思考,丰富想象,帮助发展问题意识。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分析的主轴。第二,以若干有效的概念烛照、总结复杂而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复杂甚至矛盾,巧妙运用一些具有高度解释性的概念或理论,可以达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第三是逻辑推理,分析概念(材料)与概念(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阐述这些关系所透出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概念、逻辑和证据的有机结合。 我借余英时先生的记叙中,举两个例子说明这点。一是王国维,另一个是陈寅恪。王国维早年浸淫于德国哲学(黑格尔、叔本华、康德),又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代表当时国人对西学理解的最高峰。后来他回头研究中国中古史地,固然得益于出土文物及欧日汉学,但主要是接续乾嘉之学,发扬光大。他最成熟的著作里几乎不提康德,彷佛完全不懂康德似的。但他弟弟王国华说,王国维如无早年的西学训练,断无法创造转化,以至于对中国史学更新推进,影响了几代人。 陈寅恪早年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有志于治世界史。但回国以后捐弃故技,中年以转治隋唐政治史及制度史,蔚为一代宗师。他也是得益于早年游学的经历,精通多种外语,掌握大量史料,概念运用自如,使得史实复活。1950年代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矢言要和陈寅恪比赛史料,那不啻是要倾全国之力对付一个人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主张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视野。史学家对史学是否要有概括性有争议,但社会学家深信他们的研究既是比较的,也是概括的。我在那篇文章提出,就从具体经验材料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出发,逐渐提升抽象层次,在适当点连结文献,交流之、参考之、诘问之,这样才能够赋文化的特殊性以理论的普遍性。我的这个立场反对直接套用西方时髦的理论。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解构主义,一个是建构主义。 先说解构主义,若干海外华裔学者企图以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解构“中国性”。后现代的精神是边缘对抗中心,“去中心化”。他们认同安德森的说法,以为民族国家是个共同想象体,而不是实质的东西。例如一位印尼出生的华裔学者在澳大利亚教书,有一天碰到从中国大陆移民的出租车司机,司机问这位教授明明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讲中国话,又安慰她说中国入学讲中国话不难。她不领情,写了一篇文章切割自己和中国的关系,解构她的中国性。类似例子有不少,不赘举了。身份认同是个人的事,但“中国性”不是随个人意志解构得了的。葛兆光先生说,不能低估“汉族中国”的延续性及其文化的同一性;中国的边缘可能是移动的,但至少汉族的中原和中心却稳定的,在宋朝已经形成近乎民族国家的状态了。 另一个例子是水中倒影的建构主义。不光是中国学者套用西方理论,外国学者也套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史。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家们研究早期的《申报》、《点石斋画报》以及上海小报,结论是它们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共同体”。当中有学者研究专登闲言闲语、名媛、名妓的小报,这个癖性研究有趣,但她偏要提升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我实在看不到当中的逻辑联系在哪里。他们把“公共领域”界定非常浮游宽松,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这是理论先行,逻辑跳跃,削足适履,脱离历史语境。 我觉得还不如采取莫顿“中距离”的分析路径。与其套用“公共领域”的宏大理论,不如降低调门,问一连串“中距离”的问题:上海兼具西方殖民主义、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中国现代化前沿、以及外国租界地的特性,如何形成早期报业?上海为何是中国报刊中心,其经济基础何在?各报竞争态势如何,企业化与发行网如何建立?报人的阶级性与读者的社会分层如何?严肃大报与娱乐小报如何互动?鲁迅常从娱乐小报找材料,然后在《申报》撰文骂人,他的论敌也在小报上回骂。这些都需要一点一滴的材料,不能想当然,更要从材料衬托出其中的意义。其实,我们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基本理解都还很粗浅。 我再举两篇习作,说明受社会科学暗示做新闻史研究的尝试。一篇是我和密苏里大学张咏教授一起合作的,分析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为何势如破竹,移植到中国一点儿障碍都没有。中国人一讲到新闻教育就会想到密苏里。第一个问题:美国精英大学(如哈佛)看不起新闻教育,密苏里在1908年成立新闻学院,为何十年内北大蔡元培、徐宝璜、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就成立新闻学会?我们认为中国知识领袖以新闻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何以见得?美国新闻教育背后的精神是进步运动,进步运动发展出美国新闻界的扒粪运动,其改革精神符合五四运动“德先生”的呼声。进步运动也鼓励美国的海外扩张。第二个问题:为何这种范式这么容易转移?“范式”牵涉两部分,一是理念,二是操作。密苏里提倡的理念是新闻道德、新闻伦理,中国知识领袖认为切中时弊;在操作方面,密苏里强调动手做,这是不难学的。 第三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的地位高得多,它的新闻学院只迟密苏里四年成立,为什么密苏里在中国一枝独秀?那必须归因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创院院长威廉斯的传教士精神。他一辈子访问中国五次,当年坐船来中国一趟要多久,他一来就呆上几个月,《申报》还可以读到他当年演讲的报道。他的学生也来中国驰骋,30多名密苏里毕业生在中国做记者;威廉斯把中国学生带回美国,他们从密苏里回来创办各种新闻系。他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在美国募款。许多学校的课程都仿效密苏里。美国其他新闻学院的创始人也深具人格魅力,但他们心不在中国。 接下来,我们又举出若干旁证,以支持以上的分析。其一,派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的掌门人,在燕京大学当客座教授,对燕京社会系影响很大。但威廉斯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影响之大,无有出其右者。其二,在密苏里拿学士、然后到哥伦比亚拿硕士的中国学生,回国后自称是“密苏里帮”,而不说是“哥伦比亚帮”,耐人寻味,个中原因就不多说了。其三,威廉斯在中国演讲时,胡适为翻译;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华时也是他当翻译。胡适名满中国,愿意为威廉斯效劳,不也佐证知识领袖寄望以新闻改造中国? 另一篇是《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前面说过,历史不是为社会科学服务的,但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的习作受到社会学的暗示,尽管我没有把生硬的社会学名词或理论塞到里面去,却是以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时代变化与个人选择的交光互影。我一向对改朝换代的众生相感兴趣,大时代提供场景,个人做出什么选择,付出什么代价?除了了解这三个人的记者生涯与处境,我想以小见大,提供现代新闻史乃至政治史的侧面。触动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易地易时而处,我会做出什么选择?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主观客观互相渗透,所以这篇文字有我个人的寄托和影子。这三个记者代表不同意识光谱与时代背景,我从中探讨记者与报馆的关系、报馆与时代的关系以及记者与时代的关系。换言之,撑起这篇文章的是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个人能动性与结构制约之间如何交涉?这个初步尝试,尚不成熟,要努力的还很多,敬请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