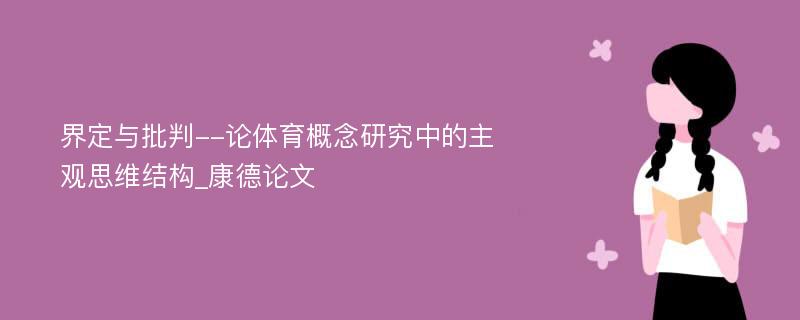
划界与批判——论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思维论文,概念论文,结构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义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观”与“Sport大体育观”是我国体育界人士伴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围绕着体育概念问题进行学术探讨而形成的两大思想流派。这两派学术观点长期以来针锋相对,无法调和。在对体育概念问题持续争论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尚未见有人从哲学“真”、“善”、“美”价值领域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两种体育观是在同一个价值领域探讨体育概念问题的吗?
对这两种体育观,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我国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争论只是围绕着几个术语概念进行的,但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1]。最近随着持“大体育观”人士提出“用汉语拼音‘tiyu’作为‘体育’总概念”这一新观点[2],更进一步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是准确的。这一新观点充分表明,国人目前对“体育”的理解,已完全融进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体育”一词已成为一个“直觉语词”,已是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产物。
在“近世第一大哲”(梁启超语)康德的墓碑上,铭刻着出自康德的这样一句人类思想史上气势磅礴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句格言表明,康德是把自然律看作与道德律等同起来的东西,自然与本体,知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真与善是同样神圣互相独立的两大体系。从哲学的视域说,这两者分别涉及到的是人的两种根本能力——认识能力与道德行为能力。我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也曾明确指出:“真的命题说它美似乎是废话;善的行为说它真似乎也是废话。”由于中国体育界的学人们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儒道互补”、中庸思想的影响下,在其哲学思维发育阶段缺乏一个对思维与存在、知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严加区别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阶段”,因此,许多学人撰写的研究体育概念的文章,常常把诸多审美道德实践层次的问题,当成理论性的问题来探讨。当我们今天对这场学术争论作一番东西方哲学文化审视时,在从科学认知价值领域对这两种不同的体育观作一纯粹理性分析后可以看出,今天首先应该被遗弃的、成为牺牲品的,恰恰是那些超出理论领域进入实践道德审美领域中的,混淆了界限,本不该被提到科学认知价值领域中来讨论的问题。因此,划清界限,确立一种从事学术活动所必需的主体思维结构,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体育概念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 两种体育观与两种主体性思维结构
1.1 “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
经过考证,深深觉察到,我国体育理论界目前之所以出现对体育概念研究的这种窘境,主要是由于争论双方分别采用两种迥然不同的主体性思维结构,在不同的价值领域中来探讨体育概念问题而造成的。“真义体育观”讲分析、重逻辑和正的方法,主张研究体育概念应从科学认知价值领域用“可以言说”的精确语言来探讨、解决体育概念问题,强调体育概念术语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体育(PE)不是竞技、运动、消遣、娱乐、比赛、金牌,体育不是sport,体育的真义是健身的教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强调指出,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与作为身体娱乐文化活动组成部分的竞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竞技和体育不同一个层次,竞技教育跟健身教育或体质教育(体育)是同一层次。这为人们在实践层次实施健身教育和竞技教育奠定了牢固的理性认识基础;而与其对峙的“sport大体育观”则讲综合,重直觉和负的方法,主张探讨体育概念应从美学和伦理价值领域,用一种国人所喜爱的“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语言来探讨体育概念,强调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认为体育就是运动、竞技、娱乐、消遣、比赛、金牌,体育就是sport,并明确指出竞技运动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不仅如此,还进一步指出,sport不仅是体育,而且是包括了PE的“大体育”,强调指出PE体育观是一种“小体育观”,认为这种“小体育观”已经过时,即将“消亡”,必然要被“sport大体育观”所代替。在这一学术观点的影响下,“竞技体育”、“娱乐体育”、“休闲体育”、“体育教育”、“棋牌体育”、“麻将体育”之说流行全国。其中又以“竞技体育”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彻底解决多年以来悬而未决的这个学术难题,必须深入到哲学思维层次,从语言与思维角度加以综合分析,并着重从分析材料和语词概念转向转变思维方式。
1.2 知识主体结构与伦理主体结构
徐复观先生(现代新儒家开山熊十力在港台的三大弟子之一,另两位是牟宗三和唐君毅)曾指出:“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文化问题。”因此,要对持续争论了多年的体育概念问题作出“最根本”的思考,就必须深入东西方哲学文化层次对体育概念问题作一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人类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渊源于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与滥觞于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哲学与文化,是在相对隔离的特定环境下(如,中国的地理属于封闭的内陆整体型地理结构,而古希腊的地理属于开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结构)发展起来的,在当时就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中国古代哲学家始终把伦理道德政治放在首位。在方法论上多用具体的事物代替抽象的概念,用叙述道理代替逻辑推理;而希腊哲学家多讲宇宙论等纯哲学问题,把宇宙论、认识论与伦理道德和政治相分离,并把伦理道德和政治放在为宇宙论和认识论服务的从属地位。在方法论上多用逻辑推理、演绎、判断和求证等方法。因此,有人称中国哲学为伦理道德型哲学,称西方哲学为知识科学型哲学[3]。这些特点与倾向集中表现在哲学思维层次方面。西方重分析,讲究逻辑思维;中国重整体,讲究直觉思维。
纵观中国近2000多年的思想史,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其实只有3家:儒、法、道。东汉之后,又增加了释家(佛家)。所以,贯穿中国2000多年漫长历史,真正构成了中国人可选择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这4家,这也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做出的选择。虽然在先秦时代,墨家亦曾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墨家思想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统治者的视野,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而长期被中国后人所遗忘。
虽然这4家的思想各异,但在反智和愚民方面却是特别一致。这突出表现在思维方式上,都推崇直觉思维,而轻视西方哲学家以探求客观自然、追求科学知识所惯用的逻辑思维。在中国先秦各家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墨家有对逻辑问题的探索,而占据中国思想主流的这4家均与逻辑无关,他们的思维方法基本上都是直觉思维的独断论,而根本不关心思维规律本身。黑格尔在这点上对中国人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他说中国人事实上“无哲学”。因为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思考,首先就是爱探索人类思维自身的规律——逻辑。
在这4家中,最突出的自然还是儒家,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加之,隋唐之后兴起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获得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进行垄断性教育和传播的专利。由于儒家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及其所起的主导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哲学文化层次上来审视体育概念研究中最为焦点的一个问题——“sport——体育”问题,儒家的这种注重实用理性的讲情感的心理——伦理主体性思维结构,是导致“以竞技(sport)当体育(PE)”的最主要思想根源。下面着重对儒家的这一思维特征作一剖析。
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关于伦理的学说,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旨在维护种种关系的学说。梁漱溟老人讲:“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在人伦关系上面去了。”伦理之网裹住了中国人的一生。我们动辄讲儒家是理性主义,不去细究的人一听而过,把儒家当成了直觉主义的对立面。这是很大的误会。所谓儒家理性,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实用理性的伦理型思维。“所谓‘实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4],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做抽象的玄思。因此“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4] 而西方哲学上的理性是对本体进行逻辑的、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为科学最基本的一个原则要求“是什么就说什么”。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不在此。这主要是因为儒家理性不含这一点。儒家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直觉主义之上的,当它在宣扬伦理的理性时,在哲学上恰恰是非理性的。
把“sport”当“体育”,以“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而且又把“竞技运动(sport)”仅仅理解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比赛”。这种狭隘的急功近利的认识,就是这种实用理性的伦理型思维在当今体育界的最具体表现。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极不科学的术语——“竞技体育”。
当血缘、心理、人道、人格(构成儒家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大因素)形成了以实用理性为整体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时,当伦理型思维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维模式时,种种弊端便在所难免。正如李泽厚[4] 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强调人世现实,过分偏重与实用结合,便相对地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使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辨的兴趣爱好。而没有抽象思辩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一点今天特别值得注意:必须用力量去克服这一民族性格在思维方式上的弱点和习惯。这一弱点与孔学有关。”伦理型思维使科学不能独立,失去科学应有的纯洁性,还可能导致已经发现的科学走向没落,并可能导致伪科学。它导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泛道德主义。所谓泛道德主义就是把人间任何事物都置于道德观点之下来作评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源远流长的泛道德主义,衍到今天已成泛政治主义的根底。因此,我国著名学者殷海光先生(金岳霖先生在台湾的弟子)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曾说“董仲舒这个人是使中国文化法力无边的千古罪人!”(2002年上海三联书店第283页)如果说,在漫长的文化史中,中国创造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人伦之学,即人生意义之学,那么西方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却创造了以两希文化(希伯来和希腊)为代表的神学和哲学。而贯穿西方学术思想并使之不断进化的东西,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少的东西,这就是逻辑。西方逻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到西方中世纪之末,是演绎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之前,是归纳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康德开始及其后,是直觉逻辑革命及发展阶段,直到维特根斯坦,逻辑被引向停滞和退行的语言逻辑(哲学)而告终[5]。西方的科学理论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强大优势,与其确立的这种讲逻辑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密不可分。
西方哲学界把18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在这个世纪,不仅产生了卢梭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之说,而且诞生了一位哲学巨匠——康德。黑格尔曾概括说“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康德的三大“批判”为我们从哲学视角划清“真”、“善”、“美”这三者界限提供了极好的答案。《纯粹理性批判》针对着形而上学(关于“真”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针对着伦理学(关于“善”的问题),《判断力批判》针对着美学(关于“美”的问题)。这三大“批判”,实际上也是康德在哲学研究中一直要致力解决的这样3个相应的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这3个问题,综合起来也就是康德哲学所关心的最终一个问题:人是什么?[6]
康德把人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理性的理论应用)和实践理性(理性的实践应用),并认为前者关涉认识问题,后者关涉人的一般行为的基本法则,也就是道德法则,当道德法则关涉理性存在者自身的行为时,就是我们理解的道德原则,而当它关涉行为的外在关系时,在康德那里就是法的原则。康德一方面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保证了科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保证了自由的合法性。康德对思维与存在的这种区分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探讨体育概念问题仍具有巨大的启蒙价值与时代意义,它将结束中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道德主导型思维结构,取消它的独断论话语特权,使其回到它应在的价值领域中去,这就为知识、科学腾出了地盘。
由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从未经历过西方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分离与抗争阶段,更未经历过康德式的批判阶段,而是以先秦儒家道德独断论的方式划定的,因此,这种讲情感的建立在以心理机能为基础的中国伦理型主体思维结构,是使中国体育学术思想一直无法获得一种强固的理性分析系统,使中国体育学术主体的理性精神不够坚实,特别灵活、善变,以及特别容易走向“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源。这从大体育观50年来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况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把前苏联的身体文化与竞技当成“体育”,形成了“体育运动”——“大体育1”,到80年代把安德鲁斯所批判的三角形中的“高级竞技”、“体育”、“身体娱乐”当成“竞技体育”、“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形成了“Sport大体育”——“大体育2”,以及最近又提出“用汉语拼音‘tiyu’作为体育总概念”的主张。在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的是学术问题政治化、情绪化或情感化,总是很少见到“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学术对话,却不断上演“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现实冲突,而各种知识体系在其中所承担的也不过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把理论问题降为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对体育概念这一纯学术理论论争,常常变为意识形态上的“你死我活”或“攻占阵地”的政治斗争。如在体育概念研究中,许多体育界学人在探讨体育概念时,只是用自己的“经验”去批判对方的“价值”,或者为了维护自身的“价值”而否定对方的“经验”。其真实用途正如古人所说,攻击汉学的人,并非真要攻击“汉学”,而是要批倒那些研究汉学的学者。这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痼疾,同样异常明显地表现在当今一些体育界学者身上。《谈我国体育体系的根本性大变革》、《走进体育语言——对体育与竞技思维混乱问题的认识》被无端上纲上线加以评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用行政手段制止、干预对体育概念的争议,就表现出这种伦理主体性思维结构的劣根性。如果不对这种实用理性的伦理型思维方式加以纯粹理性批判,对体育概念的争议将难以彻底消除。
2 在科学认知价值领域用科学语言解决体育概念
经过研究,现在已充分表明,无论是“用sport作为体育的总概念”,还是“用‘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都表明“大体育观”不是科学认知的产物,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独断论的产物(尤其是其中的实用理性的伦理直观,同时包含有强烈的政治因素)。在这里,不管是用“sport”,还是用“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都已经没有任何科学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只有审美道德伦理价值和意义,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具有审美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已。在对体育概念持续争论了多年以后的今天,随着“用汉语拼音‘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这样一个最新观点的提出,实际上等于持有“大体育观”的人士自己从科学认知的角度上宣布了风行我国体育界多年的“sport大体育观”理论已彻底破产[7]。
由于问题主要出在哲学思维层次,特别是出在康德的“先验观念”领域,因此,当我们在进一步探讨体育概念时,首先就应该从传统的心理——伦理主体思维结构的经验批判方式中挣脱出来,以便清理出一种作为真正精神生产创造活动所应具有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并从真、善、美这三大价值领域确立一个立足点。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诚然,体育应该是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完整体现。但从中国体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从解决人的认识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我们在探讨体育概念时,首先,而且必须从探讨体育的“真”入手,而这就必须从科学认知价值领域来解决这一问题。
要谈体育的“真”,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应用什么语言来谈论这一问题。唐君毅先生[7] 曾将语言划分成3类,即科学语言、文学语言、启发语言。科学语言是一种逻辑语言,是一种用精确的语言来陈述客观事实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概念与实在现象之间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学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表达虚构的理想化人生,也表达人类的生存情感和美好愿望;启发语言则是一种暗示语言,启悟道德、宗教、形而上的那些东西。
西方哲学由于历来强调应用明晰的“可以言说”的科学语言对概念下定义,所以科学理论在西方得以昌明发达,现代化得以在西方率先实现;而中国哲学由于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天人合一”,审美直觉,中庸之道,讲究实用,或者说只重视文学语言和启发语言,而不重视逻辑和科学语言,因此,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就是说没有理论科学,它的科学都是技术科学,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注重实用的伦理型思维方式,在体育概念研究与理论建设中也表现得异常明显。
唐君毅先生对语言的分类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讨论体育概念问题时,在确定要解决体育的“真”这一前提下,首先就应对所使用的语言有所限制或指定。显然,从中国体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而且也只能用科学语言来谈体育概念问题,而不应该,也不能用文学语言和启发语言来谈这一问题,更不应该用脱离中国体育和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什么“后现代主义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来谈这一问题。实际上我的这一观点,也正好吻合于维特根斯坦那句著名的哲学名言,即“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讨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8]
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8] 有如下观点,“人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获知语言逻辑”、“语言掩饰着思想”、“逻辑是先验的”、“逻辑的探究就是对所有符合规律性的东西的探究。逻辑之外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很清楚,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维特根斯坦所指的“可以言说的东西”,绝不是指在伦理和审美价值领域,也不是指“日常语言”,而是指在科学认知价值领域,能够符合真正的逻辑形式,具有真值的事实语言,也就是科学语言。强调用维特根斯坦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日常语言”来研究体育概念问题[9],都是混淆了“真”、“善”、“美”价值领域,以及“可说”与“不可说”语言界限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哲学界对他后期的哲学评价大不以为然,并不像国内有些人士所推崇的那样。维氏后期自己也坦言,“哲学的问题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他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5]。他的老师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就说道:“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没有找到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然而,今天我们却有人用这些被人遗弃的东西来研究“体育”概念问题,这对原本理性思维资源就极其匮乏、尚未彻底接受启蒙思想启迪的诸多体育界人士来说,是极其可悲的。
由于以严密的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真义体育观”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可以“言说”的科学语言,在科学认知价值领域来探讨体育概念,因此,笔者一直对“真义体育观”持支持与赞赏的态度。虽然这种观点至今仍让大多数体育界人士感到不习惯、不可爱,但它的确令人可信。反之,“sport大体育观”虽符合大多数中国体育界人士的思维方式与习惯,但由于这种观点是用一种“不可言说的语言”,是用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独断论的方式在伦理美学价值领域来探讨体育概念问题,因此“大体育观”虽让人感到亲切、可爱,但它由于缺少“真义体育观”精确语言的“洗礼”,因此,这种体育观难以令人可信。尽管持“大体育观”的人士在探讨体育概念问题时说了许多,但其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说”,是“不可探讨的东西”,因此持有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士,在今后探讨体育概念问题时,就“必须保持沉默”。
而眼下在以“sport大体育观”为主导的中国体育界,体育语言却被搞成了一个语言迷宫,成了一种“你不说我反而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的“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语言。有些体育学者总用一些令人只能意会的语言,来构建一座座晦涩难懂的迷宫。用这种“不可言说”的语言撰写的许多专业文章,常常概念模糊、论证乏力,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追问,仅以情感辞藻的语言迷宫来打动和迷糊读者。因此中国体育要实现科学化与现代化,首先必须走进语言,应该确切地、科学地使用语言,应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加强体育语词概念的规范化研究工作,因为这是从事真正的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体育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直觉、情感、非理性、后现代化、自然语言和“大体育”,而是逻辑、科学、理性、现代化、科学语言和“真义体育”。中国体育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还有一段艰难和漫长的道路要走。中国体育现在最需要用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和科学语言,来对目前体育界的这种思维和语言混乱现象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礼”。
3 弘扬逻辑,建立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
眼下体育界的学风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严重关注。老实地说,体育学术界诸多的“假”与“伪”,在注重科学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学风下,是不会有什么市场的。而逻辑受到“冷落”,与整个体育学术界在立论、创说、评判、辨伪等学术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重逻辑、不合逻辑以及逻辑贫乏以至于无知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体育学术界与其“打假”,不如弘扬逻辑。
弘扬逻辑,就是建立一种讲逻辑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就是把一种不够坚实、特别善变、灵活,承担着政治任务的情感心理——伦理型主体思维结构,转变为一种坚实、稳固的讲逻辑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这是因为,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结晶。学术不能没有思维,思维不能没有工具。而逻辑则是学术理论建设的唯一工具,它是理论的筋骨,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清扫文字垃圾的“铁扫帚”和“破冰船”。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所以弘扬逻辑的目的就为了发展理论。因为,理论不是说法,不是看法,更不是想法。理论就是一套逻辑体系,是一套可供证明、证伪、推演和预测的逻辑系统。
常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没错。但须知,实践只是检验理论功能和作用的标准,而逻辑才是检验理论真伪或者能否成立的标准;实践验其结果,逻辑验其结构,因为逻辑是体,实践是用。而理论的检验必“先观其体而后察其用”。“体”之不存,“用”之焉附?因此,逻辑上成立与否是鉴别理论的核心所在,逻辑是理论成立之“本”,而是否与现实实践相符,则是其“用”。
目前风行欧美学校的“健身教育(fitness education)模式”和“竞技教育(sport education)模式”,就是应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具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两种主导型体育教学模式。《体育原理》(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竞技教育学》(1999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体育工作者思维方式亦已日趋于科学化与现代化。
标签:康德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体育价值论文; 主体性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中体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