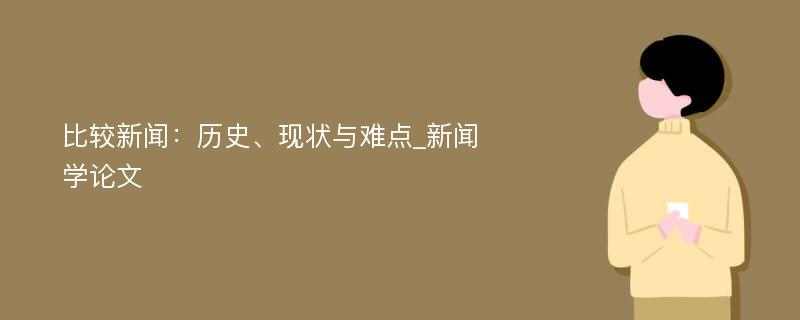
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难题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百年比较新闻学回顾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建立首先应归功于以佛雷德·塞伯特为首的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注:Fred S.Siebert,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uramm (1956),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Urbana: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国内一般将此书译为《报刊的四种理论》,但原书名中的Press一词内涵实际比“报刊”宽泛,它还具有报刊作为新闻企业的含义,故作者以为采用“报业”比“报刊”更准确。)。该书使人们对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首次有了全球的观点,说它是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并不过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学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这个窠臼。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早期,理论研究的先锋们曾试图对特定国家的媒介进行研究,那时的媒介当然只有报纸。从20年代起美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报纸的研究,较著名的篇什有帕特森的“中国的新闻业”,Y.P.Wang的《中国本地报纸的崛起》,庭坡罗的《中国新闻业的发端》,白瑞德的《中国的期刊报纸:1800-1911》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一国学者对另一国媒介的观察,但已初见比较新闻学的端倪。此后,比较研究的范围随着交通、资讯、科学的日益现代化而扩大,从单一国家扩展到洲际国家,又逐渐产生了对全球媒介的综合透视。1928年,意大利帕鲁扎大学政治学院首开比较新闻学课程。1935年,日本学者小山荣三在其著作《新闻学》中专辟章节讨论比较新闻学;而小野秀雄的《国外新闻史》则是比较新闻学的专著。
但是,比较新闻学羽翼未丰便很快进入到一个死胡同。这是个生命力先天不足的婴儿。60年代这个领域是沉寂的。70年代,英国的报刊史专家安东尼·史密斯的《报纸:世界的发展》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进程,到底在比较新闻学上涂了厚重的一笔。遗憾的是,在整个10年中,西方国家的比较新闻学并无其他重要著作问世,史密斯的大作不免有些形单影只。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前后是各国之间关系最微妙而严峻的时期。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曰西方和东方,正处于冷战期。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融。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比较新闻学的步伐沉重而迟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当国际大变动开始,当东西方的政治关系松动时,一个小小的繁荣期就出现了。1981年,吉姆·理查斯坦德和麦克·安德森率先写出一部研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信息流动的著作《世界性的危机:政策和展望》,这部书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地的传媒研究者特别是比较新闻学者的士气。1983年,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问世。该书将世界传媒按社会状况分为三个领域: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并将新闻学中的一些重大概念拿出来比较鉴别,比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的功能等。此书可谓系统比较东西方新闻观念的开山之作。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翰·迈瑞尔的著作以一个惊人的标题命名:《环球新闻业:一个对国际传播业的考察》。迈瑞尔的研究保持了与马登等研究者同样的风格——不去玄而又玄地死缠理论,而将讨论集聚在几个重大概念上,比如:哲学、社会制度、新闻自由、新闻理论、新闻管制以及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此书自1983年问世后一版再版,长盛不衰,其1995年版本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有关前共产主义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新闻业在历史变革中的最新情况。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出发,更加精确地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在西方,首次以“比较新闻学”为题的著作恐怕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艾文森教授等撰写的《比较新闻学》。这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将世界报业一分为三:西方世界、第三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该书收进了许多重要文章并有大量实例研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比较新闻学丰收的年代,那末90年代这项研究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传媒空前交融出现了理论家们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这使研究者们需要静心观察一下再作出理论概括。
中国新闻业是步西方后尘、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中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斗争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开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到1979年为止,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新闻业和国家的其他事业一样,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至此,源与流被断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80年代的台湾出现了李瞻等学者撰写的一批比较新闻学著作,但由于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这些著作还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不久,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大陆恢复了和世界的接触。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被认为是有用的,于是,介绍西方国家新闻媒介状况的篇什陆续问世。
从90年代起,中国比较新闻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成果。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4)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7)将中外新闻理论、文化、业务三方面的异同加以对照;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1999)简括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观念等方面作了比较。从方法上来说,以上著作基本是平行展示、资料编辑整合,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共同的弱点是理论辨析稍嫌不足。相对来说,樊凡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1994)倒有一种独辟蹊径的突破。该著作运用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有些牵强,但该著作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专著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作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严谨;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一部分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漠视甚至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凡此种种,当应改进。
总的来说,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艰难的开创阶段。摆在人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从平行展示、资料排列演进到理论的整合与重建,从而创造出系统而科学的比较新闻学。
意识形态的敌对和学术领域的宽容
一个需要反复揣摩的问题是,为什么发轫于20世纪初的比较新闻学直到80年代才开始出现繁荣?回答几乎是不加思索的:是因为东西方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从4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明显对峙,不仅限制了各国实际的接触,还阻遏了双方思想意识的交流。在西方,共产主义曾被当作洪水猛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一律遭到禁止。一些曾经报道过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在政治压力下甚至无法在本国生存,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斯诺,就不得不客居瑞士;《纽约时报》进步记者爱泼斯坦也在政治压力下来到了中国;《时代》杂志的白修德则被多次吊销护照。反过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情景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的书刊报纸一度被禁止传播,不允许“偷听敌台”。在这种情形下,东西方之间连思想都无法正常交流,又遑论互相比较?
冷战以来双方的敌对和隔绝使西方学者无法真正接近中国,从而看清其真面目。前美国驻华记者、明尼苏达大学东亚系教授爱德华·法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出“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历来是混乱不清和充满矛盾的,而冷战使本来就混乱不清的图画变得更糟”。(Farmer,1994)。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波尼·卡博认为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并未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公众。(李希光,1999b)
在中国的记者的眼中,美国的情况一度也是灰色的。1980年,人民日报在报道美国电影时说:“美国的电影电视正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极度空虚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带有毒素,对社会起了腐蚀作用……”(人民日报,1980年3月11日)。
然而20年后,当北京的观众起劲地为《泰坦尼克》和《拯救大兵瑞恩》叫好时,各大媒体的主导倾向也是对美国电影的一片赞美。“毒素”和“腐蚀”似乎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
美国印地安那新闻学院教授大卫·亚当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媒体冷战”,一方面,美国传媒追随了政府的“遏止中国”的政策,在人权、台湾以及西藏问题上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介“抨击美国”、“反美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他呼吁,“大洋两岸的中美新闻报道应当改善”。(亚当斯,1998,pp.16-17)
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一部分记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都是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报道新闻而只是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记者则认为西方传媒虽标榜客观,却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水火不能相容。
在实践上,西方的强盛使它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在新闻传播上也压东方一头。在1985年的一次世界新闻会议上,学者瑞门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流动,80%以上是从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传媒中发布的,而占世界2/3以上的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发布的新闻仅占10-20%。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们曾指责西方的“新闻帝国主义”,批评西方新闻媒介在新闻中只报道发展中国家政变、灾害、落后等“负面新闻”,从而诋毁了他们的形象。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便与西方抗衡,力争新闻流通上的平等,强烈要求西方媒介报道的公平。这股潮流被称为“世界新闻和传播的新秩序”。这个呼声贯穿了整个70-80年代。(Raman,1985,p.3)
打破东西方(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坚冰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和美国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当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当东方国家越来越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东西方思想的交流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一个迫切了解对方的时代已经来临。东方会见西方,西方会见东方,双方终于伸出了阔别多年的双手。
就中国来说,它和西方恢复媒介交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一项文化交流协议,由墨尔本《世纪报》派出一个小组来帮助中国首家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这是1949年后,中国的报纸第一次被注入西方的血液,它的版面设计酷似西方报纸。《中国日报》前任总编冯锡良采用西方报纸通用的大照片,赢来国内新闻界一片叫好,冯因此而荣膺“总编辑慧眼奖”。《中国日报》对中国新闻界的冲击是巨大的,起码人们看到:西方的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同年,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闻界。同行们开始了坦率的交流和对话。这是建国以来中国与西方新闻界最密切的接触之一。几乎在同一期间,新华社邀请国际新闻组织“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基金会”为国内培养英语新闻写作人才。此时,西方新闻理论和业务直接进入森严壁垒的中国新闻界。中国记者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软新闻”、“硬新闻”、“新闻价值”……,冲击同样是巨大的。近年来,中西新闻学者持续互访,在交流中,双方更清楚、更系统地了解到各自的观点,以较平和的态度讨论新闻学面临的问题,敌意和偏见在逐渐减少。所有这些都为比较新闻学奠定了客观基础。
当政治上的冷战结束后,媒体冷战也缓解了,亚当斯教授的研究发现,最近一些年来:“《纽约时报》发表了无数有关中国改革的报道,它告诉读者,在世界历史上,很少哪一个国家像过去20年中的中国一样如此迅速地变化和发展……”(亚当斯,1998,p.10)。
尽管在新闻实践上,东西方的媒体反应仍然随着政治形势左右动荡,反复无常,然而,双方的确都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国家,人民都需要准确、平衡的媒体信息,为了这个目的,媒体冷战应当结束。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在现存的比较新闻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双方从冷战时期继承过来的敌意、成见和偏见往往会表现在学术讨论中。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迈瑞尔在其研究著作《环球新闻学》中武断地说:“人民日报没有幽默成分,没有文娱消息,也不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Merrill,1983,p.123)。其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体育版和文艺版是人民日报多年就有的传统版面。虽然这张党报以正面宣传为主,但有时批评和异见之声也还是发表的。在西方著作中,类似迈瑞尔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不在少数,更多的偏见被精明的学者们巧妙地掩藏了。虽然,成见和敌意是铸成错误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盲目批评西方新闻事业弊端的情况可能更普遍。在很多情况下,滥批一通西方,不仅能躲避麻烦而且能令大家拍手称快。这种不科学不严谨的学风,导致一批伪劣产品充斥书架。
简单化倾向
简单化是中西新闻比较的一大障碍,它也是敌意、偏见、成见的结果。西方多将社会主义中国的传媒归于“传声筒”和“宣传机器”,极大地忽视了对方的新闻功能。中国对于西方也同样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传媒有关的研究大都以鞭笞批判为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批研究生的某些学术论文可以为例,一些研究者的结论不是证明资产阶级记者“已经成为美国垄断机器的组织成员”,就是暴露“西方客观报道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虚伪性”……90年代中期,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分析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时说:西方国家传播活动表面上确实存在新闻自由……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媒介的报道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有闻必报。……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新闻媒介有自由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这种自由有其局限性的一面,虚伪的一面”。(《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8,p.401)。
说“确实存在”,又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就很难自圆其说。现象一定是本质的某种反映,这是起码的哲学原理。说西方传媒报道自由有一定限度这种概括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绝对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并未宣称他们的自由是无限的、绝对的,事实上,大多数西方记者仍然在为他们的新闻自由而不断奋争。
将某种东西加以错误的概括、不展示被批判方的全貌、曲解之后再加以评驳,这是学术问题简单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比如,在一本比较新闻学著作中,作者在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中说:
……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并没有超脱权利的制约而享受到“绝对自由”。恰恰相反,在当代,新闻媒介正在走向集中,正在受到垄断集团和政府权利的严格控制。(刘夏塘(编),1997,p.45)
然而,作者并没告诉读者“绝对自由”的出处。人们会问,究竟哪个西方媒介说它享受到“绝对自由”了呢?作者在讨论西方的客观主义时说:
……比如美国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撰写新闻……(刘夏塘(编),1997,p.55)
将一部分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概括成全部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观点,这种非科学的方法是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凭据的。
在许多敏感的问题上,一些人常常以“阶级性”划一道鸿沟,以“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指斥作为尚方宝剑匆匆结束讨论。立场是鲜明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西新闻的许多关键问题如新闻自由、客观性等多年来仍然是雾中看花,悬而未决。
简单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论据和引述没有出处。比如,一位研究者曾引用了如下例子:
……几年前,美籍华人赵浩生到中国访问后,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文章,但报社把这篇文章退给了作者,理由是:“你这篇文章都说中国好,要是能骂中国,我们就可以采用。谈起这件事,赵浩生颇有感触地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刘夏塘(编),1997,pp.44-45)
这个没有出处的引用很难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此外,作为重要论据的引用应是那些能进入学术视野的分析和论证而不是被引用者即兴、随意的言谈。
简单化使研究浅簿、没有说服力而最终失去学术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中国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进行”的。(孙旭培,1999,p.4)在《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一书中,为了展现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作者例举了《纽约时报》中一些“妖魔化”的报道来说明问题,但该报同时期、同一题材的某些比较平实的报道却被略去不提……此外,作者展现的“妖魔化”报道在有些关键地方的翻译上没有忠实反映原文风貌,比如其中一篇报道中的原文是:
Ever since NATO bombs hi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last Friday,China's state-run media have dished up a ceaseless stream of banner headlines and jarring photos...(NewYork Times,May 14,1999)
作者的译文为“……,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不停地展示鼓动人心的通栏大标题和照片……”(《妖魔化与媒体轰炸》,p.94)
原文中的"State-run"(国家经营的)本是中性词,但被翻译成中文时译者使用了贬义词“操纵”,于是报道就成了“妖魔化”。这种随意性不仅难以服人,也有欠公允。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东西方任何一方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逻辑都是不现实的。人们不可能要求美国新闻界去“弘扬社会主义”,正如人们也不指望中国传媒去实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一样。一个严峻的思考是:意识形态的敌对情绪是否一定要渗透到学术中去?东西方相矛盾的某些观念在学术讨论中应当如何“费厄泼赖”?激情、偏颇和脸谱化固然有煽情效应,固然可以令人拍手称快,但它不是科学,只能加深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是跨文化研究经常使用的概念,它的含义是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其中包括“对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从事跨文化研究的留美学者陈向明认为,很多学者发现人们在对他文化进行评价时通常使用一些先入为主的“定型观念”(Stereotype),往往无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大多数人对自己熟悉的文化总是有所偏爱,当别人的行为与自己的准则不相符合时,便给予负面的评价。这种以本民族文化模式为基准来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心理倾向往往使人们对异文化产生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偏见。(陈向明,1998,p.19)。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认为,用一种文化批评的模子评价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歪曲。(叶维廉,1983)
显然,在跨文化研究中首先要跨越的就是成见和偏见,而摆平这两者的惟一路径就是公平。在“公平”这个问题上历来争论不休,传统上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公平根本不存在。不过,学术上的公平并不复杂,它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之上,即,尽量准确、均衡、全面地展示对立面的风貌,而尽量避免丑化、曲解、肢解。
学者汤一介认为,“文化学术发展、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过分意识形态化”,它和政治是有一定距离、有一定的界限,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论证。(汤一介,1996,p.2)。
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种现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论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发: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o.1.,p.7)。
西方中心论、妖魔化中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权面前,东方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受压制的劣势。贯穿19世纪西方知识界的“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怀疑或漠视。这种理论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发现,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历史(乐黛云,1998,p.6.)。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中流行的“向往西方”可以看作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的投影。该理论的另一反射出现在苏联和东欧。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衰落,西方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终于实现了。用美国学者福山的话说,“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最后形式的政府取得了世界的胜利”。曾经是共产党喉舌的新闻媒介欣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和新闻价值。苏联、东欧的风暴给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思考,同时也给比较新闻学者推出了崭新的课题。
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作为意识形态前哨的中国新闻界全力抵御的结果——不过,它还是留下了阴影——在西方现存的有关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几乎都是西方学者之间的旁征博引,很少有借鉴中国大陆学者成果的。除了意识形态和语言障碍外,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漠视和轻慢。在中国新闻界内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自由化”倾向,一些学者试图比照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和自由观来对中国的新闻模式加以改造,这实际上也表现了一种推崇西方价值的倾向。不过,以上思潮都远未形成气候。
自1993年以来,哈佛大学教授亨庭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有关“文明的冲突”,引起了知识界的轩然大波。亨庭顿认为,冷战之后的非西方文明的崛起,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将取代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西方文明受到了挑战,它必须学会与非西方文明相处。一些学者认为,“文明冲突”产生的基础是西方哲学、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衰落,同时亦反映出一些人想继续维护西方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幻想。然而,在一些传媒研究者眼中看到的则是西方的一种新威胁。李希光、刘康确信,西方传媒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的报道。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强烈地反对西方遏止和文化霸权的情绪中,中国出现了一股“非美主义”思潮,其标志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其后陆续有《中国不仅仅说不》,《中国有多坏?》,《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妖魔化与媒体轰炸》等。这些作品挑战了国际霸权,激励了民族士气,在与世界进行更平等的对话的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多有启迪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情绪化、简单化的倾向。
1996年,新闻学术刊物《国际新闻界》发表的“妖魔化”理论在平静的新闻理论界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该理论试图证明“美国报人……只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人描写成妖魔”(李希光,1996,p.5)。编者认为,李文“用学术的标尺也许不尽完善,但它所提炼的“妖魔化”命题,无疑具有一种思想的烛照与洞见……”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李文有失偏颇。新闻学博士焦国标在同一刊物上指出,所谓“妖魔化中国是以偏盖全”,其逻辑“不足以证其实,倒足以证其伪”,李指责美国“专职干‘妖魔化中国的事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焦援引了《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大量美国传媒有关中国的客观报道来说明美国传媒并非“一心一意妖魔中国。”(焦国标,1997,p.39)
妖魔化问题也引起了另一个角度的思索,一些学者提出要对美国媒体、美国文化、美国的媒介理论和价值观做进一步研究,否则,就会变成“哑巴和聋子的对话”。
妖魔化问题植根于东西方之间长期的对峙中。它是不是冷战在新时期的继续须拭目以待。不过,即使“妖魔化”的事实成立,那也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在历史上,西方“妖魔化”过中国,中国也“妖魔化”过西方。有谁不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名言呢?“鬼佬”——人们至今还这样称呼洋人,这些算不算“妖魔化”?
中美之间的相互妖魔化是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处于被动的受者地位,在人权、个人价值、国家与社会的观念方面,西方一直享有稳固的话语霸权……”。(简艺,2000,p.86)。要摆脱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敌视和控制,在国际传播中长期以来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就没有平等对话的地位。从这种观点出发,有时,矫枉过正也许是必要的。
作为对美国传媒为首的西方传媒的一种当代解析,“妖魔化”正在被人们慎重的讨论。在肯定它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击霸权、争取平等对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须注意不要陷入简单化的泥沼;在抨击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要慎防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在拥抱全球化、推崇和平与进步时要警惕新的西方中心论一样。至少,妖魔化问题不应成为中西新闻比较的新障碍。
以世界经济渗透、信息与科技高度发展和融合为特点的全球化为比较新闻学带来了宏观的视野。今天,西方记者在接近中国老百姓方面已没有了昔日的桎梏;中国记者甚至可以到当年敌对的美国新闻机构中去做访问学者。国人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受西方信息而不必担心获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被打破是划时代的进步。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双方可以充分占有资料、更近切地研究对方,对于比较新闻学来说,这是一个必备的客观基础。
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是摆在比较新闻学者面前的一个课题。如果说以往比较新闻学出现的偏颇主要因为资讯不全和偏狭,那么在全球化和资讯发达的今天,创造出较高水平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而为达到这一目标,学者们既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也需要有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冷静观察与思索。全球化意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观照,但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后冷战期各民族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一方面要发展民族文化,一方面要有全球化意识,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又要积极与世界对话,为创造比较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而努力。
标签:新闻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