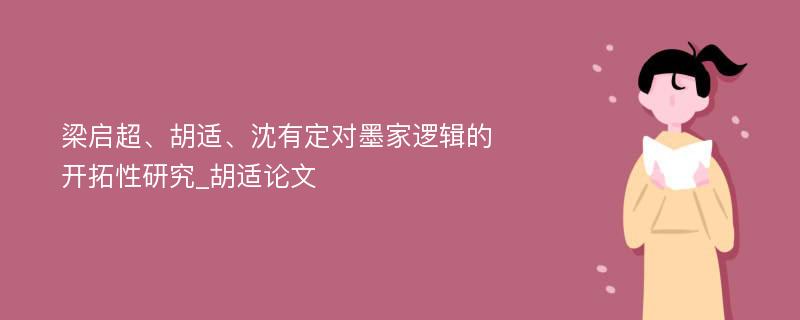
论梁启超、胡适、沈有鼎对墨家逻辑的开拓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墨家论文,逻辑论文,梁启超论文,沈有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6)01-0061-05
墨家逻辑是指中国先秦时代墨家学派的著作《墨子》一书包含的系统逻辑学说。它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光辉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典范。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从秦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中,墨家逻辑随着墨家和墨学的衰微而被埋没。进入20世纪以后,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一批具有中国国学功底的学者,凭借他们所接触和掌握的西方逻辑知识,比较解释墨家逻辑原典,对墨家逻辑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开拓性研究。
一、梁启超开墨家逻辑比较研究先风
梁启超(1873~1929年)在1904年发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试图用西方逻辑的术语来比较解释《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从而摆脱了乾嘉学派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局限,开墨家逻辑比较研究和义理研究先风。之后,梁氏又著《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对《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进行了开拓性的解释工作。这些文字或基本概念主要有:辩、名、辞、说、实、意、故、类、或、假、效、譬、侔、援、推等,梁氏将它们与西方逻辑术语相对应并一一进行了解释。
梁启超说:“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墨辩’两字,用现在的通行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梁氏把“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分别解释为西方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三种思维形式。“‘名’在论理学上叫做名词。”“‘实’是客观上的对境,‘名’是主观上的概念。”“‘辞’在论理学上叫做命题。”“以辞抒意”就是“用命题的形式表示所判断”,“‘意’字含忖度判断的意思”。命题有不同的类型,“尽”即逻辑上的全称命题,“或”即逻辑上的特称命题,“假”即逻辑上的假言命题。“说”是“证明所以然之故”。而“故”即原因。“‘效’即是法则”。“仿照那法则去做,叫做效。那法则便是所效。与法则相应的论辩,便是中效。反是,便是不中效。”梁氏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中,释“譬”为“立证”即证实,“侔”为“比较”。在《墨子学案》中,梁氏又在吸收胡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释“譬”为“譬喻”,是“用那个概念说明这个概念”;“侔”是用“那个判断说明这个判断”;“援”是“援例”,即“援子以利我”,与“譬”、“侔”相比较,“援”是“用之于推论”,“要援他所以然之故”。《经下》说:“推诸其所然于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梁氏认为,这里的“推”是“演绎归纳两法通用,总是举所已知以明所未知”,即指一般的推理,而《小取》篇所说的“推”则是指的归纳法[1]61。
通过比较,梁启超认识到了墨家逻辑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之间既存在着差异性,也存在着一般性。他说:“《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1]48“墨家论理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论法则。”[1]51梁氏认为,《小取》篇中的“或”、“假”、“效”、“譬”、“侔”、“援”、“推”,就是墨家逻辑中七个重要的法则。梁启超所说的法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论证方法。墨家逻辑在论证方式上虽然不如西方和印度的精密,但也有其相通之处。与印度因明相比,墨家论式为“辞”、“故”、“类”结构,因明论式为“宗”、“因”、“喻”结构,二者基本一致。梁氏说:墨家“名学之布式,则与印度‘因明’有绝相类处。”[2]7又说:墨家论式“和因明的三支极相类。内中最要紧的是‘因’。‘因’即‘以说出故’之‘故’。”[1]49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墨家逻辑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比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说梁启超的比较研究就是“比附”。因为“比附”仅仅是梁氏在墨家逻辑比较研究中存在的现象,而且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在尚未充分掌握西方逻辑知识的情况下进行比较研究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失误,而且也是中国人在首次将中西逻辑进行比较研究时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弊端。梁氏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今文经学得到大力倡导的时代,他校注《墨经》文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校注来阐发义理。所以,他在校注的过程中已经事先有了义理的主观认识。当然,如果事先获得的主观认识是正确的,则校注也往往十分可靠。但是,如果事先获得的主观认识不正确,校注就会生出“主观臆改的绝大毛病”来。梁启超校注《墨经》时存在的这一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例如,《经上》说:“坚白,不相外也。”梁氏从他所坚持的“经上必为墨子自著无疑”的观点出发,认为当时未曾讨论到“坚白石”的问题,于是将“白不”二字作为“旧衍”而删去。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墨家逻辑研究者所回避不了的,这说明了无论是对墨家逻辑的义理研究还是文本校注,都必须具有更丰富的知识,掌握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二、胡适对墨家逻辑研究的巨大贡献
胡适(1891~1962年)非常重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用1/3以上篇幅论述墨家逻辑。在1918年写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又用1/4以上的篇幅论述墨家的哲学与逻辑。胡适在上述著作中,运用梁启超首创的比较研究法对墨家逻辑进行开拓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逻辑是关于推理的学问。胡适运用比较研究法,着重讨论了墨家关于“说知”即推理的学说。《经说上》说:“方不障,说也。”胡适认为“这是《墨经》的一大发明。”[3]175《经上》说:“说,所以明也。”《大取》说:“以说出故。”胡适指出:“‘说’是说明结论的‘故’的。”“可以把‘说’理解为:依靠一个或若干前提的认识过程。”[4]84
围绕“说”,胡适着重解释了墨家逻辑中“故”、“法”、“类”等基本概念。《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胡适认为,“故”既可以是“物之所以然”的原因,也可以是“立论所根据的理由”。《墨经》中的“小故”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故,“大故”是完全的“故”,即“各种小故的总和”。作为前提的“故”与结论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即“故”与结论的关系正如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在胡适看来,墨家逻辑是要人研究“物之所以然”,然后用来做立论的根据。正确的结论,科学的推论,都必须用“大故”来做理由。《经上》说:“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说:“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胡适解释说,“所若而然”便是“仿照这样去做,就能这样”,“法即是模范,即是法象”。[3]184譬如画圆,可以根据圆的概念,也可以根据圆规和已成的圆形。这里,圆的概念、圆规和已成的圆形都可以叫做“法”。《小取》说:“以类取,以类予。”胡适指出,这六个字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根本方法,“凡一切推论的举例和断语,都把一个‘类’字作根本。”[3]180胡适认为,“法”、“故”、“类”三者是一致的、相通的。他说:“一事物的法就是一事物已知的,为了推论而明确表达的故。”又说:“法是一个或一类同样的事物据以形成的原型。而这正是类名所代表的东西。”[4]86例如,用规画圆,这既是成圆之故,也是为圆之法,还是一圆所属的类。《经下》说:“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如方之相合也。说在方。”胡适解释说:“凡正确的故,都可作为法;以他做去,都可发生同样的效果。若不能发生同样的效果,即不是正确之故。”[3]184胡适还进一步指出,找出事物的故、法、类,是归纳法的任务;根据已知的、被明确论述的故、类、法进行推论,则是演绎法的任务。他说:“名学的归纳法是根据于‘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名学的演绎法是根据于‘同法的必定同类’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立论之故。看他是否能生出同类的效果。”[3]184胡适对墨家关于推论的故、类、法三个基本概念及其和演绎、归纳的关系,做出了创造性的、准确精辟的比较解释和贯通说明,把握了其内在的条理。
通过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相比较,胡适看到了墨家逻辑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胡适认为,在论式上,墨家关于“效”的演绎法不是三段论而是基于类的推演的二段论。他说:墨家“演绎法的论证,不必一定用三支式。”“《墨辩》所说的‘效’只要能举出‘中效’的‘故’,——因明所谓因,西洋逻辑所谓小前提,——已够了,正不必有三支式。”[3]189“类”的原理在墨家逻辑推理中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类”概念,墨家关于“效”的演绎法“不必同时具有大前提和小前提”,“当只提到小前提时,类就作为大前提;当只提到大前提时,类就作为小前提。”[4]88就此看来,胡适并没有否定西方逻辑的三段论与墨家逻辑基于“类”的推演的二段论之间的相通性。如果将“类”还原为西方逻辑中的大前提或小前提,墨家逻辑的演绎论式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式是一致的。但毕竟在墨家逻辑推论式中,大量表现为二段论式,“法”的观念、“类”的观念都只是作为一般推论的要求。胡适进而指出,墨家逻辑虽然不重视对法式的研究,但是却“有其学理的基本”,即包含了逻辑学说的基本理论。他说:“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3]198墨家逻辑的优点主要体现于对逻辑理论和思想的阐述上。这些见解都是十分可贵的。
总之,由于胡适对西方逻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能准确抓住逻辑主要是从推理方面来研究思维形式这一重要线索来考察墨家逻辑,从而对墨家逻辑文本中有关推论的许多条目做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国逻辑断代史专著,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6]400需要指出,胡适把墨家逻辑在论式上的缺乏和不足说成是墨家逻辑的优点,这是不正确的。胡适在墨家逻辑比较研究中尚存在一定“比附”现象。如他认为《墨经》中的“同”是求同法、“异”是求异法、“同异交得”是求同求异并用法等。但这并不是胡适的真实意图,而是他在尚未充分把握西方逻辑和墨家逻辑的情况下进行比较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失误。
三、沈有鼎的研究成果使墨家逻辑获得了新生
沈有鼎(1908~1988年)是现代逻辑学家,曾留学美、德、英等西方国家,精通西方逻辑和现代逻辑,又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校勘和训诂方法。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以《墨辩的逻辑学》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于1980年结集为《墨经的逻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他所掌握的西方逻辑和现代逻辑工具,来系统解释和估价墨家逻辑原典,使墨家逻辑获得了新生。
沈先生认为,墨家逻辑“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实,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7]303充分肯定了墨家逻辑的存在及其价值。沈先生从《小取》篇出发,全面揭示了墨家逻辑的思想和理论。沈先生认为,《小取》篇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恰好与逻辑学通常所叙述的概念、判断、推论三个部分相当。逻辑学对于思维形式的研究,需要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分析来进行,墨家逻辑关于思维形式的理论是通过名、辞、说这些语言形式的分析来进行的。
“名”本来是指语词,但可以用它来表达概念,《墨经》只称表达概念的词项为“名”。《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举,拟实也。”《经说上》说:“名若画虎也。”名是用来“举实”、“拟实”,即反映事物的性质、本质的,就像画虎以表现真虎一样。《墨经》根据外延不同,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类,这是墨家在概念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经说上》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达名外延最大,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实际存在着的事物。类名外延比达名小,比私名大,它所概括的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一类事物。私名外延最小,只能指称一个实体。墨家还从内涵上讨论了集合名和元素名的区别。《经下》说:“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兼”指“兼名”,即集合名,例如“牛马”是一集合,它由“牛”和“马”两元素构成,由于集合不等于元素,所以“牛马非牛”、“牛马非马”的论题成立。《经下》说:“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是。”《经说下》说:“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俱一”是说一切事物每一个都是一个,如说“牛马四足”,意味着“牛四足”、“马四足”,即四足的性质可以平等地分给“牛”、“马”两个元素。“惟是”的字面意思为“仅仅这一个”,指集合所具有的整体的、唯一的、不可分配于其元素的性质,如“牛马”的集合,从元素说有两个,从集合上说只有一个。再如手指分开来数有五个,即一只手“指”的元素有五个,但合起来也只有“一个”五,即“五指”的集合只有一个。
逻辑中的命题或语句墨家叫“辞”。“辞”所表达的“意”即判断。《小取》说:“以辞抒意。”墨家认为,一个命题是真的,既要“言”合于“意”即“信”,还要“意”合于“实”,这样的命题就是“当”即真的。言“信”不必“当”,但“当”必定“信”。《墨经》研究了全称、特称、模态等判断的表达方式。全称判断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语言里是用一个“尽”字。《经上》说:“尽,莫不然也。”《经说上》说:“俱止、动。”“俱”和“尽”都是全称量词。“然”是肯定,“不然”是否定,“莫不然”即是说“并非有个体不是如此”,等值于“所有个体都是如此”。特称判断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语言里是用一个“或”字。《小取》说:“或也者,不尽也。”如“马或白”这个特称判断包含有“马不尽白”的意思。这里的“或”相当于我们日常语言里所讲的特称量词“有些”,特称肯定间接地隐含着特称否定的意思,与西方传统逻辑中所讲的特称量词“有些”是有区别的。必然判断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语言里是用一个“必”字。《经上》说:“必,不已也。”《经说上》说:“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必”比“尽”更进一步,“必”是“全都如此并且一直如此下去”。如“有弟必有兄”,“有兄”的性质遍及所有“有弟”的场合。“一然者一不然者”是“不尽然”,所以一定是“不必”而不是“必”。模态逻辑中有些模态词可以转换为量词,但是有些却不能。墨家在这里所说的“必”就不能转换。“既然这些模态词不能用量词来代替,那么在逻辑学中模态这一题目,就有单独提出研究的必要了。”[8]32
逻辑中的推理或论证,《墨经》称为“说”。《小取》说:“以说出故。”《经上》说:“说,所以明也。”“说”是把一个“辞”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论据阐述出来的论证。《大取》说:“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故”是理由、根据。“故”有规律地与结论即论题的内容密切地联系着,这规律就是“理”。在论证中,如果我们仅有一个论题即辞,但没有论据,不能言其“故”,那就是胡说 (“妄”也)。“理”在论证中则相当于指示道路的东西,我们必须遵循它才不至于受困。“理”的具体表现是“类”。“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后总要从“类推”出发。《小取》说“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指的是“说”和“辩”都必须遵守“类”的规则。“故”、“理”、“类”是“立辞”必须具备的三个因素。沈先生说:《墨经》“‘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7]336
“说”和“辩”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包括:假、效、辟、侔、援、推等。“假”是与当前事实相违背的假设。不过,这假设也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从这假设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推出一些结论来。“效”是在“立辞”之先提供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即“法”,然后看所立的“辞”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符合则为“是”,不符合则为“非”。由于“法”、“理”等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在具体论证中是以大前提的姿态出现的,因此,“效”意味着演绎推论。“譬”是比喻,“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话作为推论的前提,二者都是类比推论。区别只在于:“譬”的前提是以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内容的主方自己的话,而“援”的前提则是对方说过的话或对方所赞成的某人说过的话。“侔”是复构式的直接推论,在本质上是演绎的。“推”是归谬式的类比推论,即为了反驳对方的某一句话,就用这句话作为类比推论的前提,得出一个荒谬的连对方也不可能接受的结论,这样就把原来对方的主张驳倒了。
沈先生由于有扎实的古文字学功底和较为充分的知识准备,他对《墨经》中许多有关逻辑学的条目都给予了比较准确的解释。例如,沈先生围绕“止”这一论式对《墨经》中相关条目所作的校注就是如此。《经上》说:“止,因以别道。”这是“止”的定义,即“止”这种反驳方式是用来区别和限制一个一般性道理的。《经说上》说:“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若‘圣人有非而不非’。”这是“止”的步骤和举例,即对方通过列举一些个别的正面事例,然后推论出一个并不正确的一般命题,我就可以列举反例来问难。例如对儒家中有人说“圣人看见别人有错误却不揭露其错误”命题的反驳。《经下》说:“止,类以行之,说在同。”这是“止”的规则,即我所举反例必须与对方的例子“同类”,因为我所反驳的和对方所证明的是同一论题。《经说下》说:“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这也是推理的步骤,即对方从其并不正确的一般命题,用演绎法推论出个别结论,我则以对其大前提真实性的否定,怀疑其个别结论的可靠性。相比之下,一些有名的校注家都存在许多问题。如高亨《墨经校诠》把“止,因以别道”中的“因”误校为“同”,误解为全称命题,把“道”这个关键字和《经说上》“若‘圣人有非而不非’”的例误置于下条,将此条与下条的校释都搞乱了。谭戒甫在《墨辩发微》中则把“止,因以别道”中的关键字“止”误属上读,根本未能看出《墨经》中有“止”的反驳方式。
综上所述,胡适由于对西方逻辑知识的掌握比梁启超更准确,所以,在墨家逻辑比较研究中的“比附”就要少得多。沈有鼎由于精通现代逻辑,他的墨家逻辑研究成果更是远远高出了梁启超和胡适。在文本校注上,他对《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许多条目都做出了较为准确的注解,纠正了自梁启超以来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解释。在义理阐释方面,他“第一个系统、深刻、独立地阐发了《墨经》的逻辑体系,把墨家逻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8]428今天,掌握现代逻辑的优秀成果,全面正确地把握西方逻辑精神,并恰当地运用于墨家逻辑研究,依然十分重要。
收稿日期:2005-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