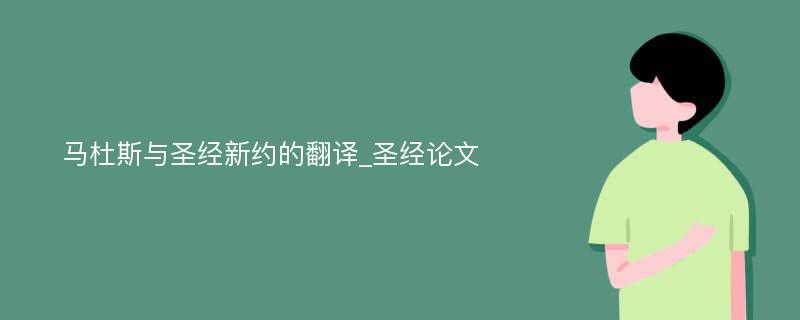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诏论文,译本论文,圣经论文,麦都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10-0095-06
麦都思作为圣经译者已广受学界关注,焦点集中在他的“委办本”《圣经》。如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详述了“委办本”《圣经》的译经过程、麦都思的作用、麦都思和王韬的合作关系。游斌在其《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圣经文学研究》2007年第1辑)一文中则重点讨论了“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王韬在翻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采用的策略。和“委办本”《圣经》相比,麦都思的早期新约译本《新遗诏书》①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一般被视为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修订本,是一种过渡性的译本。但实际上,经过仔细的版本对比,会发现这一译本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神天圣书》。《新遗诏书》1837年甫一发行,就替代了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神天圣书》,并在此后的十年至十二年,成为在华及南洋的新教教会的主要圣经译本,被广泛采用②。1856年以后还为德国传教士所刊印,至1865年在一定范围内还在使用③。这一译本的“文体和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④为后来的圣经译本奠定了基础⑤。此译本后经郭实腊多次修订。郭氏修订本成为太平天国所刊刻发行的《新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的底本。本文以版本为依据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遗诏书》与《神天圣书》:修订,还是重译?
马礼逊1807年入华后,便致力于圣经翻译。1813年译毕新约。1819年,与同会传教士米怜合作完成旧约的翻译。1823年,新、旧约结成一册在马六甲发行,名为《神天圣书》。《神天圣书》一般被认为是第一本中文圣经,马礼逊和米怜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译经者所推崇。但马礼逊完成《新约》时,到华才仅有七年,完成《旧约》时也不过十二年,中文修养有限。早在1826年就有人批评其译文诘屈聱牙,过于拘泥原文⑥。而马礼逊本人生前也数次修订过《神天圣书》,但只做了微小的改动⑦。1835年,即马礼逊去世的第二年,修订工作提上日程,一个为修订《神天圣书》的翻译小组成立,成员四人,有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翰。新约部分于1835年完成,并在1836年麦都思回英前经他最后修订,于1837年在巴达维亚印刷,书名《新遗诏书》。
其时,批评并主张修订马礼逊译本的传教士虽不乏其人,但背后真正的推动者、实施者则是麦都思。他在马礼逊生前即写信表达自己对马氏译本的不同意见,但这并没引起马礼逊的重视⑧。接着,在马礼逊去世这一年,麦都思出版了编译作品《福音调和》(Harmony of the Gospels)⑨。《福音调和》是一次重要的翻译试笔,译文融入了他的翻译理念,赢得了中国士人的好评⑩,并为他翻译《新遗诏书》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福音调和》和《新遗诏书》的相关章节就会发现,《新遗诏书》的四福音书是以《福音调和》为基础修订而成的。
编译圣经实际是麦都思避免直接挑战马礼逊作为中国新教教会奠基人及圣经译者地位的一种巧妙的策略。在马礼逊1834年8月1日去世后,麦都思加快了其圣经中译的进程。1836年回英前已最终校订完毕,并委托在巴达维亚的同工印刷这一新的新约译本。1836年10月28日他写了一份正文加附录长达四十余页的“就新版中文圣经译本致大英圣书公会备忘录”,以求新译本获得大英圣书公会的资助。在给大英圣书公会的这份备忘录中,他措辞谨慎,用意详审,分别用传教士、中国的皈依者及中国士子的观点来说明马氏译本的不足,如他引用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话来批评旧译本并为自己重译圣经辩护,“当前的圣经中文本很古怪,中国人读来晦涩难懂;这无疑是因为译者尽力忠于原文所致,但可悲的是这样做却是以牺牲中文的风格和习语为代价。”“如果译文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那就必须推翻重译(entirely remodeled),否则就不会达到预期目的。”(11)但麦都思“彻底修订”(thorough revision)或“推翻重译”(re-modeled)的提法刺痛了大英圣书公会中那些马礼逊的老朋友。此外,麦都思在刊印《新遗诏书》之前没有把它送到马六甲去听取传教士埃文斯(John Evans)和台约尔(Samuel Dyer)的意见,从而得罪了他们。这两人在写给大英圣书公会的信中极力贬低这一新译本,批评它不够忠实原文,只是一种释义(paraphrase),并称“如果公会资助这一译本,就是在资助圣经的释义,而释义根本就不算是翻译。”(12)这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新遗诏书》未获得大英圣书公会的支持与资助。
《新遗诏书》所激起的纷争显然不能用新译本只是对旧译本的修订来简单作出解释,《新遗诏书》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译本,而不是对马礼逊译本的修订。两译本无论从译者的翻译理念还是所使用的核心词汇看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麦都思和马礼逊所秉持的翻译理念之间的冲突从当初麦都思给马礼逊寄去的译文为马礼逊所排斥就已现出端倪。马礼逊一直想以一种雅俗共赏的中文“俗语”或“普通语言”来翻译圣经,而不是只有受教育者才能明白的高雅、古典的语言风格。而后者正是麦都思所追求的。马礼逊甚至把中国的古文比喻成欧洲的拉丁文和埃及祭师所使用的象形文字,为一部分人利用来维护阶级特权(13)。而麦都思的《新遗诏书》则明显以中国士子为阅读对象,追求圣经中译本能够和中国的《四书》等典籍相埒,译文务求典雅。
马礼逊倾向直译而麦都思倾向意译。马礼逊认为译者职责有二:“一、理解原作意思准确无误,把握原作的精神;二、忠实、清楚、地道地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但在他看来前者更为重要,因为“表达再优雅也不能弥补对经文意思理解错误之过,任何译文某种程度上风格粗俗一些并不会影响达意。苏格兰教会使用的笨拙的圣歌译文优于那些优雅的译文。”(14)这种看法就使得好的译文应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达成一种巧妙的平衡片面地滑向了直译的一面。两人对合作的中方译者也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麦都思会去积极寻找那些合格的中国译者并努力与之合作以译出合符中国文法的圣经,但马礼逊对中国的译者却充满了怀疑与忧虑,“我认为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敷衍了事,或者即使他们会热心一些,也会在原文含义和他们所秉持的观点不一致时修改原文。”(15)他既担心中国人不够诚实,又担心译本会渗入他们的异教观念,这样与他合作的中方译者就难以发挥其精擅中文的优势,译文诘屈聱牙就不难理解了。马礼逊赞同的是一种异化的策略,不容许中国宗教和哲学中的词汇术语出现在中文圣经当中,而麦都思实际上更倾向于归化、调和,更能包容中国文化这一“异教”文化。他主张尽量不创造新词,尽量从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发掘出近似的表达,以现有词汇传译圣经中的术语。而且,翻译时要灵活处置,对原文文法要适当变通。
马礼逊译本和麦都思《新遗诏书》在核心词汇的翻译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核心的词汇当属“God”的译文。这一明清之际“礼仪之争”的焦点问题在新教初入中国时又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延续。马礼逊把“God”译为“神”,米怜开始时主张译为“神”,后来则赞同译为“上帝”(16)。麦都思在其《新遗诏书》中以“上帝”译“God”。“上帝”一词是中国的既有词汇,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但和基督教的造物主并不同义,这种欲以中国既有词汇来翻译基督教造物主的做法体现出一种文化调和的倾向。而马礼逊欲赋予中国文化中泛指性的称谓“神”以造物主的含义,实际是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植入这一新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异化的文化策略。此外,其他核心词汇的翻译如“宠”改译为“恩典”,“耶稣基利士督”改译为“基督”,多为后来的圣经汉译本所采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麦都思曾在致大英圣书公会备忘录的附录中把中文新旧译本的《路加传福音书》部分回译成英文,以便于圣经公会了解其翻译策略,可见他对此部分的中译颇为自得。比对《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7)和《新遗诏书》中的《路加福音》,可以看出两种译文在中文句式、专名翻译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相较马礼逊的《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麦都思的《新遗诏书》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译本。麦都思也当仁不让,在《新遗诏书》封面上注明“尚德者纂”四个字,说明他已经自认为是这一译作的独一译者了。客观而论,《新遗诏书》的确要比马礼逊的《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语言更流畅,文采更出众,也更明白易懂,是一个优于马氏译本的新译本。
二、《新遗诏书》与《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及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是何关系?
《新遗诏书》于1837年发行后,郭实腊曾数次修订麦都思的《新遗诏书》,书名也改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并发行了十几版(18)。经郭实腊所修订的《新遗诏书》和郭实腊所译的《旧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采用,更名为《新遗诏圣书》和《旧遗诏圣书》,于1853年出版发行。郭氏修订本因被太平天国所采用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1837年后,郭实腊一直在不断修订《新遗诏书》。他把1849年发行的那一版称为第14版(19),如果再加上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郭实腊死后修订并发行的两版,那《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就至少有16个版本(20)。各个版本之间有多大的区别?现在已难以窥得所有版本之全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记录中得到一些信息。麦都思在1849年致伦敦会信中就提及:“在我离开中国回英后,郭实腊常常重新刊行这一新约译本,起初几版只有个别文字之别,后来则变化较大。”(21)看来郭实腊的修订本越到后期改动越大,有逐渐偏离1837年版译本的趋势。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认为后期的版本在术语和风格上显著不同于前期的版本(22)。有学者已经考订了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是以郭实腊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底本修订而成,而这一底本是洪秀全于1847年在广州随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学习基督教义时所获得的(23)。但郭实腊生前所发行的数版《新遗诏书》的修订本中,太平天国所刊行的圣经以《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的哪一版为底本修订而成?《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又在多大程度上对麦都思的《新遗诏书》进行了修订?太平天国的《新遗诏圣书》和其最终来源译本1837年的《新遗诏书》有多大不同?
洪秀全于1847年到广州时获得《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且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即据此版本修订而成,这是可信的。但洪秀全所获得的是哪一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呢?在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版本比较出发进行探讨。笔者所见的《新遗诏圣书》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流传较广,只包含新约第一卷《马太传福音书》。此书封面黄色,正中竖书“新遗诏圣书”,旁饰龙凤花纹,上横书“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目录页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十五部,首页题“马太传福音书卷一”,有“旨准”朱印。正文共28章,47页。有学者从1853年4月至1854年6月访问天京的外国使节所带回的太平天国文献推断,太平天国前期只刊行了《新遗诏圣书》的第一卷《马太传福音书》,随即于1854年7月以新、旧遗诏书“多有记讹”为由而“不用出先”(24),从而停止刊行新、旧遗诏书,直到1860年重新刊行经洪秀全修改过的《钦定前遗诏圣书》和《钦定旧遗诏圣书》(25)。第二个版本是完整的《新遗诏圣书》(26)。此书封皮左上竖书“新遗诏圣书”,次页的左半页中间竖书“新遗诏圣书”,其下偏右有“卷之”两字,图案和上述癸好三年版相似,有龙凤花纹。再次页的左半页正中题“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左下有“依本文译述”,再次页左半页为目录页首页,右半页底部载“Gutslaff NT Singapore 1840”。目录页共两页27章,以《马太传福音书卷一》始,以《圣人约翰天启之传》终。这很明显表明《新遗诏圣书》是以郭实腊1840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一书为底本修订而成。麦都思亦在1853年谈及太平天国所刊行的圣经时说:“叛军的《旧遗诏圣书》一字不变地采用了郭实腊的译本,……而《新遗诏圣书》则是采用我和郭实腊1835年的译本,……所采用的版本则是郭实腊最早的修订本之一”(27)。麦都思已肯定太平天国使用的新约是自己所译但经郭实腊修订的早期版本之一,虽未明确指出这是1840年版。比较此书之《马太传福音书》与上述癸好三年版,发现两书无一字差别,应是采用同一底本所刻无疑。
因无法找到郭实腊1840年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28),我们将郭实腊1839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29)以及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30)的《路加福音》1章1-13节,以与以上麦都思的《新遗诏书》(1837年版)相应部分互相参照对比,可以看出,郭实腊的1839年版与麦都思1837年版只存在几个人名音译及个别词语的不同,如以“以利沙百”替换“以利撒别”,以“焚香”代替“烧香”。这正好印证了麦都思所言的“起初几版只有个别文字之别”。再对比郭实腊1839年版与太平天国的《新遗诏圣书》版,即使缺少郭实腊1840年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仍可通过他的1839年版本看出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和郭实腊早期版本的渊源关系,即两译本人名音译和核心词汇的翻译皆无不同,太平天国译本应是修订自郭氏译本。郭氏1839年版本即和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如此接近,可以推知其1840年版本和《新遗诏圣书》差异会更小、更为相似。
如果我们跨过郭氏版本,把《新遗诏圣书》和麦都思的《新遗诏书》做一对比,可明显看出《新遗诏圣书》脱胎于麦氏译本的痕迹非常明显,两个版本的核心术语、句式、习语并未有根本不同。可以说,麦都思《新遗诏书》是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之最终来源版本。而处于链条之中的郭实腊1839年和1840年两个版本只是对1837年的《新遗诏书》做了一些细枝末节的,甚至可以忽略的修订。
三、《新遗诏书》与“委办本”《圣经》
麦都思的《新遗诏书》体现了他的翻译理念和目标,即要给中国士人提供一本不亚于中国经典的文学著作。尽管他的初步尝试即受重挫,译本为大英圣书公会所否定。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完全丧失希望,相反,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在1836年11月25日新的译本被大英圣书公会否决后,他在12月18日致伦敦会董事的信函中提出将来圣经修订的模式:让所有在华传教士都参与译经,完稿后彼此互审,再集合统一校对,最后修订形成一个最终译本(31)。这种思路实际上在若干年后“委办本”圣经的翻译中得到具体的贯彻和实施。“委办本”以其流畅性和卓越的文采而为人称道,多次再版。
同时,《新遗诏书》的翻译理念也为“委办本”圣经所继承。两个译本都是以中国的士人为诉求对象,都致力于翻译出雅训、简洁的译文,也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表现出文化调和的倾向。
《新遗诏书》与“委办本”《圣经》的主要译者虽皆为麦都思,且体现着相似的翻译理念,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译本,原因何在?这应该和麦都思的中方合作译者关系极大。《新遗诏书》的主要中方译者很可能是朱德朗,他以一位誊抄者(transcriber)的身份出现在伦敦传道会和大英圣书公会视野中,但其真实的身份应该是笔述,是王昌桂、王韬父子之前麦都思的重要的合作译者。1838年出版的《中国:现状与展望》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他和麦都思的合影。照片中麦都思持书口述,朱德朗执笔书写,反映出典型的西译中述模式。实际上,1835年时,麦都思就把新约译文的部分草稿带到广州,在当地几位学者的帮助下修订,大概其中之一就是朱德朗(32)。麦都思带朱德朗回英以翻译还未完成的旧约译本,但新译本为大英圣书公会否定后,本由麦都思和郭实腊分工合作翻译的旧约转由郭实腊独立完成,朱德朗协作麦都思翻译旧约的任务也就终止了。但朱德朗还是在英国居住近两年,直至1838年7月31日和麦都思同船返回,临行前不久他皈依基督教。他先是于7月6日,致信伯德博士(Dr.Burder)表达自己入教之心愿,以及回国传教之决心(33)。随后麦都思于7月20日在哈克尼的圣托马斯广场教堂(St.Thomas-square Chapel)给他进行了洗礼。洗礼前麦都思问了他四个关于信仰的问题,他都给出了非常虔敬的回答(34)。
16年后,帮助麦都思完成“委办本”《圣经》翻译的王韬受洗入教(35),他的申请受洗的文件表现出同样的入教热忱。把这两位前后期分别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的中国译者对比一下,可能会很有趣且颇富启发性。这两位底层中国士人都是在阶段性帮助麦都思完成圣经中译后皈依基督教的。翻译过程中对圣经的深入了解无疑为此后两人的信仰选择奠定了宗教知识基础;身边接触的教会人士对他们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朱德朗在英国的近两年时间,麦都思的相伴,基督教会朋友的照顾,王韬在翻译“委办本”《圣经》时则整天和对中国传教事业影响巨大的人物如麦都思、慕维廉等共事。当然,也可能是麦都思在无法获得中国上层仕宦阶层的支持,而力图归化底层士人的努力的结果。虽然这种努力最终还是未达圆满,王韬在晚年对基督教大加贬斥;朱德朗1839年回国后,开始还能效力伦敦会,但随着中英矛盾的激化,他避居乡里,和教会不再联系(36)。
两人无疑都在其参与的译本中留下了痕迹。每一译本面世时和之前的译本相比,都更符合中文的行文习惯、更注重使用中文的习语,在流畅性上也更胜一筹。但相较之下,王韬在“委办本”《圣经》中留下的痕迹更为明显。因王韬的相助,“委办译本”在文笔上比之前的几种译本都大有进步,其文风打上了王韬本人的烙印(37)。但在流畅、顺达的同时,“委办译本”有时牺牲了原文的含义,“其中所用的名辞多近于中国哲学上的说法,而少合基督教教义的见解”(38)。无属灵经验的人“容易把耶稣误认为是孔子”(39)。王韬带给“委办译本”风格上的变化无疑是麦都思所赞赏的,麦都思翻译“委办译本”比翻译《新遗诏书》时对合作的中方译者无疑表现出了更大的宽容度,他甚至容忍了“委办译本”中出现的儒学化的倾向。而《新遗诏书》虽然被埃文斯等人批评有释义的倾向,但至少此译本还没有渗入儒家的词汇、概念或术语,或者有也不显著,也没有传教士因为这一点而批评此译本。这无疑和麦都思给中方合作译者的自由度有关。朱德朗等《新遗诏书》的合作译者很可能在合译时还只是被局限在一个誊抄者(transcriber)的功能定位上,顶多可以对原文稍加润饰。而王韬无疑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以致赋予“委办译本”以特有的文体特征。迟至1908年,还有人批评麦都思等“委办译本”的译者“给那些中国助手以无限的自由,以随意改变、省略、合并甚至替换圣经中的词句”(40)。
《新遗诏书》和“委办本”《圣经》的中方译者享有着不同的可自由支配的翻译空间,这无疑和两个译本的灵魂人物麦都思息息相关。和朱德朗等早期合作译者的关系相比,麦都思可能和王韬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契合,这才会放手让王韬去润饰,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从麦都思对王韬的赞誉以及王韬日记中传达出的对麦都思的敬重获得证实。再则,麦都思1843年从东南亚来到中国本土后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深悉这是一个仕宦阶层统治着的国度,要想获得中国士人的响应,就要先译出他们尊敬并喜欢阅读的圣经译本,采取调和的文化策略、归化的翻译方法正是对此现实作出的回应。麦都思理想中的中国合作译者是一个徐光启式的人物,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在本族人中颇有影响的士人,一位精于中文的皈依者(41)。而相对于朱德朗,王韬似乎更符合他的标准。
麦都思在“委办本”圣经译本中几近实现他作为圣经译者的目标,即译出一本雅驯而忠实,为中国人所尊重的译本。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他坚持1837年《新遗诏书》的翻译理念,总结《新遗诏书》译本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也是他和中方合作译者更卓有成效地合作所取得的成绩。
注释:
①《新遗诏书》名义上是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和马儒翰四人翻译小组合作之成果,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麦都思一人之译作,见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31.此外,《新遗诏书》独署“尚德者纂”,且《新遗诏书》的福音书明显脱胎于麦都思早期编译作品《福音调和》,皆可为证。
②贾立言,冯雪冰:《汉文圣经译本小史》,上海:广学会,1934年版,第29页。
③⑤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9,pp.66,67.
④梁工:《圣经指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⑥⑧[美]韩南:《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第19页,第20页。
⑦⑩(11)W.H.Medhurst,"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Oct.28,1836,i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London,1836,pp.3-4,5.
⑨麦都思:《福音调和》(下),巴达维亚,1834年版,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
(12)"Copy of a Letter from the Rev.Messrs.Evans and Dyer to the Rev.Joseph Jowett," Nov.15th,1836,i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London,1836,p.46.
(13)(14)(15)Robert Morrison,Eliza Morrison,Samuel Kid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Vol.II.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and Longmans,1839,pp.7,8,9.
(16)Robert Morrison.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in the Native Character; with Transl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Remarks.London:S.McDowall,1825,p.41.
(17)《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马六甲英华书院藏板,出版年代不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
(18)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pp.62-63.
(19)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p.69.
(20)(21)(22)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p.69.
(23)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4)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25)张铁宝:《关于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26)见珍本圣经数位典藏,http://bible.fhl.net/new/ob.php?book=19&version=&page=1。
(27)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p.72.
(28)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藏有另一版本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缩微资料,年代标记为1836-1840年之间,笔者认为此版本更接近1837年的版本,发行时间约在1839年之前,1837年之后。
(29)郭实腊:《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1839年版,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30)珍本圣经数位典藏http://bible.fhl.net/ob/s.php?DETAIL=1&LIMIT=id=19。
(31)W.H.Medhurst,"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e Projected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Dec.18,1836,i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London,1836,p.64.
(32)Patrick Hanan."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Writing Process," in Patrick Hanan ed.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Yenching Library,2003,p.270.
(33)英文信件全文见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September 1838,Vol.XXVIII,pp.139-40.
(34)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September 1838,Vol.XXVIII,pp.140-41.
(35)段怀清:《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6)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p.40.
(37)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p.92.
(38)贾立言,冯雪冰:《汉文圣经译本小史》,第39页。
(39)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52.
(40)Letter from D.Z.Sheffield to ABCFM of Jan.12,1908.见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p.92.
(41)W.H.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London:John Snow,p.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