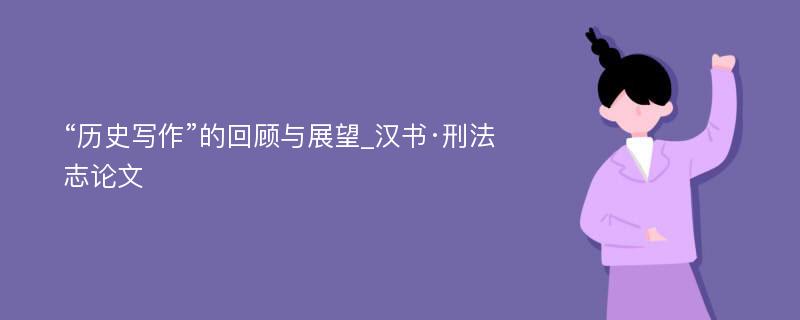
“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作为一种研究取径,“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之称频繁见诸中古史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进而标举流派、组构学群,流风所及,连研究生举办的论文发表交流会也有冠以此名者。按照学人基本取得共识的定义,历史书写研究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
虽然历史书写的取径还能继续细化(参见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但其核心要义无非是展现史料形成的过程并探求其背后的动因。因此这一取径的落脚点不在于史料本身,也不在于史料所记载的“史实”,而在于执笔书写“历史”的人。书写者或出于个人好恶,或限于知识结构,或迫于政治压力,或习于文化风气,或拘于大义名分,在对相同“历史”的书写上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了虚实交错的叙事文本,这就为历史书写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素材。既然历史书写的目标锁定为书写者,所谓的“史料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便立基于对书写者主观世界的分析之上,那么我们有必要对书写者之所以如此处理“史实”的主观意图进行细致分类。由于笔者所关注的领域为中古法制史,以下用于说明的实例亦限于此。
从意识性的强弱而言,支配人行为的主观因素无非介于自觉与自发之间,即对行为及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有无认知、行为本身有无明确目的等。譬如盲人摸象,各自以触摸到的部分来描述大象,对于这种记载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盲人并无“自觉”,而是囿于自身能力进行以偏概全的记录,其主观性最弱;再如掩耳盗铃,盗窃者明知铃声大作,却佯装不闻,并由此推定他人亦无所闻,类比于书写历史者,便是肆意歪曲或隐匿事实、虚构情节,并试图销毁一切承载“真相”的素材,其主观性最强。正因如此,布洛赫才区分有意识的证据与无意识的证据,“让我们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法老时代埃及人放在墓穴中的游记加以比较,然后,对比一下这两大范畴的原型,将史学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划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的证据是有意的,而第二组则不是”(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滋贺秀三在《汉唐间の法典についての二·三の考证》(《东方学》第17辑,1958年)中推测,《唐六典》关于《开元后格》“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初为七卷,其曹之常务,但留本司,别为留司格一卷”的描述误为《旧唐书·刑法志》继受,并系于《贞观格》下,导致原本不存在的《贞观留司格》一卷由此产生。笔者进而认为,唐格的篇目并非固定不变,“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目”并非贞观以下诸格的共通形态(《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令·狱官令〉“僧道科法”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换言之,《旧唐书·刑法志》的执笔者将《唐六典》所载《开元后格》的篇章结构用于概括唐中前期颁布的历次格典,恐怕是一种盲人摸象般的误解。
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史书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足所导致的误判,也可能是因“前见”的影响而产生的“格义”、套用,后者依然是一种内化于心、日用而不自知的结果。如刘俊文在考辨《新唐书·刑法志》疏误之时,曾将致误原因之一归结为新志作者昧于唐制(《〈新唐书·刑法志〉证误》,《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而张雨围绕《天圣令·狱官令》宋46“奏下尚书省议”一句复原唐令的问题,比较《旧五代史·刑法志》、《册府元龟》与《新唐书·刑法志》的不同表述,藉此提醒现代学人,《新唐书》的作者身为宋人,在执笔撰史之时,会产生以其熟谙的宋制附会唐制的问题,由此混杂唐宋之制(《唐宋间疑狱集议制度的变革——兼论唐开元〈狱官令〉两条令文的复原》,《文史》2010年第3辑)。
相比于简单的传抄之误,上述两种史书撰写可能存在的问题其实或多或少都融入了执笔者的推理与判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主观性创造。但这依然无法达到“自觉”的程度,亦即执笔者显然不认为自己是在“制造历史”,他们仍然以“叙述历史”为责任与目的。那么史书的撰写者是否会自觉地“制造历史”呢?
冨谷至对读出土的制度史文献与《汉书·刑法志》,认为班固编纂此志的意图,并非要准确地再现西汉一代的刑罚、法律制度之实态,作为一个深受礼教主义浸润、支持儒家思想的史家,班固在《刑法志》中随处并举礼与刑、德与法的写法,使《刑法志》不再是制度之“志”,而是政治思想之“志”(《解说》,内田智雄编、雷谷至补《译注 中国历代刑法志(补)》,创文社,2005年,第259—260页)。在冨谷氏的笔下,汉志有可能是一位带有明显立场的史家刻意构造出来的一种叙事文本,而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呈现。
与此相类,陶安在讨论《刑法志》有关文帝刑制改革的记载时,也提出了一个看法:“通过班固的《刑法志》可知,在东汉律学的眼光中,文帝刑法改革是西汉法制的一大转折点。这一观点似与文帝至武帝时代的一般认识略有出入……在当时的一般认识中,废除肉刑一事也仅是文帝慈善事业之一,与‘除诽谤’、‘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等没有本质差别,恐未被视为法律制度的一大里程碑。班固刻意强调文帝‘除肉刑’一举,这应是复活肉刑的政治主张所致。”(《复作考——〈汉书〉刑法志文帝改革诏新解》,《法制史研究》第24期,2013年,第162—163页)也就是说,作为《汉书》的执笔者,班固因其特有的法律立场,通过史书的叙事,夸大了文帝“除肉刑”的历史意义。
冒谷氏与陶安氏的上述研究皆聚焦于一人、一志,此外,还有以一事为线索,考察数种文本,由此展现“历史”被书写出来的过程及其生成的动因。如《史记》的《高祖本纪》、《萧何世家》与《汉书》的《高帝纪》、《萧何传》未见萧何增加律三篇之事与“九章”之语,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最早见于《论衡》和《汉书·刑法志》。因此,陶安认为“九章律”并非汉初官方编纂的法典,而是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律学传承与集约法律知识的产物(《法典编纂史再考——汉篇:再び文献史料を中心に据ぇ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0册,2000年,第4—20页)。滋贺秀三同样关注到这一现象,但他的解释是:当时所形成的法律家集团采取儒家围绕某一经书进行讲学、注释的学问形态(章句之学),创造了名为“九章”的法学经书,这与法律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构筑其地位相关。而之所以用“九章”为名,可能是出于对抗秦朝以六为尊、汉家改以九为尊的意识(《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创文社,2003年,第35—39页)。概言之,在他们看来,“九章律”出现在《论衡》与《汉书·刑法志》中,并非因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一部名为“九章”的律法,而所谓萧何作律九章,只是由于律学兴盛而被制造出来历史。
由于《法经》编纂的说法首见于《晋书·刑法志》,较此更早的《史记》与《汉书》皆无相关记载,学界历来就有将李悝《法经》视为传说的观点。广濑薰雄结合上述有关“九章律”的研究,梳理出汉唐之际“李悝《法经》→商鞅《法经》→萧何《九章律》”这一法典传承脉络的构建过程:第一,《法经》与《律经》只是汉文帝废止肉刑之后所出现的法律学的经书而非法典,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唯《律经》在《法经》之上增补了事律三篇;第二,东汉初年,《律经》作者为谁并不明确,曾有假托皋陶之说。然自《汉书·刑法志》采用萧何为《律经》之作者后,此说便成定论;第三,曹魏以降,《法经》为秦律且作者为商鞅之说出现;第四,《晋书·刑法志》又在商鞅《法经》之前增加了李悝《法经》;第五,唐《永徽律疏》最终确定了商鞅六律改李悝六法的源流图式。广濑氏认为,上述法典编纂的叙事发端于《汉书。刑法志》,经由《魏律序》、《晋书·刑法志》(虽然无法确定该篇以张斐所撰《汉晋律序注》为祖本而撰成,但可推断它有律注序言的特征)、《唐律疏议·名例律》的篇目疏等而渐次丰满起来,这些律序、律注序所述,仅仅是律的基本理念而已,并非历史叙述,由此便得出类似于上述冨谷氏的判断:这种法典编纂的叙事并非法制史的资料,而是法制思想史研究的资料(《秦汉律令研究》,汲古书院,2010年,第41—75页)。
广濑氏虽然试图将律注、律注序对于律典篇序的排列与三才思想等易学相关联,但并未解释在这一法典编纂叙事被构建出来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法律思想。笔者尤其好奇的是:这种法律思想是否为各篇律序、律注序的作者所共享,在汉唐之际呈现一以贯之的状态?抑或是各篇律序、律注序的作者其实出于各自的知识背景、文化意识,在无意之中恰巧形成了如此完整的叙事谱系。
以《刑法志》的撰写为例,汉唐之际的史家并未共享相同的撰写模式、执笔意图。如陈俊强认为,就《刑法志》的流变而言,作为创始文本的汉志应出于班固之手,鉴于其“兵刑合一”的理念,该志与《史记·律书》之间应有渊源关系,只是在汉志之后,《刑法志》尚未成为史书必备的篇章,仅有如魏收这种立志师法班固的作者,才会在《魏书》中单辟一目,至晋志、隋志以后,《刑法志》才在历代史书中确立稳固的地位;自其叙述内容的比重而言,汉志是“刑主法从”,魏志则“详刑略法”,至晋志、隋志则“刑、法并重”;至于撰写者的主观意图,汉志表达了班固在“述古”之外强烈的“论今”倾向,晋志、隋志的作者则有标榜唐制源远流长且集其大成的目的(《汉唐正史〈刑法志〉的形成与变迁》,《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3期,2010年,第1—48页)。
而且在一味强调执笔者有意为之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完全排除汉唐之际史家“自发”而非“自觉”的因素?如萧何于汉初“为法令约束”之事见诸《史记》,萧何作为立法者的事实无可否认。至于东汉史家为他所立之法冠以“九章”之名,或许并非有意构建,只不过是因他们想要叙述的内容有所侧重而仅取汉初立法之一端罢了。换言之,以律九章统括汉初全部立法,只是因为后世之人无从得见书写者所据的全部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理解。如徐世虹认为“法经”之名、“九章”之语,可能是当时法律人“在以刑法为核心地位的意识下的表述”,“其主要指代的应是秦汉的刑事法律而非全部的秦汉律,秦法经、汉九章同宗六篇,凸显的是刑法意识下的法制变迁”(《文献解读与秦汉律本体认识》,《史语所集刊》第86本第2分,2015年,第240页)。
上述梳理仅限于笔者目力所及,自是挂一漏万,无法全面展示中古法制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不过,以点带面,由此归纳三点心得体会,想来不会有太大偏差:
第一,中古法制史的研究者并未特意标举“历史书写”的研究取径,亦未将之视为特殊的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此一取径既非中古史研究所特有,亦非仅限于对正史的考辨。远自民国以来,禅宗史研究对唐宋以来的灯录文献系统的怀疑与突破;近则20年多来,华南学派对族谱文献、民间传说等的解读与重构,皆令我辈瞠乎其后。而前述广濑氏也把自己的研究上接至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论”。因此,辨析史料的源流及撰作背景,以确定其可靠性,本就是现代史家基本的史料处理手法。
第二,解构文本只是“历史书写”的手段,其最终目标还在于文本如此形成的动因解释。所谓胜必正义而非正义必胜,书写历史的权力本就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唐初历史因李世民登基而被刻意删改,宋初帝位传承又因斧声烛影、金匮之盟等而扑朔迷离,史家历来对此都进行过拨云见日的“史料批判”努力。当下标举历史书写取径的研究者之所以很少溯源于此,或许是因为不满足于政治斗争的简单解释。在这个层面上言,时兴的历史书写研究,其新意不在于处理史料的方法,而在于最终归诸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等的历史解释。以此反观中古法制史研究,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走出法律儒家化之类的解释模式。
第三,历史书写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史书执笔者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恰恰是最难探究之处。这些书写历史的人究竟是在叙述历史,还是创造历史,诸种文本之间的差异是执笔人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有时实在很难说得清晰明了。更何况,史书本来就有“撰”、“述”并存的特征,其中大量文字不过是因袭前人而来,在无法穷追史源的情况下,就可能存在将“撰者”之意误置于“述者”身上的风险。因此,陈寅恪“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书写研究而言,或许同样适用。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与中国独创的社科理论的缺失,30多年来,中国史研究便成了运用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试验田,以东方经验填充西方范式。而且得风气之先的中国学人用于治疗这一“理论饥渴症”的妙方,有时并非直接受启发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本身,而是转售自膜拜这些理论的海外汉学家,个中隔膜,不言自明。就中国史研究而言,不论标举何种范式、运用何种方法,能否有力地推进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认知,才是检验作品价值的永恒标准。笔者由衷地期待,集结于历史书写(以及其他各种范式)旗帜之下的学者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方法论之外精彩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