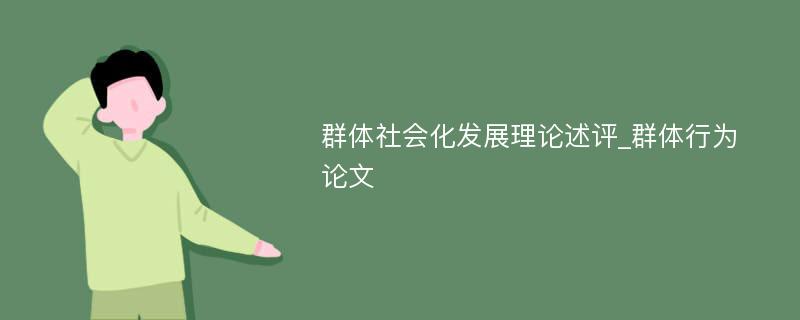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群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领域中,人们一向认为,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但是,这种看法近来受到了挑战。8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者麦考比(E.E.Maccoby)和马丁(J.AL.Martin)以翔实的研究资料为依据,提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们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近,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Judith RichHarris )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杂志《心理学评论(psychoiogicai Reviw)》上发表了长篇综述, 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并首次提出了一个“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本文拟对哈里斯的这一理论作一个简要述评。
一、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提出的背景
哈里斯是受到麦考比和马丁的启发,提出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的。麦考比和马丁10几年前的研究发现,同胞兄弟姐妹或被收养的子女,虽然都在同一家庭环境中长大,但他们后来形成的个性特征却大相径庭。他们的结论是:“(1)父母的行为对孩子没有显著影响;或者(2)在同一家庭中,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影响各不相同。”
这个结论引起了许多发展心理学者的研究兴趣,随后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根据行为遗传学的实证研究资料,人们把造成个性差异的因素分成三类:(1)遗传因素, 在个性特征中所占比重大约为40—50%;(2)“家庭因素, 所占比重大约只占0—10%。也就是说, 子女之间的相似性绝大部分应该归因于他们共同的遗传基因,而相同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增加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3)其他非共有的环境因素,即家庭环境之外的所有环境, 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环境。来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这些环境往往是不同的,称为非有的环境。这类环境在个性特征的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约为40—50%,而其中又有20%是测量误差。对同卵双生子重复研究一再证实,在同一家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他们的个性特征的相关一般不超过50%。这表明,除去遗传和相同的家庭环境之外,如果再减去20%的测量误差,还有至少30%的个性差异无法解释。
为了找出这30%的差异来源,研究者们开始重视麦考比和马丁的第二个结论,即在同一家庭中,“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影响各不相同”,这30%的差异是否由此产生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因为家庭内部每个孩子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了这30%的差异?针对这一问题,最近10年来,人们做了大量关于家庭小环境的研究,涉及到父母对待子女态度不同的原因、出生次序的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影响、家庭规模问题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的研究都不能证明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差异有必然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并没有解答那30%的个体差异究竟源于何处。一位研究者(Rowe,1994)在综述这些结果时总结道:“家庭环境(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在人的一生中,也许对个性发展并没有什么影响。”
哈里斯针对这些疑问,从另一角度来考虑那30%的差异,提出了他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Group Socialix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二、群体社会观发展理论的核心假设
哈里斯认为,社会化是儿童被其所在社会接纳的过程,是通过学习逐渐成为一个有明确行为、语言、技能、恰当的信念和态度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在这一社会化的学习过程中,儿童可以模仿父母来发展,同时也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包括同伴来学习。一般来说,儿童在家中,从父母和兄弟姐妹身上学到的东西,在家庭之外并没有很大作用。社会对儿童在家庭内外的行为要求并不相同,一个在家里随意宣泄感情的孩子,出了家门再这样做就得不到认可。哈里斯据此提出了群体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假设:社会化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学习形式。儿童独立地在家庭内外习得两套行为系统。这两套行为系统的学习方式和强化途径均不同。在家中,儿童做错事会受到惩罚,做对了会得到赞赏;在家庭之外,如果做错了什么,儿童必然会受到同伴的嘲弄,但他们行为表现很好时,也许根本没有人在意。
哈里斯引用了许多经验和实验研究来论证这一假设。其中以语言研究最有说服力。许多关于语言的研究证明,移民的子女在家庭内外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如果语言不同,移民家庭的子女会尽力地学习当地语言。无需很长时间,他们就可以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一种是在家里说的母语,另一种是在外面说的当地语言,而且可以同时与父母和同伴用两种语言交替谈话,不会混淆。这些双语儿童在家庭内外的行为系统有很大的差异。这表明社会化的特定情境化特征。对单语儿童而言,尽管在家庭内外的行为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在不同情境下,个体表现也各不相同。
儿童的社会化之所以有情境化特征,主要是因为个性结构中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遗传决定的,如气质,这一部分个性相对稳定,在各种场合均存在,影响儿童的所有行为,也影响他人对儿童的看法。另一部分是由各种不同的环境决定的,儿童在不同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系统。哈里斯试图从这一个基本点出发来解释那30%的个性差异。
三、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哈里斯认为,既然家庭影响无法解释另外30%的个性差异,我们就应当分析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儿童社会化。群体社会化理论就是要描述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各种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化问题。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1)关于群体现象及儿童的同伴群体;(2)发生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化和社会文化传递的机制。
1.群体现象及儿童的同伴群体
动物天生是群居的,人也不例外。人总是要把自己归于一定的群体。研究表明,群体存在以下五种基本行为现象:(1 )群体中的友好行为。群体中的成员喜欢自己所在的群体胜过别的群体,会自发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群体的行为;(2)群体外的敌对行为。 人们对不同于自己所在群体的别的群体有一种强烈的、甚至是互相伤害的敌对行为;(3 )群体间的对比行为。不同群体之间会由于群体内的友好行为与群体外的对立行为作用而使原来并不明显的群体差异不断加大;(4 )群体内的同化行为。在同一群体中,各个成员会主动或被迫地与群体保持一致,从而使群体的一致性不断增强;(5)群体内的异化行为。 在同一群体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等级,使各个成员彼此不同。同时群体中各个成员也以各种方式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以便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儿童的同伴群体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存在以上五种机制。哈里斯认为,人类群体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把人归于各个群体之中。尽管皮亚杰认为分类是在学前期发生,但许多研究表明婴儿期分类就已出现。年龄、性别、人种是人类分类的三大范畴。对学前期儿童,年龄与性别范畴是主要的。一岁之前,孩子就能很好地区分男女、成人与儿童。到一岁时,儿童会对陌生成人感到害怕,对同龄儿童感兴趣,喜欢与之交往。2岁时,儿童会表现出对同性别儿童的偏爱。
无论在任何文化和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儿童的游戏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儿童期的这些同伴群体之中。社会化是一个使群体中每个个体彼此更为相似的过程。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关注同伴群体的异化和同化现象。希望从这一角度解释个性差异。
儿童群体发展中,成员同化与异化现象是并存的。在同一群体中,各个儿童总是力争在言语、穿着、行为上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群体奉行多数成员认同的行为规则。一旦某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行为不一致,他就会受到群体的严厉处罚,直到他改正为止。有关气质的许多研究表明,在儿童群体中,为免于同伴压力,儿童不得不与群体规则保持一致。这种因为群体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个性有长期影响。此外,除了同伴压力和群体惩罚之外,儿童本身对参与群体也有十分强烈的愿望。促使儿童自觉主动地与群体行为保持一致。正是这些群体同化现象,使同一群体的儿童逐渐地相似化。哈里斯指出,在群体中,同化与异化并不互相排斥。当旁边没有对立群体存在时,群体的自身特性就会变得不突出,群体成员会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相似的群体成员,群体中会出现等级地位与社会比较的差异。在每个群体中,儿童由于统治力量与受欢迎程度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而这种群体内的等级地位高低,会对个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对成年以后的生活产生长期影响。此外,同一群体中的儿童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明确自己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其他同伴或成人也会对儿童进行社会比较,以此对儿童进行群体中的定位。这种社会比较与群体定位,加大了同一群体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差异,也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作了预测,从而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儿童在家庭之外,总是将自己认同于一个群体,他们在家庭之外的行为系统是由同伴群体规则决定的,这对他们今后个性发展有深远影响。同一家庭之间子女各不相同,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属于不同的同伴群体而造成的。群体的同化现象,使得同伴群体而非家庭完成了社会文化的传递,直接促进了儿童在群体中的社会化。
2.发生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化——社会文化传递
按照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儿童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化是发生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文化传递是社会化的重要机制,我们所了解的所有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社会规则,无一不是通过社会文化传递完成的。传统观点认为,家庭在这种文化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哈里斯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文化传递不是由家庭完成的,社会文化不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而是由儿童群体传递的。如果说父母在文化传递中也起作用,那么他们也是与所有同辈人一起,作为一个父母群体、把文化传递给了下一代。社会文化的传递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传递,而是群体对群体(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传递和群体内部的传递(同伴群体向每一个群体成员传递)。
同伴群体中的同化现象告诉我们,同一群体中多数成员共有的行为与习惯会被整个群体接受,成为群体准则。对于来自同一文化、同一种语言体系的儿童群体而言,也许这一论断很难得到证实,但是那些从亚洲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子女的行为却是无法否认的;他们的父母不讲英语,不用刀、叉吃饭,但是,这些孩子在同伴群体中学会了说英语和用刀叉吃饭。他们是从同伴群体中学这些社会文化的。研究还发现,如果在一个同伴群体中,各个儿童的文化和语言各不相同,他们必然会创造一个新的、大家都认可的同伴群体文化。上个世纪夏威夷岛移民语言的产生和演变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19世纪初,一批移民来到夏威夷开荒、种植甘蔗。他们来自各地,有不同的母语。最初,为了相互交流,他们创造了一种从语言学角度看很不完善的“皮金”语。这种语言没有介词、定冠词,动词不变位,也没有固定的词序,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说皮金语时总是带着自己原来母语的口音。大约100年后, 移民的后代又创造了一种新语言“克列奥尔”话。这种语言发展相当完善,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意思和思想,而且新的年轻移民说的克列奥尔话都是一样的,再也听不到他们父辈那些形形色色的口音了。“克列奥尔”话的产生过程很有趣。当最初创造了这种话的年轻人回到家里时,跟他们的父母仍然说“皮金”语,但一出家门,就和同伴讲“克列奥尔”话。而他们的父母一直到死,也没有几个人会讲“克列奥尔”话。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认为,儿童同伴群体一旦形成,就成为儿童社会化发展的主要场所。儿童从群体学习社会文化,形成自己的群体文化。对那些违背了群体规则的儿童,同伴会给予严厉惩罚。儿童正是在自己的群体中学会了怎样在公众中行事,怎样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于大家,怎样认识别人和自己,从而形成自己的社会性,完成了社会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成为他们个性的组成部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简言之,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认为,儿童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独立地习得了两套行为系统,一套用来适应家庭内部的生活,一套用来适应在社会上的生活。家庭对儿童年幼时最初社会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后来逐渐减弱、淡化,被群体影响所取代。每一个儿童都必然要参与并认同于一个社会群体,在群体中学会在社会公众中的行为方式,在儿童群体中,共有的群体文化、规则和准则及其同化作用所导致的文化传递,使得群体中各个儿童变得十分相似;同时群体中也存在着由于等级地位不同和社会比较机制而产生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是造成来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个性差异的一部分原因。儿童在家里也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也存在着家庭内部的社会比较,但这些相对来说影响较小。举例来说,来自同一家庭的两兄弟后来上了不同的学校,每个学校有不同的校风、班风,而这两兄弟在各自班里的地位又不同,哥哥所在班级班风好,学习空气浓,而且他始终担任班干部,而弟弟所在班级则是一个“乱班”,他又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哥哥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热情、善交际、自信心强、品学兼优的学生,而弟弟则变成一个不善交际、自卑、成绩平平的学生。应该对这一结果负责的,不是家庭,不是父母,而是他们所在的学校和班级。也许正是这一机制,导致了来自同一家庭环境的兄弟姐妹的除遗传和测量误差之外的另外30%的个性差异。
四、从我国文化出发评价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
美国心理学者J.R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新角度。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没有什么影响”,儿童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同伴群体中完成的,这种论断和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家庭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完全不同,同过去在我国很有市场的所谓“家庭烙印”的观点更是格格不入。因此,首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理论。在用我们自己的研究去验证这一理论之前,不妨先结合在我国文化中发生的一些事实,加以思考。
在我们周围,当一个孩子长到五、六岁时,常听到他们的父母说,孩子变得“自己有主意了”,“不那么听话了”。假如这个孩子不爱吃某一种食物,父母无论怎样说都不管用,但是当他跟五六个同年龄的孩子在同一个饭桌上一起吃饭时,他挑食的习惯却慢慢改了。同样地,一个一到医院打针就大哭的孩子,妈妈劝不管用;但如果让他和几个同年龄、但不怕打针的孩子一起打针,他也不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用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种现象。当原来挑食的孩子看到别的孩子都吃这种食物的时候,自己之所以也跟着吃,是因为,吃与不吃这种食物对孩子有了社会意义。如果他在孩子中不吃而别人都吃他也许怕别人笑话,也许要显示自己不比别人差,也许什么也没想,只是对同龄伙伴的单纯模仿。不管怎么说,是同伴这个“社会”改变了他挑食的习惯。而家庭这个“社会”则对他无济于事,他回到家里,还是继续挑食。
再举一个人人熟视无睹的例子。假设一对夫妻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南方调动工作到了北方。这对夫妇的普通话说不好,要说,也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他们在家里完全说家乡话,对孩子也说家乡话。可是非常奇怪,当孩子长到三、四岁时,说的却是一口北方话。当他长到十五、六岁时,他就更是象别的孩子一样,说着满口纯正的北方当地话了。
在学校教育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东西:从穿着、发型、说话的口气和用词,到所爱好的音乐和形形色色的各类明星。他们大多不会回到家里跟父母滔滔不绝地讲这些事,他们越来越觉得跟父母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也不会傻到经常干多数同学都恨的一些事,如向老师打小报告。一旦一个班的学生都认为某个老师不好时,他们会齐心协力地和这个老师作对,背地里说他的坏话,给他起外号。
为了验证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最近我们设计了一项研究,向中学生提出了6个有关群体与家庭影响的问题, 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假定你很想买一件衣服,父母没时间陪你去买,他们给了你一笔钱,并要求你买某一种式样和颜色的衣服。但父母要求的衣服式样和颜色跟同学们的看法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你将按照父母的建议去买,还是按照同学中流行的式样去买?为什么?
结果发现,多数中学生回答:“按照同学中流行的式样买”。这一结果基本反映了当前我们中学生的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揭示我们,我们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第一线工作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应该更加重视学生群体的建议,我们作为学生的长辈群体,应该在文化传递中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在学生心目中威信很高的老师,大多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活动,一起玩,说学生说的话,听学生爱听的音乐,身上充满“孩子气”。用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来解释,当这样的老师出现在学生中间时,学生实际上是把他当作自己群体的一个成员来看待的。如果他再具备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他自然容易在学生心目中形成威信,这种威信主要不是来自他的教师身分所给予他的固有权威,而是来自他在学生群体中的“头儿”的角色。这样的教师,将会对学生群体风气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作用,如哈里斯所说,将远远大于家庭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里斯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提出其理论的。而社会学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东方的家庭关系模式与西方不同,家庭中两代人的关系,东方比西方远为密切。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较早地鼓励孩子独立,到18岁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断绝了经济联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在中国,情况大相径庭,中国的家长往往管了儿子管孙子,他们不仅心甘情愿地为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和前途负责,而且不希望孩子过早地独立。这种现实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从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中汲取些什么的话,也必须充分地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成分。
标签: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