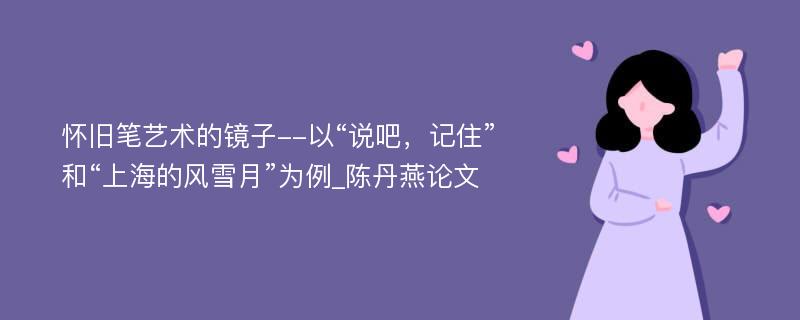
怀旧之笔 艺术之镜——以《说吧,记忆》和《上海的风花雪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说吧论文,风花雪月论文,上海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2)-02-0126-12
怀旧(又称乡愁)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体验和文化情愫。在经验和美学范畴里,怀旧主体通常以个人形式出现,但怀旧折射着个人所属群体的文化传统、集体(无)意识、身份建构和生活理想。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怀旧,反映了农人对故土深沉的眷恋。漂泊不定的游牧者总是怀想或向往一片青青牧场,表达了一种落地生根的梦想。远航的水手在星空下思念遥远的故乡,是对岸上家园的牵挂。在(后)工业时代,怀旧情感的导向更加复杂多维,在时间维度上指向失落的传统和历史,在空间维度上指向想象的家园和现实的居住地,在心理维度上寄予对前现代生活方式惆怅的向往,表达了怀旧主体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寻,及其对断裂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根据珍尼斯·多恩(Janice Doane)的看法,怀旧不仅是一种感伤情绪,还是一种修辞实践[1:3-15]。怀旧诉诸艺术表现,艺术符号充当怀旧书写的媒体。中外著名的怀旧文学表达不胜枚举:荷马的《奥德赛》,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鲁迅的《故乡》,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怀旧文本的深层结构如下所示:在“家”—离“家”—想“家”—寻“家”—回“家”。怀旧书写的意义内核是“家”、“家乡”或“家园”,其诱因是离“家”或“家园”的失落,其表现形式为想“家”或思“乡”,其价值目标是回“家”。赵静蓉在《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一书中指出,“人类必须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某种突然中断、剧烈分裂或显著变化的生活经验,才有可能生长出怀旧的情绪,而怀旧就是现代人思乡恋旧的情感表征,它以不满现实为直接驱动,以寻求自我的统一连续性为矢的,它正是现代人为弥补生活的不连续性而自行采取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①[2:2]在现代语境中,怀旧就是现代人的一次精神“奥德赛”,是现代人重返梦中“伊萨卡”的心路历程。
本文对跨文化语境中的两个怀旧文本——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和旅美作家陈丹燕的文化随笔《上海的风花雪月》进行比较阅读,从怀旧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分析“文化的怀旧”与“怀旧的文化”两种怀旧文学表达的区别:前者属于带个人性质的精神性追求,后者属于非个人化、趋同性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笔者借助“怀旧之笔”和“艺术之镜”两个隐喻,观照怀旧书写与时间、记忆、空间、历史的纠缠关系,管窥纳博科夫和陈丹燕在价值标准和美学取向上的差异性选择。
一、文化的怀旧与怀旧的文化
作为一种“回望”和“内视”的精神活动,怀旧具有明显的选择性、意向性和构造性。怀旧主体在过滤时光、净化记忆、凝固空间的过程中,有选择性地激活或再造过去的经验,赋予过去时光价值和意义。过去不一定美丽,但怀旧必然是美丽的,是“蓦然回首”时的“灯火阑珊”。一次怀旧,就是一次赋意行为(meaning attribution)。生活在当下的主体,对此时此地的现实做出回应和判断,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经过记忆发酵后对过去进行粉饰和美化,过去幻化为完美的曾在,充溢着高贵脱俗的价值,怀旧情结油然而生。不断地召唤过去,使主体对过去产生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怀旧自然成为此在主体通达彼在精神乐园的渠道和媒介。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导致怀旧情结的发生、形成和定型,怀旧情结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情结。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自传体回忆录《说吧,记忆》堪称怀旧经典之作。②纳博科夫式怀旧是流亡生活背景下的“追忆似水年华”。就主题和创作意图而言,《说吧,记忆》可以被纳入流亡文学之列。根据李小均的观察,“乡愁是流亡文学永恒的主题,家园的失落与怀乡的冲动是流亡文学的经典标志”[3:8]。但就叙述模式和艺术情绪而言,它又与常规的流亡文学相去甚远。常规的流亡文学往往表现为模式化的苦难叙事,流亡者痛失故人、故园、故国,发出“人不再人、家不再家、国不再国”的悲叹,通过哀怨、愤懑、仇恨、颓唐、沮丧、绝望等消极情绪的宣泄,确认自己的流亡者身份,且常常栖身于流亡群体,从中获得归属感。现实生活中的纳博科夫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不信怨天尤人的爱国主义和政治,厌恶餐馆和咖啡厅,不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忏悔,不喜欢结伴旅行。无论生存境遇如何,他总是“在一个新的、挚爱的世界里”,学会“感到无拘无束”[4:331]。作品中的纳博科夫多为从容淡定的行吟者,从不刻意渲染流亡生活之苦,从不宣泄流亡者之悲,而是用“美妙”、“快乐”、“神奇”、“完美”、“爱”等字眼写下另类的流亡诗篇。他把自己的一生形容为“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在俄罗斯祖国度过的20年构成“那命题弧”,在英国、德国和法国自愿流亡的21年“提供了明显的反题”,而在移居国度过的时期构成了“合题”和“新的命题”[4:329]。他坦然地说:“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时,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万其他俄国人,过着一种奇特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苦和思想的奢华之中。”[4:330]
纳博科夫大半生飘零,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是战争和流亡的牺牲品,是无根的浮萍,具有萨特所谓的“无根性”[5:65-66]。但记载纳博科夫流亡生涯的《说吧,记忆》却未流露出“生如浮萍”的悲情。全书给人一种“有根”的温暖和踏实。纳博科夫的俄国主要不是指一片广袤的疆土,一个专断的政权,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而意味着文化故乡和语言乌托邦,其精神从4岁开始就在那里生根。那精神根系“能够越过一些障碍,穿透另一些障碍,巧妙地爬进狭窄的缝隙,从而横跨漫长的距离”[4:367]。尽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未丢弃从祖国携带出来的母语文化行囊,里面装满普希金和丘特切夫的诗歌、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散文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以及伟大的俄国自然主义作品。纳博科夫的“怀旧”具有动词属性,表明了一种姿态、一种立场,是作者对俄罗斯黄金时代的隔空眺望,对俄罗斯绚烂的文化传统绵延的渴望,那份渴望凝结成最高贵的乡愁。纳博科夫始终保持着精神贵族和文化精英的“那双眼睛,那个微笑”,尊贵地活着。
如果说纳博科夫是俄国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守望者,那么陈丹燕就是上海殖民文化+小资情调的玩赏者和消费者。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上海文化史书”接连问世,掀起了阵阵“怀旧风”[6]。上海“怀旧书写”的核心人物之一陈丹燕以“时光旅者”的身份,穿越60年风尘,翻阅一桩桩陈年旧事,把玩一件件旧器物,浏览一张张旧照片,寻访一栋栋旧房子,走过一条条旧弄堂,从中捕捉旧上海的风华气韵,感受那花花世界的声色犬马,最后把走马观花的印象化成“风花雪月”的文字。陈丹燕的怀旧之旅充其量就是一次旧上海文化的消费之旅,旅者更多地从当下流行的时尚、消费意识和审美趣味出发,玩味流光声色的历史,与消费文化潮流亦步亦趋。戴锦华在《隐形的书写》一书中指出,“如果说精英知识分子的怀旧书写,旨在传递一缕充满疑虑、怅茫的目光,那么,作为一种时尚的怀旧,却一如80年代中后期那份浸透着狂喜的忧患,隐含着一份颇为自得、喜气洋洋的愉悦。”[7:107]
世纪之交,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繁华国际大都市。上海“梅开二度”的繁华,使上海年轻人尤其向往不属于自己的美好过去,对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莺歌燕舞的百乐门、富丽堂皇的花园洋房和小资生活生出浓浓的怀旧之情。媒介和商家迎合并利用上海人的心理需要、文化诉求和消费欲望,仿制五花八门的“旧”文化俗物,煽动现代欲望主体的“恋物癖”(fetishism),为其供应精神抚慰品。商业化怀旧的“卖点”在于文化体验,即“以当下的体验置换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以视觉化的怀旧之情替换本真性的深度历史感”[2:357]。在消费文化背景下,亲历历史的直观感受和经验显得无足轻重,过去的一切都可以被制作成符号,为消费主体提供大众化的精神消费。在此,麦克卢汉的观察可谓精辟:“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经验转换为新的媒介,确实赐予我们愉快地重温过去知觉的机会。”[8:264]
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怀旧”是带修饰性的形容词。怀旧对象——上海,是陈丹燕不曾经历也无心回归的地方。在租借时代的旧上海,其实无根可寻,无根可留,无根可守。陈丹燕写道:“骑车的老人也是坐船到上海来的,只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发财。可为什么他怀念从来不属于他的那种上海世面?……好像是他失去了根,好像是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好像是他终于能在缅怀里得到什么。”[9:129]陈丹燕对“镀金时代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存有隐忧,害怕“价值判断中的文化意义会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一切都因为标上了价钱而庸俗”[9:47]。尽管如此,她仍旧是上海怀旧文化成功的消费者、制作者和经销商,其怀旧书写散发出浓浓的商业气息。
二、时间的失乐园与记忆的复乐园
怀旧书写是保存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记忆形式包括“自传性记忆”、“传记式记忆”和“想象性记忆”等,记忆类型可分为听觉记忆、视觉记忆、映像记忆、语义记忆等。④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是关于“自传性记忆”的言说,同类作品包括英国作家斯特雷奇夫人(Lady Strachey)的《漫漫人生路的回忆点滴》(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忆旧》(A Sketch of the Past),美国作家艾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的《往事回眸》(A Backward Glance)。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可被归为“传记式记忆”,主要是根据口述材料、档案资料等二手材料写成的文化随笔。无论记忆形式和记忆类型如何,都是时间意识的不同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书写可被视作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文化诗学实践,是德里达所谓的“时间修辞学”或“记忆修辞学”[10:67]。在某种程度上,怀旧的意义在于“占有时间,维系个体的历史感,以抵御时间的流逝对个体所造成的放逐感和恐慌感”[2:38]。然而,时间是不能被真正占有的,我们在拥有时间的同时也在失去时间,时间永远流逝着,不可挽留,不可抗拒。在时间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有者。占有时间不过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想。恰恰由于时间的不可得性,人类才分外珍视曾经拥有和可以拥有的记忆,在记忆中维系其自足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幻觉。
纳博科夫把时间视作一个封闭的空间,一座“球形的监狱”。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尝试,都找不到出路,只能被终生囚禁。但记忆是那“不具个人色彩的黑暗中最微弱的带个人性质的闪光”[4:4],能够从时间之墙细小的缝隙里渗透进来。纳博科夫式怀旧,其实是个体摆脱时间禁锢和抗拒时间暴政惟一的手段,也是他寻找失落的童年伊甸园的惟一途径。纳博科夫写道:“在我的美利坚的/天空下怀念/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4:69]。在纳博科夫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里,怀旧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生活目的本身。纳博科夫执着地怀念着自己在时光中永远失落的精神乐园。
青年陈丹燕把自己的精神根系种植在遥远的欧洲,那里成为她梦中的家园,常常撩拨莫名的乡愁——“是指导,把他心中象征着全部无法形容也无法想象的生活的美丽欧洲,像树根一样从他的心里插进我的一片空地的心里,使它疯狂地生长,盘根错节,以至于永远不能收拾”[9:354]。中年陈丹燕的怀旧留有社会记忆的印痕,鲜有“带个人性质的闪光”[4:4]。《上海的风花雪月》产生于上海人的集体怀旧之中,同时又浓化了上海的怀旧氛围。陈丹燕写道:“但,上海这地方实在是怀旧的,像破落贵族的孩子那样地怀着旧,他没有正经过上什么好日子,可天生的与众不同。那见所未见的辉煌在他的想象里,比天堂还要好。”[9:26]陈丹燕为当代上海人精心绘制了物质的复乐园——“现在要说八十年代是旧时代了。九十年代已与租界时代的上海在物质和物欲上对接,完成了血缘上的回归”[9:169]。她彷徨在真实的家园和想象的家园之间,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无所归依。由于文化“不适症”,青年时期种下的“精神之树”并未开花结果。
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在于你可以回到熟悉的地方,却回不到熟悉的时间中去。记忆中的时间不能用现实来检验,只能靠主观意识来衡量,而主观意识这个尺码又在不断变化着,难以充当可靠的衡量标准。时间的长短快慢,空间的大小宽窄,有赖于主观意识。尽管如此,怀旧主体仍然可以利用记忆材料“发明”一个心理坐标:时间为横轴,空间为纵轴,时空交叉点为意识的中心点或原点。怀旧主体以记忆为纽带联结时间和空间,将时间空间化并将空间时间化,从而打破机械时间匀速、单向的流动,改变空间在心理坐标上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怀旧的时间向度永远指向过去,是记忆后视镜中的回望,是转过身来的召唤。怀旧的空间不像物理空间那样无限敞开,而具有封闭性,它是一个心理空间,是记忆库,是记忆停留和累积的地方,具有超大的容量。
记忆犹如一面后视镜,映射着过去的岁月。过去不可逆转、不可挽回,只有图像和文字才能重现它。作为“时间修辞学”的怀旧书写往往由记忆碎片累积和堆砌而成。纳博科夫的回忆录充满繁琐的生活片段、细碎的日常话题、粗线条的人物素描。读者眼中的这些碎片是作者珍藏在记忆中的钻石,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的童年的和谐世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几乎不用什么努力就能够写下来;只有在进入青春期的回忆的时候摩涅莫辛涅才开始挑剔,找起岔子来”[4:9]。记忆碎片不断填充着维拉庄园、圣彼得堡、剑桥、巴黎和柏林等现实空间,并成为纳博科夫构思棋题的素材,“伴随着想出这样一种象棋排局的过程的是一种半音乐、半诗歌,或者确切地说是诗歌数学式的灵感。”[4:344]大量的记忆碎片组成一个美丽而简洁的棋题世界,它结构精美,主题模式丰富多彩。编制棋题,帮助纳博科夫排遣了从人间天堂跌落下来的荒谬感和恐怖感。而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记忆累积多以一种非个人化方式进行。陈丹燕关于普希金雕像、“朱丽叶阳台”和修女院的个人记忆消散在上海阴霾的天空下,成为历史的浮尘,沉积下来的是上海年轻人对“东方巴黎”的集体想象和集体记忆。陈丹燕说:“对于1931年的怀旧,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用一小块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碎片,努力构筑起一个早已死去的年代。”[9:12]上海1931年留下来的碎片(如:一张拜耳大药厂的阿司匹灵药饼广告、一张旧结婚纸、双妹嚜生发油的玻璃瓶、美国的老无线电、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烘托出陈丹燕对“彼在”文化(欧洲文化)和“彼时”文化(上海租界文化)错位的怀念。
除了碎片连缀,意象叠加也是记忆累积的主要方式[11:409]。纳博科夫和陈丹燕都喜欢用意象叠加和累积的方式来构筑叙事空间,试图把二维的纸上空间变成三维的叙述空间,使之在阅读感受上具有丰富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在《说吧,记忆》中,彩色玻璃球、弧线、水晶蛋、蝴蝶等意象繁多茂密,构成童年伊甸园的完美形象,一个“名副其实的视觉和触觉的极乐园”,永远保留着“神奇完美的光泽和色彩”[4:8]。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1931’S咖啡馆、裘德酒馆、和平饭店、外滩的三轮车、旧货街、弄堂等意象重重叠叠,组合成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面貌。异域色彩和乡土图案“混搭”构成上海文化的底色,殖民文化、买办文化、市井文化、港口文化、移民文化的杂交是上海文化的精髓,其存在本身就是怀旧的理由。在《说吧,记忆》和《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碎片和意象统统成为记忆符号,或开启记忆,或保存记忆,或抹除记忆。碎片连缀和意象叠加使得线性叙事空间化,拓展了作为“时间修辞学”或“记忆修辞学”的怀旧书写的叙事空间。
三、主观的历史与历史的主观
怀旧是人类主观意识的产物,怀旧书写是关于主观意识的想象和表现。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活动,记忆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文化的,既是随机的也是建构的。记忆的发生、选择、存储、整理和遗忘,时时刻刻与文化实践活动发生着关系。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充满着盲点、遗漏、删减和歪曲。记忆时而遮蔽,时而揭示,时而真实,时而虚渺。记忆筛选、删除、更改、夸大、缩小、歌颂,也毁损,但记忆最终会创造出自身的现实,一种属于自身的真相。记忆的主观性减损了记忆的可靠性。不论什么样的记忆方式和记忆类型,都会产生屏蔽效应。生活经历被投射在记忆的帐幔上,光阴荏苒,空间变化,记忆痕迹随之变得模糊不清。由于记忆失真,关于记忆的叙事就无法保证其真实性。
当艺术家以个体的身份进入历史和阐释历史时,原来朦胧含混的历史真相被“揭示”或“敞开”,原来复杂完整的历史真相被筛选或歪曲。带有很强主观性和虚构性的“历史叙事”具备“揭示”和“遮蔽”的双重功能。赵静蓉认为,“一方面,怀旧保存过去,是美好的真理;另一方面,怀旧又‘遮蔽’和‘改变’过去,是虚假的谎言。怀旧所指向的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对象,但对这一对象的‘诗意’阐释却是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它不是一次完成的,根据怀旧主体所处身的现实情境的改变以及怀旧主体本身的心理变迁,主体、对象与其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变化。”[2:413]
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饱经沧桑的郭家小姐,南昌路上江青故居里气量狭小的蓝苹,美丽知性的莎士比亚专家张可,忧国忧民的国学大师熊十力,意气风发的学界泰斗王元化,大大小小的历史人物经过作者意识之镜折射后,半明半暗,半真半假。复杂动荡的时代历史被简化或省略:“我和这个娟秀老太太,中间隔了1949年解放,1957年‘反右’,1960年毛主席说以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6年打倒‘四人帮’,1992年经济起飞,这么多这么多,说着张爱玲的小说。”[2:54]这是对上海地下革命史、解放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文革史”的刻意回避。陈丹燕像剪辑电影胶片一样剪掉60年“大”历史,把今日复兴上海的国际化进程和旧上海殖民的国际化剪接在一起,制造了上海城市发展史的“蒙太奇”效应。它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新历史主义所谓的历史文本,是经过想象加工过的历史,是一种主观的建构物。⑤与其说作者是在书写历史,不如说是在改写历史;与其说是在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是在虚构另一种历史真相,一种浪漫化的“小历史”。“小历史”是另类的历史,是日常化、世俗化、民间化的主观历史。作者动用锋利的叙事之剪,把历史之布裁剪得零七八碎,用“大历史”所遗弃的边角料和花边拼凑成罗曼蒂克的“小历史”。
在纳博科夫的笔下,俄日战争(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等重大历史事件,时而以儿童游戏的形式展开,时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而退居历史后台,成为记忆彩排和表演的背景。例如,纳博科夫父亲的朋友库罗帕特金用火柴游戏演示战争场面:十根火柴首尾相连成一条横线,是“无风天气时的海洋”,呈“之”字形的火柴是“风暴中的海洋”[4:11]。一切客观现实都蒙上一层主观色彩,历史事件或日常事物本真的面目若隐若现,增强了历史的虚幻感。纳博科夫清醒地意识到记忆的反常和脆弱,他不仅张冠李戴,弄错日期和事件的细节,还混淆“小历史”和“大历史”的时间界限,把他“自己的年龄与世纪的年龄等同起来”,从而导致时间顺序上“一系列惊人的大错”[4:V]。为了揭开记忆的朦胧面纱,为了唤醒记忆的“睡美人”,为了保持总体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纳博科夫把更多、更细致的笔触留给个体瞬间的感受,40年人生被一笔带过,关于瞬间感受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却又细致精美如工笔画。所有的叙述因素都带有言说主体的内心印记,刻录着个体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的生命感受。
就阅读感受而言,《上海的风花雪月》的叙事结构形如方块,“小历史”被镶嵌在“大历史”的镜框里。由于“卖点”取代焦点,陈丹燕的怀旧叙事面目模糊、语调含混。而《说吧,记忆》的叙事结构呈扇形。纳博科夫以个体意识为轴心,以记忆为轴线,以历史为轴边,言说记忆和书写历史。他采取“守卫者”的姿态,固守原点,即个体的主观意识,任记忆的轴线延长或变短,任历史的轴边伸展或萎缩。多个扇形最终形成一个环形,那是作者在时间、记忆和历史中辟出的“微观”宇宙。纳博科夫写道:“宇宙多么小啊(袋鼠的育儿袋就能够将它装下),和人的意识相比,和个人的一个回忆及语言对这个回忆的表述相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4:9]。在绵绵不绝的回忆中,在对回忆周而复始的阐释之中,作者赋予有限的“微观”宇宙一种主观感受上无限的可能性:“从一个私人事件的温柔的核心——画出半径,直至宇宙极端遥远的地方”[4:354]。究其根本,那个“微观”宇宙是用语词做原材料,借助意象、主题、人物、地点、情节、修辞手段等构筑而成的艺术宇宙。纳博科夫终其一生都在摸索其边界和局限。
四、艺术的异化 异化的艺术
艺术是一扇双面镜,一面折射客观现实,一面映照主观现实。艺术的双重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使得艺术具有现实性和虚构性的双重属性,其现实性表现为艺术对世界的模仿和指涉,其虚构性体现在艺术的自我模仿和自我指涉上。艺术既连接又隔离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所谓外部现实,即此时此地的现实,是我们所观看、所聆听、所感受、所体验、所思考的日常生活现实、政治现实、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艺术主体疏离外部现实,遵循或偏离艺术成规,运用艺术符号和各种形式手段,诉诸想象,从而构造出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自足的世界和时空,一个情感和想象的世界,一种彼时彼地的存在,亦即艺术的内部现实。“艺术的世界是另一种现实原则的世界,是疏离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作为疏离,才能履行一种认识的职能;它传达不能以其他任何语言传达的真实;它反其道而行之。”[12:9]艺术的疏离常常产生异化效果,即对艺术指涉性“陌生化”的反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艺术的使命在于实现“艺术的异化”:“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13:51]。艺术又是一面多棱镜,许多条边组成许多个面,一个面就是一种颜色,一个角度就是一个世界;每调整一次角度,每玩味一次,就会获得不同的视觉印象和审美感受。多棱镜的魔力和魅力在于它是种种矛盾的统一体:它坚硬而脆弱;它本身缺乏温度但又能折射阳光的温暖,它原本透明无色,但却能呈现缤纷的色彩;它看似简单,但却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它凝固静止,却又能通过言说和叙事获得流动的时间感。一切琐屑的事物和生活细节,在艺术这面多棱镜的折射下,在时光中反复显影,幻化成艺术世界里的吉光片羽,带来审美的狂喜。
作为怀旧者的纳博科夫不断疏离历史语境和客观现实,返回过去,返回记忆的家园和想象的世界。现实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他对客观现实进行加工、编辑、剪裁,将之转化为记忆图式和主观感受,继而将之冶炼成艺术符号,以“历史的文本”的形式存留下来。纳博科夫主要借助隐喻来构筑自足的主观现实。“球形的时间监狱”、“彩色玻璃球里的弧形”和“魔毯”是3个关于时间、记忆和书写的重要隐喻,它们把记忆碎片连缀成统一的叙事。“球形的时间监狱”指物理空间中的心理感受,“彩色玻璃球的弧形”指记忆空间中的生命轨迹,“魔毯”指想象空间中的命运图案。纳博科夫的似水年华,渗入“球形的时间监狱”,汇聚成“彩色玻璃球里的弧形”,最后渗透在艺术“魔毯”的纹理之中。每一次记忆,就是“魔毯”的一次抖动和折叠,时间的纹理和命运独一无二的“水印图案”被呈现在读者眼前。每一次折叠“魔毯”,就是一次对记忆的整理,也是艺术对生活的塑造和定型。纳博科夫把无形的时间变成有形,把杂乱的时间变得纯粹,把不可感知的时间变成可感知的,需要“艺术的选择、艺术的融合和对具体时间的艺术的重组”[14:186-187]。“时间监狱”、“彩色玻璃球里的弧形”和“魔毯”等语言符号进入叙事空间,成为时间、记忆和生命存在的隐喻,激发了诗性感觉和诗性创造。纳博科夫摒弃怀旧的陈词滥调,借助隐喻式语言制造了多层多义、色彩斑斓的艺术空间。
处理怀旧主题时,作家意志的不同表现,决定着不同的艺术选择。纳博科夫选择了“守卫者”的立场:“两条胳膊在胸前一抱,身子向后靠在左边的门柱上,享受着闭起眼睛的难得乐趣,我会这样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感受隐约的细雨落在脸上和头发里,我听见远处断断续续的比赛声,想象自己是一个在英国足球队员的伪装下的创奇式的外来生命,用没有人能够懂得的语言创作一个关于遥远的国度的诗歌。”[4:318]终其一生,他都在秘密地守卫着那童年的伊甸园,那纯真年代的初恋,那俄罗斯,那失落的天堂。出于一种炽热而痛苦的精神渴求,纳博科夫的个体诗学体现为对艺术的精神认同。于他而言,“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艺术不是以现实的方式解决某时某地的社会问题,而是独特的文化传统,以自身的方式对创新提出的挑战;艺术家的作用在于指示超越感官世界的更高现实”[15:93]。当童年、家园、亲人、母语、故国都迷失在历史的天空下面,当纳博科夫只能一手举着艺术之镜,一手挥动怀旧之笔,奇迹般地勾描出“失而复得”的乐园,虽然它无法再现完美的过去,丧失了过去特具的温暖和感染力,但它毕竟保存了记忆的碎片和历史的痕迹,使之获得象征意义上的永恒。虽然它是一种镜中真实,一种虚构的真实,不是“更高现实”,但它不失为另一种自足的艺术真实。
在上海怀旧文化的背景下,陈丹燕采用“仿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和白描式语言,间或穿插着明喻和类比。例如:“一个城市的咖啡馆,就像这个城市的起居室一样”;“那里的一面老镜子,水银定得那么好,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考究而微微发黄”;“他紧握着那只把手,好像握着自己的过去”[9:5,52,174]。由于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着并联的、表层的联系,明喻起到消除时空间隔的作用,把此时此在的上海和彼时彼在的上海勾联起来,把镜中世界的主观真实变成仿真的超现实,消解了艺术和现实的距离和界限。陈丹燕的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合流的,而非疏离的。陈丹燕的写作立场和艺术选择多少带有媚俗的意味。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解释,媚俗的基本特征为“肤浅”、“廉价”、“垃圾性”、“庸俗”、“粗糙”、“炫耀”、“哗众取宠”、“虚假”等等,是为了迎合大众“最肤浅的审美需求”的“美学谎言”[16:252-253]。即便是她那“到处看到历史对接时讥讽的微笑”[9:374],也带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是对现实屈就和容忍的微笑。陈丹燕挪用商业化的怀旧文化,使怀旧书写落入大众消费文化的俗套。艺术成为被生活复制和批量生产的廉价艺术品,表现了媚俗的价值观。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作为双面镜和多棱镜的艺术变形为单面的梳妆镜,日常生活的广阔时空被框成镜中的风花雪月。只有艺术对世界平面化的映照,没有艺术自反的深度观照。那样的艺术因而丧失了异化日常生活的能力,它本身不免成为被异化的对象。
纳博科夫和陈丹燕的怀旧书写体现了两种相关而又迥异的价值立场和美学取向:个体与集体、生产和消费、精神和物质、超越和媚俗。如果说纳博科夫倾向于前者,那么后者就是陈丹燕的文化选择。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怀旧既是探寻、摸索和保存记忆的过程,直到记忆碎片形成独特而鲜明的个体感知,又是在越来越远离精神家园的时候挽留和守护“根柢”意识的艺术尝试。他从此在的现实中抽身而退,清洗并抛弃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和庸俗性,完成了自我精神上超越性“归乡”。在一部精神超越的回忆录中,纳博科夫引领我们接近、熟悉和感受那种“艺术的异化”——艺术方舟的构筑与栖居。纳博科夫建造的艺术方舟存在于世俗洪流的咆哮和恐怖之中,而又独立于生活的暴风骤雨之外,永远驶向失落的天堂,即“诗意栖居”的天堂。《上海的风花雪月》产生于上海的怀旧文化之中,迎合了一批上海小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心理需要和文化诉求。这种怀旧与大众消费文化形成暧昧的共谋关系,着意于对时尚趣味的模仿。陈丹燕笔下的风花和镜中的雪月,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消费文化情调和风格,实质上是异化的艺术,媚俗的艺术。异化的艺术迷失在物质里和潮流中,沦为生活的镜像,变成欲望深渊里模糊的倒影。其虚弱的反光稍纵即逝,缺乏艺术之光持久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无法点亮个体生命之灯,无力照亮灵魂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只有集体无意识的“回望”,没有个体有意识的“内视”,“回家”的价值目标就会落空,就会导致某种怀旧“传染病”。弥漫的“怀旧病”极有可能制造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功能性障碍,使文化步入迷途。
注释:
①《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怀旧主题的专著。作者赵静蓉以现代文化转型和现代性冲突为问题情境,从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和问题视角切入,对怀旧进行理论构建和文本解读,深入考察了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发掘了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性。
②纳博科夫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圣彼得堡和城郊的维拉庄园度过幸福快乐的童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两年之后,纳博科夫随家人踏上了漫漫的流亡旅途,先后辗转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1940年迁居美国,1959年辞去美国大学教职移居瑞士,直到1977年病故,至死未能回归祖国。其自传体回忆录书名几经更改,从美国版(1951)《确证》到英国版《说吧,摩涅莫辛涅》,再到“The Anthemion”,最终命名为《说吧,记忆》,被翻译成俄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国文字。
③陈丹燕因《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这“上海三部曲”名噪一时,故被媒体冠以小资“教母”之名。
④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Douwe Draaisma)对时间与记忆、知觉与记忆、遗忘与记忆、脑损伤与记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着重分析“自传性记忆”、“闪光灯记忆”、“绝对记忆”、“怀旧情结”等记忆形式和类型。参见杜威·德拉埃斯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张朝霞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⑤根据葛林伯雷、怀特等新历史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文本,是关于历史的阅读、释义和阐释。“过去性”并非历史的全部属性,而包含着“当下性”,反映着时人的利益、立场和观点,渗透着主观因素。参见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5、293、2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