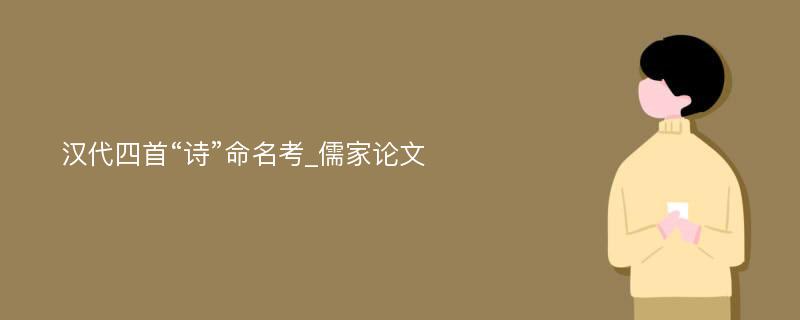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四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9-0103-06
汉代传《诗》者主要有四家,即鲁、齐、韩、毛,《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1](P1708)其中《鲁诗》《齐诗》以本学派宗师的故国命名,《韩诗》《毛诗》以本学派宗师的姓氏定名。显然,就其命名而言,或以国名或以姓氏,并不整齐划一。那么为何会如此来命名,四家《诗》之名又起于何时呢?
一、《鲁诗》《齐诗》之称在鲁学、齐学观念明晰之后
王应麟说:“《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齐、鲁以其国所传,皆众人之说也;毛、韩以其姓所传,乃专门之学也。”[2](P1395)但由王氏所引《汉书·儒林传》之语是看不出王氏所言之意的。实际,鲁、齐亦为专门之学。《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1](P3608)申公虽学《诗》于浮丘伯,但其“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其开创之地位显而易见。据《汉书·楚元王传》,申公同学复有鲁穆生、白生,只有申公“弟子为博士十馀人”、“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1](P3608)。故《鲁诗》创始人为申公无疑。又《史记·儒林列传》:“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3](P3124)《汉书·艺文志》说“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1](P1708),荀悦《汉纪》:“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亦作《诗外、内传》。”[4](P435)辕固为《齐诗》创始人,《齐诗》亦为专门之学。
既然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何以《鲁诗》《齐诗》不以创始人姓氏命名呢?就汉代各经派来看,一般皆以创始人的姓氏命名。若说例外,则为《鲁论》《齐论》。《汉书·艺文志》:“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1](P1717)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皆传《齐论》,皆不知其学所自。可能《齐论》在齐地流传非常广泛,故以上诸人学源反而难以知晓。《鲁论》的问题也当如此。而《鲁诗》《齐诗》却是专门之学。
汉代有齐学、鲁学之分。《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1](P3618)在先秦,齐、鲁两地儒学都较为盛行,《史记·儒林列传》:“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3](P3116)又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3](P3117)由于两地不同的文化与风俗,两地的学术也存在差异。盖而言之,鲁学谨严,谙于典章;齐学好议论,与阴阳五行学说关系较密切[5](P46-48)。程元敏说:“鲁为孔子故里,夫子经学教化,鲁学早成显派;齐有稷下,诸家讲经,游学其间,次鲁学而亦早为经学重镇。战国中晚叶,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师为荣。故言《诗》则《鲁诗》《齐诗》,言《论语》则《鲁论》《齐论》,而韩婴、毛公讲论于燕、赵、河间国,学风非盛,远逊齐、鲁,故不足以《诗》学大宗——《燕诗》《赵诗》或《河间诗》而尊称之也。”[6](P24)说燕、赵学风非盛,故不得命名为“燕诗”、“赵诗”,应该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依次介绍战国以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宋、卫、楚、吴、粤等地的风俗,唯于齐曰“其士多好经术”[1](P1661),于鲁曰“其民好学,上礼义”[1](P1663)。但说“鲁学早成显派”、“战国中晚叶,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荣”,则是混淆概念之论。齐、鲁两地已经存在的学术差异和人们对其较清晰的认识并不是一回事。
韦贤、夏侯胜、史高言《榖梁春秋》为鲁学、《公羊春秋》为齐学,则在宣帝即位时已经有明确的“鲁学”、“齐学”的说法,但却不能据此推断这种说法始于何时。再看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语,也看不出汉初是否有“鲁论”、“齐论”的说法。因为《艺文志》所举诸人,没有汉初人。王吉为昌邑王中尉在昭帝时,宋畸为少府、夏侯胜为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庸生授张禹《论语》并在宣帝世,贡禹为御史大夫、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皆在元帝世。萧望之《论语》学出于夏侯胜,张禹先事王吉、后事庸生。龚奋、扶卿则活动时间不可考。要之,以上诸人即使习《论语》在其少年,也不会早于武帝时。据此,可以说,汉初在齐、鲁两地有不同的《论语》本子流传,即二十二篇本和二十篇本,且有不同的解说,但却不能说在汉初已经用“鲁论”、“齐论”来标识这两种本子及其学说了。再来看《诗》的情况,《汉书·儒林传》:“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1](P3614)韩生自称尝受《韩诗》,亦在宣帝时。元帝初即位,翼奉上疏曰:“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1](P3173),则在元帝时。但《汉书·楚元王传》说:“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1](P1922)楚元王汉六年(前201年)立,立二十三年而薨,则至迟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已经有了《鲁诗》的称法。不过,此很可能为追述。程元敏认为《鲁诗》《齐诗》为“尊称”。由于鲁地、齐地儒风盛行,颇为人们所推崇,故以其命名自然有尊崇的意味。但说申公自号其学为《鲁诗》,却与申公的性格不相符。《史记·儒林列传》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3](P3121)显然申公为学谨严。由此也可看出申公不是一个好自称誉的人。武帝初即位征申公,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3](P3122)。则申公在政治上也注重实践,表现出来的是求实、尚质的精神。而就“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一语来看,也有疑点。“世或有之”,似为注释之语,有证明“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之语的意味,但“世或有之”恰说明班固未曾见《元王诗》。“世或有之”无疑为班固语,而“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等等应该为刘向、刘歆语。《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1](P1921)杨树达说:“汉诸王未有记字者,此独记字。盖向、歆父子曾续撰《史记》,于其先世必有记述,疑班此传承用其文。”[7](P286)但《艺文志》却不著录《元王诗》,而《艺文志》是本于刘歆《七略》的。这样,对于《元王诗》何以不见于《艺文志》、班固何以说“世或有之”,学者也只能猜测,王先慎说:“《艺文志》不载《元王诗》,《志》本《七略》,刘歆不应数典忘祖,当是次而未成,故班史传疑云‘或有’,以示未成之意。”[8](P950)实际由班固“或有”是看不出《元王诗》“次而未成”之意的。
二、武帝置《五经》博士时尚未有《诗》派之分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申公、韩婴均于孝文时为博士,辕固于孝景时为博士,则文景之世,鲁、齐、韩三家《诗》已经立博士。”[9](P183-184)既然三家分立,自然应该命名。但这实际是出于对汉初博士性格的误解。汉承秦制。秦有博士七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3](P258)汉初因之,应劭《汉官仪》曰:“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馀人。”[10](P830)秦朝置博士着眼于其博通,主要备问古今,为施政顾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1](P726),《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10](P830)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初立,“召以为博士”[3](P2491)。贾谊之学不主一家,说明汉初博士也主要取其博学。秦朝博士学术品格比较混杂,为杂学博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3](P2720)叔孙通以通儒学而被任命为博士。《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羊子》四篇”,班固注曰:“故秦博士。”[1](P1726)《晁错传》:“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1](P2277)伏生为博士当为其治《尚书》而有成。《艺文志》“名家类”著录有“《黄公》四篇”,注曰:“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1](P1736)则黄疵为名家者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使博士为仙真人诗”[3](P259)。又“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3](P263),占梦博士又为数术之士。由此可见,秦朝博士或擅长“六艺”,或习“百家之语”,或为术数、方伎之士,品流复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公孙臣善言五德终始,正说明汉初所置博士不仅有习六艺者,而且也有习诸子、术数、方技者,学术品格恰与秦朝博士同。当然,杂学博士于博学中亦可能各有专门之业,甚且以某专门之业知名,因而得为博士。如叔孙通在秦朝以文学被召而为博士,又《史记·孝文本纪》:“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3](P429)“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3](P430)则公孙臣被任为博士,是因其善说“五德终始”,文帝以其为博士,也是需要他的专业知识。由此,再来看研习儒家经典者在汉初被任为博士的情况,《汉书·楚元王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1](P1922)《史记·儒林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3](P3122)“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3](P3124)“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亦为博士。”[3](P3124)《汉书·晁错传》:“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1](P2277)《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3](P3127)“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3](P3128)上引材料可分为两类,一为因治某经而为博士者,一为仅说在何时为博士者。就前一类来看,实际和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类似,既然不能说秦时设有文学博士,也就不能说汉初有《诗》《书》《春秋》等博士。既然尚无专经博士的设立,也就不能据此以为有经派的分立,更不能说已经有了为各派命名而区分各派的做法。赵岐《孟子题辞》:“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11]此语可能沿袭刘歆之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1](P1969)由赵岐所言,可以看出刘歆所说“诸子传记”即指《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但刘歆所言可能是对汉初博士的误解。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被征为博士,不言通何家,恰说明文帝时并未置诸子博士。刘歆、赵岐所言,一为争立古文而发,一为表彰《孟子》来说,是以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的情形来谈论汉初的博士制度。实际情况是,文帝所立博士中有习《论语》等诸子传记者,并非为诸子传记置博士。如此来看《后汉书·翟酺传》,“初,酺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12](P1606)文帝虽因申公、辕固治《诗》而以其为博士,因董仲舒治《春秋》而以其为博士,也仅为任申公、辕固、董仲舒为博士,并不能说明设立了《诗》《春秋》的博士,因而李贤注曰:“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文帝之时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据。”[12](P1606)则翟酺所言也是对文帝时博士性格的一种误解,因为某位学者因治某经有名而被任为博士,很容易理解为为学者所习之经置博士。
武帝立《五经》博士,实际是为了对抗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学,卫宏《汉旧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为高第,朝贺位次中郎官史,称先生,不得言君,其真弟子称门人。”[10](P831)这时的博士,仍沿用汉初博士“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的品格,仍主要做施政顾问。武帝立《五经》博士,也就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其他各家尤其是黄老学者不能进入其政治顾问团,无疑有向喜好黄老的窦太后示威的意味。这样,只要研习儒经而博学者就有成为博士的可能,并不包含习某经某派者才能成为博士的意味。也就是说,这时只是立了《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并未专立《鲁诗》《齐诗》《韩诗》《公羊春秋》博士。
武帝置《五经》博士是为了凸现儒学,那么其博士员数又如何呢?《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1](P726)学者们一般都依据“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之语断定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应为七人[9](P183-184),即《易》《尚书》《士礼》《鲁诗》《齐诗》《韩诗》《公羊春秋》各一人。但上已证明,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尚未分经派,故七人之说并不正确。再者,武帝置《五经》博士时也非经各一人。经各一人的做法可能始于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13](P215-221)。也就是说,在武、昭、宣、元朝,博士员数仍为七十馀人,与汉初同。《史记·儒林列传》:“(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3](P3122)申公主要在景帝及武帝前期教授,他的弟子则主要活动在武帝时期,所以这十几人为博士应该皆在武帝时,若说这十几人是次第为博士的,显然不合情理。《汉书·儒林传》:“(欧阳)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后为博士,论石渠。”[1](P3603)“林尊字长宾,济南人也。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1](P3604)欧阳地馀、林宾皆习欧阳《尚书》,则论石渠时欧阳《尚书》博士不止一人;又:“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1](P3610)“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1](P3611)张长安、薛广德皆传《鲁诗》,则论石渠时《鲁诗》博士也不至一人。《百官公卿表》“员多至数十人”并非仅指汉初的博士员数,更有可能是指两汉的博士员数。由于博士员数在变化,所以班固用了约数。实际情形也是如此。成帝以前博士员为七十馀人,在王莽时为三十人①,东汉立十四博士,经各一人②。而“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此部分则专就《五经》博士为论。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各经尚未分派,但在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后,各经派逐渐产生,故《诗》分鲁、齐、韩。至宣帝进一步分置,成十二家,故班固用“增”。这十二家,根据王国维的意见,为《易》施、孟、梁丘,《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9](P183-184)。当然,《百官公卿表》“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之“人”可能是“家”之讹,可能是班固以东汉博士制度来看西汉时而误。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也。”[1](P1969)在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先师说经尚粗略,其说相合才能解释一部完整的经书,故派别实际是不存在的。又《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1](P3617)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公孙弘为丞相在元朔五年,元狩二年(前121)卒于丞相任上。则《公羊春秋》之盛行应在公孙弘任丞相之后。如果武帝置《五经》博士时立了《公羊春秋》博士,就不待董仲舒与江公论辩了,武帝也不会于此时才尊《公羊》家。
三、《诗经》各派之命名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石渠阁会议之前
武帝于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但直到元朔五年才为博士置弟子,上距置《五经》博士已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博士主要作为政顾问,并不一定居官教授。而置博士弟子后,博士的工作转向教授、课试。但博士七十人,而博士弟子员才五十人,竞争于是起。《汉书·夏侯胜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1](P3159)“应敌”恰说明置博士弟子后博士间论难的兴起。而由于竞争,派别观念渐渐明晰起来。
《汉书·儒林传赞》:“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1](P3621)这“初”是指什么时候,有学者认为是武帝立《五经》博士时[14](P62),实际是以后来所立博士的情形来窥测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是错误的。《汉书·儒林传》:“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馀侍中,贵幸,至少府。……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1](P3603)欧阳生为伏生弟子,应该为汉初人,且在武帝时可能还在世。不过,在汉代经学中能“自名其学”者,往往是对原有师法、家法的改窜[15](P496-507)。但欧阳生似乎不具备这个条件。在欧阳生这一系中具有改窜师法条件的应为倪宽,倪宽既从欧阳生学,又受业于孔安国,可能会混合欧阳生和孔安国之学而有所发展。据《汉书·倪宽传》,倪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而据《百官公卿年表》张汤为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年),五年后迁,则其受业于孔安国在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其授欧阳生子则更在这之后,所以在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所谓的欧阳氏学尚未形成。何况,汉代经学中“自名其学”者往往都是为了与其他各家竞争而形成,就《尚书》中的大夏侯来说,主要活动在昭宣之世,也就是说,在武帝时尚未有促使欧阳氏之学形成的条件。同样,《汉书·儒林传·赞》所说《礼》后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后仓为博士不会早于武帝后期。关于《易》,《汉书·儒林传·赞》称《易》杨,可能是涉《史记》“然要言《易》本于杨何之家”而误,因为《汉书》不称《易》有杨氏学,《史记·儒林列传》也仅说:“(杨)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3](P3127)《汉书·儒林传》同。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说:“窃疑《诗》分齐、鲁、韩三家,其说亦后起,故司马迁为《史记》,尚无《齐诗》《鲁诗》《韩诗》之名。惟曰:‘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又曰:‘韩生……其言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燕、赵言《诗》者由韩生。’至班氏《汉书》则确谓之《鲁诗》《齐诗》《韩诗》焉。是三家《诗》之派分,亦属后起。……石渠议奏不及《诗》,是《诗》分三家,疑且在石渠后矣。”[16](P216)钱氏主要讨论三家《诗》分派的问题,不过就其论述来看,则以三家是否命名看作其是否成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依据钱氏所述,则三家《诗》命名在石渠会议之后。但这个看法并不符合实情。太史公不用《齐诗》《鲁诗》《韩诗》之名,是否能成为断定史公为《史记》时有无其名的问题暂且不论。石渠议奏不及《诗》并非《诗》尚未分,而是《诗》于此时无所增置,且“异议最少”的缘故。钱氏也于上引文字后随文注曰:“刘歆《移书》《汉书·宣纪》,及《儒林传赞》,列举诸经家数先后异同,均不及《诗》,非《诗》之分家最早,乃《诗》之争议最少耳。”而钱氏把石渠会议看作各经分派的开始,也可谓忽视了石渠会议的性质。《汉书·宣帝纪》:“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1](P272)既然是讲《五经》异同,则各经派已经形成,石渠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评判各经派之是非,其中虽然以平《公羊春秋》与《榖梁春秋》的是非为主,但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也应该对《易》各派、《尚书》各派的是非有所评判,而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石渠《议奏》来看,有《尚书》类、《礼》类、《论语》类,以及附于《孝经》类的《五经杂议》,几乎遍及群经,故不能说各经分派在石渠会议后。
《诗经》各派之命名应该是经学派性意识明晰的产物,从时间来说则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石渠阁会议之前。《汉书·蔡义传》:“久之,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敞为丞相,封阳平侯。”[1](P2898)元凤三年(前78)蔡义以光禄大夫迁少府。其授昭帝《诗》则在始元年间,也就是昭帝即位后不久。而昭帝特诏求《韩诗》,说明至迟在昭帝即位前,《韩诗》已经命名。蔡义为韩婴再传弟子,则为《韩诗》命名者很可能为韩婴弟子贲生、赵子之类。类此,《鲁诗》《齐诗》之名也应该是由申公、辕固弟子所命。就时间来说,很可能在武帝后期。可能司马迁为《儒林列传》时尚未有《齐诗》《鲁诗》《韩诗》之名;也可能已有其名,但使用尚不太广泛,故司马迁为《史记》不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由于利禄的刺激,竞争于是乎起,申公、辕固弟子尊崇其学,故以《鲁诗》《齐诗》来命名,韩婴弟子也以老师的姓氏来命名其学。
四、《毛诗》因三家各自命名而名之
关于《毛诗》,《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1](P2410),河间献王景帝前元二年(前155)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薨。献王立《毛诗》博士不知始于何年?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1](P741),则其置《毛诗》博士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之前。此时,朝廷尚未立《诗》学博士,献王之立《毛诗》主要在于崇尚学术,实际《毛诗》尚未具备形成学派的条件,则其是否有《毛诗》之名也是有疑问的。“毛诗国风”题下孔《疏》引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又引郑玄《六艺论》说:“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17](P2)二说显然是矛盾的。据《诗谱》,河间献王先得到《毛诗诂训传》,而后才以善《毛诗》的小毛公为博士,则《毛诗》之名在立《毛诗》博士前已经有了;依《六艺论》,毛公善说《诗》,而河间献王以其为博士,且命其所说《诗》为《毛诗》,则在立《毛诗》博士后。孔颖达等虽强为之说,却也无法疏通二说,故只能两说并存。孔《疏》:“不言名而言氏者,汉承灭学之后,典籍出于人间,各专门命氏,以显其家之学,故诸为训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为传,亦应自载‘毛’字,但不必冠‘诗’上耳。不然,献王得之,何知毛之为之矣。明其自言‘毛’矣。”[17](P2)此为《诗谱》说寻找依据,但所说理由都讲不通:“专门命氏,以显其家之学”,应是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的事了;“献王得之,何知毛之为之”,则是对《汉书》河间献王立《毛诗》博士说法的推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孔颖达等对上述推论也不自信,故又说“不必冠‘诗’上耳”,以表对毛公加“毛”于“诗”上的不解。又曰:“‘诂训传’,毛自题之。‘毛’一字,献王加之。”则又从《六艺论》。而陆玑又提出第三说:“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曰《毛诗》。”[18](P21)显然也是出于推测。
实际《毛诗》之命名也应与三家《诗》类似,是经派观念的产物。而《毛诗》之命名更在三家《诗》之后。陆德明谈及《毛诗》命名,虽也举郑玄两说,但说“‘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19](P53),无疑是正确的。故《毛诗》之命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为。
注释:
① 《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四年“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
② 《续汉书·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
标签:儒家论文; 汉朝论文; 论语论文; 博士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武帝论文; 艺文志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