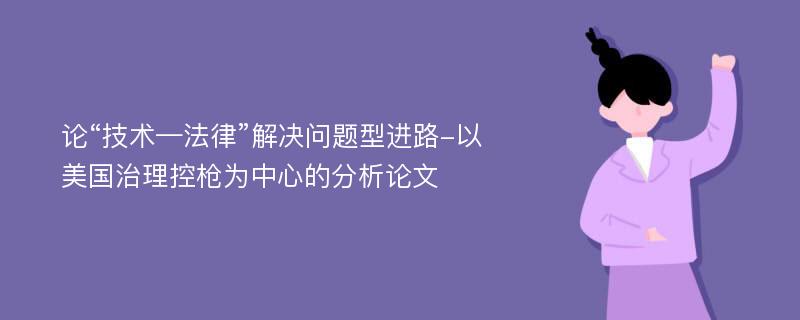
论“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
——以美国治理控枪为中心的分析
张 鹭1,侯明明2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 130024;2.吉林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长春 130012)
[摘 要] 关于美国枪支问题,国内法学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宪法—解释进路、枪支—宪制进路和权利—冲突进路。从宏观上讲,以上三种进路都有自身的研究特色和局限。从工程思维上讲,宪法—解释进路和枪支—宪制进路都属于解释分析问题型进路,而权利—冲突进路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来缓解美国控枪的困境,但是其是一种大词化的“权利冲突理论”,并未精细化地阐释到枪支问题如何解决,操作性不是很强。在此境遇下,“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进路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路径选择。此进路因为智能枪支技术的嵌入对身体和灵魂产生双重规训力而在理论上具有了治理控枪的可能性,而无线频率技术与生物识别技术的突破、智能设备使用的路径依赖、规训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下的财富最大化以及道德上的不可谴责性等条件使得此进路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进而,此条进路可能会迂回地缓解美国面临的枪支宪制下的民主困境。
[关键词] 宪法解释;枪支宪制;权利冲突;控枪;技术实用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奥巴马政府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禁止持枪与其他控枪命令在2017年2月被特朗普政府推翻以及2017年10月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音乐节枪击案造成59人死亡、527人受伤,同年11月德克萨斯州教堂枪击案使得正在祷告的27人死亡、25人受伤,2018年2月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导致17人死亡,2019年8月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大规模枪击案造成至少31人遇难等系列重大枪击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关于枪支的控制问题以及如何控制再次甚嚣尘上,进入到社会公众的视野,各种群体的抗议活动以及游说演讲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19年8月,已经退居幕后的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谈及枪支政策,他认为枪支法虽不能阻止所有谋杀,但是会有效遏制谋杀。就在2018年的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中,美国多地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枪支暴力,呼吁控枪;美国佛罗里达州议会受校园枪击案触动,同年3月7日通过一项控枪法案,允许部分教职员工持枪上岗、上调法定购枪年龄、为销售武器设定等候期。但是紧接着就受到了佛州州议会民主党众议员默卡多的质疑,而且美国步枪协会也对这一法案表示不满。在法案签署的几小时后,步枪协会就将佛州政府告上法庭,称禁止21岁以下成年人购枪的规定“不合宪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和第十四修正案。同时,也有很多企业宣布终止与美国步枪协会的合作[1-2]。就连具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最大枪支生产商雷明顿户外公司也在2018年3月申请了破产保护,以上事件继而引发控枪问题不断发酵[3]。再加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倾向、美国步枪管理协会等利益集团的干扰、移民国家的种族问题、持枪的文化传统、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美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公共政策执行的漏洞等因素的嵌入与博弈,导致美国控枪问题极其复杂,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一直未达成一致。在如此境遇下,凸显了美国制度性因素在治理控枪中的困境和悖论[4]。但是也正是这种极其难以把控的局面吸引了很多学人将研究聚焦于此,其中的解说与阐释也是纷繁复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的视角,还拓展到法社会学、法政治学等跨学科的进路。那么对于美国枪支治理问题,中国国内法学界具有国际视野并且关注此问题的学者是如何具体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有哪些特色以及局限?他们的研究进路是一种纯粹价值层面的逻辑演绎还是具体“枪支治理社会工程”的蓝图绘制?以及在现有的研究现状之外能否提出另外有效的研究进路?
笔者在文献梳理时,发现在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研究进路,所以对其加以抽象概括,提炼出核心的主题元素,将其类型化,最终总结出中国法学界关于美国枪支治理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宪法—解释进路、枪支—宪制进路、权利—冲突进路。(1)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进路的总结主要是从理论法学的视角去提炼的,与理论法学视角无关的研究进路并未得到关照,比如枪支文化的视角、民族性格的视角、枪支犯罪学的视角等。 接下来,笔者在第二部分中,依托体现这几种进路的典型论文对这三种进路分别加以阐释反思,试图找到这三种进路的优势和劣势;在第三部分,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一种“技术—法律”解决问题的总体进路,并对这种进路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加以论证。最后,笔者对此文中“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与传统法哲学分析解释型进路之间容易造成的误解给予了简单的说明和澄清。
夏日哈木矿区总共圈出铜镍矿体20条[3],其中HS26号异常区圈出8条铜镍钴矿体,含矿岩性主要为橄榄岩和辉石岩,其次为辉长岩,通过对8条矿体进行资源量估算,求得333+334镍金属量105.06万吨,其中(333镍金属量84.62万吨,334镍金属量20.44万吨),镍平均品位为0.64%;8条矿体中伴生铜金属量20.86万吨,铜平均品位0.169%;伴生钴金属量4.22万吨,钴平均品位为0.026%。
二、中国法学界研究美国枪支问题的三种进路
(一)宪法—解释进路
在美国,宪法的解释权归属于联邦最高法院,所以对于涉及枪支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一般都要以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作为蓝本,即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看持枪权问题。就目前看来,涉及到枪支问题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合众国诉杰克·米勒、弗兰克·雷顿案”“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麦克唐纳诉芝加哥市案”。[5-7]所以,宪法—解释进路主要是指学者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为依据,对其中涉及枪支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解释问题给予分析。[8-11]正如有学者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史,特别是晚近的司法史,就是宪法解释史。”[10]而宪法解释必然涉及到方法之争(2) 宪法学家张千帆认为,宪法的司法解释大体有四种:文字、结构、历史和目的。在“赫勒案”中,这四种解释方法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12-13]183-188比如原旨主义的解释方法、新原旨主义的解释方法等。[14-15]
(二)枪支—宪制进路
枪支—宪制进路主要是以枪支问题作为切入点,透视出枪支问题背后隐藏的美国宪制问题,比如,联邦和州的权力划分、三权分立制度、两党制、民众的抵抗权、选举制度等等,亦即枪支管制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还经常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美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枪支宪制”。而这些内容碎片化地反映在学者的研究当中,比如,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拥枪的选民越多,政客就越拥枪;美国立宪建国之时,最棘手的一个难题就是业已存在的各州与即将建立的全国性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16]。分别透视出的就是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和联邦制度。
其中,比较详细地从枪支—宪制角度论述问题的是蒋龑所著的《“枪支条款”还是“民兵条款”: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17]一文,其从立宪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追溯到北美殖民地的五月花号公约,到1776年独立战争,再到1787年宪法、1791年权利法案,一直到现在,将枪支涉及到的政治问题穿插其中,给予阐释。可以说,美国的枪支进化史就是一部美国宪制的演变史。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黄萌宇在其学位论文《美国枪支管制困境研究》中,通过对美国枪支管制困境中的个人基本权利与公共安全、立法与司法、联邦与州之间张力的描述,揭示出美国枪支管制所面临的困境归根结底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16,18-21]。这些论述都从某个侧面描述了美国的宪法制度。
2.3 transwell小室检测人前列腺癌细胞PC3侵袭能力 shRNA-NC组和pcDNA3.0组PC3细胞侵袭能力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KIP-shRNA组PC3细胞侵袭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和shRNA-NC组(P<0.05),pcDNA3.0-RKIP组PC3细胞侵袭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和pcDNA3.0组(P<0.05),pcDNA3.0-RKIP组PC3细胞侵袭能力显著低于RKIP-shRNA组(P<0.05,表2、图2)。
(三)权利—冲突进路
权利—冲突进路主要是指将冲突的两种或者多种权利进行理论和现实分析,运用相关的理论模型试图对现有问题进行解释。权利—冲突进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冲突权利的识别问题,即哪两种权利或者几种权利之间出现冲突。如果识别正确,那么接下来的论述可能是准确的,否则可能会出现方向性的偏离。具体到美国枪支问题,权利冲突进路主要是寻求美国枪支问题背后的多种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人持枪的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也可表述为个人持枪权与他人生命、健康权之间的冲突。在将各个冲突的权利逐一列出之后,试图在各种权利之间预设一定的位阶,按照优先权利优先保护的原则,对认定的位阶较高的权利给予优先保护;或者是提倡通过比例原则对各种权利进行调试权衡,对其各自的边界持一种动态的标准[22]。
三、对中国法学界研究美国枪支治理问题三种进路的反思
(一)对宪法—解释进路的反思
第一,仅限于解释方法之争容易忽视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在诸多的宪法解释方法背后隐藏的是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只谈方法,不谈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遮蔽了问题的实质。保守派大法官和自由派大法官各自所坚持的立场往往不同(3) 关于这一点,看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组成就会一清二楚。虽然大法官不归属任何党派,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因此大法官也可以划分为保守和自由两派。各个时期,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不同的。目前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加入之后,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包括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内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形成了五比四的比例,使得最高法院再现由保守派主导的局面。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曾毫不讳言地对国会关于法官提名确认的政治化倾向提出过批评,其提到:“我认为,让法官意识到他们不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这点很重要,让民众意识到这点也同样重要。法官通过裁决具体案件去影响政治分支的政府权力的范围是有限的。尽管解释宪法也是法官的责任,但法官不能毫无节制、不受拘束地按照自己理解的宪法含义作出裁判。” 。[23]其实,不管是涉及到持枪权的问题还是同性恋、堕胎的问题,其本身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甚至可以说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变为了一个关乎意识形态、价值立场的问题。大法官的基本立场已经“前见”性的决定了其在未来判决中阐释理由的裁剪性。如果只是一味地对大法官的解释以及意见进行批评,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就不可能理解大法官做出如此判决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大法官会遵从一种法律认知科学所讲的系统一,[24]先运用直觉对某个案件感性地做出一个结果,然后再仔细地审阅案卷,运用系统二进行理性化地思考,甚至有时候,根据系统一的直觉式思考会一以贯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官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系统一、系统二都会产生作用。即法官完全可以以一种“倒置”的三段论形式(4) 这种倒置的三段论形式又可称呼为后果导向裁判或者是司法裁判的“逆推法”。 ,[25-26]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得出结论,然后再根据结论倒推大前提和小前提,寻找可以得出符合自身政治立场的前提以及某种方式的核心法律概念理解。[27]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官裁判案件首先产生的是直觉,它将提供被遵守的假定,然后才是寻求法律根据以支持上述的智识性任务。”[28]24也正是这种倒置思维方式的可隐藏性以及判决外表的法律可包装性,使得宪法—解释进路仅浮于表面进行解释,而忽视了背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或者这种进路也已经意识到了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苦于无据可循以及深入研究的高成本投入,而索性策略性地自愿放弃了背后所潜藏的内容。
在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科技确实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是先于法律或法律理论而存在,以至于很多科技世界成为法律或法律理论的真空区域,但是其在其他机制的治理下,依然可以自洽而妥帖的生长,这恰恰说明了法律或法律理论的滞后性以及其本身万能论的祛魅。那么,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大有赶超理论之趋势,甚或在某些领域技术到位而理论缺位的背景下,把一些理论上处于棘手状态,难以达成一致共识的问题,我们可以先通过技术的路径将其解决掉。著名法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llen Posner)也提到:“我使用它(新实用主义)时,首先是指一种处理问题的进路,它是实践的和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是有效和有用,而不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36]1波斯纳的新实用主义侧重的是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实践操作的情境选择,而不是一味地遵循传统固认的普遍抽象理论。而个性化技术在枪支上的应用也因烙上了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而具有了以解决实践问题为指归的可操作性。
在这种进路中,规训机制和市场机制可能会实现某种程度的完美结合。由于技术规训下的智能枪支使用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其会生产出一种安全的枪支文化氛围空间,而这种空间在市场中具有比纯粹毫无安全措施的枪支存在较大的竞争优势,即使这种竞争优势不是存在于全部的群体,至少在女性或者顾忌家庭孩童安全的父母群体中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因为这些群体使用枪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安全性的保障。
(二)对枪支—宪制进路的反思
传统的法哲学分析问题的进路是从静态的意义上对价值问题进行分析,比如美国枪支涉及到的个人持枪权和公共安全之间的价值或者利益冲突问题,正如上文所讲,传统的法哲学分析只是聚焦于当下的利益或者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没有试图对当下的利益或者价值进行动态意义上的调整之自觉意识。亦即,传统法哲学的分析是一种“基于现状”的深入式分析,而笔者提出的“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总体进路是一种尝试通过“技术+法律”改变价值观念的方式来实现价值之间的转换,其是一种迂回却又不仅仅停留于分析层面的非常有功效的路径。这种功效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因为枪支技术的嵌入而对身体和灵魂产生双重规训力,从而在理论上具有了治理控枪的可能性;二是,无线频率技术与生物识别技术的突破、智能设备使用的路径依赖以及规训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下的财富最大化等条件使得此进路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三)对权利—冲突进路的反思
权利—冲突进路让我们对美国枪支问题涉及的各种权利冲突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特别是对个人持枪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可见,其对枪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一方面,权利—冲突进路之分析过于笼统以及过于宏观,分析问题的方式是粗线条和大词化的,不够精细,换言之,较之其所阐明的,它遮蔽了更多。笔者承认,宏观视角也是认识问题的一种思路,我们也经常讲到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但是权利—冲突进路不是一种新鲜的知识增长,而是学界的老生常谈。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法学界用一种宏大的视野处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方向指引性的重大治理问题,比如张文显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定位》、龚廷泰教授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法治实践动力系统》等[30-31]。权利—冲突进路这种宏观分析问题的思路对于人类知识积累不够的早期理解某些现象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知识异常丰富、思想逐步深刻的今天,如果再延续这种宏观的阐释难免有一种浮于表面的浅薄之感。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识到了技术作为一种规训方式在社会治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中的作用。他提到:“通过庄重地把犯罪纳入科学知识的对象领域,他们就给合法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不仅控制犯人,而且控制个人,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的现在、将来、可能的状况。”[33]20我们在枪支问题上可以利用此技术规训所产生的治理功能,对潜在的未来犯罪分子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训,实现其身体和行为的活动保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虽然正如意识终归是意识的,价值终归是价值的,但是技术可以改变价值观,智能枪支可以作为致力于改变价值观的个性化技术被嵌入。如果我们承认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最后归结到诸神之争或者价值之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价值的终归是价值的问题,亦即价值问题只能通过价值来解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使其得以演变。价值问题并非是一定要通过价值说服或者劝说的途径来解决,或者说,对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价值本身,亦即可以通过其他的非价值路径来影响价值的立场或者内容。著名法学家帕特里克·德富林(Patrick Arthur Devlin)在论述公众道德观念时提到,允许和容忍道德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相应的代际变迁[34]17-19。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虽然要通过价值来解决价值问题,但是前后的价值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如果通过“技术—法律”的途径可以改变美国公民的价值观,那么其最终仍是通过价值观来实现价值问题的解决,只不过,这里前后的价值观是有差异的,而枪支技术的嵌入就是其中的动力和启动装置。比如,技术实践的改变对价值观念的变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到美国枪支问题,则是技术型智能枪支的使用会逐步降低犯罪率或者伤害率这一基本的共识,如果基本目标达到了,民众自然是乐于接受的,即价值观上的认同。可见,枪支技术的运用也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中介,在技术实现的过程中本身就融合进了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意识演变的契机,从而实现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达至推动制度重新确认的目的。
四、美国治理控枪的“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
枪支—宪制进路是在对宪法—解释进路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思路,其从枪支的视角透视美国的宪制,让我们跳出了基于宪法基础之上的解释这一单一视角。在充分发掘Constitution作为“宪法性法律”的内涵同时,也探索了作为“宪章”的Constitution。其最为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揭示出美国枪支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归根结底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但是,此条进路依然面临着瓶颈需要突破。不管是对美国宪制史历史语境的梳理,还是对现在宪法制度困境的描述,几乎都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接受状态,在面临宪制困境的场域下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只是停留于一种“同情式”理解的层面。即其揭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不在于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式的不屑或者研究进路的一种只描述式策略,而在于极力思考之后的无能为力。未提出解决问题之道也许无可厚非,但是面对问题的存在却无能为力才是这种进路的悲凉与苍白所在。
(一)作为规训身体与灵魂的枪支技术嵌入而产生的双重规训力
另一方面,权利之间是否具有通约性以及如何通约仍然值得研究。虽然权利之间是否可以通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对此问题的讨论以及能否找到一个中间装置将其互相通约,也许是权利冲突理论未来精细化的一个方向。同时,研讨认知神经科学在利益之间互相通约[32]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有助于权利冲突理论突破其发展的瓶颈,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而且,这种规训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一旦这种技术方案付诸实践,其将可能产生一种隐晦的心理控制,它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外在的技术纪律内化为人自身关于枪支的思维方式和使用风格,因为改变心理态度和倾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驯顺枪支使用人身体的行为,因而它是一种由外向内到由内向外的互动规训机制。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进路中的宪法—解释进路和枪支—宪制进路都属于解释分析问题型进路,而权利—冲突进路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从宏观上来缓解甚至是解决美国枪支的困境,但是其是一种大词化的“权利冲突理论”,并未精细化地阐释到枪支治理问题如何解决,也不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由此可见,学术界亟待一种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缓解甚至解决美国控枪治理难题,而且可以付诸实际操作,亦即在实践当中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型进路。
此外,我们需要铭记在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称的“共同建构”领域中,技术理性和社会经验是纠缠在一起的[35]6-7。亦即技术理性在对社会公众身体和精神进行规训而产生某种社会经验和社会价值的同时,这种塑造生成的价值和经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技术理性的发展。在“共同建构”的领域,技术理性和社会经验是互相形塑的,可见,如果枪支技术嵌入在观念上能够被认同,这反而使得枪支技术的社会领域加入取得了先发形塑的优势,进而可能形成治理控枪过程中“技术理性—社会经验—技术理性”的良性循环。使得后期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在社会支持下的枪支技术控制又在不断地提升智能控枪的共识,形成愈益向好的局面。
(二)“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的可操作性
16日,事件当事人曾先生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他回述了事件全过程和此前未被报道的细节,并对网络舆论和瑞典媒体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
其实,对于一些传统的法学棘手境况,特别是涉及到伦理困境的难题,比如“电车难题”(5)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发表的《堕胎问题与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后来具体的版本有很多,但是都涉及到有轨电车在面对生命多数与少数时的选择问题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37],我们也许可以走某种技术的路线。如果技术达到了某种程度,那么它可能不再是一个从伦理上、规范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的紧急刹车技术达到“秒刹”的程度,那么“电车难题”将不再是一个难题,而简单的变为了“踩一踩刹车”的技术问题;再比如,如果电子监控在公共场所变得更发达一些,南京彭宇案的事实认定也就不会变得那么扑朔迷离,进而产生如此多的道德负面影响(6) 进而可以联想到,技术在营造全民守法氛围中的功用。技术的发达可以为公民守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公民对于守法或者遵守道德传统的程度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心理认同,而是关切于付诸实践行动。在此意义上讲,技术的进步不仅因为创造了一种“守法有利”的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素质评价,鼓励了人性之光辉的一面,弥补了以往道德认同与实践行动的“二歧鸿沟”。 ;还有,如果我们的人工胚胎繁育技术发展的更繁荣些,也许就不会再有人处心积虑的到处暗地里找人代孕,以至于发展出一条黑色的代孕产业链条,那么代孕的伦理难题以及背后的权利保障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再比如,大家热议的乘客抢夺司机方向盘造成公共安全隐患的问题,[38-39]如果我们的技术设置能够达到将乘客和司机完全分离的驾驶环境标准,那么与此有关的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等相关问题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在这种语境下的讨论,恰恰是过分的偏离了现实生活,成为了一种纯粹逻辑化的思辨。正如苏力教授所言:“目前有许多法律问题之所以始终局限于没有结果的思辨性论证,这常常是并更多是与缺乏可靠的经验性科学研究成果相关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分歧恰恰是因为科技之不足而发生的。”[40]
具体到控枪,“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是指,技术应该不断争取在降低枪支使用风险上取得突破,而法律在市场化机制运行下以及民众逐步接受、适应智能枪械的基础上,对这些技术的枪支嵌入与结合加以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逐步从市场机制和技术规训机制下的行为习惯和心理认同上升为法律规定下的强制性行为规则。其实,纵观西欧和英美的立法史就可以看出,从宏观的发展趋势上看,其基本都走了一种“技术先行、法律跟进”的立法模式。某种技术的出现或者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将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需求加以解决或者满足之后,法律进而就会顺理成章的将其固定化以及制度化。即使法律对技术的样貌规制具有一定的裁剪性与前瞻性,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各国通行的“技术先行、法律跟进”的基本立法模式,也压制不了人们对于制度的想象力,特别是在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与应用的大背景下,其时刻刺激着法律制度的供给。
1.列举法。在教学中,以形符为纲,选取造字能力强的常用形符,以形符为中心展开教学。例如形符“木”,后面列举出“朴”、“机”、“杠”、“杖”、“村”、“材”、“枝”等由“木”这个形符构成的形声字。
第二,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的第二修正案代替了历史中的第二修正案。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的第二修正案并不一定是整全意义上的第二修正案,可能只是众多理解中的一种版本。只不过最高法院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最终决定了这么理解。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所言:“我们的终局性不是因为我们(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引者注)一贯正确,恰恰相反,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局的,所以我们一贯正确。”[29]但是,我们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于此,必然要试图探究一个整全意义上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且尽最大可能还原或者呈现出历史上的第二修正案与当下的第二修正案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演变逻辑。
而人类虽进化已久,但是人性里边流露的仍是基本的财富最大化经济原则。把技术应用于枪支而出现的智能枪支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成本”投入,这种成本的投入不仅收获了某种程度的安全,而且也保障了根深蒂固的持枪文化以及持枪权利的个体化实现。这样一来,市场机制和技术机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枪支技术已然成为了枪支市场的一部分,其在起到对身体和精神规训作用的同时,又能保障财富的最大化。而这种财富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认为是“一种正义理论”[41]239,而且相比于功利主义的“幸福的最大化”[42-43]60、29而言,它是一种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价值”[44]450,而且不具备道德上的可谴责性。
(6)增加与约旦能源合作。约旦页岩油富足,中国资金技术雄厚,且中国已投资阿塔拉特油页岩电站项目。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国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加快中国“走出去”战略,让约旦对中国友好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从而最大限度地对中国开放。
同时,美国最近几年在无线频率技术以及生物识别技术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特别是指纹识别技术的加入使得只有对枪支具有所有权或者授权的人才能启动枪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那些被盗(抢)枪支(7) 据报道,美国大约每年有23万支枪被盗,这些被盗枪支给犯罪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45]而产生犯罪的问题以及未成年人使用枪支自杀或者误杀的问题。(8) 美国枪支暴力的严重程度令人震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死于枪支(包括自杀、谋杀和意外)的人数超过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死于所有战争的人数。根据哈佛大学学者戴维·海明威的研究,美国儿童死于枪支的风险是其他发达国家儿童的14倍。 [46]由于无线频率或者生物识别技术在枪支上的嵌入,使得枪支变为了具有个性化和个人化的产品,其具有了更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的身份性。由此,因枪支的追踪变得更为简单而提高了潜在枪支犯罪者的犯罪成本和被惩罚的必然率。因此,对于潜在犯罪分子的震慑力和控制枪支犯罪都大有裨益。
其中,εLMD、LSD1和 LSD2分别由式(9)、(10)和(11)给出,δε为Dirac函数,由式(3)给出。
科学家还分析了超过20万名女性的数据,其中1054人患有卵巢癌。研究发现,与未服用阿司匹林的女性相比,每天小剂量(100毫克或更少)服用阿司匹林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降低23%。但是,服用325毫克标准剂量阿司匹林则没有这种效果。
此外,现代年轻人具有使用智能设备的路径依赖,其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接受智能枪支的使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国际旧金山智能枪支研讨会上讲到:“既然我们可以采用指纹解锁手机,为何不将指纹技术应用于枪支呢?!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打不开一瓶阿司匹林,那么就应该确保他们无法扣动扳机。”[47]智能手枪的直接功效是方便枪支的管理,从而间接的防止枪支被盗、被抢以及被未成年误用而带来的刑事犯罪或者伤亡事件。当然,并非所有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都侧重于武器集成上。比如说,LEID Products LLC开发的借助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访问控制系统(BACS)就用在了枪支存放管理上,既可以限制有人未经许可使用枪支,还能跟踪枪支的使用情况[48]。
必须要承认的是,个性化的技术在枪支中的应用也只能是部分的解决美国控枪难题中因意外或者未经授权而造成的伤亡,同时可以有助于枪支的追踪,有利于犯罪案件的侦破。但是,其并非是能万能地完全解决控枪的难题,对于那些具有合格身份通过合法途径购买枪支而产生的犯罪则是感到鞭长莫及。此外,本文只是从“技术—法律”的视角提供一种宏观的思路,至于技术具体的接入方式以及技术本身发展的瓶颈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等待科技界的精细化和明朗化。
女性盆底在垂直方向上分为前、中、后3个腔室,前腔室包括阴道前壁、膀胱、尿道;中腔室包括阴道穹窿、子宫;后腔室包括阴道后壁、直肠。三腔室概念的提出,可根据器官脱垂的部位判断盆底缺陷的类别和层次,进一步指导临床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确定修复层面。膀胱颈在经会阴超声的正中矢状切面易于识别,是前腔室的重要标志点,其位置和移动度代表了前腔室脏器的位置和运动,并可反映相应腔室支持组织的松弛情况及功能状态。
五、代结语:法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
读者也许会心生疑问,笔者提倡从“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总体进路来尝试性地缓解或者解决美国的控枪治理难题,是否意味着追求一种法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
关于此问题,可以联想到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起的“技术治理主义运动”,此运动虽然失败,但是极大地传播了技术治理的思想。(9) 技术治理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思想家贝拉米、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凡勃伦,奥地利哲学家纽拉特、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 [49]技术治理主义者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冲击,但是他们把这种冲击过分的极端化,甚至上升到了“非暴力革命”的政权更替高度。之后,技术治理主义演变为温和的改良主义,主张把技术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而加以使用,不再试图构建宏大的社会理想蓝图,而是注重脚踏实地实施改造社会的工程,尤其发挥了技术实用主义的一面。所以,在此必须予以说明,提出“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进路并非是代替学界研究的其他三种进路,也并非提倡原初意义上的“技术治理主义”,而是并行的、温和的第四条技术实用主义进路。“把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对其实施模式进行选择、修正和调整,使之适应社会总体制度,为社会总体目标服务,比如为民主制服务。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文精神等与技术治理相冲突,就像认为文化与科学必然冲突一样,是缺乏剖析的先入为主之见。实践经验表明,某种温和的技术治理模式与民主制能很好地相互支持。”[50]对于控枪问题而言,在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法制度下,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两党制下的民主机制已经失效不能发挥其作用。曾经一度将公共问题转向契约化轨道而形成某种同意秩序的民主化方式已经被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严重侵蚀,在民主化机制无法运作的压力型境遇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技术解决方式,这种迂回的、非民主化的方式也许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够从技术上达到控枪的目的,就可能从技术的角度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民主政治困境,从而发挥技术对于政治实践的影响作用,这也许是一条迂回的解决法律理论与现实境遇尴尬的可尝试性路径。
当然,不管是前文所述的三种研究进路还是后文提到的“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总体进路,其都还处于一种思想的样态,并非是直接付诸实践的规程操作。但是前者是一种分析解释型的思路,而后者却属于实用性的解决问题型的思维方式。只是,其还未达成思想层面的共识以至于也未完全相继付诸实践。同时,这里强调的是“总体”进路,亦即为美国枪支的治理提供一种相对宏观的思考进路,而并非具体的技术发明或者技术操作,但是探索此条路径并非意味着法哲学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及“电车难题”等思想实验的隐退,因为并不存在能够排斥所有其他方式的唯一“正确”方式。恰恰理论模型在面临技术的冲击时更应该奋起直追,增强自身的解释力和对问题的解决力。思考进路的并行不悖意味着各自研究领域的继续,其不是法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也并非鼓吹原初意义上的技术治理主义,只是希望在面临各种难题时多一种选择而已。
参考文献:
[1]枪案促变,佛州通过控枪法案规定教师可持枪上岗、上调购枪年龄等,但争议仍存[N].解放日报,2018-03-09(11).
[2]枪案促变,美佛州州长签署控枪法案:部分教职工可持枪上岗[EB/OL].(2018-03-10)[2018-09-11].https://news.qq.com/a/20180310/014190.htm.
[3]美国拥有200多年历史制枪商雷明顿申请破产[EB/OL].(2018-03-26)[2018-09-29].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26/c1002-29889992.html.
[4]梁茂信.无望的困局——美国的控枪政策及其制度性因素[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
[5]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ant, v.Jack Miller and Frank Layton,59 S.Ct.816 ,59 S.Ct.594(1939).
[6]District of Columbia, Petitioners, v.Dick Anthony He11er.128.S.Ct.2783(2008).
[7]Otis McDonald, Petitioners, v.City of Chicago, IILLINOIS, 130.S.Ct.3020(2010).
[8]张业亮.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学术研究和司法诠释的嬗变[J].美国研究,2016,(05).
[9]江振春,任东来.持枪权与美国第二宪法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02).
[10]任东来,江振春.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J].读书,2009,(09).
[11]江振春,任东来.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02).
[12]张千帆.宪法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3]江镇春.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收[D].南京: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
[14]马洪伦.论原旨主义内部的理论分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Heller案为例[J].当代法学,2011,(04).
[15]侯学宾.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6]任东来,江振春.持枪权的全国化与美国联邦制[J].学术界,2012,(07).
[17]蒋龑.“枪支条款”还是“民兵条款”: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A].强世功.政治与法律评论(第5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8]黄萌宇.美国枪支管制困境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2015.
[19]林垚.美国的枪支问题(一)第二修正案之争[EB/OL].(2017-10-20)[2018-09-11].https://zhuanlan.zhihu.com/iamelection/20354828.
[20]美控枪争论陷入僵局[EB/OL].(2017-10-09)[2018-10-03].http://www.cankaoxiaoxi.com/special/20171009/2237286.shtml.
[21]林垚.枪支管理的社会演化:民兵迷思、种族政治与右翼草根动员[EB/OL].(2017-10-22)[2018-10-06].http://www.sohu.com/a/199449974_506073.
[22]刘作翔.自由和安全如何权衡[N].人民法院报,2013-07-19(5).
[23]科技正在挑战法律的边界[N].法制日报,2017-11-8(11).
[24]郭春镇.法律直觉与社科法教义学[J].人大法律评论,2015,(02).
[25]宋保振.后果导向裁判的认定、运行及其限度——基于公报案例和司法调研数据的考察[J].法学,2017,(01).
[26]王彬.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1).
[27][美]邓肯·肯尼迪.判决的批判[M].王家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8][美]披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M].翟小波,刘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9]Kylesv.Whitley,514 U.S.419(1995).
[30]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定位[J].法学,2015,(11).
[31]龚廷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法治实践动力系统[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05).
[32]郭春镇.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3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34]P·Devlin.The enforcement of morality[M].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Press,1965.
[35][加]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M].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
[36][美]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7]Philippa Foot.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J].Oxford Review,1967,(05).
[38]让公交司机安全才有公共安全[J].宁夏画报,2018,(09).
[39]乘客抢夺司机方向盘武警战士挺身制止[N].上饶晚报,2018-12-13(A03).
[40]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1999,(05).
[41][美]布莱恩·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M].邱昭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2][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3][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44][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5]CCTV新闻直播间之枪口下的美利坚(第六集)[EB/OL].(2016-06-18)[2018-11-18].http://tv.cctv.com/2016/06/15/VIDEE7xSS8TIltuHmGaAfNTQ 16061 5.shtml.
[46]外媒:美国枪支犯罪触目惊心 还会发生更多[EB/OL].(2017-10-14)[2018-11-18].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1004/2236823.shtml.
[47]19岁青年致力枪支安全 造出指纹识别智能枪[EB/OL].(2016-10-12)[2018-12-06].http://www.sohu.com/a/115989129_119709.
[48]智能枪支更安全吗?[N].沈建苗,编译.计算机世界,2012-12-31(024).
[49]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J].哲学研究,2012,(03).
[50]刘永谋.技术治理主义:批评与辩护[N].光明日报,2017-02-20(15).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5-0101-08
[收稿日期] 2019-07-2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研究”(11&ZD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鹭(1992—),山西忻州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侯明明(1990—),山东惠民人,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司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赵方]
标签:宪法解释论文; 枪支宪制论文; 权利冲突论文; 控枪论文; 技术实用主义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 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