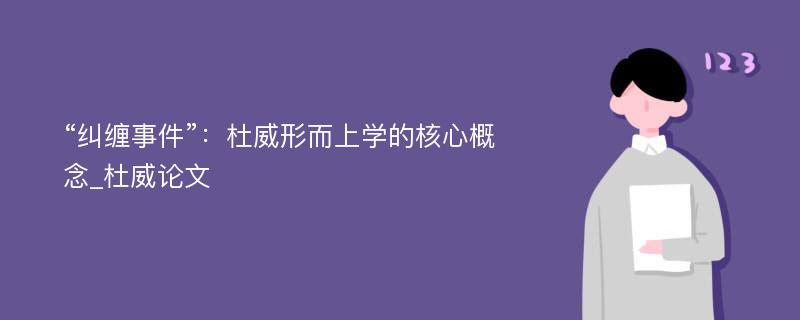
“交缠的事件”——杜威形而上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交缠论文,概念论文,关键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7-0025-08 与另外两个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家相比,讨论杜威的形而上学要困难许多。詹姆士(William James)后期的形而上学、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都是明确的,然而杜威是否有明确的形而上学?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并没有定论,除了解释者和研究者大相迥异的立场与路径,这一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威本人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困难和挣扎。1949年,在对卡恩(Sholom J.Kahn)的文章《杜威自然形而上学中的经验与存在》的回应文章中,杜威这样写道:“以前我认为将‘形而上学’这个词从其深陷其中的传统用法中解救出来是可能的,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异常天真的想法。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再也不将这个词用于我自己的哲学立场的任何方面,我有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慰藉?不管怎样,我的著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我是在与传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并且,我认为这个词虽然受到了最为不幸的使用,但其所指的东西依然是真实的和重要的。”①因此,比较安全的说法是:杜威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但有属于他自己的、经过更新和改造的形而上学。我们的任务便是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揭示出来,不过这一任务并不简单。一般认为,《经验与自然》(1925)完整地表达了杜威的形而上学,但仅仅考察《经验与自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在仔细追溯了杜威式形而上学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了它在各个哲学层面的运用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新形而上学的根本旨趣以及它与旧形而上学的关系。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首先,经验是生存性的和生成性的;其次,我们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经验,而是如何改造经验。在他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如实地展现第一点,并彻底地践行第二点,而正是这一要求让任何抽象形而上学成为不可能。不过杜威思想的彻底之处还不在于此。在他看来,过程性的形而上学[以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为代表]和多元论的形而上学(以詹姆士为代表)都不足以充分地表达第一点并完成第二点要求,因为一旦我们将“过程”和“多元”通过抽象概念固定下来,经验的改造就只能在思维中展开,而非在实际中展开了。因此,为了表达经验中的实际“交互过程”(transaction),我们必须将形而上学“祛本体论化”,或者说,将其“方法论化”。这是杜威提出以“存在的类别特征”(generic traits of existence)来引导经验建构的根本意图。在杜威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不但应该揭示出经验的结构,更应该揭示出经验的走向;形而上学应该成为“批评的地形图(ground-map),为接下来的更为复杂的三角丈量法建立基线”。②因此,在杜威看来,哲学家必须关心形而上学,但这种关心不是为了用理性结构来框定和压缩经验,而是为了更加智性地引导经验。形而上学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先于经验,形而上学在引导经验的同时也接受着经验的指引。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作为地图学和地形勘探学的形而上学。 斯特劳森(P.F.Strawson)在《个体》(1959)中对形而上学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区分,他将形而上学区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和“修正性的”(revisonary):描述性的形而上学试图“描述我们思考世界的实际结构”,而修正性形而上学则试图“制造一个更好的结构”。斯特劳森进而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形而上学归为描述性的,将笛卡儿、莱布尼兹、贝克莱的形而上学归为修正性的,而休谟的形而上学则“有时是描述性的,有时是修正性的”③。但在杜威看来,这两种形而上学在本质上都属于旧形而上学,因为它们只关心找出或制造一个关于世界的结构,而不关心这一结构是否能够为世界带来真正的更新。并且,尽管修正性的形而上学希望以一个更好的结构来替代已有的结构,但它所考虑的只是结构本身的优劣性,而没有对获得结构的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因此,在杜威之后,我们也许应该对形而上学再次作出区允将其区分为“描述性的”(包括斯特劳森意义上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和修正性形而上学)和“方法性的”(methodological)。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定位这样一种方法性形而上学?这一定位不但需要将它同一切描述性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还需要将它同单纯的方法论区分开来。这个任务的困难之处在于,既然方法性形而上学本身就是反对抽象概括并以具体的问题解决为理论旨趣的,我们又该如何对此进行“描述”或“叙述”(任何描述或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抽象性和还原性的)?为此,我希望从一个关键性概念——“交缠的事件”(entangled events)——入手来把握杜威的形而上学。在我看来,杜威在各个层面上对形而上学所作的思考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概念可以代表杜威的形而上学,而是说,这一概念是一个必要的生长点,离开了它,杜威的形而上学不可能呈现当下的形态,我们也不可能对这种形而上学作出准确的把握。 既然方法性形而上学在引导经验的同时也接受着经验的指引,在经验中探究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就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并且,既然杜威哲学的根本意图在于探索经验的不同“模式”,我们也有必要为了探究的明晰性将经验区分为直接的经验进程、经验的工具化进程,以及作为完成形态的审美经验。不过,这种区分本身也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而不是绝对的(比如,直接经验也可以是工具性经验)。我将逐一探究这个关键概念是如何蕴涵在不同的经验模式当中的,并在最后给出一个简明的结论。 一、个体的事件化与直接经验的事件化 在实在论和观念论的争论中,杜威特有的自然主义将他放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实在论发现自然,观念论创造自然,而杜威式的自然主义则致力于建构自然;实在论者敦促杜威对建构的材料给出说明,而观念论者则试图强调建构主体在杜威那里的决定性地位。尽管杜威一再要求我们从真正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建构理解为经验本身的情境化展开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推进的),但是只要我们还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下,对这一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就始终难以到位。在杜威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停止对经验主体和经验对象进行区分,并通过切合实际的反思将它们都把握为相互关联的过程性“事件”。较之于将经验对象把握为事件,将经验主体把握为事件要困难很多,因此,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强调:“人格、自我和主体都是伴随着复杂的有机体交往和社会交往出现的事件性(eventual)功能,而更为简单的事件是人格个体的基础和条件。”④作为事件的个体和自然不再具有各自的结构,而是作为一种进程被其他事件影响和规定;事件的界限也不在于与非事件对象的区分,而是其所处情境本身的界限。 需要指出的是,“事件”这一概念在杜威的时代并不特殊,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都分享了这一观念,比如怀特海和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这一观念的产生与当时对俗常时间观念的重新理解密不可分,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当时在这一观念上对美国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几本著作: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物质与记忆》、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的《空间、时间与神》⑤,以及杜威的《经验与自然》。这些思想家都认为时间的展开就是实在本身,而个体的体验则是时间最为本质的表达方式。线性展开的时间并不具有创造性,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是包含了过去与未来的绵延于当下的时间。因此,“时间性”是我们理解“事件”的基本维度,而“时间性”又必须在“个体性”的层面上得到理解。杜威在1938年于纽约大学所做的讲座“时间与个体性”中这样说道,个体“是一个广泛的时间,或者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是一个由时间组成的进程,每一个事件都带上了之前的某些东西,又指向将要来临的东西”,并且“人类个体自身就是一段历史、一段轨迹,正是由于这样,人的传记只能是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杜威接着又告诉听众,个体性不是“某种从一开始就被给予的,进而像解纱线球一样不断展开的东西”,个体性是“一种时间性的发展”,它包含了“不确定性、未决定性或偶然性”。⑥ 这一将时间与个体相关联的思路是当时哲学思考的主流,但杜威的新意并不在于通过将时间内在化而将其作为理解个体存在的基础,而在于通过将个体事件化,从而真正打开可操作的未来维度。杜威在讲座中说道:“真正的时间,如果以在空间之中的可测量的运动之外的形式存在,一定只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体,与创造性,与不可预测的新要素的出现相关联。所有与这一结论相反的观点只能说明个体已经丧失了他的个体性,个体被囚禁在常规性中,并堕入到了机械论的水平。真正的时间不再是他们存在的一个组成要素。我们的行为也因此变成了对于过去的外在重组从而变得可预测。”⑦个体,作为时间性的事件,不再是被限制在机械的时间中,而是因为绵延的时间获得了无限的创造可能。限制个体的不再是具有硬性界限的世界,因为世界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绵延的时间性事件。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实用主义的思路很自然地从探讨世界的可能性(詹姆士、皮尔士)转变成了探讨个体的潜能。个体通过对经验的改造无限地扩大、重构自己的界限,这种扩大和重构就是杜威所谓的“生长”。 以上关于个体与时间性的讨论对于理解直接经验的事件化是关键性的,因为只有在将个体事件化的前提下,直接经验的事件化才是可能的,否则直接经验只能是静态个体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得到的静态内容(传统认识论称之为“所予”)。在杜威所揭示的图景下,获得直接经验的基本机制不再是经验主体对经验内容的直觉性把握,而是经验事件本身的生成和生长。换言之,事件化的经验是首要的,经验主体与经验内容的区分是次要的。用詹姆士的话来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思维”和“事物”这种分离的“单管”(single-barrelled)概念,纯粹经验是“双管”(double-barrelled)的,“思维”和“事物”不过是纯粹经验的一体两面(纯粹经验也即杜威语境中的经验事件)。 经验事件在时间的进程中相互交缠,并向前推进,这才是杜威眼中的“有机”经验观。在杜威看来,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互动并不是“有机”的原初含义,有机的原初含义是生物性的和生存性的。任何经验的初始形态都是“冲力”,这一点是杜威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他在《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中写道:“任何经验,无论其意义微小还是巨大,都是从冲力开始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冲力。”杜威建议我们将“冲力”(impulsion)与“冲动”(impulse)区分开来。冲动是特殊的,是环境调适过程中的一部分机械运作,而冲力则指示了“整个有机体向外和向前的运动”。比如,生命体对食物的欲求是一种冲力,而吞咽过程中唇舌的反应则是一种冲动。⑧直接经验本身就是生命体的冲力,正因为如此,直接经验必须是时间性的事件,否则作为生命欲求的冲力就无法向外和向前推进。并且,这种冲力必须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处在反思性的抽象和分离之前,它代表的是生命体的一种原始状态。换言之,作为冲力的直接经验必须是由事件交缠而成的整体,这一整体是生命体进一步展开的基础。 这一点也决定了杜威的经验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部分论的(meristic),而是整体论的(holistic)。在杜威看来,离开了事件的交缠来讨论个别事件一定会对后者造成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扭曲。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说明经验事件的个性(identity)呢?换言之,我们该如何在经验事件之间作出区分呢?杜威的回答是,经验事件的个性是作为质性统一体(qualitative unity)呈现的。质性统一体并不是原子性的、简单的质(qualia),相反,正如杜威在《质性思维》(1930)中指出的,“生存性命题最终指涉的内容可以是一个聚拢在一起的复杂存在,不管这一存在的内在多么复杂,它仍然可以被一个单一的质所主导并以此为特征”⑨。杜威进一步指出,这种用来描述经验事件的质性统一体是被感觉到的(felt),而不是被思维到的。我们习惯于将被感觉到的质性统一体实体化为“感觉”(feeling),但是通过反思得到的感觉并不等同于实际的感觉状态,比如,作为分析对象的生气感觉并不等同于生气的状态。⑩杜威希望由此揭示出将经验事件实体化和静态化的危险,并强调直接经验的个性只有在连续的事件进程中才能被把握。 直接经验的事件化让整个经验领域真正活动起来,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经验的更新和生长才是可能的。不过,除了这一基础,经验的改造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二、经验事件的工具化 直接经验与工具化经验是杜威的一个基本区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区分本身也是工具性的,也就是说,这一区分是出于改造经验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工具化经验并不是运用工具对直接经验加以操作,而是将直接经验本身置于一个探究的情境中,作为探究的一个有机部件,以实现当下的实际意义向未来的可能意义的转化。换言之,经验事件的工具化考虑的是如何推进已有的质性统一体。在杜威看来,这种推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进程。我们只有通过“生活的介质”(也就是具体的效应和后果)实现并评估这些进程。这一点也就决定了经验事件的工具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过程,而是一个扩大生命意义、重估已有价值的过程。不是把经验作为认识的一个方面,而是把认识作为经验的一个方面,这是杜威经验观的一个基本洞见。正是这一点要求我们将经验事件的工具化放到一个远超出“认识”的关系领域中来理解。 仅就直接经验事件的相互关系而言,就存在着两种关系——匿名关系或工具关系。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指出:“……或者屈服、顺从,为了和平的目的变成一个寄生性的附属体,沉溺在自我主义的孤独中;或者根据欲望去进行对环境的重塑。智性诞生于后一进程中。智性的心灵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去占用和享受整体,而是作为个体去开辟、冒险、实验和消解。”(11)我们可以称前一种情况为匿名关系状态,后一种情况为工具关系状态。在匿名关系状态下,事件与事件的交缠是整体性的,在工具关系状态下,目的性的区分开始出现[注意这里的目的是可预见目的(end-in-view)]。在后一种情况下,某个经验事件不只感受到与其他事件交缠的张力,同时还感受并认识到交缠这一事实本身。换言之,某个经验事件不只感受到其他事件,同时还真正感受并认识到自己与其他事件同处在某种交缠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交缠被情境化了。生命体不只是生物性地经受(12)这种交缠,同时还有目的地探究处于交缠当中的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操作,以满足自身的原初冲力。生命体开始智性地思维:“我作为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处在关系X中,如果我采取行动Y,就会导致结果Z。”这种智性的意识,或者说“排演”(rehearsal)的意识标志着从直接经验到工具性经验的转化。 在杜威看来,工具性经验不但要求我们感受并认识到直接经验事件处在怎样的当下“交缠”中,还要求我们“想象”出这一事件在进入情境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交缠”。因此,工具性经验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它发生在行动之前。杜威又将这种想象称为“慎思”(deliberation)。他在《人性与行为》(1922)中指出,“慎思是一种实验,其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考量一个可能的行动。它将所选的习惯和冲动进行各种实验性的组合,看会引发什么样的行动。但是这种实验是在想象中进行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13)。当然,这种对于未来交缠的想象一定是基于当下的实际交缠。为此,杜威区分了“假想”(the imaginary)与“想象”(the imaginative)。他在《民主与教育》(1916)中提出,“想象”不应该被等同于“假象”,想象是“对于一个情境整体的温暖而亲密的把握”(14)。而在《人性与行为》中,杜威又指出,“生命的材料在想象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年轻化的、沉着的、增强的形式”,而假想则“以自身为目的。它沉溺于幻想当中,这些幻想从所有的现实中撤退,无法用行动来创造一个世界,又希望能以此带来短暂的刺激”。(15)想象与假象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的产物,想象能带来经验更新,而假象只能是没有根据的虚构。只有掌握了想象的艺术,工具性经验才能真正以事件的交缠为基础实现它的工具性。 在工具性经验的语境下,我们对事件的交缠有了两个认识上的更新。首先,在直接经验中,事件与事件的遭遇最多意味着原初冲力或质性统一体的改变;而在工具性经验中,事件与事件的遭遇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经验事件不再是被直接拥有的东西(had),而变成了皮尔士意义上的索引(index)。这是从关系向关系项的转向,所有有意识的经验都是对关系而不是对事物本身的认识。不过在杜威那里,这并不是一个观念论的表达。在他看来,对关系的意识意味着对行动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向未来敞开的,换言之,它关心的是可能的行动。因此,事件的交缠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只不过这一进程并不像詹姆士所理解的“纯粹经验”那样可以自动推进,而是需要“创造性智性”(creative intelligence)的参与。(16) 其次,工具性经验要求我们在感受并认识事件之间的交互交缠的同时将这种交缠理解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工具性经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交缠作为交缠整体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交缠并不只是瞬时而偶然的,而且还是整体性的。德语中用来表达经验的两个词可以很好地表达这两层意味。德语中一般用“erlebnis”来指独立的直接经验(或内在体验),而用“erfahrung”来指持续的累积经验;前者是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拥有的,后者则是我们在某段时间经历的。前一种经验的对象比较容易确定,而后一种经验的对象则更倾向于某种整体性的“界域”(hotizon);前者以独立性为特征,而后者则以统一性为特征。除了《经验与自然》之外(17),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中也对这两种类型的经验作出了区分。杜威区分了随机而零星的独立经验与作为整体或统一体的经验。在后一种经验中,“每一部分都自由地流向相继的后一部分,没有接缝,也没有未被填充的空档。与此同时,每一部分的自我认同并没有被牺牲掉。与池塘不同,河流是流动的;河流的流动更加明确地关注前后相继的部分,而非存在于池塘中的同质部分。在一个经验中,流动是从某物到某物。……这种(经验的)统一既不是情感的,也不是实践的,更不是理性的,因为这些概念表达的是反思可以在经验中作出的区分。……经验并不是这些不同性质的总和,这些性质在经验中变成了可区分的特征。除非被本质上具有价值的整体性经验吸引并进而得到奖赏,没有一个思想者能够进行他的工作”(18)。这段引文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杜威是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经验整体的。在他看来,经验的这种整体性并不是总和意义上的,而是通过流动中的累积实现的。这里,我们不应该将累积理解为是一种简单的叠加,在杜威那里,整体的意义永远大于部分意义的总和。因此,杜威在《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中进一步区分了“统一体”(unity)与“单位”(unit)。经验的整体一定是一个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单位。统一体中“包含着成员,但它并不是部件的集合或收集”,并且,如果要改变作为质的整体的情境,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情境”,以“剔除某些要素,引入其他的新要素”。(19) 在一个经验整体中,我们不再能区分出单个的经验,只能区分出单个经验的特征(trait),而这些特征也只能通过与整体的关联才能被理解。整体是部分的完成和升华。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直接经验”与“整体经验”之间的区分在杜威那里同样也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的界限随着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不断变动、调整,这一刻处于前景之中的经验在下一刻会变成背景,而原本处在背景中的某个经验特征会在下一刻明确地“站”到前景中来。在杜威看来,经验的流动性和生长性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中才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将杜威的工具主义与机械主义以及俗常意义上的技术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工具化的过程是以经验事件的交缠性整体为前提的流变和生长,任何脱离经验整体的工具性运作都是不妥当且无法实现的。 三、作为完成经验的审美性事件 我们在以上两部分尝试描述了直接经验事件与工具化经验事件之间存在的张力。杜威指出,一方面,只有在经验事件化的前提下,交缠的事实才能成立;另一方面,事件本身又是基于交缠的事实才能成为可能。前一方面描述的是直接经验事件的基本存在状态,后一方面描述的则是处在关系当中、自身不断生长并且不断促进其他经验生长的工具化的经验事件。因此,在杜威的语境中,直接经验事件与工具化经验事件是相互依赖,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相互转换的。在他看来,这种“实际/理想”(real/ideal)之间的转换与推进是人类经验的基本运作模式。但是,杜威思想中存在的黑格尔因素让他希望这两种经验模式能够以某种方式“扬弃”对方,并进而上升为一种更加整体性的经验模式。(20)这种经验模式就是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是对质性统一体的直接把握,但这种把握又不是原始的、无意识的,相反,它深刻地意识到了存在于质性统一体当中的复杂关系,或者说,它的着眼点首先是艺术构件之间的关系,而非艺术构件本身。因此,审美经验表达了一种上升之后的、更加全面的直接性,它将关系拉入到直接的经验事件内部,让关系不再是被思维(thought),而是被直接拥有(had),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性的经验事件。 杜威将这种审美性的经验事件视为经验的“完成形态”(consummation)。在他看来,任何经验都是趋向于最终的完成或高潮的(“consummation”具有完成和高潮两层含义),他在《作为艺术的经验》中写道:“如果我们获得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预期和累积的运动最终完结了。‘结论’并不是分离和独立的东西,它是一个运动的完成。”(21)但是,这种经验的完成并不只是简单地得出结论,经验的完成形态具有审美性质,或者说,只有与审美体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经验的整体感与完成感。在杜威那里,经验的完成与审美的高潮是完全同质的。不但情感性和感觉性的经验具有这种审美性,理性的思维经验同样具有这种审美性。杜威写道: 因此一个思维经验具有自己的审美性质。它与那些审美经验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材料上的。艺术的材料由质组成,而那些具有理性结论的经验则是以符号或象征为材料,这些符号或象征自身没有内在的质,但代表了那些也许在其他的经验中被质性地经验到的事物。这里的不同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严格的理性艺术永远不会像音乐那样流行的原因。但是,思维经验本身具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情感性的质,因为它具有通过有序的和有组织的运动而得到的内在完整性和完成性。这种艺术性结构也许可以被直接地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思维经验是审美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审美性不但是我们在从事理性探究中的一个重要动机,而且——我们可以真诚地说——任何理性行为只有拥有了这一性质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或者说成为一个经验)。缺少这一性质,思维是无结果的。简言之,我们不能将审美性从理性经验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因为后者只有具备了审美性才是完整的。(2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威的艺术理论是其经验观的一个基本维度,缺少了这一维度,任何对经验的理解都缺少一个最终的“完成”。艺术中所体现的趋向完成的整体性质性思维是经验建构的基本方式。杜威晚年对艺术的思考正是在这一基本诉求下进行的。 因此,在杜威的语境中,审美性经验的范围要远远大于通常意义上的审美经验。一切将复杂的关系表达为直接的质性整体的经验都可以被称为审美性经验。但需要强调的是,审美性经验并不意味着经验事件本身的完成或终结,而是说,某个经验事件或某一些经验事件在某个情境下达到了意义的最大化(“高潮”)。任何经验事件都处在事件的交缠当中,审美性经验也不例外。这种交缠让任何事件都具有无限的敞开性,即便是完成的经验也会因为身处这种交缠之流中承受来自各方的力量和影响,并在下一时刻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也许是高潮的进一步持续或增强,也许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情境中重新作为原初的直接经验,也许是为其他经验的生长提供工具性的帮助。而这一切只有在一个不断流变的事件之网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作为完成经验的审美事件与下一个经验事件是紧紧衔接在一起的,并且,这种连续的推进并不是抽象的螺旋上升,而是真实的生长。作为生长的目标或理想,审美高潮作为一个经验片段有机地整合在经验过程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经验、工具化经验和审美经验的这种交缠让杜威能够最终建立起一种关于游戏(play)的形而上学。他在《民主与教育》中写道:“游戏中带有目的,因为它引导观点,并提示接下来的行为。游戏中的人并不只是在做一些事情(单纯的物理运动),他们在试着去做某些事情或去影响某些事物,这一态度包含了激发他们当下回应的预见,而预见的结果则表现为相继而来的行为,而不是事物的特殊变化所造成的产物。因此,游戏是自由的和可塑的。”(23)游戏是一种自由的探究,它是实验性的。处于游戏中的人根据自己的预见时刻调整自己的回应,而这些预见又是根据游戏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而时刻发生着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游戏是一种理想的对话模式。杜威补充道,游戏最终的教育意义在于它为“意义的拓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工具”。(24)皮尔士对“游戏”的强调来自他对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游戏说”的改造,而杜威对“游戏”的强调则来自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心理学。游戏的要点在于,游戏者在游戏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地转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随时预见到自己的回应会如何影响到其他游戏者的回应,从而事先调整自己的回应。而这一点,在杜威看来,正是我们希望通过对话与交流达到的目的。在《我们如何思维》(1910)中,杜威建议我们区分出“游戏”和“游戏感”(playfulness)。他指出,“游戏感比游戏更为重要。游戏感是一种心灵的态度,而游戏则是这种态度的外在体现”(25)。态度的培养比具体的操作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前者,后者的展开一定是机械的或强制的。对话的展开必须以对话性的态度为依托。 经验事件的交缠正是一种游戏性的展开,在杜威看来,这一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培养游戏感的可能性。对形而上学思考是一种培养游戏感的训练,而体现在审美过程中的经验进程则最为典型地代表了经验生长的游戏性质。杜威写道:“为了感知,欣赏者必须创造自己的经验,并且他的创造必须包含那些艺术创作者本人所经历过的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之间并不是照实重复。但是欣赏者必须像艺术家那样对于整体之各元素进行一种排列,这种排列是形式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而这一组织的过程正是艺术创作者有意识地经验到的。”(26)我们无法用事后的分析来准确重构上面描述的经验进程,所有的经验交互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且都是具体的,并可在已有的交互上再一次展开新的交互。审美性经验不但将各种关系包含在某个情感性的质性统一体中,还通过经验事件的游戏性交互不断更新这一质性统一体,从而实现经验的整体性推进。 以上对经验所作的三层区分的前提是经验事件的相互交缠这一基本事实,这种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一事实具体化。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还原性是杜威所拒斥的,也是方法性形而上学要极力避免的。但是,杜威对形而上学的具体化并不是要走向抽象的反面,而是要将形而上学引向未来的可能行动,从而对具体的“发生”进行指导。因此,“交缠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而上学描述,而是改造经验的基本前提。在这个理解之下,“形而上学在引导经验的同时也接受着经验的指引”这个要求才有可能实现。 只要我们还是将形而上学把握为一种“系统哲学”,我们就很难把握杜威所提出的方法性形而上学的真谛。为了生命的进展和丰富,人必须把握世界,赋予世界以形式,在杜威看来,形而上学正是在这种生存性实践的要求下出场的,因此,形而上学本身首先必须是一种工具。如果我们真正认同杜威,将经验的生长作为哲学的根本目标,那么我们也能够认同杜威将形而上学方法论化的做法:任何非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只能描述经验,而不能提升经验。形而上学不是位于经验之先或背后的东西,而是指引经验的东西。因此,任何形而上学都必须是处于经验之中的,正如任何经验的勘探者最终只能被经验所包容和浸润一样。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性形而上学又不能是单纯的方法论,因为它在指引经验的同时还强调一个基本的本体论事实,那就是经验事件的相互交缠。不过,这一本体论事实必须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事件化的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脱离狭隘的形而上学范畴。它试图将人类精神(或者说人类文化)的所有层面都事件化为可进一步操作和建构的材料,只有这样,人类精神才能摆脱封闭性的自我展开,从而有机地融入自然进程之中,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吸取新的、有益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艾斯冯特(Raymond D.Boisvert)称杜威是一个“事件主义者”(eventualist)。波艾斯冯特指出:“对于杜威来说,事件本身便是反思和探究的界限。自他的黑格尔时期以来,自然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就没有被切断过。”(27) 方法性形而上学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描述作为整体的宇宙,而是如何促进经验的整体性生长。在《经验与教育》中,杜威为我们指明了经验的“生长”真正要考虑的问题:“这一方向的生长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一般性的生长?”“这一方向的生长是否为进一步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又或者对于向这一特殊方向生长的人来说,它所创造的条件关闭了朝新的方向继续生长的机会了?朝某个特殊方向的生长对于态度和习惯(正是这些态度和习惯打开了朝其他方向发展的通路)有什么作用?”(28)在我们真正将存在的体系把握为交缠的事件之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只能是“描述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很困难。 注释: ①LW 16:388. ②LW 1:309. ③P.F.Strawson,Individuals: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London:Routledge,2003,p.9. ④LW 1:162.这里对“eventual”的翻译经过了一番斟酌。此词的基本意思是“最后的、最终的”,但这里指的是经过了一段不明确的时间之后最后和最终,当作名词使用时(eventuality),指的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某种情况。因此,为了保留这些“不确定”和“可能”的意味,这里把它译为“事件性的”,因为“事件”本身指的便是“在时间中发生”。另可参见LW 1:57。 ⑤Samuel Alexander,Space,Time,and Deity,New York:The MacMillan Press,1920. ⑥⑦LW 14:102-111,14:112. ⑧⑨⑩(11)LW 10:64,5:246,5:248,1:188. (12)"undergo"和"suffer"这两个杜威经常使用的动词都可译为“经受”。 (13)(14)(15)MW 14:132-133,9:244,14:113. (16)《创造性智性》(1917)是杜威和其他一些实用主义者(包括米德)发表的一本文集的标题。杜威的《哲学复原之需要》就发表于该文集中。 (17)参见杜威对“意识”与“心灵”所作的区分(LW 1:229-230)。 (18)LW 10:43-44. (19)(21)LW 12:218,10:45. (20)关于杜威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参见孙宁:《从黑格尔式的外衣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39期,2013年4月15日。 (22)(25)(26)LW 10:45,8:285,10:60. (23)(24)MW 9:211,9:215. (27)Raymond D.Boisvert,Dewey's Metaphysic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8,p.204. (28)LW 13: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