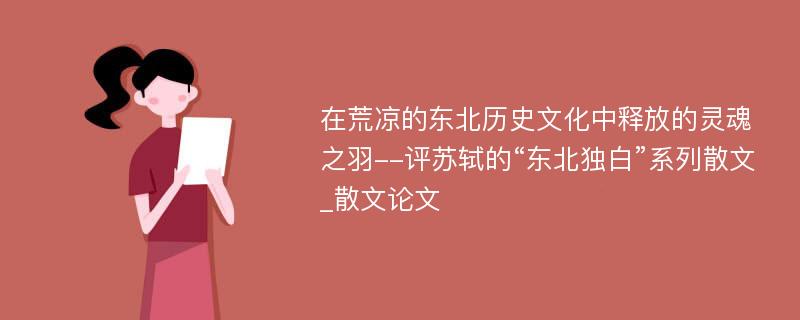
心灵之羽,在大东北的苍凉历史与文化中放飞——评素素的“独语东北”系列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苍凉论文,素素论文,散文论文,心灵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缠缠绵绵或者挥挥洒洒地写着“北方女孩”和“心灵羽毛”的那个原来的“北方女孩”素素,在废寝忘食情深意浓艰苦卓绝地写了二十几年的“素素心羽”之后,给越来越喜欢着她的人们留下了一册纯情洋溢的《北方女孩》和一册“全新感觉”的《素素心羽》,突然微笑着从唯美纯情这样的最适合女性作家施展的散文领地“转身离去”(见《素素心羽》自序),已经成长为大“女孩”的素素决心不再回头看自己的来路。1996年她毅然决然地请了半年创作假,背起简单的行囊,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柔弱的身躯扔进大东北苍苍茫茫的山林和平原,也把自己的灵魂抛入茫茫苍苍的大东北的历史。她要让大东北的全部苍茫重塑一个素素,她要让自己的在大东北的风雪洗刷之后的心灵,重写一种面貌崭新的素素散文。回到她居住的城市之后她果然一气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大东北系列,她叫做“独语东北”。从目前已经发表的十几篇作品来看,如《煌煌祖宅》(《鸭绿江》1997.9)、《走近瑷珲》(《人民文学》1998.2)、《绝唱》(《中国作家》1998.2)、《黑颜色》(《十月》1998.6)、《空巢》(《萌芽》1998.1)、《笔直的阴影》(《北方文学》1999.1)、《火炕》(《美文》1999.4)等,我以为素素的确是成功了。虽然她仍然是以“素素心羽”去感受着大东北,虽然她也仍然是以明显的女性语态讲述着自己的感受,但是,这样的散文中铸进了大东北的魂魄、气度和风骨,素素与那个人们熟悉的“北方女孩”真的彻底告别了。
其实,我到现在内心中还依然存有一种顽固的偏见,我总是以一个男人的心理觉得,像这么沉重的话题,像这么以散文的形式对大东北的漫漫历史和古老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文学表现,应该由男性作家来承当,或者干脆说应该由贾平凹、余秋雨这样大手笔的男性作家来承当。然而,事实上素素已经让我匪夷所思了。就这么一位原本意义上的“女孩”型作家,却极其游刃有余地把大东北那么丰厚深邃的文化底蕴用她的女性话语轻松自如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让我感到由衷的感慨和震惊。
大东北,也许它过于蛮荒、古老和雄悍,也许它过于神秘、傲慢和不可思议,我国文坛至今没有对它做出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文化发掘和展现。虽然也有过“北大荒文学”以及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也毕竟形不成很完整很丰满的“大东北文学”。其在整体上的成果和面貌,远远不及中国的西部文学或者“大西北文学”。我以为,素素的这个大东北散文系列,很可能成为中国“大东北文学”的核心性构成。当然,中国“大东北文学”的真正出世,还需要更加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产生。但起码,素素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大东北文学”的作家。早在1992年,她就曾经写出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大东北》。她说:“大东北是一种图腾,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精神。大东北十分的质感,十分的写意,雄壮得咄咄逼人。”她还深深地懂得:“大东北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任百年又百年岁月流淌而过,灵魂不老,总是从原始的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辽河滚滚而来,凝成一道永恒的风景。”直到1996年她只身遍访大东北,就已经迈开了自觉创造“大东北文学”的第一步。
素素自然在实际的游历中更加感到了自己这种选择的英明。她在第一篇“独语东北”的散文中开篇就这样写道:“真正地贴近了东北的山林和平原,才惊心地感到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议。一路走着,突然就能拣拾到某个民族扔在历史上的那些散乱的碎片,由那碎片,就可以拼出一个不完全是喜也不完全是悲而是悲喜交加的故事。”于是,就诞生了素素的充满历史文化意味的大东北散文。
在岁月的密林中穿行,素素首先走入历史的纵深。她看到了“那被匈奴追杀得无路可逃的鲜卑人,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自己舔干了自己的血迹……经过一代一代的跋涉,终于登上了中原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云岗石窟大佛的嘴角,流露了这个民族内心谁也猜不透的笑。”她看到了,那个在草原上长大的耶律阿保机——那个契丹人的太祖,率领的震撼整个北方的马队和他们建造的遍布北方的自成一体的辽塔。她也看到了:那古老的额尔古纳河边,那个总是眉头紧锁总想报杀父之仇的铁木真,后来“和他的子孙们挥舞着上帝之鞭,几乎踏平了亚欧大陆……”而她更看到了,那个在商周时候就生存在大东北的游猎民族肃慎,以及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三次瀑布般的辉煌”……总之,这一切都使素素对大东北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于是她深切地写道:“原以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便覆盖了整个华夏。走过东北才知,如果以黄河为轴心,黑龙江与长江一样,是中原文明的另一翼。只是我们没有像对长江黄河那样,认真关注过它那曾经雄壮的飞翔。”这实在是对中华文明构成的一次重大的发现。
要问大东北的文化究竟有多深有多久有多古老,请看素素对一个辽西故事的探究吧,这个故事就是红山文化。原来:“裸露的辽西却怀揣了一个旷世的秘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和积石冢群。在这些遗址和冢群下面,有美仑美奂的玉器,那玉器以它墨绿色的晶莹,雕刻出自己的光芒。红山文化宣布的是一个最新消息,辽河文明早于黄河文明,中华文明史由四千年改写成五千五百年。”
辽西古老的当然不仅仅在于她的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的漫长,如果仅就历史的长度而言,素素说“辽西比我原初想像得更古老”。六亿年前这里就有了海洋中的生命,二亿年前这里是恐龙的家园,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的足迹。而辽西更古老的还是她的艺术的创造,让素素更钟情于辽西的,就是那红山女神:“她让我一下子望见了中华民族早期原始艺术的高峰,望见了原始宗教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原来,辽西是因为有了她,而成了一条更大的河之源。”从红山女神的塑像上,素素对辽西乃至大东北有了更深刻独到的理解和发现,她说:“辽西真的是母性的。只有母性,才会把那么久远的美丽完好地庇护到现在。只有辽西,才会哺育出这样一位妩媚鲜润的女神。在那之前,人们还在崇拜自然,突然间就崇拜了人自己,而且是崇拜自己所爱的女神。母性的辽西,赋予了它的子民先知般的智慧,让他们总是走在历史的前头,向世界发出文明的曙光。”这是素素这么一位女散文家对辽西文化的一种新的价值定位,也显然是对大东北文化的一种崭新的意义的发现。
素素的大东北散文,自然不仅仅是在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源流,更多的是从众多的历史遗迹中看取我们历史的曲折与挫折。她也不仅仅是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古老和辉煌,也常常在一些特定的遗迹中,感受我们曾经的耻辱和磨难。
作为天然性别区分的女散文作家,素素总是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从一些历史文化遗迹中感受或发现某些超乎常人的极其深刻的艺术内涵和理性意义。如《走近瑷珲》,文章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乃至文章篇幅都堪称一篇地地道道的大散文,且是表现一段沉重历史并揭示其中特殊文化内蕴的沉甸甸的大散文。作为天生的女性作家,素素内心深处的那种女性写作意识是极其突出的,所以,这篇我们可以称作大散文的《走近瑷珲》,也仍然是以一种非常明显的女性语态来传达一种独特的女性体验和女性心理的。正由于这种女性细腻而敏感的体验与瑷珲那样的极其沉重的历史关节的碰撞,才使这篇散文有着格外特殊的韵味和价值。
关于瑷珲,正如女作家在文中所言:“这世界任何一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瑷珲。”然而,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位女作家笔下,却为我们又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瑷珲,或者更应该说又为我们揭示了瑷珲的更深一重的历史蕴涵。作品开头的一段虽然可以看作只是一段普通的引子,但如仔细品味却也是意味深长的:“我常常能想起走在瑷珲的那个中午,以及那个中午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体验过历史给予我的伤痛,因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承担那么沉重的历史。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女人,我可以和它保持一点距离。然而那个中午,我的心被我曾经敬而远之的历史烧成了一片焦土。”这段极其真挚而又坦诚的表白,一方面让我们隐隐感到了这些女性散文作家们以往那种较普遍的创作心态,一方面也实际上更让我们许多人从中照见了自己,那种和历史保持距离的心理也许是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曾有过的。当作家用被瑷珲烧成一片焦土的心理感觉终于抹去了这样的距离之后,显然也就把读者与历史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作家不仅以这种独特的女性感觉征服读者,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她能在行文中不断地超越女性感觉,冲破女性意识,从而站到全人类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更深透地把握瑷珲以及由瑷珲串联起来的漫漫历史,并进而从中提炼和抽取具有全人类参照价值的历史蕴涵和思想意义。她说:“瑷珲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人类共同书写的,它的过去和现在,人类都要共同面对。”这里没有呼天抢地的批判与指责,却有着女性固有的柔中的刚力与深沉。似乎于轻描淡写之中,瑷珲悲剧的意义便被提升了。
素素毕竟是一位女性散文作家,当然,我一再强调这样的称谓也许会让作家本人以及某些读者心里感到不怎么舒服,但是,也正由于这样的一种称谓,才能从根本上体现素素的独特。于是,当她进入大文化散文创作领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仅仅看到那些“大男人散文”以及“老学者散文”的模仿或照搬。素素散文的基本语式仍然是女性的。而她正是以其女性独有的叙述方式和话语构造,把一段曾被男性不断讲述的历史做了全面翻新。而且,这其中也决不仅仅是女性感觉的细腻,其对宏大的历史过程以及细微历史掌故的通透把握与自如调度,让人简直很难看出作家原是应该惯于讲述家长里短的“小女人”。作家把瑷珲作为一个历史的凝聚点:“它让我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更深远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都能与我同行的。因为史书上并不认为瑷珲悲剧是在尼布楚的那个山坡种下的恶果。然而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想流矢般的从瑷珲向遥远的尼布楚和并不遥远的卢沟桥飞去了。”这也许就是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思绪了。作家从康熙大帝追溯瑷珲悲剧的历史根源,从一次又一次中俄战争和国内的战乱中寻找历史的环节和脉络,并从那些愚昧的皇朝和卖国的奸佞寻找历史演变的契机,一场壮阔的历史大悲剧的里里外外和前前后后就被作家描摹和展示得清清朗朗,这的确是固守考据的史家和学者所难于做到的。
尤其是,素素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决不仅仅是平板机械地复述历史,然后空洞抽象地大发议论。素素散文以其女性叙述,把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全都加以日常化和生活化,使读者完全是在审美过程中体验和感受那段壮阔的历史,并深入观照其中的文化内涵。那段历史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历史都无疑是极其沉重的,然而作家讲述的语言却又故意运用得那么轻巧,如:“在漠河北极村的黑龙江边,有人曾经指着对岸的山告诉我,山那边就是当年的雅克萨。遥望着它,我想起了第一个率领哥萨克闯进黑龙江的波雅科夫。他带着哥萨克匪徒一路屠杀,走得太远,走得粮尽食绝,居然吃了五十多个达斡尔人的尸体。这样一个恶魔,成了俄罗斯新土地的开发者,他的名字也成了黑龙江彼岸一个小镇的名字。而今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广场上,我看见了他的塑像。他手中举着一张阿穆尔州地图,下面写着:阿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我曾经想,如果康熙能看见这一行字,他还会沾沾自喜于那个尼布楚么?”在这种看似轻巧随意的言辞中,不仅深藏暗现着历史的沉重,而且还时时流露出女性作家特有的机敏和睿智。如:“最早走向海洋的是中国人,最早占领这个世界的是欧洲人。因为第一张远洋航海图是中国明朝一个叫郑和的人绘出的,第一个率船队远航重洋的人也是郑和。同样是航海,郑和只是代表中国皇帝去远方看望一下,只是想让那些被看望的国家心中要有大明王朝。……在郑和之后,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也出发了几只船队。他们不是去看望,而是去测量。不是去邀请,而是去占领。”至于对中国最终成为战败国,素素以其独特的语言方式议论道:“封闭的中国人,不知道此刻的西方已经有资本主义这个奇怪的东西在萌芽在膨胀。不知道在西欧的海盗们扬帆驶向大洋的时候,那个曾经是远离中国的东欧民族也已沿着地球的北边,越过乌拉尔山脉,小心翼翼地走进亚洲大陆。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把贝加尔湖当做一个宿营地,他们将不停地占领不停地向东,他们很快就将打碎你的小桥流水田园牧歌,打碎你的宁静,打碎你的古老而冗长的大国之梦。中国人太习惯以我为中心了,对这个已经开始动荡的世界,从精神到物质,全然没有准备。”
人类的全部历史过程,当然并不只是人类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过程。或者改换一个角度来说,具体的人、个体的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或毁坏者,他不仅要为自己和自己同类的生存创造必需的精神文化和物质财富,从而实现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价值;而且每个人的一生,还要更多地承担个人命运的重负。作为文学,实际上应该更加关注的就是全部历史过程中的人的命运和遭遇。因而,素素的“大东北散文”,也就不仅仅在探究大东北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也常常进入到历史上的某个人的命运之中。《消失的女人》就是重新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后婉容的悲惨命运的。婉容的命运具有太突出的典型性,婉容的身上,集聚了太多的人的命运的信息和密码。所以才让素素为她那么动情那么着意。婉容的一生的确是极为凄惨的,她先是疯了后来又死了。而她死了之后又至今没人知道她埋在哪里。在婉容生活过的城市素素回想着婉容的一生遭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延吉停留时,我的眼前却总有婉容的影子。中国有数百个皇后,她是最后一个皇后。读中国历代皇帝全传,再读中国历代皇后全书,几乎就读了中国封建社会通史,读了中国宫廷史。在中国的皇宫里……皇后就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就是那个统率六宫母仪天下的女人。……婉容统率的只有一个比她更弱小的文绣。她眼看着大清王朝被席卷出北京,又眼看着满洲国倾倒于新京。当一切都进了地狱,她还跌跌撞撞地在老家的土地上流浪。所以我始终认为,婉容从来就没有真正当过皇后,皇后这个角色却让她失去了一个女人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大东北的文化中还有什么呢?自然少不了土匪。素素说“东北原本就没有士大夫文化,俗文化一直就是汪洋大海”。她还知道,“在东北部那片山岭里,蝴蝶迷有许多个,座山雕也有许多个。座山雕是一个符号,一个代名词。在近代史上,他们盘踞了东北,让东北有了一个独特的盛产土匪的时代,土匪居然成了许多男人的人生理想和英雄情结。最多的时候,曾有几十万人加入此列……”大东北性格的雄悍,很大程度上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素。对此,素素也从大文化视野上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思考和解释:“一个土匪时代,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东北的宿命。东北太特殊了,既是日俄两强凯觎的肥肉,又是关内移民者谋生的沃土,这片原本属于游牧者和猎人的领地一下子变成了被外扰与内患挤逼的夹缝。移民者本是最有生命气息的人群,但移民者内心裹藏的那种绝望,又使他们最具破坏力。在他们还没有扔下手中的讨饭棍,生存状态还非常严峻时,做土匪便成了一种极端的人生选择。我发现,那些可以叫出名字的老牌土匪,没有一个不是闯关东的移民者或他们的后代。当我把他们置入移民文化的背景里,我的心便被触痛了。这其实是移民者共有的心态。我知道许多人和我一样,在回望那段历史那一群人的时候,有可能惶悚,却不会觉得陌生。东北从来就不是梦幻的,我们祖先也不是朝圣者,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就是死或者活。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东北于是被追逐和洗劫,喧哗和陷落。”(《黑颜色》)这样视野宏阔居高临下游刃有余地对土匪现象的理性把握,实在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所能达到的境界。
当然,素素说到底是在写文学散文,而根本不是写历史教科书或文化学术论文。因而,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还是她的这些大东北散文的生命。素素散文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她的语言上。素素散文语言的调度和组构实在让人感到作家聪明灵透之致。她经常采用这样的多重语义和语法拼合的句式进行表述:“大北风刮得你根本没办法说服自己站稳脚跟。”“在远古,人们好不容易栽种了一块文化的绿茵,因为横冲直撞的一支马队,便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满眼又是荒凉,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由于屠杀,人类在黑暗中的爬行不知有多么漫长。”还有,“在鸭绿江边,在他们当年洗过衣裙的地方,我把汗湿的脚伸了进去。”素素散文景物描写的语言也从不落旧套,而是完全传达自己的独立感觉,并建立语言的特殊的组构方式。如:“原以为,大兴安岭应该是触目惊心的那种挺拔。歌里也是这么唱的。但我似乎始终也没走到大兴安岭,因为始终也没看见那种逼人的高大。它一直就是一些岭,或者是一些山的连绵,络绎不绝层出不穷,以一种密不透风的郁闷阻挡着你的视线,羁绊着你的脚,让你山不转水也不转地安守本分。它的大,也是那块山地太大,颜色太深重,从地图上看,像一只雄鸡打架时凸起的颈骨,显出北方的坚硬和强壮。然而,那种婆婆妈妈式的纠缠,并没有挽留住那群躁动的灵魂,那种露骨的坚硬,却哺育出一支支膘肥体壮的马队。”(《痴迷的逃亡》)
素素散文中的主观情绪的投入也大大强化了其审美意味。其实素素散文的“散文”之魂,全在于作家的主观情绪在作品中的自始至终的充沛和洋溢。可以说,素素散文很少纯客观地向你讲述、描述或转述,而是在发自肺腑地向你倾诉。她把大东北最有文化意味和审美意味的对象首先摄入内心,然后再从心底向人们敞开她的大东北。如:“盛夏的时候去辽西并不是有意,而是这个时候就走到了辽西。原以为冬天去辽西,辽西才像辽西。没想到夏天去辽西,辽西更像辽西。那庄稼太矮小了,遮不住辽西的山。那庄稼是季节安插在这里的过客,一场秋霜,它们就将踪影全无。绿色在这里显得刺眼,它的那种隔膜和匆忙,仿佛是故意来伤辽西的心。它使盛夏的辽西比冬季的辽西还苍凉。辽西的山并不高,但它们绝对是山,曲线优美,迤迤逦逦。偶尔地,也有高耸和挺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论它高或者低,它为什么那么光秃,石化铁化尸化一般,与阳光河流雨伞花裙近在咫尺地恍若隔世。那些没有生命的山,让你感觉辽西是赤裸着的,那些山是被榨干了乳汁的女人的胴体,她们疲惫地仰卧在辽西,死了仍然做辽西的母亲。”这里全都是素素眼中的辽西,心中的辽西,是注满了素素情绪情感和联想想像的有着形象与生命的辽西。素素的全部大东北散文,都是这样的充满生命活力和情感张力的文字。
我想我以这么一篇短小的文字根本无法将素素大东北散文的丰富与深邃全部说透。而且素素散文中的多重文化意蕴和审美意味也只能从其作品本身去实际地加以领略。那么,你不妨随着素素的散文,直接走进一次浩瀚神秘的大东北。
1999年6月4日于河北大学当春斋
标签: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