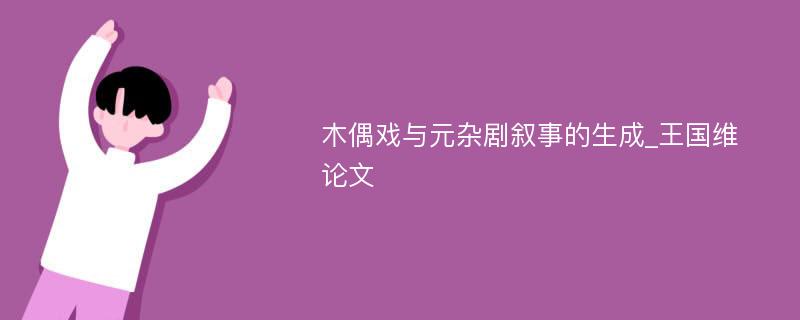
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叙事的生成——为孙楷第“傀儡说”正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傀儡戏论文,影戏论文,傀儡论文,元杂剧论文,孙楷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6-0060-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609 孙楷第在《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①(以下简称《唱演形式》)一文中,将标题的观点具体简化为“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出于傀儡戏影戏” (研究者简称“傀儡说”)。此论一出,研究者几乎给予全盘否定。否定论者将孙楷第的观点理解为是谈戏曲“表演”的来源问题。这其实是对孙楷第观点的曲解。考之文章内容,孙楷第文章标题中的“唱演”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科白”的“表演”,而是指构成戏曲“故事”的“曲白”的“唱演”。因为“戏曲故事的形式”是由“曲白”构成的,所以,孙楷第所说的“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不是泛指戏曲“表演”“出自傀儡戏影戏”,而是专指构成戏曲“故事”的“曲白”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这实际是在谈戏曲“叙事”的生成问题。这本是孙楷第的一个重要贡献,却长期被误读,故有为其正名的必要。以下分四点对孙楷第“傀儡说”的原意作解读分析。 一、前人对孙楷第傀儡说的曲解 前人对孙楷第的“傀儡说”的否定,主要是就戏曲“表演”的来源这一角度。如周贻白先是列举了从汉代百戏到宋元戏文杂剧的“中国戏剧之由真人扮演”的历史,然后说: 此即中国戏剧之本源,脉络分明,不容或紊。至于傀儡戏影戏,以其本身历史来说,傀儡与影人的出生,便是由模仿真人而来,进一步才模仿真人扮演的伎艺。及至有了真人扮演的戏剧,乃再进而模仿真人之戏剧表演。此为一定不移之逻辑……孙楷第先生认为中国戏剧之由真人扮演,系出自傀儡戏影戏,不惜颠倒事实,造为异说。……反映出他是从一己的主观出发,只从片面来看问题,因而把中国戏剧之发展的这条支流——傀儡戏影戏,认作本源。②(P78-79) 对孙楷第的“傀儡说”,任半塘先生也曾提出质疑: 戏剧乃人为戏,以人像人;傀儡戏乃物为戏,以物像人,而由人为之声。我国有戏剧出于傀儡戏之说,殊为可异……此在我国戏剧之演进史上,实造成一大惑不解之问题。③(P416) 周贻白、任半塘二位先生认为,傀儡本是模仿人的,哪有人反过来模仿傀儡的道理?这一看法影响甚大,至今,有学者在总结20世纪“傀儡戏与戏曲的渊源关系研究”状况时,依然沿着这个思路,从“表演形式”的时间先后上去否定孙楷第的观点。如陈维昭《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一书说: 从表演形式看,傀儡戏、影戏属于歌舞的范围;从表演性质上看,傀儡戏诞生于傩礼的仪式中。无论从表演形式还是表演性质上看,傀儡戏和影戏都不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第一历史时间。歌舞与戏剧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更早的历史时间,为什么却要“源于”或“原出”后起的傀儡戏或影戏呢?孙楷第把“渊源”问题不恰当地置换成“起源”问题,这使当时其他研究者可以轻易地把他的观点证伪。④(P106) 更有研究者借孙楷第的观点,断然否认傀儡戏影戏与戏曲有渊源关系,如徐弘图《南宋戏曲史》认为:“傀儡、影戏对宋元南戏与杂剧尽管有一些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十分有限。然而,孙楷第先生却把这种影响扩大到极点,以致得出‘宋元戏文杂剧源于傀儡戏与影戏’的结论……总之,宋代傀儡戏影戏与宋元戏文杂剧,各自有着不同的发生历史与发展轨迹,脉络分明,不容混淆。”⑤(P339-340) 这些否定论者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孙楷第“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出于傀儡戏影戏”的观点,理解为是谈戏文杂剧的“表演”“出于傀儡戏影戏”。实际上,孙楷第具体谈的是构成戏文杂剧“故事”的“曲白”的“唱演形式”“出于傀儡戏影戏”。“戏曲故事的形式”是由“曲白”构成的,而“故事”是中国戏曲形成的前提条件,正如王国维所说,只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才是“真正之戏剧”。⑥(P55)正是受王国维的启发,孙楷第对戏曲“故事”“唱演形式”的来源及生成,即戏曲叙事的生成问题,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探讨。 孙楷第“傀儡说”,重点谈的是傀儡戏影戏与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的生成关系,而不是谈傀儡戏影戏与戏曲“表演”上的渊源关系。这从孙楷第编《沧州集》保留的最初的论文题目上就可看出。其题《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考之文中的大部分论述,题目中所说的“唱演形式”多为傀儡戏影戏的“话本”与元杂剧“曲白”“唱演形式”的关系问题。由此,文章结尾也是从“话本”说唱与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的关系对全文作了总结: 凡中国伎艺之以扮唱故事、讲唱故事为主者,语其源,皆出于唐之俗讲……后世讲唱故事自俗讲出者,如宋之说话、元明之词话、及今之弹词鼓词是……后世扮唱故事自俗讲出者,如宋之傀儡戏影戏是。此等戏与说话较,唯增假人扮演为异,其话本与说话人话本同,实讲唱也……自宋戏文元杂剧兴,易傀儡儿词影词为南北曲词。⑦(P118-119) 这段话总结了中国古代说唱伎艺“皆出于唐之俗讲”,但又可分为以“讲唱故事”为主的如宋代“说话”等及“扮唱故事”为主的如傀儡戏影戏等,而“宋戏文杂剧”故事的“唱演形式”则是“易傀儡儿词影词为南北曲词”,是直接来自于傀儡戏影戏的“扮唱故事”。显然,这是在谈戏曲“故事”的叙事形式问题,而不是谈戏曲表演。 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戏曲“表演”的渊源与生成问题,很少有像孙楷第那样对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的来源及生成做系统研究。任半塘先生曾注意到孙楷第对戏曲“故事”的研究,可惜的是,却是给予全盘否定。其《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一文就否认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与宋代讲唱伎艺有渊源关系,他说,“不要过分强调故事性”“傀儡戏影戏不能真用话本,中国戏剧更不可能出于说话”“宋傀儡设若真用话本,则它的来源,将不出于唐傀儡戏或宋戏,反出于唐宋讲唱了。孙《考原》力主中国戏剧出于宋傀儡戏,这样一来,就可推进一步,认中国戏剧是出于宋讲唱或说话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纠纷更加复杂”。⑧(P181-192) 虽然现今的研究者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唐宋讲唱伎艺在戏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孙楷第有关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出自“扮唱故事”的傀儡戏影戏的论述却长期被误读。所以,对孙楷第《唱演形式》一文的写作初衷及内容有重做探讨的必要。 二、孙楷第的“傀儡说”源于王国维的相关论述 谈及《唱演形式》一文的写作缘起,孙楷第在文末明说是受王国维的启迪: 《宋元戏曲考》,绝作也。然读其书,亦时觉征引博而判断少……至于傀儡戏影戏,静安先生认为与戏曲更相近,有助于戏曲之进步,不能不注意;静安先生当时已注意及此,可谓有识。惜乎未详言之也……故余此文所论,非敢故与静安先生异。亦缘读先生书,寻绎久之,偶有所见,略欲发挥先生未竟之论。其言之有当与?则余与先生书稍有拾补之功。其言之未必当与;则故提出此问题,以与世之治曲者商讨;虽与先生言微异,亦无妨也。⑦(P121-122) 孙楷第这里明确说,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一书中提出傀儡戏影戏“与戏曲更相近”,但所言不详,为此,自己有意作文“发挥先生未竟之论”。为此,要想搞清孙楷第的“傀儡说”,当先明了王国维的有关论述。 王国维给戏曲下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⑥(P163)由此,他将戏曲的生成分为“歌舞”表演和“故事”叙事两个系统分别论述。就“歌舞”系统而言,王国维从“歌舞”的起源谈起,“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⑥(P4)进而论到汉代百戏、唐代踏摇娘、参军戏以及宋代滑稽戏等,这是戏曲来源中的“歌舞”表演系统,而在戏曲的“故事”渊源系统中则论到宋代的“说话”、傀儡戏、影戏等。 从王国维先生有关戏曲生成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将“故事”作为戏曲生成的前提条件而加以反复强调的。 在《戏曲考原》中,王国维围绕“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戏曲定义,在判定元代以前的表演伎艺是否为戏曲时,主要是看其中的“故事”因素。如他说:“[柘枝][菩萨蛮]之队,虽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戏曲也。”认为汉之角抵戏《东海黄公》《总会仙倡》等“所演者实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宋代“优伶调谑之事”“虽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词与故事否?若有歌词,果与故事相应否?今皆不可考。此时尚无金元间所谓戏曲,则可固决也。”⑥(P164)王国维列举这些例证想要说明的是,没有故事就没有戏曲。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依然以“故事”成分的多少来判定各种歌舞表演伎艺在戏曲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俳优歌舞戏“演故事”始自汉代,但只是“问演故事”:“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他举出北齐《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为例,认为“此二者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又指出唐代《樊哙排君难》戏与《破阵乐》《庆善乐》诸舞,“相去不远,其所异者,在演故事一事耳”。王国维先生还认为,宋杂剧之所以不能算作“真正之戏剧”,是因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他认为促成“真正之戏剧”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宋代的“小说”即“说话”:“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其原因是,宋代“此种说话,以叙事为主,与滑稽剧之但托故事者迥异……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王国维更提请注意的是宋代的傀儡戏和影戏认为:“至与戏剧更相近者,则为傀儡”。说傀儡戏“以敷衍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剧。此于戏剧之进步上,不能不注意者也”。又说“傀儡之外,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尚有影戏……然则影戏之为物,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傀儡同。此亦有助于戏剧之进步者也”。王国维之所以特别强调傀儡戏影戏与戏曲形成的关系,是由于他认为小说(“说话”)、傀儡戏、影戏“三者,皆以演故事为事。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然而非以人演也”⑥(P8、9、12、25-28)王国维认为傀儡戏影戏与宋代“不以演事实为主”的“滑稽剧”即宋杂剧相比,傀儡戏影戏“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宋代的“说话”相比,傀儡戏影戏则有“形象”。也就是说,在元杂剧之前宋代杂剧、“说话”及傀儡戏影戏三者比较而言,只有傀儡戏影戏不仅“专以演故事为事”,而且又有“形象”(即后来孙楷第所说的“扮唱”),所以“与戏剧更相近”。由此,王国维得出结论说: 综上所述者观之,则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⑥(P55) 王国维认为“纯粹演故事”的“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沿此思路,孙楷第《唱演形式》一文主要论述的是元杂剧“故事”“唱演形式”的来源与生成这一问题。他认为元杂剧“故事”的“唱演形式”不是来自非“纯粹演故事”的宋杂剧而只能来自“专以演故事”的傀儡戏影戏等故事说唱。 三、孙楷第对宋杂剧与傀儡戏影戏的比较 孙楷第在论及元杂剧“唱演形式”的来源时,用了比较的方法,他说: 傀儡戏影戏与杂剧在宋时同是杂伎艺。……今欲考察宋元以来戏文杂剧与傀儡戏影戏之关系,须先考察宋元以来戏文杂剧与宋杂剧之关系。盖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如与宋之杂剧关系极深者,则其体似即从宋之杂剧出,与傀儡戏影戏当无涉。设宋元以来戏文杂剧与宋杂剧之关系不深,则吾人今日视线,似可转移于傀儡戏影戏,而思及其与宋元戏文杂剧之关系矣。⑦(P72-73) 为此,孙楷第首先从“扮演之事类”,即题材内容的不同类型做比较,因为他认为扮演何种题材内容“事类”决定着其他诸方面的不同:“其事类既同,其人物登场之数与夫脚色之配置亦必相近。”⑦(P76)也就是说,“扮演之事类”不同,决定着“脚色之配置”“人物登场之数”等方面的不同。由此,他依次列举了宋杂剧与元杂剧在“扮演之事类”“脚色之配置”“人物登场之数”以及剧作长短等四方面的不同: 其一,孙楷第指出,从“扮演之事类”看,宋杂剧“虽敷演事状,而以诨谐为主,与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扮演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极世态人情之变者,绝对不同。此不合者一也。”⑦(P73) 从这一点可知,孙楷第所说的“扮演之事类”,实际就是指是否扮演“故事”。他认为,是否“扮演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是宋杂剧与元杂剧最大的不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宋杂剧与元杂剧在“脚色之设置”“人物登场之数”以及剧作长短等方面均不同。 其二,在“脚色之设置”上,孙楷第指出,“宋之杂剧,元之院本,其扮戏之重要脚色为副净,副末次之。元之杂剧,以末旦为重要脚色。其剧非旦本,即末本。戏文虽主从不分,然大致亦以旦末为主。若净则在南北曲中,均不占重要地位。无论南曲北曲,统全剧观之,绝无以净为主如宋杂剧元院本之所为者。此不合者二也”。⑦(P73) 沿着“扮演之事类”决定“脚色之设置”的思路,孙楷第这里列举了有着不同“扮演之事类”(是否“扮演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的宋杂剧与元杂剧不同的“脚色之设置”。我们知道,不同脚色职能总是与不同的“扮演之事类”相配。据《梦粱录》卷二十“伎乐”载,宋杂剧副净、副末的脚色职能是“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⑨(P309)“发乔”“打诨”的职能是由宋杂剧“以诨谐为主”的内容决定的。而旦、末脚色是人的性别区分,性别脚色的设置是由“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决定的。因为人之男、女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有了演述“极世态人情之变”的故事,才会有标明男女性别的旦、末脚色。《梦粱录》卷一“元宵”所记,杭城“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中,已有“细旦”脚色。⑨(P141)与“以诨谐为主”的宋杂剧用“发乔”的副净、“打诨”的副末不同,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都用“旦”脚,正是因为“宋之傀儡戏影戏,以其扮演之事类言,实与元杂剧全同也”。它们“扮演之事类”都是演述“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 其三,从“人物登场之数”看,孙楷第指出,“宋杂剧元院本,其登场人物极少……其脚色不过戏头、引戏、副净、副末四人,其装孤、装旦,可有可无。而戏头、引戏,尚非参加扮演者。实则一剧之演,有二人即可成立。若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其脚色名目虽亦不出旦、末、孤、净四种,而外脚极多。虽以北剧之短,其登场人物有多至十人以上者。……若南戏统全剧观之,其登场之人物亦众。皆与院本迥异。此不合者三也”。⑦(P73-74) 与上一点论证的思路一致,这一点是想说明“人物登场之数”也是由“扮演之事类”决定的,“事类既同,其人物登场之数与夫脚色之配置亦必相近”。元杂剧“扮演之事类”是“极世态人情之变”的“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所涉人物必然众多。至于宋金杂剧院本,孙楷第指出:“其事意略如今杂耍场中之对口相声、彩唱双簧等,非大戏。”⑦(P72)故“有二人即可成立”。 其四,从剧作长短看,孙楷第指出,“宋之杂剧元之院本,其事既简质,其文应极短……余谓宋元杂剧院本之特征有二:其一为诨体,其二为短文……若元杂剧则以四折为度,其长者有多至六折乃至十余折者。至戏文之长者,更叠至数十折。此不合者四也”。⑦(P74) 孙楷第以剧作的长度判定其是否为“纯粹演故事之剧”,这正符合戏剧、小说的经典定义。因为有无一定长度的故事,是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成立的前提。如亚里斯多德《诗学》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⑩(P16)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引述的小说定义是“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11)(P3)戏文、元杂剧敷演“极世态人情之变”的“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涉及的人物多,内容复杂,篇幅必然就长。 由此,孙楷第得出结论:“以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与宋元之杂剧院本较,从各方面观察,其不同者如是之多。乃谓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应从宋之杂剧及元明人所谓院本者出,无斯理也。”⑦(P74) 总之,孙楷第先生认为,相比“以诨谐为主”的宋杂剧,元杂剧脚色分旦末、登场人物多、剧作篇幅长,这些都是由元杂剧“扮演之事类”是“扮演社会上历史上种种故事”决定的,与“诨体”“短文”的宋杂剧无缘。 四、元杂剧的“唱演形式”来源于傀儡戏影戏 王国维认为宋杂剧“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傀儡戏影戏“以敷演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剧(宋杂剧)”,而“说话”与傀儡戏影戏,“皆以演故事为事”,不过“说话”“但以口演”,傀儡戏影戏则有“形象”,所以“与戏剧更相近”。孙楷第则区分“说话”是“讲唱故事”,傀儡戏影戏是“扮唱故事”。为了论证“纯粹演故事之剧”的元杂剧“唱演形式”是来源于“扮唱故事”的傀儡戏影戏,而不是源自“诨体”、“短文”的宋杂剧,《唱演形式》一文,首先从“扮演之事类”的继承关系上论述了元杂剧“唱演形式”是来源于傀儡戏影戏: 宋之傀儡戏,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所记,乃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或讲史。影戏据《都城纪胜》,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由此观之,傀儡戏影戏决不与当时之所谓杂剧者同,以诨谐为主。且考其名目,不唯与说话人之小说讲史者同,即元杂剧戏文,所敷演亦不出演烟粉、灵怪、公案、铁骑、史书五种。⑦(P74-75) 由此,《唱演形式》一文得出结论:“宋之傀儡戏影戏,以其扮演事类言,实与元杂剧全同也……与戏文亦必有许多相似者。以是言之,则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与傀儡戏影戏乃同一系统者。”孙楷第在文末特别提到:“夫论事必明其系统,系统明而后主从可分。”⑦(P76、121)可知,孙楷第认定戏曲故事“唱演形式”的生成有一个渊源系统,文中反复论证了“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与傀儡戏影戏乃同一系统”,并说明这一系统的组成还包括唐代俗讲转变、宋代说话等说唱伎艺。 接下来《唱演形式》一文从“剧本”和“扮戏”两方面举例证明了元杂剧曲白的“唱演形式”是来自傀儡戏影戏等故事说唱。“剧本”方面的例证,孙先生列举了两点,即“偈赞词之使用”和“说话口气之保留”。此外,还谈到“似说话人”的“当场扮脚人之往复对答”。所以,实际谈了三点: 一是“偈赞词之使用”。 “偈赞词”本指唐代俗讲的唱词形式,这在现存的诸宫调及南戏作品中均有遗存,如《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杀狗记》中就有曲调为[傀儡儿][大影戏]的曲词。由此,孙楷第说:“傀儡戏影戏唱词,余谓其词当沿唐五代俗讲偈赞之体……其词似以六言为骨干而稍变化之……如今所见《丑女变》即多用六言词。余考其体,实与《杀狗记》等所引大影戏词为近。”⑦(P80)南戏《杀狗记》第三十一出[大影戏]词如下: (小生唱)[大影戏]嫂嫂行不由径,(旦)开门!(小生唱)我应是不开门。自来叔嫂不通问。休教说上梁不正。(旦白)你哥哥也在这里。(小生慌介)呀!(唱)忽听得一声唬了我魂,战战兢兢,进退无门。心儿里好闷!我便猛开了门,任兄长打一顿。(12)(P104) 另外,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记有张戒“弄影戏语”的七言影戏词: 郭公凛凛英雄才,金戈铁马从西来。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13)(P95) 针对这些例证,孙楷第说:“宋之影词有七言者,亦有六言者,其体与唐俗讲本变文之偈赞正同。”至于元杂剧,孙楷第认为,“元曲之白,尚非纯粹白文。在诸白中,往往藏有若干吟词,其吟词皆为偈赞体。如《薛仁贵》《渔樵记》《酷寒亭》《潇湘雨》《冻苏秦》等剧中,皆有其例”。⑦(P82)以《冻苏秦》第二折“孛老”说白中的吟词为例: 不由我哭哭啼啼,思量起雨泪沾衣。且休说怀躭十月,只从小偎干就湿。几口气抬举他偌大,恰便似燕子衔食。今日个捻他出去。呸!那里也孟母三移!(14)(P254) 据此,孙楷第指出,这些“偈赞词”“实与今之傀儡戏影戏本子同。故余疑此等词即傀儡词影词之未删者……《潇湘雨》《冻苏秦》二剧之多着偈赞词,或即缘其剧据傀儡戏影戏话本改编”。⑦(P85)这就说明了元杂剧曲白的“唱演形式”是来自唐代变文及宋代说话、傀儡戏影戏的“话本”。 二是“说话口气之保留”。 关于这一点,孙楷第有一段完整的论述,他说: 宋之傀儡戏,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讲史。宋之影戏,其话本尤与讲史为近。此二者以词言,皆不尽为代言体,应参杂说话口气。以傀儡戏影戏虽扮演故事,而其扮演与讲唱本分为两事,其讲唱固可适用于说话体也。及傀儡戏木人为真人,以讲唱之事付之真人之为肉傀儡者;影戏以真人代纸人,以讲唱之事付之真人之为大影戏者;此时讲唱与扮演为一事。扮演之人,即讲唱之人。以理言,其话本固应一律改为代言体。然将话本一一追改,其事至繁,非人情所乐为者,此时所用话本,或犹是旧本。纵有改动,亦不过一部分而已。其话本之参杂说话口气如故也。宋之戏文元之杂剧,以余所考,实即肉傀儡及大影戏,不过以南北曲词代傀儡儿词及影词耳。当戏文杂剧造作之始,或即就傀儡戏影戏话本改编。其执笔时,话本文句,固不暇一一删除;话本之体,或犹徘徊于胸中,不能一时忘净。则戏文杂剧中,宜必有说话口气。此事余在戏文中未发现,而元杂剧中却有其例。其最著者,为扮脚人之宣念剧名。⑦(P89) 这里是说,傀儡戏影戏的故事说唱在“说话体”中出现“代言体”有一个过程。当傀儡戏影戏中的“木人”和“纸人”由“真人”代替,出现了肉傀儡和大影戏时,就有了更多的代言体。宋代的“说话”有故事,但没有“代言体”,而宋杂剧有代言体却没有那种“极世态人情之变”的故事,只有肉傀儡和大影戏与元杂剧全同,既有代言体又有故事。由此,《唱演形式》一文得出结论:“宋之戏文元之杂剧,以余所考,实即肉傀儡及大影戏。”具体例证见于剧中“扮脚人之宣念剧名”,即在剧作结尾剧中人站出来面向观众宣告剧名。如杨梓《承明殿霍光鬼谏》第四折在唱曲中宣告剧名: [落梅风]灭九族诛戮了髫龀,斩全家抄估了事产。可怜见二十年公干,墓顶上滟滟土未干,这的是《承明殿霍光鬼谏》。 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第四折是在剧末“吟词”中宣念剧名(“吟词”内容有省略): (寇准云)……则为这“刘员外云锦百尺楼”,结末了《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还有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四折: (正末云)……这的是“西邻友生不肖儿男”,结末了《东堂老劝破家子弟》。 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第四折: (洞庭君词云)……这的是“泾河岸三娘诉恨”,结末了《洞庭湖柳毅传书》。(15)(P740、369、58、749) 针对《霍光鬼谏》于唱曲中宣告剧名现象,孙楷第指出:“剧演霍光,非霍光所能知。剧取何名,宜非霍光所能言。今竟着此语,明是说话人口气也。”⑦(P90)又说《破窑记》等剧末所谓“结末了”即指“此剧已了”,但“剧之了与否,与诸人无涉。今竟着此语,明是说话人口气也”。其体例渊源是来自宋代的“说话”及傀儡戏影戏:“凡说话人演说,每一段终了,多缴清题目。如宋人小说《冯玉梅团圆》,第一段入话叙徐信、刘俊卿互易其妻讫,释云:‘此段话题作交互姻缘。’百回本《水浒传》第十六回,记晁盖劫生辰纲事讫,释云:‘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第四十四回记晁盖等劫法场拥宋江至白龙庙讫,释云:‘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百回本《水浒传》书编定在元末。其为此等语,定是沿宋人说话旧例。宋之傀儡戏影戏,其事即近于说话,其话本每演一事讫,亦当缴代题目。”这就说明了:“元曲临了以扮脚人宣念剧名者,乃沿傀儡戏影戏话本之体也。”孙楷第又将此种宣念剧名的“偈赞体”,上溯至唐代俗讲:“此临了所念词偈,等于唐俗讲之有解座文。傀儡戏影戏于剧临了时诵此词,其事必遥有所承。而元杂剧为新兴之剧,亦承用此体,不能遽废,亦可见旧习之不易打破矣。”⑦(P91-92)这是论证了元杂剧曲白中“说话口气之保留”,是承自唐代俗讲、宋代说话及傀儡戏影戏。 三是“大似说话人”的“当场扮脚人之往复对答”。 《唱演形式》一文又以无名氏《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尚仲贤《尉迟恭单鞭夺槊》等剧中“探子报前方军情”为例,说明其“当场扮脚人往复对答”的说唱形式来自话本。如《单鞭夺槊》第四折:“此折所演,绝非寻常问答方法,其神情意态,乃大似说话人在场上讲唱问答者。又勣(指剧中人徐茂功)白皆为偈赞之词。故此折词文,与其谓之北曲,无宁谓之话本。元曲有此体,其必受话本影响甚明。”与说话人只有单一的“说话体”相比,元杂剧这种“代言体”和“说话体”二者兼有的叙述方式,孙楷第说:“余意若认为效傀儡戏影戏话本之体,则尤适宜也。”⑦(P95) 孙楷第又将《单鞭夺槊》中这种“似说话人在场上讲唱问答”之体,追溯至唐代俗讲。他说: 此体唯适用于北曲,南曲不得沿用。以北曲每折只以一人唱,其相对讲谈者为宾,与古人讲唱之制合也……说话讲唱之制,宋人书亦不载,余意定同唐人俗讲;以宋人说话,即从唐俗讲出也。凡俗讲之讲经文者,其制以一人司唱经,谓之都讲;以一人司讲解,谓之法师;以一人司吟词偈,谓之梵呗。其不讲经文唯演经中故事者,则都讲似可省。其以一人司讲一人司吟词偈则如故。此一人司讲一人司吟之制,当即后世影戏说话讲唱之制。⑦(P95) 他认为这种“讲者可请可问,而唱者唯以唱词作答。此是自唐以来说唱相沿一定之例”。⑦(P97)也就是说,元杂剧“当场扮脚人往复对答”的“唱演形式”,亦“自唐以来说唱相沿一定之例”发展演化而来。 “扮戏”方面的例证,孙先生列有三点,即“自赞姓名”“涂面”和“步法”。“步法”纯属表演问题,此处不论。孙楷第论元杂剧的“自赞姓名”和“涂面”也是从与傀儡戏影戏“故事”的“唱演形式”渊源关系角度论述的。关于“自赞姓名”,孙楷第先生认为:“凡元杂剧及戏文,其脚色初次上场,皆念诗词。念讫,自道姓名。”“若一脚色同他脚色一齐上场,则视其关系身份,由其中一脚色先自道姓名讫,然后为其他脚色道姓名。”⑦(P97)这实际就是戏曲中的“自报家门”,属宾白叙事问题。但是,宋杂剧中就没有这类“自赞姓名”,因为“宋之杂剧,其所演者大抵为村俗鄙俚之事,演古传记者极少。其中人物多不必有姓名”。⑦(P98)而“傀儡戏影戏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之事。此所演以事实为主,非以诨谐为主甚明……其事多见于古传记,其所扮之人,必须有姓名。傀儡戏又演史,影戏则以演史为主,其所扮之人,更须有姓名。然则元杂剧戏文脚色之自赞姓名,宜出于傀儡戏影戏无疑也”。⑦(P98-99) 关于戏曲“自赞姓名”与宋代说唱伎艺的关系,在孙楷第之前,李家瑞于1937年发表的《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一文也有过论述。他先是论述了傀儡戏影戏、连厢词等这类说唱伎艺与“说书”(即“说话”)的关系,如“连厢词”:“打连厢是用一人说唱一段故事,而另以若干人扮演故事中人的举动,实在就是说书人用人做傀儡以表现他所说的书里的人物。”(16)(P409)再如“影戏”:“最早的灯影戏,也是叙述故事的说书……那影人的功用,也如同打连厢之用人做傀儡,不过补助故事说唱而已。”(16)(P411)接着又论述了打连厢、傀儡戏影戏等这类既有说唱又有“扮演”“叙事代言互用的”说唱伎艺与戏剧的关系:“用叙事方便的时候,就用叙事;用代言方便的时候,就用代言;因此这种话本即成为说书与戏剧混用的本子了,就是说书变成戏剧过渡时期的本子。”(16)(P417)其后,又以戏曲的“自表姓名”为例,说明了戏曲与说唱伎艺的关系: 剧中人自表姓名,且自言自语的自述来历,这等地方,不能不说是受了说书的影响。初看中国戏的人,往往以这种戏剧体裁为奇怪,但要知它是从说书转变来的,那就不觉得奇怪了。中国说书变成章回小说,说的人已不少了,但说书变成戏剧,似乎还没有人提到过。我们希望对于说书和戏剧有兴趣的人,参加这种讨论。(16)(P418) 继李家瑞之后,孙楷第系统论述了傀儡戏影戏话本即属于“说书变成戏剧过渡时期的本子”。 “自赞姓名”还涉及“他赞”与“自赞”的叙述人称转换问题。与一般的“讲唱制”话本相比,傀儡戏影戏有“扮演”就会有第一人称的“自赞”,“于是道姓名之事不复由他人行之,即由扮脚人自行之,此时人之为影人者,不唯肖古人之貌,兼亦肖古人之言”,这样,就“由他赞改为自赞”了。⑦(P100-101)《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从傀儡戏影戏与其他叙事伎艺的比较中说明了这一问题:“凡傀儡……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更有弄影戏者……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⑨(P311)其中所谓“或讲史”,是说傀儡戏影戏的话本有如“讲史”般的“他赞”叙述,“或作杂剧”是说有如杂剧般的“自赞”代言,“如崖词”是说有如崖词般的唱词。正如王国维所言,与宋代的“小说”等讲唱伎艺相比,“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傀儡戏影戏在“口演”时有“形象”扮演,孙楷第称之为“扮唱故事”,这使得故事的演述在“他赞”中又有了“自赞”,就使傀儡戏影戏“与戏剧更相近”。 “涂面”,即指人物的脸谱化妆,这与“自赞姓名”密不可分。因为戏曲开场人物的“自赞姓名”,常与“涂面”相配以区分善恶。《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记影戏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⑨(P311)说的就是以涂面区分善恶。《梦粱录》卷一“元宵”条还具体描述了傀儡戏中“细旦”的化妆是“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⑨(P141) 《唱演形式》一文从故事人物与“涂面”关系角度论述了元杂剧的涂面不是来自“滑稽小戏”的宋杂剧而是来自“演史书传记之事”的傀儡戏影戏。元杂剧“涂面”的脚色数量多,是因为:“其演史书传记之事,人物多,每一脚色皆有涂面机会也。”⑦(P107)而“宋杂剧脚色之涂面者,唯副净一色,其副净之涂面方法,亦至简单”。这是因为宋杂剧“为滑稽小剧,其事简质,登场人物至少也”。与宋杂剧不同,“傀儡戏影戏演史书及小说、传奇、烟粉、灵怪、铁骑、公案之事,无所不备。其事既繁,其登场之人物必众。其以妍媸区别人物,以及善神恶鬼,何方?何界?何人之灵?咸须有安排计较,不可雷同。故其雕形饰貌,经纬百端,应远较宋杂剧之涂面为复杂”。这就使得傀儡戏影戏的“涂面”“必为宋戏文元杂剧所取则”。⑦(P109) 另外,从“涂面”的寓意看,宋杂剧的涂面“无深意”,是因为“宋杂剧副净之涂面,不过故为猥琐之状以博一笑耳。无他深意也”。而“以扮演故事为主”的傀儡戏影戏要以涂面辨善恶:“若傀儡戏影戏以扮演故事为主,其木人影人貌像之妍媸,视所扮人之品类而定。是则以像别贤愚,以像觇地位,以像辨性情。其为物也,近乎相法。名脸谱,实人谱也。”⑦(P109)总之,元杂剧的“涂面”,只能是来自故事繁、人物多的傀儡戏影戏而不是宋杂剧。 傀儡戏影戏有“形象”(王国维语),有“扮演”(孙楷第语),所以有“自赞姓名”与“涂面”,这就使傀儡戏影戏区别于“说话”而“与戏剧更相近”。这也开启了中国戏曲审美的先河。戏曲人物出场,先通过第一人称的“自赞姓名”和“涂面”,让观众立即区分出善恶好坏之人,这是戏曲审美区别于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伎艺的显著特征。如焦菊隐所说:“咱们群众欣赏戏曲的习惯是什么呢?人物出来先看你是好人坏人。”(17)(P228)齐如山说得更具体:“什么是开门见山呢?就是国剧的规矩,无论任何人,只要他一出台帘,便要使观众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种规矩,是处处都要表现出来的。……正人一张口,便是正经话……坏人一张口,便是没有道德的话……脸谱,这更是表现善恶更明显的一种办法……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或用哪一种办法,总要使观众一看一听,便知道该剧中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各国戏剧所没有的。”(18)(P349-350) 如上所论,由王国维初步提出,孙楷第详加申论的戏曲“故事”“唱演形式”的来源与生成问题,其意义正如解玉峰《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一书所说,故事讲唱“是中国戏剧产生的前提性条件。没有讲唱文艺为中国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故事作先行性的普及,中国戏剧可能便无从产生”。但是,《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对王国维、孙楷第有关论述的评判却失之偏颇。书中说,王国维的戏曲定义“以歌舞演故事”,只是对“歌舞”扮演“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没有意识到”中国戏剧中“故事”的重要性;认为孙楷第“‘傀儡说’是有很大问题的”“没有很明确地认识到……唐宋以来讲唱文艺讲唱的故事,是中国戏剧产生的前提性条件。”这些评价显然是在没有深入研究王国维、孙楷第的相关论述的情况下草率得出的结论。这种评价实际正反映了《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一书所总结的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偏向,即“在20世纪中国戏剧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所有带有‘扮演’性质的戏剧现象和戏剧形态都受到足够的关注,从‘优孟衣冠’到‘二圣镮’、从‘兰陵王’到‘踏摇娘’、从两汉‘百戏’到两宋‘杂剧’,而讲唱文艺因为没有‘扮演’,没有‘戏剧性’,所以被严重忽略!”(19)(P64)实际上,孙楷第承续王国维,对唐宋“讲唱文艺”与中国戏曲生成的关系已经做了系统论述。 孙楷第的“傀儡说”,长期以来遭冷落,被尘封,有关的学术著作,要么简单引述不予置评,要么云其“缺乏证据”,(20)(P452)要么进行质疑、批驳。孙楷第《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一文或有不确、不周之处,但其努力探寻戏曲“故事”的“唱演形式”即戏曲“叙事”的生成之路,其方向是正确的,其开创之功应予肯定。 注释: ①孙楷第《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一文,作于1941年秋,1942年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1、2合期,改题为《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1952年收入《傀儡戏考原》时即为此题,1965年收录于《沧州集》时仍用原题,文字略有删改。1952年由上杂出版社出版的《傀儡戏考原》一书收有《傀儡戏考原》和《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两篇文章。《傀儡戏考原》一文主要考证傀儡戏本身的问题,《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则多论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的关系,文中第五节的小标题即为“宋之傀儡戏影戏与宋元以来戏文杂剧之关系”,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傀儡戏影戏与元杂剧的关系。 ②周贻白.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对孙楷第先生《傀儡戏考原》一书之商榷[C]//.周贻白.周贻白戏剧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③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④陈维昭.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⑤徐弘图.南宋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⑥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⑦孙楷第.傀儡戏考原[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2. ⑧任二北.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J].戏剧论丛,1958年第1期.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⑨(宋)吴自牧.梦粱录[M].《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⑩[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2)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宋)张戒著,陈应鸾校笺.岁寒堂诗话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4)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5)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6)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焦菊隐.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探索[C]//.焦菊隐.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8)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9)解玉峰.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