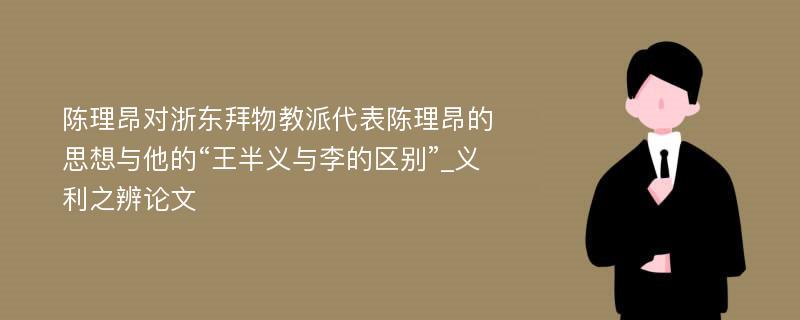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事功论文,义利论文,代表人物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浙东事功派
宋学到南宋发生了一个急剧的、重要的变化。在宋高宗、孝宗之际的四十年间,北宋宋学兴盛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派——二程洛学,亦即当时人们称之为“道学”(即理学)学派,像暴发户一般,成为当时的显学。亦正是在社会上充斥一片道德性命的说教时,与道学相对立的浙东事功派亦突然兴盛起来,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从而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大放异彩。
浙东事功派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学术思想的根基。下面首先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先说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浙东学派诞生的土壤是浙东路。北宋时浙东、浙西两路谓之两浙路,南宋时才析而为浙东、浙西两路。两浙是宋代社会经济最称发达的地区,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城镇都居全国之最。到南宋,这里的经济发展又具有新的特点。其一是,由于杭州成为南宋行在,人口激增至百万,两浙路许多城市也随之增长。城市人口增长,商业贸易更显得兴盛。这样,商人的力量较之北宋更加扩大了。其二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各种生活必需品如粮米布帛的需求随之大增,而物价随之提高,生活在宋孝宗宁宗诸朝的叶适对此曾有所记述:
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徒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1](卷2《水心别集·民事中》)
值得注意的是,米帛薪炭生活必需品价格倍增的同时,地价增长尤为惊人,不仅是“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地价增长如此迅猛,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因此,随着物价的增长,又形成了两浙地区社会经济上的又一特点,即土地转移的急遽是前所未有的。有关这类材料为数不少,就拿陈亮所记录的他的家乡永康一带的情况予以说明:
[喻夏卿]中年与其侄分田,不过百三十亩,卒亦几至于千亩。[2](卷36《喻夏卿墓志铭》)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夫人初归吕氏,家道未为甚裕,吕君不遗余力,经理其家,至有田近数千亩,遂甲于永康。[2](卷38《吕夫人夏氏墓志铭》)
永康陈氏……百四五十年之间,衣被国家之饱暖,大家世族或已沦替而无余。[2](卷36《陈府君墓志铭》)
喻夏卿之田地自百三十亩到近千亩,以及永康吕氏有田数千亩都是二三十年实现的,足以说明土地转移之剧烈。而在陈氏家族百四五十年中,即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二世纪末,土地转移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新兴起的土地势力——暴发户,而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土地势力,“大家世族或沦替而无余”,衰落下来。土地势力中的大起大落,极其明显的是,与城市商人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的土地暴发户大都出自这个势力。浙东事功派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形成的。
南宋初的几十年,浓重的反动政治气氛弥漫于朝廷上下。宋高宗——秦桧集团以“绍兴和议”的方式向女真贵族屈膝投降,轰轰烈烈的抗金卫国战争为之葬送,抗金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与此同时,这个卖国集团一再加强其反动专制统治,主张抗战、谈论恢复的有罪,顺从其卖国媚外的则鸡犬升天,而舆论的钳制,篡改、销毁抗金斗争的史实,则是其反动统治的小焉者也。“隆兴和议”再度屈节以来,宋孝宗虽欲有所作为,但内受制于身为太上皇的赵构,外又被汤思退们把持政柄,这种形势用陈龙川的话来说,依然是“架漏过时”、“牵补度日”,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之中[2](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在这种政治低气压的窒息之下,固然有利于投机取巧者、庸人的钻营,以及一些保守落后的思想得以孳生;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亦激发、砥砺了一批士大夫的爱国壮志,使他们积极献身于恢复的大业,以彻底改革这一屈辱的局面。浙东事功派便置身于这批士大夫中,成为时代的前驱。亦正是由于浙东事功派献身于恢复的伟大事业,力图改变现有局面,他们便极其自然地继承了宋学建立以来自范仲淹到王安石等的面向社会实际、讲求应用于社会实际的优良学风,从而形成为浙东事功派。浙东事功派指的是生活成长于浙东地区的士大夫,除吕祖谦作为从理学向浙东事功派转折过程中的学者外,主要代表人物则有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和叶适等人。如薛季宣、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曾经说:
[士龙,季宣字]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3](卷7《别集·与朱侍讲》P239)
这封信说明,薛季宣所研治的学问如田制等都是供实际应用的学问,与胡瑗所讲究的务实之学多么一致!薛季宣在给薛象先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自己的治学态度是:
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4](卷25《答象先侄书》P395)
“无为空言,无戾于行”,是薛季宣务实的最扼要的说明。薛季宣的治学态度和道路,是所有浙东事功派治学态度和道路的体现,或者说是浙东事功派的同具的特点。
从学术渊源来看,浙东事功派大都入经出史,从史学中寻绎出解决当前政治经济中种种问题的办法,充分地体现了史学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与理学家有所不同。洛学的创始者程颐还懂得利用史籍提高自己的思维认识能力:“先生(指程颐)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5](卷22《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八上》)。程颐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中来谈历史,用来提高自己。但包括程颐在内的二程没有对他的学生多谈史学的功能。朱熹不仅自身反对吕祖谦、陈亮,且把史学也作为自己的反对对象,从而表现了他的偏狭:“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6](卷123《陈君举》)实际上,史籍“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语),既能够从成败盛衰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又能从典制的因革损益中,为今天的措施规划找出路子,历来都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浙东事功派都非常重视对史籍的研究,而且,也都有有关史学著作。这一点是人们都知道的,不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既然要献身于恢复大业,而恢复大业就必须懂得军事,因此,事功派对军事格外重视。概括来看,他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如陈亮的《酌古论》,通过前代许多人物在军事活动中取得的成就、经验,为今所用。另一方面是从讲求制度入手,前面说过的薛季宣讲“兵制”即是一例。陈傅良的《周汉以来兵制》论述历代兵制,又是一例(注:据先师邓广铭教授《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枢廷备检>》一文,题名为陈傅良所作的《历代兵制》,卷八则录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之《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前七卷即《周汉以来兵制》,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叶适对前代兵制的优劣得失,也有所论述。总之,浙东事功派之探索、研究历史,旨在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浙东事功派既然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对于空谈道德性命之学亦即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理学创始者程颢在领悟了“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这一矛盾对立的道理时,“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5](卷11《河南程氏遗书·师训》)。在南宋反动统治四十年间,在北宋不过一个小的宗派——二程理学,却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显学,这自然是程颢所未曾料到的。当着道德性命之学成为暴发户、居于主导地位之时,就在其身旁、突兀而起,形成了批判道德性命之学的浙东学派,这同样是领悟了“无独必有对”矛盾对立这一道理的程颢始料未及的。程颢亦没有料到他所创立的道学受到浙东事功派的有力的冲击。浙东事功派之批评道德性命之学,是这一学派再一共同的特点。前面提到的薛季宣即对崇尚空谈的学术予以鄙夷和批评。在给一位心学家杨简的一封信中,薛季宣指出,“灭学以来”,把“言行判为两途”的偏颇、不全面,称那些“矫情之过者,语道乃不及事”,徒发空论,“其为不知等尔!”同时,表明他对那些“清谈脱俗之论”,“未能无恶焉”[4](卷25《抵杨敬仲简》P397)。在给另一位著名学者沈焕的信中,将那些“言道而不及物”的空谈家视之为“今之异端”[4](卷25《抵沈叔晦焕》P398)。如果说,薛季宣这些言论对理学家们还留有三分情面,而在另外两道策问中,对“道学之统,源流之辨”,则指出理学家们所开列的“道统之序应当去其亡而辨其惑”,直指程系理学的要害!陈亮和叶适,特别是陈亮,对程系理学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的。
除陈亮外,浙东事功派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虽然怀有经世之志,但他们并没能登上朝廷这个政治舞台,施展其政治抱负,而只能够屈居于州郡,作出许多斐然可观的政绩,为当地造福。除事功派外,像理学中的朱熹、陆九渊、杨简等,以及既非事功派又非理学家的辛弃疾,在思想认识上并不一致,而且,寓存尖锐的矛盾。但他们属于中下层士大夫,对改变南宋的政局则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认识,他们和事功派一样,屈居州郡,在地方上做出可观的政绩。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我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7]一文中提出的,到南宋,中下层地主阶级经济力量削弱,使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发挥政治才能。其次,在他们当中没有出现一个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的领导群伦的杰出人物,统一大家的认识,实行第三次政治变革运动,只能分散在各地,进行局部的改革。因之,浙东事功派给人们留下来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业绩,而是绚丽多彩的精神财富。
二、陈亮——终生为恢复大业而奔走呼号的杰出思想家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市)人,学者尊奉为龙川先生。
陈氏家族是绵延二百年的永康大族,陈亮一支则在其祖父时家道已经衰落,青年时期的陈亮生活是较为清苦的。大约在陈亮中年时期,家道又复振兴。从淳熙十二年(1185年)陈亮给朱熹的一封信中,叙述其灌园治产、兴修土木的怡然自得的情况可清楚地表现出来:
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数处小亭子。……两池之东有田二百亩,皆先祖先人之旧业,尝属他人矣,今尽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复何憾!田之上有小坡,为园二十亩。……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对之。屋之东北,又有园二十亩,种蔬植桃李而已。[2](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
此外,陈亮在京口还置有别业,包括房舍和芦地。单是信中所说之田二百亩、园四十亩,陈亮已经是一个经济力量较强的中等地主了。这些田产约在陈亮34岁时恢复起来,使一家无衣食之忧。但没有料想到,家道的复兴,却招致了不少的闲言风语,给陈亮添了不少的麻烦。
陈亮本来是一个功名之士,可是命途多蹇,屡试不中,摧折锐气。尤为不幸的是,陈亮一生又遭到两次狱事。据先师邓广铭《陈龙川狱事考》[8],陈亮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第一次入狱。入狱原因是当权者“主于治道学”,陈亮与道学家们来往甚多,加上其他琐事,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亮遭此无妄之灾达数月之久。第二次狱事是在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冬,历时约一年半,至绍熙三年春方从衢州监狱中出来。这次狱事是由于陈亮得罪了考官何澹,何澹任御史中丞后当即予以报复,而陈亮家道的复兴招人嫉忌,从而给陈亮横添上“豪强”、“任侠”等许多罪名。从陈亮出狱后给郑汝谐侍郎等人的几封谢启中,就可以看出狱事的始末端倪:
[亮]晚乃自安于一廛。身名俱沈,置而勿论;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2](卷26《谢郑侍郎启》)
同故旧之戚休,乃名“任侠”;通里闾之缓急,见谓“豪强”。欲为饱暖之谋,自速摧残之祸。[2](卷26《谢何正言启》)
谓其豪强,处以任侠。[2](卷26《谢葛知院启》)
重以当涂之切齿(指何澹的迫害),加之群小之凿空。[2](卷26《谢梁侍郎启》)
上述材料对了解陈亮的狱事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对进一步了解陈亮的财利观、功利主义尤为重要,后面再加叙述。
陈亮虽命途多蹇、两遭狱事,但贯穿他一生的则是为抗金而奔走呼号,为恢复大业而著书立说。乾道五年(1169年),陈亮以所著《中兴五论》上奏宋孝宗,“不报”,之后十年,又于淳熙五年(1178年)向孝宗连上三书,淳熙十五年(1188年)再次向孝宗上书,至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殿试的对策,六次上书,以及《酌古论》、《三国纪年》、《汉论》和一些史传序文等等,都是围绕抗金恢复大业这一根本问题的。综论陈亮对抗金恢复大业的论述,可以分析如下几点。
(一)陈亮指出,宋孝宗“愤王业之屈于一隅”,“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因而,积极推动宋孝宗投身于抗金恢复大业:“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2](卷2《中兴论》)。过去之所以不能从事于恢复,“独畏其强尔!”其实这是不对的:“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势不与虏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虏”。可是,自从秦桧破坏抗金大业,“忠臣义士斥死南方”,“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为何事也”!杭州这个南宋行都所在之地,秦桧不遗余力地打击抗金力量,“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而余矣”[2](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晏安鸠毒。如果再这样耽误下去,“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不仅“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而且,形势变化如此,抗金恢复大业“可得而缓乎”
(二)抗金恢复大业既然是如此紧迫,那么,从何处下手呢?陈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察,他认为:从守的一面看,“吴会者,晋人以为不可都,而钱镠据之以抗四邻”,“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则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泽横亘其前。虽有戎马百万,何所用之”!仅有一条海可以“径达吴会”,但“海道之险,吴儿习舟楫者之所畏,虏人(指女真贵族)能以轻师而径至乎”?京口、建业,“登高四望,深识天地设险之意”,但守江必须守淮,“韩世忠顿兵八万于山阳,如老罴当道,而淮东赖以安寝”。如果以恢复大业为重,“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即将都城自钱塘迁至建康[2](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从战略全局出发,陈亮特别重视荆襄,他认为荆襄“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是战略要地。在陈亮之前,李纲在南宋之初即以襄阳作为收复中原要地,而岳飞则以军事实践,以荆襄作为向关陇河洛进军之基地。从这一认识出发,陈亮提出“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的主张。尔后论述“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之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2](卷2《中兴论》)。沿着这两个战略方向收复大河以南地区!
(三)要想实现恢复大业,必须改变朝廷上“烂熟委靡”,无所作为的保守局面。陈亮指出,“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现今的儒生们,“烂熟委靡,诚可厌恶” [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三书》)。同他们“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安一隅之地则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则不足以立人道”[2](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因此,陈亮以愤激的语言称:“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庳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2](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改变这种保守的无所作为的局面,就不能“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2](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而是应当选拔一些讲究实际的有用人才,这就牵涉到许多制度变革的问题了。
(四)要实现恢复大业,必须对北宋以来的立国之制有所变更。陈亮指出,“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而无所因革变通。当前急需变动的,在于宋初以来为解决藩镇割据,使中央集权制日益走上极端,所谓“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2](卷1《上孝宗皇帝书第一书》)。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提出,便意味着有关官制、科举、财政、兵制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必须予以考虑而加以变更!
陈亮的这几次奏书,虽都石沉大海,而且,还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但是陈亮的奔走呼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才气纵横的爱国者的形象终于树立起来了。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亦即陈亮自衢州监狱出狱后的第二年,又参加了科举考试,并通过了礼部试的三场考试,名列第三,从而由此又参加廷试对策。宋光宗赵惇策问中的开头几句是:
朕以凉菲,承寿皇付讬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
由于宋光宗在泼悍的李皇后挟制之下,不朝重华,同其父宋孝宗关系极为紧张,朝臣们沸沸扬扬,议论光宗之未能克尽孝道,陈亮在这几句话下的对答是:
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
陈亮的这些话,极其露骨地为赵惇不朝重华宫的不孝予以开脱。宋光宗看到自然高兴,认为陈亮“善处人父子之间”,擢为第一名状元。宋孝宗听到陈亮被取为状元也极为高兴。但陈亮对策的这几句话也受到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指责,以为陈亮为攫取状元科名而不惜为光宗的不孝曲为回护,全祖望甚至有“抡魁晚节尤有惭德”[9]这样过头的错误评论。陈亮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宋光宗真正能够继承宋孝宗力图恢复的壮志,又何须乎每月四朝重华宫而向寿皇请安?陈亮这些话是从大局方面向宋光宗提出的要求,值得肯定[8]。
三、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有关朱熹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持续了两三个年头,是宋学演变过程中浙东事功派与二程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一场大辩论,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鹅湖之会”的辩争。
朱陈之间的这个大辩论并不是偶发有,而是两个学派在思想认识上矛盾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在道学急剧发展问题上,陈亮曾写有两段文字,其一是陈亮《送王仲德序》:
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虽夷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谀而不能同其说也。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为不足学矣。世之为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能麾其后生以自为高而本无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后欲尽天下之说一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2](卷24《送王仲德序》)
其二是陈亮的《送吴允成运干序》: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讬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2](卷24《送吴允成运干序》)
陈亮所说的二十年、三十年,指的是在宋高宗绍兴末(绍兴三十年左右)至宋孝宗乾道五、六年间。这两段文字一方面说明了道学在南宋初四十多年间的急剧发展,另一方面说明了陈亮对道学之空虚无用的憎恶。陈亮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对道学采取憎恶的态度,而且,如前面引证的,陈亮在淳熙五年(1178年)《上孝宗皇帝书》中一再提出道学不单单是空洞无物,而且朝廷上如不改变“道德性命”笼罩下的保守政治气氛,就无从议论恢复大业。陈亮把学风上的问题,以及由学风而蔓延成为政风的问题,视作为实现恢复大业的重大问题而提出并要加以解决,由此可见,陈亮对道学的鄙视到了什么程度。陈亮在为其弟子钱叔因所写的墓碣中径直地提出:
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菜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之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2](卷36《钱叔因墓碣铭》)
矛头所向,直指朱熹。这个墓碣是在朱陈论战以后写成的,时间虽晚,却能够进一步说明真像。由此可见,陈亮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同理学周旋到底的。唯其如此,朱熹出自维护道学的立场,虽然陈亮对其礼敬有加,不论生日与否都要馈赠礼品,朱熹却不但不遗余力地招架陈亮的咄咄进攻,而且,此后对陈亮一直贬斥,从来没有一句好评。即使是在陈亮身后,朱熹亦不肯写一篇墓志。朱陈日常生活往还还算得了什么,而朱陈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则是无法调和的。
直接引发朱陈之间那场大辩论的是朱熹给陈亮的一封复信。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陈亮第一次狱事结束,出狱后给朱熹一信,说明狱事原委。朱熹回信是以规劝面目出现的,信中除一句安慰话外,称:
然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虽朋友之贤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处,不敢进其逆耳之论。……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雍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高大而高明矣。[10](卷36《与陈同甫》)
此信不长,但从陈亮之为人到陈亮之思想,都涉及到了,这些当然是陈亮无法接受的。先师邓广铭在《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一文中指出,朱熹的“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一语,激起了陈亮的反驳,朱陈之间的“战幕从此揭开了”[8]。
“王霸义利”这一议题,既不是来自陈亮,也不是来自朱熹,而是来自二程。《二程集》上有两条关于这一议题的语录: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5](卷1《端伯传师说》)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2](卷11《河南程氏遗书·师训》)
另外还有一条与本议题甚为关切,也录于下面: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5](卷11《河南程氏遗书·师训》)
案二程哲学系统所讲的“道”亦即是“理”,因而,引文中的“以道治天下”或“顺理者也”,其义一也。又二程继承了先秦儒家孔孟正统派的义利观,把义利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三代之以道治天下,是公、是义;而秦汉以下则是以法或是以智力把持天下,也就是私(或私欲)、是利。朱陈“王霸义利之辨”就是从这一论题开展起来的。陈亮在给陈傅良的一封信中指出,自己之与朱熹辩论,在他自己则是为“天地日月雪冤”,而在朱熹则是为“二程主张门户”[2](卷29《与陈君举》)。这样看来,朱陈之间的这场论战是以浙东事功派的代表者陈亮同朱系正统派道学之间的论战,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朱陈之间的论辩是以书信形式展开的,从淳熙十一年(1184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往返信件重要的有十几封之多,均收集到先师邓广铭教授点校的《陈亮集》中。综合双方争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对“道”的认识上双方存在歧异。陈亮认为:
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2](卷9《勉强行道大有功》)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2](卷10《六经发题·诗》)
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2](卷10《六经发题·书》)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2](卷27《与应仲实》)
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2](卷10《语孟发题·论语》)
夫道,非出于行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夫喜、怒、哀、乐、爱、恶,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2](卷9《勉强行道大有功》)
根据陈亮的论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道和事(或物)是紧密结合着的;充满宇宙之间的是物,而日用之间无非是事,所以,与事物紧密结合的道,“无本末,无内外”,同样是无限的,或者说是横无际涯的。陈亮在对“道”的认识上,与程朱系道学将“道”(或理)看作为离开事物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的本体,显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即把“道”看作与事物紧密结合而不能独立存在,因而,在认识上是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而程朱系理学则是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
其次,陈亮对“道”的认识,不是像程朱系理学那样,认为“道”“为不传之妙物”,而是把它看作与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恶即六欲是分不开的,这六欲得其正即为“道”;而所谓的“行道”,则是审查六欲的始末,因而“道”“平施于日用之间”,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由于陈亮把“道”看作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所以,他对高谈“道德性命”的道学家之无补实际、之空洞无物是不满的,进行批判的,如上面所说。因之,陈亮之对“道”研究、探索,在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供实际应用。浙东事功派之重实际,显然继承了宋学建立以来自范仲淹到王安石这一优良的传统学风。
(二)陈亮为答复朱熹的责难而在《又甲辰秋书》的长信中,对程朱系统道学的王霸义利观提出了全面的批评。首先,陈亮认为这种义利观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指二程),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包括朱熹在内的二程派信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2](卷28《又甲辰秋书》)
从陈亮以上有关“道”的认识出发,“道”是亘古迄今存在并流行于万事万物之中的,陈亮则进一步把这种认识运用到历史上去,反对汉唐千五百年间“道”不存在这一看法,从而为汉唐辩护: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陈亮在批驳了“暗合说”的同时,公然申明汉唐同样是“以道治天下”,不过“其间有所渗漏”而已。这样,陈亮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同他的历史观结合起来了,把三代汉唐联系起来,形成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统一体。还不止此,陈亮不仅把历史看作为连续的统一体,而且认为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前代与后代有着因革继承性,他毫不含糊地说:
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
杂霸也是以道治天下也,而这个“道”是从前代的“王”延续、继承下来的。本着对哲学的和历史的这一认识,陈亮毫不客气地指出: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2](卷28《又甲辰秋书》)
陈亮的这封信,给朱夫子带来不少的难堪。儒家正统派历史观从孔夫子始,就带有形而上学色彩。孔夫子颂扬三代即已是古而薄今,但他还承认历史的因革继承关系,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还没有割断历史的联系。孔夫子以后的儒家正统派则是每况愈下,美化三代,丑诋汉唐,认为历史越来越倒退。从二程到朱熹一直都坚持这种倒退论,朱熹在答复陈亮来信中:“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这句话时说:
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10](卷36《答陈同甫》)
朱熹不仅把三代与秦汉割裂,坚持其历史倒退论,而且,在陈亮咄咄逼人的话锋下,不得不承认由于“儒者之学不传”,道在汉唐千五百年间不复存在。因此,陈亮在《钱叔因墓碣铭》中指出,汉唐千五百年间“道”这个“不传之妙物”,“儒家又何从得之,以尊其身而独立于天下?”[2](卷36《钱叔因墓碣铭》)看来,从二程到朱熹,把“道”攫为己有,是厚自标置的!
(三)王霸义利究竟如何分辨呢?归根结底,朱熹和陈亮还是从自己的认识论考察的。朱熹指出:
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老兄视汉高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正耶?出于邪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
朱熹在答陈亮信中不只一次地以这种认识方法辨析王霸义利,甚至还引司马光、二程以来经常引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用来论证方寸之地的认识作用。心的认识功能虽很重要,但从朱熹辨别王霸义利的方法来说,则是从动机——心的认识作用入手的。朱熹认为汉高帝唐太宗特别是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的,而只是“假仁借义”掩盖他的这种私欲,从而得到成功。单单从心念亦即从动机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这种方法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
在论战中,朱陈双方都有不周到处,亦都有“小辫子”被对方抓住。朱熹贬抑汉唐,把三代说得纯粹又纯粹,干净又干净,因此陈亮说:
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秘书亦何忍见二千年间世界涂涴、而光明宝藏独数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时而若合符节乎?[2](卷28《又乙巳秋书》)
但在王霸义利的辨析上,陈亮一直坚持自己的认识方法。在回答朱熹“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这一指责时,陈亮答复道:
其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2](卷28《又乙巳春书之二》)
在《又乙巳秋书》中,陈亮又说:
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犹是小事,而向来儒者所谓“只这些子殄灭不得”,秘书便以为好说话,无病痛乎!
陈亮之一再为汉唐辩护,称汉唐本领闳阔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朱熹在答陈亮甲辰书中说:“若以其(指汉唐之君)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得架漏牵补过了时日”[10](卷36《答陈同甫》)。陈亮对朱熹这句话进行反驳时,和盘托出了他推尊汉唐的实际意义:
(信中有孟子一段射者御者配合无间,才能多所获禽)亮非喜汉、唐获禽之多也,正欲论当时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纯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终归于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2](卷28《又乙巳春书之二》)
陈亮的这些话的意思指明,汉高祖、唐太宗本领宏大开廓的结果是,“终归于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而“禁暴戢乱、爱人利物”云云,当然为仁为义,符合于“道”,当然与三代之“王”没什么差别。由此可见,陈亮之推尊汉唐,是从汉高唐宗活动的实际效果而言的。
朱陈之间的论战涉及的问题不少。朱熹曾称陈亮“自处于法度之外”,让陈亮“迁善改过”,“以醇儒之道自律”。陈亮回答朱熹的是:他自己曾对吕伯恭(祖谦)说过,“亮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2](卷28《又甲辰秋书》),绝不以儒自居;特别是回答以“以醇儒之道自律”时称,“学者先学成人”,他自己绝不肯“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陈亮以咄咄逼人的话锋,确如陈傅良所说,“跳踉叫呼,拥戈直上”,在重大问题上寸步不让。朱夫子毫无办法,最后话锋一转,结束了这场辩论。
对朱陈王霸义利之辨,陈傅良是陈亮的好友,双方的论争都曾过目,因而,他在给陈亮的信中予以评论道: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工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
陈亮对陈傅良的信上说自己“跳踉叫呼,拥戈直上”,称朱熹“占得地步平正”云云,极为不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并将同朱熹论战的材料寄上,嘱其再作考虑。在第二封信上,陈傅良称陈亮“之论要是颠扑不破”,朱熹“何尝敢道老兄点当得错”,如果像朱熹那样认为“汉唐事业”,“并无分毫扶助正道,教谁肯伏?”“暗合两字,如何服人”陈傅良对这场论战的态度是很清楚的。
另一个浙东事功派人物叶适,在《龙川文集》的序言中对这场论战评论道:“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1](卷12《水心集·龙川集序》)
概括朱熹陈亮之间有关王霸义利之辨,从历史观来看,正统派儒家一直坚持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到二程、朱熹则更加绝对化,形成为历史倒退论;陈亮则坚持东汉王充以来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前进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从对王霸义利的认识方法看,朱熹从动机来考察以识别王霸义利,而陈亮则是从活动的实际效果来判断王霸义利。前者为动机论,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而后者则可称之为效果论,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朱陈王霸义利之辨,反映出来了陈亮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前引陈傅良曾对朱陈论辨的评论,其中对陈亮的评论是: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
陈傅良的这句话是对陈亮功利主义哲学最为准确的概括,犹之乎司马光反变法派所概括的“三不足说”,最为准确地概括了王安石思想的这一特点一样。陈亮的这一哲学思想是在对历史的探讨论辨中表现出来的,但它同陈亮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个人经历等方面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后者则是陈亮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根基。下面将侧重对这一问题以及这一哲学的社会倾向进行探索。
四、陈亮功利主义哲学形成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倾向
如果把“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一哲学观点,放在形成这种哲学观点的社会经济环境里,亦许更能够说明这种哲学思想只看效果、不看动机,只问目的、不问(择)手段这个特点。
在财富观上,陈亮有其独特的看法。岳珂《桯史》曾经有如下一则故事:
东阳陈同甫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尝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2](卷2)
而陈亮在《赠楼应元序》中所写的一段话,尤为值得重视:
夫一有一无,天之所为也。裒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圣人之惓惓于仁义云者,又从而疏其义,曰若何而为仁,若何而为义。非以空言动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独以为:“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为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虽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2](卷24《赠楼应元序》)
合观这两条材料,前则认为仁义礼智信是阻碍发家致富的“五贼”,后则认为仁义是劫取人财的“空言”,两则材料是贯通的,《桯史》所记是真实的。在财富观上陈亮具有这样的认识,与经年口诵仁义道德的儒生背道而驰,无怪乎一再受到朱熹的讥讽,称陈亮“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等等。
事实上,陈亮就是他所论述的这一财富观的实践者。前文说过,陈亮青年时家道衰落,祖父母、母亲三丧未葬,父亲系狱,生计至为困难,因而一度要下海经商。吕祖谦曾因此写信劝阻:
闻便欲为陶朱公调度,此固足少舒逸气,但田间虽曰伸缩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则与俗交涉,败人意处亦多,久当自知之。恃契爱之厚,不敢不尽诚也。[3](卷10《别集·与陈同甫》P284)
吕祖谦此信下文如何无足多论,但这时的陈亮则是投入到灌园治产的活动中,而且不十年间,到甲辰年(1184年)以前陈亮已经有了40亩园、200亩田的产业,京口的别业芦地尚不在内,成为一个中等力量较强的地主士大夫。陈亮的这200亩田,根据当时地价十贯一亩计算,费资二千贯以上。显而易见,单靠陈亮教小秀才的收入是置办不了的,只有经商和放高利货才有可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置办这些田地。陈亮比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家真诚得多,他对朱熹说:“亮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云云,并非空话,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在1184年第一次狱事之后,陈亮在向那些帮助他脱狱的官员们致谢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情况。在《谢陈同知启》中说:“岂求田问舍之是专,亦闭门造车之可验;一毫以上,通缓急于里闾(此指借贷事);终岁之间,仅饱暖其妻子”;在《谢梁侍郎启》中说:“豪于里闾,所得宁几!迫于妻子,无策自资”;在《谢郑侍郎启》中说:“身名俱沈,置而不论;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2](卷26)等等。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陈亮在治生活动中,他的子弟、奴仆参与了商业经营,而所谓“通缓急于里闾”也明显地透露了从事于放债活动。陈亮之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恢复了过去的田产,与经营商业、放债是分不开的。尽管陈亮还不时说自己贫穷,但在甲辰年(1184年)给朱熹信中,对他此前的治生,已沉浸在志满意得、自我陶醉的境况中了。
陈亮以其资生之业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发财致富的财利观,同时,也为他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一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作了注释。
陈亮不仅为他的资生之业而自我陶醉,对他周围的暴发户,同样是颂扬有加。在他写的何夫人的墓志中说:
始余闻东阳何君坚才善为家,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2](卷38《何夫人杜氏墓志铭》)
对东阳郭德麟的父亲郭彦明宣扬得尤为厉害:
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必有过人者。
像郭彦明一类的新兴经济势力——暴发户,既包括大商人,也包括向土地转化的商业资本,当然引起老牌经济势力(主要是地主及部分士大夫)的嫉忌,不仅啧啧烦言,而且造端生事,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陈亮为这类暴发户鸣不平,接着上文:
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求自达。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雠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纲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2](卷34《东阳郭德麟哀辞》)
“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云云,陈亮所发感慨竟如此之深,是来自他的切身感受。陈亮正是由于治生而引起邻里和所谓“士”的编造而入狱的,借着这个机会为那些不当权的乡闾之豪呼号。
从陈亮对乡闾之豪——暴发户的颂扬中,又可以看出:不问暴发户们的资产得来是否合法,只要是家资巨万,就受到赞扬。这样,只问目的,不问手段,陈亮为他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作了注释。
前面提到,陈亮对他的才具是极其自负的,自诩为“有推测一世”的英雄气概。陈亮对上述那些能够发家致富的人物,也称赞为“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其智必有过人者”等等。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其中的帝王将相,陈亮更是赞颂不已,如前引对汉高祖、唐太宗,不仅认为他们有本领,而且是有“大本领”的人。如在《酌古论·崔浩》中说:“古之所谓英豪之士者,必有过人之智。”[2](卷8《酌古论》)又在《酌古论序》中论文臣武将说,“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世之才;武非剑椠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2](卷5《酌古论序》)在陈亮心目中,本领、才智等等,以及由此而体现的斤量或者说实力,是实现功利主义目的的重要条件,因而受到格外重视。
概括看来,陈亮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一哲学思想,在其具体运用中,本领、才智,或者说实力,是极为重要的。还要注意的是,对实际、实践的重视。如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本领、才智放在实践才能检验出来,重实际、实践是陈亮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特点,而这个特点成为高谈道德性命的道学的对立面。是否可以这样说: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派及其哲学思想是南宋理学勃兴的一个反动?
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派的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还是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陈亮说:“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公然替商贾富民说话,而富民如上面所叙述的则包括暴发户在内,其中有一些是转化为土地势力的商业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