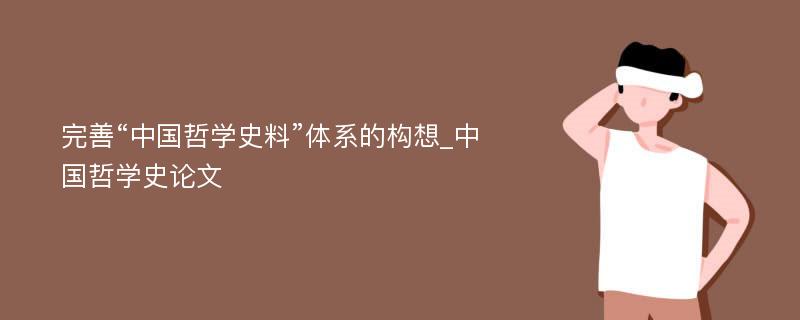
关于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史料论文,中国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现状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按最保守的说法,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编箸《别录》《七略》算起,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年间,不断发展,积累了大量著作和宝贵经验。至清代,朴学大兴,考据盛行,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密切关系的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训诂学等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从而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它年青,是因为把“史料”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毕竟为时不长,是直到中国近代才开始的。如果从近似的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的《治学方法与材料》等)算起,不过六七十年;如果从正式提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算起,则仅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值得令人兴奋的是,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来,史料学一科得到普遍重视。80年代初,出现过一个史料学研究的小高潮。在哲学、历史学领域,有一批史料学专著问世。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刘建国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高华、陈智超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同时,在高校教学中,史料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年,冯友兰先生的《初稿》原是为“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大概指哲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编写的;而今,这一课程则成为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普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参见李宗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文中称:当前“国内几乎所有招收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都给研究生开设史料学课程”)此举无疑是恰当的,有针对性的。勿庸讳言,我们的许多哲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对于史料学比较生疏,从而限制了眼界和能力,给今后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造成困难,这与新一代学子在学术上担负的继往开来的重任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为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但是,与对课程开设的普遍重视形成反差的是,对史料学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从80年代中期至今,长期没有史料学专著出版,报刊上有关史料学的论文也比较少见。可喜的是1998年5月出版了萧萐父先生的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该书“弁言”称,它是在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历届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见,它实际上讲的就是史料学,之所以名为“史料源流举要”,是因为“中国哲学文化史料之繁富,可谓浩瀚无涯;其源流考辨也异说纷纭,难以穷举”,因此只能“略举其要”。这固然是谦词,也是深知其中甘苦的经验之谈。该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在内容上既有所扩充,又有所提炼。但是,该书基本上仍属于史料介绍式著作,与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似还有距离。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发展,都呼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应该开出新生面。
首先,体系有待完善。迄今为止,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主要有四部著作,即冯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和萧著《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它们各有特点,冯著比较通畅,且有首创之功,张著比较简明,刘著比较详悉,萧著比较凝炼。前三书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基之作,对这一学科的确立有重要贡献。但也有所不足,主要是对有关史料学理论的阐述尚嫌薄弱。三书在详略取舍上虽有所不同,但在体例上倒基本一致,即都是以时代为序,用绝大部分篇幅逐人逐书地介绍史料。严格地说,这与“史料学”的名称不甚相符,倒与“史料介绍”大致近似。史料学既然是“学”,就应该以探讨史料的有关理论为主,而不能仅止于介绍史料。此点,上述三书其实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只是,它们更多的是将有关理论分别穿插在史料介绍当中,因而理论的阐述就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或不够充分。萧著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它认为,“本课不可能(按,似应作“不能”)单是介绍现成史料,而必须考索源流,辨析真伪,故其内容近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因此,该书特设“古史祛疑”、“朴学简介”两讲,使其理论色彩大为加强。但是,该书仍然以绝大部分篇幅按人物、学派或思潮介绍史料,“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贯注于清理和评介史料当中,没有超出冯、张、刘三著的基本模式。这是有待于改进和完善的。
其次,需要吸收有关新成果。80年代中期以来,专门的史料论著诚然比较缺乏,但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少,需要加以吸收。其中,尤以考古新发现所涉及的问题最为突出。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著名观点(参见李先生的同名著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通过对70年代以来的考古成果的具体分析论证,对从清代到近代在疑古思潮下产生的关于中国古籍的一些“定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如认为疑古思潮一方面有冲击封建独断和古史迷信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有怀疑过度、否定过多,难免造成古史研究的空白的消极作用,因此需要重新认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和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释文的发表,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短短一年间,已有数十篇文章见诸报刊,《中国哲学》第20期还出了“郭店楚墓竹简研究专辑”,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也在国内、国际开过多次。郭店楚简直接涉及到对《老子》与早期道家和《子思子》与早期儒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填补了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资料真空;有的学者认为,楚简中的道家著作,呈现了《老子》的原始面貌,可以去除关于老子的弥漫千古的迷雾;有的学者认为,郭店楚简影响所及,也许要部分地改写先秦思想史。尽管有关研究尚在进行之中,但对于如此重要的史料,“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显然不应置之不理。萧著在介绍文史考古知识方面比较重视,但所论及的内容中上古的居多,而与中哲史直接有关的考古重要发现,论述则嫌过于简略。
第三,许多新的哲学史料需要补充介绍。冯、张、刘三书在介绍有关著作的版本时,偏重于历史上的版本沿革和珍养本的评介,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许多史籍的原始版本和珍善本,今天已很难看到,常见易得的倒是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十几年来,中哲史籍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有古籍珍善本的影印本,重新点校的古籍单行本或丛书本,今人的译注本、选注本,其他相关著作如年谱、评传和研究论著也很多,这些,无疑是史料学应该加以介绍的。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介绍书籍以“常见易得”为原则,颇为后人称道。这一宗旨我们也应加以遵循。只有从当今的实际出发,为今天的读者着想,注重介绍和评介新版史籍,才能使“史料学”更好地起到“为学习者指示读书门径”的作用。萧著在这方面有了较大改进,值得称道和发扬。
上述三点,就是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定义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由于对其定义、对象和范围的理解所决定的。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顾名思义,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但实际上,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以致写出来的史料学著作,从内容到形式就有所不同。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附录中引述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给“史料学”下的定义,即“史料学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是历史辅助科目之一。”“史料学的任务,是把史料分类,予以批判地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综合研究整个的史料。”众所周知,从50年代初开始,我们曾经一边倒地全面学习苏联,在冯先生编写此书的60年代初期,虽然中苏两党两国在政治关系上恶化了,但在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苏联的一些理论仍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圭臬。苏联大百科全书对于“史料学”所下的这一番界说,自然也为中国学人所遵循。冯先生的这部书乃至其后的史料学著作,实际上都受到它的巨大影响。
可贵的是,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初稿》中对“史料学”提出了一个简明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尽管冯先生在书中没有把这个定义贯彻到底,没能全面地讲史料的方法论,而是仅仅写了一章“论目录”,其余各章都是关于具体史料的介绍,但这一定义的提出仍然是了不起的真知卓见,因为它清晰地指明了史料学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冯著还有一个特点是选了51篇有关史料学的原始资料作为附录(长达92页)。这些资料大部分是讲史料的方法论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文的不足。而且,它们有些是不易看到的;有的即使不难得到,将它们汇编在一起,也省去了读省的翻检之劳。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编排方法。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没给史料学下定义,只提到其“任务”,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作为真实史料的价值。”根据这一界定,张著便主要是具体介绍史料,而将方法贯注于评介当中。张著比冯著晚出20年,广泛吸收了其间关于考古新发现(如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学术成果,因此,观点较新、考订更加翔实。相对而言,该书先秦两汉部分内容比较丰富,魏晋以后略嫌简略。张著也收录了几篇附录,与正文也有相得益彰之效。
比张著晚一年出版的刘建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分上下两册,从先秦写到现代,共20章,容量较前两书大为扩充。该书对史料学下了较长的定义:“史料学是阐明史料的来源,辨别史料的真伪,评判史料的价值,为史学研究提供客观依据的一门科学。”进而推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阐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来源,辨别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真伪,评判中国哲学史史料的价值,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客观依据的一门科学。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如何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来源,怎样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分类,以及学会搜集史料的方式方法,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打下基础。”就内容来说,“基本包括:到何处找史料,怎样才能找全史料,史料利用的价值,以及积累史料的方法诸方面”。从刘先生的这一界定看,他也是主张史料学应该讲关于史料的种种理论和方法的,但遗憾的是,在刘著中只有前两章(共34页)属于此类内容,而其他篇幅(共18章,934页)都是逐人逐书介绍史料,未能将自己所下的定义贯彻到底。
比张著、刘著略为晚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辞条(石峻先生撰),首段便是给该条下的定义:“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使用的科学。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这里,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但既然说史料学是关于史料诸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那也就是史料方法论的意思,与冯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此点从其后的文字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该辞条在定义之后,分为对象与范围、任务与方法、总结与展望、参考书目四节分别论述。其“任务与方法”一节说:“发掘隐没史料、辑佚、鉴别真伪善否、校勘、训诂等,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主要任务。”然后分发掘、辑佚、鉴别、校勘、训诂五个方面分别作了论述。显然,石峻先生是把这些理论视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应该加以阐述的内容,在提法上更加清晰明确了。
对于什么是史料学,还有一种提法值得注意,即把“史料学”分为“史料学通论”和“具体的史料学”两类(见陈高华、陈智超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该书“前言”中说:“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史料学可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的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还说,他们编著的这本书仍属于后一类,即“具体的史料学”。
陈高华等提出的这一理论颇有可取之处,一方面,它对已出版的几部史料介绍型的史料学著作的价值和合理性给予了肯定;另一方面,又对理论型的“史料学通论”的出现作了呼唤。它虽然是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角度立论的,但对于解决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体系构想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陈高华等关于“史料学通论”的呼唤在历史学界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反响,倒是在中国哲学史界有人著文对此作出了回应,这就是洪波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史料学刍议》(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该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史料学的历史发展,评价了冯友兰、张岱年、刘建国三先生的史料学著作的得与失,进而,该文总括道:“总之,这些著作深受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欢迎,但尚感遗憾的是,基本上还是有关哲学史论著提要的汇集,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需要。”进而认为,史料学应该“主要解决史料研究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要培养同学了解史料的内容和价值,以及搜集史料、审订史料、运用史料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使同学认识祖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接着作者还提出了对《史料学概论》课应讲授内容的设想,即“应讲授与搜集史料、审订史料、运用史料有关的问题,如史料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相关知识的联系,史料学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关系,与图书目录、类书丛书的关系,与正史、野史、笔记、杂艺的关系,与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辑佚汇编的关系,以及有关工具书的介绍、重要史料学著作的评价等。”这一看法,除细目的设定,内容的取舍和次序的安排等细节尚有可斟酌之处以外,总体上是可取的,与陈高华等提出的“史料学通论”的看法大体上不谋而合。
近年出版的萧萐父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没有对史料学的定义进行论述,但该书说:“其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历代哲学资料及有关史料为对象,序列文献,综述目录,介绍研究成果,考辨学术源流。”可知它讲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具体的史料学”。其“朴学简介”一讲,偏重在知识介绍,方法涉及较少。这与上述关于中哲史史料学体系的设想仍有距离。
三、关于中哲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
通过上面讨论,可以得出下面的认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应该担负两个任务,一是阐述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方法论,一是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指示读书门径。前一个任务由“史料学通论”解决,后一个任务由“具体的史料学”即“史料举要”加以解决。这样,与其说史料学著作分为“史料学通论”和“具体的史料学”并行的两类,不如说,一部完整的史料学应该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史料举要两部分更恰当。
史料学应该讲关于史料的理论(即通论),此点,冯、张、刘、萧四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其实也都有所体现,冯著的前两章(共20页)、张著的引言(共4页)、刘著的前两章(共34页),萧著的前三章(60页),都带有通论性质,只是篇幅未免太短,没有达到通论性史料学应有的规模。
张岱年先生另外有一部著作,恰好包含了史料学通论的内容,这就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与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构思于同一时期,二书都是在给硕士研究生授课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因此两书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今天看来,该书虽然没有使用“史料学”之名,但其中一部分内容,讲的正是关于“史料学”的通论。这就是该书的七八两章:“整理史料的方法”(上下),共讲了五个问题:(一)史料的调查与鉴别;(二)校勘;(三)训诂;(四)史事的考证;(五)史料的诠次。这些内容,讲的都是关于中哲史史料的方法论问题。该书把这些问题归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的这两章,视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固然言之成理,因为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研究当然可以说是中哲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哲学史”与“哲学史史料”毕竟有区别,关于哲学史的方法论与关于哲学史史料的方法论讲的也不是同一个问题。“史”包含“史料”,“史学”要利用和分析“史料”,但“史”与“史料”毕竟不能等同。因此,我们觉得,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的这两章,视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倒是更合适些,至少是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提供了雏型。
前引洪波《刍议》一文关于“《史料学概论》课应讲授内容的设想”,也很有参考价值。只是文中所列各项略嫌琐细,有的内容只须在有关章节中作些交代就可以,不宜做为一章展开论述。有些问题(如史料学与相关资料、相关知识的联系,史料学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关系,与图书目录、类书丛书的关系,与正史、野史、笔记、杂艺的关系)是“史料学”编著者应该加以仔细考虑的问题,但将这些内容写入书中,似不合适,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关于“中哲史史料”的方法论问题。不然,史料学的内容就未免过于庞杂了。
综上所述,谨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设上下两编,上编讲史料学通论,下编讲史料举要。另外,酌情设附录。
上编通论部分共设八章。第一章为“绪论”,讨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定义和任务、史料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学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意义和方法等。第二章至第七章是主干部分,分别论述中哲史史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校勘、解释、运用诸问题的意义、历史发展、主要成绩和代表著作及其研究方法等。其中,涉及到中国古典学术中的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校勘学、版本学、训诂学等许多学科。这些学科,每一门都有自己的体系,企图把这些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入史料学中,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而应择其精要,做概括介绍,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哲学资料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具体分析。最后一章介绍与中国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工具书的主要类型、代表著作及其编排和检索方法。以上各章都应尽可能安排一些练习,以利于不单获得知识,更应掌握方法。
下编“中国哲学史史料举要”,设若干章。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各流派、各思想家的主要哲学著作。如果说,上编以开扩见闻、掌握方法为目的,那么,下编则以指示读书门径、分别版本优劣为目的。因此,在内容取舍和详略安排上应贯彻下述几点:
1.力求精当。人物、著作的选择,应避免烦琐。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自许“要言不繁”(第四册“自序”),“提纲挈领,提要勾玄”(第五册“自序”),诚非“自吹自擂”。皇皇六册巨著,涉及的人物并不太多,堪称精炼。我们讲史料举要,可大体以《新编》所收范围为限。
2.不求划一。人物、著作的介绍,大致包含生平史料、流传、真伪、版本等方面的内容,但不求划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般不必讲“史料分布”,以防止以偏概全,对读者造成束缚和误导。
3.切于实用。版本介绍以习用常见易得为主。古旧版本,着重介绍有代表性的,有影印本的,对流传过程不过多介绍,以省篇幅。对最新版本则尽量介绍,以利易于寻求,切于实用。
关于附录。附录选得好,可以与正文互相补充印证,有相得益彰之效。而且,等于为读者提供了学习史料学最必需的参考资料,省去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其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只要篇幅允许,适当设附录十分必要。但是,由于版面、书价等原因,又不能收得太多。冯著、张著在这方面已提供了先例,足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