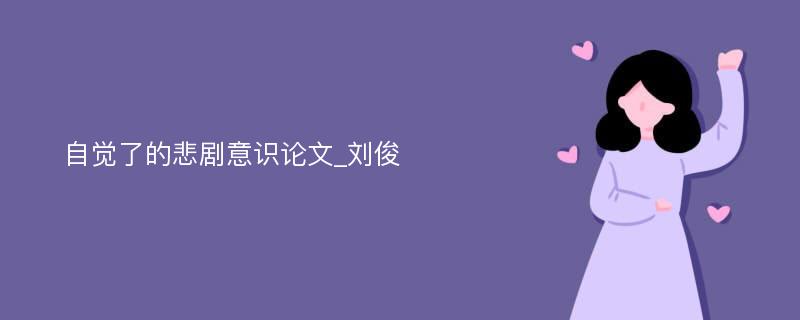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G68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0257-2826(2019)11-195-02
悲剧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总体性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它是在人类对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中和对自我的人生命运的根本思考中产生。悲剧意识作为西方悲剧美学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学就没有体现,恰恰相反中国文学是最富于悲剧性的。中国的文学一向有“以悲为美”的传统。从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古代神话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古人对壮美的悲剧性的审美追求。于是有屈原作《离骚》、司马迁著《史记》等富于悲剧色彩的伟大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正是以“以悲为美”作为审美的主流,这是悲剧意识觉醒的表现,它伴随着“人的觉醒”而觉醒。而这些特征在阮籍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就体现了“以悲为美”审美追求。而他的这种追求和《咏怀诗》独特的悲剧感绝非偶然,作为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诗人,阮籍以自己对社会现实、自我存在、人生价值等问题独特的思考和体察,即兴咏怀塑造了自我的悲剧形象。因其身处魏晋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咏怀诗意旨飘忽隐晦,李善在《文选注》中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给后人留下永恒的嗟叹。
咏怀诗是阮籍心灵的真实写照,组诗在情感和意旨上反复凌乱但风格充满了浓浓的悲情气氛表现当时充满悲观、虚无、危机、焦虑、绝望、荒诞的现实。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题:
一、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穷途之哭”的无奈
《晋书》记载“籍本有济世志”,阮氏是曹魏新兴得士族,其父阮瑜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所器重,其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士人的人生追求,阮籍从小就攻读儒家经典“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诗其十五)来修善德行,“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磨砺才干(咏怀诗其三十一)表明他建功立业的渴望。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以后会向更高层次追求。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终极需要,是表现个体在社会中存在的具体意义,是低层次需要的共同指向。这和儒家思想推崇“修身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是十分契合。尽管动荡社会导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也随之动荡,取而代之的是士族门阀制度,但功业、学问仍是作为一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矢量。尽管身处乱世,建功立业的梦想往往超出了人理想,但是阮籍还是一度把“取义成仁”作为自我价值最大实现的矢量。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身躯?放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其三十九)
这首诗全篇流动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正气,大有“建安风骨”的遗风,通过对“壮士”的重忠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献身精神的赞美,表达的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奋斗目标。诗中阮籍充分肯定了“壮士”、“英杰”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是对个人力量和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这时候个体的力量并不是被消融在集体力量之中,而是从抽象的“仁”中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魏晋时代“人的觉醒”特征。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表现个体生命的忧患与孤独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其一)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四亲友,晤言用自写。(其十七)
“孤鸿”的哀号、“翔鸟”的悲鸣与“明月、清风”形成了一组悖论式的意象组合表现作者满怀的“忧思”和孤独。这里“孤鸿”、 “翔鸟”又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可以是作者用以表达自己的孤独,也可象征不安的民生,作者巧妙的借助它们的视野隐晦的表露自己的心迹。在强烈的悲剧意识中,充满生气的如“桃李花”和“太阳”也被赋予衰亡的悲剧意义:
三、与黑暗现实的抗争与迷惘
虽然阮籍以种种假象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政治态度,但在精神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与黑暗现实的抗争。他以隐晦的笔法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和险恶的世道人心进行揭露“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外厉贞素谈,湖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阮籍在更多的诗作中表达自己挣脱黑暗现实羁绊、追求自由人生的强烈愿望:“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为冲青天,旷世不再鸣。”“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除了这些托物的诗作,他还借以梦幻般的仙游表达同样的愿望“微冠切浮云,长剑除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无论是托物还是假借仙游,对阮籍来说都只能是一种精神寄托,当他从虚无的精神世界回到黑暗现实不得不妥协:“莺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宁与燕雀游,不与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途将安归?”他并没有和黑暗现实作彻底抗争的打算,也没有对世俗权贵完全臣服与妥协,而是选择了政治性的退隐来换取生存的安宁,但这样的安宁也是不容易实现的。
四、“人的觉醒”带来悲剧意识的觉醒
阮籍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在这里袁行霈、罗宗强两位先生对文学创作主体的自觉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文学创作中创作者应该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作家完全是被动的,或者成为自然的奴隶,或者他的活动完全属于别人,那么,他就是‘自身的丧失’,就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主体。”对《咏怀诗》解读与鉴赏应该充分尊重作者的主动性,应该把“悲情美”作为阮籍自觉追求的一种行为。汉末魏晋是历史上一个充满战争、动乱和痛苦的时代,它直接造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社会思想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士人便把自己的思考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加上在这样的时代缝隙中往往容易孕育新的哲学新的思想,而魏晋恰恰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再次繁荣的时期。它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但在更深层次却是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所说的“人的觉醒”。“人的觉醒”集中体现在: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切思考中;对个人力量和个人价值的强烈呼唤中和对个性解放、个人意志宣泄的渴望中。这些在阮籍和他同时代人的诗文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而言之,阮籍在悲剧意识上有比朋辈更高的自觉,但始终没有上升为悲剧精神,没有感受到西方悲剧中倡导的震撼和力量。原因在于阮籍的并没有理性的看待社会的变迁,更没有因为这样的变迁形成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为之永不妥协的反抗与抗争。阮籍在“悲情美”的追求中也是很自觉的,但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传统下,悲情被冲淡了朝着“中和之美”方向律动。这是中国人在面对人生悲剧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乐观态度的独特方式。阮籍开创了抒情组诗的先河,继他之后唐朝陈子昂作“感遇”三十八首、李太白有五十九首“古风”诗,还有张九龄的十二首“感遇”诗,虽不以“咏怀”为题,但即兴发咏来书写内心的感慨、哀伤一定程度上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论文作者:刘俊
论文发表刊物:《教学与研究》2019年1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20
标签:悲剧论文; 阮籍论文; 自己的论文; 自觉论文; 社会论文; 意识论文; 现实论文; 《教学与研究》2019年1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