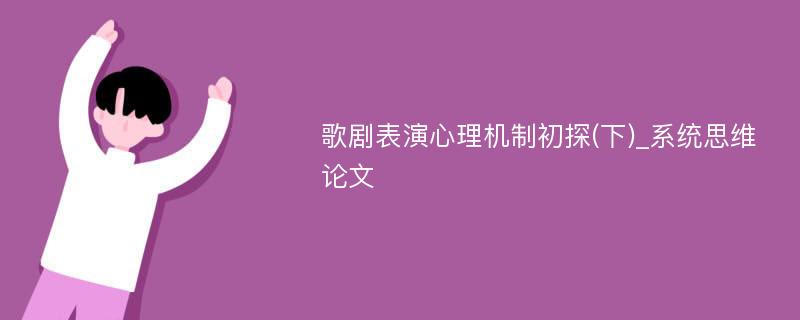
戏曲表演心理机制初探(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机制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动作系统化机制
动作,属于运动器官的功能,而动作系统化,则属于脑神经的功能亦即心理功能了。动作系统化机制,也是我们戏曲演员的一种重要心理机制,是它,维系着演员在舞台上形体动作准确而有序的运行。
动作系统化的含义,是指我们的形体动作,经过严格训练,做成稳定的模式,牢固地存留在我们的脑神经之中。这些动作,一旦需用,呼之即出。
动作系统化的基础是记忆,记忆的生理基础是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活动。当我们感知外界事物、身体状况或内心情态的时候,脑神经的相应部位便会产生兴奋而建立起临时的联系。过程结束后,这种联系会在脑神经中留下“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记忆。记忆有长有短,分为瞬间记忆(以秒、分计)、短时记忆(以时、日计)和长时记忆(以月、年计)。记忆是无意识的,容易消失,如果想要获得较长时间的记忆,无论是知识和技能,都须经过训练,之后还须不断地进行复习。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体态动态,都已不是生活中的体态动态,而是舞姿舞态。舞姿舞态必须遵循严格的规范和要领,才能达到雕塑美的要求,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运动时候的大小身段套数也要呈现出流动的美感。正如盖叫天先生说的:“一戳一站,一动一转,一走一看,一扭一翻,一抬一闪,一坐一观,都要顾到四面八方,要叫人人爱看。……站要站得好看,动要动得好看。”(《粉墨春秋》第67页)这里随意举两个例子,比如指一下天或指一下地,这在生活动作来说是极简单的,举手伸指向上或向下一指即可。但在戏曲因是舞姿舞态,做来就十分复杂。以旦角为例,指天是这样指的:
左手叉腰,右指从鼻尖,由下指上,眼看右指。左脚前,右脚后,仰望天空。(眼一定不要离开手指去看天)
——阳友鹤《川剧旦角表演艺术》第24页
再如指地,是这样的:
右转,双手兰花形手心向里顺花,由左鬓指向右地面,同时左脚后支,眼随指去。
——同上书第24页
由于属于舞姿舞态,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右手指和右胳膊动,连左手左胳膊双腿身躯头项统统都配合着动,用整个的身姿塑成一个优美的身段造型。
为了使自己造就戏曲中动和静的身体塑型,每个戏曲演员都须经受四年以上的正规的“系统的形体训练,从踢腿、下腰、园场、拿顶、云手、提甲,一招一式,到毯子功、把子功,程式套路,勤学苦练,那真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成之后,仍然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天天坚持练基本功,免得“百日练得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艰苦训练和天天练使戏曲演员的形体和动作获得了动作系统化的成果。而动作系统化的重要特征在于动作的自动化。即便再复杂的动作系列,一经系统化和自动化,就会铸成一条组合有序的锁链,环环紧扣,前后连贯,只要提起头,就会带来尾。你只消发出第一个指令,一整套的动作就会自动地完成。其实,人们的生活动作,多是系统化自动化的,行动坐卧自幼习得早成为本能自不必说,就是技术性较强的,比如骑自行车,只要学习完成,那动作也就形成为系统化自动化的了。会骑车的人无论上下车或车的行进当中,已勿须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车的平衡的操作上,他可以一面驾驶一面与人谈话甚至点火抽烟。斯坦尼曾经说到蜈蚣有21对足,在它行走的时候,各对足都会自然地此起彼落地向前活动,它不用先指挥某足怎么动,再指挥某足怎么动。这就是动作系统化的作用。
对曲动作的系统化无论对文戏对武戏,对单元动作对组合动作,都同样重要。而对武戏和组合动作(套路)来说,更其要紧。翻扑腾挪打把子,讲究紧凑火炽,长短筋斗,讲究飘帅,一旦启动,再想是动胳膊还是动腿,根本就来不及了。打把子不管是对打是群档,上步、撤步、抬腿、跨腿、转身、回旋,手脚胸腰头身,那一处都要动到地方上,动到时候上,尺寸长了短了,时候早了晚了,配合不到,不但不好看,还会出事故。这一切全靠系统化。
动作的系统化自动化使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获得了解放,他得到了自由,可以匀出最大的精力去进行人物形象的创造。如果一个戏曲演员没有达到动作的自动化,他在舞台上势必要时时留意自己的声音、表情和动作。但是人的身体器官偏偏有一种最糟糕的习性,你越留心它怕它出问题,它越不自在尽出事,又僵又板,指挥失灵,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斯坦尼在谈到前辈名演员时说:“他们表演角色最好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种他们共同具备的东西……一切伟大天才所共同具备的这一种东西是什么呢?那种共同点是我最容易看出的,那就是他们的生理自在,丝毫没有紧张。他们的身体对于他们意志的内在要求唯命是从。”(《我的艺术生活》第412页)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动作系统化心理机制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根好拐杖。
四、灵感思维机制
戏曲演员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灵感思维的运行机制。
当今世界文化的大发展,呈现出思维模式的多元化,除了我们熟知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外,更有模糊思维、逆向思维、多侧面思维、控制论思维、系统论思维等等。而与我们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关系密切的是灵感思维。
灵感思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思维模式。以往有人把它看做心理状态。其实,它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灵感思维也称直觉思维。德国数学家施特克洛夫这样描述灵感思维的过程,他说:“过程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形式逻辑在这里一点也不参与。真理不是通过有目的的推理,而是凭着我们称做直觉的感觉得到的。直觉用现成的判断,不带任何论证的形式进入意识。”爱因斯坦谈他自己的思维过程时,说:“在我的思维机构中,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地’再生和组合。……这些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种必然的,直觉的(心理的)联系。”根据今天的研究水平,人们尚未能对灵感思维下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试把灵感思维和逻辑思维
作一个简略的比较:
逻辑思维灵感思维
逻辑性 非逻辑性
可解析性不可解析性
循序渐进性 跳跃性
理智的 情感的
清醒的 迷狂的
推理的 直觉的
受意志支配的不受意志支配的
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
模仿性的创造性的
有我有物的 忘我忘物的
意识活动下意识活动
这两种思维模式对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我国以往就有不少的成语说到它们。我们说逻辑思维的认识程序是:“经一事长一智”、“失败为成功之母”、“熟能生巧”。说灵感思维则是“举一反三”、“急中生智”、“茅塞顿开”、“触类旁通”、“豁然贯通”。司马光打缸救小朋友的故事是我国妇孺皆知的灵感思维的例子。
灵感来临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曾有很多科学家有这种经历,我这里举两位艺术家作例。德国大作家歌德谈他作诗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然袭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像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在这种梦游状态中,我往往面前斜放着一张稿纸而没有注意到,等我注意到时,上面已写满了字,没有空处,可以再写什么了。”(《歌德谈话录》第207页)灵感像梦境的冲动,不知是怎么的就完成了诗的创作。另一个例子是郭沫若写作《地球,我的母亲》的情形。这诗是他早期的名篇。他回忆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放完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索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疯狂,然而在当时却委实是感受着迫切。在那样的状态下受着诗的推荡、鼓舞,终于见到了它的完成,便连忙跑回寓所把她来写在纸上。……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边牙齿都在打战。”待他完成了诗篇,“自已觉得好像是新生了一样”。对这样的灵感爆发的情景,他自己也戏称是“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这种创造境界确实可以达到迷狂的地步。古希腊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必须迷狂。他说:“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页)柏拉图也持同样看法,他说:“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文艺对话集》第8页)
处在这种灵感境界的时候,艺术家的创造力达到顶点,联想丰富,思维活跃,形象活龙活现,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致对外界的知觉迟钝,物我交融,物我两忘,我化为物,物化为我,如梦如醒,如醉如痴,真像庄子说的,不知是我庄周做梦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化为了我庄周。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好境界。但是灵感之来又何其不易。如果说别的艺术家已经不可能常常受到灵感的青睐的话,那么我们戏曲演员就更少有这种幸运了。我们工作的性质中,有一条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也是最为难的,就是工作时间的预约性。演出的时间、地点、剧目都是早计划好的,时间一到就实行。这使得我们不能像其他艺术家那样从容。但时间的预约性,给我们约束了观众,观众的观赏和反馈恰又是我们戏曲演员艺术创造的必不可少的和比别人优越的条件。有副戏曲对联说: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
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徐兰沅操琴生活》第5页
这种忘我失我像角色不像我的状态,不就是戏曲演员的灵感状态吗?
戏曲演员在表演中进入灵感境界的时候,常常显示出两个特征,一是开启了真情,二是激发出即兴表演。
灵感开启真情。人说京剧老前辈谭鑫培先生演《洪羊洞》最拿手也最动情。一次演至《病房》一场,八贤王问杨延昭:“御妹丈此病因何而起?”别人的演法是接口叹息答话,谭老先生既不叹息也不张口,却把一双眼睛直勾勾凄凄惶惶望着八贤王足有七八秒钟,才缓而又缓地长叹出一口气。等到他念“千岁爷”三个字的时候,眼眶都红了。这真切的情意不但抓住了前排的观众,就连同台的八贤王也看傻了。(苏雪安:《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梅兰芳先生说他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最后舞剑之前,虞姬慢步后退,霸王则步步紧逼了相送,双目直注虞姬。真像过电一样,每演到此处,我眼睛里是有泪水的。(《黄裳论剧杂文》第538页)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记得有一次我演出《庵堂认母》的时候,真情的涌现,事后想来觉得很意外也很复杂。戏中我扮演志贞。戏的最后一段,志贞被徐元宰认出是自己的母亲,哀求要与她母子相认,志贞一颗母亲的心也切盼要认下亲生儿子,可是又跳不出佛门的屏障,两难之间心乱如麻,于是她奔去禅房。元宰也追下。然后志贞奔上,推开门。此时的表演是,往前一看申郎的挂像,身子往后一闪,乐器捏住,静场,之后扑到像上大哭,再起滚白。但是,这次鼓师敲错了。该把乐器捏住却忘了捏住,反而紧接着就起滚白。我发现他敲错,心里急坏。这瞬间,志贞也心乱如麻,我也心乱如麻,两个心乱如麻加在了一起,急得我直跺脚。鼻孔一酸,泪花在眼眶里转。观众受到感动。这个跺脚的动作,是临时突然出现的,预先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演员的真情的火花,只有他同角色融合起来的瞬间,才会不自觉地止不住爆发出来。
其次,灵感激发出即兴表演。郑法祥先生的悟空戏可称一家,他回忆说:
有一次演《闹天宫》,“大战”之后,悟空耍棒花下场时,我的思想浸透了战胜十万天将的自豪感,真是心花怒放,手里的金箍棒也伴随着这种情绪添了“花活”,与往日耍的大不相同。第二天我的徒弟牛富贵对我说:“老师,昨天《闹天宫》你那趟棒耍得真好,浑身上下全是棒,孙大圣的神威全发出来了。”他要跟我学可我再也想不起那天是怎么耍的。
——《谈悟空戏表演艺术》第78页
可以看出,即兴表演,是演员真实地进入了角色,忘记或几乎忘记在演戏,真情流露的时候自然地生发出来的。记得1980年,我们剧团演出新创古装戏《葫芦案》,我在剧中扮演一位新媳妇。新婚第二天清晨她由新房中出来。我轻开门扇步出房门,只觉得阳光耀眼,稍一定睛,发现院子中已有几位邻居,且正在向我观看,我顿觉十分害羞,不由得忙把头轻轻别转往侧面一躲,左手也随之掩到脸颊边上。过后几位同事来谬奖我,说“神啦”。这里的开门、出房,都是排练好的,但那一羞一躲一掩,不仅没有排过,而且我事先也没有想过。不知怎么一来,自然就出来了羞的感情,自然就来了那组身段。感情不多不少,动作也不多不少。这显然不是理智在指挥,而是下意识在运行,也是灵感思维在运行。钱宝森先生说:“三形,六劲,心意八,无意者十。”灵感思维帮助我们戏曲演员进入这个“无意”的境界,进入斯坦尼说的“忘记了自己是在角色中,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我所扮演的人物”的境界。
灵感思维对我们戏曲演员的艺术创造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如何获得它呢?说来遗憾,尽管有声有色地描绘灵感情景的文字很多,但是指出灵感的来路的却又太少。作为戏曲演员,我们不能守株待兔,翘首坐等灵感的光临,只有勤奋地劳作。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说:灵感不拜访懒汉。我想,勤奋,它该是灵感最好的苗圃和温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