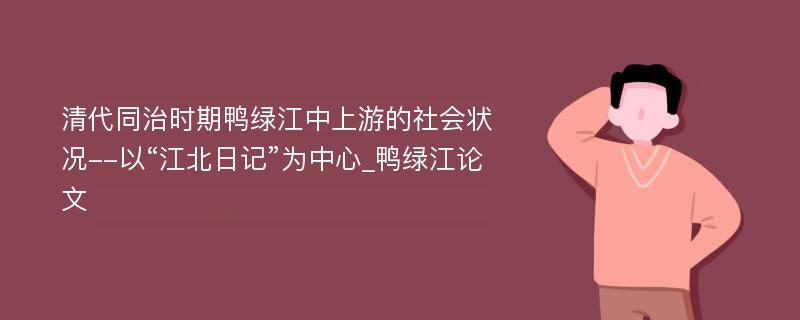
清朝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状况——以《江北日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鸭绿江论文,同治论文,清朝论文,江北论文,年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鲜高宗九年),朝鲜平安道厚昌郡郡守赵玮显派遣崔宗范(厚昌首乡、寨将)、金泰兴(防将、及第出身)、林硕根(译官)等三位谍报人员,秘密越境潜入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进行侦探,随后留下了《江北日记》。①日记的执笔人为崔宗范,调查时间是五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一日的40天期间,侦探地域是当时朝鲜平安北道厚昌郡、慈城郡对面的中国鸭绿江中上游地区,大致范围包括现在临江市及其周边的集安、通化、桓仁、长白、抚松、靖宇的部分地区,有600公里路程。本文拟以《江北日记》为中心,结合中、朝两国相关文献资料,探讨清朝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清中叶以后鸭绿江封禁区流民社会的形成
清朝对鸭绿江流域长期实行封禁政策。清初,借鉴明朝初年在鸭绿江和连山关之间留数百里瓯脱地带隔绝中外的做法,在盛京柳条边和鸭绿江之间的中朝边界地区留出缓冲地带,严禁中、朝两国人民进入此地伐木、行猎、采参、垦种。“凤凰城边栅北自石人子与叆阳接界,南至海滨,亘百六十里有奇,出栅至与朝鲜分界之中江,北远而南近,其地皆弃同瓯脱者,盖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设官置汛立法綦严。”②清政府主要通过柳条边及边门、内外卡伦,对鸭绿江流域实施封禁政策。到乾隆年间,为了加强鸭绿江流域的防守,在增设卡伦的同时实行统巡制度,按四季派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巡边搜索犯禁入居者。到19世纪,随着闯入鸭绿江封禁区的流民越来越多,鸭绿江防务进一步加强,实行中、朝两国“会哨制”,“统巡官出边,应令先知照朝鲜地方官会哨,如无搭盖窝棚处所,该国地方官具文,由统巡官申报将军以备稽核”。③如发现垦荒居住者,不论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田舍平毁,人员驱逐。
朝鲜方面,为防止边民偷越边境制造事端、引起外交纠纷,也采取严格的边禁措施,防范犯越事件的发生。早在1672年朝鲜即规定:“西北边犯越人随从之类,自今拿致本营严刑三次,再犯者严刑五次,仍置本镇,三犯者枭示。”④1685年,朝鲜政府加强北方四郡、六镇的警戒,在平安、咸镜两道江岸陈兵严守,断禁边民越境。第二年正月特制定《南北参商沿边犯禁断事目》,凡潜出国界私人中国者,无论事由,不分首从,一概境上枭首示众。⑤1687年,又制定《边民采参犯禁之律》,决定对渎职的地方官员以及“群聚犯采者”,诛其首倡,协从及一二人犯者,宜用次律,“上从其议”。⑥同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对“发告潜越之人者,论以重赏,知情不告者及守令、边将之故为掩饰置者,绳以重律,以防日后无穷之弊”。⑦
但清朝和朝鲜的所有防范措施,都未能阻止中国关内流民和朝鲜北部边民犯禁潜入鸭绿江封禁区谋生的潮流。从清朝方面看,自18世纪中叶以后,关内流民相继潜入鸭绿江沿岸封禁地区采猎。随着流民增加,他们便趁卡伦官兵入冬撤走之机,进入浑江流域、鸭绿江中下游盗伐木材。嘉道之际,关内流民不断冲破封禁徙居东北,其中部分流民进入鸭绿江封禁区,搭盖窝棚,盗伐树木,开荒种地,采挖矿场。但一旦被八旗官兵发现,则无条件地被驱逐出鸭绿江流域。到咸丰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局势,盛京地区八旗兵被大量抽调入关作战,无暇维持鸭绿江流域的封禁。在这种形势下,流民不仅大量涌入鸭绿江流域,并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咸丰间中原多故,封禁隐弛。东沟、通沟诸处,私垦之豪,据为己地,敛财编户,自成风气。”⑧到同治年间,“自东边门外至浑江,东西宽百余里至二三百里不等,南北斜长约一千余里,多有垦田、建房、栽参、伐木等事;自浑江至叆江,东西宽数十里至三四百里不等,南北斜长约二千余里,其间各项营生与前略同,惟人皆流徙,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立会、团练、通传、转牌”。⑨说明鸭绿江流域的流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朝鲜方面看,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为当木筏水手而越境潜入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发现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江流域土地肥沃,易于垦种,便就地转而务农。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朝鲜北部边民犯越国境,移居鸭绿江北岸私垦荒地,朝鲜人越境由过去以采参、捕貂、伐木为主变为垦荒居住为主。尤其是1860年到1869年期间,朝鲜北部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原本因残酷的封建统治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阶层,被迫背井离乡,铤而走险,冲破禁令,私编木排,载运家眷,犯越鸭绿江、图们江,潜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谋生之路。一些人携老扶幼进入中国今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筑室定居,逐渐形成流民社会。
清朝后期,随着统巡制度的松弛,为过去“令紧暂退,令弛复返”的越境朝鲜人垦居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从前统巡之行,例皆索钱,办给若干赂钱,则自无事矣……每年统巡之来,必领率甲军,声言逐匪,而何曾有驱逐之举乎?例有情给,便同一收税之行也。”⑩统巡制度已变成地方官兵受贿索钱的手段而已。1872年十二月,出使清朝归国的朴珪寿给朝鲜国王的进言中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封禁政策的虚实:“自义州至栅门为一百二十里,自此以北至于江界以外,皆是禁地也。奥自清初,不许垦田筑室,以严两国边禁。挽近各处流民往往冒禁,聚集于其地,年加岁增,其数渐多。中国虽行察边之政,而亦渐归文具。虽然,入栅贡路,终无犯禁耕垦之弊矣。臣于渡江以后见之,则殆无一片闲地,黍粟诸谷宛然成林,比较他地尤为丰登矣。第此禁地之烂漫垦辟,人烟相望,必至两境之奸细匪类,隐伏滋长,出没惹事,其为深忧,诚非细虑矣。自江界以下沿江诸邑只隅一江,而况于冰合之时,每多冒禁犯越之弊。近日所闻,尤为狼藉,诚极闷然。”(11)说明清朝的统巡察边政策已名存实亡,鸭绿江流域的闲旷地带已被流民开垦殆尽。据《江北日记》记载,到1872年为止,来自山水、仁遮(现两江道北部)和厚昌(现慈江道北部)等郡的朝鲜人在鸭绿江上游今中国临江六道沟至长白县十三道沟400多里(160多公里)(12)的地区,聚居成了18个部落,共有193户,1673人。(13)在朝鲜厚昌郡对岸,鸭绿江中游今临江市三道沟至六道沟一带,聚居朝鲜人270户,1465名,农舍零零落落绵延150里(60公里)。(14)而当时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朝鲜移民十之七八来自咸镜北道茂山,其原因是地方官的苛政及“别界”之说的诱惑。“丁卯之夏,马行逸为茂山府使,查出无名还逋十余万石,狼食虎吃,半岁之间,一邑涂炭,富者贫,而贫者死,至于哭声连巷,甚于兵火。民既无告号天叫生之际,适有此地别界之说,狼藉相传,民皆耸喜,相促而发,如水赴海。而路出白头山腰,是五百余里无人之地也。夏而病暑,冬而饥寒,死于中途者,不可胜数,至今犹腥。而幸其不死者,皆到此地,是所以居人之茂山多,而他来小也。”(15)关于“别界”之说,《江北日记》载:“茂山名不知金有司云者,七八年前潜到此间,及其回还,做出伪书,盛称葛郭之德,甘言山水之美,甚至图画地形,详录里数,故落于慈城闾延面。此书始播传,各处之人,美其名而辐辏越来,横死者,不知几千。苟活者,皆佣于胡,而家有妇女,皆为胡妻,所有财物尽作胡有。使我西北两道之人,半死于途,半佣于胡……若使金有司初无伪书,则人必无来此者,而既来而畏法未归。边禁之法,去来一般,而来易去难,是亦天之所使耶。”(16)“我亦为此等说所误,三年前携眷到此,未见如所闻者。而贫不资生,雇于胡,而至于浮江流木。自巴江历凤城(凤凰城)抵我界龙川(隶属于旧平安北道)越边孤山,匝岁而还,竟无别界,且无高人之居。”(17)反映了当时大批朝鲜人因“别界之说”的诱惑而犯越国境来到中国所导致的悲剧。
据《江北日记》记载,当时住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朝鲜人,以1872年六月为准,有十年前、六七年前、四五年前、三年前、昨秋、昨冬、今春越江者,其中,“三年前”即1869年越江者最多。从越境者的籍贯看,有茂山、厚昌、楚山、江界、义州、宁边、宣川等朝鲜北部地区,其中“三年前”从茂山长白山麓僭越者最多,其次是从江界越江者,而大多数是被“高人”、“别界”之说诱骗而犯越国境者。
总之,自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和朝鲜均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无力固守封禁锁边政策,关内流民和朝鲜北部边民不断闯入鸭绿江流域伐木、垦荒、采矿,逐渐形成流民社会。19世纪60年代大批朝鲜人冒着生命危险越境移居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谋生的原因是朝鲜封建统治的残酷及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其中大部分人是因“别界”之说的诱惑铤而走险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的。
二、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民间自治机构
因清朝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在设府县之前,鸭绿江流域处于有军政无民治的状态。自同治年间,随着中、朝两国流移民的不断闯入,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流民社会自发形成了民间自治机构,自行管理当地的民事及社会治安,保护所辖地域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就是所谓的“会上制”,有的地方志文献中则称“会房”。
例如,现在的临江一带,设立“会上制”之前,各村落虽然都有称“把头”的首领,负责管理当地居民的事务,但各村落之间则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因为村落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势单力薄便无法抵御土匪、马贼等的骚扰和侵袭。据《江北日记》记载,为了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侵袭,维护各村落居民的安全,1872年四月,临江一带各村落“把头”聚集在一起,共创民间自治机构“会上制”。“会上”首领称“大会头”或“都会头”,下设“会头”或“统首”。“大会头”或“都会头”由各村落的“把头”中推举产生,“会头”或“统首”则由各村落“把头”担任。一个“会上”的管辖范围相当于当时朝鲜的郡或县。“会上”的“大会头”代表各村落“统首”掌握“会上”内居民(包括中国人和朝鲜移民)的人户、民兵及兵器情况,负责惩治罪犯、征收公共事务费用、组织武装等各种民事及兵事。“此地虽无官长,也不是全无管领。而近来朝鲜人无数越来,外似贫乞,每每为盗。故自前月议定头目,名曰:会上会头、统首。而禁断可疑之人,立科甚严。每见初来人,辄夺其赍粮,例行箠楚,克断来路。”(18)外来人进入鸭绿江流域之后,如果没有“会上”发的许贴(通行证),则寸步难行。“前月各处把头立议,以巾裹头而行,虽尔国人(指:朝鲜人)来此者不敢违越。若以衣冠行者,指谓初来者,每有夺物结果之举。”(19)
据《江北日记》,1872年鸭绿江中上游今长白、临江、集安、通化等地有四个“会上”,老岭前东、西各一个,由归化的朝鲜人任大会头;老岭后亦东、西各一,由中国人任大会头。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犯越来到鸭绿江北岸的朝鲜人中,有的剃发易服归化为华人,其中具有威望且具财力者成为“会上”大会头,管理当地的村落社会。据《江北日记》,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朝鲜人“会上”会头有辛太、金元泽等,“会上”统首有秋成律、金成必等,四人都是剃发易服归化为华人的“假胡”。中国人大会头有王保太,统首有李瑞八、王春阳、韩五亭等。每个“会上”有关于人丁及兵器的登记册。今临江市七道沟穴岩坪“假胡”朝鲜人会头辛太家的人丁成册及兵器成册中记录:从今临江市六道沟到长白县十三道沟的160公里之间,分布着18个村落,合为一“会上”。在这18个村落中,朝鲜人193户,1673人;中国人163户,人数不详。(20)除壮丁外,还有310余名兵丁。根据兵器册,中国制枪85柄,大枪20柄,朝鲜鸟枪48柄。而朝鲜人的枪,则立冬收聚,放置会头家,翌年寒食颁给。“聚分常以寒食、立冬为限者,寒食冰解,立冬成冰。成冰之后,我人易攻,而或虑我人之居在彼界者,从后而应之也。”(21)即为了防止中国境内的朝鲜移民和朝鲜官兵里应外合,从立冬到寒食期间收聚朝鲜移民武器。又据《江北日记》,金汝玉是十多年前犯越鸭绿江居住中国今临江市三道沟的朝鲜茂山人,其父亲也是“会上”会头。“吾父近为大会头,自清金洞下三道沟,至往绝路为名处,一百五十里(60公里)之间,所居人丁军物,皆在于此。”(22)据其人丁成册记载:朝鲜人277户,人丁1465名,鸟铳73柄;胡人(满、汉族人)幕220户,人丁792名,大铳20柄,胡铳216柄。总之,清朝设府县民治机构前,随着鸭绿江流域流民村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根据保护地域社会安全的共同需要,民间自发形成了自治管理机构“会上制”。当时,鸭绿江流域既有中国人“会上”,也有朝鲜人“会上”,共同承担管理和保护村落社会利益的责任。如:鸭绿江上游的中国人经常越境到朝鲜盗伐木材,1871年冬天被朝鲜驻防军禁止,而导致武装冲突,“会上”遭到损失后,为重新组织武装而需要的费用,由当地中国人和朝鲜移民共同承担。“昨冬厚昌严防,不得伐木流下之故,失利之钱殆至数十万,而请兵接战之费,亦为万余金。故江边诸处之胡,共议收敛,我人(越境朝鲜人)一千两,彼人一千两,合二钱两,将贸火药,期开伐木之路云。”(23)
三、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
当时居住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有房舍、地产及其他产业,而大多数越境朝鲜人则身无分文、缺吃少穿,十之八九沦为满、汉人的雇佣,过着悲惨的生活。生产活动,除了农业外,还有参圃、伐木、采矿、捕猎等。现将《江北日记》中反映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村落社会生产生活的情况列举如下:
业在于农,且务采参、捕鹿、猎貂、淘金,又或有参圃为业。彼富我贫,我人之佣于彼者,十常八九。而虽不役于胡者,如退奴之事其主,皆资胡为生也。(24)
西行三十里(12公里)许,地名三千洞,所过胡幕二十余处,皆是参圃为业,或二三日亩,或五六日亩,皆覆以白西洋木。我人之雇于胡者,不计其数,而绝无作家独户者也。(25)
(始头河)江边三胡幕,皆是大参圃主,而每圃大至十余日亩,小不下六七日亩,皆覆以白西洋木,望之如白云满野,亦一壮观。(26)
远看江边,结幕栉比,假量为数三百户,而数千人列坐淘金。(27)
川边有胡人猎幕一处,悬鹿茸四首,问捉鹿之术,则曰:“捉鹿不难,多财多捉。斫木为篱,包围三四百里(120—160公里),间间作门,门外掘井,捕尽篱内之鹿。每年填井,使鹿自入,而当时复掘,从篱内驱之,则无不捉。多财则作篱尤广,广而捉鹿尤多,是所以多财多捉。”(28)
胡人之越境伐木,无年无之,而曾不得禁止。忽于昨冬赵官之来,何为严防,至于发兵杀戮乎?此间胡人之业农,利在卖谷于伐木人也。伐木之利,每年以百万计,故不惮远来,而来者皆买谷于此,谷多而不难卖,卖而利甚多,故渐来务农矣。昨冬则严防伐木之胡,既无伐木之胡,而仍无卖谷之处,谷虽多,不食则无用也。(29)
胡幕三十四座,我人家二十七,而我人之佣于胡者,无幕无之,家居者,亦未免为胡奴隶。(30)
昨秋以后,自江界越来者,不啻四五百户,而皆散作胡奴。……然来此者,未必皆贫,而来辄为胡雇佣,终岁自苦,有妻而妻胡者,十常八九,有财而自活者,百无一二。(31)
庚午九月惑信此说,携眷渡江,中路丧母,初接厚州越边八道沟,转至三道沟,复从八潴江边而上,权接于此,无处不行,而既无别界,且无高人。……苟活者,皆佣于胡,而家有妇女,皆为胡妻,所有财物尽作胡有。(32)
有我人九户,尽是茂山来人,皆至贫,男衣胡服,女不着裙,裤弊生腿,真不堪见也。(33)
另外,鸭绿江流域流民社会经常受到土匪威胁,该区域山高路险,清政府对此地的治理鞭长莫及,各种利益集团任其发展。自同治初年起,随着流民的增多,匪患不断,响马贼、红胡贼劫掠事件时常发生。“此地,即中国之边外也,所以设把守边,在于此江三十里之内,把守以外无法之地也。有力者为上人,众多者为强贼,入此地,有谁言法者乎?”(34)“下江诸处,红胡子数千名,以响马贼为业,见财则夺,小弗杀害,人莫能过此者也。”(35)在这个“有力者为上人,众多者为强贼”的匪盗世界里,流民的生命财产难得安全保障,特别是对无依无靠的朝鲜流民来说,境况更是险恶,经常遭到匪盗之害。“自此出洞一百五十里(60公里)之间,曾有我人七户,今春为响马贼所灭,他无人家。”(36)此地朝鲜人“全无家居,皆为吾们雇佣。而昨冬流来四百余户,尽为红胡贼所掠夺。妇女之被擒,亦至数百”。(37)“我本楚山人,姓金,五月间三人作伴,从江界渡江,自罗段洞逾大岭,道遇红胡贼党,见夺衣褓,两人被杀,我则疾入林丛之中,误落断崖,折臂几绝,仅保到此,痛甚欲死也。”(38)
犯越国境的朝鲜人不仅仅是贫苦农民,也有少数没落“名人”,但他们的遭遇同样悲惨。“今春义州洪进士为名人,乘轿子,以其家丁妆作前陪军牢而前导之,内眷之乘轿子者亦数十,而后从人丁殆近三百。从江界白昼渡江而来,威仪甚盛。然到道里沙阿峙为名处,遇红胡贼党,尽夺妇女、财货,人命死伤者,亦近三十名,至今结构于山谷苟活,而多眷无米,率来之人亦未免为胡雇佣。”(39)
除了土匪的袭掠,随着朝鲜流民的增多,鸭绿江流域的中国人恐其生存环境受影响,便设法阻碍朝鲜人流入。“而近者我人之来甚多,胡亦虑其来多而害之。故种种有遮路夺物之举,而春来益甚,我人之遇害于途中者,不知其数。”(40)
总之,据《江北日记》反映,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生活状况,中国人富,朝鲜人穷。朝鲜人十之八九沦为满、汉人的雇佣,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大多数朝鲜人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犯越国境,潜入中国鸭绿江流域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而且还要逃避清朝官府的驱逐,忍受满、汉地主的剥削和马贼的侵扰,非常艰难地维持生计。很多人是因“别界之说”的诱惑铤而走险犯越国境,来到中国后,不仅没有寻到什么“别界”,反而因违法的恐惧和叛国的痛苦,过着进退两难、忐忑不安的日子。
1872年,正是清政府在流民的不断冲击下放弃封禁、开放鸭绿江流域的前夕,也是朝鲜饥民涌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时期。越境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遭遇,包括中国流民在鸭绿江流域的生产生活状况,这些关于清朝封禁区域内的社会基本情况,当时人给我们留下的记载非常有限,而《江北日记》提供了这方面珍贵的资料,弥补了不足。
抛开崔宗范等人越江“考察”的目的不谈,《江北日记》至少提供了如下重要的信息。
第一,鸭绿江北岸虽然是封禁区,却没有能够阻止中、朝两国人民犯禁进入,谋求生存。在封禁解除之前,那里虽然尚未达到人烟辐辏,至少已经不是人迹罕至,而在有些地段,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村落社会。这就意味着,清朝的封禁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开禁与开发,成为清政府不得已的举措。如此局面的出现,自然是两国下层民众冒险犯禁斗争的结果。
第二,自清初至1875年,将鸭绿江流域定为封禁区域,当然不会在那里设置行政管辖机构,但随着流民村落社会的发展,自发形成了民间自治管理机构及武装,即所谓的“会上制”,中国的地方文献称之为“会房”。这种“会上”或“会房”,既有中国人的大会头、统首,也有朝鲜人的大会头、统首。“会上制”在清政府行政管理鞭长莫及而土匪、马贼横行的边境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保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
第三,当时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村落社会中,满、汉人富,有房,有地,有产业;朝鲜人穷,无房无地,十之八九沦为他人奴佣。生产活动,除了农业外,还有参圃、伐木、采矿等。大多数朝鲜人因“别界之说”的诱惑犯越国境来到鸭绿江北岸以后,虽然能够逃脱饥荒,获得了生存,但他们的处境却是异常艰难。除了生活环境的困扰与约束,非法越境的恐惧及客居他国的心理压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然而,绝大多数朝鲜流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鸭绿江北岸定居下来,为当地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朝鲜族的先民。这种毅力与精神,值得后人钦佩。
最后,在日本人牛丸润亮著《最近间岛事情》、(41)朝鲜总督府编《在满朝鲜人概况》(42)以及韩国人玄圭焕著的《韩国流移民史》(43)中,都主张1870年(玄圭焕主张1869年)朝鲜平安北道观察使把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的居住地分割成28个面,划入朝鲜北部江界、楚山、慈城、厚昌等四郡管辖,对当地的朝鲜流民进行保护。笔者认为,如果此说属实的话,朝鲜平安道厚昌郡郡守赵玮显不可能不知道此事,更没必要于1872年派遣谍报人员到鸭绿江流域秘密调查朝鲜移民情况。而且当时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没有得到清朝政府的允许下不可能擅自把中国领土划入朝鲜版图。《江北日记》的出现,证明此说是不成立的。
可见,《江北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异常珍贵的第一手流民社会史资料,它不仅揭示了清朝设府县民治机构前鸭绿江流域流民社会的民间自治机构及其生产生活状况,而且还弥补了中外文献资料对相关内容之记述不足及漏洞。其中还蕴藏着许多尚未挖掘的内容,值得去深入研究。
注释:
①《江北日记》原为中文繁体字的手写本,收藏在韩国旧藏书阁,1977年韩国弘益大学崔康贤教授在《国学资料》26号上发文,揭示于世。1978年,韩国高丽大学柳承宙教授在《亚细亚研究》59号上发表《对朝鲜后期西间岛移住民的考察——〈江北日记〉解题》,转载了全文。1989年,延边大学高永一主编《朝鲜族历史研究参考资料汇编》第一辑转载了《江北日记》全文内容。1994年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郑求福发表《〈江北日记〉解题》一文,将《江北日记》全文影印收录在《江北日记·江左舆地记·俄国舆地图》一书中。2003年崔康贤韩译《江北日记》,并附《〈江北日记〉题解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收录于《间岛开拓秘史》一书。
②(清)博明:《凤城琐录》,《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74页。
③《清宣宗实录》卷442,道光二十七年五月。
④《通文馆志》卷9,显宗十三年正月壬申。韩国民昌文化社1991年版。
⑤参见《备边司誊录》第39册,肃宗十二年一月十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影印本。
⑥《李朝实录》,肃宗十四年三月庚辰。
⑦《备边司誊录》第39册,肃宗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⑧徐世昌:《东三省政略》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923页。
⑨《清穆宗实录》卷85,同治二年十一月中。
⑩《江北日记》,六月初九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4年影印本。
(11)《承政院日记》,高宗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12)当时朝鲜人所说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0公里。
(13)参见《江北日记》,六月三日。
(14)参见《江北日记》,六月八日。
(15)《江北日记》,七月初二日。丁卯年,公元1867年;还逋:还子,还租。“别界”之说:当时有人传说,中国鸭绿江流域有罗善洞、杨花坪、玉鸡村、铁铺城等别界及蔡先生、郭将军、葛处士、金进士等高士,是人能够安生的理想之地。
(16)《江北日记》,七月二日。
(17)《江北日记》,六月初五日。
(18)《江北日记》,六月初一日。
(19)《江北日记》,六月初二日。
(20)参见《江北日记》,六月三日。笔者认为193户的朝鲜人口数不能达到1673名,当时平均每户不能有八九口人,而应该是193户朝鲜人和163户中国人加起来356户的人口数为1673人,每户平均四五口人,才是合理的。
(21)“我人”指朝鲜人。
(22)《江北日记》,六月初八日。
(23)《江北日记》,六月初九日。
(24)《江北日记》,六月初三日。
(25)《江北日记》,六月十八日。
(26)《江北日记》,七月初二日。
(27)《江北日记》,六月二十四日。
(28)《江北日记》,七月初一日。
(29)《江北日记》,七月初十日。“昨冬”指1871年十二月,在《李朝实录》高宗八年十二月条上有相关记录;“赵官”指朝鲜平安道兵马节度使赵台显。
(30)《江北日记》,六月十三日。
(31)《江北日记》,六月二十一日。
(32)《江北日记》,七月二日。“庚午年”指1870年。
(33)《江北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34)《江北日记》,六月二十日。
(35)《江北日记》,六月二十二日。
(36)《江北日记》,六月五日。
(37)《江北日记》,六月十九日。
(38)《江北日记》,六月二十二日。
(39)《江北日记》,六月二十一日。
(40)《江北日记》,六月十九日。
(41)[日]牛丸润亮:《最近间岛事情》,朝鲜人及朝鲜人社1926年版,第76页。
(42)《在“满”朝鲜人概况》,日本外务省1933年印行,第3页。
(43)玄圭焕:《韩国流移民史》,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67年版,第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