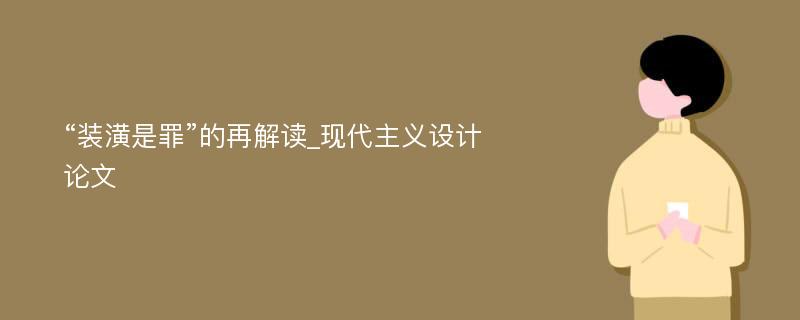
对《装饰即罪恶》的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装饰=罪恶?鲁迅先生说过“矫枉必过正”,但因为“过之而无不及”,过激的言语往往又与真理擦肩而过。因此,对大师提出的看似过激的言论,我们有必要做出历史的、辩证的的评价,借以对当下存在的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
“装饰即罪恶”可以说是“少即是多”“形式追随功能”“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等代表现代主义特征口号的近义短语。它几乎成为一种语言符号被广泛地复制、模仿或批判,以至于“装饰不是罪恶”、“装饰是罪恶吗?”等成为各理论人士论证或反证所青睐的选题。它的始作俑者为著名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他于1908年以此作为论文的标题,英文版的题目为Ornament & Crime(原题为Ornament und Verbrechen),在国内被翻译成《装饰即罪恶》或者《装饰与罪恶》。这两种译法各有优点,前者因其“过正”的言辞令人印象深刻,然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译法,原因在于后者在字面意义和文章主旨的表达两方面都更为接近原作。
为求表里如一,此文发表的时候甚至没有用任何插图或其他形式的装饰。此书中,卢斯以嘲讽的口吻列举了装饰的种种“罪恶”:“巴布亚人杀死敌人,吃掉他们。他不是罪犯。但是一个现代人杀了个什么人,还把他吃掉,那么,它不是个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一个纹身的现代人不是个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
罪恶一,装饰是原始的、未经开化的人类或者是心智发育不完全的儿童的行为,是不发达人类阶段的表现,因此在先进的社会中不应被提倡。“装饰匠必须干20个钟头的活才能挣到现代化工人八个钟头就能挣到的收入……用同样价格的原材料,花费三倍长的时间,装饰过的物品却只有朴素的物品的一半价钱。”
罪恶二,就当时实际的社会境况来说,制造带装饰的产品价格反而低于造型简洁的工业产品,由此造成了装饰工人生活困窘。
“装饰的变换使劳动产品过早贬值”。
罪恶三,过度的装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提倡装饰的“落伍者”延缓了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进步。
……
要明确装饰和罪恶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应了解卢斯所指的装饰为何。
在英语中,含有装饰意味的词语很多,以ornament、decoration较为常见。卢斯所指的装饰由“ornament”翻译过来,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典》,ornament的基本含义为:因美丽而非因实用而置于房屋内的物品。Decoration的基本含义为:某种漂亮的东西,用以附加在别的物体上,以便其更具吸引力;装饰的手法;装饰的行为或过程;类似勋章等作为政府荣誉的事物。从概念上我们可以得出装饰的两个基本属性:一、附加的,也就是实用功能以外的;二、美的。或者说装饰行为即“附加无用物以使另一物美”。由此可见卢斯提到的“巴布亚人的纹身”“红色天鹅绒长筒袜上的金色流苏”“鞋子上布满的扇贝纹样和窟窿”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装饰。装饰的起源有森伯的技术说,博阿兹环境说,威林格的抽象与移情说,赫伯特·里德的充填虚无的冲动说,李格尔艺术意志说,易中天的人类自我确正的冲动说,宗教说,图腾说等等,然而这些在抽象美产生之前就存在了。也可以说“附加的”在“美的”之前成为装饰的属性。当然如今在普遍意义上,装饰和“美的”不可分离。“附加”是美化客体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惟一的方式。比如荷兰著名建筑设计师里特威尔德于1923年设计的乌德勒支住宅,不需要添加任何花纹或者装饰材料,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构成、简洁之美。因而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结构本身的装饰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所谓装饰性是指:装饰所具有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即使某物本身功能性占主体地位,然而它自身能够体现出美感,作为一种附加物能够使另一物显得美观。比如一盏设计精良的灯具,它在作为“灯”行使其使用功能的同时,作为一种附加物它还能够起到美化房间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是有装饰性的灯,但其本身不是装饰。由此可见,虽然乌德勒支住宅本身具有美感,但是如果它并不能起到衬托周围景色的作用,就不能称作有“装饰性”,最多也只能用“美的”来形容。然而鉴于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模糊性,本文中的“装饰”既包括真正意义上附加性质的装饰,也包括美的物化结果。
在明确装饰为何意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联系卢斯所列举的装饰所犯的“罪行”展开以下讨论。
就第一点来说,卢斯从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装饰本身发展的角度否定了装饰存在的价值,并提出当时盛行的矫揉造作的装饰风格是历史的倒退,无装饰的简洁的风格才是应当推崇的。
首先,卢斯看到了与装饰并存的消极的社会现象,如厕所的涂鸦等为现代文明所不齿的行为,然而他过于武断地否定了装饰本身的价值。对于装饰是否“应该”存在似乎尚无定论,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有: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无论在怎样的时代,处于怎样的生产力状况,受怎样的道德观价值观影响,装饰变化的只是其载体与方式,它作为人类的天性一直存在:从古希腊的陶瓶、帕提农神庙到阿拉伯的织毯、印度的泰姬陵,再从中国春秋时代的青铜器、明清时代的家具到日本的浮士绘,再从北欧维京人的“攫取兽”图案到非洲的土著木雕……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一直伴随着装饰风格的不断演变。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设计革新思想领袖拉斯金曾说道:“装饰是建筑的首要部分。一座建筑物的绝顶高贵并不在于它建造得好,而在于它被雕刻或绘画得华美。”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也曾写道:“编好的篮子、织成的布、削凿成形的石块或雕花的木头都记录和保存了人类乐于掌握技艺的天性,装饰艺术的兴起离不开这种天性”。卢斯本人也在文章末尾提到“我可以容忍卡弗尔人的、波斯人的、斯洛伐克农妇的和鞋匠的装饰,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能够给他乐趣。”这恰恰说明了装饰行为可以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愉悦感的积极意义。装饰是情感的体现,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举世为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在装饰行为过程中,劳动者投入了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情感,这也可以看成制造者向使用者的一种“移情”,令使用者感到同类的关怀。大机器的批量化生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这种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个人生存能力的提升却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塑料、金属制品的标准和冷漠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产品情感上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手工艺产品往往在价格上高于大机器生产的原因之一。更进一步说,当今即便是大机器生产的产品也提倡产品外观设计上的low-tech,即“高情感”,比如叙事风格的产品设计就突出了产品的生活气息,令使用者倍感亲切。装饰还是等级制度的体现,拿装饰在建筑中的作用来说,从古至今它就被用以区分重要的和普通的建筑,华贵和朴素的建筑,官用和民用的建筑等等以配合不同阶层或不同活动的需要。中国古代朝服的装饰图案也明确指示了官员职位的高低。简而言之,装饰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次,卢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装饰发展的内在规律,得出的结论有其局限性。国际风格的衰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迄今为止,现代主义是工业革命以来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念上发展最为完善、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设计思潮。它所提倡的设计原则就是“简单优于复杂,平淡直率优于鲜艳夺目,单一色调优于五光十色,经久耐用优于追赶时髦,理性结构优于盲从时尚”。[2](P.162)也就是说带有附加性质的装饰是不被现代主义提倡的。此原则在解决大量民众住宅需求以及战后城市重建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伴随着现代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倾向的“国际主义”风格,其过于理性、冷酷的原则忽略了人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从而遭到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等逐渐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中发展起来。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当今的设计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注重感性、个性化、文脉、历史、人文关怀等因素。尤其是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孟菲斯”设计小组,他们否定理性主义设计原则,认为设计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假设。他们追求装饰,认为设计中形式、功能、材料三方面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功能与形式相矛盾的产品只要能表达某种情趣,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就有其存在价值。这和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形式追随功能”不说背道而驰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虽然“孟菲斯”的设计由于实用性缺乏只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但是它独特新颖的设计却给无数设计师以灵感,使设计不断在自省中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卢斯提出的“文化的进步跟从实用品上取消装饰是同义语”,我们是应该质疑我们当今的文化倒退与否还是应该质疑卢斯得出的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呢?
就第二点来说,卢斯认为造成手工艺人生活的窘迫的根源是装饰,实际并非如此。卢斯所处的社会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正处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工业化正像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一样,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从未发生过如此突然,如此剧烈的变化。1880-1914年间,在欧洲刮起一阵乐观的现代主义风。欧洲人相信进步,不惧怕未来。”[3](P.501)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当时手工艺人的收入比普通工人收入低得多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实在不能归咎于装饰。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由于机器化大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生产某种商品个人必要劳动时间越低,其个人在相同工作时间内生产的产品价值总量就越大。具体来说,假设手工艺人和普通人每天都工作8小时并生产同一种商品,由于普通工人的个人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手工艺人,他们在8小时之内生产的产品单位数量也会远远高于手工艺人,由于同一种商品的价值相同,单位商品所卖的价格一般也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普通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总量远远高于手工艺人,他们的收入自然相距颇大。这就是为什么“装饰匠必须干20个钟头的活才能挣到现代化工人八个钟头就能挣到的收入”。因此,当时手工艺人生活窘迫的最根本原因恐怕不能说是装饰,而是由于一般的手工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大机器生产低下得多。
就第三点来说,由于人们要求装饰不断变化的天性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但是这仍旧不能成为否定装饰本身的理由。这涉及到装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科瑟(L.A.Coser)和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Dahrendorf)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指出;所有的社会在对其珍贵稀有的资源进行分配时都充满着不平等的现象。纵观人类发展史,无论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条件或是社会形态下,客观上总是存在着消费资料相对不足的情况,即使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仍旧有着贫富差距。同时传统的道德伦理又把诸如“节制”、“节约”作为美德的一种不断传承下来。与理智的德性不同,作为伦理的德性的“节制”关系到情感和行为,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道”的概念来区分好的德性与其他不好的品性,“中道”是好的,而“过度”和“不及”因其极端的性质被当作不好的。这也和中国传统儒学提倡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那么对于装饰来说,符合“中道”的装饰是好的,“过度”或者“不及”的装饰就是不好的。古人云“过之犹无不及”,过度的装饰会造成视觉污染,以至于劳民伤财,但是适当的装饰能够既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又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早已超越了马斯洛所提出的最低生理要求,而已经发展到审美需求乃至自我实现需求等更高一层的心理要求。因此装饰作为满足人们更高理需求的一种方式有其存在价值。
在有关装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卢斯认为装饰所造成的浪费和社会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说,人们对作为消费资料的装饰的过度追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然而社会变迁的原因是复杂的,经济原因只是其中之一。现代进化论者认为社会进化的形式可以是多元的,认为不同的社会都有自己的进化阶梯,而且每个社会中的不同领域都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方向。根据边沁的功利正义论,凡是最大程度地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正义的。由此可见理想中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创造更高的生产力,而是创造更公平、更人性化的社会,使大多数人在物质、精神两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人们对装饰的追求属于内在的精神需求,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理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综上所述,卢斯的观点在当时既有其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其进步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过度的装饰给社会和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准确地预言了大工业生产背景下现代主义风格的来临;其局限性在于,他一味夸大装饰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认识到装饰存在的价值,以至于把装饰和“罪恶”等同。实际上卢斯并未否定装饰追求“美”的属性,而是反对装饰另一个“附加的”,即无实用功能的属性。众所周知,设计中与功能对应的是人的需求,人对某种设计功能的需求层次也有高低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应具有的审美功能不能被称作“附加的”,而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有实用功能”的。同时“附加”也是美化的方式的一种,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恐怕有失公平。从伦理学方面看,所谓“善恶”是就德性和物性的“好坏”而言的,对应的“罪恶”就应该归属于“坏”的一方。但是善和恶之间有个过渡阶段,那就是“非善”,但是不能被称作“恶”。由此看来,我们只能对卢斯所处社会的装饰,或者说是矫饰过度现象扣一顶“不合理”的帽子,但不能以“罪恶”盖之。如同美和丑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带那就是“不美”,但是并不能说是“丑”,这有别于传统工具理性鼓吹的非此即彼。
“装饰与罪恶”的问题是形式与功能的矛盾在社会伦理上的体现。而形式与功能这对矛盾又是贯穿于整个人类设计史的矛盾之一。同时伦理道德的实现究竟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依然是一个问号。由此可见,只要人类存在,关于它们讨论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这也可以看作是卢斯《装饰与罪恶》一文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所在,他的论述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从而引发人们对现状的思考。
首先,它再次证明某种装饰风格,审美趣味、设计理念的形成总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生产力状况的反映,由此提出注重历史和文脉以及创造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审美语境的重要性。1851年,伦敦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展出的产品暴露了工业化生产初期工业产品的粗糙以及深受历史影响的矫揉造作的装饰风格;孟菲斯反映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设计中过于理性、过于功能主义与冷漠的一面的不满;太空风格的设计是人类登月成功后对征服自然表现出的好奇与信心;绿色设计是针对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危害后提出的设计要求;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更是在对现代主义风格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同理,卢斯所批判的“罪恶装饰”的产生也是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写照。19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在短时期内聚拢了巨大的财富,由此对物质生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卢斯等提倡简化甚至取消装饰相反,一部分暴富者热衷于利用象征贵族生活的巴洛克、洛可可式装饰来炫耀他们的财富,因而此时期的装饰就呈现了一种庸俗而毫无节制的状况。从这一点上看来,卢斯等为简洁的装饰风格奔走呼号确有其进步意义。
当今,卢斯所深恶痛绝的“罪恶的装饰”在我国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一幢幢所谓的“罗马式风格”“欧陆风格”居住小区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争相涌现,爬满山花的墙群、花哨的科林斯柱头此起彼伏……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于2001年十一月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提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装饰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装饰和审美息息相关,而审美趣味的培养不仅关系到个人,更是社会大范围之内的必修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对艺术设计的认知的社会语境,大众,甚至一些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员对设计、装饰、艺术并无深刻理解,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审美趣味的相对低下。而为了迎合这样的审美趣味,大量的急功近利的设计被制造出来,进一步对大众的审美形成错误的导向,引起恶性循环。因此对装饰,或者进一步说艺术设计进行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欣赏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功课,而且是消费大众的功课,因此面向大众的审美教育也至关重要。如果大众热衷于低俗浅薄的装饰,纵使设计师拥有再高品味的理念和作品也只能束之高阁。艺术的基础教育、各社会性艺术机构如艺术馆、艺术学院等等应从一定程度上担此重任。
其次,它再次引起了社会范围内对艺术设计中的功能与审美关系、装饰与伦理、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涉及到设计、设计者、设计消费者、个人道德及社会伦理。大到建筑,小到锅碗瓢盆,艺术设计是社会性的活动,这要求设计师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威廉莫里斯曾经提出他的民主思想;我不希望那种只有为少数人的教育的艺术,同样也不追求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与其让这种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存在,倒不如把它扫除掉来的好。人既要劳动,那么它的劳动就应该伴随着幸福。现代设计教育的先驱包豪斯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在他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中就非常重视对设计师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他在1923年发表的《国立魏玛包豪斯的理论与组织》中提到:“……包豪斯感到自己负有双重的道义责任:应该是学生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的时代;并应训练他们运用自己的天资和所获知识去设计各种模型,直接表现自己时代的这种思想意识……在所有这些饶有兴趣的工作中,我最关注的却是为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提供最起码住所的问题;中产阶级住宅必须是本身齐全而装备经济的单元的问题;以及它们每一种应该采取什么结构形式才是合理的……”。
最后,它提醒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装饰本身。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都是一种过程,都会处于某种阶段,而不会永久性地停留于某种恒定的结果。装饰发展到卢斯所处的时代,其含义已经产生了变化,如前所述,有人认为所谓装饰已不仅仅局限于附加物,而可能是某种本身具有美的性质的结构或物化功能。1893年卢斯参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深受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骨架结构和芝加哥学派高层建筑的影响,从而提出今后建筑发展的趋势是附加性装饰的简化甚至消亡,这无疑是有其预见性的。但是因其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在现代主义发展初期就能窥见到现代主义发展到后期才会逐渐显现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作为表层结构的装饰形式总是在作为深层结构的装饰心理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下进行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
装饰意识是人类的天性或者可以说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之一,长久以来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抛开其他一切因素单纯地讨论装饰好还是不好,属于善还是属于恶恐怕毫无意义。如贡布里希所说:“从心理学上和历史上追溯反对装饰的根源时,我们必须注意反对装饰的不同动机。如果装饰被看作庆祝的一种形式,那么只有装饰得不恰当时,才是应该反对的。”[4]那么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究竟什么样的装饰、怎样去装饰才恰当?在笔者看来,这首先要和中国的资源状况以及生产力状况联系起来。中国虽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一个拥有广大潜在的设计消费的市场,但是这同时造成了相对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物资匮乏。而且中国的沿海和内陆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明显不同,而且还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由于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就学困难的问题而反对政府大张旗鼓地申办奥运,因为奥运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也不能因为加强东部沿海的发展而放弃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同理,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可以给予不同的设计和装饰方式,具体如何协调处理各方面的问题值得也需要每一位设计师在实践中思考。
艺术设计以“人”为本,在于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而装饰是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在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也更加趋于多样化,很难设立一个特定的标准。时代在变化,人们追求美的事物的内在需求却将会永久性存在。因此,与装饰有关的伦理的讨论也将永远继续下去,平衡艺术设计中装饰及其有关问题之间的矛盾依旧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