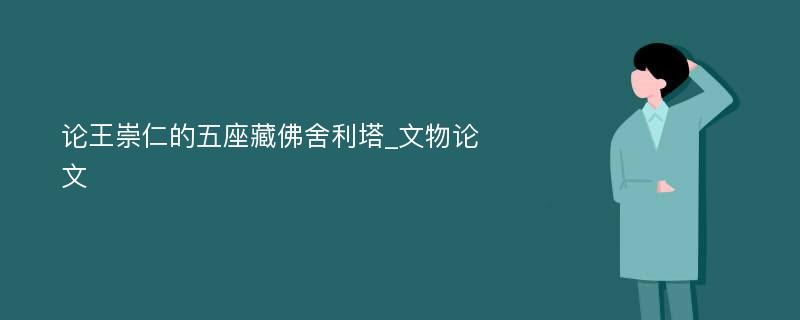
谈王崇仁藏佛舍利五重宝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仁论文,宝塔论文,舍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4月,王崇仁先生以巨资购回的“佛舍利五重宝塔”(以下简称“宝塔”)运抵西安市,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这座宝塔,是内外五重塔相套的组合。最外层是石塔并圆雕四大护法天王。可惜石塔底座佚失,残高173厘米。石塔内,是圆筒状铁塔,开四门,上有八角攒尖顶,高80厘米。再内(第三重)为圆筒状铜塔,开一门,高48厘米。更内(第四重)为圆筒状银塔,高23厘米。最内(第五重)为宝瓶状金塔,以金龟为座趺,高8.5厘米。金塔至今仍未开启。金塔置于八角束腰须弥座上(图一:宝塔系列图片及线图,见封三)。
为探究该宝塔的年代及文化内涵,王先生自从2007年4月至11月间,先后邀请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20多人前来西安实地考察,发表高见。据《佛舍利五重宝塔回归捐献大事记》(止于2007年11月12日)介绍,对于该塔的年代,重要的有下列诸说。金申:“晚唐至辽之间”(4月23日),9月17日修订为“辽统和——重熙年间,即11世纪前半期。”北京大学宿白老师:“介于唐末、五代到宋代之间”(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老师:“应为五代时期之遗物”(6月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韩伟:“晚唐至北宋之间”(6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可以与南京栖霞寺五代南唐(公元937-975年)时所建的舍利塔对照研究。”(9月12日)。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9月3日云:“其年代是晚唐、五代或北宋时期”,即从宿白老师之说;2008年4月28日论文称:“属于西夏前中期之物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为辽国西南地区或北宋西北地区之物。”这一推论亦来自宿白老师论断“不是中原地区的”。实际上,西夏与辽的佛教图像有显著区别。
2007年4月28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的“五重佛舍利宝塔学术研讨会”上,本人发表意见称:“该宝塔是辽代前期之作”;出土地点则应在北院大王统辖区,“大约在内蒙古赤峰至辽西朝阳一线”(见“中国佛学网”5月2日报道:《佛舍利五重宝塔时空认定的重大突破》)。
一、宝塔为辽代之作
该宝塔具有明显的辽代特征,这一望可知。
第一,该塔中的铁塔、铜塔及银塔皆是圆筒状之舍利函具,是契丹民族的创造。众所周知,契丹乃游牧民族,生住圆形帐篷,死后亦多用圆形骨灰罐。1973年在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出土的泥质灰陶帐篷形骨灰罐就是典型代表。契丹人土葬墓的平面,也多作圆形,其例繁多。甚至投降契丹的汉族官吏,也效法之。如北京地区发掘的赵德钧墓(公元958年)、韩佚墓(公元995年)、王泽墓(公元1053年)等等。契丹人以圆筒形骨灰罐为原型,创造了舍利函。典型器物是北京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塔墓内出土的陶质圆筒形舍利函(公元932年),其形制是把骨灰罐的圆筒状向下方延伸二倍左右,再加上圆形底座(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图版三四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刊)。
至于金属制圆筒状舍利函,则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银塔(高46.3厘米)及其内部套装的圆筒状金塔(高25厘米),有门,塔身刻法舍利真言及发愿文。朝阳北塔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金银经塔”,皆圆筒状,内外四重相套,外刻佛像及经咒等等。
另外,在巴林右旗的庆州白塔(公元1049年)天宫的秘藏室内,出土了圆形小木塔108件,有的塔身刻出七身立佛并有彩绘、贴金。
同样,汉民族土葬用棺、槨。故唐宋时代葬佛舍利也用金棺、银槨等等。
第二,铁塔外所悬挂的直棱叶状口沿的铜铃形制,近似于辽阳辽代白塔所用的铜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黄心川先生指出,这种铜铃形状乃是象征“菩提叶”(9月2日),十分准确、生动。而汉地的同期铜铃,口沿多作半圆形。西夏所用铜铃,则是小钟形状,贺兰山西夏3号陵即有出土。
第三,石塔上所刻坐佛,露一足,且足心向外,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也只见于辽代。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内出土的“建塔碑铭”(公元1049年),在额额佛龛中所刻之坐佛,即露一足,且足心向外。此等作法在汉地及西夏均未见过。足心向上,才是正统的作法。
第四,圆雕托塔北方天王及金塔上錾刻的北方天王,皆在胸以下佩有一条鱼。这是中国佛教考古史上的首例。原来,这是标志着辽代调动军队的兵符。《辽史·仪卫志三》符契条云:“自大贺氏八部用兵,则合契而动,不过刻木为半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鱼。金鱼符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半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事讫归于内府。”《辽史·礼志一》云,皇帝参加“祭山仪”时,也是白绫袍,绛带悬鱼,则是右半金鱼。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用虎符。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颁木鱼符。唐武德元年九月(公元618年)改为铜鱼符。宋仁宗时下令造铜虎符,金代沿用之。隋、唐的鱼符都是“左者进内,右者在外”(《新唐书·车服志》。这就是说:隋、唐、宋时代的鱼符,“左半鱼”掌握于朝廷,“右半鱼”颁给大将。这是中国古代礼制以左为上的结果。中国人所谓“虚左”、“操左券”,皆此意也。但契丹人刚好相反,“左半鱼”授给大将,而“右半鱼”则留在朝廷。我们观察两个北方天王所佩之鱼,恰恰是“左半鱼”,“长六寸”,以天王身体比例看,亦较符合。这佩左半鱼的天王,是宝塔定为辽代文物之铁证!辽宁省朝阳市曾出土一件铜鱼符,内侧有契丹文字(图二,见封三)。
关于天王的形象,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汤池先生指出的,它与河北省曲阳县五代王处直墓(公元923年下葬)武将“有相近的地方,但更加生动自然”(7月31日)。
二、宝塔为辽代前期之作
我们认定宝塔为辽代前期之作,理由如下:
第一,石塔外立面下层雕刻了萨满教巫的形象。下层是小巫,上层是大巫(太巫)。在石塔外立面“八佛”像的下部,雕刻了两排丫髻、羽袖的人物。大多数专家认为是供养人。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判定是女巫(2008年4月28日),颇有见地。首先,依铜塔外所刻的供养人全为跪姿,而这批人物全为立姿;其次,供养人不应持剑。实际上,这是葬礼中的一批巫觋。《辽史·礼志二》丧葬仪云,皇帝崩,先有“巫者祓除”,此后则有“太巫祈禳”。石刻下层持剑的八身男性,便是“巫者祓除之”的场景;上层持羽扇的八身女性乃是“太巫祈禳”的场景。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指出:“侍女手持羽葆、宝剑,是瘗葬仪式的场景”,一言中的(9月2日)。
这种佛巫合一的仪式,只应存在于辽代前期。辽圣宗以后,佛教大盛,义理分明,仪轨严格,不会再有这种作法。另据《辽史·礼志一》,“巫衣白衣”。石塔上的巫觋色彩不知是何时塗上的。
第二,石塔上所刻女巫的丫髻,双髻并立于头顶上。这与辽上京开悟寺塔上石刻飞天(公元937年或稍晚)丫髻相似。而将二髻分在头顶左右者,则较晚。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彩绘的飞天,乃公元1020年之作。
第三,五重宝塔中还有若干细节表现其早期性。如天王甲胄继承五代形制而有发展,更接近内蒙昭乌达盟喀喇沁旗西桥乡鸽子洞沟的耶律琮墓(公元929-979年)神道上的武将形象。佛的袈裟不做锒边,耳轮不作刀状,卧佛不设枕头等等。庆州白塔(公元1049年)中的汉白玉雕佛涅槃像即设有石枕,已是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形态。那么,我们所说的“辽代前期”,具体时段是怎样的呢?读《辽史》可知,太祖耶律阿保机崩(公元938年),太宗耶律德光“为父求碑铭”于后晋(《旧五代史》卷137)。可证太宗初年,契丹人还没有刻碑的能力,更不可能雕造石塔。公元947年正月,耶律德光入汴京,二月定国号“大辽”,三月尽迁汴京宝物送上京,并有大批工匠迁来。据此,我们推断“宝塔”的上限在世宗耶律阮时代,下限在圣宗统和年间,即公元947-1000年之内。要而言之,宝塔属十世纪下半叶的文物,不会在公元1000年之后。
金申同志的年代推断大体不差,但晚了四、五十年。他认为应该在“十一世纪前半期”即公元1001—1050年间。此时辽代佛教文物基本上与北宋同步发展,数量也较大。典型的佛像是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公元1044年)出土的铜坐像(参考图三,),与“宝塔”上的佛像有显著区别。大同华严寺(公元1062年)的辽代菩萨也与宝塔上的菩萨像明显有别等等。
三、宝塔的出土地点、供养者及结语
综上所述,“宝塔”表现出较多的契丹文化内涵,表明它的制造地域应处在北院大王辖区之内。尤以辽上京、中京至兴中府一线的可能性大。即今内蒙古赤峰市至辽两朝阳市一带,应是该塔原出土地区。至于“宝塔”的功德主,可以从铜塔所刻八位贵族妇女供养人身上得到信息。八位供养人皆丫髻,服饰一致,皆执器皿(盘口瓶等)供养,皆有一侍女执曲柄伞盖在身后。八供养人下方,皆有武士(力士)作托举状。可以推测,这是一次以女姓贵族为主体的“集体行动”。八人不分主次及地位高低。他们应是一个女性“邑社”的成员。或许与上京“圣尼寺”及“崇孝寺”(承天皇后所建)等尼寺有关,此有待进一步研究也。
另外,在铁塔塔顶内檐上,铸有“句宗受为守”五字。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解释为:“受持佛法就是对佛舍利的守护”,(2008年4月28日)颇有见地。如果我们联系到大日如来佛像在石塔及金塔上两次出现,把“句宗”理解成“真言宗”(密宗)的俗称似更准确些。当然,辽代的密宗多与华严圆通。契丹人有很多自己对佛教的理解而加以独特命名的。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上(公元1044年),砖雕了八方佛像及名称。把西方阿弥陀佛称作“平等佛”;北方不空成就佛称作“大慈佛”等等(《辽海学刊》,1986年2期)即为显著例证。
总之,王崇仁先生所收藏的这座“佛舍利五重宝塔”,的确是一件辽代前期(十世纪下半叶)契丹民族所创制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它使人们对辽代前期佛教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它表明,契丹民族在极力继承、吸收中原汉民族文化(如八角塔式、天王形象、龟趺的使用等)的同时,又充满了探索与创造精神。它把萨满教巫术与佛教信仰融合为一体;它把契丹人的葬俗与佛舍利保存融合为一体。这使宝塔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国内外仅此一件,十分珍贵。
契丹民族强大起来以后,萨满教崇拜天、地、东方等神灵,已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大胆采取了“借神”的活动。辽初,辽太祖就把幽州大悲阁的“白衣观音”像移到契丹发祥地木叶山,奉为“家神”,与族神“木叶山神”一同供祀。公元980年,“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兵神”者,应该就是我们论述的佩有金鱼兵符的北方天王像。契丹人崇拜东方,他们把东方佛称作“慈悲佛”,而把东方的阿閦佛改成东南方的佛(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他们还把列祖列宗像供奉于佛寺里。雄心勃勃的契丹民族不但在拓展着新领土,而且也在拓展着神灵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