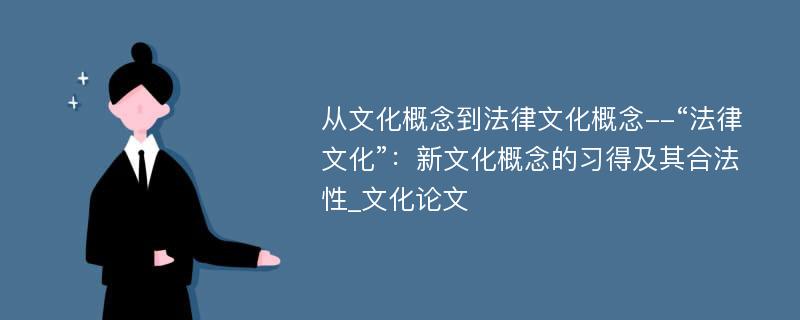
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文化论文,法律论文,新文化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概念进行分析。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E.霍贝尔教授在其代表作《原始人的法》一书中,对概念的重要性作了如下的一段说明:“一个探索者在任何领域中的工作总是从创造该领域中有用的语言和概念开始。‘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同一的’。开始工作时,人们总是企图把新思想装入原有的语言框架中。但当他扩大了知识领域或加深了某一观点时,他必然发现旧词的意义实际已经变更,或者新词已从新现象中被锤炼出来。而这些概念是同旧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新的事实和新的思想总是在召唤着新的词汇。实际上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师,他们总是以熟悉的措词以似乎更好的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假如这不影响事实及其意义的真实性的话。因此,在任何法律的研究中,理想的情况是法理学在尽可能的限度内同时创造词汇和概念。”〔1〕霍贝尔教授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概念是重要的。 概念如同语言一样,是思想表达不可缺少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曾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概念的性质作了如下的界定:“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2 〕毛泽东将“概念”看作是跨越了实践感性阶段的理性认识阶段,并且认为概念是进行进一步判断和推理以得出论理认识和结论的前提和基础。
当人们对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时,首先碰到的便是概念。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科学地认识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是科学地认识该事物的前提。一个概念包含着一定的内涵和外延,一定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实际上指明了它所包含的特定范畴和研究对象。因此,对概念的研究与对新问题的研究同等重要,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法律文化的概念是法律文化基本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入手,都离不开“法律文化”这一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虽然每个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都有其所指,即有其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自身理解,但分歧也是很大的。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所引起的一些学术分歧,从另一方面恰好说明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理论问题。
要研究法律文化的概念,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只有在了解了文化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对法律文化的概念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文化概念是法律文化概念的源头和基础;并且,在所有的法律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所出现的争议和歧义,始终是同对文化的了解相纠缠着,相联系着。因此,理解和认识文化的概念,是理解和认识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理论问题的钥匙。
一、文化概念的多义性
文化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这种多义性已被中外许多文化学研究者所认识。一位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一书中研究了文化概念的产生和起源,他指出:“关于文化概念的探讨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思想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和基本的关系。”〔3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位学者的研究认为,法学家穆萨埃尔·普芬道夫(1632—1694)关于文化概念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其主要理由是:法学家兼外交家普芬道夫是最早不带限定词使用文化这个词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确定了政治思想和文化概念的关系。”〔4 〕普芬道夫认为:“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上是同义词。”〔5 〕这位作者还援引了另外一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所阐发的观点,威廉斯认为,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有五个单词在英语中变成了常用词: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最能表达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其他一些基本词汇也都和文化概念的产生有关,如:自然法、宪法、自由、公民和人,等等。正是这些词汇标志着18世纪政治思想的演变〔6〕。 维克多·埃尔则进一步指出:“各国的百科全书告诉我们,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术语是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他的依据是《美利坚百科全书》,该书讲道:“文化作为专门术语,于19世纪中叶出现在人类学家的著述中。”〔7〕
另一位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研究文明史问题时,也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文化一词在1800年以前还很少见到”〔8〕。“文化和文明在法国几乎同时问世。 文化一词由来已久(西塞罗已经谈到‘精神文化’),只是到了18世纪中叶才真正具有知识的特殊含义。”〔9〕
1980年5月底至6月初,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了法国。访问期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的演说。这次演说被认为是“长期以来一直蛮横地反对与文化概念不可分割的思想运动”的“罗马教廷的演变”〔10〕。他讲道:“正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文化是人类‘生活’和‘生存’的一种特有方式。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特有的文化生活着;反过来,文化又在人类中间创造了一种同样是人类特有的联系,决定了人类生活的人际特点和社会特点。在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的统一性中,同时又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而人类就生活在这种多样性之中……,文化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础,它使人类更加完美或日趋完美。”〔11〕
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既表现在人类文化生活的实践中,也表现在文化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释中。有位中国学者指出:“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12〕而有位日本学者则认为:“文化的定义从来就众说纷纭,据说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260种。”〔13 〕不同的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化”有不同的解说。每个人从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出发,给文化概念赋予不同的内涵。我国文化学者司马云杰先生指出:“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认识它,自然应该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由于方法论的不科学、不统一,对文化概念所引起的纷争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学派常常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的遗产,或者传统的行为方式的全部丛结;心理学派则往往把文化视为主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总映象,或者是满足个人心理动机所选择的行为模式;结构功能主义者强调文化是由各种要素或文化特征构成的稳定体系;而发生论者则分辩说文化是社会互动及不同个人交互影响的产品;有的人偏重文化观念的作用,把文化定义为观念之流,或观念联结丛;有的人则倾向文化的社会规范的价值,把文化界定为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或者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如此等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文化定义。”〔14〕总之,林林总总的不计其数的文化概念可以说包含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难怪乎苏联政治学家尼·米·凯泽罗夫认为:“文化”是一个最一般的、包括一切的概念,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容量〔15〕。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讲道:“各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无限止地记述下去。”〔16〕她对这种多样性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仅是由于各个社会随意地精构细琢或竭力弃绝生存的各个潜在方面所造成的,而且更多地则是由于各种文化特质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缘故。”〔17〕在我看来,文化概念的多义性从表面上看来源于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广泛的包容性,而从实质上看,则源于人类生活的多样性。
二、几个“经典性”的文化概念
在文化理论研究中,有几个被称为是“经典性”的文化概念。当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在其1871年写的代表作《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共用。他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18〕文化学研究者将泰勒的这一定义看作是最早对文化进行界定的一个经典性定义,并且对其后文化概念的研究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由于泰勒的文化定义缺少“物质文化”的内容,后来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对泰勒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补充进了“实物”的文化现象。泰勒的定义是描述性的,但却第一次给文化一个整体性概念。后来的文化定义,都没有超出泰勒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基本观念〔19〕。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1905—1960)曾在《文化概念:一个重要概念的回顾》(载1951年第41期哈佛大学《小人物陈列馆论文集》)一文中,对161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认为这些概念基本上都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20〕克鲁克洪在《文化的研究》一文中讲到:“美国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一词,当然是一个术语,绝不能与普通语言以及历史和文学上比较有限的概念相混淆。这一人类学术语所确定的涵义,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21〕他对文化概念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也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22〕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克鲁克洪提出的“对文化作分析必然包括显露方面的分析也包括隐含方面的分析”〔23〕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研究法律文化的概念和结构,也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是一位文化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从“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角度来阐释文化概念。他说:“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24〕“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特性,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25〕他认为,一切文化要素,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因此,“功能”的概念是文化学的主要概念。“文化是指那一种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26〕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27〕。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各方面”(即文化的组成要素)分解为如下几点:
甲.物质设备,也即物质文化。他说,人的物质设备, 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在一切关于民族“优劣”的争执中,最后的断语就在武器,它是最后的一着。在一个博物院中的学者,或在一个喜讲“进步”的政客心目中,物质文化是最先被注意的。他认为,社会学中的唯物史观,想把人类进步的全部原动力、全部意义及全部价值,都归之于物质文化。他说这是一种“带着哲学外表的偏见”〔28〕。
乙.精神文化之方面。 他针对“物质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全部原动力”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一种带有“偏见”的学说指出,若我们稍加思索,就可以明了文化的物质设备本身并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对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工具亦要手工的技术来制造,制造就需要知识。在生产,经营及应用器物,工具,武器及其他人工的构造,都不能没有知识,而知识是关连于智力及道德上的训练,这训练正是宗教,法律,及伦理规则的最后源泉。因此,物质文化需要一相配部分,这部分是比较复杂,比较难于类别或分析,但是很明显的是不能缺少的。这部分是包括着种种知识,包括着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包括着社会组织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包括着我们可以总称作精神方面的文化。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个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
丙.语言。马林诺夫斯基不同意那种将语言视作是人类特具的机能以及认为语言是和人的物质设备及其他的风俗体系相分开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字词的应用是和人类一切动作相关连而为一切身体上的行为所不能缺少的配合物。说话是一种人体的习惯,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风俗的方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丁.社会组织。 马林诺夫斯基不同意一些社会学者常将社会组织放在文化之外以及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科学——社会学——的独立题材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所谓社会集团的组织却是物质设备及人体习惯的混合物,不能和它的物质或精神基础相分离的。社会组织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在任何人类社会中,社会生活是系于地域上的集居,好像市镇、乡村及邻舍。社会生活有它的地方性,有一定的界限,这界限联系着种种经济、政治及宗教性质的公私活动。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连于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则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人体习惯的一类,或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精神文化〔29〕。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文化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如下一句断语:“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他说,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一群人中,有它特有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织部分〔30〕。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研究法律制度的文化属性极具帮助意义。
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文化学家对文化的定义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梁潄溟先生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梁潄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梁潄溟把人类生活的样法分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文化的涵义是很广泛的。1920年蔡元培在湖南演讲《何谓文化?》,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并列举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事。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书中,谓“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在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中,文化包括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足见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胡适则于1926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化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文化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唯有陈独秀对这种宽泛的文化定义提出了反驳,他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曾批评道:“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到文化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所不包?”他力主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31〕。而社会学家司马云杰先生则给文化下了一个简要定义:“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他对这个定义作了如下四点解释:1.是人类创造的。2.是人类创造的特质。特质指二:一是指人类创造物的最小独立单位;二是指人类创造物的新的内容和独特形式。3.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4.不同形态的特质〔32〕。
三、归纳:三种文化观〔33〕以及法律文化研究应对文化概念的定位
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对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文化学家都不得不被迫放弃了对文化下定义的企图。文化概念简直像一座学术迷宫, 进去后却出不来。 80年代初,庞朴先生去问钱钟书先生,文化如何定义,钱钟书说,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34〕。8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讨论中,有的学者建议说,文化的概念就像“模糊逻辑”、“模糊数学”一样,它的界域本来是不可能确定的,只要确定它到底包含哪些范围,也就没有必要追求简单而确定的定义了。司马云杰先生也说到,文化的定义已如此之多,分歧如此之大,如果想回避矛盾,少惹是非,“最聪明的办法是列举文化的几条基本特征而不给它下定义”〔35〕。那位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对文化概念的发展历史和各种关于文化的概念进行比较之后甚至认为:“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36〕但是,这位学者也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在不企图用同一个概念概括所有一切(宗教、神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科学、工艺、技术等等)的情况下,尽量给它下个定义。
在我们给文化概念试图确定一个范围时,我们发现,各种关于文化概念的解释,包括一些经典性的解释,大都是用现象描述的方法,指出“文化是什么”,或者“文化包括什么”等等。这种描述方法在论述某一具体问题时可能是有效的和有用的。维克多·埃尔也指出,在早期,“文化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某些时代,它具体体现在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中。这些成就揭示了文化概念的某些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指导人们思考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37〕。但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概念来讲,任何一种现象描述法都可能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都可能挂一漏万,不能准确地反映它的内涵。因此,要给文化概念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我认为最好用哲学抽象法,即从众多现象中抽象出一种概括。
通过对各种文化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三种文化观:即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
(一)广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完整表述,见之于我国出版的《辞海》中。《辞海》讲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8〕用文化学术语来讲,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文化由三个重要因素组成:①符号、意义和价值观;②规范;③物质文化。”〔39〕这种文化观,也见之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定义之中(马氏认为文化分为器物和风俗,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和苏联〔40〕学者的文化定义之中。苏联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从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1956年出版的《现代俄语标准辞典》(多卷本)对文化概念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中、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总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956年出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称:“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有价值的珍品的总和。”到了1973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没有正面对文化概念下定义,而是对文化的解释作了两点说明:“1.文化的概念可用来说明一定的社会经济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水平的特征;2.狭义来讲,‘文化’这一术语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范畴。”在苏联学者中,尽管对什么是文化众说不一,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三大类型:一类是指人类活动的结果、成就。如苏联学者萨哈罗夫指出:“文化从广义上讲,就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总和……”;兹沃雷金称:“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与自然界所赋予的一切是不同的。”谢班斯基称:“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价值以及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等等。这类定义的共同点是强调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另一类则把文化定义为活动,如马尔卡良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手段,生存的手段。”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苏联一些学者的支持。第三类是兼具上述两类的特点,称之为“活动——结果”型或“结果——活动”型。如冈察列科说:“文化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是扩大和运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手段,是人类在建立相互的社会关系,以促进自身进步所取得的成就。”索科洛夫指出:“从现代意义上讲,应把文化理解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服务于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总和,是人的思维过程和状态及活动的企图的总和。”〔41〕当然,对上述一系列文化定义,苏联学者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二)中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完整表述也同样见之于我国出版的《辞海》中。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讲,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42〕这种中义文化观注重的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或曰精神文化,剔除了物质文化作为文化的构成成分和要素。而对精神文化的内涵又分解为两大块,即(1 )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2)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这一中义文化观,见之于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中(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泰勒的文化定义注重精神文化之内容),见之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的文化定义之中(克鲁克洪的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分类就表达了这一内涵),也见之于苏联一些学者把文化只看作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范畴的观点。
(三)狭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这一观点的最经典的表述者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在1940年2月15 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经典性的著作中,提出了“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完整表述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43〕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节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44〕“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45〕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一观点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以及列宁关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观点,并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46〕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文化观念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思想,以至于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47〕。当人们谈起“文化”这一概念时,很容易认为就是指的思想观念等与人的思维相关的东西。
以上三种文化观的归纳,从哲学抽象的层面上大体可以反映中外学者、思想家关于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这三种文化观,从文化发生学的原理看,都有其阐释的理由。如果我们先粗线条地把文化看作一种区别于自然界所赋予的一切事物的“人类的创造物”的话,广义文化观包容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和。从这一文化观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现代社会被人们所贬抑的“文化大泛滥”、“文化大爆炸”等难以理解的文化词汇和用语,诸如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建筑文化、雕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等林林总总的文化之称谓和现象,因为这些文化类型是以物质为载体,但其中又包含了人类精神文化之底蕴;中义文化观则将文化的焦点集中在人类精神之创造方面,突显了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将人类的思维和与这种思维相联系的制度、组织机构等浑然为一体,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人类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外化物——制度这样一种既非心态又非物态之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联系;而狭义文化观即观念形态文化观则将文化的中心放置于人类的思维层面,即同人类的大脑相关的事物上面,如知识、思想、价值、心理等等隐型文化形态之上,加深对人类内在理念及自我意识之认识。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三种文化观各有其自身不同于其他种类文化的对应物,也即不同的分类标准。广义文化观的对应物是自然界(或自然物),即凡那些不属于人类创造之事物,不属于文化,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之包容是极其广泛的,可以说它包容了除自然界以外的所有人类之创造物、行为、思想等等;中义文化观的核心概念是“精神文化”,它的对应物是广义文化观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即中义文化观不承认“物质文化”是文化,而只承认与人的精神相关之创造物及其表现形态(制度、组织等);狭义文化观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它与人类的大脑——即思想,意识相关连,它的对应物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精神文化,而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又具体化为社会经济、社会政治,而后者(社会政治)则又是前者(社会经济)的反映〔48〕。
针对上述三种文化观,我们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文化概念如何取舍,也即如何定位?任何一个研究者在使用和界定一个概念时,都是和他的研究对象分不开的。对于一个研究建筑文化的人来讲,他可能会认同广义文化观,因为他首先得面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建筑这一物质形态。建筑是一种物质形态,但在这种物质形态之中,却包含着人类从古至今无数精神之创造、智慧、经验、知识等等,如法国的卢佛宫、埃菲尔铁塔;中国的长城、故宫、天坛等等。我们现在研究的是被谓之为“法律文化”的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中义文化观将成为我们选取的文化定义。之所以选取中义文化观,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我们对中义文化观进行描述时,我们会发现,中义文化观所涵盖的文化内容同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9〕马克思将社会结构分为两大块,即经济基础(也叫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所有的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当代日本社会学家横山乔夫在研究文化概念时,涉及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以及与文化的关系。他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看成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即意味着进行生产的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基础,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世界观、法律、政治、宗教、艺术等理念形态就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理念性的文化都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50〕“意识形态(Ideologic)也译作观念形态。 ”〔51〕当代美国文化学家罗伯特·达密柯在《马克思与文化哲学》著作中也专门研究了马克思关于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讲道:“我们所获得的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应当用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这是合情合理的。”〔52〕“马克思把文化比喻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53〕,“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的意思以及这一比喻是如何包容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就必须先搞清楚劳动这个概念。”〔54〕把“文化”概念同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联系起来,绝不是一种牵强附会,而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联。理解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就必须从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入手。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指上层建筑,文化包括了上层建筑的全部领域。无论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艺术等上层建筑范畴的事物,都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
第二,中义文化观所涵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机构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然的、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他们两者都属于人类精神之产物,只不过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其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都同人类的大脑思维相关联,都属于人类精神、思维之派生物,只不过一则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一则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化物——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等形态。如果割断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仅从“观念形态”上把握和定义文化概念,那就等于割断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一个完整的体系分割为支离破碎的单元,无助于对人类精神现象之认识。
第三,我们研究的是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机构及其派生物(历史、行为、活动等等)。这样一个对于法律文化的认识,决定了我们选取中义文化观。因为法律文化的构成内容同中义文化观的构成内容相吻合。
四、文化能否有附加词——法律文化的概念能否成立?
当今,人们已经很习惯的在各种意义上大量的使用文化概念,并给文化概念加诸许多前置附加词或后缀附加词等“意群”。前置附加词如法律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技文化等等,后缀附加词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文化法规、文化宪章、文化活动等等,这已成为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惯用术语,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能够接受顺手拈来的概念。但是,在文化学的研究中和文化概念的演进中,这一问题并不是一番风顺的,至今仍引起一些学者的争议。
法国文化学家维克多·埃尔是反对将文化概念和任何专业化概念混为一谈的一位学者,他说:“文化不应该和任何专业化概念混为一谈,不管它被称为医学文化、文学文化、哲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所谓文化概念,就是按其本来面目对文化进行思考,而不加任何限定词。”〔55〕同时,埃尔也指出:“不加限定词,并不等于和其他方面无关,比如政治。”〔56〕埃尔还较详尽地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说,文化是一个时髦的术语,它在不断地产生新词,产生奇特的意群和乍一看令人难以理解的词组。这种简单词和复合词的大量增加,使本身已经十分复杂的语义范围无限扩展。埃尔指出:“它显然不单单是一种时髦的表现;各种迹象表明,它实际上表达了各种深刻的需要和忧虑。许多人甚至似乎把过去对政治问题的关心转向了所谓的文化现象。”〔57〕“这种词汇的大量增加所表达的愿望和需要的多样性,使‘什么是文化?’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此,只靠查词典是不够的。尽管词典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宝贵工具,但靠它来给纷纭复杂的人类现实下定义还远远不够。”〔58〕
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分析文化和文明的词语变化时也讲道:“所有的词在使用中都有变化,而且必定会发生变化。这既由于科学术语的需要,也由于文化的潜在进步,还因为所有人文科学都面临思想和方法的危机。”〔59〕“活词汇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每个人几乎都能随意去使用它。……就是眼下,这两个词(指文明和文化——作者)还在演变,原因十分简单:我们往往在模棱两可的名词后面加上含义比较明确的修饰词,例如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学文明,技术文明(文化亦然),甚至说到经济文明。”〔60〕
按照埃尔的观点,文化就是文化。文化虽然同许多事物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关,但不应给文化附加上任何限定词。当然,他同时也稍带妥协地承认给文化附加上许多限定词“显然不单单是一种时髦的表现”,“它实际上表达了各种深刻的需要和忧虑”。而布罗代尔则充分肯定了这样一种现象,认为给文化概念加上修饰词,可以使含义变得比较明确。
文化的研究如同任何问题的研究一样,都有一个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过程。文化概念的演进,反映了文化本身的演进,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现象的认识的深化。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将注意力放置于说明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以此为线索而逐步展开。于是,语言、艺术、文学、诗歌、绘画、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哲学、数学、道德等等都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人们感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和方法,需要寻求一些新的概念、术语、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即埃尔所说的一种“深刻的需要”。于是,各种各样的文化附加词便出现了。
新的带有附加词的文化概念的出现并不同原有的文化概念解释相矛盾,相冲突。譬如,在被视为“经典性”、“权威性”的泰勒的文化定义中,“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泰勒的定义中,强调了文化是一种“复合整体”,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复合整体”予以分解,那就成为文化中有知识、信仰、艺术,文化中有法律、道德、习惯等等,因为它们都是组成文化复合整体的单元、要素、分子。用现代系统论的说法,是“文化子系统”。这样一种分解并非毫无意义的,也并非破坏了文化的整体性原则。分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整体性。只有在对文化的组成单元有了更好地认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文化的整体。梁治平先生把这叫做“循环解释”。他说:“事实上,我们通常并不是一般地谈论文化及其特征,而更多地是讨论它的某些方面: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法律、建筑、医学、语言等,毫无疑问,离开这些具体有形的领域即无所谓文化,但在另一方面,除非我们对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所了解,文化的这些部分也都无从认识。这是因为,在每一文化内部,不同的部分和方面不但彼此关联和互相渗透,而且共享和体现着文化的一般精神。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层层叠架而又互相包容的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其真实意义只能在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得到说明。”〔61〕
于是,当我们说“文化包括法律”或“文化中有法律”时,我们等于说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概念, 这个新的概念是这样演化而来的:由(1)“文化包括法律”→(2)“文化中有法律”→(3)“文化中的法律”→(4)“法律是一种文化”→(5)“法律文化”。其实,各种各样的文化新概念的出现都是沿着这样一个过程而出现的,只不过不同的“子文化”概念出现的时间不同罢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子文化”是构成文化整体或整体文化的基本单元,是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相对于其他子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的出现,是稍晚时代的事情。据研究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此概念的出现,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在美国,这一概念最早始于1969年〔62〕,在苏联,最早始于1962年〔63〕,在日本,最早始于60年代〔64〕。而在中国,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行研究,最早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65〕。经过近10多年的研究,这一概念基本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获得了作为一新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地位。
五、小结
从文化概念的探讨到引出法律文化新概念的出现,其间笔者用了如此之多的笔墨来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其目的就是想详尽地分析文化概念的实质。因为只有了解了文化概念的实质,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法律文化的概念,才能给予“法律文化”这样一个新文化概念以一个“合法性”地位的说明,为这样一个新法学问题的全面展开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并且,在有关法律文化理论的研究中,对文化的理解始终成为一个影响研究结论和分析结果的重要因素。因为笔者深知,这样一个新文化概念并非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同,甚至一些“权威”的法学家至今并不认同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注释:
〔1〕 [美]E.霍贝尔著:《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毛泽东著:《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3〕 〔4〕〔5〕〔6〕〔7 〕[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9、17、18、 5页。
〔8〕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页。
〔10〕 转引自[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一书, 第9页。
〔11〕 转引自[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2〕 田汝康:《序》,第1页。 载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 [日]名和太郎著:《经济与文化》,高增杰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文化的定义到底有多少个,这是个谁也无法说清楚的数字。
〔14〕 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5〕 转引自井勤孙:《“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内容简介》,《政治学参考资料》1983年第2期,第51页。
〔16〕 〔17〕[美]本尼迪克特著:《文化模式》,孙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6页。
〔18〕 [英]泰勒:《文化之定义》,顾晓鸣译,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9〕 参见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0〕 〔21〕〔22〕〔23〕[美]克鲁克洪等著:《文化与个人》,高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注〔3〕、第4、6、 8页。
〔24〕 〔25〕〔26〕〔27〕〔28〕[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1、4页。
〔29〕 〔30〕[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8页。
〔31〕 〔32〕以上资料参见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11—13页。
〔33〕 〔34〕“三种文化观”不同于“三种文化”。前者是属于文化概念和文化观,后者属于文化的结构层次分类。如80年代我国历史学家庞朴先生把文化分为三大结构,即物质层,心物结合层,心理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临)第17号,第9、8页。
〔35〕 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6〕 〔37〕[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5页。
〔38〕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3页。
〔39〕 [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上),刘云德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40〕 本文采用“苏联”概念,而没有用“前苏联”概念,因为我认为“苏联”是一个特指特定时间内的国家形态。
〔41〕 以上资料参见鲍良骏:《苏联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转引自《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76—379页。
〔42〕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3页。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在《辞海》中,将此定义解释为文化的“狭义”定义。但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应是一种“中义”定义,还有一种比此内涵更狭义的文化定义,即笔者在后面将要论述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定义。
〔43〕 〔44〕〔45〕〔46〕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694、695、 664页。
〔47〕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思想观点,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
〔48〕 十五大报告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这等于说,同文化相对应的是经济、政治。而如果将文化理解为政治、经济的反映物,那么,作为经济之反映物——政治又如何理解?如果我们将政治、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那么,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存在?作为经济反映物的政治可以作为社会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属上层建筑),那么作为政治、经济之反映物的文化,又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政治、经济又指的是什么?因此,我认为,政治、经济、文化这样一个分类,是一种社会学上的社会结构分类,而不是一种文化学分类。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50〕 〔51〕[日]横山乔夫著:《社会学概论》,毛良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74、173页。
〔52〕 〔53〕〔54〕[美]罗伯特·达密柯著:《马克思与文化哲学》,顾晓鸣等译,转引自《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92—93、94、80页。
〔55〕 〔56〕〔57〕〔58〕[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5、1、3页。
〔59〕 〔6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0页。
〔61〕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页。
〔62〕 见[美]Susan Finder:《美国的法律文化观点》,《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第63页。
〔63〕 见[美]范思深:《苏联的法律文化观点》,《中外法学》1989年第2期,第63页。
〔64〕 见何勤华:《日本法律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外法学》1989年第5期,第53页。
〔65〕 见刘作翔著:《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