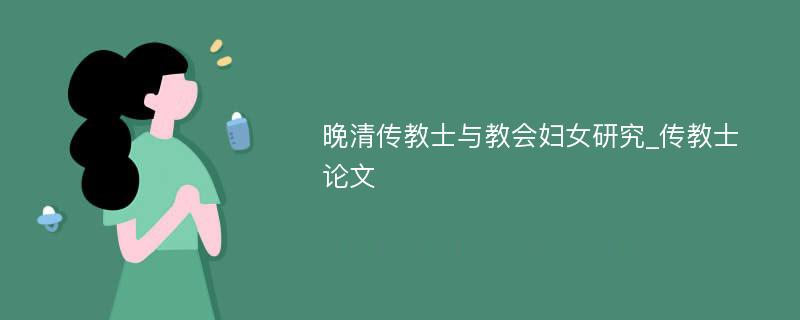
传教士与晚清教会女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传教士论文,教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处在一个新旧递嬗的历史时代。处于这一历史的大变局中,中国教会女学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之先声。
一、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844年至19世纪末,是教会女学兴办和初步发展时期,其主要特征是数量少,规模小,程度低(以小学为主);第二时期从20世纪初叶至50年代初期教会学校的撤离,这一时期教会女学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办学重心由初等教育转向中等和高等教育。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没有出现过女学,但却有过女教,女子足不出户,只是在家庭中接受业师的指导。女教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行为准则形成于汉代,西汉大儒刘向撰《列女传》,赞扬明贤、仁智、贞顺、节义的女性。东汉班昭的《女诫》,则是第一部由女子自己编撰的谈论妇道的书,影响深远,成为封建社会妇女的行为准则。
中国妇女接受近代教育始于教会学校的产生。早在1834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温施娣便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被认为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的女子学塾,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相继而起的教会女子学校有镇江宝盖山的镇江女塾,上海和天津的中西女塾,苏州的景海,南京的汇文,九江的儒励,汉阳的训女,长沙的福湘,福州的陶淑,广州的英光,北京的贝满等女子学校。至1877年,新教传教士在华共办各类女子学校120所,学生2084人,其中隶属于美国差会的有81所,学生1421人,均占学校和学生总数的68%左右[1](p.226)。
当时较著名的教会女校有: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格兰德女士(后与裨治文结婚)于1850年在上海设立的女塾,1861年改称裨治文学校;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女士于1851年在上海虹口设立的文纪女校;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于1854年创办的福州女书院;裨治文夫人1864年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学;美以美会女差会1871年在福州设立毓英女学等。
教会女学创办之初,招生工作十分困难。广州一所教会女学1850年开办时,一开始只有3名学生入学,后来不堪舆论的压力,开学不久,又有两名学生退学。同年在广州开设的另一所教会女学,开学那天,已经报名的女生一个都不敢来,后来总算动员来了几个,不久又全部退学了[2](p.557)。
教会女学初创之难,究其原因,第一是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相冲突有关。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紧紧地束缚着广大妇女,儒家的“三从四德”,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种种社会恶习,使广大妇女只能扮演男性附属物的角色。妇女除了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外,其他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被剥夺了。鸦片战争后,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国风气渐开,但女子教育仍然受到纲常之礼的限制。直到20世纪初,清廷在商讨开设女学问题时,仍然遇到了强大阻力。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女学问题上便仍持顽固立场,认定:“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因而,普通女子教育仍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理由是:“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3](pp.220~221)《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在评论当时女学的现状时愤怒地说:“历代以来,帝王圣贤创制兴学,独不为妇女立教育之科……务使女子不读一书,不明一理,蓄之如奴婢,玩之如花草,使数千载聪明灵秀之才束缚于蠢然七尺之下……”[4]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者的恐惧和戒备心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办学的,中国民众对其始终存在着一种恐惧和戒备心理。而且当时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华夷之辩,新学之风未开,送子弟入“夷馆”求学在当时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学生来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吸引学生就学,这些教会女校在初建时,不但不收学费,并且供给学生衣食起居各项用费;有时候,学生的家属还可以得到5文10文一天的津贴,以弥补女儿不在家助理家务所受到的损失。因此,许多人只是由于贫困才迫不得已上教会学校,一有机会就退学,所招收学生质量也不高,据说是“不堪造就者十之九,其效用于教会者一人耳”。美国传教士保灵夫人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她在福州创办女学时的艰难情况:
在这里的第一年,我渴望办所女学。国内主日学校答应每年资助我70美元,于是,我着手寻找学生。人人都对我说:想办女学,不可能成功,已有人试过,但失败了。我不甘心。我不能到街上挨门逐户去问,保灵先生在一个当地教习的帮助下,为我这么做了。结果,无人愿意送女入学。在当地人看来,男孩上学还可以,至于女孩,教她们何用?保灵先生颇感失望,因为他连一个学生也没找到。在此情况下,我叫一个我拟聘用的当地教习,到其住处附近寻些学生。他花了两三天时间,去劝说其熟悉的人送女入学,结果,还是竹篮打水……后来,这位当地教习问我是否愿意每天给她们一些铜钱,因为这些女孩在家都是做些事的。我答应每天给她们十文钱。我购置了图书、钢笔、墨水等物。在国内,我们都很乐于为读书付费,在这里,恰好相反,教书付费。[5](pp.295~296)
经艰苦创业,教会女学终于相继度过难关,并逐渐得到发展。1877年第一届全国新教传教士大会后,传教士逐渐改变了低层次的办学模式,教会女校的办学规模日渐扩大,一批教会女子中学相继出现。1881年,圣公会将上海文纪、裨治文两女塾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1892年,林乐知在上海创设中西女塾,1895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学扩大为贝满女中。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兴女学被维新派提到“强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警示国人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6]1897年6月,梁启超、汪康年、康广仁等率先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其他维新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如广东、苏州、湖南等地私立女学也纷纷兴起,成为一时的潮流。
二、教会女学的特点
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校的办学模式而言,教会女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重视教学对象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于“德”,教育目标是忠、孝、节、义、仁、和,教学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至于女子,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如何侍奉父母、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如何恪守妇道,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死从子等。清朝在这方面集历代女教之大成。成书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的《女学》是清朝最早出的一本女教书,分列妇德、妇官、妇容、妇功四篇,该书特别强调“妇以德为主,故述妇德独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考察中国女子教育后颇有感触,称中国女子的“三从四德”可以用一个“顺”字来概括,她们不得不逆来顺受地忍受男性的暴虐和折磨,而且要“谄媚其夫,谄媚其夫之父母,谄媚其夫之兄弟,无往而不谄媚焉”[7](p.33)。而教会女学堂则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学堂在进行宗教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还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和才艺。许多学堂都开设了体育课和美育课,例如,镇江女塾为12年一贯制,而在每个年级的教学计划中都有体操和诗歌课程。除课程设置外,许多教会女学还会因地制宜,开展球类、田径和文娱等各项文体活动,并且举办各类辩论会、交际会、音乐会和白话剧,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艺术修养。
二是中西兼顾,在重视西学的同时,兼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的顽强挑战。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时,利玛窦曾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因此引发了天主教内部不同派别的争执,最终导致了“礼仪之争”和康熙禁教。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入华后,马礼逊、理雅各、李提摩太、林乐知等新教传教士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承袭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口号,在传教时注意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衔接与融合。因此,传教士在华创办女学,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注意了教俗兼顾,中西并重。在课程设置时,既有宗教和西方近代科学的课程,如圣经、植物、英文、数学、地理志、动物浅说、孩童卫生、万国通鉴、天方略解、格物入门等;又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如三字经、百家姓、诗经、四书摘要、左传摘要、背讲古文等[8](p.298)。
三是加重了妇德和妇女职业的训练,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
许多教会女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主要培养知书达理,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贤妻良母”型人才[9](p.87)。如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后改称圣玛利亚女书院),其课程设置主要有:
初级课程(相当于小学程度):初等女国文、初等女修身、圣教、初等描红格、初等习字帖(印格)、启悟初津、笔算加减法。备级课程(相当于初中程度):高等中学历史、高等女国文、高等女修身、蒙学论说、基督本记、短信、短论、记事文、譬喻类纂、地理志略。正级课程(相当高中程度):女子伦理学、近时名家论说、读经、地理初桄、临帖(大字、小楷)、论说(作说理文)等。
除上述课程外,该校还开设纺织、园艺、缝纫和烹调等家政训练课程,以培养学生操持家务的能力[10](pp.221~223)。
三、教会女子大学的建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教会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的办学层次已经不能适应教会女学日益发展的需要。1905年5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要在中国建立4所女子大学:华北、华中、华西、华南各建一所。但后来只建了3所。
1905年宣布成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该校前身是北京贝满女中,1905年开始添设大学课程,并招收大学生5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除了设置4年的本科课程外,还有两年制的专科课程,自建校至1919年并入燕京大学,共毕业本科生22人、专科生27人[11]。华南女子大学于1907年5月在福州正式成立,这是外国教会在我国南方创办最早的一所女子大学。该校创办伊始,只设有预科班,经过数年的努力,才于1914年开设了两年制的大专课程。第三所教会女子大学是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该校得到了美国五个差会的资助,经费较充足,一开始便开设了4年的本科课程,招收具有高级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到1925年,入学的人数达到137名,超过了任何其他教会大学。
20世纪初叶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中国社会风气日开的产物,也是19世纪后半期教会女子学校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社会风气而言,洋务运动后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女子跨出闺门,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一批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谈论女子教育的重要性。20世纪初,清政府对女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06年2月,慈禧太后谕令振兴女学,翌年3月,《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11](p.150),中国官办女学的闸门终于被打开了。中国朝野对女学态度的转变,使嗅觉敏锐的传教士立即感到在中国创办女子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1911年,美以美会在华教育秘书盖蒙韦尔洛撰文指出:“近年来在中国的急速变化,需要受过高级训练的妇女来担任教育工作的要求日益迫切,天意授予我们去促进已在福州实施的一所女子大学的计划。”[12]
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建立,还得益于20世纪初叶来华女教士结构的变化。
在早期,来华女教士多为中小学文化程度,亦非专门办学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大学相继取消了对女子的限制,女大学生毕业人数日渐增多,1900年美国女大学毕业生达到了5237人[13](p.179)。当时,赴海外传教对女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因为女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的出路主要是做小学教师,不仅薪俸微薄,而且升迁渺茫。而赴海外传教,犹如拓荒探险,颇有挑战性,亦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因此,一大批美国女大学毕业生踏上了东方传教之路。在这批赴华传教的女大学生中,有不少是女权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男女平等观念,当她们看到男子教会大学在中国相继建立时,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使命感促使她们要在中国创办女子大学。一些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教士教育家还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大声疾呼:“人们给我们女孩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中等教育,那一定也要给女孩子中等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学教育,那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14]显然,来华女教士结构的变化和强烈的男女平等观念,为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作了人员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初叶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也是19世纪下半期教会女子中、小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初期中国3所教会女子大学来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由贝满中学发展而来的;华南女子学院是由福州毓英女子学校发展而来的,只有金陵女子大学是一开始就作为大学来创办的。可见,教会女子小学和中学的发展,为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教会女子中小学的发展,也在呼唤着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金陵女子大学创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江浙一带各教会女子中学日益发展,女中毕业生在国内升学无门;再则,随着教会女子中学的发展,女中师资的培养也日显迫切。据统计,20年代初期仅江苏一省就有美国教会女校22所,入学学生达到2068人,[15](p.574),但却无法找到大学毕业的中国女教师。因此,中国女子大学正是适应教会女学的发展而建立的,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
